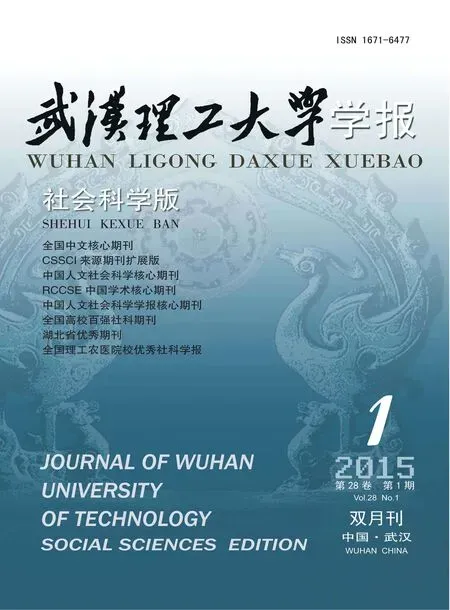“反概念”:禪與后現代主義哲學的異質同構性
摘要:中國古代的禪宗哲學和20世紀西方后現代主義哲學極大地沖擊了傳統的理性哲學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大膽挑戰理性的形式邏輯規則,并以反邏輯的話語形式顛覆了傳統的邏輯規則。這兩種異質的哲學都質疑理性邏輯概念的唯一性和合法性,都反對理性哲學為了堅持概念的普遍性而扼殺語詞的個性化生命的舉措,都采用了超越語言邏輯規范的話語策略來反對理性主義邏輯的霸權等,因而,它們在反邏輯、反概念方面表現出鮮明的同構性。
關鍵詞:禪;后現代主義哲學;反概念;反霸權話語;反邏輯
中圖分類號:B8302 文獻標識碼:A
概念是西方傳統理性主義哲學最基本的元素,是建構理性哲學體系最重要的構件,因此,在理性主義哲學家的眼中,概念的地位非常重要,堅不可摧!西方哲學家們認為,“理性就是思維”,“理性等于概念”。黑格爾曾說:“思維的產物一般地就是思想;但思想是形式的,思想更進一步加以規定就成為概念,而理念就是思想的全體。”[1]“哲學是概念性的認識……概念才是一切生命的原則,因而同時也是完全具體的東西。”[2]在西方哲學中有一種“樹喻”理論,該理論認為,哲學的思維結構就像一棵大樹:樹葉、樹枝、樹干最后都歸總于樹根,而樹根的根須廣布四方并深深地扎于地下,這龐大的根系就是龐大的概念系統。沒有這個龐大的概念根系,西方一元化的理性哲學就喪失了其存在的基礎。不僅理性主義哲學家崇尚概念,甚至著名的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德勒茲也說:“人人都知道哲學與概念打交道……但概念絕非唾手可得,它們并不會預先存在:你得創造,創造概念,這其中所包含的創造絲毫不亞于你在藝術之中所見到的創造與發明”[3]4。這充分說明了概念在西方哲學中的重要地位。
20世紀在歐洲崛起的非理性主義文化思潮是一場涉及到人類哲學思維方式的革命性的思潮。從哲學認識論來看,它極大地沖擊了傳統的理性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否定了理性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大膽挑戰理性的形式邏輯規則,并以反邏輯的話語形式顛覆傳統的邏輯規則。正因為如此,非理性主義者們才集中火力猛烈攻擊理性哲學概念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并力圖用非概念的語詞來取代概念,以完成后現代主義思潮“非理性”化的哲學革命。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在人類思想史上,中國禪宗是率先反思理性的缺陷與局限性的哲學流派。禪宗高舉“不立文字”的非理性大旗,并站在哲學思維的高度上自覺地采用非理性的處事策略。可以說,禪宗思想是中國古代詩性的、非理性的那一支思想文脈滋養出來的奇葩,是中國非理性文化觀念和詩性智慧的代表。
相比較而言,中國禪宗思想同西方非理性思潮都具有鮮明的反對“唯理主義”的特點,但兩者的反理性主義卻是異質同構的。兩者的異質性表現為:中國禪宗的反理性主義思想是來源于本民族精神文化傳統,尤其是對道家思想的繼承、升華和張揚。一方面,禪宗是站在中國傳統的整體性思維的立場上,在主張無撿擇、無取舍、無是非的“中道”態度上來反對理性主義的單方面的霸權的;另一方面,禪宗又繼承了大乘佛教的“空”論和“中道”思想。例如,中國晉代的僧肇在《不真空論》等哲學著作中所闡述的“非有非無、亦有亦無、有無統一、不落兩邊、不偏不倚”的佛教“中道”的世界觀,是禪宗“中道”思想的直接來源。由于禪宗堅持“中道”——無撿擇、無取舍、無是非的處事態度,所以禪宗對理性哲學思想的態度就是:批判它,卻不否定和拋棄它。中國禪宗是以“中道”的態度來對待理性主義哲學思想的。因此,絕沒有西方的非理性主義者們,例如德里達、德勒茲那樣的過激和偏激。而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則是站在非理性主義的立場來反對西方文化傳統,尤其是對傳統的理性主義哲學的反抗、否定、顛覆與砸碎。兩者的差別是明顯的。
兩者的同構性在于:禪與后現代主義思潮都反對理性主義,雖然在反理性主義方面兩者動機不同,目的不同,但是,兩者所瞄準的靶心都是理性主義的思維方式以及其制定的原則、規范,例如,在反對理性主義的形而上學思想體系上,在反對理性的二元對立的原則上,在反對理性主義的語言中心論和邏輯概念上,在提倡直覺認知方式以及對真理的把握方式上,它們的方法與策略卻非常相似,可以說在反對理性主義思維方式和哲學思想上,禪與后現代主義思潮是殊途而同歸,兩者的思想觀念和運作策略都表現出很多的“家族相似”的同構性。
一、質疑理性邏輯概念的唯一性和合法性
禪宗和后現代主義者批判理性主義“霸權話語”的基本策略都是首先質疑理性主義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其次,是從根子上挖斷理性主義的命脈——理性形而上學哲學和邏各斯中心主義概念的合法性。
現實生活本身并沒有什么邏輯,鮮活的世界是自然而然地生成和存在著,它看起來可能是雜亂無序的,未必符合理性邏輯的規律和秩序。邏輯是人類思維創造出來的精神成果,是人類智慧對生活現象加以編織的結果。理性主義常常教導我們,怎么樣才是合理的,怎么樣才是符合規律和原則的。如果原生態的大自然與人的思維方式不符合這些人為制定的規則,就是不合理的,就應該受到貶斥、打壓,就要被“糾正”到理性的邏輯軌道上來。“一切都要經過理性的審判臺”(恩格斯語),只有經過理性審查或應允的東西才是合理的存在:合乎理性、合乎邏輯的就是真理,不符合理性和邏輯的就是謬誤。這就是理性主義權威性的體現,也是理性主義“權力話語”專橫之所在。對于理性主義這種天賦的霸權,20世紀西方非理性主義者群起而攻之。海德格爾曾尖銳地質問:“什么是理性?理性之為理性,是在什么地方,通過誰人決定的?理性已經自稱哲學之王了嗎?”[4]羅蘭·巴特指出:“語言既非反革命的,也不是進步的,因為它原本就是法西斯的。”[5]79羅蘭·巴特指出了一個重要的文化事實:“任何語言具有人們無法抗拒的強制性力量,不管面對著語言的人是誰,不管這個人有沒有權力或地位,都必須接受語言存在的事實,同時必須承受由語言存在所造成的一切客觀力量,并接力其控制。”[5]79
法國哲學家德勒茲和加塔利指出了西方傳統語言通過“同質化”和“政治化”,不僅成為“霸權話語”,而且成為了不可動搖的鐵的規范:“將語言作為一種研究對象的那種科學模式與一種政治的模式聯為一體,而正是通過后者,語言自身被同質化、中心化、標準化,形成一種強勢的、支配性的語言,一種權力的語言。……對于一個正常的個體來說,形成語法上正確的句子,這就是服從社會法則的先決條件。誰也不可以無視合語法性,而那些無視它的人則歸屬于特殊的體制。”[3]137著名的解構主義理論家德里達對理性邏輯概念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德里達發現,要徹底顛覆西方傳統形而上學和傳統文化的基本原則,就必須摧毀傳統形而上學的二元對立模式;要徹底批判和顛覆形而上學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則首先要“解構”西方傳統的語音中心主義和邏各斯中心主義。德里達揭示了傳統的語音中心主義的基本特點在于:
首先,語音中心主義把語音所標示的思想觀念當作語言的“意義”,而“意義”則又直接等同于客觀的對象或客觀的事物。其實,語音符號并不直接傳達某種“意義”或者說僅限于傳達某種“意義”,這種人為規定的“意義”更不意味著代表客體事物本身,更不代表它的本質和真理。語言、語音它只是一種指向,“能指”與“所指”之間總是存在著差異,就像我們用手指月亮,“手指”只是必要的中介和符號,它可以指示月亮卻并不是月亮本身。西方傳統的語音中心主義不僅把符號與意義看作是“同一”,并把這種“同一”建構成了“語言符號/意義”的二元對立統一結構,而且無視語音符號與客體事實的差異,把它們直接變成了“同一”。語音主義的重要地位的確立,也意味著排斥其他非語音的語言文字符號。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表述了這樣的思想:“符號的任意性,能指和所指的聯系是任意的,符號是能指和所指相聯結所產生的整體,簡單地說,語言符號是任意性的。一個社會所接受的任何表達手段,原則是都是以集體習慣,或同樣可以說以約定俗成為原則。”[6]索緒爾強調了詞并不指向實在的對象本身,詞義是由符號之間的排列或者形狀的差異所決定的。
其次,傳統的西方語言文化認為,語言通過系統性的符號結構和表達上的邏輯性可以精確地表達意義。這是對語言符號的統一性和邏輯性的迷信。事實上,任何現象之間都是差異性的存在,并且,任何語詞同它所表達的意義之間總是存在著距離和差異的。中國古代的文論家早就指出過語言、語詞同意義之間始終存在著差異,這就是所謂的“言不盡意”、“辭不逮意”、“言有盡而意無窮”、“言有盡而意有余”的道理。
對于理性邏輯概念這種本質性缺陷和局限,德里達采取的策略是:首先,不再使用概念,而用“非概念”(nonconcepts)取代概念。“他試圖用一種沒有中心(Decentre,去中心)的非邏輯概念的手段和形式,用非傳統語言的符號和意義的解構過程,在傳統文化所建立和占據的‘中心’之外,在沒有邊界、不斷產生區分、不斷‘擴散’和‘散播’(dissemination)的‘邊緣’(marge)地區,重建一種新的人類文化,以便實現在不受‘中心’管制的邊緣無限地區的自由創作。”[7]303304總之,德里達的“非概念”就是強調內容的“極端的含糊性”、多義性、意義漂移性或者說是“詩性”,就像康德美學所說的“沒有概念的普遍性”一樣,康德認為,“美”既非概念,卻又具有“普遍性”——人人都認可并贊同。其次,德里達主張使用“新的表達差異的概念”,即“延異”(difference,“產生差異的差異”)。“延異”概念不同于以往概念的特點在于:要顯現出內容意義之間的不同;并且“還要在這種‘不同’之中隱含的某種延緩和耽擱的意思。”這意味著概念之中“包含著當場顯示和未來在不同時空中可能顯示的各種特征和功能。”[5]274這種差異蘊涵著不斷自我變異和不斷自我增殖的過程。德里達理想中的“延異”概念很類似于中國哲學、美學范疇的自我生發、自我繁衍和自我變異的功能。
最后,德里達企圖尋找一種“非語言文字”的表情達意的符號或方法,借此解構和替代傳統的概念。其實,19世紀中葉以來,就有過一些現代主義的詩人和藝術家想跳出傳統語言的樊籬,他們試圖擯棄西方傳統的語言文字,改用自然的或者想象的圖形、圖像符號來傳情達意。這些現代派藝術家追求創建一種“非語言文字”的“語言”,表現了對西方語言傳統的逆反和背離。德里達曾經多次嘗試過尋求多種非文字的圖形語言。
著名的法國哲學家德勒茲采取了另一種“反概念”的策略,就是獨創一系列的“新”概念來取代傳統的“精確”的概念。例如:解域、結域;平滑空間、層化空間;根莖;游牧空間;游牧民;逃逸線;共變;平滑;紋理;千高原……這些概念同傳統哲學概念相比較,在內涵上更豐富,“所指”更多樣化,顯示出某種程度的模糊性、不確定性;概念的樣態更具有形象性和詩性。
相比較而言,中國禪宗在“反概念”上態度堅決,做法徹底,持續了上千年之久。禪宗不承認理性邏輯概念的權威性和有效性。鈴木大拙指出:“禪宗排斥一切由概念構成的東西。”[8]12同樣,著名的美國學者候世達也指出:“禪宗的觀點認為詞語與真理是不相容的,或至少是詞語不能捕捉到真理。因為,語言很容易把全部意義歸結于詞語,而不是真實的對象、事物與世界的聯結。”[9]323“詞語把我們引向某種真理。——或許,同樣也引向某些虛假——但肯定不能引向所有真理。你若是依賴詞語走向真理,那就如同依賴一個不完全的形式系統走向真理。……無論一個形式系統多么強有力,都不可能給出所有真理。數學家的困窘就在于:除了形式系統還有什么可依靠?而禪宗信徒的困窘則是:除了詞語,還有什么可依靠?無門禪師把這一困境闡述得很清楚:‘不得有語,不得無語’。”[9]330
禪宗的“反概念”的策略非常奇特。
首先,它以反常的反概念的方式提問。例如,人們說:“炭是黑的。”但禪說:“炭不是黑的,至少可以不是黑的。”人們說:“花紅柳綠。”但禪說:“花可以不是紅的,柳也可以不是綠的。”因為,這些概念所表達的事物的性質都是人們賦予事物的,是人們對這個事物定下的名稱和規矩,并不是事物自身原有的本性。既然事物的名稱、概念是人為的規定,為什么不可以用另外的詞語來替代、來表達呢?理性有什么資格來規定這一切并且強迫別人接受呢?德勒茲指出:“規定可以是偶然的,至少它只能通過一種原因、一種目的或機緣維持其存在,所以它包含著一種固有的外在性。”[7]513禪宗偏偏要突破理性概念的規定性,偏偏要用另外的思想觀念的內涵來取代某一個概念原本的意義。對此,我們試舉幾則禪宗的公案①來說明。
有一個禪師指著炭火問弟子:“我把它叫做火,你不如此叫,該如何叫?”同樣,首山省念禪師拈起竹篾問弟子:“喚作竹篾則觸,不喚作竹篾則背,喚作甚么?”這時一個弟子站起來奪過竹篾折成兩截,說:“是甚么?”這兩則公案要表達的是什么意思呢?爐中燃燒的炭火通常都叫做火,竹篾這一名詞規定了竹篾這一事物,這是邏輯概念所規定的名稱,因而具有普遍性、共識性和權威性。禪師啟發弟子,如果要超越或打破傳統邏輯概念所規定的內涵,你用什么名詞(話語)稱呼它?首山省念禪師的弟子為了跳出概念的桎梏,重獲思想上的自由,就把竹篾折成兩截,竹篾不復存在了,任何命名都沒有了意義。禪師們的意思在于說明:真實的事物與它的“假名”是兩碼事,符號不能替代真實的存在。“摒棄感知,摒棄邏輯、詞語、二元化的思維——這就是禪宗的實質,主義的實質。這即是‘無’方式——非智能、非機械,就是‘無’。趙州處于無方式中,而這就是為什么他的‘無’廢問了那個問題。”[9]332禪宗認為,只有不問這種問題才能知道問題的答案。只有不以這種抽象思維的、邏輯的、哲學的方式提問,才能了悟真理的答案。禪家啟發我們,為什么人們要把理性的規定看成唯一的真理呢?為什么人們沒有想到從新的、非理性的“第三只眼”的視角看一看事物又是什么樣的面目呢?
其次,禪宗故意用不合邏輯的方式把意義對立或相反的語詞強行捏揉、拼湊在一起,以荒誕怪異的話語來顛覆傳統的理性概念和語詞邏輯。例如,在禪師們所說的偈語或創作出了的詩歌中,常有令人驚愕不已的詩句:
“三冬華木秀,九夏雪霜飛。”
“大洋海底紅塵起,須彌山頂水橫流。”
“胎中童子眉如雪。”
“烏鴉似雪,孤雁成群。”
“冰河焰起,枯木花芳。”
“石上栽花,空中掛劍。”
“千歲老兒顏如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昨夜三更月正午。”
為什么禪師們故意用這些矛盾的語詞來表達呢?其實,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改變對立的雙方“非此即彼”的沖突狀態,使之成為一體,達到“非此非彼”、“即此即彼”、“無此無彼”的結果。這就是為了要去掉人們頭腦中的“分別心”和執著之心。對此,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指出:“現實生活本身并無什么邏輯,因為生活先于邏輯的。我們認為邏輯影響生活,實際上,人并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是個理性動物。”[10]自然的時序不是邏輯,邏輯是人類用抽象思維編織的結果。鈴木大拙指出:“我們通常總是絕對化地思考‘A是A’,卻不大去思考‘A是非A’或‘A是B’這樣的命題。我們沒有能夠突破這種知性的各種局限,因為它們已經非常強烈地控制了我們的大腦。然而,在這方面禪宗卻宣稱,語言是語言,它只不過是語言。在語言與事實并不對應的時候,就是拋開語言而回歸到事實的時候。邏輯具有實際的價值,應當最大限度地活用它,但是當它已經失去了效用或越出了它應有的界限的時候,就必須毫不猶豫地喝令它‘止步’!”[8]36禪充分運用上述看似矛盾的話語,來樹立一個新的觀察事物的角度,把語言從邏輯的專制與日常語法的片面性的習慣中解脫出來,開辟出另外一片語言的新天地。禪的智慧“使我們領悟了‘A即非A’,知道了邏輯的片面性。所謂‘非邏輯性’,細究起來未必就沒有‘邏輯’,看上去不合常理的東西竟然也有那對應其實相存在的獨特邏輯。……我們開始明白,‘A是A’這一命題的意味包含了‘A是非A’的意味,所謂自身,又不是自身——這是禪宗的邏輯。”[8]36
二、揭露理性哲學為了堅持概念的普遍性而扼殺語詞的個性化生命
傳統的理性主義和形而上學都是通過歸納和論證概念內涵的“同一性”來建構其邏輯體系的。黑格爾在《邏輯學》中說過,語言實質上只表達普遍的東西。“同一性”就是同類事物的共同的或普遍的性質。人們為了追求普遍性或者說“同一性”就采取“去粗取精”、“去蕪存真”的抽象手法,把理性概念中原本包含的現象、事實等特殊性因素都過濾掉、清除掉,只突出共性、普遍性的因素。例如,“桌子”概念就一網打盡了天下各式各樣的、各種大小的、各種材料的桌子。桌子的普遍性、同一性的確是抽象出來了,但是,桌子的具體性特征、個性化的形態卻沒有了。這樣的“桌子”的概念只是共性和普遍性的空殼,沒有了桌子的生命。因此,非理性主義者指責理性主義哲學把鮮活的、生動的事物擠壓并濃縮為干癟的普遍性的概念,以此來質疑邏輯概念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黑格爾是較早發現理性邏輯概念具有這一重大缺陷和局限性的哲學家。他在《邏輯學》一書中企圖嘗試用他創立的、包含有“單一、特殊、普遍”三個環節的“具體概念”(辯證邏輯的“理念”)來改善傳統概念的純粹抽象的品格。但是,由于黑格爾的《邏輯學》精致的邏輯結構和更加系統化了的邏各斯中心主義,把他的創新性見解給遮蔽了,憋死了。
生命哲學家柏格森指出,傳統的哲學家全都犯了“一種根本性的錯誤,認定任何一種認識都必須從一些有固有界限的概念出發,才能用這些概念去把握流動的實在。”[11]147柏格森指出了理性主義哲學把概念當作真實的實在這一弊病。按照柏格森的意見,理性概念、邏輯的構架只適用于僵死的無生命物質。對于有生命的東西用邏輯的、靜態的、幾何學的方法去進行處理,必然“把它所有的一切本質的東西統統剔除干凈。”針對傳統哲學和實證主義對概念分析的癡迷,柏格森指出,分析所面向的往往是不動的東西,它以抽象概念為工具,而概念雖然作為滿足于我們生活的實用目的的工具是有用的,但想通過它們達到事物最內在的本質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最大的功能是抽象和濃縮,“只能變個別為一般,變雜多為單一,變全體為部分。一句話,把川流不息的、活生生的實在肢解成一毫無生氣的碎片。……它要求認識主體要置身于對象之內,與對象合一,從里面體驗而不是僅僅進行外在的觀察,這就要求摒除一切概念。”[11]134同樣,阿爾多諾強調他的“否定的辯證法”的根本作用就在于消除對于一切概念的崇拜。在阿爾多諾看來,傳統的、“古老形式的”概念有兩個缺陷:一是只體現普遍,從而不能與作為特殊的對象同一,即不能夠與具體的事物同一;二是不能把握運動。法國學者J·祁雅禮指出:“我們的內在生活既非常豐富又多種多樣,尤其很難用那種會使它變成抽象名詞因而使之喪失本質,就像玻璃罩下的死蝴蝶一樣的概念來把握。”[12]美國耶魯學派的學者莫瑞雷·克里格認為,文學創作中的思想情感本身具有強烈的生命力,但是,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思想一旦變成語言文字,就以符號/意義的二元對立形式存在,從而也就將其中的鮮活的感情和生命加以固定化和僵化,變成了語言符號化的“思想骷髏”。
非理性主義者都指明了理性主義哲學的“邏各斯中心論”致命的弊病在于,概念把鮮活的思想和生命加以擠干、濃縮、抽象,制作成為干癟的普遍性符號和標志[13]。面對傳統理性哲學形而上學的原則和規范,后現代主義采用各種各樣異于傳統表達的特殊方式:或發明創造新概念、新詞匯,或采取形象性的象征、比喻的手法,或采取多種詮釋、修辭和批判的方式,來摧毀傳統概念的所謂“清晰性”、“準確性”、“系統性”、“穩定性”,并采用非體系化的象征性符號及生糙的語詞來表達含糊不清的、不可捉摸、流動漂移的思想。從而形成一種特殊的“反傳統語言”、“反語音中心”、“反概念”的語言革命。
“隔山唱歌山答應,隔水唱歌水回聲”。中國禪宗或許是人類最早質疑理性邏輯概念的合理性并主動擯棄理性概念的哲學流派。
有一個鐵定的事實是:在個體的思想和情感體驗中,有很多東西是無法表達出來的。盡管很難表達,但又不得不表達。這種“不可言說”,而又必須“言說”的訴求,就形成了人類多種不同的表達方式。禪宗獨辟蹊徑,采取“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的方式傳情達意是有著深厚的傳統依據的。古代印度人和中國人往往采用多種非語言的傳達方式,來表達情感體驗和思想。例如,大量的形體語、肢體語、手勢語、眼神語、表情語、圖形符號、音調、鼓點等。這些表情達意的方式既可以達到交流溝通的目的,又憑空增添了神秘性和敬畏感,也達到了對有聲語言的排斥和回避。“不立文字”就是用象征、比喻、暗示的方法來表情達意。它不用干癟的說教為手段,不用抽象的概念為媒介。因此,慧能說:“諸佛妙理,非關文字。”所以,禪者之間的對話,是大量利用隱語、暗語、形體語、手勢語、眼神語和各種圖形符號來表達心中的想法和體驗。這就是“繞路說禪”。禪家相互之間所謂的“參禪”,采取的手段就是“繞路說禪”,也就是用彎彎繞的方式來表情達意。正是這種表達方式,使禪僧之間的對話顯得撲朔迷離、神奇無比,處處有玄機,句句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以“不立文字”這種奇特的方法來傳授禪法,就叫做“教外別傳”②。這就是禪宗的獨門絕活,這也是禪宗最根本的特點。
禪宗的“教外別傳”、“不立文字”揭示了一個語言學的重要秘密,這就是:人類表情達意的方式有多種多樣,我們通常所使用的有聲的、概念性的語言文字,其表達范圍極其有限。20世紀英國哲學家波蘭尼說:“我們能夠知道的比我們能說出來的東西多。”[14]禪宗的“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走的就是采用“非概念性”的語言“繞路說禪”的路子。這就是禪宗的創造性之一。
禪宗的公案絕不采取對概念進行抽象的分析和論證,也沒有對命題進行嚴密的推理和演繹。禪宗的公案“很樸素,因為它們既沒有概念的證明,也沒有知性的分析。”[15]89“禪宗的真理與魅力,正在于它的單純性、直接性和極度的實際性。”[8]68“禪是非常務實的。它和抽象思考或復雜的辯證法沒有任何交涉。……禪在解開最艱深的哲學問題時,竟是如此的淋漓暢快、充滿生命。”[15]54禪師們喜歡用日常生活中的瑣屑事情來借機啟示弟子的思想,指出新的思維方向。我們在此試舉幾則公案加以說明。
“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十四,來禮祖(三祖),曰:‘愿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于言下大悟。”[16]
有一則著名的禪學公案“懷讓磨磚”就是通過“磚頭終究不能磨成鏡”來喻示“坐禪不能成佛”的道理。
“開元中,有沙門道一,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么?’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磚,于彼庵前石上磨。一曰:‘師作什么?’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磚豈得成鏡耶?’師曰:‘如人駕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于無住法,不應取舍。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17]
有一則公案叫“丹霞燒佛”:丹霞禪“師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呵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院主自后眉須墮落。”[16]
這三則公案都涉及佛教和哲學的深層問題。第一則公案涉及佛教的心性及其自由的本性問題。在西方哲學中屬于心靈哲學研究的課題。第則二公案屬于修身與修心的哲學方法論問題。第三則公案涉及佛教信仰的核心——“三寶”(佛、法、僧)的權威性問題。禪宗的公案面對如此重大而深奧的哲學問題,既沒有長篇的分析論證,又沒有概念的邏輯推演,卻是運用日常生活中的話語,通過具體的、具象的生活場景活脫脫地表現出來,而深奧的哲理就蘊藏其中。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已看到了一千多年前的禪宗就已經采取“詩性的”、“日常的語言”高談闊論復雜的哲學問題。這可以說明,20世紀西方思想界出現的“禪宗熱”絕不僅僅是為了獵奇,其中肯定蘊藏著“借他山之石,攻自己之玉”的目的。
三、為了“反邏輯”而采取的超越語言邏輯的話語策略
后現代的非理主義哲學主張用日常生活話語替代理性概念,主張用“延異”、“痕跡”等話語方式改造理性的概念和范疇。迄今,在哲學領域這一些主張都還僅僅停留在“主張”之中,只是在文學與藝術領域有明顯的表現。“后現代藝術的基本范疇,荒謬和解構在實際上就是在藝術創作中貫徹反理性化和反語言化的原則。”[5]446具體地說,就是德里達所主張的“不再通過語言的通道而寫出的‘語言文本式的作品’。”[5]446或者是像荒誕派戲劇、黑色幽默小說、魔幻現實主義小說那樣,通過荒誕、變形的反邏輯的不確定的話語形式來反對傳統的文學語言的思想性、邏輯性。與之相比,中國禪宗在超越通常的邏輯思維方式上,在開創新的語言表達形式上,在追求思想自由表達的主動性上,充分顯現出了深刻的中國式智慧。
禪宗詩歌語言充滿了生命情趣。禪師們在詩歌和公案的話語中,力求“語不驚人死不休”,采取多種手法把語言弄得奇麗險峻,千姿百態,生動有趣,富有生命感。
例如,禪詩善于運用夸張的比喻:“一口吸盡西江水”。禪詩中有不少極富想象力的詩句:“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云半間。昨夜云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閑。”船子德誠禪師寫了一首極富形象性和美妙詩意的詩歌:“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才動萬波隨。夜盡水寒魚不食,滿船載得明月歸。”龍光諲禪師的詩句:“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以及佚名禪師的詩句:“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等,這些詩句的語言都奇麗俊俏,同禪所追求的超塵脫俗的精神境界融為一體。
禪宗話語大量采取違背思維邏輯和生活常理的語言結構方式。禪的反邏輯概念的話語表現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那些故意采取一種獨特的言說方式,即采用某些對立的生活現象、意象所組成的話語形式并由此形成一種故意違背思維邏輯和生活常理的語言結構方式。它顯得荒謬背理,自相矛盾,自我否定。這種話語方式所表達出來的東西,我們用通常的邏輯的思維感覺不可理喻,很難理解,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從反邏輯的角度看,它們有不可否定的緣由和價值。例如,著名的傅大士(傅翳)的詩:“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這首詩,單從語言邏輯的習慣上看,是不可理喻的,荒誕不經的。但是,你從相對主義的角度看,它卻符合自然的情理邏輯:手不拿東西即“空手”,拿了東西(“把鋤頭”)就不是空手;人的手不總是處于這兩種狀態之中的嗎?人的運動不是自己步行,就是采取騎、乘、搭坐的運動方式,非有其他。人的視角如果以橋為基準點看,水在流;以流水為視覺基點(人與水同流),則是橋在流動。再如這首禪詩:“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身心清靜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這首禪詩,教導我們看待事物可以轉換習以為常的視角,采用新的角度就有新的發現、新的表現方法。人們習慣于抬頭看天,禪詩告知我們可以低頭看天(古人觀日、觀月都是用盆中盛油的方式來看);人們從來都認為,向前才是進步;禪詩告訴我們,退步也就是向前。這就是禪的思維方式——反常、荒誕卻有道理。
禪與后現代主義者通過“反概念”作為它們質疑和批判理性主義哲學權威的出發點,就是從基礎上、從根子上顛覆理性主義哲學的正統地位。禪與后現代主義哲學質疑理性邏輯概念的合法性,否定其權威性,揭示理性邏輯概念的僵化性、空洞性,主張用日常生活的鮮活的話語替代空洞的邏輯概念,用自創的名詞、概念去取代傳統哲學概念的地位;甚至大膽地采用反邏輯的語詞組合的方式去顛覆和消解傳統的邏輯結構,以此顯示創新的決心。
禪與后現代哲學從“反概念”開始,進而反對概念的“二元對立”結構,大膽破除“二律背反命題”,最終發展為用“悖論”來彌合概念與思維之間的裂縫。這一路走來,盡管禪與后現代主義哲學在反對理性主義哲學的霸權問題上,動機不同,目的不同,方法上也有著明顯的差異,具有異質性,但是,它們之間“家族相似”的同構性顯得更為清晰分明。從這種同構性中,既可以看到西方后現代主義哲學對東方禪學的汲取,又可以啟示我們如何把古老的中國智慧轉化為人類社會新的精神資源。
注釋:
① 公案是指歷代禪師所搜集和輯錄的禪師與弟子之間的各種機鋒、對話、棒喝的事例。這些事例被后人編輯為語錄或燈錄之類的書籍,被稱之為“公案”,猶如官府所積累的辦公文案一樣。
② 釋迦牟尼佛通過語言傳授的、由弟子記錄下來的思想觀念叫做“經”,禪宗稱之為“教內之法”。釋迦牟尼離開語言教誨,直接通過心傳或行為來教誨弟子,即沒有通過語言文字所表白的心印、默許、認可等所傳授的知識和真理,叫做“教外別傳”。
[參考文獻]
[1]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M].賀 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25.
[2]黑格爾.小邏輯[M].賀 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327.
[3]德勒茲,加塔利.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 [M].姜宇輝,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0.
[4]海德格爾.什么是哲學[M].復旦大學國外馬克思主義與國外思潮研究中心,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高宣揚.后現代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6]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 高名凱,譯.岑麒祥, 葉蜚聲,校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102.
[7]馮 俊.后現代哲學講演錄[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8]鈴木大拙.通向禪學之路[M].葛兆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侯世達.哥德爾、艾舍爾、巴赫:集異壁之大成[M].本書翻譯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10]鈴木大拙.禪風禪骨[M].耿仁秋,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9:166.
[11]洪 謙. 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12]約瑟夫·祁雅禮. 二十世紀法國思潮[M]. 吳永泉,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36.
[13]王治河. 后現代哲學思潮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14]李景源. 史前認識研究[M].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78.
[15]鈴木大拙.禪學入門[M].林宏濤,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
[16]普濟.五燈會元: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4.
[17]道原.景德傳燈錄:卷5[M].顧宏義,譯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329330.
(責任編輯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