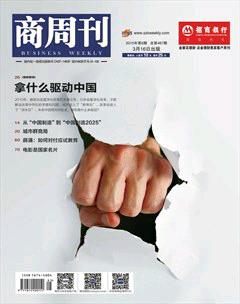一帶一路:看得見的未來
郭霞

“一帶一路”構想有意通過在鄰近各國開展基礎設施建設來消化中國國內的過剩產能,從而形成中國經濟圈。可以說,改革開放前30余年,中國靠引進外資,分享世界的“奶酪”而發展,當前,中國需要走出去,需要靠給予世界“奶酪”而發展。
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訪問哈薩克斯坦時首次提出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設想;2013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提出了中國愿同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
自“一帶一路”提出以來,全國各省市紛紛“點贊”。在2015年地方人代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31個省份提到要積極參與、主動融入“一帶一路”戰略。這個有4條主線,輻射范圍涵蓋東盟、南亞、西亞、中亞、北非和歐洲的理念,一旦成為現實,將構建起世界跨度最長、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走廊。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面臨著太多的“糾結”,要穩增長,又不能片面追求GDP;要投資,又要消化過剩產能。但是,這些“糾結”只能在發展中解決,而不能停下來解決。1984年,我國開放了14個東部沿海城市,也由此開啟了中國,特別是東部30年的高速發展。
30年的節點剛剛過去,此時,重啟改革和開放的焦點,恰恰落在了“一帶一路”。2015年3月7日,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在參加人代會期間的記者招待會時表示:“一帶一路”對于中國而言,有利于形成陸海統籌、東西互濟的對外開放新格局。“中國的西南、中國的西北、中國的東北通過‘一帶一路的建設,就會由腹地變為開放的前沿。”
“中國夢”照進現實
一般意義上的“絲綢之路”,指的是連接中國腹地與歐洲諸地的路上商業貿易通道,形成于公元前2世紀與公元1世紀之間,直至16世紀仍在使用。借助這條紐帶,東西方進行著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中國,也因此成為當之無愧的開放大國。
絲綢,在古羅馬的市場上,1磅的價格曾高達十余兩黃金,全長達7000多公里的“陸上絲綢之路”沿線各國中,絲綢、瓷器等中國商品都是當時最貴重的產品。
據統計,自1500年至1870年這300余年中,中國GDP占全球份額均是當之無愧的第一名,無可撼動,其中1820年,中國GDP占全球份額高達32.9%。時至今日,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任何一項大的戰略決策,都牽動著整個世界的神經,一個古老的大國,有著如此輝煌的歷史,又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期盼著新一輪的開放,“絲綢之路”再次引發了關注。
而除了著眼陸路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帶一路”,還包括了“海上絲綢之路”,前者從中國經由中亞,抵達荷蘭的貿易港口鹿特丹;后者將在印度洋沿岸各地由中國主導建立港口,通過海路連接中國與鹿特丹。
具體而言,“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分為三條線路:一條北線,北京-俄羅斯-德國-北歐;一條中線,北京-西安-烏魯木齊-阿富汗-哈薩克斯坦-匈牙利-巴黎;一條南線,北京-南疆-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意大利-西班牙。
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以泉州為起點,橫跨太平洋、印度洋,途經南海、馬六甲海峽、孟加拉灣、阿拉伯海、亞丁灣、波斯灣,涉及東盟、南亞、西亞、東北非等相關國家。
未來的“中國夢”,離不開對過去的回眸,也離不開對現實的關照:經過持續30余年的高速增長,中國面臨著來自內部、外部的諸多瓶頸。大量投資導致地方政府債務居高不下;產能過剩,制造業急需轉型升級;環境問題突出,過去的模式不可持續。這些都是“內憂”。外部環境也不容樂觀,出口不振,歐美經濟的下滑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美國正試圖通過TPP(跨太平洋自由貿易協定)和TTIP(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協定)來推動全球規則的大變局,這兩個協定,都將中國排除在外。
中國不能被邊緣化于全球之外,“一帶一路”也因此成為本屆政府的“招牌政策”,并被各界寄予厚望,認為是未來10年發展動力所在。據統計,陸上絲綢之路的區域覆蓋人口約46億,沿線各國經濟總量21萬億美元,分別占全球的63%、29%。而陸上絲綢之路沿線各國多為發展中國家,有著巨大發展潛力和需求,向這片區域開放,無異于打開一個廣闊的市場。
全球經濟,離開中國的參與,不能成為全球化;而中國面對全球高標準自由貿易區和規則變局的挑戰,也必須全面深化改革,開啟新一輪高標準的開放,重塑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力。
中國拿什么奉獻給世界
“一帶一路”構想有意通過在鄰近各國開展基礎設施建設來消化中國國內的過剩產能,從而形成中國經濟圈。可以說,改革開放前30余年,中國靠引進外資,分享世界的“奶酪”而發展,當前,中國需要走出去,需要靠給予世界“奶酪”而發展。
“一帶一路”既涉及貿易,又涉及投資,貿易與投資并重,這是中國拿出的“奶酪”。而不同以往的是,這次的“走出去”,不再只是輸出襪子、皮鞋、內衣等,高鐵、核電等高端制造業和基建項目成為熱門。據不完全統計,在2014年的外事活動中,李克強總理至少單獨向15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推介過高鐵、核電及基建項目,17次談及互聯互通及中國走出去戰略。
中國有著優質的過剩產能,以高鐵為例,成本是國際水平的三分之一,運營里程卻占全球的48%,企業本身也有向外擴張的動力,南車北車的海外業務占比還不到10%,而國外同行業的龐巴迪、阿爾斯通等,海外業務占比達90%。此外,我國的核電、高端裝備、建材、生產線等等,都具有產業優勢。
然而,此之甘飴,彼之砒霜。中國的貿易和資本要沿著“一帶一路”走出去,還需要考慮他國的階段性需求,比如對有些欠發達國家來說,最缺的是基礎能源建設而非高鐵,且高鐵造價昂貴,很難被接受。這就需要因地制宜。“一帶一路”是一個跨越時空的宏大戰略,并且要結成“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如何避免中國的“一廂情愿”,讓所有國家在“雙贏”中順暢接受,不但需要合理的頂層設計,更需要實際操作中科學的策略。
錢從哪里來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對于一個涵蓋60個國家和地區的宏大戰略來說,沒有什么比資金重要,這個戰略實施,意味著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錢從哪里來?
當前,同“一帶一路”密切關聯的資金池主要為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金磚組織開發銀行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其中,絲路基金總規模400億美元,首期資本金100億美元中,初定由外匯儲備占比65%。亞投行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中國初始認繳資本為500億美元,出資50%。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初始資本為1000億美元,由5個創始成員平均出資。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開展,越來越多的民間資本也對此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2014年11月,媒體曾報道一家名為“海上絲綢之路投資基金管理中心”正在籌建“海上絲綢之路銀行”,計劃私募1000億元人民幣投向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沿岸國家、地區、城市和企業相關項目。未來,公私合營(PPP)融資模式也將越來越多地用在“一帶一路”的項目上。
有觀點認為,目前我國外匯儲備近4萬億美元,其中大部分都用來購買美國國債,收益率低,這部分資金可以用來支持“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但同時也有觀點認為,外儲投資以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為基本原則,而“一帶一路”中大多為投資回收期10-30年的基建項目,不符合外儲投資的原則。
同時,“一帶一路”是一個尋求各方利益“最大公約數”的戰略,不同于過去的單邊援助,中國的金融機構不能再做賠本買賣,投資風險也是必須要考慮的因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環境不如歐美,并且存在地緣政治的因素,這也加大了投資的風險性。
商路重啟
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三次提及“一帶一路”,而在此之前,2月1日,“一帶一路”工作小組成立,張高麗任組長。2015年,是“一帶一路”落地實施的關鍵之年,互聯互通、大通關、國際物流大通道建設是經濟合作、文化交流的先決。
國內外對“一帶一路”有極大關注,也有積極支持和參與。截至目前,亞投行有20多個國家同意成為初創國,新西蘭等發達國家也陸續同意,希臘總理齊普拉斯近期稱將支持和參與中方提出的海上絲綢之路、中歐陸海陜線建設計劃,以便使希臘成為中國產品進入歐洲的主要門戶,而國內31個省市自治區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紛紛尋求定位。
全長1.29萬公里的貨運列車,從中國的義烏開往馬德里;重慶和德國杜伊斯堡開通了貨運列車;鄭州和德國的漢堡也開通了貨運列車;面向黃海的江蘇連云港開通了駛向哈薩克斯坦的定期貨運列車,“中哈物流基地”已經建成……
古老的絲綢之路,承載著跨越大洲的嶄新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