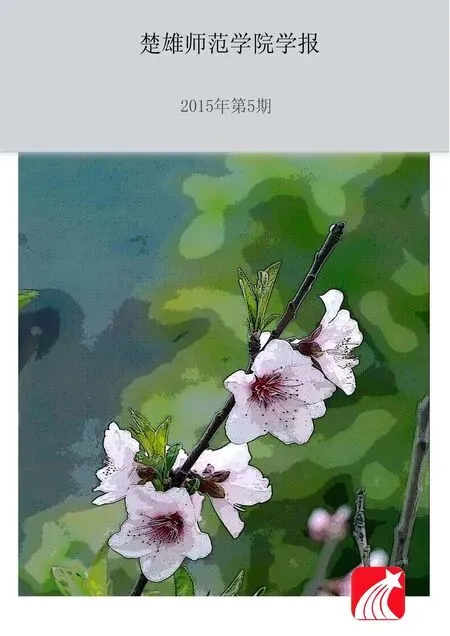“言外之意”理據探究*
陳麗梅
(云南師范大學,云南 昆明 650091)
“言外之意”是表達者用一定的語言形式來表達其語表意義之外的內容,使人思而得之,進而收到言近旨遠效果的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一種被廣泛關注的修辭現象。在古今漢語及其他語言運用中都普遍存在。
“言外之意”修辭現象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是源于其堅實的理據基礎。但就現有研究而言,對其存在理據的系統研究還未出現。因此,本文從哲學、語言、文化、審美及心理等五個方面,嘗試性地作系統探究。
一、“言外之意”現象存在的哲學基礎
哲學上對“言”、“意”關系的探討,實質是對語言與思維關系的探討。這在我國先秦、魏晉時期的“言意之辨”以及國外20世紀語言哲學轉向的相關理論中都有體現。
我國先秦及魏晉時期的“言意之辨”,主要涉及“言盡意”、“言不盡意”及“言”能屈折地“盡意”三種觀點。
“言盡意”觀是從形而下的角度,肯定語言具有表意的功能。這主要體現在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及魏晉時期歐陽建的“言意觀”中。特別是歐陽建在其《全晉文》的《言盡意論》這段文字中,指出:人們用名稱和語言來辨物定理,而且“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因而言稱和事物可以保持一致,所以“言”是可以“盡意”的。這就肯定了言表意的功能。
而“言不盡意”觀,是從形而上的角度,認為語言在表達抽象的“道”時存在局限。這以道家老、莊的言意觀為典型代表。老子認為“言”是不能傳達“道”的,即“道可道,非常道。”莊子在繼承老子“言意觀”的基礎上,對“言”、 “意”做了層次的區分,即《莊子·秋水》所說:“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物之粗”、“物之精”,是可以言論和以心體會到的;而對于“不期精粗”的“體道之意”是不能言論和不能意識到的。這是對“言”存在表意局限的認識。
此外,先秦及魏晉“言意之辨”中,也認識到“言”、 “意”間的辯證關系,認為“言”雖不能直接表達形而上的“意”,但能屈折地“盡意”,即“言”對“意”的“不盡之盡”。這在儒家和道家相關人物或著作的觀點中都有體現。如《易傳·系辭上》所言:“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圣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 ‘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在孔子看來,書面文字并不能完全記錄語言,語言也不能完全傳達旨意,需要借助直觀的“象”,才能將幽昧深邃的“意”表現出來。但是,卦象的內容要被傳達,仍需要借助語言這個工具。這也就是“言”對“意”的“不盡之盡”。而道家對“言意”辯證關系的認識,主要體現在莊子《莊子·外物》篇提出的“得意忘言”的理解方式及魏晉時王弼的言意觀中。特別是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在繼承《周易》“立象盡意”觀及莊子“得意忘言”等觀點基礎上,對“言”、“意”、“象”的關系進行了深入闡釋。王弼認為: “言”、 “象”是“意”外化的形式;“意”是“言”、“象”存在的依據和目的。 “言”并不只是為了“明象”,因“象生于意”,所以“言”最終是為了“明意”;只有忘掉具體的“言”、 “象”才能“得意”,即“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王弼的言意觀,詳細地談到了“言”如何曲折實現“盡意”。
綜上所述,從先秦及魏晉時期“言意之辨”所包含的這三種觀點,可以看出:作為表達工具的“言”,與主觀之“意”有著本質的不同。“言”具有“盡意”的功能,但有時又是“不盡意”的,“意”可以寄托于“言外”。這也就是“言外之意”產生的哲學依據。
而國外“言意”關系的相關探討,主要體現在20世紀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中,特別體現在維特根斯坦早期的哲學思想中。在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中,將世界劃分為“可說的”和“不可說的”兩部分。“可說的”即“包括日常經驗命題和自然科學命題,其中主要是自然科學命題。”[1](P78)“除了可以說的,即自然科學的命題之外,什么都不說”。這也就肯定了語言能表達形而下的內容,即能表達自然科學及邏輯范圍內的命題。而對于形而上的,包括價值、美學等相關的命題,是不能表達的。
綜觀國內外關于語言與思維關系的探討,可以看出:語言可以表達思維的成果,但對思維的幽深微妙處,及形而上的思維內容是“言不盡意”的。因“言”具有“盡意”的功能,所以可以借助語言來表達思想。又因“言不盡意”,才推動語言表達的不斷發展,尋找“言外”“盡意”的方式。這也就從哲學層面指出了“言外之意”現象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二、“言外之意”存在的語言學基礎
“言外之意”的表達是將“意”寄托于“言外”,“言”和“意”在語表是分離的。這種現象的產生與語言的符號性密不可分。
首先,語言符號的離合性,為“言外之意”的表達提供了工具性保障。一方面,因能指與所指約定俗成為固定的符號,人們可以運用語言符號進行表達。另一方面,因“能指與所指的聯系是任意的”[2](P101),這就使人們在語言運用中,為了表達的需求,可以對語言與客觀世界的聯系作一定主觀性的選擇,使辭面與辭里分離,借助辭面來傳達辭面意義以外的內容。這也就產生了“言外之意”。
其次,語言符號的模糊性、開放性也為“言外之意”現象的存在提供了條件。
語言的模糊性,主要指詞義的模糊性,也就是詞義邊界的模糊性。這種模糊性為詞義的多義理解提供了可能。在特定的語境中,也就能表達“言外之意”。
另外,“言外之意”現象的產生還與語言的開放性有關。語言的開放性,是指“語言的結構、內容、意義以及對意義的理解包含著無限的可能性。”[3](P11)“語言能突破語形、語音和語義之間的約定俗成的聯系,使它們之間產生新的聯系,語形和語音由此而獲得新的意義。”[4](P11)由此,語言在特定語境中,可以使辭面與辭里分離,突破能指與所指原有的聯系,產生新的聯系,形成“言外之意”現象。
概括而言,語言符號的離合性、模糊性及開放性,為“言外之意”表達和理解提供了語言基礎。
三、“言外之意”現象存在的文化基礎
“言外之意”在漢語及其他語言運用中都廣泛存在。這種普遍存在性,與其體現了人類共同的文化因素有關。具體來說,主要與委婉心理、意象思維密切相關。
首先,“言外之意”現象與委婉心理的推崇有關。
委婉心理,即是人們不喜直陳的一種心理特征,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文化心理。其產生與社會審美心理及相關社會習俗特別是禁忌有著重要關系。
首先,因禁忌“是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文化心理現象”[5](P99),其產生與人們的迷信、恐懼等心理有關。這就誘發了人們運用語言時的委婉心理,特別是在言說生老病死及生理現象等“不能直陳”的現象時比較明顯。
此外,委婉心理的產生還與人類審美追求—— “距離美”有關。關于“距離”的學說,德國哲學家叔本華 (ArthurSchopenhauer,1788—1860)和英國現代著名心理學家愛德華·布洛 (Edward Bullough,1880—1934)都有過相關論述。叔本華曾在“一群豪豬擠在一起過冬”的寓言中,指出了人與人相處應當有適當的距離。繼叔本華之后,布洛提出了著名的“心理距離說”,認為“心理距離”是“創造和欣賞美的一個基本原則”[6](P202)。對“距離美”的追求,就使人們在面對一些“不便直陳”的現象時,形成了委婉心理。
由禁忌、“距離美”等形成的委婉心理,為“言外之意”現象的產生奠定了心理基礎。當交際中出現“不能直陳”、“不便直陳”的情形時,“言外之意”的表達方式就是最好的選擇。通過將“意”寄托于“言外”,婉轉表意,就能避免直接表達帶來的負面效果,具有含蓄美。
其次,意象思維也是“言外之意”產生的重要影響因素。
“意象思維”是“在概念思維的基礎上改造過了的形象思維”[7](P146),是“替某一確定概念找到形象顯現”[8](P388)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是人類的一種普遍思維方式,在不同民族的語言交際、文學傳統中都有體現。特別是我國文論中的“意境論”,更是意象思維的典型體現。
“意境論”是將主觀之“意”通過客觀之“境”表現出來。也就是將抽象的內容通過具體形象直觀地表現出來。這也就形成了“言外之意”現象。這在詩詞中特別常見。如: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
詩的題目為《玉階怨》,但詩中卻未見一“怨”字。而是將“怨”化作具體場景的描寫:露重濕襪,主人公返室放下門簾,明亮的月光卻從門簾縫隙中投射進來,讓這位難眠之人癡癡凝望。通過整幅畫面的渲染,將內心的憂愁形象地表現出來。因此,正如《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中所說:“無一字言怨,而隱然幽怨之意見于言外。”此詩所傳達的“言外之意”,正是運用“意象思維”的結果。
當然,運用“意象思維”所形成的言外之意,并不一定都借助于具體的“象”,其表達“言外之意”的“言”,也都是表達“意”的中介。
綜上所述,委婉心理和意象思維是“言外之意”現象得以存在的文化基礎。
四、“言外之意”現象存在的審美基礎
“言外之意”現象備受青睞,與其具有“以一當十”、 “余味無窮”的表達效果密切相關。從審美角度來說,即“具有不盡的審美余味”[9](P209)。
這種“余味美”的產生,源于“言外之意”間接的表達方式,引發了接受者的審美想象。
想象,從心理學角度來說,“是在頭腦中改造記憶表象而創造新形象的心理活動,是過去經驗中已經形成的暫時神經聯系重新進行結合的過程。它的突出特點是新形象的創造。”
因“言外之意”的辭面與辭里 (所要表達的思想內容)間的聯系是間接的,這就留給了接受者思考的空間,需要接受者在辭面信息刺激下,在自己積累的知識中搜尋與辭面相關的信息,再根據語境進行加工、改造,從而產生新的認識。這也就是接受者發揮想象的過程。
接受者在想象過程中,在辭面和語境限定的范圍內,實現了思維的自由馳騁,“滿足了人的自由本性的欲求,擴張了人的精神境界,讓人感到了主體價值的崇高”[10](P254),由此體會到審美愉悅。此外,通過想象,尋找到辭面與辭里的聯系,恰當地理解了表達者的“言外之意”。這就使接受者超越了語言的限制,在精神上實現了與表達者的交流。這種交流的實現,是對接受者思考過程的肯定,讓接受者體會到自我肯定的滿足,美感也便油然而生。因此,“言外之意”的“余味美”,就是接受者在理解時,發揮想象所體會到的思維自由的快感和自我肯定的滿足。如下面的例子: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此詩短小精悍,意境深邃,含蓄雋永。其審美體驗主要體現在“以少總多”及“以樂景寫哀”所引發的想象之中。
天寶末年進宮而幸存下來的白發宮人在冷清的上陽宮中回憶、談論天寶遺事。辭面只寫到此,但辭面內容卻能引發鑒賞者的想象:宮女們年輕時的花容月貌,被禁閉于這冷清行宮中的寂寞無聊。年復一年,容顏憔悴,白發頻添。這些年的凄苦與孤獨,都寄托在這短短的二十字中。因此,正如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卷二中評論此詩時所說: “語少意足,有無窮味。”而這“無窮味”正是鑒賞者通過想象所體會到的,也是詩歌所要傳達的“言外之意”。
同時,詩歌的雋永美,還體現在“以樂景寫哀”的表現方式中。
在寂寥的古行宮中,宮花競相爭艷,而生活于其中的宮女卻是白發蒼蒼。將這兩種場景組合在一起,就產生了強烈的對比:“紅花”與“白發”,“花值正春”與“人之遲暮”。這種強烈的顏色和情感的反差,便能引發接受者的想象。通過想象,將聯想到的信息進行對比,就能將白發宮女的悲涼、哀怨之情凸顯出來。而這“悲涼、哀怨之情”正是詩人選擇這些場景所要傳達的“言外之意”。因此,如清人沈德潛《唐詩別裁》中所說:“‘說玄宗’,不說玄宗長短,佳絕。只四語,已抵一篇長恨歌矣。”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鑒賞者在辭面信息刺激下,引發關系、對比聯想,再將聯想的內容結合詩歌描寫場面進行加工,在較少的語辭中,拓展出豐富的內容。在這個過程中,鑒賞者的思維在辭面刺激的范圍內得以自由馳騁。同時接受者發揮能動性對聯想內容進行了組合、拓展,透過字面領會到詩人所要表達的思想內容,體會到精神交流的滿足。這種思維馳騁的快感及精神交流的滿足,即是鑒賞者所體味的雋永美。
“言外之意”現象的存在除與哲學、語言學、文化及審美等密切相關外,相關心理因素也是必不可少的。不管是“言外之意”的表達還是理解,都是雙方各自心理活動的結果,都涉及記憶、聯想、想象等心理因素。特別是表達者選用何種語言形式進行表達,接受者如何尋找到辭面與辭里的聯系,這些都與相應的心理活動密不可分。
綜上所述,“言外之意”修辭現象的存在,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其中,“必要性”主要體現在哲學、美學及文化等方面。哲學上認為“言”對“意”是“不盡之盡”的。要解決這個矛盾,就需借助于“言”又不局限于“言”,于“言”外去領會“意”,這便出現了“言外之意”現象。在美學上,“言外之意”所能激發的想象美,給言語交際帶來美的享受。此外,文化因素中委婉心理及意象思維,對“言外之意”的產生也有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而“言外之意”產生的可能性,主要與語言符號的特征和相關心理因素直接相關。語言符號“能指”與“所指”的離合性、模糊性及開放性,為“言”外傳“義”提供了工具性保障。此外,相關心理因素的調用,更是表達和接受的基礎。
可見,“言外之意”現象的存在是必要的和必然的,有著堅實的存在基礎,是一種很值得研究的現象。
[1]尚志英.尋找家園——多維視野中的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瑞士)索緒爾著,高名凱譯.普通語言學教程[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3]王曉升.語言與認識 [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4]王曉升.語言與認識 [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5]鄭卓睿.漢語與漢文化 [M].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
[6]吳禮權.委婉修辭研究 [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8.
[7]胡經之.文藝美學 [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8]朱光潛.西方美學史 [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
[9]曾祖蔭.中國古代美學范疇 [M].武昌: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6.
[10]楊守森.藝術想象論 [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