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海 《中國(guó)詩(shī)歌通史·先秦卷》的幾個(gè)問(wèn)題*
楊德春
(邯鄲學(xué)院中文系,河北 邯鄲 056005)
關(guān)于所謂的《彈歌》是現(xiàn)今所能見(jiàn)到的最早的歌謠的問(wèn)題
李炳海《中國(guó)詩(shī)歌通史·先秦卷》:
現(xiàn)今所能見(jiàn)到的最早的歌謠,是載于《吳越春秋》卷九的《彈歌》:“斷竹,續(xù)竹,飛土,逐宍 (古肉字)。”相傳這首歌謠作于黃帝時(shí)期,雖然斷代未必十分準(zhǔn)確,但從內(nèi)容和形式上看,它產(chǎn)生的年代確實(shí)很古老。這首歌謠敘述由砍竹制作彈弓到獵取野獸的全過(guò)程,反映的是先民的勞動(dòng)生活。[1](P30)
李炳海所謂的《彈歌》是現(xiàn)今所能見(jiàn)到的最早的歌謠之說(shuō)是值得商榷的。
《文心雕龍·通變》:“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zhì)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于黃世;”[2](P198)
《文心雕龍·章句》: “至于《詩(shī)》、 《頌》大體,以四言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為句。尋二言肇于黃世,《竹彈》之謠是也;”[2](P219)
《文心雕龍·通變》和《文心雕龍·章句》均以《彈歌》為黃世之歌,其說(shuō)沒(méi)有任何依據(jù),不可信。
《吳越春秋》云:
于是,范蠡復(fù)進(jìn)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qǐng)音而問(wèn)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 “臣,楚之鄙人,嘗步于射術(shù),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愿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柰何?”音曰:“古者人民樸質(zhì),饑食鳥(niǎo)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見(jiàn)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niǎo)獸之害。故歌曰‘?dāng)嘀瘢m(xù)竹,飛土,逐害’之謂也。于是神農(nóng)、黃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3](P152)
《吳越春秋》明確記載,古者人民樸質(zhì),饑食鳥(niǎo)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并未記載古者即黃世。
《吳越春秋》明確記載,先有孝子不忍見(jiàn)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niǎo)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xù)竹,飛土,逐害”之謂也。于是后有神農(nóng)、黃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可見(jiàn),《彈歌》非為黃世之歌,《彈歌》的產(chǎn)生不僅在黃世之前,而且在神農(nóng)之前,故以《彈歌》為黃世之歌之說(shuō)法不能成立。
《吳越春秋》明確記載,孝子不忍見(jiàn)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niǎo)獸之害。
傳說(shuō)中的炎帝、黃帝是中國(guó)很早的原始社會(huì)的人,實(shí)際上,炎帝、黃帝之時(shí)代在社會(huì)發(fā)展的階段上是處在原始社會(huì)之晚期,已越過(guò)血緣群婚制階段而發(fā)展到族外婚制階段。傳說(shuō)中的炎、黃事跡,更說(shuō)明中國(guó)原始社會(huì)已發(fā)展到父系氏族社會(huì),并明顯地向?qū)ε蓟榧耙环蛞黄拗瓢l(fā)展。但中華民族的前身的歷史已有一百七十萬(wàn)年之久,其中原始社會(huì)很長(zhǎng)很長(zhǎng),傳說(shuō)中的炎黃時(shí)代僅僅反映了原始社會(huì)相對(duì)比較短、比較近的一個(gè)階段。
傳說(shuō)中的神農(nóng)要早于炎帝、黃帝之時(shí)代,而《彈歌》的產(chǎn)生不僅在黃世之前,而且在神農(nóng)之前,這就產(chǎn)生了一個(gè)問(wèn)題,《彈歌》的產(chǎn)生如此之早以至于《彈歌》的語(yǔ)言文字形式和藝術(shù)形式與《彈歌》的產(chǎn)生年代是否相符合的問(wèn)題。
北京房山的山頂洞人文化遺址明顯分為下室和上室兩部分,下室發(fā)現(xiàn)青年女性、中年女性和老年男性之頭骨各一個(gè),在一骨盆和股骨周?chē)l(fā)現(xiàn)赤鐵礦粉和赤鐵礦石,還有介殼等裝飾品,基本上可以認(rèn)定山頂洞的下室當(dāng)是墓地,并且是我國(guó)至今所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墓地。山頂洞人活動(dòng)的時(shí)代屬于舊石器時(shí)代晚期,中國(guó)在舊石器時(shí)代晚期就已經(jīng)將死者埋葬,并且以赤鐵礦粉末和礦石及少量裝飾品飾終。
《彈歌》的內(nèi)容反映的情況是尚未將死者埋葬,其反映的年代只能是在舊石器時(shí)代晚期以前,即在山頂洞人之前。山頂洞人活動(dòng)時(shí)間一般認(rèn)為約在距今五萬(wàn)年前,《彈歌》的內(nèi)容所反映的情況則在距今五萬(wàn)年前之前。這樣就產(chǎn)生了《彈歌》的內(nèi)容和形式之間的時(shí)間矛盾。
《彈歌》的語(yǔ)言文字形式是整齊的四個(gè)動(dòng)賓結(jié)構(gòu),這是語(yǔ)言文字發(fā)展的高級(jí)形式之一,一般認(rèn)為在語(yǔ)言文字發(fā)展的初級(jí)階段是沒(méi)有詞類之分的,也不可能達(dá)到語(yǔ)言文字形式的整齊劃一。《彈歌》的語(yǔ)言文字形式與《彈歌》可能產(chǎn)生于舊石器時(shí)代晚期以前的推測(cè)不相符合。
《彈歌》的語(yǔ)言文字形式是整齊的四個(gè)動(dòng)賓結(jié)構(gòu),而且《彈歌》的整齊的四個(gè)動(dòng)賓結(jié)構(gòu)還可以組成兩個(gè)整齊的四言句式,《彈歌》的所謂二言極為整齊劃一,與《詩(shī)經(jīng)》中的二言句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詩(shī)經(jīng)》中的二言句一般不可能組成整齊的四言句式,這說(shuō)明《彈歌》所具有的既是整齊的四個(gè)動(dòng)賓結(jié)構(gòu)又是整齊的兩個(gè)四言句式只能是借鑒了《詩(shī)經(jīng)》的語(yǔ)言文字形式,即《彈歌》的語(yǔ)言文字形式產(chǎn)生于《詩(shī)經(jīng)》之后。
裘錫圭《文字學(xué)概要》:“從我們現(xiàn)有的知識(shí)來(lái)看,世界上從來(lái)沒(méi)有一個(gè)民族是在進(jìn)入階級(jí)社會(huì)之前就創(chuàng)造了完整的文字體系的。根據(jù)絕大多數(shù)史學(xué)家的意見(jiàn),我國(guó)大約在夏代進(jìn)入階級(jí)社會(huì),所以漢字形成的時(shí)代大概不會(huì)早于夏代。”[4](P25-26)
甲骨文中已有老、考二字,老字見(jiàn)于鐵76·3,考字見(jiàn)于前7·35·2,老、考二字皆可以通孝,但有了孝的通假字,不能說(shuō)明孝的觀念已經(jīng)產(chǎn)生。關(guān)于孝產(chǎn)生的時(shí)間問(wèn)題不當(dāng)以孝的通假字之出現(xiàn)為準(zhǔn),而當(dāng)以孝字之出現(xiàn)為準(zhǔn)。現(xiàn)在甲骨文未見(jiàn)孝字,而金文始見(jiàn)孝字,《彈歌》所反映的主要是孝的觀念,故筆者認(rèn)為《彈歌》的產(chǎn)生不會(huì)早于周代。
由此可見(jiàn),野外裸葬之年代當(dāng)早于北京房山山頂洞人于下洞墓地埋葬死者并以赤鐵礦粉末和不少裝飾品飾終之年代,即野外裸葬之年代當(dāng)早于距今五萬(wàn)年前之舊石器時(shí)代晚期。而《彈歌》的語(yǔ)言形式和所反映的孝的觀念卻又不可能早于周代,即不可能早于《詩(shī)經(jīng)》的語(yǔ)言形式之前。如此則《彈歌》只能是后世追記或臆測(cè)古代之情況而形成之作品。
關(guān)于所謂的《國(guó)風(fēng)》是歌詞選集的問(wèn)題
李炳海《中國(guó)詩(shī)歌通史·先秦卷》:“《國(guó)風(fēng)》是十五個(gè)地區(qū)的歌詞選集,地域上的覆蓋面很廣。”[1](P74)
中國(guó)傳統(tǒng)的四部分類法將集部分為別集和總集兩個(gè)大類。所謂別集就是收錄一人作品之集子,所謂總集就是收錄多人作品之集子。總集又可分為全本式總集和選本式總集兩類。別集又可分為全集和選集兩類。所謂全集就是收錄一人全部作品之集子,所謂選集就是收錄一人部分作品之集子。
現(xiàn)代漢語(yǔ)卻有將別集中的選集與選本式總集混淆之趨勢(shì)。別集中之選集是收錄一人部分作品的集子,而《現(xiàn)代漢語(yǔ)詞典》第6版將“選集”解釋為:“選錄一個(gè)人或若干人的著作而成的集子 (多用于書(shū)名): 《老舍選集》。”[5](P1476)《現(xiàn)代漢語(yǔ)詞典》第 5 版對(duì) “選集”之解釋與此全同。[6](P1544)《現(xiàn)代漢語(yǔ)詞典》第6版將“選本”解釋為:“從一個(gè)人或若干人的著作中選出部分篇章編輯成的書(shū)。”[5](P1476)《現(xiàn)代漢語(yǔ)詞典》第5版對(duì)“選本”之解釋與此全同。[6](P1544)這實(shí)際上就混淆了別集中之選集與選本式總集之本質(zhì)區(qū)別,似乎選集與選本就完全等同了。《現(xiàn)代漢語(yǔ)詞典》的這種解釋忽略了漢語(yǔ)之歷史發(fā)展,過(guò)分關(guān)注和強(qiáng)調(diào)漢語(yǔ)在現(xiàn)代之使用情況,而《現(xiàn)代漢語(yǔ)詞典》混淆選集和選本之本質(zhì)區(qū)別是完全錯(cuò)誤的。
由此可見(jiàn),李炳海《中國(guó)詩(shī)歌通史·先秦卷》所謂“《國(guó)風(fēng)》是十五個(gè)地區(qū)的歌詞選集”之說(shuō)是完全錯(cuò)誤的。
首先,一般認(rèn)為《詩(shī)經(jīng)》分為《風(fēng)》《雅》《頌》三部分,《國(guó)風(fēng)》只不過(guò)是《詩(shī)經(jīng)》的一個(gè)組成部分,從現(xiàn)在所掌握的材料來(lái)看,《國(guó)風(fēng)》并沒(méi)有脫離《詩(shī)經(jīng)》而成為單行本。或曰,從現(xiàn)在所掌握的材料來(lái)看,《國(guó)風(fēng)》并沒(méi)有脫離《詩(shī)經(jīng)》而成為一本獨(dú)立的書(shū)籍。而選集是中國(guó)傳統(tǒng)的書(shū)籍的四部分類法對(duì)于書(shū)籍分類的一種,從現(xiàn)在所掌握的材料來(lái)看,《國(guó)風(fēng)》并沒(méi)有脫離《詩(shī)經(jīng)》而成為單行本,即《國(guó)風(fēng)》并沒(méi)有脫離《詩(shī)經(jīng)》而成為一本獨(dú)立的書(shū)籍,那么,《國(guó)風(fēng)》也就不可能是選集。
其次,中國(guó)傳統(tǒng)的書(shū)籍的四部分類法將集部分為別集與總集兩類。別集是收錄一人作品的集子。別集又可分為選集和全集。收錄一人部分作品的集子稱為選集。既然《國(guó)風(fēng)》收錄十五個(gè)地區(qū)的歌詞,那么,《國(guó)風(fēng)》就不可能是一人的作品。既然《國(guó)風(fēng)》不可能是一人的作品,那么《國(guó)風(fēng)》也就不可能是什么選集。
由此可見(jiàn),李炳海對(duì)于中國(guó)古典文獻(xiàn)學(xué)是多么不了解。一個(gè)想要學(xué)習(xí)或研習(xí)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的人,如果不具備起碼的中國(guó)古典文獻(xiàn)學(xué)常識(shí),是寸步難行的。李炳海連中國(guó)古典文獻(xiàn)學(xué)的一些常識(shí)都不清楚,還要地研究先秦文學(xué),其所謂研究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關(guān)于所謂的《詩(shī)經(jīng)》為樂(lè)官采錄編選的問(wèn)題
李炳海《中國(guó)詩(shī)歌通史·先秦卷》:
《詩(shī)經(jīng)》作品來(lái)自多個(gè)渠道,它的選錄、結(jié)集,是由周王朝樂(lè)官完成的。成書(shū)后的《詩(shī)經(jīng)》,許多地方留下了樂(lè)官采錄編選的痕跡。
第一,《詩(shī)經(jīng)》章句排列比較整齊,有規(guī)律可循。[1](P56)
這是一個(gè)什么理由?難道章句排列比較整齊、有規(guī)律可循就是樂(lè)官采錄編選留下的痕跡?如此則《楚辭》章句排列也比較整齊、有規(guī)律可循,難道《楚辭》也是樂(lè)官采錄編選的?《玉臺(tái)新詠》章句排列也比較整齊、有規(guī)律可循,難道《玉臺(tái)新詠》也是樂(lè)官采錄編選的?《全唐詩(shī)》章句排列也比較整齊、有規(guī)律可循,難道《全唐詩(shī)》也是樂(lè)官編輯的?
李炳海《中國(guó)詩(shī)歌通史·先秦卷》關(guān)于《詩(shī)經(jīng)》是樂(lè)官所編選的第二條理由是:
《詩(shī)經(jīng)》個(gè)別作品所流傳的不同版本說(shuō)明,樂(lè)師對(duì)這些歌詩(shī)進(jìn)行了加工。《衛(wèi)風(fēng)·碩人》第二章描寫(xiě)莊姜的美貌,后半部分有如下三句“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論語(yǔ)·八佾》篇寫(xiě)道:子夏問(wèn)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子夏所引用的詩(shī)句出自《衛(wèi)風(fēng)·碩人》,但今本《詩(shī)經(jīng)》沒(méi)有“素以為絢兮”這句。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情況,是樂(lè)師在編輯時(shí)刪節(jié)的結(jié)果。《衛(wèi)風(fēng)·碩人》全詩(shī)四章,每章七句,如果把“素以為絢兮”這句加入,第二章就變成八句,在句數(shù)上與其它三章不一致,給演唱造成障礙。樂(lè)師《碩人》一詩(shī)各章句數(shù)作了整齊劃一的處理,刪去了原有的“素以為絢兮”。這種整齊劃一的刪節(jié)造成了文學(xué)表現(xiàn)上的缺失,但卻適于演唱,各章能采用同一曲調(diào)。[1](P57)
李炳海《中國(guó)詩(shī)歌通史·先秦卷》云:
另一種類型是詩(shī)的前半部分各章句數(shù)相同,后半部分各章句數(shù)也相同,前后兩部分每章句數(shù)不同。《大雅·卷阿》屬于這種類型。全詩(shī)十章,前六章每章五句,后四章每章六句,依此推斷,《卷阿》前六章是用一種曲調(diào)演唱,后四章用另一種曲調(diào)演唱。《詩(shī)經(jīng)》的章句結(jié)構(gòu)適合演唱,不會(huì)給演唱造成障礙,這是樂(lè)師對(duì)章句精心編排的結(jié)果,使它們都以歌詞的形式出現(xiàn)。[1](P57)
首先,既然《卷阿》可以前六章用一種曲調(diào)演唱而后四章用另一種曲調(diào)演唱,那么,《衛(wèi)風(fēng)·碩人》全詩(shī)四章,每章七句,如果把“素以為絢兮”這句加入,第二章就變成八句,完全可以第一、三、四章用一種曲調(diào)演唱而第二章用另一種曲調(diào)演唱,樂(lè)師無(wú)由非要對(duì)《碩人》一詩(shī)各章句數(shù)作整齊劃一之處理。《碩人》第二章變成八句根本不會(huì)給演唱造成障礙,若《碩人》第二章變成八句會(huì)給演唱造成障礙,則《大雅·卷阿》前六章每章五句而后四章每章六句也會(huì)給演唱造成障礙,但是李炳海說(shuō)《大雅·卷阿》不存在演唱造成障礙的問(wèn)題,如此則《碩人》第二章變成八句根本不會(huì)給演唱造成障礙。李炳海之說(shuō)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shuō)。
其次,周代推行禮樂(lè)文化,音樂(lè)文化藝術(shù)十分發(fā)達(dá),音樂(lè)具有無(wú)限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對(duì)于句數(shù)、字?jǐn)?shù)根本不在話下。李炳海把周代高度發(fā)達(dá)的禮樂(lè)文化研究成為單調(diào)貧乏的幾種演唱方式,實(shí)屬不妥。
再次,李炳海說(shuō):“《詩(shī)經(jīng)》的章句結(jié)構(gòu)適合演唱,不會(huì)給演唱造成障礙,這是樂(lè)師對(duì)章句精心編排的結(jié)果,使它們都以歌詞的形式出現(xiàn)。”[1](P57)《詩(shī)經(jīng)》的章句結(jié)構(gòu)適合演唱,當(dāng)然不會(huì)給演唱造成任何障礙,這如何能夠得出這是樂(lè)師對(duì)章句精心編排的結(jié)果之結(jié)論?若《詩(shī)經(jīng)》是樂(lè)師精心編輯的,樂(lè)師之所長(zhǎng)在于音樂(lè),樂(lè)師不編輯樂(lè)譜,卻來(lái)編輯修改歌詞,最后以歌詞的形式來(lái)表現(xiàn)音樂(lè),這是什么樂(lè)師?樂(lè)師編輯一本歌詞,因?yàn)橛械母柙~用音樂(lè)無(wú)法表現(xiàn),在李炳海看來(lái)周代高度發(fā)達(dá)的禮樂(lè)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就是如此無(wú)能!筆者認(rèn)為李炳海的論述不能成立。
又次,孔子多次提到詩(shī)三百,即孔子論詩(shī)時(shí)《詩(shī)經(jīng)》已經(jīng)編成。另外,公元前544年,季札訪魯所觀樂(lè)與今本《詩(shī)經(jīng)》基本相同,此時(shí)孔子只有八歲,可證明《詩(shī)經(jīng)》在孔子出生前已經(jīng)編成。孔子與子夏論詩(shī),子夏所引用的詩(shī)句出自《衛(wèi)風(fēng)·碩人》,“素以為絢兮”必然在《詩(shī)經(jīng)》之中,若《詩(shī)經(jīng)》果為樂(lè)師所編輯,則樂(lè)師并未刪去“素以為絢兮”以作整齊劃一之處理。王先謙《詩(shī)三家義集疏》:“‘魯有素以為絢兮句’者,……以《列女傳》證之,魯詩(shī)本有此一句。”[7](P283)今本 《毛詩(shī)》無(wú)此句當(dāng)為流傳過(guò)程中誤脫,根本談不上樂(lè)師刪去此句,李炳海卻以此證明《詩(shī)經(jīng)》為樂(lè)師所編輯,真是“高論”啊!
另外,李炳海又舉一例:
再如《小雅·雨無(wú)正》,全詩(shī)未出現(xiàn)“雨無(wú)正”之語(yǔ),令人對(duì)其篇目產(chǎn)生了疑惑。朱熹《詩(shī)經(jīng)集傳》寫(xiě)道: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shī)》,有《雨無(wú)正》篇。……至其詩(shī)之文,則比《毛詩(shī)》篇首多‘雨其無(wú)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shuō)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zhǎng)短不齊,非詩(shī)之例。顯然,《雨無(wú)正》詩(shī)原本有開(kāi)頭“雨其無(wú)極,傷我稼穡”兩句,樂(lè)師在編排整理時(shí),為了使第一、二兩章句數(shù)一致,刪去了這兩句,因此,使后人對(duì)篇名的由來(lái)大惑不解。樂(lè)師是按照適于演唱的原則對(duì)各章的句數(shù)進(jìn)行調(diào)整的。以上僅是可以明顯見(jiàn)到的兩個(gè)典型案例而已。[1](P57-58)
《韓詩(shī)》是《詩(shī)經(jīng)》在流傳過(guò)程中形成的一個(gè)傳授系統(tǒng),三家詩(shī)和《毛詩(shī)》都有一個(gè)共同的祖本,也就是說(shuō),《詩(shī)經(jīng)》是在編輯完成之后才在流傳過(guò)程中形成三家詩(shī)和《毛詩(shī)》等不同的傳授系統(tǒng)的。《韓詩(shī)》之《小雅·雨無(wú)正》有“雨其無(wú)極,傷我稼穡”八字,無(wú)非是兩種可能,其一為《詩(shī)經(jīng)》原本即有“雨其無(wú)極,傷我稼穡”八字,其二為《韓詩(shī)》在流傳過(guò)程中所加。若“雨其無(wú)極,傷我稼穡”八字為《韓詩(shī)》在流傳過(guò)程中所加,《詩(shī)經(jīng)》原本即無(wú)此八字,則就算《詩(shī)經(jīng)》為樂(lè)師所編,也根本談不上樂(lè)師刪去此八字;若“雨其無(wú)極,傷我稼穡”八字為《詩(shī)經(jīng)》原本所原有,則就算《詩(shī)經(jīng)》為樂(lè)師所編,“雨其無(wú)極,傷我稼穡”八字樂(lè)師也并未刪去,也根本無(wú)法證明樂(lè)師曾經(jīng)按照適于演唱的原則對(duì)各章的句數(shù)進(jìn)行過(guò)調(diào)整或刪減。李炳海到底是如何研究出樂(lè)師曾經(jīng)按照適于演唱的原則對(duì)各章的句數(shù)進(jìn)行過(guò)調(diào)整的?
李炳海《中國(guó)詩(shī)歌通史·先秦卷》云:“《詩(shī)經(jīng)》某些作品的排列順序與先秦時(shí)期在禮儀上的演唱順序相一致,這也可以證明《詩(shī)經(jīng)》是由樂(lè)師編訂的。”[1](P57-58)由先秦典籍中所記載的《詩(shī)經(jīng)》中某些作品在先秦時(shí)期的禮儀上的演唱順序與今本《詩(shī)經(jīng)》某些作品的排列順序相一致不能證明《詩(shī)經(jīng)》是由樂(lè)師編訂的,樂(lè)師有權(quán)力、有能力決定在禮儀上如何演唱,即如何譜曲、如何配樂(lè)、如何演奏等等事項(xiàng)或問(wèn)題,這些音樂(lè)方面的技術(shù)問(wèn)題樂(lè)師完全可以做主,這是他們職責(zé)范圍以內(nèi)的事項(xiàng)或問(wèn)題。但是至于禮儀上選擇演奏什么、演奏的順序、禮儀的制定則絕非樂(lè)師所能夠染指,樂(lè)師不過(guò)是聽(tīng)令者,禮的制定完全是統(tǒng)治者或出令者之事,樂(lè)師不僅沒(méi)有出令的權(quán)力,也根本沒(méi)有出令的能力。由先秦典籍中所記載的《詩(shī)經(jīng)》中某些作品在先秦時(shí)期的禮儀上的演唱順序與今本《詩(shī)經(jīng)》某些作品的排列順序相一致不能證明《詩(shī)經(jīng)》是由樂(lè)師編訂的。
關(guān)于騷的解釋問(wèn)題
李炳海《中國(guó)詩(shī)歌通史·先秦卷》云:
騷,指的是蹇,騷是楚地方言,蹇是各地的通用語(yǔ)。《離騷》既取楚地方言作為篇名,又有通用語(yǔ)謇、蹇表示言難、行難,這種情況在屈原其他作品中是否也存在呢?回答是肯定的。《離騷》稱“憑不厭乎求索”,王逸注:“憑,滿也,楚人名滿曰憑。”憑,繁體作憑,與馮相通。 《天問(wèn)》: “馮翼惟象”、 “康回馮怒”,馮,乃是盛滿之義。憑、馮是楚地方言,但是,這并不妨礙屈原同時(shí)運(yùn)用和它們意義相同的通用語(yǔ),《九章·思美人》就有“高辛之盛靈”的句子,盛是通用語(yǔ),和楚地方言憑、馮是同義詞。再看同一篇作品中兼用表示相同意義的楚地方言和通用語(yǔ)的情況: 《九章·惜往日》:“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人以自代。”佳,洪興祖、朱熹皆引別本作娃,佳、娃相通。……再看《九章·橘頌》:“曾枝剡棘,圓果摶兮。”王逸注: “楚人名圜為摶。”摶是楚語(yǔ),圓是通用語(yǔ),都是表示圓形,兩個(gè)詞出現(xiàn)在同一句子中,構(gòu)成前后互證的關(guān)系。既然屈原在許多作品中都同時(shí)運(yùn)用表示相同意義的楚地方言和通用語(yǔ),那么,《離騷》篇名和正文兼用楚地方言騷字和通用語(yǔ)謇、蹇,也就不足為奇了,這種做法合乎屈原的行文習(xí)慣,沒(méi)有值得懷疑的地方。[1](P418)
首先,李炳海此論十分牽強(qiáng)。通行本《九章·惜往日》作佳,且佳完全可以講通,從訓(xùn)詁原則講,完全不必以佳、娃相通訓(xùn)釋,故李炳海此證不能成立。《九章·橘頌》王逸注:“楚人名圜為摶。”摶確實(shí)是楚語(yǔ),但是楚人名圜為摶,不是楚人名圓為摶,否則變成圓果圓兮就成了多余的廢話,故李炳海此證也不能成立。可見(jiàn),屈原在同一篇作品中并未同時(shí)運(yùn)用表示相同意義的楚地方言和通用語(yǔ)。如果屈原果真那樣使用的話,那實(shí)際上是重復(fù)或變相重復(fù),必將有損于屈原作品的藝術(shù)性,屈原也絕不會(huì)那樣使用。
其次,作者思維的一致性必然導(dǎo)致行文的一致性,不可能出現(xiàn)騷指的是蹇、騷是楚地方言、蹇是各地的通用語(yǔ)而同時(shí)出現(xiàn)在同一篇作品之中。
再次,標(biāo)題作《離騷》,標(biāo)題對(duì)于全篇內(nèi)容具有概括性,標(biāo)題對(duì)于全篇內(nèi)容也具有呼應(yīng)性。
所以,李炳海所謂騷指的是蹇之說(shuō)不能成立。
關(guān)于《詩(shī)經(jīng)》為歌詩(shī)的問(wèn)題
李炳海《中國(guó)詩(shī)歌通史·先秦卷》云:“十五國(guó)風(fēng),是十五個(gè)地區(qū)歌詩(shī)的匯集。”[1](P61)
李炳海《中國(guó)詩(shī)歌通史·先秦卷》云:“《小雅》、《大雅》都是周王朝首都所在地的歌詩(shī),……”[1](P61)
李炳海《中國(guó)詩(shī)歌通史·先秦卷》云:“三頌是用于祭祀的歌詩(shī),在祭祀的禮儀中演唱。”[1](P64)
李炳海《中國(guó)詩(shī)歌通史·先秦卷》云:“《詩(shī)經(jīng)·國(guó)風(fēng)》都是歌詩(shī),可以配樂(lè)演唱。”[1](P111)
李炳海《中國(guó)詩(shī)歌通史·先秦卷》:
《雅》詩(shī)還有標(biāo)明為誦者,具體篇目有《小雅·節(jié)南山》,《大雅》的《崧高》和《烝民》。《節(jié)南山》云:“家父作誦,以究王讻。”《崧高》寫(xiě)道:“吉甫作誦,其詩(shī)孔碩,其風(fēng)肆好。”《烝民》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fēng)。”從《崧高》的敘述可知,誦指可以演唱的歌詩(shī),包括歌詞和曲調(diào),歌詞稱為詩(shī),曲調(diào)稱為風(fēng)。以此類推,《節(jié)南山》和《烝民》既然標(biāo)明是誦,當(dāng)然也包括詩(shī)和風(fēng),即歌詞和曲調(diào),用于演唱。[1](P136)
樂(lè)歌:有樂(lè)器伴奏之歌或歌唱,亦泛指歌曲。
徒歌:清代納蘭容若《淥水亭雜識(shí)》云:“唯作八音而無(wú)人之歌聲,謂之徒奏。唯人聲而無(wú)八音,謂之徒歌。徒歌曰謠,謂此,非謂民謠也。”[8](P306-307)可見(jiàn),所謂徒歌就是無(wú)樂(lè)器伴奏之歌或歌唱。
樂(lè)詩(shī):入樂(lè)之詩(shī),是清唱還是配樂(lè)唱,不明確、不清楚。
徒詩(shī):不入樂(lè)之詩(shī),亦指無(wú)伴奏之歌或歌唱,與徒歌等同。
《禮記》中之《樂(lè)記》之鄭康成注云:“弦謂鼓琴瑟也。”[9](P1012)《史記》中的 《孔子世家》記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10](P1936)可見(jiàn),春秋末年孔丘亦已不知或不明三百五篇與音樂(lè)之確切關(guān)系。三百五篇孔丘皆弦歌之,周代樂(lè)師之演奏與孔丘之弦歌肯定已不一樣,在孔丘之時(shí)《詩(shī)》究竟怎么演唱亦已不得而知。
《禮記》中之《樂(lè)記》記載:“魏文侯問(wèn)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tīng)古樂(lè),則唯恐臥;聽(tīng)鄭、衛(wèi)之音,則不知倦。敢問(wèn)古樂(lè)之如彼何也?新樂(lè)之如此何也?’子夏對(duì)曰:‘今夫古樂(lè),進(jìn)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huì)守拊、鼓,始奏以文,復(fù)亂以舞,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于是語(yǔ),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lè)之發(fā)也。’”[9](P1013)
《禮記》孫紹周注云: “愚謂旅進(jìn)旅退者,舞也。和正以廣者,聲也。弦,謂琴瑟,堂上之樂(lè)也。笙,堂下之樂(lè)也。笙,以匏為體,而置管于其中。簧,管中金葉,所以鼓動(dòng)而出聲者也,守猶待也。《大師》登歌,先擊拊以令之,是堂上之樂(lè)必待拊而后作也。下管,先鼓蝀以令之,是堂下之樂(lè)必待鼓而后作也。始奏以文,謂樂(lè)始作之時(shí),升歌《清廟》,以明文德也。亂,樂(lè)之終也。復(fù)亂以舞,謂樂(lè)終合舞,舞《大武》以象武功也。”[9](P1013-1014)
《禮記》中之《樂(lè)記》明確記載古樂(lè)始奏以文而復(fù)亂以舞,孫紹周注“始奏以文”乃謂樂(lè)始作之時(shí)升歌《清廟》以明文德。此亦是舞有歌詩(shī)之明證,此即為歌詩(shī)與舞詩(shī)不可分離之明證。《禮記》中之《樂(lè)記》還明確記載演奏古樂(lè)除使用弦樂(lè)器外還使用鼓、笙、匏、簧等樂(lè)器。
《左傳》襄公十六年:“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shī)必類。’齊高厚之詩(shī)不類。”[11](P939)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云: “必類者,一定須與舞相配,而尤重表達(dá)本人思想。”[12](P1027)此足以證明舞有歌詩(shī),即歌詩(shī)與舞詩(shī)不可分離。
《毛詩(shī)》中鄭風(fēng)的《子衿》中之“子寧不嗣音”句之毛傳云:“嗣,習(xí)也。古者教以詩(shī)樂(lè),誦之歌之,弦之舞之。”[13](P314)亦可證明《詩(shī)經(jīng)》可舞、可歌、可弦、可誦,則《毛詩(shī)》絕非歌詩(shī)一種形態(tài),而是可舞、可歌、可弦、可誦四種形態(tài)。
《毛詩(shī)》實(shí)際上已經(jīng)很像后世之詩(shī)歌,既可朗誦,又可歌唱,也可以伴奏伴舞演唱,《毛詩(shī)》絕非是歌詩(shī)一種形態(tài),而是可舞、可歌、可弦、可誦四種形態(tài)。《墨子》中的《公孟》篇記載:“或以不喪之間誦詩(shī)三百,弦詩(shī)三百,歌詩(shī)三百,舞詩(shī)三百。”[14](P705)可證明 《毛詩(shī)》可舞、可歌、可弦、可誦,這說(shuō)明《毛詩(shī)》已經(jīng)脫離了歌詩(shī)之單一形態(tài),已經(jīng)相當(dāng)成熟,故不能僅由“吉甫作誦”即認(rèn)定《崧高》是誦詩(shī),因?yàn)椤睹?shī)》實(shí)際上已經(jīng)脫離了歌詩(shī)或誦詩(shī)之單一形態(tài),《毛詩(shī)》實(shí)際上已經(jīng)相當(dāng)成熟,已經(jīng)很像后世之詩(shī)歌,既可朗誦,又可歌唱,也可以伴奏演唱或伴舞演唱。
《毛詩(shī)》不僅僅是樂(lè)歌或樂(lè)詩(shī),筆者認(rèn)為比較全面的說(shuō)法應(yīng)該是: 《毛詩(shī)》是詩(shī)歌,特指《毛詩(shī)》是與音樂(lè)有關(guān)之詩(shī)歌。詩(shī)歌之起源與音樂(lè)有關(guān),詩(shī)歌發(fā)展到一定之階段與音樂(lè)分離,出現(xiàn)文人創(chuàng)作之純文學(xué)性之詩(shī)歌,但僅僅將此點(diǎn)絕對(duì)化或僅僅停留于此均為謬誤。在出現(xiàn)文人創(chuàng)作之純文學(xué)性之詩(shī)歌之后,詩(shī)歌仍與音樂(lè)有著千絲萬(wàn)縷之聯(lián)系。古典詩(shī)詞的被演唱或被配樂(lè)朗誦,古代文人的詩(shī)詞和革命領(lǐng)袖的詩(shī)詞被譜曲,樂(lè)府、詞、曲之興起,如此等等,均可證明此論點(diǎn)。要之,不論詩(shī)歌如何發(fā)展,詩(shī)歌始終與音樂(lè)有著千絲萬(wàn)縷之聯(lián)系。現(xiàn)存材料只能證明《詩(shī)經(jīng)》與音樂(lè)有關(guān),但具體什么關(guān)系無(wú)法確知。
由此可見(jiàn),《毛詩(shī)》是可舞、可歌、可弦、可誦四種形態(tài),而絕非僅僅是歌詩(shī)一種形態(tài),這說(shuō)明《毛詩(shī)》已經(jīng)脫離了歌詩(shī)之單一形態(tài),已經(jīng)相當(dāng)成熟,很像后世之詩(shī)歌,即可朗誦,又可歌唱,也可以伴奏伴舞演唱。在此種復(fù)雜情況之下而僅言《毛詩(shī)》為歌詩(shī)就是片面的,無(wú)疑也就是錯(cuò)誤的。
[1]李炳海.中國(guó)詩(shī)歌通史·先秦卷[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2.
[2]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匯考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裘錫圭.文字學(xué)概要 [M].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8.
[5]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語(yǔ)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xiàn)代漢語(yǔ)詞典 [Z].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12.
[6]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語(yǔ)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xiàn)代漢語(yǔ)詞典 [Z].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5.
[7]王先謙.詩(shī)三家義集疏 [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7.
[8]納蘭性德.通志堂集 [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8.
[9]孫紹周.禮記集解 [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9.
[10]司馬遷.史記 [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59.
[11]孔穎達(dá).春秋左傳正義 [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
[12]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90.
[13]孔穎達(dá).毛詩(shī)正義 [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
[14]吳毓江.墨子校注 [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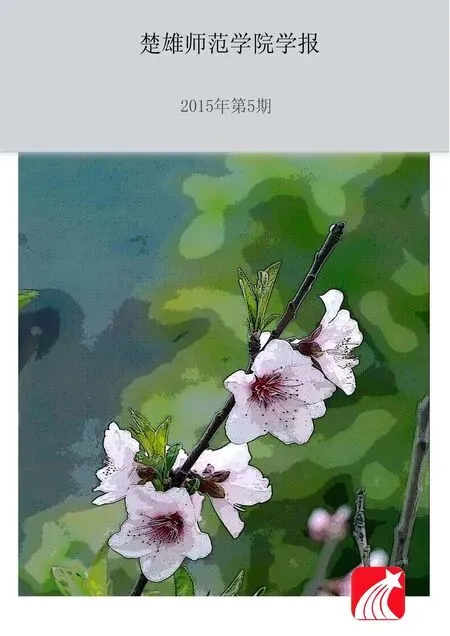 楚雄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5年5期
楚雄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5年5期
- 楚雄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地方本科師范院校應(yīng)用心理學(xué)專業(yè)實(shí)踐課程體系的構(gòu)建*
- 地方本科院校新生大學(xué)英語(yǔ)自主學(xué)習(xí)能力調(diào)查與研究*——以楚雄師范學(xué)院為例
- 中國(guó)傳統(tǒng)書(shū)籍插畫(huà)設(shè)計(jì)風(fēng)格淺析*
- 彝文書(shū)法創(chuàng)作表現(xiàn)方法探析*
- 創(chuàng)新性設(shè)計(jì)思維與創(chuàng)新設(shè)計(jì)思維模式構(gòu)建分析*
- 推進(jìn)MTI 與市場(chǎng)接軌,提升學(xué)生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力*——以云南省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