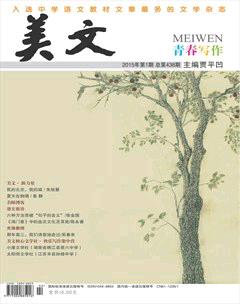《鴻門宴》中的坐次文化及其他
陳永睿
《鴻門宴》中的坐次,雖寥寥數語,卻大有文化。
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
這里是項王設宴。作者不寫宴間的觥籌交錯,而是突出座次排位,有什么深意呢?按照古代人倫禮儀,“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顧炎武《日知錄》)。帝王與臣下相宴時,帝王面南,臣下面北。賓主之間,應是賓客東向,主人西向。在一般宴席的四個方位之中,東向最尊,其次是南向,再次北向,西向是侍坐。在鴻門宴上,劉邦是賓客,項羽是主人,正常坐次應是劉邦東向,項羽南向,張良北向,范增西向。可實際是項羽及其叔父項伯坐在最上位,第二個位置是范增,再次是劉邦,張良是侍坐。鴻門宴上的坐次,首先表明項羽驕橫自大、目中無人、妄自尊大、剛愎自用,甚至把劉邦放在范增的下邊,因而張良也就只配“西向侍”了。其次也表明劉邦在當時情況下能夠以屈求伸,甚至甘居范增下位,主動迎合了項羽的驕傲心理,從而保全了自己,正是他韜光養晦的表現。
這里,司馬遷未曾加一語評論,他只是用白描的筆法記述了宴席的坐次,其含蓄的意思是完全讓讀者自行領會。我們讀書要讀出言外意、弦外音,也就在這樣的地方。而要讀出這層深意,就需要知道一點古代的文化常識。
無獨有偶,《林黛玉進賈府》中也有寥寥數語的坐次文化。
先看黛玉進入榮府,與二舅母等人相見時的情景:
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這正室東邊的三間耳房內。于是老嬤嬤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老嬤嬤們讓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卻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向東邊椅子上坐了。……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房炕上橫設一張炕桌,桌上壘著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著半舊的青緞背引枕。王夫人卻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的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著半舊的彈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攜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
古人在行請安拜見禮或是吃飯時,對坐次、位置也十分講究,如吃飯時對客人應禮讓上座,而客人若很年輕、輩分也小,應推辭坐邊座或下方座,否則就會被人輕視,受人嗤之以鼻。當黛玉去拜見二舅舅賈政時,老嫫嫫讓她炕上坐,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向東邊的椅子上坐了,因為那不是她該坐的。見舅母王夫人時,王夫人本在西邊下首坐著,見了黛玉,便往東讓,黛玉料定這本是賈政之位,再三不肯,“王夫人再四攜她上炕,她方挨王夫人坐了。”可見她年齡雖小,卻十分明白事理,懂得禮貌。
吃飯時,黛玉對坐次的態度,更見出她的“時時在意,步步留心”。
于是,進入后房門,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邊四張空椅,熙鳳忙拉了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你嫂子們不在這里吃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座方上來。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邊丫鬟執著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于案旁布讓。
在中國的飲食禮儀中,坐在哪里非常重要。主座一定是買單的人,主座是指距離門口最遠的正中央位置。主座的對面坐的是邀請人的助理,主賓和副主賓分別坐在邀請人的右側和左側,位居第三位,第四位的客人分別坐在助理的右側和左側,讓邀請人和客人面對而坐,或讓客人坐在主桌上都算失禮,中國的文化是不讓客人感到緊張。
中國人傳統上用八仙桌。對門為上,兩邊為偏座。請客時,年長者、主賓或地位高的人坐上座,男女主人或陪客者坐下座,其余客人按順序坐偏座。在中國,左為尊,右為次;上為尊,下為次;中為尊,偏為次。而在西方,右為尊,左為次。
邀請人可以指定客人的座位,自己的部下或晚輩也可被安排在比自己更重要的位置上,通過分配座位,中國人暗示誰對自己最重要。
林黛玉在賈母的要求下,在鳳姐的強“拉”下,十分推讓不得,才以“客”的身份,坐了“客”座的首位——左邊第一張椅上,“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即分別坐了第二座、第三座、第四座,真的是禮法井然,尊卑分明。
同樣是寫坐次,兩本巨著貌似閑筆多“扯”了一點細節,實際上,我們從中不僅看出了“古代文化”,也看到了“人物修養”,對照現在的實際,還看出了當今年輕人文化素養的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