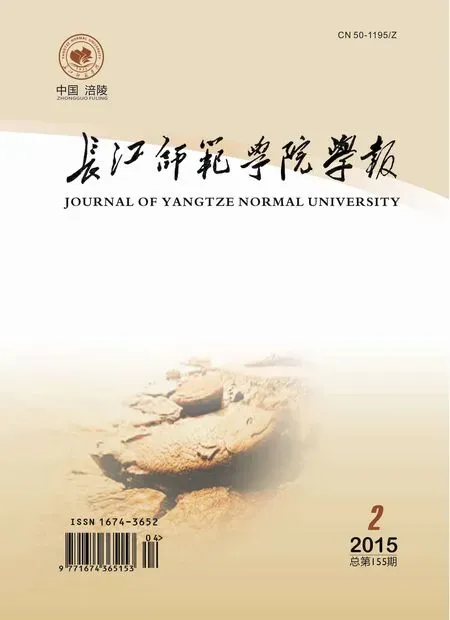關于詩歌“運動”的內在觀照
關于詩歌“運動”的內在觀照
韋文韜
(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重慶400715)
[摘要]自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盛行以來,詩歌研究已經真正的從外部研究進入到內部研究。詩歌“運動”當屬內部研究的范疇。然而這種內部研究僅僅停留在具體的幾個抽象概念之間的關系上,無法取得一個統一的整體。事實上,詩歌總是處于不斷持續運動的過程中,并且由各個成份之間相互交錯而產生詩意。這種詩意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指向和轉換方式,兩者構成了詩歌內在的運動狀態。
[關鍵詞]“鐘表”結構;回旋;隱含;轉換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652(2015)02-0094-04
[收稿日期]2014-12-20
[作者簡介]韋文韜,男(壯族),廣西羅城人。主要從事文學詩歌研究。
一、引言
藝術首先存在一個結構,它通常貫穿著藝術家們的主體創造意識,尤其在“新批評派”看來,是作為一種本質性的存在而區別于其他種類的藝術。很難想象一個沒有結構的藝術存在,即便是解構理論的開創者雅克·德里達也認為:“即使在今天,無中心的結構的想法,也是不可思議的……結構的中心通過引導和組織該結構的內在一致性,會允許其構成成分在總體形勢的內部自由嬉戲。”[1]然而結構內部是如何嬉戲的?這是詩歌內部研究面臨的根本問題。自20世紀初俄國形式主義文學研究伊始,詩歌研究就已經真正地從外部研究進入到內部研究。但俄國形式主義批評仍局限于語音、格律和節奏等韻律層面,直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英美新批評”,詩歌的內部研究才算深入到一個全新的境界,詩歌由此也被更多人視為一種“勢能”或“動能”。新批評更著重的是詩歌的整體結構、符號代碼的深層意義及其各個成分之間的相互關系。布魯克斯在《精致的翁》中就以“結構”區分了各個詩人的不同。他認為結構不僅僅是一個外殼,更是一種意義、評價和闡釋,在他的結構觀里包含著“運動”所產生的無限意義。瑞查茲著意于詩人在心理上對詩歌中對立統一事物的調和,在他首先強調詩歌中存在著相互干擾、相互沖突又相互獨立的各種組織,而后詩人加以平衡,生成整體協和的效果。瑞查茲的弟子燕卜蓀繼續發展了老師的“對立統一”之說,強調詩意含混、模糊,實際上和泰特的“張力”如出一轍。只不過“張力”更在意的是詩意的產生,而“含混”則限于“能指和所指”的關系。作為詩歌內部研究的領軍人物,蘭色姆似乎有些另類,他更重視的是肌質。肌質就是細節,可以充實構架,比結構更為重要,實際上這是推崇“運動”。溫特斯最為具體地闡釋結構,他甚至將詩歌分為六種結構法,其中反復法、邏輯法和質的推進,都是內在變換的體現。綜觀他們的詩歌觀,顯然都將詩歌看作一種戲劇化的運動,但遺憾的是這些研究卻又自我封閉,孤立獨行,缺乏整合,失去了方向性,無法構成一種更為有效的詩意運動狀態。盡管如此,從各家詩論中,我們仍不時可窺視到詩歌運動的大概輪廓,觸摸出詩意的運行指向及轉換原則。實際上,早在古希臘的赫拉克利特就已經提出了詩意的“對立統一”說,到柯勒律治開始,詩歌便有了具體的運行方向。美國漢學家奚密則以“環形結構”來探討了現代詩歌內部運動的某一回旋特征,中國老一輩詩人成仿吾、穆木天、鄭敏等也很具體地論析了詩歌的整個轉換過程。綜合這些觀點,我們認為可以用詩歌的“鐘表結構”來對詩歌的詩意運動問題作一次試探性的觀照。
“鐘表結構”的概念,不是沿襲他者的概念,而是我們為了下面探討之需要所預設的一個機械時間。自
然而然,“鐘表”是通常意義下的指涉時間的圓形器具,同時圓形器具中含有秒針、分針和時針的相互牽制。用“鐘表結構”來解釋詩歌結構不是為了設立一個普遍性原則,而是尋找如弗里德里希所說的“不同的共同之處”。自然,“鐘表結構”要涵蓋以下兩個層面的意思:
二、鐘表中的“環形結構”
所謂“環形結構”是指詩歌運動的情感指向。詩人在創作時的情感處于不斷的回旋往復之中,以開端感受為旨歸,從而不斷地推移、深化,在詩末悄然完成了詩意的轉換和整體性意義的升華。
奚密認為,“所謂環形結構,就是情感的回旋,是開端與結尾的意象和母題的重現。這種意象和母題在他處不曾出現過。”[2]這種結構上的認識對詩歌的創造來說有失偏頗。偏頗之處何在呢?他是把“意象和母題的重現”等同于“情感的回旋”。他首先是從表象的字面意義上去推斷詩歌的情感流程。照此假設,如果首尾沒有相同的“意象和母題”,詩歌就沒有“情感回旋”了?而從詩歌藝術創作的過程來看,始終都存在情感上的回旋。如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此詩同樣出現了情感的回旋情形,即最后一句又回到了“河流”的中心,以“河流”為主體意象將首尾情感對照升華,很多古詩(尤其好詩)都如此。實際上,即使出現了相同的“意象和母題”,這個尾部的“意象和母題”也不是和首段的“意象和母題”意義簡單重復,而是情感回旋加強了,“意義”變化了。柯勒律治認為,“一切記敘文字,甚至所有詩篇,……在訴諸我們的領悟時,應呈現出破方為圓的運動,即環形運動。”所謂“破方為圓”,是指在閱讀過程中,從個別具體的事物中體會到永恒的思想。這種永恒的思想一開始將主客觀統一起來,最后呈現出回旋的狀態。
情感上的回旋結構,首先就關涉到詩意的轉換和統一的問題。這種統一是思想的本質意義,它代表一種對世界的看法和態度。早在20世紀初的穆木天就在他的《談詩——至沫若的一封信》中說到:“我主張,一首詩是表一個思想。一首詩的內容是表現一個思想的內容。”[3]他進而從內在的聯系上說明:“一個有統一性的詩,是一個統一性的心情的反映,是內生活的象征。心情流動的內生活是動轉的,而他們的流動動轉是有秩序的,是有持續的,所以它們的象征也是有持續的。一首詩是先驗狀態的持續的律動。”[4]穆木天至少告訴我們,詩意是統一完整并且是持續流動的。統一完整必然會涉及到首尾情感的回旋對應等。也就是說,開端往往涉及到在何種程度上何種時空里可能會產生具有代表詩歌意圖的詩意,依著這種詩意,詩意的推移才有目標和動力。“新批評”派的領軍人物蘭色姆認為,“如果第一個短句出語不凡,引人注目,我們可能馬上就會根據短句文法所提供的線索,將一部分注意力轉移到一個臨時建立起來的語境上去……我們發現它和其它更多的短句在語法上相互聯系,使語境得到不斷的拓展。”[5]如“移舟泊煙渚”,只有在移舟、泊煙渚的時候,才有最大的產生詩意的可能性。尾聯“江清月近人”既銜接了“野曠天低樹”所升華起來的感覺,又轉回到首聯的真實的情感之中:孤獨寂寞,無依無靠。情感回旋,詩意才能統一完整,才能如司空圖所認為的“超以象外,得其圜中”。鄭敏認為“有了最后一段的升華,開端那些平淡的都有了感情。”[6]鄭敏暗示了開端的詩意設置是在尾聯的一定的感受程度上產生的詩意,是與詩歌的結尾情感吻合的詩意。假如結尾沒有情感回旋,開端的詩意就變成了脫韁之馬。
情感的回旋實在是創作者的需要,如果更深一點說,是“文學邏輯推動力”所致。詩歌的批評很少注意邏輯推動力和內在意義的轉換問題。結構主義批評以及后現代主義批評所談的基本上是“能指和所指”的關系,囿于詩歌中的某一個肌質“張力”,失去了構架。他們避開了詩歌另外一個極為艱難的話題即詩意轉換的話題。實際上,情感的回旋恰好是詩歌邏輯推動的一種表現。正如遠遠而來的海潮,除了浪花,還有那來自海水深處的回環往復的推動力量。叔本華曾在《作為表象和意志的世界》中認為,作為表象的世界是在對立中產生的,要感受到自我,就要從與對立物觸碰的結果中尋找其原因。詩歌總有一個結果,結果總有原因,原因和結果是重合的,他們構成一個整體。所以說,只有情感的回旋,才形成情感物質性的鏈條,造成情感邏輯的推動力,意義才可以轉換升華!至于以不以“相同意象和母題”回旋卻可另當別論。
三、鐘表中的“隱含結構”
鐘表的“環形結構”是要通過鐘表中的“隱含結構”的具體體現來使其最終完成的。而“隱含結構”所包含的是詩歌字面意思隱含的意義及其轉換方式。正如秒針、分針、時針一樣,秒針的轉動并不代表真正的
時間,而是代表一種情感的符號,真正隱含在背后的是分針和時針。如果說秒針是主客體的錯落演變,分針則是段落的推進,而時針才是真正的詩意體現者。在三者之間的關系位置上來說,秒針是變化不定的變形詞,推動著段落的意義的形成,段落的意義的形成又不斷地穿透了整個詩意的產生。成仿吾認為詩歌里有一種“暗示的推移”,艾青更為具體地認為“詩都是從抽象到具體,具體到具體之間的一個推移,一個跳躍,一個轉化,一個飛翔。”[7]他們的詩觀實際上和新批評理論的“張力”“含混”“曲線”殊途同歸,指向了隱含結構里的詩意產生和運動狀態。
(一)秒針的變幻莫測
在詩歌的結構元素中,如同秒針速轉不斷的詞語,涵蓋了地點、人物、事件、景物等等元素。這些元素的不同組合,構成了詩歌的內在情感流動。
1.主體“我”的參與。20世紀中國現代詩歌多有“我”的出現。“我”就是“自我表現”。自我表現可以達到感覺,進而達到感受,這是詩意產生的基礎。由于主體“我”的參與,往往會造成時空錯置。而時空錯置又極易造成情感的抑揚頓挫。或者可以這么說,尤其是在抒情詩中,主體“我”帶動了情感的跨越,接通了因異時異地情感變化所帶來的阻拒感。首先,由于“我”的主動參與,可以直接地進入到詩歌的情感本質當中,導引著詩意的律動及其脈絡,并在轉換詩意的時候,“我”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實際上,“我”是無處不在的。尤其是在浪漫主義詩人群里,“我”就是詩意的導火線,很直接地、通俗地將詩歌傳播到社會群眾當中。其次,“新批評”的理查茲認為“我”可以起到平衡詩歌中相互矛盾的事物的作用,帶有更多的主觀心理傾向。例如余光中的《當我死時》: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張大陸/……/從前,一個中國的青年曾經/在冰凍的密西根向西瞭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國的黎明/用十七年未饜中國的眼睛/饕餮地圖,從西湖到太湖/到多鷓鴣的重慶,代替回鄉。“我”掌控了整個詩意的節奏。“我”改變了時間和空間。從“從前,一個中國青年……”開始,詩意便轉換得令讀者回想到整個過去的時間,詩人是如何苦苦地望穿黑夜思念大陸的,也突然理解了我對未來的“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的各種幻想。同時,“我”可以通過調和,最后抵消這種矛盾的心理反差。
2.客體的貫穿。20世紀后,世界呈現出不穩定、對立的特征,意識處于失序狀態,詩歌意識也潛移默化。但在形式上基本落于“客體的貫穿”。“客體的貫穿”意味著主體的漸漸消隱。主體的消隱不等于主體的退場。主客體在任何時候都是一體的,只是當生活變得千頭萬緒,令人眼花繚亂的時候,主觀不得不稍微讓與客觀,詩人不得不小心深入,重新觀察生活的細微變化。越是細微的變化,可能越是穿越了人的內心。于是,碎片、反常、非邏輯、不對等、晦澀等現代詩歌藝術有意導向著讀者的閱讀。實際上,這是從“自我表現”到“客體的貫穿”,是從“外部世界”進入了“心理世界”。回到個人的內心,這是詩歌更真實的體現。看似顛覆了整體統一,但是并沒有真正地丟掉有“意味”的形式。尤為出現一個普遍的現象是弗里德里希所說的:“現實世界的貶值。……,現實世界破碎成個單像,被描寫出來,取代了某個整體的位置。……,通過實物和風景讓一個與人近似的靈魂說話的中介抒情詩幾乎不再出現。”[8]各種各樣的詩歌形態相依并存,而且越來越成熟壯大。而中國古代的大多數詩歌也都是客體的貫穿,詩言情、言志都落于客觀景物的描繪之中,這種“客體的貫穿”和現代詩歌稍有不同,即很少內心曲折微妙的變化,很難深入內心的綿緲之處,反而是外在志趣情感的普遍抒情,詩意常常被稀釋為一種情趣、釋然。
(二)分針的順序推進
分針可以定義為“段落”和“分層”的意思。有些詩歌有好幾個段落,沒有段落也會有好幾個層次,它們各含的意思相互映襯、對比,從而順利地推動了詩意的轉換。分針和秒針的區別在于秒針是勻速奔跑性的,而分針是定點跳躍性的。分針和秒針又具有非同一般的聯系。秒針的勻速奔跑帶動了分針的定點跳躍,它們的共同的方向是往前。詩歌亦然,許多詞語的并列組合完成了段落的意思,并同時推動著段落的轉換。巴甫洛夫說:“詞,由于成年人過去的全部生活是與那些達到大腦半球的一切外來刺激或內起的刺激物相聯系著……因而詞也隨時能引起那些刺激所制約的有機體的行為和反應。”[9]語詞這種引起了人們內心情緒變化和行為反應的能力,直覺地帶動了聲音、色彩及其嗅覺的各種組合,使人感受到了詩意段落的進程。正如艾青的詩:《樹》:一棵樹/一棵樹/彼此孤離地兀立著/風與空氣/告訴著它們的距離/但是在泥土的覆蓋下
/它們的根生長著/在看不見的深處/它們把根須糾纏在一起。整首詩只有兩段,但是卻用了對比的轉換手法。第一段用了四行表達了樹孤立地兀立著。從“一棵樹,一棵樹”和“風與空氣告訴……”可以看出,它們有著真正的距離。第二段用“但是”轉換到了泥土下,實際上是深化了“樹”的思想,使“樹”具有了生命的力感。這種推進的敘述正如鄭敏的“展開式的結構”里所說的“詩歌結構有些像我國傳統的庭院房屋,通過一進到二進、三進、四進……一直到后花園;又像我國的廟宇、寺院,從第一個大殿到第二個大殿、第三個大殿……當你讀這種展開式的詩時,你的驚訝可以說是一步步加深加大,也可能是對前面幾個大殿的陳列感到平淡、一般。但突然,在你跨進最后一個大殿時,你猛然發現眼前是一尊極美的如來坐像,……好像將你引入了一個深博的智慧的世界。”[10]在“新批評”的文本研究中,溫特斯同樣用“邏輯法”來表明,從一個細節到一個細節,邏輯推進脈絡分明,各個環節間的順序推進最為關鍵。所以說,不同詞語的組合,可以推動層次意思的轉換。
(三)時針的靜態映現
時針其實是動的,但是表面看來卻總是靜態的。因為靜態,所以我們總是能夠看到它的存在。我們一般會忽視了秒針和分針,直接地捕捉到跟我們現實有關的明確的時間的東西。人類的語言最終指向的跟時針一樣有意義。就算日常語言,總是直接或者暗含著另外一層意思,那就是所謂的詩意。生活通常要求我們領會這樣的詩意,仿佛生活通常要求我們明白一個準確的時間。當然,詩歌的詩意要高于生活的詩意。生活的詩意更多的在于情趣,而詩歌的詩意除情趣之外,更多的在于個人的感受和生存的況味的體現。朱光潛在《詩的境界——情趣與意象》說:“詩與實際的人生世相之關系,妙處惟在不即不離。惟其‘不離’,所以有真實感,惟其‘不即’,所以新鮮有趣。”[11]例如舒婷的《神女峰》,首先讓我們看到的是一些詞語的重組,但最終要知道的卻是“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肩頭痛哭一晚。”如何理解這詩句的意思?那是憑著生活的經驗無法得到解釋的,因為這里暗含的意思比日常語言更深遠,要通過前邊的詩的語言來加以理解方能夠明白。正如蘇珊·朗格在《情感與形式》里說:“運動在邏輯上與線性形式有關;而且,在線條連續、支承的圖形又傾向給它以方向的地方,人們對它的感知就充滿了動的概念,體現了抽象的趨向原則。”[12]
詩歌中的“秒針”“分針”和“時針”的互相牽制,推動了詩意的有序變化。至于讀者看到“不同時候的不同時間點”,那正好說明了詩歌作為藝術的一種開放性、超越性。盡管這里面意思多變,內容深晦,但詩意是往前推進,并且是統一有序的。盡管在現代詩歌藝術結構中,似乎出現了混亂、變動不居、碎片化、滑稽、不對等、非邏輯等等不統一現象,這里面仍然暗含了作者有意味的形式,是無序中的“有序”。蘭波就曾經在紙上反復修正他的作品,這一點,應該是有目共睹的。因此,鐘表中的“環形結構”和鐘表中的“隱含結構”這兩種結構的統一構成了詩歌的“鐘表結構”,也就構成了所謂的詩歌運動的整體的動態的結構。
參考文獻:
[1] [法]德里達.最新西方文論選[C].王逢振,等,編;李自修,譯.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133.
[2] [美]奚密.現代漢詩[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31.
[3][4]楊匡漢,劉福春.中國現代詩論(上冊)[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5:387、349.
[5] [美]約翰·克勞·蘭色姆.新批評[M].王臘寶,張哲,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165.
[6][10]鄭敏.結構·解構視角·語言文化評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134、251.
[7]艾青.艾青詩論全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49.
[8] [德]胡戈·弗里德里希.現代詩歌的結構[M].李雙志,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184.
[9]李澤厚.美學論集[C].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7.
[11]朱光潛.談美書簡[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210.
[12] [美]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M].劉大基,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78.
[責任編輯:黃志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