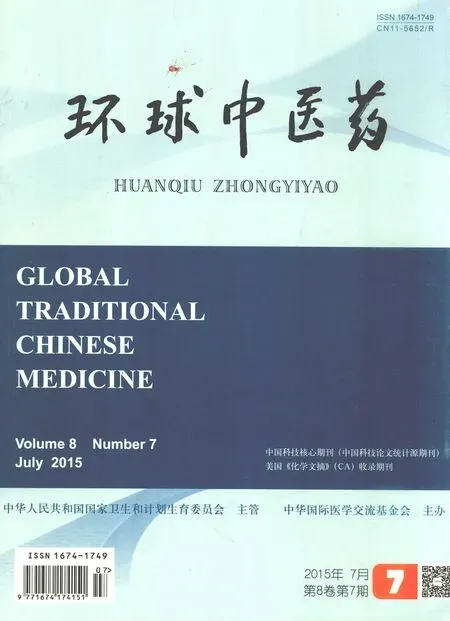天人相應(yīng)是中醫(yī)學(xué)的理論基礎(chǔ)和指導(dǎo)思想
王振海 王蕾
天人相應(yīng)是中醫(yī)學(xué)的理論基礎(chǔ)和指導(dǎo)思想
王振海 王蕾
針對(duì)有關(guān)中醫(yī)學(xué)的理論基礎(chǔ)和指導(dǎo)思想存在著“天人相應(yīng)”“天人合一”和“整體觀”表述上的混亂,從“天人相應(yīng)”一語的語源,“天人相應(yīng)”與“天人合一”的聯(lián)系與區(qū)別,“天人相應(yīng)”與整體觀,新老中醫(yī)藥專家學(xué)者的論證,現(xiàn)代科學(xué)的研究,及便于當(dāng)代理解、把握和傳承、交流等幾個(gè)方面出發(fā),認(rèn)為應(yīng)把中醫(yī)學(xué)的理論基礎(chǔ)和指導(dǎo)思想表述為“天人相應(yīng)”思想。
中醫(yī)藥學(xué); 理論基礎(chǔ); 天人相應(yīng); 天人合一; 天人相分; 黃帝內(nèi)經(jīng); 整體觀
有關(guān)中醫(yī)學(xué)的理論基礎(chǔ)和指導(dǎo)思想,存在著“整體觀”“天人相應(yīng)”和“天人合一”表述上的混亂。表述上的不一致,反映了理論上的不明確。而理論上的不明確,必然導(dǎo)致人們對(duì)中醫(yī)認(rèn)識(shí)理解上的困惑。筆者認(rèn)為,應(yīng)把中醫(yī)學(xué)的理論基礎(chǔ)和指導(dǎo)思想表述為天人相應(yīng)思想。
1 天人相應(yīng)的語源
《黃帝內(nèi)經(jīng)》沒有明確記載“天人合一”一詞,而是從生命和醫(yī)學(xué)角度擇取、倡導(dǎo)了“人與日月相應(yīng)”“人與天地相參”的天人相應(yīng)思想,“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經(jīng)歷了“應(yīng)于人”“驗(yàn)于今”的實(shí)踐檢驗(yàn),從而為中醫(yī)學(xué)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理論基礎(chǔ)。
2 天人相應(yīng)與天人合一的聯(lián)系與區(qū)別
2.1 對(duì)“天”的含義不同
天人合一說的天,有多重含義,眾說紛紜。有一義說,認(rèn)為“天”即大自然(季羨林);二義說,認(rèn)為“天”一指有意志的天神,一指自然的天體(王明);三義說,以張岱年、宋志明為代表,張岱年認(rèn)為“天”一指最高主宰,二指廣大自然,三指最高原理。宋志明說“天有主宰、自然、義理三種涵義”;四義說,認(rèn)為“天”指意志之天、無為之天、道德之天、自然之天(康中乾);五義說,以馮友蘭、任繼愈為代表,馮友蘭認(rèn)為“天”有五義:物質(zhì)之天、主宰之天、運(yùn)命之天、自然之天、義理之天。任繼愈也主張“天”有五義:主宰之天、運(yùn)命之天、義理之天、自然之天、人格之天;六義說:天地之天、自然之天、皇天之天、天命之天、天道之天、天理之天(傅偉勛);混沌說,認(rèn)為“天”是一個(gè)混沌概念,神、本體、本原、自然、必然、命運(yùn)、心性等均在其中(劉澤華),林俊義則根據(jù)歷史順序,抽出天有人格神,天象或氣象及其規(guī)律(天道)、天命、自然、天然、天志,群物之祖,天理、天性、天心、天氣和宇宙空間等12種涵義[1]。
而《黃帝內(nèi)經(jīng)》中的天不止包含天象、天氣、氣候等,也包含了“地”和環(huán)境中的各種因素;既包含直接的“象”,也包含“象”后面所蘊(yùn)含的“道”——變化的規(guī)律,既有“形而下”的,也有“形而上”的[2]。也就是說不但包含產(chǎn)生人和對(duì)人發(fā)生影響的自然之天,也包含了人事社會(huì)之天。《上經(jīng)》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zhǎng)久……”(《素問·氣交變大論》),人事與天地并列,屬于社會(huì)意義的天。中醫(yī)學(xué)很早就注意到人的社會(huì)屬性,認(rèn)為社會(huì)環(huán)境的優(yōu)劣或劇烈變化等因素會(huì)影響到人體健康,從而把人事社會(huì)之天與天地自然之天并列。《素問·移精變氣論和湯液醪醴論》中,岐伯在回答古人和今世療效的差別問題時(shí),就強(qiáng)調(diào)這是社會(huì)之天變了,生活條件和生活方式變了,病情也和古人不一樣,所以治療方法也隨著發(fā)生變化而療效還不滿意。《素問·陰陽應(yīng)象大論》在談到“生乃不固”的兩個(gè)原因時(shí),就指出一是自然之天的方面,一是社會(huì)之天——人的方面,“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喜怒不節(jié),寒暑過度,生乃不固”,因此在診治過程中不要忽略“故貴脫勢(shì)”“始貴后貧”的社會(huì)因素。
2.2 對(duì)“人”的含義有別
“人”的涵義既指單個(gè)的人,也指整體的人。天人合一說的“人”不是指普通的平民大眾,而是大人、君子,如《周易·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荀子·五制》“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禮天地”。《黃帝內(nèi)經(jīng)》中的“人”是不帶任何社會(huì)屬性的全體,是普遍意義上的人的總體,全書對(duì)人使用的是“民”“萬民”“百姓”“眾子”這樣的概念[3]。
2.3 目的不同
天人合一主要目的不在于關(guān)注自然界的規(guī)律,而是為尋求現(xiàn)實(shí)世界的道德原則和人類政治生活的普遍原則,尋求政治存在的意義,是指君主要遵守天道,效法天道,體道而治。如《呂氏春秋·圜道》“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主執(zhí)圜,臣執(zhí)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
《黃帝內(nèi)經(jīng)》天人相應(yīng)思想的目的是為了尋求掌握自然規(guī)律以及研究天人相應(yīng)規(guī)律和運(yùn)用天人相應(yīng)規(guī)律為人類健康服務(wù),為人類尋找更適當(dāng)?shù)纳嫔罘绞胶头乐渭膊〉脑瓌t與方法。《素問·金匱真言論》指出“所以欲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者何也?為冬病在陰,夏病在陽,……皆視其所在,為施針石也”,《素問·陰陽應(yīng)象大論》更指出“故治不法天之紀(jì),不用地之理,則災(zāi)害至矣”。
2.4 內(nèi)涵不同
古人對(duì)天人關(guān)系的探索經(jīng)歷了漫長(zhǎng)的歷程,“天人合一”包含了諸如“天人合德”“天人相分”“天人相通”“天人感應(yīng)”“天人相應(yīng)”“天人不相預(yù)”“天人交相勝”“天人合一”“天人同性”“天人同體”“天人同類”“天人一氣”“天人一心”“天人一理”等多種學(xué)說,概括起來可歸約為“天人相分”“天人相應(yīng)”“天人合一”三類。“天人合一”觀念,其本義并非直接討論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雖然“天人合一”的理論也涉及人與自然生態(tài)的關(guān)系,但這種關(guān)系是以政治、倫理和精神境界為本位的。“天人合一”理論所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更多體現(xiàn)在其社會(huì)、政治、道德、倫理、價(jià)值、認(rèn)識(shí)論、人格修養(yǎng)方面的意義[4]。“夫禮,天之經(jīng),地之義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誠者天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中庸·十九章》),天人合一說把禮、性、德、誠提高到天的地位,然后反過來要人去合天,只是為了說明人類社會(huì)道德原則的客觀性、天道性。
面對(duì)天人關(guān)系的諸多提法,《黃帝內(nèi)經(jīng)》從生命和醫(yī)學(xué)角度擇取、倡導(dǎo)并發(fā)揮了“人與日月相應(yīng)”“人與天地相參”的天人相應(yīng)思想。天人相應(yīng)思想既承認(rèn)天與人的區(qū)別,又承認(rèn)天與人的聯(lián)系,同時(shí)還認(rèn)為“‘參’是相互的,人法天地而也可以參贊造化”[5]。天的變化影響著人,人又通過自身的活動(dòng)影響著天[6]。既包含了“天人相分”區(qū)分主客的內(nèi)涵,而不致聽其走向片面和極端;另一方面又把“天人合一”所體現(xiàn)的社會(huì)、政治、道德、倫理、價(jià)值、認(rèn)識(shí)論、人格修養(yǎng)方面的意義及孜孜以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包攝在天人相應(yīng)思想中而不致使其流于玄遠(yuǎn)。
天人合一追求的是最高精神境界,天人相應(yīng)注重的是客觀自然規(guī)律。天人合一反映的是理想狀態(tài),天人相應(yīng)反映的是現(xiàn)實(shí)狀態(tài)。因此,“天人相應(yīng)”顯然要比“天人合一”更明白更確切地反映了天人關(guān)系。
2.5 《黃帝內(nèi)經(jīng)》繼承發(fā)展了天人相應(yīng)相參思想
天人相應(yīng)相參說在先秦諸子著作中是零散的,范蠡、子思、荀子都提到了天人相參相應(yīng),但都沒有展開論述,形成系統(tǒng)。如“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后可以成功”(《左傳·國語》);“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第二十一章》);“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禮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荀子·五制》);“天行,有常……故應(yīng)之以治則吉,應(yīng)之以亂則兇”(《荀子·天論》)。
面對(duì)天人關(guān)系的諸多提法,《黃帝內(nèi)經(jīng)》注重的不是抽象的論辯,而是如何運(yùn)用天人相應(yīng)思想處理實(shí)際問題。《黃帝內(nèi)經(jīng)》繼承發(fā)展了天人相應(yīng)相參思想,并將之系統(tǒng)化。《黃帝內(nèi)經(jīng)》以天人相應(yīng)相參思想為指導(dǎo),融匯諸子各家學(xué)說,對(duì)成書之前的醫(yī)學(xué)資料和各家學(xué)說進(jìn)行了全面整理和繼承,構(gòu)建了一個(gè)貫通天地人的理論體系。
3 天人相應(yīng)與整體觀
對(duì)中醫(yī)學(xué)理論體系的理解,長(zhǎng)期以來一般是以整體觀和辨證論治來加以概括。這顯然難以涵蓋和體現(xiàn)這一體系的豐富內(nèi)涵、內(nèi)在聯(lián)系及其特色,也就難以具體有效地指導(dǎo)臨床、科研和教學(xué)[7]。
通常認(rèn)為,一個(gè)科學(xué)理論體系,起碼包括作為體系基本元素的基本概念,和聯(lián)系這些基本概念的基本關(guān)系做出的推論。天人相應(yīng)理論的基本概念就是“天”“人”。“人”包括個(gè)體的人和群體的人。人類生活在地球上,吃穿行住產(chǎn)生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及社會(huì)環(huán)境與自然環(huán)境構(gòu)成了從單個(gè)人到群體人生活在其中的天。每個(gè)人對(duì)他自己來說是人,相對(duì)于另一個(gè)人來講又屬于天。毫無疑問,人作為一個(gè)獨(dú)立的實(shí)體,有著自己生命運(yùn)動(dòng)變化的軌跡,但人是“天”的產(chǎn)物和組成部分,所以生命運(yùn)動(dòng)變化的軌跡必然要服從、受控于“天”運(yùn)動(dòng)變化的規(guī)律。天的變化產(chǎn)生和影響著人,人又通過自身的活動(dòng)影響著天,天人之間相互作用,人天相應(yīng),這就是天人之間的基本關(guān)系[6]。可以看出,中醫(yī)整體觀主要包括的三個(gè)方面:人體本身是一個(gè)有機(jī)整體;人與自然環(huán)境是一個(gè)有機(jī)整體;人與社會(huì)環(huán)境是一個(gè)有機(jī)整體,歸根到底依然是“天”(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huì)環(huán)境)“人”兩個(gè)概念,也就自然而然包括在天人相應(yīng)思想理論中。事實(shí)上,中醫(yī)整體觀就是從《黃帝內(nèi)經(jīng)》關(guān)于天人相應(yīng)的論述中概括出來的,是建立在天人相應(yīng)思想方法基礎(chǔ)上的。
天人相應(yīng)思想理論提供了天人相應(yīng)的思想方法[8]。醫(yī)學(xué)就是伴隨著對(duì)天的認(rèn)識(shí)、對(duì)人的認(rèn)識(shí)和對(duì)天人關(guān)系的認(rèn)識(shí)而發(fā)展的。天人相應(yīng)思想方法不僅指導(dǎo)古人創(chuàng)建了中醫(yī)理論體系,同樣可以指導(dǎo)今人,像復(fù)雜性理論、系統(tǒng)論、控制論、模糊理論、信息論、全息論、協(xié)同論就可以運(yùn)用于醫(yī)學(xué)領(lǐng)域,用來闡明對(duì)人的認(rèn)識(shí)。同樣,自然科學(xué)的方法、社會(huì)科學(xué)的方法、數(shù)學(xué)的方法、觀察的方法、實(shí)驗(yàn)的方法、邏輯的方法、猜想的方法、理性思維的方法、非理性思維的方法等,都可以用來研究人及其健康與疾病問題。顯而易見,天人相應(yīng)方法論不僅包含了整體觀的方法,還包含了其它方法,從而體現(xiàn)出開放性、包容性和與時(shí)消息性。
4 新老中醫(yī)藥專家學(xué)者的論證
老一代中醫(yī)藥專家早就指出了天人相應(yīng)思想在中醫(yī)學(xué)中的理論基礎(chǔ)地位這個(gè)問題。“氣或精氣學(xué)說,陰陽學(xué)說,都以天人相應(yīng)思想為基礎(chǔ)”(岳美中),天人相應(yīng)思想是“中醫(yī)學(xué)理論的淵源所在”,是“貫穿整個(gè)《內(nèi)經(jīng)》的指導(dǎo)思想”(方藥中),是《內(nèi)經(jīng)》理論的精髓,“中醫(yī)學(xué)中的陰陽學(xué)說、五行學(xué)說、藏象學(xué)說、經(jīng)絡(luò)學(xué)說、精氣神學(xué)說、運(yùn)氣學(xué)說等,幾乎無不根據(jù)天人相參的原理而闡明其所具有的規(guī)律性”(裘沛然),是“貫穿整個(gè)中醫(yī)學(xué)理論和臨床的最核心、最根本的思想”(陸干甫、謝永新)。新一代中醫(yī)藥學(xué)者通過對(duì)《內(nèi)經(jīng)》及其時(shí)代,對(duì)中醫(yī)基礎(chǔ)理論,對(duì)天人相應(yīng)思想的深入研究,進(jìn)一步明確了《內(nèi)經(jīng)》體系的最重要的邏輯起點(diǎn)是天人相應(yīng),《內(nèi)經(jīng)》體系,主要是天人相應(yīng)的體系[9]。中醫(yī)理論要還其本原——人與天地相參[10],認(rèn)為天人相應(yīng)思想不僅僅是傳統(tǒng)中醫(yī)學(xué)的理論基礎(chǔ),也應(yīng)該成為現(xiàn)代醫(yī)學(xué)的理論基礎(chǔ)[6]。
5 現(xiàn)代科學(xué)的研究
一種生物生存在什么條件下,是環(huán)境因子綜合作用的結(jié)果,也是生物適應(yīng)的結(jié)果,生物的進(jìn)化過程也就是天人相應(yīng)的過程。從人類基因組計(jì)劃到克隆羊,從生態(tài)學(xué)到微生態(tài)學(xué),從宇宙飛船載人航天飛行到蛟龍?zhí)柹顫摚烊讼鄳?yīng)思想經(jīng)過了現(xiàn)代科學(xué)從宏觀、中觀、微觀以至宇觀的檢驗(yàn),證明了天人相應(yīng)的正確性和科學(xué)性[6,8,11-13]。天人相應(yīng)不僅是中醫(yī)學(xué)關(guān)于天人關(guān)系的基本看法,而且是生物界的一條基本規(guī)律。要想真正認(rèn)識(shí)人類本身與人類疾病,就必須把人與其生活在其中的天聯(lián)系在一起。因此,把天人相應(yīng)思想作為醫(yī)學(xué)的理論基礎(chǔ),也是邏輯的必然。
6 便于當(dāng)代理解把握和傳承交流
如何完善中醫(yī)學(xué)理論體系的框架結(jié)構(gòu),建立與中醫(yī)學(xué)理論體系的豐富內(nèi)涵相適應(yīng),便于當(dāng)代理解、把握、傳承、交流的理論框架與結(jié)構(gòu),是中醫(yī)學(xué)理論繼承與創(chuàng)新的重要課題[14-15]。而明確了天人相應(yīng)思想的理論基礎(chǔ)地位,就理順了中醫(yī)體系的邏輯結(jié)構(gòu),這就是:用對(duì)天的認(rèn)識(shí)說明對(duì)人的認(rèn)識(shí);用認(rèn)識(shí)天的方法去認(rèn)識(shí)人;從人和天的相互關(guān)系中去研究人;研究天人相應(yīng)規(guī)律和運(yùn)用天人相應(yīng)規(guī)律[8]。同時(shí),也就明確了中醫(yī)體系“道、理、法、術(shù)”四個(gè)層次結(jié)構(gòu)。“道”就是中醫(yī)學(xué)的理論基礎(chǔ)——天人相應(yīng)思想。“理”屬于第二層次——在天人相應(yīng)思想的指導(dǎo)下,綜合對(duì)天的認(rèn)識(shí),對(duì)人的認(rèn)識(shí),形成適用于預(yù)防、診斷、治療各方面的基礎(chǔ)理論,如氣血津液、陰陽五行、升降出入、藏象經(jīng)絡(luò)、寒熱虛實(shí)等。“法”屬于第三層次,是用基礎(chǔ)理論研究具體的天與具體的人相互作用產(chǎn)生相應(yīng)變化的規(guī)律,總結(jié)歸納形成如六淫辨證、傷寒辨證、溫病辨證、雜病辨證、攝生、經(jīng)絡(luò)、以及“汗吐下和溫清消補(bǔ)”等的臨床應(yīng)用理論。“術(shù)”是第四個(gè)層次,就是在以上基礎(chǔ)上產(chǎn)生的對(duì)某一具體病種、證治、藥物、方法提出的具體的理論見解和治療方法,如傷寒護(hù)陽,溫病存陰等。
正因?yàn)橹嗅t(yī)理論是用天人相應(yīng)思想方法建構(gòu)起來的,隨著對(duì)天的認(rèn)識(shí),對(duì)人的認(rèn)識(shí)的發(fā)展和深入,對(duì)養(yǎng)生及疾病防治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的積累和總結(jié),中醫(yī)理論不但可以根據(jù)時(shí)代和需要對(duì)原有理論進(jìn)行部分的修正和改造,補(bǔ)充和發(fā)展,還可以在條件具備的時(shí)候,以現(xiàn)代自然觀、宇宙觀為參照系,用天人相應(yīng)思想方法建構(gòu)起新的理論大廈。也就是說,天人相應(yīng)思想使中醫(yī)理論具備自我更新的內(nèi)動(dòng)力。
天人相應(yīng)思想既為理解、把握和傳承交流中醫(yī)理論提供了方法,也為中醫(yī)走向世界打開了方便之門。筆者相信,只要從天人相應(yīng)思想出發(fā),就如高屋建瓴,一通百通[16],從而應(yīng)對(duì)和解決中醫(yī)學(xué)面臨的困惑、危機(jī)和挑戰(zhàn)。
[1]林俊義.從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中的“天人合一論”,尋覓“自然與人的和諧”[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0,16(9):4-8.
[2]楊光.正確看待“天人相應(yīng)”[N].中國中醫(yī)藥報(bào),2010-05-05(8).
[3]申詠秋,魯兆麟.《黃帝內(nèi)經(jīng)》的醫(yī)學(xué)人文精神探析[J].中國醫(yī)學(xué)倫理學(xué),2006,19(6):108-109.
[4]耿云志.近代文化與儒學(xué)[N].人民日?qǐng)?bào),1988-03-21(5).
[5]裘沛然.裘沛然選集[M].上海:世紀(jì)出版集團(tuán) 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180-184.
[6]淮輝先,王振海.試論天人相應(yīng)思想的科學(xué)性[J].中國醫(yī)藥學(xué)報(bào),1988,3(1):9-13.
[7]許家松.把根留住 繼往開來——中醫(yī)理論現(xiàn)代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之我見[N].中國中醫(yī)藥報(bào),2004-09-13(3).
[8]王振海,淮輝先.從《黃帝內(nèi)經(jīng)》談天人相應(yīng)思想的方法論[J].中國醫(yī)藥學(xué)報(bào),1998,13(3):20-23.
[9]趙洪均.內(nèi)經(jīng)時(shí)代[M].北京:學(xué)苑出版社,2012:293.
[10]張效霞.回歸中醫(yī)——對(duì)中醫(yī)基礎(chǔ)理論的重新認(rèn)識(shí)[M].青島:青島出版社,2006:57.
[11]周鵬,高學(xué)敏,張建軍,等.從中醫(yī)天人相應(yīng)理論看人體太空生理紊亂[J].中華中醫(yī)藥雜志,2008,23(6):472-475.
[12]劉煥蘭,談博.天人相應(yīng)理論的發(fā)展及其意義[J].廣州中醫(yī)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0,27(4):407-410.
[13]熊德鑫.微生態(tài)學(xué)研究的重要意義和實(shí)際應(yīng)用[J].中國微生態(tài)學(xué)雜志,2001,13(5):252-253.
[14]潘桂娟.中醫(yī)學(xué)理論體系框架結(jié)構(gòu)之研討[J].中國中醫(yī)基礎(chǔ)醫(yī)學(xué)雜志,2005,11(7):481-483.
[15]王耘,顏素容,喬延江.中醫(yī)理論建模的天人相應(yīng)形式化方法[J].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9,32(7):437-439.
[16]王振海,王蕾.高屋建瓴 一通百通——關(guān)于天人相應(yīng)思想研究問答[J].按摩與康復(fù)醫(yī)學(xué),2011,27(60):181-183.
“Correspondence of human bod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theory w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guiding ideology of TCM
WANG Zhen-hai,WANG Lei.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No.2 hospital in Handan,Handan 056001,China
WANG Zhen-hai,E-mail:wang_zhenhai@126.com
This paper concluded that“correspondence of human bod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theory w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guiding ide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due to the following reasons:the etymology of“correspondence of human bod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theory,difference and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of“correspondence of human bod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and theory of“man wa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theory of“correspondence of human bod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and holism,demonstrations of young and old Chinese medicine scholars,modern scientific researches,and the convenience in understanding,inheritance and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confusion state of TCM guiding ideology descriptions such as“correspondence of human bod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man wa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and holis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heoretical basis;Correspondence of human bod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Man wa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Separation of nature and man;Inner Canon of Huangdi;Holism
R221
A
10.3969/j.issn.1674-1749.2015.07.012
056001 河北省邯鄲市第二醫(yī)院中醫(yī)科(王振海);河北工程大學(xué)文學(xué)院(王蕾)
王振海(1950- ),大專,副主任醫(yī)師。研究方向:天人相應(yīng)思想理論和中醫(yī)臨床。E-mail:wang_zhenhai@126.com
2015-04-22)
(本文編輯:董歷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