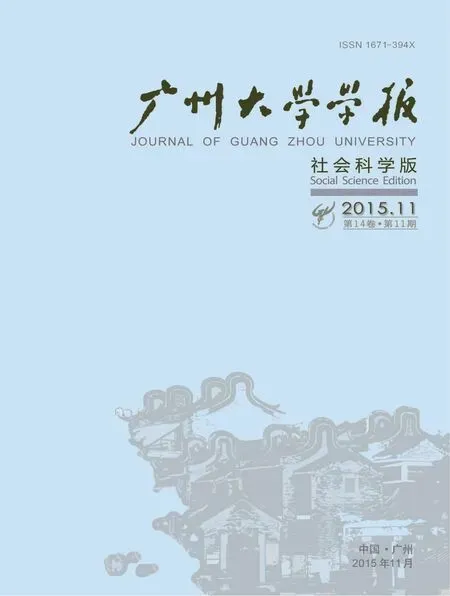稅收法定原則新探
向明華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法學院,廣東 廣州 510420)
一、稅收法定原則面臨的挑戰
稅收法定原則作為一項重要的憲性原則,得到了世界各法治國家的廣泛接受。對于正在走向全面法治的我國,似乎也不應存在任何疑問。①參見張守文《論稅收法定主義》,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6期;饒方《論稅收法定主義原則》,載《稅法研究》1997年第1期;劉劍文、李剛《稅收法律關系新論》,載《法學研究》1999年第4期等。2013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還將“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作為執政黨“推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的一項重要改革任務。然而,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于2014年11月28日、12月12日、2015年1月13日先后聯合發布《關于提高成品油消費稅的通知》《關于進一步提高成品油消費稅的通知》和《關于繼續提高成品油消費稅的通知》,在一個半月內三次提高成品油消費稅的稅率,其中前者中尚有“經國務院批準”的表述,但在后兩者中則無“經國務院批準”。稅率的這種頻繁調整基本上顛覆了人們對我國稅收法定原則的信心和期許。政府部門的這種“任性”再次引發了人們對稅收法定原則的熱切關注。②杜麗娟、許浩《律師質疑提高成品油消費稅程序不當:兩部委越權》,載2014年12月20日《中國經營報》;丁超《45 天內三次提高成品油消費稅合法嗎》,載于http://www.sxdaily.com.cn/n/2015/0126/c350-5611811.html.;黃世楊《云南律師“公開提高成品油消費稅的法律依據”申請獲回復》,載于http://yn.yunnan.cn/html/2015-05/24/content_3743155.htm.訪問時間:2015年5月30日。而財政部樓績偉部長對此的回應是:“三次適當提高了成品油消費稅,有收入上的意義同時也有節能減排方面的意義,它對整體的實體經濟影響是比較小的。”[1]該回應強調了調整稅率的經濟意義,卻回避了大眾關于其合法性的質疑,與我國全面推進法治建設的努力背離。中國稅務學會涂龍力教授對此評價認為:“任何一項稅收基本制度的改革與立法,即便經濟層面縱有千萬條理由,如果決策與立法程序違憲,也難以令民眾滿意,因為這違背了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基本原則。”[2]盡管其后3月15日通過的《立法法》修訂案第8條第6 項明確規定“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可能是為了證明其調整稅率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在其后不到兩個月的時間,2015年5月7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布《關于調整卷煙消費稅的通知》,將“卷煙批發環節從價稅稅率由5%提高至11%”,再次將稅收法定原則的解釋與落實等問題推向輿論中心。[3]相對于專家的理論推演,普通群眾因此往往基于對稅收實踐的感性認識,大多認為稅收法定原則在我國尚未完全確立。如在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稅收法定原則的確立與落實方式等仍然是全社會高度關注的問題,“關于稅收法定原則的實現方式和路徑,有人認為,實現稅收法定越快越好。有人認為,要分步驟推進。”[4]政府稅收權力的“任性”與學界、民間高度疑慮之間的巨大反差,凸顯稅收法定原則在我國遠未形成共識,有必要進一步探討。
二、稅收法定原則發展回顧及啟示
稅收法定原則,又稱稅收法定主義原則、稅收法律主義,既是一種憲性基本原則,也是稅法的最高原則。該原則要求稅法主體的權力與權利、職責與義務,稅法的構成要素,稅法程序等都必須而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確規定。征稅主體必須依且只能依法律的規定征稅;納稅主體依且僅依法律的規定納稅。即“有稅必須有法,未經立法不得征稅”[5],“而法律只能由民選的國會制定,稅的行政與裁判只能依據法律進行。”[6]也有學者提出,稅收法定原則應當涵蓋“征稅”至“用稅”的全程,包括立法機關依法設置稅收、納稅人依法納稅、征稅機關依法征稅、國家依法取得財政收入、國家依法使用財政收入。[7]筆者以為,除此之外,其還應當進一步涵蓋依法監督、依法追責等。
稅收法定原則肇始于英國。早期的君主、國王為籌集戰爭費用或為滿足其奢侈生活,往往巧立名目,肆意征收各種苛捐雜稅。然而稅負一旦危及民眾的正常生機,必然引發民眾的反抗,導致社會動蕩。在抵抗政府捐稅的市民運動中,雙方逐步達成了“無代表則無稅”(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共識,即國家征稅須經國民同意,并應以國民代表會議制定的法律為依據,否則不能征稅。如1215年《英國大憲章》(Great Charter)第12條以肯定方式確認稅收法定,明確規定國王有權征收三種稅。①1215年《英國大憲章》第12條:“除下列三項稅金外,設無全國公意許可,將不征收任何免役稅與貢金,即贖回余等身體時之贖金〔指被俘時〕,策封余等之長子為武士時之費用,余等之長女出嫁時之費用——但以一次為限。且為此三項目的征收之貢金亦務求適當。”第14條和第15條則以否定方式保障稅收法定:其一方面規定,非經“大委員會”的同意不得征稅,即“無代表權不納稅”;另一方面要求征稅應得到王國的一致同意,間接地認可了“全體國民”的“征稅同意權”。②1215年《英國大憲章》第14條:“凡在上述征收范圍之外,余等如欲征收貢金與免役稅,應用加蓋印信之詔書致送各大主教、住持、伯爵與男爵指明時間與地點召集會議,以期獲得全國公意。此項詔書之送達,至少應在開會以前四十日。此外,余等仍應通過執行吏與管家吏普遍召集凡直接領有余等之土地者。召集之緣由應于詔書內載明。召集之后,前項事件應在指定日期依出席者之公意進行,不以缺席人數阻延之。”第15條規定:“自此以往,除為贖還其本人之身體,策封其長子為武士,與一度出嫁其長子以外,余等不得準許任何人向其自由人征取貢金。而為上述目的所征收之貢金數額亦務求合乎情理。”其后英國1627年《權利請愿書》再次明確要求,國王非經國會法案同意,不應強迫任何人征收或繳付任何貢金、貸款、強迫獻金、租稅或類似負擔。通過這些早期的不成文憲法,稅收法定原則在英國基本得到確立。如在對蘇格蘭的戰爭中,英王查理一世為了籌集軍費,在1640年先后兩次召集議會討論增加稅收,不但未能如愿,反而引發了英國內戰,查理一世兵敗后被送上斷頭臺。“光榮革命”勝利后,英國國會制定1689年《權利法案》,其第4條再次明確規定:“凡未經國會準許,借口國王特權,為國王而征收,或為國王使用而征收金錢超出國會準許之時限或方式者,皆當非法。”重申“國王不經國會同意而任意征稅,即為非法”,這標志著近代意義的稅收法定原則正式確立。
在北美,英國為從其殖民地攫取更多財富及支付對法戰爭費用,未經各殖民地同意,先后頒布1765年《印花稅條例》、1767年《唐森德稅法》,向殖民地增收“印花稅”和“茶葉稅”等,激怒了殖民地民眾,①為抵制英王對殖民地的盤剝,弗吉尼亞殖民地議會于1764年率先做出決議:“對人民課稅依人民自身所為,是防止過重課稅的唯一保障。唯有人民代表才知道人民能負擔何種租稅,何種征稅方法最易為人民接受。”因此引發了美國獨立戰爭(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或American Revolution,1775年—1783年)。美國在1776年《獨立宣言》中嚴厲抨擊英國:“未經我們同意,任意向我們征稅”。美國獨立后,1787《美國憲法》第1條即明確了稅收法定原則:“一切征稅議案應首先在眾議院提出,但參議院得以處理其他議案的方式,表示贊同或提出修正案。”“國會有權賦課和征稅……”②參見《美國憲法》第1條第7 款第1 項、第8 款第1 項。
在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在1789年被迫重新召開自1614年以來就停開的三級會議,意圖向第三等級開征新稅,但第三等級卻乘機將三級會議改為國民議會,要求限制王權,實行改革。路易十六遂擬使用武力解散議會,因此引發了法國大革命,路易十六兵敗后亦被處死。隨后發布的法國《人權宣言》規定,人民財產不得任意侵犯。此后1793年《法蘭西共和國憲法》第34條明確規定:“征稅必須以法律規定。”世界其他主要國家莫不作類似規定,如《日本憲法》第84條規定:“新課租稅或變更現行租稅必須有法律或法律規定的條件為依據”。《埃及憲法》也規定:“只有通過法律才能設置、修改或取消公共稅捐”。
從上可知,世界近代史上的重要大革命,大多起源于政府和民眾對征稅權的爭奪。財產權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其重要性并不亞于生命權。因為沒有財產,何以支撐生命?因此,稅收作為一種典型的財產權強制轉移方式,應當事先得到財產所有人即民眾的同意(即法定化),否則民眾就可能產生類似于“被搶劫”的屈辱感和被剝奪感,其稅收遵從度必定不高;當稅負超過一定限度甚至危及民眾生存權時,就可能出現權力與權利、少數統治階層與多數大眾的激烈對抗,甚至發展到大規模流血沖突,乃至舊政權被推翻,稅賦決定權最終回歸民眾或其代議機構。因此,作為一個理性的法治政府,沒有不謹慎對待稅收問題的,沒有不充分尊重民意的。
由此可知,征稅權的范圍和邊界是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相互關系之中聯系最密切、矛盾最突出、沖突最激烈的領域之一,而稅收法定原則恰恰是各國協調這種關系,處理這種矛盾、平衡這種利益沖突的首選方案。北京大學劉劍文教授因此認為,稅收法定原則的確立與發展過程,就是各國從封建走向民主、從專制走向自由、從人治走向法治的過程。[8]相應地,稅收法定原則的內涵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與時俱進,處于不斷豐富與發展的過程中。目前,我國不僅應肯定稅收法定原則的憲性地位,更應強調其必須符合實質正義原則的要求,即確立實質的稅收法定原則。
三、從形式稅收法定走向實質稅收法定
稅收法定原則的核心內涵是對于其中的“法”的界定。一般認為,稅收法定中的“法”,應指狹義的法律,即由一國的民意代表機構即最高立法機關通過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文件,其屬于各國最高立法機關的保留事項。如在我國,其僅指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而不包括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立法及其他規范性文件。而作為例外的授權立法,必需嚴格符合特定的要求。③參見《立法法》第9—13條。一般認為,稅收法定原則包括以下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三部分內涵:一是稅收要素法定,即征稅人、納稅人、稅目、稅基、稅率等基本稅收要素應當由法律規定;④還有學者將“稅收優惠政策”也納入稅收要素范圍,主張應由全國人大立法確定。參見李萬甫《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快好還是慢好?》,載《中國稅務報》2015年4月29日第B01 版。二是稅收要素確定,即法律對稅收要素的規定應當明確,避免出現疏漏和歧義;三是稅收“程序法定”,即征稅機關必須嚴格按照法定的課稅要素與征納程序征收稅款,而不允許擅自變通或更改。但筆者認為,這還僅僅是強調形式要件法定性的形式稅收法定主義,即通過法定程序,實現稅收要素法定和內容確定。至于其中的程序是否正當,內容是否公平、公正,并非關注的重點。這主要是構建在一種理論假設之上,即國家有權(依法)征稅,民眾應當(依法)納稅。但該理念與民主、民生等現代基本法理念沖突,亟待發展、完善。
筆者以為,在當代的稅收法律關系中,稅收關系應當被定位為一種公共產品的買賣關系:國民(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向政府支付價款(稅金),政府應當等價地向國民提供公共產品。這是一種平等互利的、等價有償的交換關系,應當符合實質正義原則的要求。但鑒于強勢政府與弱勢國民之間這種明顯的不平等,必須建設一種權力制衡與利益平行機制,方可保障實質稅收法定原則的實現。因此,我們目前應當更加著重強調符合實質正義要求的實質稅收法定原則。
所謂實質稅收法定原則,可簡稱為稅收的“良法善治”。所謂“良法”,是指通過民主立法、科學立法,制定符合實質正義原則要求的財稅法律;避免“惡法”出臺,或其能及時被修改或廢止。所謂“善治”,是指上述“良法”得到切實執行,及時追究有法不依或選擇性執法等不法行為。該原則涵蓋稅收立法與執法的全過程,因此可簡稱為稅收法治。然而,我們還應清醒地認識到,“實質稅收法定原則”“稅收法治”或稅收“良法善治”均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及主觀性,對于其的解釋可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國學者或稅收法律關系各方主體基于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地位和認知背景等因素,未必能達成共識。目前,可以彌和各方分歧或爭議的方法首推正當程序原則。換言之,只要有關的稅收立法與執法符合正當程序原則的要求,就足以認定為實質的稅收法定。實質稅收法定原則基于但高于形式稅收法定原則。符合形式稅收法定原則要求的,不一定符合實質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
與實質稅收法定源于形式稅收法定一樣,程序正當也源于程序法定,后者只有前者的部分內涵。事實上,程序法定和稅收法定有著共同的歷史淵源,它們共同起源于1215年《英國大憲章》的“法定程序條款”(第39條):“凡自由民,如未經其同級貴族之依法裁判,或未經國法判決,皆不得被逮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流放,或加以任何其它損害。”其后,1354年英國國會通過的《自由令》規定:“未經法律的正當程序進行答辯,對任何財產或身份的擁有者一律不得剝奪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監禁,不得剝奪其繼承權,或剝奪其生命之權利。”這是首次以法令形式表述了法律的正當程序,并將該正當程序的適用范圍從人身權擴大到財產權。該原則后經美國憲法進一步發展,成為“正當程序原則”(Due Process)。如《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規定:“凡在合眾國出生或歸化合眾國并受其管轄的人,均為合眾國的和他們居住的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實施限制合眾國公民的特權或豁免權的任何法律;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對于在其管轄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絕給予平等法律保護。”即非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均應予平等保護。權力因此被關進了“正當程序”的籠子。
正當程序原則目前已經成為各國公認的法治基本原則,其要求“正義不僅應當實現,而且應當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9]基本內涵不僅包括“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告知、說明理由和聽取申辯等傳統要求,還包括公開、透明、公眾參與等現代性要求。正當程序原則不僅適用于各種司法和準司法行為,也適用于立法行為、行政執法行為與行政決策行為,甚至可擴大適用到政治行為和社會公共組織的行為。正當程序不僅是程序性的,即程序法定,也應當是實質性的,即程序正義。正當程序原則不僅強調立法、執法本身的公平正義,還強調非正義、不公正的法律和不正當法律程序的非法性。
在實質稅收法定主義者看來,正當程序與形式稅收法定主義的程序法定存在重大差異。符合程序法定的稅收立法和執法,并不一定是“良法”和“善治”。相反,在法律工具主義者或法律水平較低的立法、執法人員手中,程序法定往往被作為權力濫用,權力驕橫、恣意或執法水平低下的檔箭牌或遮羞布。諸如越權立法、選擇性執法、濫用程序、曲解法律、“證明你媽是你媽”等中國特色的法律問題或“難題”,[10]在我國仍存在。
無疑,符合正當程序原則的稅收法治,首先應當是符合程序法定要求的,盡管其結果不一定是權益沖突各方均認可的“良法善治”。兩者的根本差別是,正當程序原則是通過程序的正當性,賦予程序結果的可接受性,從而有助于增強民眾對稅收法治的認可和遵從度。故“良法善治”強調的是過程的公開、公平、公正與效率。因此,我們不能再滿足于簡單的程序法定,而應當對程序法定或法定程序本身是否正當進行拷問,[11]從程序法定走向程序正當。通過正當程序原則的保障,促進稅收法定原則實現從形式法定到程序法定的飛躍。
從不同視角看,正當程序原則具有不同的內涵。
對程序主持者而言,程序正當意味著:(1)程序中立,即任何人均不得擔任自己訴訟案件的法官。這主要通過程序主導者的資格認定、回避制度、權力制約等一系列制衡機制來保證。(2)程序理性,要求程序的步驟明確、有序,環節相互銜接;程序公開、公正、公平,并具有效率;程序主導者應闡明其決定的理由,防止不必要的自由裁量,禁止專橫、恣意。如稅法立法者應當公開其立法說明,向社會說明各法條的制定或修改依據、理由及相關情況等;稅法執行者應公開其稅收行為的依據和裁量理由;要求稅法司法者公開其司法裁決理由。(3)程序獨立,要求法律程序本身是法律結果的惟一決定因素,排斥程序外社會主體主導或干預程序。國務院及其財政部、稅務總局目前集稅收立法權、稅收征管權、稅收使用權于一身,制定了我國絕大部分的稅收規范。[12]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何以保持其中立性、獨立性及裁量理性?因此,我國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首先應將稅收立法權收回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
對程序結果接受者而言,程序正當意味著:(1)平等參與權,程序參與各方的權利義務應相當,在相同或相當的條件下(時間、方式、內容、數量等因素相同),可以從程序主導者獲得相關信息,并有相同的機會向程序主導者舉證、陳述看法;(2)程序自治權,可以自主地決定參與或拒絕程序,提出問題解決方案;(3)程序公正,即程序公開、公平,禁止暗箱操作;(4)程序效率,要求法律行為及時終結,有明確的程序期限,避免不必要的程序限制,防止程序草率或久拖不決。對該結果的修正必須通過啟動另一個專門法律程序。然而,在我國稅收執法方面,面對稅務機關超強的行政裁量權,行政相對人往往選擇了服從與沉默,致使稅收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案件極少。故上述四點要求均難以實現。因此,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必須厘清財稅部門的職權范圍,清理其越權制定的各種稅收法規,防止稅務機關越權、擅斷,建立起服務型的現代稅收征管模式。
四、我國應全面落實實質稅收法定原則
在我國,稅收法定原則已經得到有關立法的多方肯定,但亟待完善和落實。
首先,稅收法定原則在憲法層面得到了反映。1982年《憲法》第56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對于該法條是否或能否完全確立稅收法定原則,學者們存在分歧意見。有的認為,其雖然僅強調公民應依照法律納稅而未明確限制國家應依照法律征稅,但因其已經為公民納稅明確設定了前提條件,即納稅人僅承擔法律所設定的納稅義務,因而有權拒絕法律以外的其他行為規范所設定的稅收義務。而根據我國《憲法》,法律應當由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因此“這實際上是從公民負有依法納稅義務方面,間接地規范和限制了國家賦稅征收權的行使方式—依照法律”。由此可合理地推導出,我國憲法已經包括稅收法定主義原則,或至少這一規定隱含了或揭示了稅收法定主義的意旨。[5]但有學者認為,該規定僅為公民設立了依法律納稅的義務,這只是稅收法定原則的部分內涵,而未明確“征稅主體依法律征稅”這一更重要的內容,因此其無法全面體現稅收法定主義的精神,故不能說明稅收法定已經入憲。[13]甚至還有人認為,稅收法定主義中的“法”是廣義的,“我國的法律制度既包括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也包括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以及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條例、國務院部門規章和省級政府規章等。”“‘法’外‘法’立法的靈活性更能滿足納稅人權利保護的現實需要。”[14]同期實施的其他法規也作出了類似詮釋。如1986年《稅收征收管理暫行條例》第2條規定:“凡由稅務機關主管的各種稅收的征收管理,除國家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都應當按照本條例規定執行。有納稅義務的單位和個人(以下簡稱納稅人),有代征、代扣、代繳稅款義務的單位和個人(以下簡稱代征人),都必須按照稅收法規的規定履行納稅義務或者代征、代扣、代繳稅款義務。”第3條進一步規定:“各種稅收的征收和減免,必須按照稅收法規和稅收管理體制的規定執行。”顯然,根據該條例的規定,《憲法》第56條項下的“法律”是廣義的法律,包括法律、法規及其他稅收規定。根據這種廣義論,確實可以得出稅收法定原則在我國早已經得到確立的結論。這類觀點值得商榷,其偷換了“稅收法定”與“法律制度”中“法”的概念,前者是特定的“法”,而后者是平義的“法”。相應的邏輯推理因此違背了“同一律”基本邏輯規律的要求,結論不可信。此外,《憲法》第56條將納稅義務主體限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顯然也是不全面的。稅法中的納稅人既包括中國人也包括外國人,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及其他組織。故其日后修訂時不僅應明確國家應當依照法律征稅,還應將所有的納稅義務主體涵蓋。
其后,1992年《稅收征收管理法》對《憲法》第56條作出補充,稅收法定原則基本得到確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3條要求:“稅收的開征、停征以及減稅、免稅、退稅、補稅,依照法律的規定執行;法律授權國務院規定的,依照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任何機關、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擅自作出稅收開征、停征以及減稅、免稅、退稅、補稅的決定。”①該法在2001年修訂時,第3條第2 款被修改為“任何機關、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擅自做出稅收開征、停征以及減稅、免稅、退稅、補稅和其他同稅收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決定。”該法其后在2013年及2015年的兩次修訂中,該第3條均保持不變。該法條強調國家征稅必須基于法律(包括根據授權制定的法規),一定程度地彌補了憲法上的缺失。這使稅收法定原則在稅法但不是在憲法上基本得到確立。②參見張守文《論稅收法定主義》,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6期,第59頁;饒方《論稅收法定主義原則》,載《稅法研究》1997年第1期。然而因其仍未涉及稅收法定原則中的稅收要素法定等重要內涵,也未解決授權立法中的稅收立法權旁落等問題,其局限性比較明顯。
再后,2000年《立法法》從稅收立法權行使方面進一步完善了稅收法定原則,提升了稅收法定原則的法律位階。該法第8條規定:“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八)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即將稅收基本制度作為保留事項,要求只能通過法律予以規定。然而,因該法僅提出“稅收基本制度”等概念,而未對其他作出定義或細化,其仍未能有效地規制我國稅收行政法規、規章的濫發。③我國自實行分稅制改革后,共有25個稅種、23個稅收法律規范性文件出臺,其中經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稅收法律也只占15.2%,而國務院及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制定的稅收行政法規、規章則占到84.8%。
2013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應當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稅收法定原則”第一次被寫入黨的重要綱領性文件,充分顯示我國將加強稅收立法的“頂層設計”。2015年在修訂《立法法》時,“稅收基本制度”被進一步細化為“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④參見2015年《立法法》第8條第6 項;參見萬靜《個稅法僅14條規范性文件卻有158件》,載2015年2月12日《法制日報》。盡管部分爭議得到解決,但相關爭議無疑將因其中的“等”字而繼續發酵。故到目前為止,稅收法定原則在我國尚只能稱為基本確立,尚待進一步完善和落實。
從上可知,稅收法定原則在我國是通過一系列法律而非某一部法律逐步確立和落實的。故就稅收法定原則的邏輯結構而言,《憲法》提出的是本質要求,《立法法》提出的是形式要件要求,《稅收征收管理法》及其他稅法規范是具體的落實措施。它們相互聯系、相互依賴,共同保障稅收法定原則在我國得到實現。具體而言,是應當通過民主立法、科學立法,首先使稅收法定原則在《憲法》中得到完整確認,確立稅收法定原則的憲性地位;其次是完善《立法法》中的稅收立法制度,將《憲法》確立的稅收法定原則和立法制度具體化;再次是根據《憲法》確立的原則和《立法法》的具體要求,進一步修訂、完善《稅收征收管理法》及其他稅法制度,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以此為基礎的“稅收法治”才符合實質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其中的“法”才既有“法”的形式,又有“法”的內容。
按照全國人大的立法規劃,我國將在2020年以前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然而,相對于稅收法定原則的制度架構建設,該原則的全面落實將面臨更多問題,需要更多的時間與努力。因此,我國應當通過正當程序原則的保障而不是簡單的程序法定,將實質稅收法定原則落實到稅收法治全過程,做到科學立法、稅種法定、稅收主體法定、征稅對象法定、征稅標準法定、征稅程序法定、稅收分成法定、稅收使用法定、稅收監管法定及稅收責任法定,使稅收立法、執法、司法全程服從于正當程序。具體而言,實質稅收法定原則可通過以下正當程序落實。
(1)在稅收立法程序方面,應當保證立法主體適格,立法過程民主、科學,能保障公眾的參與權,能反映民意;各種稅收要素須經法定程序,以法律形式明確確定;非經法定程序并以法律形式,不得對法定稅收要素作出變更。
(2)在稅收執法程序中,征稅主體和納稅主體均須依法定程序行事;①劉劍文教授等認為,稅收法律關系涉及三方主體,即作為納稅主體之代名詞的“人民”、作為實質意義之征稅主體的國家和作為形式意義之征稅主體的征稅機關。參見劉劍文、李剛《稅收法律關系新論》,載《法學研究》,1999年第4期。在用稅過程中,應當依照法律規定,做到量入為出,保證必要的公共產品供給;禁止“三公消費”,避免無效率的公共投資;防止行政不作為或亂作為;依法嚴格懲處貪污、挪用等各種違法犯罪。
(3)在法律適用中,禁止溯及既往及類推,但溯及適用對納稅人有利的除外。一方面,“法律不溯及既往”作為一項法治基本原則,具有普遍約束力。另一方面,個別涉稅規范不當地確立了溯及適用規則。如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2000年7月18日《關于對青少年活動場所、電子游戲廳有關所得稅和營業稅政策問題的通知》規定:“本通知第一條規定自2000年1月1日起執行,第二至第四條規定自2000年7月1日起執行。”法律原則上不應溯及適用,除非有重大理由。而在稅收方面,溯及適用時,除非有利于納稅人的,否則不過是與民爭利的“無花果葉子”。此乃為蠅頭小利,損及稅收法定大義。另外,由于我國稅務機構設置達五級之多,最高財稅部門發布的涉稅規章或規范性文件到達一線執法機關時,“短則1月有余,長則達1年之久”。有人遂認為,這客觀上導致我國稅收執法中普遍存在追溯執行的可能性。[12]該觀點值得商榷。根據透明度原則的要求,法律經依法公開后,始具有約束力。這與有關的法律文本何時送達執行機關沒有直接關聯性。如果有關法規未經依法公開,不論何時送到執行機關,均無法律約束力,故其也不存在溯及力問題。
此外,由于現實社會復雜、多變,而法律是靜止、刻板的,其自出臺即落后于現實需要,故難以涵蓋其所要規范的全部社會生活。于是法律類推作為一種彌補法律漏洞的方法,在私法領域得到廣泛適用。然而在公法或特別在刑法領域,為防止權力濫用,禁止法律類推。鑒于稅收法定原則與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同工異曲,故應當禁止稅法類推適用,防止稅務機關因此適用事實上并不存在的法律,甚至越權立法。
[1]周小璐,郭蕾.財政部:連續3 次提高成品油消費稅彌補赤字不足[EB/OL].[2015-03-06].http://news.jschina.com.cn/system/2015/03/06/023938161.shtml.
[2]軼名.外媒質疑中國“加稅沒商量”:凸顯稅收法定迫切[EB/OL].[2015-01-17].http://news.sina.com.cn/c/2015-01-17/071231411059.shtml.
[3]彭飛.煙草消費稅提稅程序遭質疑 稅收法定其路漫漫[EB/OL].[2015-06-03].http://www.chinafund.cn/article/?id=293982.
[4]李萬甫.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快好還是慢好?[N]中國稅務報,2015-04-29(B01).
[5]饒方.論稅收法定主義原則[J].稅法研究,1997(1).
[6]丁一.稅收法定主義發展之三階段[J].國際稅收,2014(5):15.
[7]劉劍文,陳立誠.如何穩步落實稅收法定原則[J].檢察風云,2014(7).
[8]劉劍文.“稅收法定原則”第一次寫入黨綱領性文件中[EB/OL].[2013-12-03].http://news.qq.com/a/20131203/000916.htm.
[9]丹寧勛爵.法律的正當程序[M].劉庸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
[10]李之南.李克強:開證明“你媽是你媽”是天大笑話[EB/OL].[2015-06-01].http://news.163.com/15/0506/19/AOV5OFOE0001124J.html.
[11]阿計.稅收法定不能止于形式[J].法治與社會,2015(5).
[12]萬靜.個稅法僅14條規范性文件卻有158件[N].法制日報,2015-02-12.
[13]龔劍.從稅收法定主義談我國稅收法制的完善[J].湖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6(2):99.
[14]王家林.“稅收法定主義”觀不符合中國國情[J].中國財政,2012(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