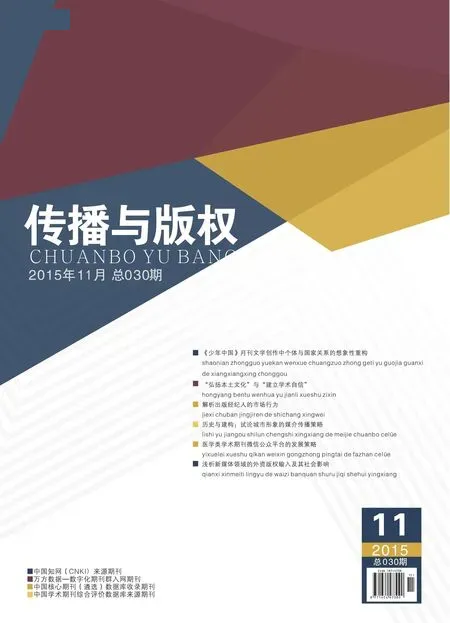依網而生的編校切片
——以兩段文稿編校為例
王 珍
依網而生的編校切片
——以兩段文稿編校為例
王 珍
互聯網對傳統出版流程影響很深,編校工作細節也隨之發生變化。在出版轉型年代,如何從細微的編校工作中探尋整個出版、傳播行業中變與不變的因素,并探討、研究、解決諸多的職業困惑,是廣大從業同仁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本文擬從日常編校工作入手,以呈現、探討職業切片的方式,為問題的解決提供粗淺的文本。
互聯網;編校案例;疑惑
[作 者]王 珍,江西高校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
一、習作緣起
互聯網對我國出版的影響,也就十多年的事,我們都還在由原有的出版結構和流程向新興的出版方向點滴融合、轉身的路途中。本文擬以兩個小校例,記錄、呈現出版轉型年代,普通文案編輯日常的兩個工作切片,并就正被互聯網改變著的編校工作做些散論,提出些疑惑,以期給深陷超負荷工作中的諸多編輯同仁們一點小小的參照。
二、兩個編校工作切片
(一)切片一
1.原稿。
一份小學生低年級的習字教材,正文之外,頁腳做裝飾和點綴用的一段詩文,字號很小,并不起眼,照錄原稿如下:
【智慧樹】名句:小雨輕風落糠花,細紅如雪點平沙。——陳獨秀
2.編校過程。
初讀,無錯字,卻起疑:“糠花”何解?鄉村揚場篩糠皮么?但“小雨輕風”,怎么會如此天氣揚場?署名“陳獨秀”,也令人警覺:有沒有可能張冠李戴?網絡年代,作者寫稿,快捷鍵復制、粘貼,方便、高效,卻也因此導致訛誤輾轉相引的現象比比皆是。猜測:這處文字,應該是來自網絡。
何處來,就往來處去查。將詩句輸入百度搜索框,果然滿屏的“糠花”。但細覽處,就發現有質疑、糾錯鏈接,顯示應該為王安石《鐘山晚步》中詩句:“小雨輕風落楝花,細紅如雪點平沙。”可以按照鏈接資料直接改掉原稿,完成編校么?答案是否。互聯網海量的信息,魚龍混雜,即便有糾錯分析,即便糾錯帖中言之鑿鑿,從信息的準確度而言,依然可疑。因此,需要找王安石的相關作品集核查。
先網絡查得宋人李壁箋注的《王荊文公詩箋注》,中華書局1958年版掃描電子本——古籍類,中華書局的本子自然是比較可靠的。但繁體豎排,標題密密麻麻,也無索引,花了半天時間,未找到此詩所在。于是再搜,得李之亮《王荊公詩注補箋》掃描電子本,巴蜀書社2002年1月1版1次。簡體橫排,雖也無索引,但行列清晰,查找還是方便多了——翻目錄40頁,查到《鐘山晚步》在此書卷四十三,正文第820頁。原詩如下:
小雨輕風落楝花,細紅如雪點平沙。
槿籬竹屋江村路,時見宜城賣酒家。
注①就是針對“楝花”的,照錄:
《東皋雜錄》云:“江南自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番風信,梅花風最先,楝花風最后。”⊙唐人詩曰:“楝花開后風光老,梅子黃時雨氣濃。”⊙晏元獻詩亦曰“二十四番花信風”是也。〔補箋〕楝,落葉喬木,四五月間開淡紫色小花,味清香。《淮南子·時則》:“七月官事,其樹楝。”高誘注:“楝實秋熟,故其樹楝也。”
據此可定,的確為“楝花”,作者王安石。但是,并不能到此為止。李之亮先生是知名的宋代文獻學專家,其補箋的文稿自然權威,不過有沒有可能,巴蜀書社這本子出現編校問題,詩句中錯訛一兩個字呢?回頭再查中華書局版《王荊文公詩箋注》,同樣在卷四十三,正文五七二頁,繁體豎排夾注,兩廂對校,除少了李“補箋”內容以及標點符號使用差異外,其余一字不差。終于踏實改定。
(二)切片二
1.原稿。
一份高校教材樣稿,古詩文讀本,選《詩經》名篇《蒹葭》,對詩題注釋如下:
選自《詩經·國風·秦風》。關于這首詩的內容歷來意見分歧,歸納起來主要有下列三種說法:一是“刺襄公”說。《毛詩》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二是“招賢”說。姚際恒的《詩經通論》和方玉潤的《〈詩經〉原始》都說這是一首招賢詩,“伊人”即“賢才”,“賢人隱居水濱而人慕而思見之。”或謂“征求逸隱,不以其道,隱者避而不見。”三是“愛情”說。今人藍菊有、楊任之、樊樹云、高亭、呂恢文等均持“戀歌”說。如呂恢文說“這是一首戀歌,由于所追求的心上人可望而不可即,詩人陷入煩惱,說河水阻隔是含蓄的隱喻。”
2.審讀意見。
此段注文,估計又是網絡“蕩”來。仔細審讀,得如下意見數條。
①先用網絡所得周振甫先生《詩經譯注》(中華書局2002年7月1版1次)掃描電子本核查原文,第181頁詩后有注文:
《毛詩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雖然周先生此版譯注本目錄中“蒹葭”錯為“兼葭”,也不能肯定此處引文是否完全準確,但周先生為編輯大家,引用文獻應大體可信,引文照改,尤其注意引文中標點的使用,“蒹葭”二字加書名號。如責編有閑暇,欲深究,可再查《毛詩正義》等文本核原文。
②《詩經通論》,網絡可得中華書局1958年12月1版1刷掃描電子本。“賢人隱居水濱而人慕而思見之”句出自此書,然該版第141頁原文為:“此自是賢人隱居水濱,而人慕而思見之詩。”樣稿斷引,尤其“之”字的意思被改變,如此處理不可取,應該用原文替換,于稿件表述并無不妥。
方玉潤所著,應為《詩經原始》,書名號內無單書名號,由網絡得中華書局1986版李先耕點校本可證。樣稿中,按順序,“征求逸隱,不以其道,隱者避而不見”,按說應引自此書,但遍尋無果,且無法確證引文正誤。查此版本第273頁,有句:“周之賢臣遺老,隱處水濱,不肯出仕。詩人惜之,托為招隱,作此見志。”可與作者商榷,以之替換無據引文。雖說“忌無知妄改,改必有據”是編校原則,但網絡年代,也不可一味拘謹墨守。
③文史類書稿,人名差錯不易察覺。此段注文出現人名7個,需注意一一核查。前2位可查無誤,再查后5人,用“今人藍菊有、楊任之、樊樹云、高亭、呂恢文等”做關鍵詞百度搜索,首頁顯示10條鏈接,均如此,似無誤。但此處自當生疑:資料如此高度一致,正顯示輾轉相引之網絡特性,訛誤即在其中矣!于文史涉獵稍深者,首先可判斷,“高亭”當為“高亨”,“亭”與“亨”,形近致誤。高先生為古文字學家和古籍校勘考據專家,曾師從梁啟超、王國維,其著作中有《詩經選注》和《詩經今注》。其余四人,雖名不彰顯,但置換關鍵詞,用“《詩經》+姓名”方式一一搜索判別,可知“藍菊有”當為“藍菊蓀”之誤,藍早年師從郭沫若,著有《詩經國風今譯》。其余三人,楊任之有《詩經探源》《詩經今譯今注》,樊樹云有《詩經全譯注》,呂恢文有《詩經國風今譯》,姓名無誤,且均為《詩經》研究專家,符合原稿意。
三、小結與疑惑
(一)小結
兩則校例,可以感受到被互聯網所改變的編校工作流程。
首先是信息的獲取和核查,突破傳統出版過程中“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藩籬,一網在手,信息盡有,無論作者、編者還是讀者,在當下,都從網絡中獲益匪淺,創作、編輯和閱讀的過程與速度,都因此發生著變化,且對網絡產生深度依賴的癥狀。
其次是因為便捷,導致信息的植入與傳播,同質化程度很高,錯訛也相應地同質傳播的概率更高,網絡中海量信息魚龍混雜,需要創作和編輯人員認真篩選和加工。
最后,我們可以延伸發現,無論未來的出版形態如何變化,圖書載體形式如何更替,但出版對知識和文化的選擇、整合、傳播和積累功能,會一直存續,而且因為信息的唾手可得與汪洋成海,對加工、處理信息的人員(或許,以后“編輯”也會改稱呼?),專業化要求程度更高。
(二)疑惑
從這兩則小小的校例中,我們或許也可以生發出一些從業疑難和困惑。比如,因為信息獲取、組合的便捷性,創作和編輯的邊界是否會日益模糊?甚至思想創造者和信息篩選、加工者身份完全疊加?如果是這樣,怎么能保證被傳播信息的創新性與高水準?
[1]陳昕.傳統出版社轉型發展的必然性——數字網絡環境下傳統出版社發展的經濟學分析之一[D/OL].(2015-07-03)[2015-07-16].http://www.bookdao.com/article/94414/.
[2]李壁.王荊文公詩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1958.
[3]李之亮.王荊公詩注補箋[M].成都:巴蜀書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