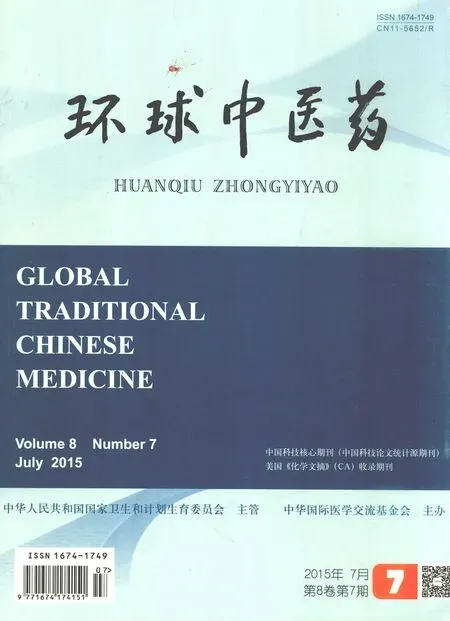王煥祿臨床治療抑郁癥經(jīng)驗淺議
燕莉 王洪蓓
王煥祿臨床治療抑郁癥經(jīng)驗淺議
燕莉 王洪蓓
本文通過對王煥祿臨床治療抑郁癥經(jīng)驗的梳理,淺述王煥祿對抑郁癥發(fā)病病機的觀點,即肝郁氣滯是抑郁癥產(chǎn)生的基本病機,且貫穿于抑郁癥發(fā)展的全過程;氣郁日久,影響他臟生理功能,又可形成新的病理機制,即痰濁內(nèi)蘊、膽腑被擾,或痰火內(nèi)擾、心神錯亂,或心肺陰虛、心神被擾幾種情況。針對以上四種不同病機,分別介紹了王煥祿運用四逆散、溫膽湯、礞石滾痰丸和百合知母湯(百合地黃湯)加減治療抑郁癥的臨床治療經(jīng)驗。
王煥祿; 抑郁癥; 名老中醫(yī); 經(jīng)驗
抑郁癥是一種常見的情緒障礙性疾病,表現(xiàn)為一種持久的抑郁狀態(tài),伴情緒低落、軀體不適和睡眠障礙等癥狀[1]。現(xiàn)代醫(yī)學(xué)一般采用口服藥物治療,雖然療效尚可,但具有藥物依賴性及副作用。在中醫(yī)學(xué)中,它歸屬于神志類病,結(jié)合抑郁癥的癥狀表現(xiàn),屬“郁病”范疇;由于抑郁癥的表現(xiàn)復(fù)雜多樣,根據(jù)臨床主訴的不同又可歸屬于“百合病”“臟躁”“癲狂”“梅核氣”等范疇。王煥祿是國家級名老中醫(yī),行醫(yī)五十余載,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jīng)驗,對抑郁癥的病機和治療形成了自己的觀點,臨床療效頗佳。現(xiàn)將王煥祿對抑郁癥發(fā)病病機的觀點和臨床治療經(jīng)驗,總結(jié)并淺述如下,與同道交流。
1 氣機郁滯,責(zé)之于肝
王煥祿認為抑郁癥的發(fā)生始于氣機郁滯之機。多年的臨床實踐,使王煥祿總結(jié)出抑郁癥患者發(fā)病前多有情感創(chuàng)傷史,由此引發(fā)患者情志不遂、精神抑郁,進而導(dǎo)致肝失疏泄,氣機郁滯。《內(nèi)經(jīng)》有云:“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中醫(yī)學(xué)認為,人精神、意識的正常表現(xiàn),有賴五臟六腑的生理功能正常發(fā)揮,正如《靈樞·衛(wèi)氣》有云:“五臟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臟腑功能的正常,就需要人體內(nèi)氣機升降出入正常,這自然與五臟中肝之疏泄功能密切相關(guān)。肝主疏泄,可以調(diào)節(jié)全身氣機的運行,亦可以調(diào)暢情志。肝失疏泄,則氣機運行失常,“出入廢,則神機化滅”(《黃帝內(nèi)經(jīng)素問·六微旨大論》)。亦如《醫(yī)碥·郁》所云:“百病皆生于郁,…郁而不舒,則皆肝木之病矣。”故臨床可見情緒低落的精神狀態(tài),并伴見胸悶不舒,善太息,胸脅脹滿等癥。
臨床治療上,王煥祿主張疏肝解郁為法,臨床常用基礎(chǔ)方為柴胡10 g、枳實10 g、白芍10 g、八月札10 g、香附10 g、炒酸棗仁30 g、菖蒲30 g、遠志10 g、生龍骨20 g。方中柴胡、枳實、八月札、香附共奏疏肝理氣之效,白芍養(yǎng)血柔肝;炒酸棗仁、菖蒲、遠志、生龍骨調(diào)心神,養(yǎng)心鎮(zhèn)靜安神。
王煥祿認為,氣郁是抑郁癥產(chǎn)生的基礎(chǔ)病機,貫穿于抑郁癥發(fā)展的全過程。有臨床流行病學(xué)關(guān)于抑郁癥中醫(yī)辨證及證候指標調(diào)查的分析結(jié)果也顯示,肝郁氣滯證是抑郁癥最基礎(chǔ)的證候[2]。因此,疏肝解郁法是治療抑郁癥的基本治法。氣郁日久,則波及影響其他臟腑生理功能,伴生新的病理機制。
2 痰濁內(nèi)蘊,膽腑被擾
肝主疏泄,調(diào)節(jié)全身氣機之升降出入。肝木調(diào)達,對于保證全身氣血的正常循行起到重要作用。肝疏泄失常,除了可以直接影響其調(diào)暢情志之功外,還會間接影響其他臟腑生理功能而引發(fā)情志變化。與肝臟相表里的膽腑為“中精之腑”,喜清靜,惡抑郁,亦主氣機調(diào)暢,正如《素問·陰陽離合》有云:“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若肝失疏泄,最容易影響膽的功能,造成膽氣不利;若肝郁氣滯,影響中焦脾胃運化,造成氣血津液運化失常,痰濕內(nèi)生,二者侵擾膽腑,則膽氣失于調(diào)達,其主決斷功能受到影響。由于人體精神心理活動與膽的決斷功能有關(guān),膽失決斷臨床上可以見到患者膽怯易驚、善恐、失眠、多夢等癥狀。
臨床治療上,王煥祿選用陳無擇《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中所載的溫膽湯加減治療,意在化痰濁,利膽氣,使臟腑功能恢復(fù)正常,氣機調(diào)順,神志自安。正如楊鵬[3]提出溫膽湯具有調(diào)暢氣機的作用。王煥祿常用臨床經(jīng)驗方藥組成為清半夏 10 g、陳皮10 g、茯苓10 g、枳實10 g、竹茹6 g、膽南星6 g、生甘草10 g、菖蒲30 g、白梅花10 g。方中半夏降逆和胃,燥濕化痰為君;陳皮理氣燥濕,茯苓健脾滲濕為佐;竹茹清熱化痰,止嘔除煩,枳實行氣消痰,使痰隨氣下為臣;甘草健脾和胃,協(xié)調(diào)諸藥為使。膽南星、菖蒲化痰開竅;雖然以上群藥配伍可清化痰濁、膽氣調(diào)順,但由于肝膽互為表里臟腑,二者在生理上相互為用,相互促進,正如《類經(jīng)·臟象類》有云:“膽附于肝,相為表里,肝氣雖強,非膽不斷,肝膽相濟,勇敢乃成。”因此,王煥祿經(jīng)驗方中又加疏肝理氣解郁的白梅花,助肝之疏泄如常,從而使膽氣更利。諸藥合用,共奏理氣化痰,清膽和胃之效。若肝火旺盛,加龍膽草6 g、黃芩10 g、梔子10 g清肝瀉火;若肝郁氣滯明顯,加八月札10 g、郁金10 g,助白梅花疏肝理氣解郁;若睡眠較差,加炒酸棗仁30 g、遠志10 g、生龍骨30 g,養(yǎng)心安神。
3 痰火內(nèi)擾,心神錯亂
在中醫(yī)學(xué)中,痰火擾心所引發(fā)的神志癥狀臨床可見狂躁不安、打人毀物、哭笑無常、不避親疏等,這一系列表現(xiàn)似乎與以心境低落為主要表現(xiàn)的抑郁癥極不相稱,更符合中醫(yī)學(xué)中“狂病”的表現(xiàn),但王老師結(jié)合多年臨床經(jīng)驗,提出痰火內(nèi)擾、心神錯亂是抑郁癥日久由氣郁進一步發(fā)展的常見病機之一。其實,在現(xiàn)代醫(yī)學(xué)心理學(xué)中關(guān)于抑郁癥患者情緒的描述中,也指出部分患者表現(xiàn)為具有明顯的焦慮和運動激越,嚴重者可出現(xiàn)幻覺、妄想等精神病性癥狀,并非疾病全程表現(xiàn)為情緒消沉,同時伴見入睡困難,睡眠障礙等。據(jù)kesssler等報道抑郁障礙共病焦慮障礙的比例達50%[4]。此類抑郁癥患者主要是由于情志不遂,氣機郁滯,病程日久,郁而化火,正所謂“五志過極皆從火化”。熱傷津液,煉液為痰,痰火擾動心神;或木郁土不達,運化失常,痰濕內(nèi)生,火邪夾痰濁上擾心神,痰火作祟,變化多端,故臨床表現(xiàn)焦慮,悲觀失望,煩躁易怒,胸脅脹滿,多夢,耳中轟鳴,頭暈,頭脹,腹脹,口苦,咽有異物感,惡心,小便短赤,或胸脘痞悶,或不寐,或奇怪之夢,或咳喘痰稠,舌質(zhì)紅,舌苔黃膩,脈弦數(shù)或滑數(shù)等癥[5]。在上述表現(xiàn)中,王煥祿認為此型患者的煩躁易怒發(fā)作程度較重,甚則暴怒不能自控。
臨床治療時,王煥祿選用王珪所創(chuàng)用于治療老痰怪病的名方-礞石滾痰丸加減變化。其經(jīng)驗方藥組成為青礞石10 ~20 g、黃芩 10 g、大黃 6 g、沉香面 1.5 g、炒酸棗仁 30 g、菖蒲30 g、清半夏10 g、膽南星6 g。方中青礞石甘、咸、平,墜痰下氣,平肝鎮(zhèn)驚安神;黃芩清熱泄火;大黃清熱瀉火,使熱從大便清;沉香降氣安神;半夏、膽南星燥濕祛痰;炒酸棗仁、菖蒲化痰安神開竅。全方配伍共奏逐痰瀉火,寧心安神之效。若伴肝火旺盛,方中加龍膽草6 g、梔子10 g,清肝泄火;若肝陽亢逆,加珍珠粉0.6 g、生石決明30 g平肝潛陽。
4 心肺陰虛,心神被擾
王煥祿根據(jù)其多年臨床經(jīng)驗,認為由氣郁導(dǎo)致心肺陰虛,從而引發(fā)的臨床以心神被擾為主要表現(xiàn)、屬于中醫(yī)“百合病”范疇的病證也是抑郁癥在臨床中常見的一種形式。關(guān)于百合病的記載,早在漢代即由醫(yī)圣張仲景所記載。在《金匱要略》中所記載此病的發(fā)生多見于熱病后,即指出此病為熱邪傷陰,虛火擾神,心肺受累所致。而情志內(nèi)傷,亦可形成百合病。病者情志不遂,郁熱傷及心肺之陰,心肺陰虛內(nèi)熱,百脈故而受病[6]。對于素體陰虛的患者,適逢情志不遂,形成上述病理發(fā)展機制,加重原有陰虛之候,亦可發(fā)病。臨床癥見患者情緒低落,對生活缺乏興趣,“意欲食不能食,常默默,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用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諸藥不能治……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脈微數(shù)”(《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陰陽毒病》)等諸多神經(jīng)癥樣表現(xiàn)。
臨床治療時,王煥祿臨床選用代表方劑百合知母湯(或百合地黃湯)加味化裁治療,正所謂“法隨證出、方隨法立”“有是證用是藥”。其經(jīng)驗方藥組成為百合10 g、知母10 g、炒酸棗仁20~30 g、菖蒲30 g、遠志10 g、生龍骨40 g。方中百合養(yǎng)陰潤肺,知母清熱養(yǎng)陰,若熱象較重則易為生地清熱養(yǎng)陰、涼血。由于抑郁癥臨床多見睡眠障礙及氣郁表現(xiàn),方中配伍生龍骨、遠志、菖蒲、炒酸棗仁安神定志;菖蒲、遠志二藥味辛,又有辛散之功,可助疏理氣機、解郁開竅。若患者為處于圍絕經(jīng)期的中年婦人,臨床伴見善悲欲哭之證,則上方加甘麥大棗湯以潤燥養(yǎng)心安神。若患者肝郁氣滯癥狀明顯,則合柴胡疏肝散組方治療。若入睡困難明顯者,可加纈草15 g,以助疏肝解郁,安神定志。
5 典型病案
患者,女,23歲,于2014年4月29日主因“情緒低落7年,間斷脾氣急躁3年”初診。患者7年前在校讀書時因為同學(xué)排擠引發(fā)情緒低沉,在當(dāng)?shù)鼐癫♂t(yī)院就診,診斷為“抑郁癥”,因患者家長及患者自己擔(dān)心西藥抗抑郁藥的不良反應(yīng),故未遵醫(yī)囑服藥。近3年來患者仍經(jīng)常情緒低落,善悲,少言寡語,甚則對生活失去希望,但有時又脾氣暴躁不能自控。時有心慌氣短,胸悶,恐懼,疲乏無力,夜寐早醒,有時幻想。以往大便干結(jié),目前大便稀,月經(jīng)經(jīng)常先期而至。舌淡紅,苔黃厚,脈弦滑。西醫(yī)診斷:抑郁癥,中醫(yī)診斷:郁病(痰火擾心)。處方:青礞石20 g、黃芩10 g、生大黃10 g、沉香曲 10 g、菖蒲30 g、郁金15 g、炒酸棗仁30 g、膽南星6 g、龍膽草10 g、梔子10 g、甘草10 g,連服14劑,告知患者若服藥后大便偏稀或次數(shù)增加無礙。二診時患者訴脾氣急躁明顯減少,恐懼略減,但仍有幻想,自覺精力、體力增加,入睡時間縮短,仍多夢、早醒,上午惡心、納食不佳,仍大便溏稀。舌淡紅,苔黃較前轉(zhuǎn)薄,脈弦。遂減郁金為10 g,加清半夏10 g、茯苓15 g,繼服14劑。三診時,患者恐懼感減輕,但仍畏懼上學(xué),仍早醒,幻想,有時情緒不能控制。舌苔黃根部略厚,脈弦滑。遂守初診方去沉香曲、郁金、膽南星、生甘草,加生地10 g、川楝子 8 g、甘松 10 g、生麥芽 30 g、茵陳 30 g,繼服14劑。如此又復(fù)診2次,根據(jù)病證變化,守初診方繼續(xù)加減進退,又服藥1個月未再復(fù)診。時隔3個月后電話追訪,患者訴目前情緒穩(wěn)定,可自行調(diào)節(jié),疲乏改善,恐懼、幻想消失,已基本可以正常生活、學(xué)習(xí),遂停藥。
按 本患者因上學(xué)被同學(xué)排擠,引發(fā)情志不遂,氣機郁滯,故癥見胸悶、氣短;肝失疏泄,調(diào)節(jié)情志功能受累,癥見情緒低落。木郁則土壅,脾運失常,因而生濕生痰;又氣郁日久化火,煉液為痰;痰火相結(jié),上擾心神,心神不寧,故癥見心煩易急躁,有時情緒暴躁,甚則出現(xiàn)幻想,夜寐早醒。證屬痰火擾心,肝經(jīng)火旺,治以化痰清火,清肝泄熱為法,方中青礞石滌痰下氣,平肝鎮(zhèn)靜;龍膽草、梔子、黃芩清肝泄熱,大黃清熱瀉火,導(dǎo)熱下行;沉香降氣安神定志;菖蒲、郁金、炒酸棗仁解郁化痰安神;膽南星燥濕化痰;甘草調(diào)和諸藥。二診患者精神躁擾癥狀減輕,后調(diào)整方藥加清半夏、茯苓增強化痰之力。三診,患者恐懼減輕,仍早醒,有時情緒不能自控,故調(diào)整方藥,增加清利肝膽之品,又復(fù)診調(diào)整方藥2次,最終使痰消火清,心主神志恢復(fù)如常,患者可以恢復(fù)正常學(xué)習(xí)、工作。
6 結(jié)語
綜上所述,王煥祿臨證治療抑郁癥時,強調(diào)氣郁為本病發(fā)生的基礎(chǔ)病機,無論是疾病早期的單純氣機郁滯,還是病程日久、伴生痰濁、痰火和陰虛之機,調(diào)理氣機貫穿于抑郁癥治療的始終,為治療本病不離之法。在臨床治療時,王煥祿指出梳理氣機之法要根據(jù)病證靈活運用,調(diào)暢氣機不應(yīng)僅僅拘泥于選用疏肝理氣之品,對于那些可以恢復(fù)人體氣機正常升降出入的治法方藥,均可視為調(diào)理氣機,例如痰濁內(nèi)蘊者化痰降濁,痰火擾心者逐痰瀉火安神,心肺陰虛、心神被擾者養(yǎng)陰清熱安神,諸法用之,助機體氣機調(diào)暢,則神機復(fù)常。除此之外,王煥祿對于抑郁癥患者常見的睡眠障礙癥狀比較重視,強調(diào)治療抑郁癥時要積極予以干預(yù)治療,對于改善患者的抑郁狀態(tài)大有裨益。據(jù)有關(guān)報道指出超過90%的重性抑郁癥患者存在失眠或白天睡眠[7],臨床中有很多抑郁癥患者是以睡眠障礙為主訴來求醫(yī),這一癥狀也是讓患者感到最痛苦的事情之一。長時間的睡眠障礙,會讓患者感到身心疲憊,從而加重患者焦慮、緊張的情緒,對抑郁癥的預(yù)后起到不利影響。郭克峰[8]的研究即提示睡眠障礙是加重抑郁癥病情的重要因素,是影響抑郁癥患者康復(fù)的主要障礙之一。正是由于改善睡眠狀況對抑郁癥患者病情改善具有重要意義,王煥祿臨證用藥時必選安神助眠的藥物,如炒酸棗仁、遠志、生龍骨、菖蒲等養(yǎng)心安神定志之品。另外,王煥祿還指出,抑郁癥屬于心理、情感障礙,臨床上除了藥物調(diào)治神志外,還應(yīng)重視對患者的精神調(diào)攝。在臨床接診時,除了處方用藥外,還注意對此類患者進行心理疏導(dǎo),指導(dǎo)對象包括患者和患者家屬兩方。對患者而言,王煥祿會支持、鼓勵患者接受并正視罹患精神疾患的現(xiàn)實,告知他(她)此病可以治愈,促使其建立戰(zhàn)勝疾病的信心;鼓勵患者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對促進患者疾病恢復(fù)有很大幫助。正如《臨證指南醫(yī)案》中指出:“郁證全在病者能移情易性。”對于患者家屬而言,王老師要叮囑其家人多與患者溝通、交流,給患者更多的關(guān)愛,為其創(chuàng)造良好的家庭氛圍,對于促進患者康復(fù)也具有重要作用。這種心理調(diào)攝也可以看做是王老師治療抑郁癥調(diào)暢氣機的非藥物干預(yù)之法。
[1]沈漁邨.精神病學(xué)[M].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1998:358.
[2]胡隨瑜,張宏耕,鄭林,等.1977例抑郁癥患者中醫(yī)不同證候構(gòu)成比分析[M].中國醫(yī)師雜志,2003,5(10):1312-1314.
[3]楊鵬,王彥輝.溫膽湯調(diào)暢氣機的作用[J].中華中醫(yī)藥雜志,2012,27(3):647-64.
[4]陳忠.抑郁障礙并存焦慮或失眠癥狀的藥物治療對照研究[J].臨床精神醫(yī)學(xué)雜志,2011,21(2):80-83.
[5]唐啟盛.抑郁癥中醫(yī)證候診斷標準及治療方案[J].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報,2011,34(12):810-811.
[6]吳曉哲,郭曉冬.“百合病”與“臟躁”異同辨析[J].實用中醫(yī)內(nèi)科雜志.2011,25(12):76-77.
[7]霍小寧,楊小龍,劉新發(fā).右佐匹克隆與阿普唑侖輔助治療抑郁癥睡眠障礙對照研究[J].國際精神病學(xué)雜志.2012,39(4):208-211.
[8]郭克峰,關(guān)菊香.抑郁癥患者睡眠障礙與康復(fù)的關(guān)系研究[J].中國臨床康復(fù),2002,6(7):952-953
R749.4+1
A
10.3969/j.issn.1674-1749.2015.07.033
100037北京市西城區(qū)展覽路社區(qū)衛(wèi)生服務(wù)中心中醫(yī)科(燕莉);北京市西城區(qū)展覽路醫(yī)院中醫(yī)科(王洪蓓);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燕莉(碩士研究生)、王洪蓓(博士研究生)]
燕莉(1979-),女,2012級在職碩士研究生,主治醫(yī)師。研究方向:名老中醫(yī)學(xué)術(shù)思想臨床經(jīng)驗傳承。E-mail:yanl125@163.com
2015-04-18)
(本文編輯: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