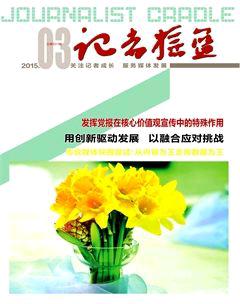傳統媒體突圍嘗試:從內容為王走向數據為王
張坤陽
維克托·舍恩伯格在《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中最具洞見和最富爭議的觀點是,他明確指出:大數據時代最大的轉變就是,放棄對因果關系的渴求,而取而代之關注相關關系。也就是說只要知道“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為什么”。筆者認為,理解相關性這一大數據時代的本質要素,從而領悟大數據環境下受眾對高品質、確定性信息的需求,可以幫助傳統媒體擺脫困境,尋求戰略突圍。
一、傳統媒體在加速衰退
今天,我們打開手機的打車軟件,以乘客為中心,可以看到,在他的附近有多少輛出租車正在待客;以司機為中心,可以看到,他的附近有多少人正在打車,其中又有多少人愿意加價。乘客、司機不再是隨機相遇,而是可以互相找到,乘客和司機都上線了。數據在線上流動,數據在線上融合,所有人都能從大數據中受益。
這在半年前的出租車業,還是無法想象的。這樣的大數據時代的縮影,又是否會在媒體上演呢?這些年,傳統媒體一直在猜測自身的衰落,有一種“狼來了”的疲憊。而又比如哪一天,我們打開智能手機,發現一個軟件,以讀者為中心,就會自動出現一堆按照他個人興趣排列的新聞,并且根據個人喜好推薦他看什么。這樣的攪局者或者淘金者,已經出現了,其中有一個叫“今日頭條”,是根據大數據思維做出的智能手機客戶端,對用戶瀏覽習慣、方向有“記憶性”,即通過一套獨特的算法,獲取用戶感興趣的分類,并向用戶推送相關的內容。這個軟件目前估值超5億美元。
我們必須承認,無論多么優秀的記者,他對于事物的觀察都只能是受制于個人的視野與立場,即使是相對深入的,也未必是全面的、充分的。而與記者在某一個視野有限的觀察點上對事物進行的觀察與分析不同的是,有效加工的大規模數據可以揭示更大范圍內的或更接近事實的情狀,從而也為報道的深入提供了基礎,從而徹底改變媒體生態。這就是大數據時代相關性和因果性的區別。
“今日頭條”這樣的媒體工具,是令人生畏的,它與傳統媒體之間有一條理論鴻溝,它實際上沒有新聞業務實踐,只注重相關性,不去尋找因果性。這顛覆了傳統媒體長期沿襲下來的新聞生產、傳播方式,也消解了傳統媒體的新聞理念。在新媒體帶來的全方位挑戰面前,傳統媒體短時間內還沒有成功開拓出突圍之路。
二、傳統媒體的突圍嘗試
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所理解的大數據思維,即不再熱衷于尋找因果關系,而尋找事物之間的相關關系。這種觀點,意在顛覆此前“有限”數據時代的信息思維理念。傳統媒體在信息思維上的不足恰恰在于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追求微觀精確,忽視宏觀把握。傳統媒體應該有大數據視野。有了這種視野,即便關注的是“點”上的微觀問題,看到的風景也會不同,不是孤零零的“點”的意義,而是具有“面”上價值的“節點”。
以首屆數據新聞獎的一個入圍作品為例,這是由英國廣播公司(BBC)和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聯合制作的《預算計算器:2012年財政預算將如何影響你?》政府財政預算向來是一項專業和繁復的公共政策事件,媒體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有效解讀它對普通居民的生活影響。BBC的“計算器”簡便實用,用戶只需在界面上輸入一些日常個人信息,就能自動算出新預算會讓你多付多少稅,你明年的生活會比今年變得更好還是更差。
在傳統時代,媒體人角色是信息采集者,主要工作內容是報道事實。在融合媒體時代,媒體人角色是平臺搭建者,主要工作內容是聚合社會化信息。在大數據時代,媒體人角色,就應該是意義生成者,主要工作內容是闡釋事件的影響。建立在大數據技術上的事件分析和意義解讀,比采訪專家和憑記者個人判斷更有可靠性。通過開掘數據,記者的工作建立在扎實證據基礎上,為讀者提供經過科學分析的洞見,把抽象的、宏觀的社會問題轉化為跟普通人相關、普通人容易理解的內容,還可分析復雜形勢中事物發展的規律和趨勢,給人們決策提供預見性內容。
很多時候,面對碎片化的海量信息,受眾無所適從,不知道如何配置有限的注意力資源和時間,把注意力和時間大量花費在低質信息上。傳統媒體可以憑借自己對社會環境以及新聞的獨特理解和經驗優勢,從海量數據中提煉出有價值的新聞信息,以滿足受眾對于高品質內容產品的需求。在“劣幣”泛濫之際,人們對“良幣”的期待就會增強。問題是我們的傳統媒體在這方面做得遠遠不夠。這就要求傳統媒體提高信息深加工能力,在淺表化、碎片化的信息汪洋中捕撈高質量的內容產品。
三、從內容為王到數據為王
大數據時代下,沒有內容,就沒有事業,沒有數據,就沒有未來。傳統媒體應當一方面承認差距,補上過去落下的功課,一方面避免盲目,實事求是地思考未來的進取之途。
為什么走在大數據技術前沿的都是一些互聯網公司,而不是傳統媒體或出版機構?技術是個重要原因,技術匯聚數據,數據自動產生意義,才會有只去了解相關性,而無需關注因果性。這一方面,傳統媒體業存在先天的技術劣勢,不僅掌握的數據資源有限,大多數機構掌握的人才和管理基本為零。
可以說,大多數媒體機構連傳統的流程、工具和方法都沒有掌握。
一個簡單的例子:中國最大的電視臺中央電視臺據稱擁有近40萬小時的節目資源,年播出總量為23.0248萬小時;而YouTube每分鐘就有72小時的視頻被上傳,更不用提每月10億獨立用戶的行為數據。數據量級相差懸殊。所以,傳統媒體深受大數據沖擊和影響,但又缺乏根基,難以出現顛覆性的創新,無法孵化出新的業務形態。
傳統媒體,勢必要從內容為王走向數據為王,著手積累數據資產
浙江日報報業集團斥資32億收購邊鋒浩方網絡平臺。邊鋒浩方擁有五六百款的游戲,活躍用戶達到2000多萬,最高在線人數150萬。浙報集團圍繞這個平臺,主要是以建設數據分析系統為支撐,深入篩選捕捉用戶行為、習慣、偏好和需求,挖掘和積累可貴的數據資源。從其自身成長性和增值可行性來看,這個平臺價值難以估量。
另一方面是加強數據能力的獲取
媒體應通過合作、購買、外包、孵化等方式,首先掌握傳統的數據處理能力,進而具備大數據應用的能力;引進和培養數據人才,包括擁有統計學、商業智能、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等多方面技能的“數據科學家”,也要有知曉如何通過運用大數據來設計產品和運營企業的分析師和管理者。浙報集團旗下的新媒體戰略投資機構傳媒夢工場投資了知微、優微等項目,主要專注社交網絡的數據深度挖掘,在這一領域布下了棋子。
從長遠看,要拓展業務,真正擁抱大數據
推出具有社交屬性的新聞產品,真正投身大數據的海洋,歐美大型媒體機構在這方面的案例并不鮮見:紐約時報公司注資URL網址鏈接縮短服務Bit.ly,后者提供的短鏈接截至2013年3月已經達到1000億次點擊;CNN收購移動應用Zite,后者作為一款免費的個性化閱讀應用,通過采集用戶的閱讀行為,抓取用戶在Facebook或Twitter等社交網絡上的數據,進而判斷用戶的興趣,聚合推送個性化的內容。
我們位于大數據時代的前夜,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包括傳統媒體和各種行業,都將發生歷史性的變革。沒人可以定義未來,也沒有人可以在大時代輕松地搭上便車,最先消亡的一定是對未來茫然無知的看客。傳統媒體的任務,也正是要找到它與這個時代的相關性,參與其中。
(作者單位:遼寧日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