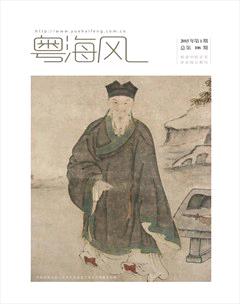黎雄才:從嶺南畫派到二十世紀中國畫
梁江
回顧二十世紀中國畫壇,嶺南畫派和海派都是繞不過去的話題。從二十世紀初“二高一陳”赴日留學算起,到二〇〇一年黎雄才去世,嶺南畫學一個世紀發展的歷史,與晚清、民國和新中國各時期中國畫的歷史行程交叉、糾結和重合。嶺南畫派以革命性、創新性的新質,以融合東洋、西洋畫法的實踐經驗,為二十世紀進入現代轉型的中國畫壇帶來了新的面貌。
從傳統意境到表達來自于現實的鮮活體驗,從程式化模式轉向真山真水。黎雄才的山水畫實踐和貢獻,明確地標示了這一轉變。
一
黎雄才自小受精于裝裱兼擅繪畫的父親黎廷俊熏陶,又從陳鑒學藝。一九二六年拜高劍父為師,高劍父讓黎雄才臨摹過數百幅古畫,且帶他外出寫生。其間,還到司徒奇、梅端清、趙世銘及何三峰主持的烈風美術學校學素描。熟諳傳統技法,有扎實的寫生能力,從高劍父這里,已構筑了他重傳統、重寫生且眼光開放的藝術理路。一九三二年再獲高劍父資助留學日本,在東京日本美術學校日本畫科就讀三年。這一經歷,不僅讓黎雄才眼界進一步打開,更成了他在繪畫藝術創造上的轉化契機。
“折衷中外,融會古今”,振興民族文化,是老師高劍父很明確的畫學主張。不過,對這位少年弟子,老師似乎更在意他對傳統筆墨技藝的基礎。高劍父帶他面對大自然寫生,命其臨摹多達幾百種的歷代名畫。還有人們熟知的故事,“每天叫他爬到閣樓里臨畫,他一上去,高劍父就把梯子抽掉了,免得他心散。”
少年黎雄才老老實實學藝,沒有過早參與“新與舊”的論戰。這一點,還只是表象。更深層的含義在于,黎雄才早年就已表明,在嶺南畫派譜系中,他是實踐家而非發言人。他的藝術個性和創新訴求,主要是通過創作、寫生與教學的具體實踐而體現出來的。據知情人回憶,在春睡畫院,高劍父教學生山水畫常以黎雄才的作品示范。這種推崇,無疑更強化了黎雄才的這一定位。
高劍父縱橫捭闔,其革命家、革新家和教育家氣質是整合一體的。高氏力倡“折衷中外,融匯古今”的藝術革新方向,同時身體力行作大刀闊斧的創作嘗試,為二十世紀的中國美術史留下了若干經典之作。但,這畢竟是邁開了第一步,推動藝術革新任重道遠。更重要的問題是,要把革新口號、藝術理念和價值取向落至實處,融入創作,最終仍需更多藝術家靠作品來說話。在這一點,黎雄才的貢獻尤顯重要。
誠如論者所關注的,一九三二年的《瀟湘夜雨圖》,是黎氏早年的成功之作。風雨歸途,竹岸泊舟,是畫有宋代繪畫式的嚴謹筆法,又融入西洋水彩的技法,以大面積渲染來營造濕潤朦朧的特定效果,這已明確顯示黎氏有傳統筆墨功力,且汲取了橫山大觀“朦朧體”色彩暈染法這樣的早期特征。顯然,留日學習對于黎雄才的筆墨語言轉向,有著非同小可的長久影響。此一時期的《風雨歸舟》《猿橋春雨》《松月圖》《富士山之夏》等作品,均表現出對單純化裝飾風格的興趣,筆墨消融于朦朧化的鋪排渲染。這種與“朦朧體”有關聯的氣息,在他日后的《幽潭》《松壑鳴泉》《一覽眾山小》《深山聞夜啼》諸作中,仍然若隱若顯透露出來。
自進入春睡畫院到留學日本回國,前后八年,黎雄才以求學、深造為主。抗戰時期,黎雄才多在祖國西南、西北地區度過,輾轉寫生并舉辦個人畫展,一九四六年還去敦煌臨摹壁畫。深入生活,體味人生,速寫和寫生畫稿數以萬計,這使他得以積攢轉變和升華的深厚藝術能量。其后作于成都的《獵得山禽信馬歸》和一九四八年所畫《牧馬》,既包含著源于生活的蒙養,也顯示出黎氏技藝進一步精到嫻熟。
作為一心傾于實踐的畫家,黎雄才很早便呈現出一種超越性的的寧靜心境。縱觀一生,他似乎沒有乃師那樣“以天下為己任”的充溢政治熱情,于各種論爭詰辯也無太多介懷。透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川蜀、西北寫生,他逐漸強化了大筆揉擦、渾融蒼莽的筆墨效果,已然越出”朦朧體』飄渺空靈的氛圍和精致趣味。緣于對中外藝術的直接體悟,其視野寬闊而開放。他尊崇乃師,也廣汲博納,且不排斥馬、夏式的蒼勁水墨。通過長期寫生的比照參悟,他終于在大自然山水結構的真實呈現與筆墨表達之間,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契合和交接點——這是黎雄才的創新基點。從寫生素材中提煉取舍,依山川景物描繪需要,讓傳統筆法與外來元素水乳交融。由是,在南宋筆墨與橫山大觀的光影色彩效應中起步,黎雄才尋覓到了一種吻合個性的語言創意。造型工寫結合,筆法雄秀相宜,設色清雅明快,這正是嶺南畫派尤其嶺南山水的特色。基于這一點,我頗認可李偉銘君的說法:“無可否認,黎雄才是高劍父所倡揚的‘現代國畫主張最忠實、最富于實績的實踐者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藝術道路,也是高劍父藝術理想的一種折射。”
二
寫生在黎雄才的藝術行程中具有特別的意義。
從春睡畫院到留學日本,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西南西北,黎雄才都在寫生。如果說,此前的寫生多著意于觀察和技藝訓練,在于收集素材和紀實,新中國成立后的一系列寫生,則促成了他在藝術創造上質的升華和意境的轉向。
特別值得提及的,當是中國美術館所藏,長達二十八米的《武漢防汛圖卷》。一九五四年夏季,百年不遇的長江洪災威脅到數百萬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當時武漢中南美專師生無一例外投入到驚心動魄的防汛搶險工程之中。正值壯年的黎雄才奔忙于泥濘坎坷的沿江堤岸,一邊參加搶險,一邊奔走寫生,晚間回駐地還對畫稿加工整理,常常忙至深夜。防洪搶險之后,黎雄才經一年多苦心經營,在大量寫生稿的基礎上創制出《武漢防汛圖》長卷。這一作品出色地運用了山水畫長卷形式, 場面恢宏,內容繁復,綿延數百里的抗洪防汛敘事一段段鋪陳推移。全圖氣勢恢宏,首尾貫通,細部刻畫精到。水墨渲染,青綠著色,干濕并用,層層暈染,雨云籠罩,水天一色,樹木、房屋、人物等遠景近景虛實有序,起伏跌宕中透出史詩般的的音樂感。
《武漢防汛圖》一問世即備受矚目。它不僅贏得“抗洪史詩”之譽,也在實踐上對50年代初期“中國畫沒有反映現實生活尤其是反映大場面斗爭生活的能力”之類的詰疑,作了很好回答。《武漢防汛圖》整合了黎雄才人物畫、花鳥畫方面的過人能力,進而創造了一種新的山水畫表現范式。這是他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來不斷寫生從量變到質變的一個直接成果,標志了黎雄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一個創作高峰期。另一個意義在于,傳統山水的空靈飄逸,由此轉入現實生活的真情實景中, 山水畫被注入新的內涵。 由出世而入世,這是一種與新時代相連的轉型。
黎雄才《武漢防汛圖》寫生稿與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西北寫生稿,可印證他在觀念和方法上,是如何在一步步延續、豐富與深化了“寫生”的內涵。他之寫生,多以毛筆直接對景揮寫,筆法精準,線條流暢,其對毛筆的使用已達揮灑自如、物我兩忘程度。他說過:“寫生方法有二字:一曰‘活,二曰‘準。‘活則物我皆活,能活則靈,靈就能變;活無法定,法從對象而生。物有常理,而動靜變化則無常,出之于筆乃真神妙。所謂神妙即熟極而生,隨手撿來,便是功夫到處。‘準一般來說不離其形,準則重規,目力準則下筆才準。形與神要合一,若只求形似,是非畫也。”
一九五九年,他開始關注韶山這一類革命題材,曾以嶺南式的筆墨對毛澤東故居及周邊場景作了很具現場感的精到刻畫。及至后來的《朱砂沖哨口》《長征第一山》《延安之春》等一系列革命圣地題材作品,黎氏山水的個性風范日漸凸顯并且鋪陳出來。
黎雄才的山水,技法上直接承傳自高劍父的并不多,而董源、巨然、大小米、馬遠、夏圭、倪瓚等人的筆法卻若有若無,轉益多師而能水乳相融。他強調“有生命,有生活感受,這正是傳統山水畫所缺少的”,重視新意境與新精神。而在形式語言上,墨重于色,突出筆法的“揮寫”意趣,雄偉壯麗與秀潤清新融為一體,這與畫中要傳遞的鮮活的生活氣息十分吻合。他所畫松樹之所以獲得人們交口稱贊,也和他經年累月的松樹寫生分不開。其留下的萬余幅寫生畫,兩千多幅是松樹,從千載古松到嫩綠幼松靡不俱列,枝、葉、根、干細部還設專冊。他的勤奮和專注讓人驚詫,陳金章教授回憶,即使在廣州炎夏,“黎老在小房間里一畫幾小時,全身都濕透。”
從藝術理路而言,同屬嶺南派的關山月、黎雄才都承繼了高劍父的現實精神,他們都努力嘗試突破傳統程式,建構與新時代新生活相連的新的筆墨語言。但比較關、黎的山水畫,在郁勃向上的共性氣息之外,又確實有明顯的區別。對于黎雄才而言,相對恒定的題材對象,長期對筆墨語言的專注,使他在嶺南山水畫的藝術探索方面,得以切入更深的層面,進而構筑起更鮮明的個人風格特色。
三
回顧黎雄才的藝術人生,不能忽略他在美術教育上所作出的貢獻。
在“春睡畫院”前后的清末民初,廣東繪畫業界仍流行一邊作畫一邊授徒的做法。“春睡畫院”的最初形態只是高劍父授徒的“私塾”,尚非現代意義的學校。高劍父曾任廣東省立第一甲種工業學校校長,且先后在國立中山大學、中央大學任繪畫教職。能同時出入于中國師徒制教學與西式現代教育體制之間,也是特定歷史時段的一道另類風景。難得的是,在“春睡畫院”高氏培育下,門人有所成就者頗不乏人。這一點,對于后來關山月、黎雄才的創建廣州美院中國畫系,有著潛在影響。
二十世紀初葉引入中國的現代教育制度,導致了中國畫在傳承方式和藝術規范上的整體嬗變。不僅“嶺南派”,絕大部分傳統的作坊式、師徒傳承式教學方式,均往奉行現代教育理念的學校教育方式,往“學院派”轉換。這是近現代中國教育制度一種根本性的轉換,其孰長孰短,一九二三年梁啟超在《治國學的兩條大路》中已有詰問,至今人們仍在反思。作為現代教育體制中的正規教育機構,廣州美院中國畫系迄今已逾五十年,一直奉行“博采眾長、兼收并蓄”,源于生活與高于生活的辦學宗旨。關、黎創建中國畫系,到楊之光等一代代后繼系主任,幾十年來廣州美院中國畫系的教學當然已遠非春睡畫院式的師徒式傳授。不過,作為一種技藝性很強,需要心手相傳的繪畫藝術,在具體的教學中挪用“師徒制”的某些做法,不僅可行,還很可能構成互補效應。
回想起來,黎雄才雖說進入春睡畫院,早期盡管也像同時許多拜師學藝的學子那樣去臨仿老師畫稿或古代的畫譜,可是他同時也已受到西方藝術教育的影響,更不要說其后還有留學日本的經歷了。明乎此,我們不難思考他教學上的做法,必定是參酌中西教學異同,依自己多年的親身體驗而又權衡再三才作決斷。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筆者曾在廣州美院就讀,適逢黎雄才“文革”后復出教學,曾直接聆聽黎老授課和臨摹過多幅作品。其時他重獲執筆機會,赴粵北連南得一批寫生稿。課程就是對著寫生畫稿及墨本松樹講解寫生要點和作畫步驟,黎老邊講邊執筆示范。畫稿則一連半月張貼在教室,讓學生課余也能臨摹。廣州美院學子大多知道,黎雄才教學一直強調,學習態度必須老老實實,循序漸進,先易后難,不可貪多求快。他主張先打好寫生技法基礎再畫山水。學技法最好從花鳥入手,因其寫生可和實物同等大小,便于細微觀察和直接比較。直接畫山水則難度大增,山無常形,水無定色,寫生時要縮小數百乃至千萬倍,沒有相應能力難以把握。這些,都是黎雄才多年創作體悟和教學經驗總結,彌足珍惜。
陳金章教授回憶說,黎雄才經常親自畫教材。在廣州美術學院的許多課程,都由他親手編寫和繪制范本。“剛入廣州美術學院國畫系的學生都會學習黎雄才親筆繪畫的石頭教材。單是教第一幅石的入手法,黎老當時畫了六塊石頭,非常仔細,反復琢磨才畫好。我當時非常不解,問他為什么這么認真地畫石頭?黎老告訴我,每一處敗筆都可能影響成千上萬的學生,所以一筆都不能錯。”陳金章還說到,為了備好山水課教材,黎老先后認真畫了六百多幅基礎課教材。《黎雄才山水畫譜》《黎雄才畫選》出版后影響廣泛,很重要的價值便體現在美術教育的應用。黎雄才在教學中常對學生說:師承古法,不能拋開前人,也不能古而不發。寫畫的藝術,就是用文房四寶加國畫顏料表達物象質感和作者意趣。畫什么要似什么,要和攝影照片有區別,要有國畫的韻味,要反映出宣紙、毛筆、水、墨和顏料等材料的特殊效果。這些見解,要言不繁,對于學生是金玉良言。
半個多世紀中,廣州美院培育的學生,許多已成為知名畫家或美術領域中的翹楚。黎雄才與關山月、楊之光等人,在廣州美院開創了一套獨有特色的中國畫教學法,這與北京、杭州以及其他美術院校的方式都有明顯區別。進一步梳理和總結,相信可為中國美術教育提供有益的經驗。
作為與關山月相提并論的嶺南畫派中堅畫家,黎雄才作出了重要貢獻。其成就主要在于:一、繼承和拓展了嶺南畫派的藝術;二、創作了《武漢防汛圖》《朱砂沖哨口》等標示二十世紀中國畫成就的經典作品;三、以富于個性特征的筆墨語言豐富了二十世紀山水畫的表現力;四、為新美術教育體系提供了新鮮而重要的經驗。由是,黎雄才的意義,不僅在于嶺南畫派,更在于生機郁勃的二十世紀中國畫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