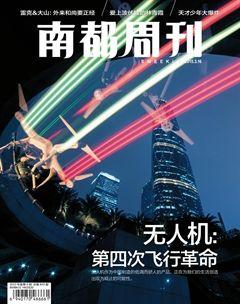銀行降準,不如降息
任志強
經濟在下滑之中,大家都在預期央行會“降準”,果然超出預期的央行提前采取了降準的行動,但降準0.5個百分點就能改變經濟的下行趨勢嗎?不能,至少一次降準拉不動。
許多人在預測降準之后會對中國的經濟起到刺激作用,尤其是對房地產市場是一種利好。其實一次降準幾乎對房地產市場沒有絲毫的影響。但如果降準能促進整體經濟的活躍,倒有可能緩解民眾對經濟下行的擔憂,增強預期消費的信心。
單純就房地產的消費市場而言,降準遠遠不如降息的作用大,降息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實際支出,等于降低了房價。
一是,從總量的支付上看,降息影響到因利息支付而增加的房價總量,讓實際的房價下浮的實惠落入消費者的口袋。
二是,降息會讓按月計算的家庭收入用于還房貸的比例會發生變化。個貸低息時,家庭支付月供的比例也許只在40%左右,但利息的上升有可能讓月供的比例超過了60%,即可能讓消費者失去了購房貸款的資格,也讓月生活的壓力難以承受,或放棄購房的交易行為。
而降準并不會直接影響消費者的支付能力,尤其是當住房市場中的投資行為在多年的限制與打擊之下,逐步退出市場時,降準提供的資金并不會直接或大量地流入市場。
降準會給開發商提供更多的周轉資金嗎?一定會有一部分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但也一定是讓資金本就不十分困難的好企業、大企業獲得的更多,而中小企業難以獲得。
中小企業是否需要大量的流動資金支持?是。市場中由于2014年銷售情況回落,庫存大量增加,確實部分企業捉襟見肘,資金周轉困難,開發商的資金增長率已經降到了幾乎為零,但銀行會將開發資金大量貸給那些銷售不中用且看不到前景的企業嗎?不會的。于是錢只會流向擴大再生產的能力之中,而具備這種能力的恰恰是那些好的企業。
中國的房地產承擔著多重的任務,除了解決居民住房、改善城市面貌之外,還被當作支撐中國GDP增長的經濟支柱。在一個長期靠基本建設推動經濟增長的國家,幾乎所有經濟波動都是用擴大或抑制基建來調控的。經濟下滑時放松貨幣、減免稅費、擴大投資,經濟上漲過快時,限制信貸規模、限制市場交易、加大稅費,尤其是價格上漲時,更是限制消費行為和個貸。
于是當調節經濟運行成為首要任務時,解決住房、改善城市面貌就被當成次要功能。當市場無力擴大投資時,政府就用計劃任務的保障拉動經濟增長,而根本不管市場中的供應量變化和對消費行為的沖擊。只要拉動了經濟的增長,這些蓋出來保障房有沒有人住就不重要了。
如果降準希望用貨幣增量支持保障性住房的上馬,以拉動經濟的增長,那么這對市場化的商品房而言,只能是災難。
被擴大化的棚戶區改造已經從早期的工礦區進入到成市的核心區,從普遍需要用實物住房安置變成了大部分可以用貨幣安置。但棚改的改革中仍以住房實物安置為主。原本房改時就希望徹底改變實物安置的方式,實現貨幣化、市場化轉換,但棚改區中的政策補償無法用貨幣支付,這就又回到了磚頭補貼的老路,變成了實物補貼與安置。
當這種政府行為的“棚改”(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居住權利保障)力度越大時,對市場的沖擊與破壞性威力越大。不但轉移了消費群體的消費欲望,而且打亂了市場中的價格信號、供給信號和需求信號,讓完全市場化的開發行為成了政策的犧牲品。
今年1月份的外貿出口和CPI、PPI的數據都顯示了經濟下行的壓力在加大,下行的趨勢并未改變。一次降準既不能改變下行的趨勢,也不可能讓房地產的投資增長和上升,尤其不會改變市場中的供求關系。
真正要解決房地產市場中的問題,更多的不僅是靠貨幣的寬松,還要改變非市場化的行政干預,改變社會與民眾對市場的預期,才能讓市場的經濟規律發揮自我調節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