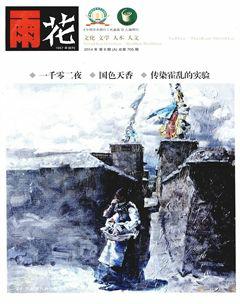風(fēng)俗人物
劉仁前
“香河”,一個被作家潛心打造的地方,靜靜流淌的一段舊時光,走來了換糖的吳麻子、扎匠“細(xì)辮子”、挑水的水生,做著不同營生的他們,肩頭都有著一副擔(dān)子,擔(dān)著自己的日子,擔(dān)著自己的喜怒哀樂,演繹出一段又一段的酸甜苦辣。吳麻子
初春,中午的陽光,親切地照在吳麻子坑凹不平的麻臉上,暖暖的。吳麻子蜷在屋前土坯墻根下,瞇著眼,似睡非睡。細(xì)看,方發(fā)覺,吳麻子正盯著墻旯旮里,那副舊糖擔(dān)子出神。糖擔(dān)子空著,僅剩兩只空籮筐,一根木扁擔(dān)。靠墻根,一只裝糖塊用的敞口木盒,折成兩半了。吳麻子給摔的。殘了。木盒板上,尚未褪盡的白色,亦在佐證著籮筐先前的用場。明眼人一望便知,木盒上的白色,是主人裝糖時,怕沾板,撒的爽手粉。吳麻子眼中的糖擔(dān)子,在初春中午陽光的照射下,特親切。歪斜著的籮筐,折射著陽光,篾色金黃,燦燦爛爛的樣子,叫吳麻子心頭暖意頓生。吳麻子依舊蜷在墻根下,一動不動,瞇著眼,盯著那副糖擔(dān)子。眼角竟?jié)駶櫫恕?/p>
吳麻子肩頭離了那副糖擔(dān)子,有好幾年了。一離了糖擔(dān)子,渾身的精氣神亦不知跑哪兒去了,整日不言不語,沒精打采。鄉(xiāng)民們見了,像是換了個人,便嘆惜道:“吳麻子,這個人,唉!”鄉(xiāng)民們這“唉”意何在,說不清。
吳麻子原先是個換糖的。說是換糖,而不叫賣糖,雖為鄉(xiāng)里人習(xí)慣叫法,然一字之差,意味相距甚遠(yuǎn)。“換”,固然潛含“賣”之意,但不等同于“賣”。其時,鄉(xiāng)里人,不論老幼,到糖擔(dān)子上,拿得出錢來買糖的,極少。多半是用家中廢棄的物件,去換糖,或是芝麻糖,或是薄荷糖,抑或是梨膏糖。用以換糖的物件,多半是女人每日梳頭所梳下的頭發(fā),牙膏殼子,鵝毛鴨毛之類。由此可見,吳麻子這一行,被鄉(xiāng)里人稱之為換糖的,極為貼切。
吳麻子挑了副糖擔(dān)子,敲著小銅鑼,走村串舍,做自己的營生。其家當(dāng)頗簡,前一只籮筐上,放有一塊木板,長方形,四周有矮邊,兩個籮筐口那般大小,專放梨膏糖用的。木板上除去梨膏糖,還有一副敲切梨膏糖用的刀、錘。換糖的,憑著收取物件的價值,在又大又圓的糖邊子上下刀,用小錘子在刀背上一敲,便敲出一小塊梨膏糖來。這當(dāng)中,人家拿來的物件價值如何,全憑換糖的估算,可換得多大的梨膏糖,亦全憑換糖的下刀用錘。或多或少。憑換糖的良心。自然,也有換糖的不公道,低估人家所送物件的價值,少給糖,以致前來換糖者與之吵鬧起來,小孩拽了糖擔(dān)子不讓走的。這當(dāng)兒,村民們便會站出來,說句公道話,指責(zé)那換糖的,不講良心。糖擔(dān)子的后一只籮筐上亦有木板。不過,不是放梨膏糖用的。而是,放滿了一只一只糖盒子。一只盒子里一個品種,有薄荷糖,圓圓的,渾身沾滿了亮晶晶的白糖粒兒;有芝麻糖,外表沾一層芝麻,做時有切成菱形,有做成小棍棒一般的;也有包了一層裝飾紙的硬糖塊。這種糖多半不是換糖的做的,是進(jìn)的城里商店,或糖煙酒公司的,顯示自身檔次的。此糖用東西換是不行的,得拿錢來買才行。不用說,一副糖擔(dān)子,就數(shù)這一頭東西金貴了。怎么倒擱在身后了呢?你沒見,那一只只糖盒子上,均有玻璃抽蓋,盒子是上了鎖的。打換糖的歪主意,難呢。說了半天,兩只籮筐難不成僅當(dāng)架子之用么?那也不是。筐內(nèi),便是存放換糖時所換得的各式各樣物件。一個換糖的,走村串舍,一天下來,兩只籮筐能滿筐而歸,那就開心煞了。
“鵝毛鴨毛換糖啊——”
“牙膏殼甲魚殼換糖啊——”
吳麻子的吆喝聲在村巷上響起,小孩子們嘴里的小饞蟲便在動了。不一會兒,簇得吳麻子的糖擔(dān)子,走不開身了。吳麻子索性擱下?lián)樱弥°~鑼,“別急,別擠,一個個來。”
“兩只鵝毛,換薄荷糖!”
“嗯,兩只鵝毛分量不少,多給你幾個薄荷糖丸。”吳麻子掂量著鵝毛,往籮筐里放。
“一只甲魚殼,換芝麻棍子!”
“哎呀,小兄弟,這甲魚殼,踩碎了,不值錢了呢。換芝麻棍子不行,給切點(diǎn)梨膏糖,可好?”吳麻子捧著破碎的甲魚殼替小兄弟可惜。
“小老弟,你想換什哩?”吳麻子在人群中發(fā)現(xiàn)一個小光頭在糖擔(dān)子跟前轉(zhuǎn)來轉(zhuǎn)去,便主動詢問。
“想吃糖!”小家伙大概五、六歲,一只手扒在嘴里,含含糊糊地說。
“去,家去到鍋灶旯旮里找找看,媽媽梳頭的頭發(fā),有沒有塞在灶殼里。拿了來,有糖吃!”吳麻子一邊照應(yīng)其他人,一邊幫小饞貓出主意。
“不能走啊!”小光頭抬腿往家溜。還生怕吳麻子哄他走。
“小鬼精,麻爺爺什呢時候哄過你?快去找!麻爺爺?shù)饶恪!眳锹樽右槐菊?jīng)對小家伙承諾。
一根紙炯的工夫,吳麻子糖擔(dān)子跟前,松散了許多。
“來了,來了。麻爺爺!”小光頭沒能從灶殼里找到媽媽梳頭的頭發(fā),倒將媽媽給拽了來了,老遠(yuǎn)就喊起來。
“你看這饞小伙,家里東西都被他找光了。便拽我來。”年輕的媽媽站在吳麻子糖擔(dān)子跟前,很為自己拿不出東西來換取兒子的“想頭”而難為情。
“咳,沒關(guān)系,沒關(guān)系。來,麻爺爺幫小饞貓解解饞。”吳麻子笑呵呵地,拿起敲梨膏糖的刀錘。
“這怎么好意思,這怎么好意思呢。你這小饞貓!”年輕的媽媽從吳麻子手上接過梨膏糖,往兒子嘴里送時,用手輕點(diǎn)了一下自己的寶貝。
望著母子倆挺感激的樣子,吳麻子挑起擔(dān)子,丟下旬“回見”,開心地走了。
吳麻子給村民們帶來的是甜蜜,也從村民們善意的笑臉上獲得一種滿足和快樂。吳麻子的糖擔(dān)子,一直在肩頭這么挑著。吳麻子的日子,一直就這么有滋有味地過著。
不知什么時候,村巷上來了個打洋鼓的。打洋鼓的跟吳麻子換糖有什么妨礙沙?你聽,打洋鼓的在村巷上洋鼓打得震天響,邊打鼓邊唱呢——
“小朋友吃了我的梨膏糖啊,好好學(xué)習(xí)(那個),天天向上。”
“老年人吃了我的梨膏糖啊,長命百歲(那個),身體健康!”
“咚咚咚,咚咚咚……”年輕小伙子的洋鼓敲得香河村大人小孩心頭癢癢的,還有那現(xiàn)編現(xiàn)唱的詞兒,更是讓鄉(xiāng)里人新鮮,好奇。小伙子的糖擔(dān)子四周簇滿了人,有換糖的,有聽說唱的,有看西洋景兒的。村上的那幫細(xì)猴子,更是歡。這洋鼓“咚咚咚”地打到哪兒,細(xì)猴子們便跟到哪兒。
“鵝毛鴨毛換糖啊——”
“牙膏殼甲魚殼換糖啊——”
吳麻子的吆喝聲再在村巷上響起時,竟沒人去注意,去理會了。香河村人似乎在一夜之間,把吳麻子這位多年的老朋友給遺忘了。沒人聽吳麻子的吆喝了,亦沒人簇著吳麻子的糖擔(dān)子了。人們被打洋鼓的小伙子吸引去了。打洋鼓的小伙子,不僅洋鼓打得好,說唱好,糖擔(dān)子上花花綠綠的紙?zhí)且埠谩?/p>
“該死的打洋鼓的。”吳麻子望著簇在打洋鼓周圍的大人小孩,心頭頓生恨意。這可是在吳麻子溫溫和和大半輩子生涯中極少有的。在吳麻子的記憶中,好像從未真正恨過誰。此時此刻,那個打洋鼓的小伙子,讓吳麻子如此難堪。如此冷落。如此難受。可恨。望著搶了自個兒飯碗的人,吳麻子只得沒聲沒響地,挑了糖擔(dān)子離開。這當(dāng)兒,村巷上,洋鼓敲得正鬧——
“咚咚咚,咚咚咚……”
不見挑了副糖擔(dān)子的吳麻子,有些時日了。香河村的人們,偶或提及,“吳麻子,好人啦,唉!”
一副跟了吳麻子有了年頭的糖擔(dān)子,吳麻子咬咬牙,硬是丟掉了。那一晚,平時滴酒不沾的他,桌上那盤花生米兒,一粒未動,一口氣干掉了“二兩五”(早先時一種小瓶裝酒),叫家中兩個大姑娘瞪大了眼,直愣神。吳麻子如此英雄氣概,在女兒們看來,真有點(diǎn)兒不可思議。
一離了那副糖擔(dān)子,吳麻子似霜打了一般,蔫蔫的,沒了原先的鮮活勁兒。整日里什么也不想干,悶在屋內(nèi),出門極少。偶或,天氣好,便是蹲在屋前墻根下,曬太陽。
一晃好幾年過去。香河村巷上再響起吳麻子的吆喝聲時,是近幾年的事了。見過吳麻子的都說,吳麻子人雖老了,挺精神。聽說吳麻子改行了。吳麻子兩個姑娘在城郊開了個雙妹饅頭店,吳麻子給女兒打工,叫賣饅頭了。你聽——
“饅頭,賣饅頭啦——”
“細(xì)辮子”
“細(xì)辮子”本名叫什么,村子上大小人等,能說得上來的,不多。
“細(xì)辮子”四、五十歲了,生就一副長茄子臉,鼻大,眼細(xì),嘴尖。茄瓜頭上梳了個辮子,不長,細(xì)細(xì)的。平日里多半盤在頂上。一個大男人,竟有此等玩意,在全村找不出第二個來。一村人以為奇。于是乎,有人便喊他“細(xì)辮子”,給起了個綽號。當(dāng)?shù)卮迕瘢徽撃信嫌祝芯b號者十有八九。只要稍微沾上點(diǎn)兒邊,這綽號便上了身,怎么辯解均沒用。有了綽號,一經(jīng)叫起,一村人立馬全知,傳播極快。不是說,“碗口大的莊子,筷子長的巷子”么,一村二、三十戶人家,百十來號人,有什么事,一陣風(fēng)似的,還不容易。“細(xì)辮子”便成了完完全全的“細(xì)辮子”了。村上沒人追究其本名了。“細(xì)辮子”整日掛在村民們嘴上,“細(xì)辮子”本人亦不在意。符號罷了,叫啥都一樣。“細(xì)辮子”的話沒說出嘴。
“細(xì)辮子”是個扎匠。“扎匠”是鄉(xiāng)里人叫法。其實(shí),就“細(xì)辮子”從事的營生而言,稱之為“篾匠”方為準(zhǔn)確。因?yàn)椋凹?xì)辮子”手中盤來弄去的,均是些篾器物件。為什么叫“扎匠”,而不叫“篾匠”呢?根子通在手藝人自己身上,怪不得村民。在香河村,根子自然便是通在“細(xì)辮子”身上。全村就他這么個“扎匠”。你聽,“細(xì)辮子”來了——
“……箬子、淘籮子扎啦——笆斗、籮筐扎啦一”
在鄉(xiāng)里,明明干是篾匠活計,一開口,便是“××、××扎啦——”天長日久,村民們頭腦中的“篾匠”,便喊成了“扎匠”。其實(shí),鄉(xiāng)里的扎匠,真正給人家扎東西的極少。
吆喝聲漸近,“細(xì)辮子”便見著影子,出現(xiàn)在跟前了。但見他,頭盤小辮子,肩挑扎匠擔(dān)子。這擔(dān)子,一頭是工具箱,另一頭是材料架。掛工具箱的一頭頗簡潔,四根算不得粗的麻繩,拴在一只工具箱上。那工具箱,木質(zhì)結(jié)構(gòu),橢圓形狀,小臉盆一般大小,尺把高,有底有幫,上口用木板封了一半,留有半圓形的敞口。里面是裝劈竹子用的劈刀,刮篾條子用的刮刀,撬環(huán)扣的撬刀,以及扎眼用的錐子之類。不僅如此,工具箱還是主人做工時的蹲身之處。作用似一張小“爬爬凳”。擔(dān)子材料架的一頭,望上去要繁亂一些。敞著,僅底是實(shí)的,不至掉東西,四周有篾環(huán),材料可依可靠,且取時方便。主人一伸手,抽而取之,不費(fèi)難。
“細(xì)辮子”靠這副扎匠擔(dān)子糊口。別看“細(xì)辮子”鼻大,眼細(xì),嘴尖,可“細(xì)辮子”一雙手,特巧。誰家淘米籮壞了,篾扁子被老鼠咬破了,笆斗丟在墻角里被潮濕氣爛了幾根筋,扛稻扛麥用不上了。“細(xì)辮子”沒二話,全管。那副寶貝擔(dān)子往巷頭上一擱。家中壞的、損的、爛的物件,一樣樣,全拿了來,“細(xì)辮子”會一樣樣給收拾的包你滿意。給“細(xì)辮子”收拾過東西的,都說“細(xì)辮子”手藝真好,會收拾。
若是碰上僅需篾條插補(bǔ)的器具,但見那篾條在他手指間,纏來繞去,在器具上或插入,或拽出,亦是出入自如,頗似女兒家做女紅一般,輕快,嫻熟。如此一來,他修補(bǔ)過的東西,不僅比先前好用,且結(jié)實(shí)、耐用了許多。但凡村民們夸他手藝比外村過來的扎匠精時,“細(xì)辮子”則搖搖頭,“錯矣。錯矣。”繼而細(xì)細(xì)道出個中原委:這小修小補(bǔ)之類,之于一個長時以此為生的手藝人,算不得什么。關(guān)鍵看他是否肯給你用工夫,肯給你用好料子。肯用工夫,手上必然細(xì)致些,周密些,活計出手就中看;肯用好料,自然結(jié)實(shí)、耐用。尤其是篾制物件,或插或補(bǔ),用篾青與用篾黃,則大不一樣。篾青為竹子取篾藤時的第一道,屬表皮,柔性,韌性,均好。篾黃則是取了篾青之后的第二道,屬內(nèi)層,柔性,韌性,與第一道篾青相比,差了很多。“細(xì)辮子”尖嘴角邊,說得生起白沫了。圍了擔(dān)子聽他講經(jīng)的,一個勁兒“嘖嘖嘖”地直夸,“細(xì)辮子”肚子里名堂大呢!
“細(xì)辮子”呢,說歸說,有一樣是忘不了的:取東西,收錢。其實(shí),那時真正給錢的極少,多半是兩只雞蛋,或是半碗米之類。“細(xì)辮子”,靠這活呢。
“細(xì)辮子”純純粹粹一個手藝人,是個扎匠。村子上,整日都會飄蕩著“細(xì)辮子”的叫喊聲——
“……箬子、淘籮子扎啦—笆斗、籮筐扎啦一”
“‘細(xì)辮子,跟我把淘米籮子扎下子。”
“祥二嫂子,淘籮子放下來,手上篾扁子插好,就跟你扎。放心,快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