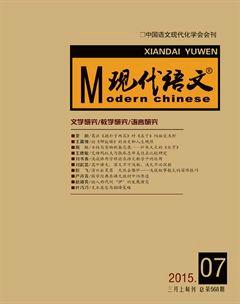陶淵明《桃花源記并詩》與王維《桃源行》比較研究
徐思穎
東晉時期,陶淵明作的一篇《桃花源記》,為我們描繪了一幅遠離世俗、猶入夢中的隱逸世界的美好圖畫,刮起了桃源詩創作的熱潮。以一篇流傳四海的奇文作為原點,以其所代表的世外桃源的理想、歸隱田園的情結為支撐,桃花源已儼然成為一個獨特的文化氣場,千百年來帶著筆墨的清香輻射浸染著無數人的心靈。據悉,自東晉以來,歷代關于桃花源的詩文多達二、三十萬字。本文就陶淵明《桃花源記并詩》與王維《桃源行》作一比較。
要談《桃花源記并詩》,首先得理解陶淵明的思想。
陶淵明崇尚“真”,“真”與世俗禮法相對立,指的就是人類自然的本性。他抱著“抱樸含真”的態度,保持這種本性,以免受禮教的約束或名利的縈擾。在陶淵明看來,一個人只要善于養真,保持真想,就能獨立于污濁的社會之外了。
“抱樸含真”又體現了陶淵明的社會理想。他認為上古生民是最真樸、最淳厚的。他的理想是擺脫禮教加在人身上的種種巧飾、虛偽和名利的欲望,恢復上古時代人類的自然本性。若人人都能如此,那么社會的污濁丑惡就可以隨之消除;一個淳樸的“傲然自足”的社會就可以建立起來。他的《桃花源記并詩》生動具體地描繪了這個“抱樸含真”的理想社會的圖景。在這里,“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制”。“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沒有人為的智巧。“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人們愉快地從事著勞動。“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沒有王稅。這自給自足、自然自得的桃源,便是陶淵明社會理想的體現。他在講“真”的同時也講到“淳”:“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桃花源詩》)“淳”有厚、清、樸等涵義,與“真”正可以互相引發。在陶淵明看來,上古伏羲、神農、軒轅、唐堯之世,三皇、五帝之時,社會是淳樸的,后來漸漸失去淳樸,而有了九流之分,九流互相推隕,社會也就變得日益澆薄了。只有在桃花源那樣的世界才保留著上古淳樸之風,而成為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這樣,陶淵明關于“養真”的哲學思考遂進入社會歷史的范圍,帶上了對當時社會的批判色彩。
那么陶淵明的社會理想,是如何體現在他筆下那個自給自足、自然自得的桃源的呢?他筆下的桃花源又是什么樣子的呢?從《桃花源記并詩》的描繪中可以看出:
首先,桃源沒有戰亂的騷擾。盡管外界亂戰蜂起,政治舞臺上猶如走馬燈一樣的變化,這里卻是“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童孺縱歌行,斑白歡游詣”,兒童和老人“并怡然自樂”,到處是一派和平寧靜的景象。
其次,這里沒有嚴酷的剝削。桃花源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人們在“其中往來種作”,“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余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早晨,大家相互招呼著一起去耕作,日落時就回家各自休息;因為耕種及時,到處桑竹成林,菽稷遍野。而這些勞動成果都屬于勞動者所有,春天收絲,秋熟打谷,都用不著繳納王稅。因此,在桃花源里人人勞動,大家都過上了豐衣足食的生活。
第三,這里民風淳樸。桃花源里的人古道熱腸,一見到漁人,“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鄰居們也紛紛前來探望,并“延至其家,皆出酒食”,熱誠款待。這里沒有標志朝代更迭的紀歷,歲月悠悠,“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世間的機詐智謀在這里毫無用處,大家都在簡樸自然的生活中得到最大的滿足。
顯然,這個“世外桃源”是作者虛構的一個理想洞天,是現實社會的對立物。陶淵明生逢“八表同昏,平陸成江”的亂世,他和飽受磨難的廣大人民一樣向往著和平、安寧。據考,陶淵明作《桃花源記并詩》時乃宋武帝永初年,陶淵明將近60余歲,且在家隱居。那么我們不難理解,在看過那么多困苦失“真”的現實生活以及經歷了那么多政治上的不如意之后,心中產生了這樣一個烏托邦社會。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將避世深山的神異傳聞作為創作素材,“直于污濁世界中另辟一天地”,借以表達自己的社會理想。值得注意的是,桃花源雖屬虛構,但并非是仙境,這里的一切,無論是“土地平曠,屋舍儼然”的景象,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情景,或是那一股古樸淳厚的鄉情,都是我們在陶淵明的田園詩中常常見到的。
相較于陶淵明筆下煙火氣息較重的桃花源,雖然王維在意象與詩文大意上都承襲了陶淵明,但王維并沒有滿足于對陶詩的綜合和模仿。王維十九歲時作《桃源行》,青年時代的他有著美好的生活理想。王維把桃花源改造成為“靈境”——一個遠比眼前的盛世更為美好的沒有紛爭、沒有沖突、自由、和諧、純凈的“塵外世界”,而《桃花源記》中有關漁人經歷的敘述式語言,也為王維那種意在表現主觀感受的濃烈抒情語言所代替。原先的《桃花源記》反映著亂世之人渴望物質生活樂土的心理,而經過這番改造的“桃源”,卻分明反映著王維本人及其同類知識分子對精神生活樂園抑制不住的向往。不是基于對現實社會的強烈不滿,不是由于政治上的挫折或其他生活打擊,剛剛處在人生開始階段的王維,即悠然神往一個任何清平盛世都無法比擬的和諧、自由、純凈的世界,這顯然是一種企圖突破現狀,向時代、向生活提出更高要求的表現;不是基于兵災戰亂的刺激,不是由于面對衰落凋弊社會而產生的絕望心態,剛剛動筆設計自己人生藍圖的王維,即對如此世界作如此熱情的謳歌,這顯然表明,一切世俗享受(例如建功封侯、名垂青史的榮譽,飛黃騰達、列鼎而食的富貴)都很難引起這位年青詩人的強烈興趣。他渴望的是另一種更高境界的生活——現實社會的矛盾和沖突都消融于完美、和諧之中的生活,一切壓抑、束縛和對他人意志的屈從,都為無拘無束的自由和永恒的心靈平靜所代替的生活。
此外,他還將桃源意象仙化了。翁方綱說:“古今詠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極。”(《石洲詩話》)從其《桃源行》中“驚聞俗客爭來集,竟引還家問都邑”“初因避地去人間,更聞成仙遂不還”“不疑靈境難聞見”“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等諸多語句中可見其作已有將桃源仙化的傾向。對于這一意象的遷變,新加坡學者王潤華有精道的論述,他說:“陶淵明的桃花源只是一個逃避亂世的、沒有兵災人禍的空想樂園,一個政治烏托邦;而王維的桃源行是一個神仙境界,他避開寫實的細節,通過靜謐、虛幻、奇妙的境界,表現一個屬于宗教的、哲學的烏托邦,一個仙人樂土。”
無論是七十而從心所欲的陶淵明,亦或是將及弱冠的王維,一個是新引與創造,一個是傳承與發展,他們都為我們展現了一派因懷有美好理想而存在的凈美的世外之景。兩位文人結合自己獨特的思想與高超的文筆,創作出這首詩作,具體描繪了桃源美景,既涵具文化的、歷史的寓意,也呈示了社會的、心靈的真實,值得我們品味學習。
(論文指導老師:周海平)
參考文獻:
[1]袁行霈.陶淵明研究[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9,20,60.
[2]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M].巴蜀書社,1988:235.
[3]梁瑜霞,師長泰主編.王維研究[M].江蘇大學出版社,2011: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