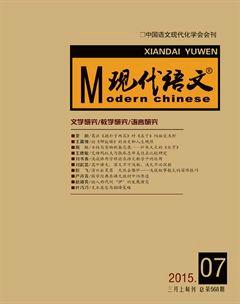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海派女作家筆下的“異鄉”上海
李鑫
摘? 要: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上海,因戰爭的到來,致使文化界的繁榮一度中斷,日偽的文化鉗制使主流文人集體失語。正在此時,一批具有青春活力的海派女作家登上歷史舞臺,在城市與女性的情感糾結中勾勒著上海圖景,而她們筆下對上海異鄉之感的描摹更是道出女性視角的獨特。
關鍵詞:海派? 異鄉? 上海
上海自開埠以來就以其飛速的發展告訴整個鄉土中國,它是一個“異數”。繁華的商業街,林立的歐式建筑,摩肩接踵的人流,“顯示了上海作為當時中國最繁榮,最有活力的經濟中心、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作為遠東第一大都會的復雜圖景”[1]。三十年代的上海,摩登時尚,文化氣氛開放,因為其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氣度促使海派的文化呈現出一種出離于傳統鄉土文化的全新文化品格。古老中國文化浸染下的兒女一遇到這種全新的文化特質,便在第一時間內做出了反映。新感覺派感受到新的文化特質在上海生根發芽,體味到了其帶來的聲色犬馬的現代生活。他們迅速地與傳統決裂,沉浸在都市文學的書寫中不能自拔。到了四十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已趨于成熟,而正在此時,戰爭的到來中斷了文化的自由發展,日偽的文化封鎖造成了上海文化界的集體失語,一派繁榮的上海文壇失去了往日的活力。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海派女作家正是在此時登上歷史舞臺,占據話語空間,繼續著海派文學的繁榮。除了張愛玲外,還有蘇青、施濟美、潘柳黛等女作家。她們在主流失語之時橫空出世,以獨特的女性視角觀照上海,將這座真實的城市通過回憶、重組、書寫變幻成“文學中的城市”,在女性命運與上海之城相糾結時流露出深深的異鄉之感。
一、文化心態上的疏離與拒斥
高度發達的上海都市文明培育了中國最早的一批都市新民,他們擁有摩登的生活方式,前衛新潮的思維模式,在上海這個超級大都市中如魚得水。然而翻開四十年代海派女作家的沉卷,我們發現了另一個上海,一個背景式的上海。這一意義上的上海在施濟美筆下頻繁閃現。與張愛玲對都市生活的狂熱不同,一些女作家表現出對都市的恐懼、厭惡、逃避等情感取向。歸根結底這是對上海都市文化的疏離,在她們筆下的上海始終是“異鄉”,從來不曾有過歸屬感。
施濟美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上海是個頂壞的地方,按照她的表述,上海是比監獄更壞的地方。然而成名于上海文壇,且作為多家通俗刊物銷量保障的施濟美為何始終視上海為異類呢?深入她的生平和作品,我們不難找到答案。施濟美生于書香門第,父親留洋歸來后在外交部工作,母親是名門閨秀,能吟詩作賦,祖父是揚州的地方官。施濟美的母親常帶著一雙女兒去揚州侍奉老人,祖父家中藏書極豐,又有許多名家書畫。施濟美在老宅中深受熏染,精神氣質自然向傳統文化靠攏。祖父家的生活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時隔多年,她仍然難以忘懷:“花白胡髭的老先生,僂著腰伏在‘大成至圣先師孔子像前的書案上,握著‘第一人書,白芨磨銀主,顫巍巍的在我們面前的大小楷上畫圈圈兒。”[2]十五歲時,施濟美到上海讀高中,畢業后考入東吳大學。來到上海的施濟美只覺得“上海似乎永遠只是上海而已,不知究竟屬于哪一個國度”[3]。她的精神家園早已有了歸屬,上海與她的文化修養相悖,一個摩登,一個傳統。上海在她的眼里不過是“放浪迷醉的生活,濃郁的酒氣,猛烈的煙味,靡靡之音,瘋狂的跳舞,賭博,一切討厭的虛偽與假裝”[4]。上海對于施濟美來說是個靈魂無所安放的臨時居所,她對于都市文化始終選擇規避,對于穿梭于舞場、迷戀物質的都市人類一直保持著批判的姿態。
《十二金釵》中,傅安妮、李楠孫夢想著成為“上海女人”,不停地學習“處世哲學”、穿衣打扮,最終扭曲了自己。曾經愛情至上的王淑君早已拋棄了信仰變成試圖變賣女兒的市井俗婦。而受人追捧的韓淑慧其實虛有其表,她的婦女參政論文都出自他人之手。上海的虛浮通過幾個女子的描寫被呈現得淋漓盡致。細讀文本我們便不難發現施濟美的謹慎和皈依,她借芳子的口說出:“前天下了大雪,我看見銀色的西湖,真美呀。如果你在這兒,我一世也不要回上海了。”[5]在所有人都確認了一個極正確的消息:“上海是個花花世界”,美好無限時,施濟美卻看透了其中的虛無,她要在這個不屬于她的地方找到一點精神上的寄托,于是我們看到了例如《永久的蜜月》這樣的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體現出了拋棄個人情感、追求人間大愛的崇高精神品格。在商業文化,功利主義大行其道的上海,施濟美以烏托邦式的文學想象來證實自己文化心態與對上海的疏離。她不愿意自己的文學始終停留在對世俗生活不厭其煩的書寫,也不愿意只一味地傾吐個人情感。她所追求的是理想化的精神信仰,面對“魔都”上海,女作家試圖筑起“幾間聊蔽風雨的小屋”。所以她在文學作品中構建著理想化的真善美。《野草》中的寶麗與杜大森苦戀重逢,相約私奔之時,二人卻毅然放棄了個人情感,寶麗開辦孤兒院,實現了社會理想。《三年》中的司徒藍蝶為了成全別人,不惜以毀損自己名譽的方式離開愛人。這種理想主義的表達方式成為施濟美疏離都市文化的策略,并以此構筑自己的精神家園。她以異于上海都市文化的精神氣質闖蕩文壇,醉心于理想主義文學世界的建構,公然標榜自己的客居身份,上海對于她來說是不折不扣的印象,她始終是個飄泊上海的旅人。
二、難以融入的“異鄉”上海
與施濟美同為外來者的蘇青、潘柳黛,也在文中表現出對上海都市生活的力不從心,以及不被認同的異鄉感。女作家筆下的人物雖然努力地適應都市生活,卻也顯得非常吃力。《歧路佳人》中,女主人公小眉初次領略竇家的豪華就備感震驚,“花園旁邊的走道上汽車魚貫而入,都是慢慢開著,像烏殼蟲在爬行。整幢大洋房像火山般吐出炫人的燈光,花園周圍燦爛如星帶”[6]。這時女主人公意識到自己與這里的格格不入,也在心中感到寒傖和可恥。在某種程度上說,女主人公的不安和自卑來自于都市文化的強大威懾。在城市文明面前,自己顯得渺小而終致產生了異鄉的孤獨感。在物質上的貧乏使小眉感到自卑,但是當她試圖安分守己地賺錢時,卻受到了代表上海功利主義的史亞倫的另類勸告:“女人身體也是天然資本之一,在必要時,也得好好利用它。”[7]于是身處旋流中的小眉迷惑了,“不知道該選擇哪一條路走——正當的呢?還是不必要的呢?”[8]突然闖入都市文化的后果是身份不被認同的尷尬及價值觀的迷失。在潘柳黛的《退職夫人自傳》中,“我”也感受到了上海都市氣息的強大,“我走在路上看見的,都是服飾入時,體面而漂亮的男女。他們高傲而營養豐富,我看著他們,覺得我自己就像鄉下人一樣”[9]。不論是蘇青還是潘柳黛,都通過筆下的人物表達了對上海仰慕又自卑的一面,上海對于她們來說是異鄉,她們始終難以融入其中。
在梳理施濟美、蘇青、潘柳黛與上海的關系時,我們不難發現,施濟美對上海是排斥的,她并不為這座大都市的繁華所動,只醉心于自己精神家園的建構。而蘇青、潘柳黛在闖入上海的同時就懷著異鄉人的心態,對上海既愛慕又恐懼,最終也只是滬上的過客。但是不管抱著什么樣的心態去觀照上海,上海最終在女作家的筆下扮演了“異鄉”這一角色。在這個不屬于自己的他鄉中,施濟美找尋激情與精神家園,蘇青筆下的小眉迷失了自己,潘柳黛則以“退職夫人”自居,在都市旋流中不斷掙扎。
(基金項目:2014年度黑龍江大學研究生創新科研項目,項目名稱: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海派女作家的上海書寫,項目編號:YJSCX2014-043HLJU。本文受黑龍江大學研究生創新科研項目資金資助,在此表示感謝。)
注釋:
[1]陳伯海:《上海文化通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6頁。
[2]施濟美:《古屋尋夢》,春秋,1944年,第6期。
[3]施濟美:《郊游兩題》,春秋,1944年,第8期。
[4]施濟美:《三年》,《鳳儀園》,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頁。
[5]施濟美:《十二金釵》,《鳳儀園》,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頁。
[6][7][8]蘇青:《歧路佳人》,《蘇青經典作品》,當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頁,第352頁,第333頁。
[9]潘柳黛:《退職夫人自傳》,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