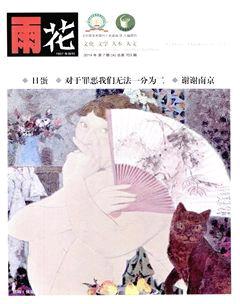歷史記錄,真實了嗎
葛劍雄
以往二十多年間,我到過世界上不少地方,有幸目擊歷史。
1990年夏,我從北京坐火車去西班牙,往返穿越蘇聯,兩次經過莫斯科,目睹紅場上的示威和靜坐,耳聞不同蘇聯人之間的爭論,感受供應的匱乏和民眾的嗟嘆。盡管當時還不知道這是我對蘇維埃帝國僅有的一瞥,卻無意中閱讀了蘇聯歷史的最后一頁。
等我到達東柏林時,兩德正在籌備正式統一。晚上我在火車站下車,詢問明天早上幾點鐘能通關去西柏林,得到的回答卻是:“還有什么關,你現在就可以坐上火車去西柏林的動物園站。”我大惑不解:“不是還沒有統一嗎?”“我們自己早統一了。”果然,我預先辦好的西德簽證根本無人檢查,次日白天見勃蘭登堡下已成通衢大道,花一個馬克租一把錘子,就能盡你所能從“柏林墻”上砸下水泥塊。而東德執政黨大樓已經人去樓空,“人民官”自由出入,局部正在改建為商場。
在布達佩斯,我問一位年輕人:“為什么你們要拆除蘇聯紅軍紀念碑呢?畢竟是紅軍將你們從法西斯占領下解放的。”他反問:“你知道蘇聯紅軍強奸了多少匈牙利婦女嗎?”我自然不知道,而且是聞所未聞的。
2000年3月8日我去臺灣“中研院”訪問一月,正逢“大選”。十天間幾乎天天感受“選情”、“選戰”,“中研院”院長李遠哲發表辭職聲明和《跨越斷層》演講,辭職力挺陳水扁;某大學董事長召集員工,“引導”支持宋楚瑜,而會場不遠處掛著他夫人(國民黨籍立委)為連戰拉票的橫幅;臺師大教師在公宴我的餐桌上一提到選情,就吵得不可開交;15日電視播出朱镕基講話,一青年副研向我表示將改投陳水扁的票。16日晚上,我先后到臺北棒球場、中山足球場和中正紀念堂參觀宋楚瑜、陳水扁和連戰的最后一場造勢會,直覺是連戰已被淘汰出局,而陳、宋之間似乎勢均力敵,但陳的勢頭更大。17日下午4時,我去附近的胡適小學投票站觀看投票,站內氣氛平靜,但即時顯示的計票結果已是陳水扁一路領先,直至晚上再無逆轉。一位朋友邀我們去他家,邊喝酒邊看電視。他的太太是《聯合報》的編輯,居然也悠閑地陪著我們。我很驚奇,今晚有這么重大的消息,報館難道不加班嗎?她說:“早加好了,已經寫好陳、宋獲勝的兩套社評,只等結果出來。”到7時半,“中選委”已公布陳水扁以近40%票當選。
2003年3月29日,我作為嘉賓主持與央視、鳳凰衛視“走進非洲”北線攝制組由突尼斯進入利比亞,從一開始就感受了這個國家的“卡扎菲特色”——國門前看不到國旗,只有一幅巨大的卡扎菲像。在邊檢站的接待室,幾位“人民代表”留了我們近一個小時,聽他們對卡扎菲的贊頌。那位婦女人民代表喋喋不休地說明全世界只有利比亞人民真正獲得解放的理由,因為在領袖領導下婦女也獲得解放。在以后幾天,無論是遍布全國的專供學習卡扎菲著作(已譯成50種文字)的“綠寶書中心”,還是在盤山公路旁巖石上巨大的綠色標語;無論是在規模宏大的國際會議中心,還是設備先進的海水淡化廠;無論是女子學校的升旗儀式,還是市人民代表(相當于市長)的會見;卡扎菲的名字和影響無處不在。主人還特意安排我們去卡扎菲的故鄉,拍攝由他曾經讀過的小學改建的革命博物館,讓我坐在卡扎菲坐過的課桌椅上,聽取館長(他的小學同學)對他不平凡的童年的介紹。4月4日中午,我們突然接到新聞司長朱瑪·艾布赫利的通知,馬上去卡扎菲的住地拍攝。我們分乘三輛車,經過三道戒備森嚴的鐵門和層層安檢,最后來到兵營中那座被炸的小樓。在拍攝過程中我們都在等待,據說有時卡扎菲會飄然而至,但那天奇跡沒有出現。朱瑪說:“我很想幫你們安排,但領袖太忙了。”我只能抓緊時間問了他幾個問題,最后問他:“卡扎菲畢竟年過六十,他考慮過交班嗎?會不會像外界所傳讓他的兒子接班呢?”他回答:“這一切都會由人民作決定。”
作為一位歷史學者,我可以肯定我經歷的這幾件事——蘇東變局、臺灣“大選”、卡扎菲的利比亞——都會載人歷史,我也盡我所能記錄了我的經歷,但我無法預測留下的歷史會如何記載,記載什么。因為在一個資訊發達甚至過剩的時代,無論歷史學家多么希望忠于史實,多么愿意如實記載,卻不得不作出自己的選擇。就是讓我來記載其中某一事件,我也未必將自己的經歷見聞都寫上,每個人所處的地位畢竟相差懸殊,他們的經歷自然不能等量齊觀。至于后人如何使用這些歷史記錄,評價這段歷史,那就更無法預料。
我們今天所知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往往并沒有多少原始記錄作為根據,有的只有唯一的來源,有的只是出于后人的綜合甚至推測。特別是早期的歷史,有些人或事跨越幾個世紀,不同的說法矛盾重重,卻找不到其他足以肯定或否定的證據。但有的人或事卻是孤立的、不連續的,即使完全可信,也填補不了存在的諸多空白。
但是我們不得不驚嘆古人記錄歷史的執著與認真,不怕得罪最高統治者,不避斧鉞,甚至不惜賠上合族的性命。他們記錄歷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們的記錄是給誰看的呢?顯然不是給當事人或統治者看的,當然也不是給自己看的,而是給主宰歷史者看的,而這一位或一群主宰者就是天、神靈或祖先。
中國古代的專職史官是從巫師分化出來的。在條件相當困難的情況下,巫師只會記錄他們認為重要的天象,占卜結果和得到驗證的人事或異常現象,目的是向主宰者報告,或給子孫后代留下有紀念、慶祝、祈念、警戒作用的證據。正因如此,他們必須盡可能保持記錄的真實性,至少在主觀上是如此,同時也要使這些記錄傳之永久,所以要刻在石上,鑄于“國之重寶”(青銅器皿),收于“天府”,藏諸名山。
隨著文字的發展和完善、記錄手段的簡化和改善、記錄對象和內容的增加,史官最終從巫師中分化出來,但其主要特點還是得到了繼承和延續,堅持記錄的真實性就是重要的原則。因為天、神靈、祖先是不可欺瞞的,否則就會受到天譴或報應。于是就產生了孔子的“《春秋》筆法”,通過用詞的貶褒對同樣的事實作出不同的評價,以達到揚善隱惡、維護禮儀秩序的目的。如明明是“天王”遭遇內亂而出逃至河陽,《春秋》卻記為“天王狩于河陽”。我想,按孔子的本意,最好將“天王”這段記錄刪去或隱諱,但茲事體大,是瞞不過天的,而稱之為“狩”(天王外出游獵)則兩全其美,老天爺那邊匯報了天王離開首都的事實,后人看了也不至損害天王的尊嚴。當然,由于篇幅有限,尊者、賢者那些無足輕重的“細行”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隱諱了。
皇權的確立和強化使史官有了新的效忠對象,也產生新的困惑。一方面,皇帝是天子,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天的意旨,所以史官的記錄必須遵守皇帝的旨意,必須解釋本朝的成立和興盛合乎天意,順應天命。特別是在編纂史書時,這成為最高的政治原則,也是對史料取舍刪改的唯一標準。但另一方面,一旦史官發現或認為皇帝的言行與天意、天命不符,就會使他們左右為難,或者懷疑自己的判斷能力。出于對天的忠誠和職業道德的堅持,稱職的史官會義無反顧地選擇如實記錄,或者有意無意留下矛盾的史實。但多數史官無法抗拒皇權的淫威,只能以曲筆順從,甚至完全按照皇帝的意愿編造史實,而以“天意”自欺欺人。
世俗的腐敗也波及史官和歷史的記錄。盡管依然保持著對天、神靈或祖先的敬畏,但世俗的精英普遍會以世俗的行為準則看待他們——他們同樣會見錢眼開,同樣只看書面材料而不作實際調查,同樣會毫無例外地庇護自己的子孫、親友、熟人,只要賄賂或脅迫史官寫出佳傳,出錢讓高官名人“諛墓”(寫吹捧死者的墓志銘、碑文),就能達到揚善隱惡、蒙混過關、流芳百世的目的。
時至今日,記錄歷史的技術手段和信息的保存已毫無困難,皇權不復存在,絕大多數人也不再信天命天意,但歷史記錄真實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