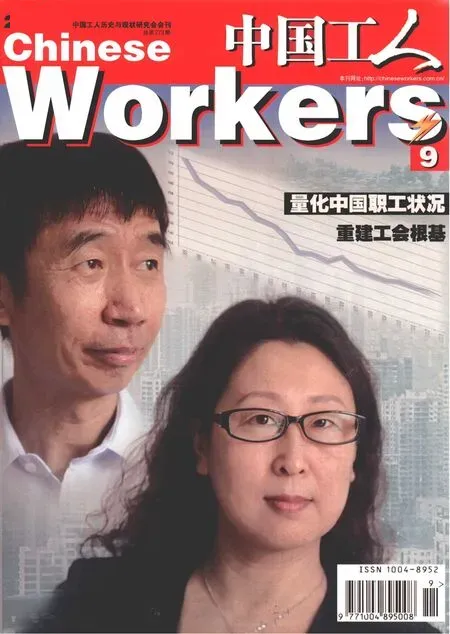無行動與記憶,災難何以興邦
●吳麟

由《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大衛?馮?德萊爾寫作,劉懷昭翻譯的《興邦之難:改變美國的那場大火》今年問世。重現了100多年前發生在紐約的三角工廠大火。與發生在中國的幾起火災作比,何其相似,效果又何其不同。作者因而呼吁,置身于當前中國的歷史場景,我們需要進一步的行動與記憶,個體痛楚才能成為普遍進步的契機。
1 911年3月25日,一個明媚春日,位于美國紐約市華盛頓廣場附近艾什大廈中的三角服裝公司,其時紐約最大的女裝制造廠,當天下班之際突發火警,短短幾分鐘,火苗吞噬了廠房。這場大火從燃起到撲滅僅半小時,但導致146名工人失去生命,大多是年輕的移民女工——或從9層高樓跳下而喪生,或被堵在封閉車間中遇難。此事史稱“三角工廠大火”,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于長達90年中一直是“紐約歷史上最慘痛、最重大的一次職場災難”。
2003年,《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大衛·馮·德萊爾(DavidVonDrehle),以一部《Triangle: TheFireThatChanged》America,生動激越地再現了這幕歷史,出版后備受贊譽,被認為“成功地刻畫了美國制衣業的成長歷史、移民工人的生活、20世紀初期紐約的政治以及1909年的罷工”;透視出這場火災的背后,是“一部驚心動魄的血汗工廠史,及工會組織羽翼未豐的萌芽時期”。的確,作者在社會正義的主題下,講述了一段扣人心弦的歷史——“三角工廠大火”如何直接觸發“當時美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立法行動,以及如何成為開啟未來一系列社會變革的鑰匙。
2015年,該書中譯本面世,名為《興邦之難:改變美國的那場大火》(以下將簡稱為《興邦之難》),梁實秋文學獎得主劉懷昭的譯筆同樣不凡,令人不忍釋卷。讀史方能閱世,此書講述的雖然是一百余年前的美國往事,然而置諸當下中國語境,一個仍在穿越“歷史三峽”的國度,一個“多難興邦”成為高頻詞的時代,非常值得關注。《左傳》有云:“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一個“或”字,顯示出“多難”和“興邦”之間只是一種或然性的可能,而非必然因果聯系。那么,“三角工廠大火”為何能夠成就美國?懷此問題讀完之后,有一句話繚繞在我心頭:無行動與記憶,災難何以興邦?
美國往事:進步時代的行動者
20世紀初,一波移民浪潮涌入了美國蓬勃興起的制衣業,源源不斷的勞動力拉低了勞動報酬,并形成殘酷的“搶飯碗”現象,造就眾多“血汗工廠”。其時,這是一種比通常意義上低薪、擁擠更為悲慘的情形——“更為昏暗、封閉出租屋作坊,獨立的承包人在那里剝削初來乍到的新移民”。后來,為集約經營,工廠開始向“天空”發展,出現“工廈”——1910年之后,“曼哈頓有一半工人都擠上了七層以上的樓層里工作”。市消防局長曾預言 “白天發生火災的話會死很多人”,但工廠主對此漠不關心。《興邦之難》寫道“危險的工作環境在當年是家常便飯……一場事故接一場事故,但一切照舊”。那么,“三角工廠大火”何以與眾不同,成為“一連串連鎖事件的關鍵點”,最終迫使紐約乃至全國的政治機器開啟了實質性的改革?要知道在那個工業蓬勃發展的時代,“146人的死亡數字雖然相當驚人,但也并不稀奇”。回到進步主義時代這一寬闊歷史語境,方能有所體悟。
其時,工業文明綜合癥——“經濟生活的混亂、社會貧困的惡化、階級對抗的加劇、政治結構的危機、文化的衰落”,使美國社會開始尋求變革,進步主義運動應運而生。1900年末至1911年初,在新鮮血液和新思想交融的曼哈頓服裝工業區,由新移民工人和進步主義者聯手發動的制衣女工罷工事件,是“三角工廠大火”引發社會變革不可或缺的前奏。在大衛·馮·德萊爾的筆下,進步主義者是可敬的。他們真誠反思社會——“在一個擁有夢幻般的60層高的摩天大樓、科學發明的自動鋼琴的城市里,不應該有上百萬窮人在悶罐般簡陋狹小的空間里為生計而掙扎”。他們積極投身行動——“美國各地高校中的高材生們紛紛進駐社區服務中心……在那里與窮人同吃同住。他們寫的第一手報告里滿是圖表、數據以及原原本本的口述見證,一個在煤油燈下熬夜做手工活的家庭能掙到幾個銅板,以及為什么貧民窟容易出現火災。他們的研究報告不僅發表在專業的新聞雜志如《調查》(Survey)上,而且還登上了專事揭發丑聞的月刊《馬魯克爾》(McClure’s)。”
從歷史的邏輯而言,進步主義運動是一次應對資本主義制度危機的“社會性努力”。我認同美國史專家李劍鳴的觀點——它實質上是一場“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文化重建運動”,旨在重建遭到工業文明摧毀和破壞的社會價值體系。盡管它并不以普遍的社會正義為追求,抵制社會主義發展、防止革命情緒蔓延,甚至是“進步派”所自覺承擔的“使命”,但以純粹意識形態批判色彩的“倒退”或“保守”視之,有欠公允。
在此意義上,《興邦之難》所述不同類型的行動者——未來美國首任女性勞工部長弗朗西斯·珀金斯(FrancesPerkins)、創立婦女工會聯盟(Women’sTradeUnion)的富豪之子威廉姆·英吉利·沃靈(WilliamEnglish Walling)、資助罷工行動的美國頭號資本大亨J.P.摩根的女兒安·摩根(AnneMorgan),倡導婦女選舉權的貴婦阿爾瓦·貝爾蒙特(Alva Belmont),乃至富有勃勃政治野心的“坦慕尼社雙胞胎”等,均有其特定社會價值。當然,制衣廠年輕的移民工人才是真正的主體,他們“洋溢著進步的精神,不耐煩于傳統的包袱,對新世界和新時代的發展充滿渴望”,通過成立工會、爭取公民權益以及街頭抗爭喚起眾生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自發組織起來去爭取一個更公平與更人道的社會”。其中的佼佼者——年輕俄國移民女工克拉拉·萊姆利奇(Clara Lemlich),她的勇敢與堅韌,百年之下依然令人動容。
悲劇紀念之道:成為歷史記憶
人的記憶是人類認知能力的基礎。一個國家、民族乃至個人,都需要關于過去的知識來幫助自己定位;如果缺乏足夠的歷史記憶,則難以具備良好的辨識方向和積極行動的能力。
古羅馬哲人西塞羅(MarcusTullius Cicero)曾云:“人若不知出生以前發生之事,則將永如幼童。”的確,歷史是人類對過去的記憶,知識的積累、進步必須以記憶為基礎。若是涂抹或遺忘歷史,往往出現法國著名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所言的悲劇——“當過去不再昭示未來時,心靈便在黑暗中行走”。由此,歷史記憶需要盡量地趨向健全。
公眾對歷史的記憶為一定社會框架所形塑。首倡“集體記憶”(collectivememory)概念的法國學者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認為:人的記憶有自傳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和歷史記憶(historymemory)之分。前者是“對我們在過去親身經歷的事件的記憶”,后者并非個人“直接去回憶事件”,而是經由閱讀、聽人講述、參與紀念慶典等活動“被間接激發出來”。因而,“過去是由社會機制存儲和解釋的”。惟在一個開放社會,擁有允許自由地集合記憶、交換記憶進而比對記憶、發掘錯誤的機制,歷史記憶方能健全。
前述“多難”與“興邦”之間只是一種或然關系,“三角工廠大火”能夠成為“興邦之難”,除了進步主義時代行動者的力量之外,與其能夠進入美國公眾的歷史記憶有重要關聯。正如此書結尾一段所寫——“至于1909年罷工的那些默默無聞的年輕男女,那些在寒冷的冬天勇敢地走在示威隊列的工人們——尤其是后來慘死在三角工廠火災中的年輕人——他們在記憶中永存。他們的個體生命多已無從查考,但他們作為歷史的豐碑和傳統已深深銘刻在我們的世界中。”
成為歷史記憶,是對悲劇最好的紀念之道。在此意義上,“三角工廠大火”可謂不幸而又有幸,這賴于各方努力——
“我第一次讀到三角工廠大火的故事,是在三十年前的研究生課上。教授講述時,悲憤難抑,令我終生難忘。若干年后,我自己教美國史,也從不舍棄講述這個故事。這是一個充滿悲情的移民故事,也是一個透徹描述資本原始積累的故事,我們得以從中窺見20世紀初新舊政治經濟秩序在紐約的博弈,更見證了美國人為‘進步’付出的代價,包括那些被大火吞噬的女工。”美國賓州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王希的這段夫子自道,顯示出學校教育作為一種社會機制,在建構歷史記憶中的作為。
“因為你的記錄,那些從艾什大廈的火災中歷經掙扎而生還的人才可能在本書中直接發聲,留下他們宣誓后的可靠證詞。”這句話是對當年庭審記錄者斯圖爾德·里德爾(Steward Liddell)的致敬。“三角工廠大火”之后,紐約州法院對兩名工廠主進行審判,庭審記錄相當翔實,形成了近2300頁的卷宗,對于日后呈現這一歷史事件而言必不可少。
“每一個瞬間都別有深意,每一個閃念都瞞不過眼睛”——火災發生之際,正值周末收工,工人開始哼唱起流行歌曲……這一動人生活細節,源自工會背景作家列昂·斯坦因(Leon Stein)溫和而有效的采訪。1950年,他通過追蹤走訪幸存者、披覽大量庭審卷宗,挽救了許多日后將無從發現的珍貴史料,將關鍵史實從塵封的歷史中挖掘出來。他于1962年出版的《三角工廠火災》,是一部完整記載這場悲劇的巨作,通過將之重建于堅實的歷史背景之上,喚醒了美國社會的記憶。
其間,美國媒體界的表現,雖然呈現出新聞生產的不足——“對死者的深度報道則付諸厥如……紐約的記者們對工廠里實際發生的情況一直懵懵懂懂……”,但是畢竟投入關注——“這些個體生命的片段,事件的花絮和插曲,一連幾天占據了當地報紙的主要版面”。此外,火災前的罷工事件,除《先聲報》等社會主義立場的報刊之外,普利策的《世界報》、蘇茨貝格的《時代》周刊、赫斯特的《美國人》報等主流商業報刊也是未曾沉默。當時,制衣業的罷工,被《世界報》稱作“是婦女爭取權利的萊克星頓的槍聲和邦克山革命”,還登上《時代》周刊的封面《為女工罷工鼓與呼》。甚至連一向對資方采取友好立場的《紐約時報》,也出現了肯定罷工行動的“編者按”。它們主觀動機如何,我們不必揣測;但其客觀效果已顯示出:大眾媒體在現代社會中是建構公眾歷史記憶的一種重要機制。
中國社會需進一步行動與記憶
社會學學者佟新在研究中國女工命運時,通過比較1924年上海“川公路織綢廠大火”和1993年深圳“致麗大火”,提出一個“歷史時間”概念——“在相同的經濟制度和文明條件下,某些社會事件可以再次出現;或者相同的社會事件說明社會是在相同的經濟制度和文明的時間和空間下。”其實,1911年美國的“三角工廠大火”與1993年中國的深圳“致麗大火”,具體場景何其相似——年輕的移民工人、強大的資本力量、危險的工作環境、艱辛的生活境遇,同樣讓人感覺到“歷史時間”之吊詭——時間失去意義,事件呈現出結構的相似性。但是,若以“災難”可否“興邦”作為觀察維度,畢竟還是差異鮮明。
中國社會需要更有力的行動。1911年3月25日的“三角工廠大火”,改寫了紐約州的勞動法,并啟動了此后“新政”改革的序幕。盡管1993年11月19日的深圳“致麗大火”,它與另一場大火——1993年12月13日的福建“高福大火”,被認為一起加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首部《勞動法》的出臺,但制度建設與轉型遠未完成。2014年8月2日,昆山“中榮事故”,再次呈現出制度性“人口紅利”掩蓋下的中國勞工問題之痛。致麗玩具廠存在重大安全生產隱患,地方政府不是積極督促廠商認真整改,而是由鎮長親自寫信要求發放消防合格證——“如不發給將會影響葵涌鎮的經濟發展,港商將會集體上訪”。中榮公司同樣存在重大安全隱患,幸存的工人事后回憶道“上工之前,沒人培訓過安全知識,也沒人說過粉塵會爆炸”。而公司的普通管理人員都因深知粉塵危害而對生產車間避之如“疫區”。政府的安全監管相關缺位——據公開報道顯示,“近 3000家企業,在昆山開發區經濟管理局僅設了 4個人的安全科”。在此,美國的“進步主義運動”有其歷史啟示性:社會正義的實現過程不應純粹由剛性國家權力所宰制,勞工權益保障需要工會、媒體、學者、NGO組織、消費者等不同類型的行動者。
中國社會需要更健全的記憶。當年,紐約市有35萬人參加了遇難者的送葬游行,冒著綿綿陰雨走完全程;還有25萬人站在路邊默默觀看了儀式。此后,諸種傳播信息和知識的公共渠道,使得此事逐步進入了美國公眾的歷史記憶。同是悲劇,然而1993年深圳“致麗大火”相形之下更為悲情。其時,盡管《工人日報》、《光明日報》等進行了報道與抗議,但是整體而言輿論遭遇嚴控,親歷者的回憶顯示:不僅當地鎮政府“不歡迎記者”,連整個深圳新聞界也都是“寂靜無聲”。對此事件,勞工問題研究者們或許不會陌生。當年,學者常凱參與事件調查,得以在火災現場收集了一批珍貴史料——230余封工友信件,以及日記、請假條、工資單等。據此以及調查感受,他寫就了長篇紀實報告《廢墟上的憑吊》,由于議題敏感,投寄多家報刊均遭拒絕,最后《中國工人》雜志施以援手,于1994年第5、6期連載發表。這篇文章后被譯成英文,刊于1998年夏季號澳大利亞《中國人類學和社會學》雜志。學者潘毅在《中國女工》一書“導論”中,也講述了在“致麗大火”中劫后余生的打工妹“曉明”的故事。那些極具歷史價值的信件,除了《天涯》雜志曾在2000年刊登小部分外,其他至今沒有正式發表;除了學者譚深、陳佩華曾分別從“打工妹的內部話題”、“生存文化”的角度對此進行分析,尚無其他有分量的研究。可見,對于“致麗大火”的記憶,局限在狹窄的專業領域,未成為公眾的歷史記憶。
在康奈爾大學勞資關系學院的奇爾中心(KheelCenter)網站上,有專門的“三角工廠火災”專題,其中顯示:2011年,又有6名遇難者的具體身份得到確認。2001年《天涯》雜志曾連載譚深等人執筆的《泣血追蹤》,這份關于“致麗大火”受害打工妹的詳細追蹤報告,讓人充滿敬意,但是似乎已成絕響,其間個體行動者的努力更映照出制度性的冷漠。“對自己的過去和對自己所屬的大我群體的過去的感知和詮釋,乃是個人和集體賴以設計自我認同的出發點,而且也是人們當前——著眼于未來——決定采取何種行動的出發點。”置身于當前中國的歷史場景,我們需要進一步的行動與記憶,個體痛楚才能成為普遍進步的契機,蕓蕓眾生才能距離社會正義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