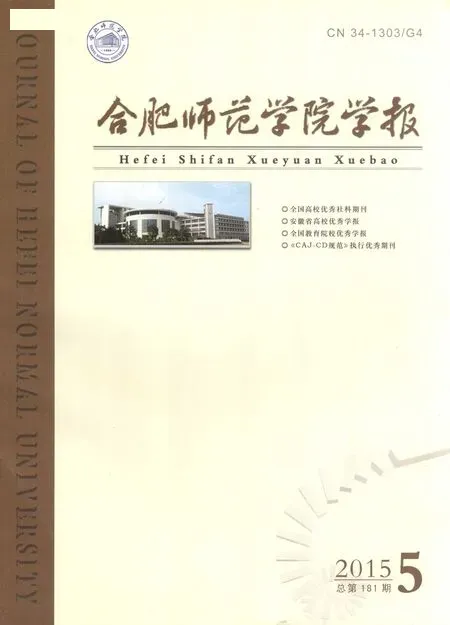朱熹幸福觀探析
陶有浩
(合肥師范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合肥230601)
朱熹的理論體系中雖未出現過“幸福”的概念,但是如果以“由于感受或意識到自己預定的目標和理想的實現或接近而引起的一種內心滿足”[1]819來定義幸福主觀感受的話,那么在其語境中則不乏類似的描述性字眼,最為典型的就是偏重于物質層面的“福”和偏重精神層面的“樂”。由于幸福主題本身具有的學術價值,加之近年來社會所給予的特殊關注,對于朱熹幸福觀相關內容的討論也成為了學界的一個熱點。但一般的成果大都從“理欲之辨”和心性修養角度來談朱熹的幸福觀問題,其獨立性未得顯現;同時,多數討論都將核心放在理性道德幸福和德福一致層面,全面性不夠。此外,部分領域認識的深刻性有待提高。本文擬在借鑒和反思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以上幾個方面出發,著力梳理朱熹幸福觀的特色性內容。
一、偏向性評斷幸福的內容結構
幸福是一個內涵和外延都非常復雜的問題,處于不同環境條件的人對她會有不同的理解。即使處于同等條件下,因為背景、立場、利益關系及認識能力等原因,對她也會有不同的把握。概念本身的復雜性帶來了對于幸福內容結構分類的多樣性,依據不同的標準,可能會出現很多種情況。從最能體現朱熹學說旨歸的角度考慮,筆者揀選了以物質向度和精神向度為分類標準來辨析朱熹對幸福內容結構的詮釋,分別將之稱為理性道德幸福和感性物欲幸福。
(一)理性道德幸福
這類幸福超越了物欲的境界,從主觀感受上說主要是由于達到或接近主體在精神向度的預期而產生的滿足感。出于理學家的文化立場和精神信仰,朱熹對這一類幸福最為看重。從具體來源上看,主要包含以下內容:
第一,成就最高理想人格。周敦頤所說的“圣希天,賢希圣,士希賢”,為理學家規劃好了理想的人格發展模式。朱熹也是遵循著這一理路,將終極理想人格目標定位為成圣,視成圣后的感受為最高的理性道德幸福。他從境界和氣象兩個向度來表述成圣的幸福。孔顏之樂是圣人境界的最佳描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對孔顏之樂的認識集中體現了朱熹關于幸福內容結構的偏向性態度。朱熹說:“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快活!’又謂:‘人于天地間并無窒礙,大小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真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于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2]1126這不是說貧賤本身有什么可樂的地方,而是指超越了感性層面的利害關系,“與天地萬物為一”、“與理為一”,從而達到一種內在愉悅感和崇高的圓滿。這樣,心胸坦蕩自然會有一種徹上徹下的通透和安泰之樂。就這種樂的本身而言,它是圣賢自然而有的心境,非得道者是無法體悟的。[3]內在的境界自會有相應的外在顯現,朱熹視“曾點之樂”為圣賢的外顯氣象。“‘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論語·先進》)。描述的是由內在自足圓滿而呈現出的美善交融氣象。朱熹認為這是圣人境界的形象化注釋:“‘曾點之樂’,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于言外。”[4]165在本質上,它和孔顏之樂一樣,表達的都是到達圣人層次后,天理具足于身,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樂境。
第二,在追求成圣過程中精神境界提高的過程性體驗。因為圣人是宋明理學理想人格的終極目標,理論上人們是可以經過道德修養來達到的。但“圣人萬善皆備”,由于其素養水平太高,實際上很難實現,所以顏元說:“學者,學為圣人也。后世二千年無圣”[5]670。這樣,是否就意味著絕大多數人不能享有成圣成賢的理性道德幸福?如果這一判斷成立,宋明理學所倡導的學問體系就不是如一般學者所說的“貴族化”問題,而是一種懸空的學問了,其吸引力會大大降低。事實并非如此,在朱熹眼中,孔顏之樂問題的提出不是讓學者如何去樂,而是通過對美好目標境界的描述引導學者學成圣成賢之道。在他的表達中就是一個如何做工夫的問題。由此出發,他對程頤否定孔顏之樂是“以樂為道”的說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程頤認為如此說有“人自人,道自道”的嫌疑。朱熹則主張樂道之說并沒有錯,當工夫生時自是以道為樂,這只是達到“孔顏之樂”境界的一個應有的過程。朱熹的工夫過程說有力地彌補了程頤自然“循理”境界說的不足。[6]由此,朱熹提出了樂處在那“極苦澀處”的看法。因為人在通過格物窮理通達圣賢境界的過程中,只有經過苦心極力的積累和體認,才能得到豁然貫通的愉悅,領略到精神境界提升的幸福。
第三,對他人和社會應盡義務完成后的一種價值實現的自我滿足感。幸福最終是以個人主觀體驗的形式來實現的,所以一定程度上講,幸福是屬于個體的。但是,個體又無法離開群體而單獨存在,同樣,人的幸福的實現也不能脫離一定范圍的群體,亦需它來提供基礎條件和衡量的標準。因而,真正意義的幸福絕不是純粹的個體幸福,而應該是個人與群體的有機統一。朱熹在詮釋幸福內涵時不僅僅重視個人主觀的內在感受,更重視個人幸福同自然、他人、社會的相互關聯。個人應該追求的是自身與他人乃至整個社會融為一體的快樂體驗,也就是孟子所說的“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在朱熹眼中即為“樂民之樂”和“憂民之憂”。獲取個人幸福并非人們行為的根本目的,人類行為的最高目標是實現群體的幸福。以儒家傳統來看,“成己”只是階段性目標,還有“成人”、“成物”的責任和義務。“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于彼矣。”[4]51這是學者自然而應履行的。《大學》的“三綱八目”一定意義也可視為是對知識分子責任和義務的規定,后一部分是道德主體分內的外向事功之事,也是成圣成德的一個必備環節。通過完成對他人、社會應盡義務的方式檢驗自己內在道德修養水平,從而獲得進步后的完滿與愉悅。
(二)感性物欲幸福
一切高尚的精神追求都要以人生命的舒適性存在為基礎條件,人有食色利欲方面的需求是一種必然。當這種需求得到滿足時,也會產生一種幸福感,由此而有感性物欲幸福。朱熹鑒于客觀的社會現實,對這一部分幸福是選擇性肯定的。其所承認的感性物欲幸福主要有:
首先是基于生存需要的物質條件的滿足,即生存型感性物欲幸福。人要維持生命存在必需一定的感性物質條件,它得到合理滿足以后,主體在和之前貧乏的狀態相比較時,會有內心愉悅感。對這種生存型幸福及其水平之上的發展型物質幸福的渴求是激發主體創造乃至推動人類社會進步不可缺少的動力。鑒于其地位的重要性,理學家不能漠視其存在,大都承認它的必要,但將之限定在僅能維持生命存在的水平上,朱熹也有過類似的表述:“饑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7]3172。本能的底線飲食需求是天理,稍高水平的美味要求就是人欲了。某種程度上,對之采取的是輕視和警惕的心態。這樣的嚴格要求如果是針對特定的群體,或者出于“法乎其上,得乎其中”的要求標準也勉強可行。可惜的是,朱熹等人將之視為針對所有對象的真實要求,這就造成了個體生命意義某種程度的陷落,也阻礙社會的發展。蒙培元說:“正是在這些地方,暴露出朱熹和儒家對人的欲望有一種謹慎的提防和警惕,當然也就限制了個人創造財富、追求幸福的內在動力。精神上、道德上的滿足感代替了物質上的追求,仁愛代替了私愛包括情愛,如此等等。”[8]167確為精當的分析。
第二,依照儒家禮制享有的發展型感性物欲幸福。雖然理學家在主觀上希望把人的感性物欲幸福限定最低本能需要的水平上,但是社會財富的時代性逐步增長現實刺激了人們對更高物質條件的渴求,以及特權階層享受型生活的事實存在,使得他們的這種愿望基本落空。理學家無法阻擋人們追求發展型的感性物欲幸福,為了使社會不至于因過度追求奢靡享受而導致無序化狀態的出現,朱熹在人們對更高期望的物質追求方面設置了一個標準,即必須按照儒家對不同社會等級的相應具體規定來享有超越生存需要的更高之福。這集中表現在他的消費倫理方面。朱熹總的消費主張是按禮消費,禮的明顯特征之一就是等級性,按禮消費社會物質財富就是要求人們不能逾越社會的等級秩序,從而不同階層享有不同水平的物質感性生活。這在社會生產力水平有限的情況下,能有效地避免因財富分配不均而引發動蕩的危險。它的具體要求是“奢不違禮,儉不失中”,因為“禮貴得中,奢、易則過于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4]84。過度的奢華會導致財富貧乏,過度的簡樸會喪失生活的嚴肅性,都不符合儒家“尚中”的精神傳統。可以說,這是一種比較合理的引導大眾消費觀念的主張,但朱熹把消費的等級性和人的身份而非消費能力相聯系的做法,降低了其理論的價值。
第三,群體層面的物質感性需求。前兩者是從個體角度來說的,這一點則是以區別個體幸福和群體幸福為視角的。這主要是通過探討義利或理欲關系體現出來的。義利之辨在宋明理學中有重要的地位,“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9]1082。其實,傳統的義利觀有兩個角度:在個體層面上,精神追求為義,物質追求為利。它強調非“義”之利不取;當義利只可選其一時,要舍利而取義。在群體的層面上,同樣是精神追求為義,其不同在于,它對于利的肯定的條件更加放寬了,除了合乎“義”之利是君子可取的選項之外,集體的之“利”是其主要的傾向之一。在一定意義上來說,“義”所指的就是“公利”,甚至是他人的個人之利也可視為某種“義”。因為主體主動讓渡本屬于自己的物質利益或者為他人和群體的物質利益盡心盡力,體現的是其精神道德修養,這就是“義”。義利之辨在這一層面其實就是公私之別,“義與利,只是個公與私也。”[10]178朱熹也認為區別義利之辨、理欲之辨不在物質和精神而主要在于公私:“循理而公于天下者,圣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于一己者,眾人之所以滅其天也。”[4]267他所反對的出于“私”的利欲,對于公共領域的感性物欲需要朱熹是肯定的,根據儒家“先富后教”的觀念,先有富足的物質生活而后才有高尚的精神生活。對公共層面的物質感性需求得到滿足而產生的群體積極心理體驗,朱熹是十分贊賞的。
朱熹對幸福內容結構的界定雖注意到了幸福的客觀條件和主觀狀態兩方面,但由于他偏向性定位兩類幸福,對感性物欲幸福限定趨于嚴格化,只承認公共領域的物質幸福為正當,使其主張呈現出片面化和單向度化特征。同時,他割裂幸福兩個方面的有機聯系,認為過度強調幸福的客觀條件(感性物欲)會不利于引導人們正確提升幸福的主觀狀態,如果一味屬意于物質層面不但會導致幸福追尋者道德境界的低層次,也會影響整個社會的道德建設和水準。這樣,朱熹就消解了先秦儒家幸福觀的多樣性選擇空間,使其有關理論因限定過分嚴格而走向了僵化。
二、對影響幸福因素的主觀化歸納
追求幸福是人們生活的主要目的之一,究竟哪些因素能夠影響甚至決定人們的幸福狀態,也就成為了討論幸福問題的應有之義。朱熹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求福主體的道德素養
在古人的觀念中,總體上幸福主要掌握在兩種力量手中:求福主體自身和異己的神秘力量。在朱熹看來,無論是從異己力量佑助獲福方向上看,還是從求福主體自我追求得福方向上看,道德對幸福的決定性作用都不可忽視。它對感性物欲幸福和理性道德幸福的獲取都有重要影響。從前者來看,在異己的神秘力量中,天命和天道是一個典型代表。其權威在古人的心目中一直不可觸動,而個人可以以高尚的道德素養來博取它們佑助的信條,自西周以來一直根深蒂固。具體到幸福問題層面,求福者通過修德和自身努力在得到異己的神秘力量肯定后,可得到其所賜予的物質福報,即可得到感性物欲幸福:“為善則福報,為惡則禍報,其應一一不差者,是其理必如此”[11]2714。這種規律對任何人都是一樣的,皇帝也不例外。“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為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為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況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為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茍能修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于禳?福祿之來何待于禱?”[12]621-622求福主體自身道德水平對幸福獲取情況的實際影響力度超過了對神秘力量的祭祀。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韋政通說:“天命、天道不過是道德的超越表現”[13]49。另外,主體道德素養對幸福獲取的決定性作用還體現在追求理性道德幸福層面。因為這一類型幸福本身的內容指向就是高尚的道德精神境界,求福主體在修德過程中以及獲得道德境界提高以后,不需經過其它的任何中間環節自然而然就會直接獲取精神之樂,例如孔顏之樂和曾點之樂。求福主體的道德素養與理性道德幸福的內在關系是不言自明的。
(二)個人的命數
在禍福這一層面,朱熹是承認命數存在的。他經常說:“死生自有定命”[2]1678,“禍福之來,命也”[7]3501。人的生死禍福是命中早就注定的。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與朱熹的本體論和世界本源論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朱熹把“理”當作最高本體,是天地萬物的本源。但只有它,也不能產生萬物,需要借助“氣”作為生物之具。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是二者相結合而成的。人作為萬物中的一個類種,當然也是理氣和合的產物。但是人和其他動植物之間、人和人之間區別的產生原因不在于理而在于氣,原因就是因為氣稟不同。朱熹所言的“命數”多與氣稟相連,“此只是氣稟之命。富貴、死生、禍福、貴賤,皆稟之氣而不可移易者”[14]210。而且這很難改變,“但恐禍福之來亦有定分,非智力所能免”[11]2607。“需要說明是,朱熹在說明命數決定的禍福時經常使用的字眼是“富貴”、“貧賤”、“壽夭”、“死生”,等等。可見,他認為命數能決定的只是俗世的禍福,也就是屬于感性物欲層面的禍福。這不是幸福的核心和重點,它不妨礙人在幸福追尋過程中的積極主動姿態,“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4]426。究極本性而知人心所具之理,即本性善端,進而知悉天理本然,以之為原則修養心性。不因為短命或長壽動搖心智。修養身心等待命運的到來,這就是君子對待命所持的正確態度。
(三)他人的德行
朱熹對德行決定幸福是堅信不疑的,同時他還認為不但追尋幸福主體自身德行影響幸福的獲取,與其有密切關系的人的道德狀況亦能對其幸福狀況產生重要影響。首先是求福者父祖的德行。其前提是幸福可以在不同的追求主體之間進行傳遞,換句話來說就是道德素養的擁有者本人并不一定是福報的對象,而可能是其后代。祖先的行為性質決定著后代的幸福與災禍,即《周易·彖傳》中所說的“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在這樣的語境中,求福主體就不是以單個人為單位了,而是以家族為單位存在。朱熹舉例說:“孟子勸滕文公為善,謂后世子孫必有王者,非但告之以周家之事,是亦以天道告之也。使周不積徳行仁,則子孫未必蕃衍,雖欲伐紂而利之,不可得矣。況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15]3547其二是君王的德行。朱熹認為一般的人修德只得個人之福,而君王修德則影響整個天下的福蔭。它是通過三條路徑來實現:一,直接以自己之德而得到的福報澤被天下臣民,“使忠言日聞,圣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真享富壽康寧之福,朝廷之上真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丘壑,無所憾矣”[9]1249;其二,以自己的德行影響臣民德行,以此使臣民獲得福報。朱熹堅持德行“為治之大原”,如果君主通過修德擁有高尚道德素質,成為天下表率,百姓自愿以之為榜樣,修身為善而得福報;其三,因為君王德行高尚,所以在具體施政時就會遵循無為原則,不生事擾民,實行以“養民為本”和“愛民為本”策略。這樣也會提升臣民的幸福水平。第三是與君王德行影響天下臣民幸福相對應,官員的德行也會影響其管轄領域人的幸福。“在昔賢君子,存心毎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眞。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12]283因為整個國家是一個大的系統,而其有效運行又有賴于每一個子系統。而在小的子系統中,其負責官員的地位就相當于君王在一個國家中的地位,因而這一部分的理由和論證方式與第二部分十分相似,區別只是在區域和范圍的大小上而已。另外,朱熹堅持“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的原則,君王的為政以德和以德為本必須依靠相關官員的認可和配合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從這一視角來看,官員對普通社會個體幸福的影響力也可見一斑。從這一部分總結來看,德行對人幸福的影響針對不同的人群處于不同的水平。普通的社會成員,其幸福狀況受自身道德水平、父祖德行、君王和官員的影響;一般的官員也是一樣。最自由的就是君王,其幸福只受自我德行和父祖德行的影響。
第四,以禮法為核心的相關制度的影響。朱熹認識到并從理論上闡明群體幸福與個人幸福的關系,因此他在討論決定幸福的因素時,既能返回人自身,認為幸福有賴于主體的德行和命數;也能看到宏觀的社會因素對個體幸福的影響,突出的體現就是有關的制度建設。其實這一點和第三個決定因素是緊密相聯系的,因為只要是君王和官員的的道德素養好,其相關的制度建設就會起到相應的積極作用。朱熹的制度規整所指的是兩個方面:積極的外在行為標準——禮;消極的行為規則——法。前者指導人們如何去行動以獲得幸福,后者則告知人們怎樣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導致本應到手的幸福喪失。二者對幸福主體的影響非常大,朱熹以法為例來說,如果制定的不好,會使小人得福而好人受損,他以當時南宋的律法舉例,導致“君子欲為其事,以拘于法而不得騁;小人卻徇其私,敢越于法而不之顧”[7]3523。因此,以禮法為核心的相關制度也是決定幸福的重要因素之一。
朱熹所歸納的影響人獲得幸福的眾多因素,從視野上看較為廣闊,既涵括了個人領域也關注到了宏觀的社會層面。但囿于時代和學術立場的局限,明顯可看得出他對道德因素的鐘情和傾向性重視。這不但導致了朱熹在評定各種因素所起具體作用的程度時出現了偏差,也使得他對一些十分重要的影響要素視關注不夠,比如主體的個人能力和突發的偶然性因素。
三、對德福關系的理學立場詮釋
不管是什么時代和學術立場,討論幸福問題都無法回避德福關系的主題。其核心觀點主要是兩方面,即德福一致和德福沖突。一般學者只能承認或贊同其中某一個,朱熹的特殊之處在于,兩個看似沖突的認識在他的相關理論中都能夠看得到,而且他把二者的關系處理得相當圓潤。
(一)德福矛盾
出于良好的愿望和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景考慮,古今不少學者都堅持德福一致的立場,認為人擁有的道德素養水平和其所得的福報是匹配的。因為從工具性角度來看,“道德是一種幸福的源泉,這種幸福不會因為享受而變得乏味,也是任何人不能奪走的”[16]237;從幸福內容來看,真正道德高尚的人應該視道德修養提高為追求的主要幸福目標,這樣德福一致就成為了一個無需證明的正確命題。但對于一般社會成員來講,后一種論證過于高遠,因而判斷德福是否一致多數是從工具性立場出發的。從幸福的物質感性部分內容來看,經常呈現的現實是:有道德的人不一定配享幸福,而享有幸福的人也不一定道德高尚。多數人從經驗層面對歷史上德福矛盾情況進行了描述與刻畫,并對道德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產生了懷疑,“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眾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于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于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于展禽”(《列子·力命》)。因為傳統儒學對于道德不遺余力的崇揚,有學者便以此為據,懷疑儒家學說的價值和完整性,“道德與苦難不能相互解釋,既不能說,為了道德秩序而受苦和遭受不幸是正當的,否則善有何意義?同時也不能說,有德的人的受苦和不幸根本不算什么。一味叫人修德,信守宗法倫常,并不能安慰人的受苦。有德性的、善良的人仍然在受苦,屈原就是其中之一。儒家學說怎么忽略了不得不說明的受苦事實呢?”[17]117德福不一致成為幸福話題不得不面對和解決的內容之一。
朱熹對于德福矛盾現象是坦然直視的,他曾經歷數過歷史上德福不一致的現象,“‘大徳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壽。’理固當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夭死,蓬蓽之士固有老死而名不著……”。[11]2690對于朱熹來說,難點不在于是否承認經驗世界的德福不一致,而在于既能在理論上解釋現實中的德福矛盾現象,又能繼續保持道德的號召力,使人們相信通過修德可以獲得福報。他是從以下角度來解釋德福不一致原因的。
首先是由氣的變動性引起的。從本源意義上說,萬物都由理氣相合而成,其運行和呈現出的現象和狀態都是由理氣共同決定,遵循理氣的規律。人們常說的“爲善則福報,為惡則禍報,其應一一不差者”[11]2714,只是在“理”的層面固當如此,而氣的變動性經常使這種應然情況發生改變。經驗世界的德福關系情況也是由理氣共同作用決定的,在決定禍福這一方面,理氣處于一種相爭的狀態,當理勝氣之時,便出現“為善則福報,為惡則禍報”;相反,如果氣勝于理,德福關系見則會出現反常,“今理既不足以勝氣。則凡福善禍淫之說不驗常多。”[11]2690當然,氣勝理并不代表德福之間就一定會出現抵觸,因為氣是隨世變化的,這要看起主要作用的氣的種類。如果是所謂“和氣”和“元氣”之類主世,則福報亦會按照福善禍淫的原則來。總之,氣起主要作用德福之間會出現一定的反常現象。其二,道德踐履不全面。在朱熹的理論中,和幸福相對的“道德”概念有三種內涵:道德意識、道德品質和道德實踐,在外延上都偏重于個體領域。決定追求主體福報情況的是三者的綜合,缺一不可。良好道德意識的形成得益于對對天理的體認,繼而對自己心性進行修養,形成高尚道德品質,這是一種知和行的關系。同時,內在的道德意識和道德品質外化為一系列的道德行為。它們之間一個嚴格邏輯關系。從大的方面來看,前兩者和道德實踐亦可視為另一種意義是的知行關系。朱熹雖然強調知先行后,但也堅持知行互發,二者“工夫須著并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廢。如人兩足相先后行,便會漸漸行得到。若一邊軟了,便一步也進不得”[14]457。知行必須一起做到,才能收到成效。朱熹尤其重視道德品質和道德意識的綜合,“德行”一詞在朱熹看來就是“道德品質和道德行為的簡稱”:“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于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4]787只有完成了“道德意識、道德品質和道德實踐”三種的結合,才能獲得相應的福報。否則,則會出現偏差。第三,主體道德素養以外的原因。通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朱熹自己也承認,影響人是否幸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德行只是其中之一,出于學術立場和精神文化信仰,人們只是聚焦和放大了道德在獲取幸福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在某些特殊時候,這些主體以外的因素往往會起關鍵作用。例如,命數,為解決佛教和道家早已解決的現實中德福不一致的問題,朱熹也引入了命定禍福的觀念。還有就是自己父祖的德行、自己所處當世的君王和所受管轄領域的負責官員的道德品質和行為,以及相關的制度和機制。這些都是幸福追求者主體道德素養之外而無法掌控的,但他們對于主體的得福狀況又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德福一致
從朱熹的整個理論體系來看,他堅信道德對個人和社會發展的作用,對德福一致是堅定不移的。之所以人們會認為德福沖突,那是討論問題的角度出了問題,表現之一就是討論時無意識地預制了一些前提,而在得出結論后又忽視了結論得出的條件、區域限制,將之普遍化。人們無意識地預設的前提有兩個,正是這兩個前提使人們得出了德福沖突的結論。首先,把道德主體和得到福報的主體默認為同一個人。如果一個人有道德,卻缺少或沒有幸福,或有幸福卻沒有道德或缺少道德,那么只能說,道德與幸福在這個人身上是沖突的。如果從宏觀視野來看,從福報獲取者可以是多元化的,既能是道德主體自身,也能是道德主體的后代或其影響范圍內的人。有德無福者,可能是其父祖或當世的君王及官員德行不佳,或者他在為自己的后代得福準備條件。相應地,無德有福者,他是在依靠其父祖或當世的君王及官員德行獲得福報,或者是在消耗其后代的福報。這樣,對于德福是否一致就不會存在問題。另外一個預設的前提就是,將幸福的內容限定在感性物欲層面。而從朱熹對幸福內容結構的詮釋可以看出,他認為幸福至少包含兩個大的領域,即感性物欲和理性道德,而且他是偏重和推崇后者的,以后者為真正的、最高的幸福。按照他的理論邏輯,如果人將福報目標定在理性道德層面,那么德福一致就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了。對于命定禍福的德福沖突問題,朱熹的態度是 “君子道其常而不道其非常”[11]2690,存而不論。因而,總體上在朱熹看來,德福一致是沒有問題的。
在理論上論證了德福一致以后,為增加道德的吸引力,還是要盡力使人們看到在實際生活中道德擁有者本人獲得福報的情況。在操作中,就需在實施教化,喚醒人內心的道德自覺作用的同時,讓人們看到善惡所得到的截然不同的結果。但是如果坐等福禍結果的發生可能會降低勸善戒惡的效率,因而需要人為地采取一些措施使結果立顯。朱熹所選擇的方法就是道德賞罰。朱熹在地方官時,對“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為學職”。其賞善的對象還延及到了歷史人物,并“訪尋陶威公侃、謝文靖公安,陶靖節先生潛、前朝孝子司馬暠、司馬延義、熊仁贍,義門洪氏等遺跡”[18]251,尋找遺址為之立祠立堂,加以旌表和紀念。在“罰”的一面,為加大道德對人消極行為的約束力,其原則是禮法相濟和“違禮入刑”,甚至在某些時候,不惜采取道德立法的方式,使法律賞罰充當道德賞罰從而部分地執行了道德的職能。朱熹明確地說:“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后聽其曲直之辭。”[12]657如此,就以人為干預的方式促進德福一致效果的發生,堅定人們對這一規律的信仰。
四、結語
面對社會動蕩對倫理規范造成的顛覆性破壞、理學內部功利主義興起以及佛道相關理論的挑戰,朱熹在繼承歷史沉淀的基礎上,著力重整儒家學說,將重點放在了對人生本質和價值的探尋上。他的理論體系中始終貫徹穿著對幸福問題的討論。其幸福學說的旨歸在于重振儒家學說的同時,將人們陷溺于佛道和功名利欲之心拉回到對天理道德的追求上來。因為自身對物質層面無需擔憂和對人生品德的一貫高標準,加之儒家學說傾向的影響,朱熹輕視甚至忽視幸福內容實際的多元化,片面高揚道德理性一面,使其學說的實際積極作用受到了局限。
[1]馮契.中國哲學大辭典(上)[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
[2]黎靖德.朱子語類(二)[M]//朱子全書(15冊).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趙峰.朱熹論孔顏樂處[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3,(4).
[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朱子全書(6冊).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5]顏元.顏元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7.
[6]李煌明.“孔顏之樂”一宋明理學中的理想境界[M].中州學刊,2003,(6).
[7]黎靖德.朱子語類(四)[M]//朱子全書(17冊).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8]蒙培元.情感與理性[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9]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二)[M]//朱子全書(21冊).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0]程顥,程頤.二程集(第三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1.
[1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M]//朱子全書(23冊).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M]//朱子全書(20冊).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3]韋政通.中國思想史(上)[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14]黎靖德.朱子語類(一)[M]//朱子全書(14冊).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5]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五)[M]//朱子全書(24冊).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6]陳根法,吳仁杰.人生幸福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7]劉小楓.拯救與逍遙[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18]王懋竑.朱熹年譜考異[M]//朱子全書(27冊)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