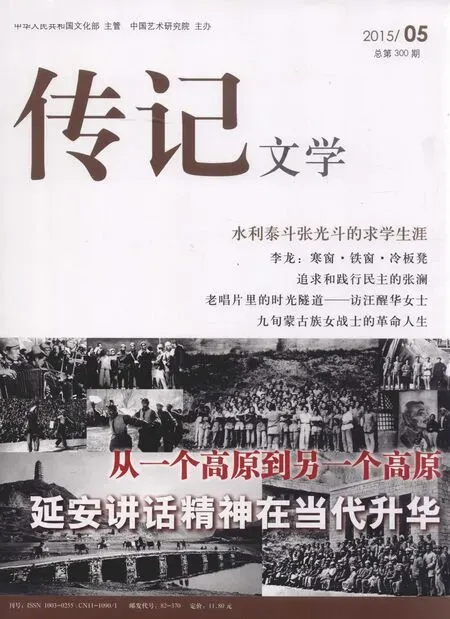《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邊疆學研究:在非洲的故事
文 蔣 暉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邊疆學研究:在非洲的故事
文 蔣 暉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后,根據毛澤東講話整理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發表在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今天對這篇歷史文獻的不斷紀念和反思則是當代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對第一個觀點,大概反對的人少,同意的人多;對第二個觀點,則可能同意的人少,反對的人多。我也持反對意見,但別有原因。反對者的理由一目了然:以《講話》的觀點指導當代文學創造的繁榮局面,確實有其局限性,《講話》是一塊“活化石”,放在顯微鏡下研究研究有其思想和價值,但我們要承認它的熱度、它的光芒已經所剩無幾。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目前國內外對《講話》的研究主要圍繞兩個前提展開,第一個前提在國內研究中很流行,即承認《講話》的歷史地位,承認它是中國革命發展到一個特殊階段而必然出現的一種左翼文學理論。國處危亡,家園不保,這個時候的文學家大多數會以救亡為文學最高使命,而顧不上閑情別寄,賞風吟月那一套文人雅士的士大夫情懷。但當救亡過后,國泰民安,經濟高度發展,文化生產納入市場體制,《講話》的現實針對性也隨之消減。哪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性文學法則呢?這是國內《講話》研究展開的前提。另一個前提則體現在國外研究上,即研究者都看到《講話》曾產生的國際影響,它曾對亞非拉革命作家的寫作起過指導性作用。外國學者想把這種影響說清楚,但是,有些研究者不認同《講話》里提出的文藝主張,筆調常含微諷。
把這兩種主要的研究方式聯系起來,我們就看到,研究《講話》的關鍵在于如何確立它的歷史地位。國內研究者緊箍咒念得太緊了,把《講話》當成了延安土特產,看不到它在國際上的流通。所以我不同意把《講話》的發表僅當成當代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的看法。它其實是唯一在國際上產生影響的中國現代文藝理論。然而,對它的不斷紀念和反思似乎又只是中國的現象,這和《講話》應有的國際地位極不相稱。那么,它為什么不能成為世界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呢?這是今天我們需要面對的問題。
國內和國外的《講話》研究主要的問題是缺乏闡釋,也就是缺乏一個根本的歷史框架去安置《講話》。《講話》確實是中國的土特產,它提出的理想必須有特定的制度保證、特定的文化心理認同和特定的經濟體制支撐。當這些條件不具備或改變了,《講話》的文藝理想就成為了空中樓閣。但我們不應該忘記,如果中國革命具有世界歷史意義,和這個革命相配套的文藝思想也必然具有世界歷史意義,只不過在全球化時代,我們要確定是什么樣的世界、是什么樣的歷史,這樣我們才能研究和闡釋《講話》的內涵。
我自從2014年8月到南非的金山大學做訪問學者,開始接觸非洲現代文學,這才對《講話》在非洲作家那里的影響力有了了解。從這伸展出去,我又讀了一些20世紀60年代美國黑人藝術運動,才知道那邊的黑人文藝家也有許多毛澤東信徒。如果再擴展一點,《講話》在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響也是一個有趣而待展開的話題。按照這種方式,得到了一個我稱之為《講話》的邊疆學研究的版圖。將《講話》從中國腹地移向亞非拉的叢林,把它的中國內涵在第三世界反帝反殖的斗爭歷史中展開,我們才可以看到《講話》的歷史位置——《講話》其實是第三世界反抗文學最為系統的理論表述。第三世界反抗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中的價值有多高,《講話》的價值就應該有多高。第三世界反抗文學是世界現代文學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不完全屬于人文傳統,不宣揚個人的價值,缺乏幻想性質,但它卻是改變世界秩序的一種文學話語,是更加重要的階級解放話語,而《講話》就是這種話語實踐的理論表述。
因此,《講話》歷史意義來自于第三世界反抗文學的整體價值。如果20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是西方殖民體系的解體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的話,那么在這個進程里所產生的文學一定和西方的主流文學有著形式和內容上極大的不同。而且,這部分文學應該成為20世紀文學的主要形式來加以研究,而不應該作為一種落后的西方附屬形式來對待。大的災難會產生大的文學。如果這個世紀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比第三世界更加災難深重的話——想想非洲的饑荒、內戰、貧困、獨裁統治、艾滋病和最近的埃博拉,那么,第三世界就應該是產生大文學的地方。第三世界文學的本質是反抗性的,是為反抗各種各樣的壓迫,階級的、種族的和性別的,而產生的文學。毛澤東的《講話》就是這種反抗文學一個非常系統化的理論表述。
第三世界的文學或許是一個過于寬泛的概念,不同國家的文學實踐面對不同的社會矛盾和文化困境。但它們又有一個共同的核心內容,即農民作為一個階級在現代社會中的歷史命運和出路問題。中國革命是一場現代農民革命。把農民組織到現代國家中去是中國共產黨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核心組成部分。作為中共文學革命綱領的《講話》深刻地體現了這點,它明確提出現代文藝必須為工農兵(主要是農民)服務這個全新的文藝方針。它用階級的語言,提出為誰寫作這個只有從第三世界革命過程中才能產生的理論問題,從這個邏輯點出發,革命文藝里面的其他問題,諸如知識分子和農民關系,內容、態度、立場、黨性,文藝的社會性、審美趣味和語言形式、西方文藝、民間文藝和士大夫文藝的關系等等,全都獲得了一套完整的解答。這些觀點從根本上顛覆了西方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它的核心是否定了后者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和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觀。
第三世界文學的本質是社會底層階級要求革命的文學表述。在不同的歷史條件里,第三世界要求革命的社會底層和他們的壓迫階級不斷變化。比如,對于黑人來說,壓迫并不完全是階級的,而且也是種族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種階級和種族相結合的壓迫模式。整個非洲的20世紀歷史呈現了三個階段的反抗形態。在60年代之前,是黑人反抗白人政權爭取民族獨立的時期。這是第一個階段。革命成功后,非洲大部分國家出現了嚴重的內戰和獨裁統治,種族壓迫變成了階級壓迫,反抗黑人統治階層爭取社會民主運動變成了非洲第二個階段的革命目標,這個目標在80年代逐漸實現。第一個階段的文學與爭取民族獨立的總目標是一致的,這部分文學在60年代被集中譯介到中國。第二個階段文學和反獨裁的政治目標相一致,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就是這種政治的文學表述。相比拉丁美洲,非洲獨裁者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更為嚴酷,所以,反獨裁文學基本由流亡英美的作家完成。獨裁統治過后,就是非洲目前面臨的問題。
《講話》在這三個階段的反抗文學里有沒有起到過什么作用呢?它是如何起作用的呢?就我目前看到的資料而言,《講話》對非洲作家的影響主要發生在第二個階段。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講話》提供的是一套以階級話語來理解文藝的目的和規律,它并沒有涉及到種族壓迫問題,而非洲現代文學的起源是西化的非洲知識分子用殖民語言書寫的文學,這種文學安身立命之處是對抗西方文學對非洲人民的負面書寫,重新喚醒非洲讀者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覺。被譽為非洲文學之父的齊努瓦·阿契貝曾寫過不少文章,闡述第一代非洲現代作家的歷史使命,那就是寫出和《黑暗的心》截然不同的描寫非洲生活的小說。他尖銳地批評西方人描寫非洲的小說不把非洲人看作真正的人:非洲在這類小說里不過是“一套裝置與背景,非洲人性的要素是不存在的。非洲被縮減為形而上的抽象戰場,是游蕩于其中的歐洲人的致命危險。難道有誰看不出幸福的歐洲的變態的傲慢嗎?他們把非洲當成道具去給自己狹隘的頭腦注入一點想象的活力。這還不是問題之所在。這種態度持續地使其筆下的非洲人看起來沒有人性。這類不把另一個人種當人看的小說能算偉大的小說嗎”?因此,在阿契貝看來,非洲作家必須是讀者的老師,他必須通過文學教育公民,“讓我的社會重新獲得自信, 拋棄長期形成的自悲和自賤的心理”。阿契貝認為非洲文學的本質是一種人學。他的觀點比起他的前輩由法語區黑人藝術家和思想家倡導的“黑人性”文學有了新的發展。由塞內加爾第一任總統桑戈爾等人在20世紀30年代發起的“黑人性”文藝運動,雖然也是強調黑人文明的歷史價值,但同時也是強調黑人藝術和其他色種人創造的藝術的差異,這樣在反對種族主義的同時便陷入了另一種種族主義。經過薩特的批評,60年代之后,非洲藝術家不再將藝術區分為黑人的和白人的兩種,而強調他們是人類共同的藝術。許多藝術家開始用現實的筆調描寫現實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但不管怎么說,這一派從20年代紐約哈勒姆黑人聚集區興起的“黑色文藝復興”到70年代在南非興起的“黑人意識”運動形成了共同的非洲人文主義思想,它們構成了非洲尋求國家獨立過程中的種族解放理論,也是非洲主要的民族主義話語的組成部分。在這種意識形態里,階級的問題相比是次要的,大批生活在非洲的白人無產者和工人階級利益被對立起來,黑人無產階級和白人無產階級無法形成政治同盟。《講話》在這種文藝思潮里難以發揮任何影響。
但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從非洲成長起來的第二代知識分子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他們看到的是獨立后的非洲社會面臨社會的貧富差距,執政的黑人形成和西方勾結在一起的權貴階層,新聚集起來的財富流入統治階層的腰包,民眾無法享受應有的政治和經濟權利。這個時候,階級的意識開始形成。文學家以南非的拉馬、肯尼亞的恩古吉和塞內加爾的烏斯曼·塞姆班為代表,向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小說傳統學習,用階級的觀點分析社會問題、描寫社會問題。《講話》在這個時候開始深刻影響非洲社會主義文學運動。
中國讀者對于非洲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的社會主義文學運動不太熟悉,對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如恩古吉和塞姆班等人的研究也不多,所以,為了不亂生枝蔓,下面將從一篇文章談起,介紹一下《講話》和這種運動的關系。
這篇文章是由尼日利亞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Omafume F. Onoge于1974年在加拿大一家雜志發表的,題目為《非洲文學中的意識危機》,此文寫作時間和恩古吉徹底轉向毛澤東思想化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時間幾乎同步。這篇文章的題目本身就很有意思,它的中心詞是“意識”,對意識的強調而不是對文學寫作現實局面的強調,暗示了作者知道在非洲并不具備社會主義文學生長的現實土壤。因此,社會主義文學只能在意識領域被率先構造出來。這種對意識的重視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的,但更是毛澤東思想式的。除了這點,這篇文章的傳播歷史也十分有趣,它于1985年被收入非洲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一部重要文集《馬克思主義和非洲文學》。這部文集的編輯是美國的馬克思主義者Georg M. Gugelberger。但文集里面的作者大多數是非洲的馬克思主義者,把他們的文章對比起來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身為美國的馬克思主義者Georg M. Gugelberger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源主要來自盧卡契和布萊希特關于現實主義文學和現代主義文學的爭論,而對中國和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卻明顯陌生。他本人想使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概念在非洲文學內部區分出代表進步和代表反動的文學動向。反動文學的代表是198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尼日利亞作家索因卡。這本書所編選的文章基本都在找非洲其他作家來對抗索因卡的傳統,這樣,本書各篇文章就被一個中心思想所貫穿——現實主義。但很明顯的反差是,非洲馬克思主義文學家并不是那么熟悉西方馬克思主義著作,也對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紛爭不感興趣。他們熟悉的是毛澤東《講話》和蘇聯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主要是列寧、高爾基、托洛斯基、普林漢諾夫和日丹諾夫,當然也包括馬克思本人的文藝主張。其結果就體現在這部集子最重要的文章《非洲文學中的意識危機》,Omafume F. Onoge在里面大談特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問題。
這篇文章一開始就論述了非洲文學意識轉變的幾個時期,作者采用歷史分期和理論分期兩種框架來描述。歷史分期強調非洲文學在非洲獨立運動中和后獨立時期的顯著差異。他特別指出,第一歷史時期文藝家的貢獻是梳理非洲文化自主意識和自豪感,錯誤是將自己的傳統文化過于浪漫化,形成了文化本質主義,這樣,階級斗爭的意識就被壓制下來。第二個歷史時期,產生了各種意識形態,但主要可以歸于兩個歷史進程,一個是批判現實主義,另一個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的代表為尼日利亞的索因卡和阿契貝。這里,Omafume F. Onoge并沒有將索因卡妖魔化,而是肯定其著作中的現實主義成分。他的文章最后呼吁,當前非洲文學創作的方向,是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建反抗的文學。而毛澤東的《講話》正是在最后一部分被集中引用。也就是說,他把《講話》看成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理論。非洲學者對《講話》的理解有很多是我們想象不到的。第一,比如《講話》最后部分盡管提到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概念,但毛澤東的想法在當時根本和此概念沒有什么關系。第二,非洲學者包括Omafume F. Onoge本人也在文章里經常將毛澤東和托洛斯基的論述并置,根本不了解國內對托洛斯基的批判。這些都是這篇文章有趣的地方。
非洲學者是如何理解《講話》和非洲馬克思主義文藝運動的關系呢?這其中的關鍵,是毛澤東提出的幾個問題,一是文學的階級性問題,二是文學為什么人的問題。文學的階級性不是毛澤東的首創,但文學為什么人這個問題盡管是所有寫作者都會自覺意識到的問題,但被毛澤東從階級的角度提出來,是極大的創造。這個問題要解決中國左翼知識分子脫離革命實踐主體——農民——的局限性,這是《講話》的核心。非洲學者對此體驗得就更為深刻。幾乎所有非洲當代文學的困境就是它的自我封閉,缺乏和人民大眾碰撞的問題。Omafume F. Onoge在文章里不斷談到知識分子與大眾的隔離,這個隔離被分為幾點談論:第一是殖民語言和大眾語言的隔離。用英語、法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等語言創造出的非洲現代文學是不能為大眾所理解的,它只是少數西化精英的文學。第二是精英和大眾的隔離。大眾識字率非常低,因此,如果文學不能口語化,不能表演,根本無法進入大眾的文化生活。恩古吉前四部小說都是用英語創作,即使描寫的多是肯尼亞吉庫尤族的農民生活,他的母親也無法閱讀。這點最后變成他拒絕用英語寫作,而采用吉庫尤語創作的主要動因,和趙樹理自敘堅定走文藝大眾化運動的敘述使用同樣的解釋(趙父聽不懂趙樹理讀的魯迅的小說)。第三就是教育系統完全沿襲殖民教育,使得學生在大學接觸不到非洲作家作品,只閱讀由利維斯等制訂的英國偉大經典。第四個隔絕就是出版業完全由西方出版商控制,他們的意識形態決定和影響了年輕作者的寫作傾向,革命作品幾乎沒有發表的地方。這四種隔絕將為誰寫作的問題提上了最重要的理論問題層面。這才有了他們對毛澤東《講話》認同的社會和歷史前提。
毛澤東的《講話》被引用了兩處,第一段:“但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么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階級則主張地主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不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這段是用來解釋非洲作家采取階級分析來認識社會的合理性。Omafume F. Onoge尖銳地指出,非洲作家比美國黑人作家的處境要好,因為,美國黑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無法放棄種族壓迫理論,因此階級壓迫只是一種次要的社會分析方法。而非洲解決了這個問題。Omafume F. Onoge在1961-1967年在美國留學,獲得哈佛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學位。他接受馬克思主義是在美國開始的,思想也是在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中成熟的。1967年后,他回到非洲在尼日利亞和坦桑尼亞等國家任教,因此對非洲和美國黑人運動是有實踐認識的。他也一定看過毛澤東于1963發表的《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斗爭的聲明》。在該文中,毛澤東鮮明提出,美國黑人的斗爭實質是階級斗爭:“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黃色、棕色等各色人種中的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開明的資產階級和其他開明人士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在美國壓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種中的反動統治集團。他們絕不能代表白色人種中占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其他開明人士。”毛澤東1968年發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支持美國黑人抗暴斗爭的聲明》再次指出:“美國黑人的斗爭,不僅是被剝削、被壓迫的黑人爭取自由解放的斗爭,而且是整個被剝削、被壓迫的美國人民反對壟斷資產階級殘暴統治的新號角……美國的種族歧視,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產物。美國廣大黑人同美國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是階級矛盾。只有推翻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摧毀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美國黑人才能夠取得徹底解放。”
毛澤東以階級斗爭理論引導美國黑人的種族斗爭,因為種族斗爭不能成為第三世界革命理論,它排斥了其他有色人種的介入,將白人無產階級拒之門外,看不清楚整個世界的壓迫模式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奧巴馬上臺后為美國黑人和非洲做了什么特殊的事情嗎?壓迫者不是個人而是制度,不是特定種族而是特定階級,這是毛澤東革命理論的核心思想。將黑人民權運動和其他社會被壓迫階級的革命運動結合起來才能最終形成第三世界革命理論。這個國際革命理論的形成始于1955年的萬隆會議,經過法農的貢獻,再到毛澤東思想,逐漸將亞非拉人民以及第一世界的被壓迫人民看成一個反抗的陣營,第三世界的概念至此超越了地域的疆界。
將毛澤東思想、法農和萬隆精神結合起來,成為20世紀70年代非洲左翼文藝思想的政治出發點。如果仔細看一下Omafume F. Onoge對非洲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特點的總結,我們會發現它和毛澤東《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斗爭的聲明》里面的思想遙相呼應。總結非洲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特點有如下五點:第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視角認為,所有社會問題的解決在于清算資本主義體制。”第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必須在殖民主義制度里解釋資產階級剝削關系形成過程。”第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寫作主題不是抽象普遍的人性,而是為農民和無產階級寫作。第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必須樂觀,必須相信廣大的民眾是改變社會的力量。他們在農民反抗、雇員協會和工人罷工的運動中看到改變的來臨。”第五,“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必須是泛非主義運動,具有國際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這些特點并不是從中國或者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作品中總結出來的,而是從毛澤東思想、法農政治理論里提煉出來的。
毛澤東的“買辦資產階級”這個概念是另一個影響非洲分析社會問題的概念,具有極高的使用率。Omafume F. Onoge引用它來分析非洲后殖民時代的階級矛盾。他說,現在非洲的核心矛盾是人民大眾(農民和無產階級)與買辦資本主義的矛盾。“買辦資產階級”的概念脫胎于中國實踐,但對后殖民的非洲社會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共同的社會現實使得非洲左翼只有讓世界看到,只有超越種族理論,非洲的革命才能成為亞非拉革命的一部分。非洲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看中階級理論,是因為這個理論是當時對非洲唯一可能的國際主義話語。他們企圖把自己的處境和亞非拉被壓迫階級的處境聯系起來,企圖將殖民壓迫轉化為資本主義對無產階級的剝削,企圖將非洲的解放作為全人類的解放之一部分,在這種視野下,階級理論被提了出來。蘇聯在這種語境下不能作為第三世界的代表,而這個代表只能是中國。所以,Omafume F. Onoge指出,現在革命最進步的地方是亞洲,他指的是中國和越南。這也就是毛澤東的理論被用在結尾闡釋的一個原因。
《講話》對非洲作家的影響到底有多深,面有多廣,是一個需要研究的課題。但是東非最偉大的作家恩古吉的文藝思想和作品所受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是不斷從他的理論文章中可以看出來。在他1974年寫的《文學與社會》這篇著名文章里,第二個注解就是來自《講話》,是毛澤東關于藝術的階級性論述那段話。在以后的文章里,也多次提到和引用《講話》。恩古吉一生寫作的主題是肯尼亞農民革命,即歷史上備受爭議的茅茅運動,他要闡釋農民革命在構建以人民為主體的新肯尼亞所產生的歷史貢獻。而當時肯雅塔政府極力抹殺這段歷史的存在,這就形成了肯尼亞知識界重要的農民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之爭的雙重歷史敘述。結果當然是恩古吉被扔進監獄一年,隨后流亡西方。但其一生寫作主題都圍繞著茅茅運動的歷史,這使得他的作品和非洲文學主流形成極大差別。他這點和中國革命歷史文學有著異曲同工之處。但是,因為茅茅運動在1953年就被鎮壓下去,十年后,肯尼亞獨立。茅茅不是導致獨立的革命,而恰恰是被鎮壓后獨立才發生,茅茅是獨立發生的前提。革命知識分子如恩古吉飽嘗革命失敗的迷茫和苦痛,圍繞茅茅運動創造出的主人公形象的精神狀態,頗似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后茅盾那代人的心情。農民革命在恩古吉筆下從來沒有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農民革命文學所體現出來的歷史進步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精神。恩古吉幾乎全盤接受了《講話》思想,特別是文藝的階級性和文藝為誰服務的論點,是理解恩古吉文學發展的根本點。恩古吉認為文學必須是為人民寫的,這樣,他在用英文寫了前四本小說后,改用吉庫尤語創作,并回歸非洲口語文學傳統。吉庫尤并不是一種書面語言,所以恩古吉的工作就是要創造出吉庫尤的書面語言。在《去殖民化的語言》一書中,他談到了發明吉庫尤書面語言所遇到的一些困難。同時,他也談到在使用自己的人民的語言寫作時所獲得的極大的解放感。因為茅茅運動是農民運動,茅茅戰士使用的不是英語,而是吉庫尤語。用英語描寫他們的對話,而且寫完后吉庫尤人還看不懂,這種尷尬恩古吉忍受了幾年,最后終于放棄英語,他說今后只用英語寫文學研究,后來他干脆宣布,連文學研究也不用英語寫了。《講話》從來沒有要求革命作家放棄普通話而使用方言寫作,因為在中國,普通話被實踐證明是保證各個民族和地區文化交流的最好工具。毛澤東只要求回到農民的語言寫作。但這個問題在肯尼亞就成為了回到一個少數民族語言寫作問題,因為除了英語,肯尼亞各個部落都有自己的語言。恩古吉沒有使用“東非普通話”——斯瓦希里語寫作,表現了他的激進政治的一面。茅茅運動主體是吉庫尤族人,所以他就用這個族人的語言書寫。這是對毛澤東《講話》語言問題的一個特殊處理。語言既是《講話》中討論文學形式時的重點,也是恩古吉創作必須做出的選擇,不僅是他,整個非洲現代作家都面臨是使用殖民語言還是自己民族語言書寫的問題,這也是第三世界文學形成自己主體性必須面對的問題。《講話》是從中國內部需求對這個第三世界語言形式問題所做出的一個說明。
《講話》在今天依然有著龐大的生命力。舉一個個人的例子。我在南非金山大學訪學期間,曾上過一門非洲文學理論的課。課上討論了南非女作家黑德的一些作品,其中授課教授引導大家討論黑德晚年想重新發現和書寫博茲瓦納民間故事和寓言的努力。討論在我看來進行得非常不得要領。因為,黑德的努力不過是用英語重寫博茲瓦納的民間故事,而且期待讀者是知識分子。黑德的工作很像中國新文化運動中對民間文學的發現和重構,是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一種努力,這和恩古吉思想也和毛澤東思想是不一樣的。我當時的發言是提出要從“為什么人”這個角度來看,就能看清楚黑德到底持的是什么知識分子立場了。發言過后,一名四年級本科生立刻對毛《講話》表示了極大興趣。他說“為什么人”是非洲文學必須面對的問題。是為白人寫,還是為黑人寫;是為中產階級寫,還是為底層人民寫,都非常關鍵。隨后我了解到,他年紀輕輕已經加入了非洲目前最激進的革命黨組織——“經濟自由戰士”。這個黨正因為表示代表黑人窮人的利益而獲得底層支持,是草根黨,口號是將所有白人趕出南非,重新收回土地分配給農民。我當時就感到,只有真正在底層進行群眾斗爭、走群眾路線的黨才會理解毛澤東《講話》的重要意義。
今天,我們重新反思《講話》,核心的問題在于,我們是否還把中國當代文學看成是第三世界反抗文學的一部分?如果脫離這個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最根本性質的思考,我們的文學在整體上就會迷失方向,《講話》當然也就會成為如有些人所說過時的東西。紀念《講話》就是重新回到真實的和能動的現實政治中,找到文學真正推動歷史進步的力量源泉。

延安楊家嶺革命舊址示意圖,其中的中央辦公廳樓,就是延安文藝座談會舊址
責任編輯/斯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