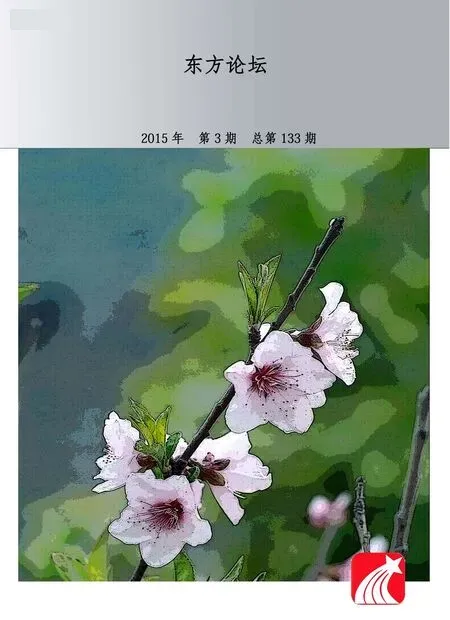自由·必然·本體:徐訏“反思文學(xué)”的聚焦——兼議其哲理路徑與空間構(gòu)型
馮 芳
(浙江大學(xué) 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07)
從作品的質(zhì)與量及影響力來看,徐訏堪稱為20世紀(jì)中國最大的自由主義作家,哲學(xué)科班出身以及畢生的皓首窮經(jīng),是其作品具有獨(dú)特價(jià)值的主要原因。由于徐訏作品卷帙浩繁凡二千萬有余,且其文學(xué)作品中象征頗多、曲折蘊(yùn)藉,因此當(dāng)前研究中不免時(shí)常出現(xiàn)“失道于博雜幽深之中”的現(xiàn)象,表現(xiàn)為以偏概全、焦點(diǎn)不明、看不到深層結(jié)構(gòu)等等。
有鑒于此,本文乃從宏觀上揭示徐訏文學(xué)作品精神聚焦的內(nèi)容、聚合起精神焦點(diǎn)的哲理路徑,以及傳達(dá)精神的話語空間構(gòu)型,并認(rèn)為徐訏文學(xué)創(chuàng)作基本屬于“反思文學(xué)”,其中不少作品是“哲理的‘藝術(shù)直觀’”。
一、聚焦于精神:“反思文學(xué)”與哲理的“藝術(shù)直觀”
徐訏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基本上可歸為“反思文學(xué)”。“反思”指的是徐訏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運(yùn)用康德所說的審美反思能力,即那種由直感反思到知性、理性的審美判斷力,以及那種懂得反思“合目的性”的審美判斷力。借著前者,徐訏由直觀世界反思到大小系統(tǒng)可能的必然性;借著后者,徐訏在反思中加入了關(guān)于萬物具有合目的性的考慮,從而反思到憑真善美可以使自然有合人的目的性而人的道德有合“自在之物”的目的性,最終反思到宇宙的本體。受現(xiàn)代科學(xué)、唯物主義哲學(xué)、非理性哲學(xué)的影響,徐訏在康德式的反思中,加入了許多新的內(nèi)容。
反思,是由直感到知性、理性,但相反的是,徐訏有部分作品是拿著理性去尋找直觀對應(yīng)物,即文學(xué)批評中常與貶義相隨的“理論先行”,但在徐訏身上我們應(yīng)摒棄這種定見,因?yàn)檎軐W(xué)專業(yè)出身的徐訏有此表現(xiàn)非常合乎邏輯,其藝術(shù)運(yùn)作方式正是謝林所說的由“理智直觀”到“藝術(shù)直觀”理論的活用。謝林說:縱觀整個(gè)歷史,人總是自由地行動,但又總是受到必然性的支配,這一矛盾過程本身使得自由與必然逐漸接近和融合,顯露出背后起作用的“天意”,不過在現(xiàn)實(shí)的歷史活動中人的意識總是難以符合對歷史的真正自我意識。因此,只有借助于一種“知性直觀”才能超前地意識到歷史的最終目的,在這種理智直觀中,人憑借自己的理智創(chuàng)造出直觀的對象來,從而使自已和這個(gè)對象直接同一。這就是哲學(xué)家所做的工作,這是一種“精神的藝術(shù)感”。但這種哲學(xué)的創(chuàng)造仍然與主觀相對立。要真正將人的精神擴(kuò)展到自然界,達(dá)到主觀和客觀在客觀上的同一,還必須借助于“藝術(shù)直觀”,即真正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在藝術(shù)創(chuàng)造中,人不但現(xiàn)實(shí)地創(chuàng)造出一個(gè)客觀對象來,還忘情于對象之中,因此有意識和無意識、直觀者與被直觀者、有限與無限、自由與必然在這里完全合一。謝林這種“藝術(shù)直觀”研究的不是藝術(shù),而是以藝術(shù)形象出現(xiàn)的“宇宙”,最終它還是返回哲學(xué)。謝林這一思想是在康德影響下生發(fā)的,而徐訏對這兩位哲學(xué)家都有關(guān)注[1](P197)。
二、精神聚焦的內(nèi)核:自由·必然·本體
徐訏的反思文學(xué)在何處聚焦?穿過所有文本,我們發(fā)現(xiàn)徐訏文學(xué)作品的精神聚焦乃在于:抒寫個(gè)體的生存體驗(yàn),反思個(gè)體生存現(xiàn)象背后的人格、人性乃至民族、人類社會歷史文化的得失,求索并揭啟個(gè)體乃至人類自由幸福之路徑。倘使我們非要從中提煉關(guān)鍵詞,那么僅有“自由”及其關(guān)聯(lián)的“必然”“本體”足以涵蓋,這些精神聚焦是由人性本然、20世紀(jì)多災(zāi)多難的歷史、徐訏的精神稟賦所共同決定的。以下便以此為綱,展示徐訏文學(xué)創(chuàng)作精神聚焦的博雜內(nèi)容。
首先,徐訏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聚焦于人性自由。關(guān)于人性自由,徐訏的聚焦又主要分為以下幾點(diǎn):其一,聚焦于人物殘缺人格及其修繕。徐訏是一位內(nèi)外體驗(yàn)都非常豐富的作家。幼年時(shí)期,他曾接受過分嚴(yán)厲的教育,年有稍長,他又經(jīng)歷頻仍的轉(zhuǎn)學(xué),且跳級與年長者同班,滋生出盲目自卑的心理,為此他研修心理學(xué)以謀求超越,并以淑世憫人之心寫成作品幫助心理疾患者。其二,聚焦于探尋能創(chuàng)建并維持自由幸福共同體所需的倫理道德。徐訏作品廣泛關(guān)注婚戀哲理與人際倫理,徐訏在屬人的因緣之網(wǎng)中沉浮,常常感到生而為人的不自由、不幸福,與他者關(guān)系的不和諧,在康德與弗洛伊德的框架中,他尋訪于各種學(xué)說,不懈地探尋并披示能創(chuàng)建并維持自由幸福共同體所需的倫理道德。其三,聚焦于喚醒現(xiàn)代個(gè)人主體意識。徐訏生長在破落的小富之家,弱冠之前混跡在城鄉(xiāng)之間,抗戰(zhàn)時(shí)隨著流民逃亡,與廣大貧民階層在情感上水乳交融,他共鳴于他們的艱難處境,看到他們精神意識的混沌未鑿感到痛心疾首,因此他如同當(dāng)年的盧梭一般,殷切地啟示廣大民眾以現(xiàn)代個(gè)人主體意識。同時(shí),作為一名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他與廣大知識分子與城市平民在生存體驗(yàn)上有廣泛的交集,他常常感慨廣大市民終日鉆營于功利而輕忽內(nèi)心需要,背離了更高自由幸福生活的要諦,他的作品也表現(xiàn)了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在20世紀(jì)風(fēng)云變幻中追求自由幸福的艱辛心路與多舛命運(yùn)。其四,聚焦于建立此岸性質(zhì)的近世大同信仰。徐訏或游學(xué)或工作于外邦,與各國人民往來密切,他洞悉西方人民的精神世界在世俗化以后、在現(xiàn)代性弊端面前已經(jīng)千瘡百孔,他由弱國人民備受歧視的處境而想到傳播“意識平等”的重要,他深感中國傳統(tǒng)的道家、儒家各有缺失,兇吉未卜的烏托邦也難成為信仰,一個(gè)多元綜合的近世信仰有待建立,并且,他在建立信仰的同時(shí)也發(fā)揮了康德對純粹理論理性的批判精神。由于徐訏是一個(gè)實(shí)事求是、具有歷史主義精神的理想主義者,因此徐訏對于人性自由的聚焦涵蓋了從人的基本生存自由到高層次的自由幸福追求的內(nèi)容。在文本中,他糅入了心理學(xué)、人生哲學(xué)、生命哲學(xué)等經(jīng)過其思力篩選過的智思,搭建起豐厚的哲理意蘊(yùn)層,如:開發(fā)生命空間、呼吁張揚(yáng)個(gè)體生命潛能、療救人的心理疾病、揭示異化生活的實(shí)質(zhì)、建構(gòu)使人際和諧的倫理、超前建構(gòu)生態(tài)倫理、倡揚(yáng)真善美價(jià)值、展現(xiàn)求索宗教信仰的心路歷程。
其次,徐訏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也聚焦于存在自由。徐訏出生在浙江慈溪,少兒時(shí)代隨父到上海生活,此后在滬京兩地讀中學(xué),在北大讀本科并進(jìn)行研修,再到上海做作家任編輯,接著到法國攻讀博士,游歷歐洲列國,抗戰(zhàn)爆發(fā)后回國繼續(xù)寫作,先是在孤島工作,而后輾轉(zhuǎn)流亡至大后方,進(jìn)而被委派到美國工作,抗戰(zhàn)勝利返回上海寫作,在居港之前他的足跡已遍及了大陸各地與世界各地。1950年他遷徙到香港居住,此后多半在香港從事辦刊、辦出版、寫作、教育工作直至終老,在此其間,他還曾兩次到新加坡任職,多次訪問臺灣,講學(xué)于印度,多次參加國際會議,訪問日本、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再游歷含蘇聯(lián)在內(nèi)的歐洲列國。由此可見,徐訏的人生經(jīng)歷非常豐富,他對于許多國家或地區(qū)的存在自由狀況頗有見聞,因此能夠?qū)⒅姓{(diào)和。在徐訏足跡播撒之處,他意識之中涌動的仍然是世界各國民眾的生存狀況,他們是否自由幸福。這自然與20世紀(jì)世界歷史進(jìn)程以及各國或地區(qū)的發(fā)展?fàn)顩r有關(guān),而20世紀(jì)是個(gè)炮火紛飛、硝煙滾滾而后籠罩在冷戰(zhàn)陰云中的世紀(jì),徐訏曾在其1957年的散文中寫道:“我們經(jīng)歷了兩次中國的大革命,兩次世界大戰(zhàn),六個(gè)朝代。這短短幾十年工夫,各種的變動使我們的生活沒有一個(gè)定型,而各種思潮也使我們的思想沒有一個(gè)信賴。……我同一群像我一樣的人,則變成這時(shí)代特有的模型,在生活上成為流浪漢”[2](P1)。身處在這樣的亂世之中,社會存在所給予徐訏的多半是創(chuàng)傷體驗(yàn):徐訏對于中國農(nóng)民低下的生活條件、城市中弱勢群體生活的窘迫耿耿于心;對于本民族在西方堅(jiān)船利炮的威壓與現(xiàn)代科技的挑戰(zhàn)之下進(jìn)行屈辱而傖促的轉(zhuǎn)型深深感思;對于人情文化與權(quán)力媾和所產(chǎn)生的貪腐、儒學(xué)及社會制度所培育出的等級意識、倫理系統(tǒng)崩潰后大行其道的庸俗社會學(xué)等深惡痛絕;對于國民黨此前的專制腐敗有話要說,對于文革的專斷統(tǒng)治也有許多警辟的思悟;在戰(zhàn)爭面前,他對于和平的脆弱、個(gè)人主義的弊端、國家主義的危險(xiǎn)、文化的虛偽、人性的罪惡看得透徹;在和平時(shí)期,他對于種族歧視、民族間的隔閡、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幕簾重重、核戰(zhàn)爭與太空戰(zhàn)的危機(jī)都希望盡一己之力去促其改變;對于現(xiàn)代科技弊端與人類生存危機(jī)的深化他也始終關(guān)注并思索出路。因此,徐訏的文學(xué)作品是對其以上生存體悟的詩學(xué)轉(zhuǎn)化,在其間他借用馬克思主義、西方自由主義以及多種文化哲學(xué)進(jìn)行反思,建構(gòu)起比上述人性自由更為真切的關(guān)于存在自由的精神建構(gòu),包括:改良文化環(huán)境、推促民族解放、促進(jìn)民族現(xiàn)代化建構(gòu)、反叛專斷統(tǒng)治、降解激烈的階級斗爭、熔爐多種宗教以求趨同、追求世界和平、建構(gòu)生態(tài)和諧文化。總之,他的作品在存在自由層面上的精神聚焦是:如何建立起個(gè)體、民族乃至人類的自由幸福家園。徐訏在存在自由問題上的態(tài)度是歷史主義的,他的理想雖然呈現(xiàn)出超越歷史的盡善盡美,卻以諸如“好政府主義”來期待現(xiàn)實(shí)。
再次,徐訏文學(xué)聚焦于對形而上必然性的追尋。徐訏尤其注重從諸多表象中反思其后可能的必然性,這也是徐訏對西方傳統(tǒng)哲學(xué)命題的承續(xù)。因此,我們在徐訏的文學(xué)作品中常常看到他意欲在人的宇宙生存經(jīng)驗(yàn)之中,提取出關(guān)于宇宙整體系統(tǒng)、中觀系統(tǒng)、微系統(tǒng)的形而上原則,具體表現(xiàn)在他對于生命演進(jìn)規(guī)則、人性本質(zhì)、情愛真諦、共同善原則、自由規(guī)律、真善美終極原則、社會歷史發(fā)展動力及必然性、人與自然關(guān)系規(guī)律、神秘的“絕對同一”等等方面的探索,其間含有對純粹理論理性的批判色彩。徐訏那些體現(xiàn)了謝林“藝術(shù)直觀”理念的作品就屬于這一視閾。
最后,徐訏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聚焦于拓展生命空間與求索宇宙本體。徐訏是一位有靈性的作家,他自小接受基督教熏染,又與佛道有興會,因此盡管后來信奉唯物主義,但易于與柏格森的生命哲學(xué)發(fā)生共鳴,又步入偏門叩問鬼域靈界,另外復(fù)蘇起與佛學(xué)、道家、基督教的因緣,最終經(jīng)由康德式的反思找到了宇宙的本體——上帝,因此此類思悟在其文學(xué)作品中俯仰俱是。
徐訏聚焦于前述自由、必然、本體,歸根結(jié)底在于關(guān)懷人的生存。值得一提的是,在自由之外,徐訏并非不關(guān)注平等。早在1930年青年徐訏就在其論著《元元哲學(xué)》中自主地思考精神平等,他認(rèn)為“在求物質(zhì)的平等以前,我們更要緊的是求精神的平等”,為此應(yīng)取消一切的精神崇拜與輕視[3](P1)。1956年他又指出:“合作、互助、互補(bǔ)、互尊,才是諧和之最高理想。”“人因?yàn)樯鐣黄降龋?jīng)濟(jì)之不齊,機(jī)會的不均;往往使任何努力都無法與社會取得諧和”。進(jìn)而要求改善社會環(huán)境:“我們的社會必須徹底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與平等,這就是說,對于社會的限度應(yīng)盡力使其減少與改進(jìn)。”[4](P35)毋庸諱言,徐訏對于意識平等有更多強(qiáng)調(diào)而對于物質(zhì)平等不夠重視。
三、聚合起精神焦點(diǎn)的哲理路徑:兩條自由路向與多重自由觀
哲學(xué)科班出身的背景,決定了徐訏求索自由的路向與中西方自由文化史息息相關(guān),表現(xiàn)在:徐訏將求真(必然性)、求善以達(dá)自由的路向與宗教救贖接受性的自由路向相結(jié)合。提及這一點(diǎn),不得不提康德哲學(xué)。從徐訏一生來看,他的精神系統(tǒng)可以說是以康德哲學(xué)作為起點(diǎn):在青年時(shí)代徐訏就接受了康德的影響,但長期以來唯物主義與存疑論是徐訏精神系統(tǒng)的基礎(chǔ),因此他曾說在科學(xué)面前“一代大哲學(xué)家康德的道德論中所容納的神,現(xiàn)在也沒有去向”[5](P45)。那時(shí),康德哲學(xué)對于徐訏的意義主要在于康德對“個(gè)人的地位與尊嚴(yán)”的詮釋[6](P9-10)、對于純理性的批判、開創(chuàng)“哲學(xué)上的研究路徑”“提供了哲學(xué)上所有的問題”[1](P196);此外,前述徐訏求索自由的兩條路向從集大成的康德哲學(xué)中也能見出;并且,此時(shí)未信宗教的徐訏已有許多宗教體驗(yàn)且頻頻勸人皈依宗教,儼然一派欽慕美德的康德作風(fēng)。晚年,徐訏最終皈依了基督教,不能不說是由于康德純理性批判早早為他開出了空間。但徐訏能打破康德的格局,他認(rèn)為康德所了解的人心過于理性而有序,這點(diǎn)已被弗洛伊德學(xué)說打破,同樣的,牛頓所認(rèn)為的世界也過分固定有序而已被愛因斯坦相對論所打破,他還認(rèn)為康德偏于唯心,未能像馬克思那樣重視人類社會生產(chǎn)實(shí)踐,因此他對康德哲學(xué)進(jìn)行了修正。也正因此,徐訏比高度強(qiáng)調(diào)“道德”的康德更強(qiáng)調(diào)“幸福”,并且比康德更強(qiáng)調(diào)非理性作用以及社會生產(chǎn)實(shí)踐。總之,我們從徐訏文學(xué)作品中可以摸索出的關(guān)于求索自由的兩條路向——求真、求善以達(dá)自由的路向、宗教救贖接受性的自由路向,可以認(rèn)為是集大成的康德哲學(xué)為徐訏指出的。
在求真(必然性)求善以達(dá)自由的路向中,徐訏文學(xué)作品表現(xiàn)出熔鑄多元自由觀的特征:譬如在徐訏作品中留下大量蹤跡的弗洛伊德自由觀,譬如徐訏并未提及而全然心契的馬斯洛自由觀,譬如徐訏有些契合的道家自由觀,譬如徐訏推崇的柏格森自由觀,譬如徐訏視為隱含參照系卻并不認(rèn)可的薩特自由觀與尼采自由觀,譬如徐訏在批判中予以一定認(rèn)可的儒家自由觀,譬如徐訏欽仰卻難以全然實(shí)踐的康德自由觀,譬如徐訏并未提及而可作為參照系的海德格爾自由觀,譬如徐訏欽慕的洛克自由觀,譬如影響徐訏早年頗多的伊璧鳩魯自由觀,譬如徐訏在相當(dāng)程度上肯定的馬克思主義自由觀,譬如徐訏由反思現(xiàn)代性弊端而接近的生態(tài)自由觀,等等。這些自由觀各有利弊,它們不但對于自由看法不同,而且其人性觀、歷史觀基礎(chǔ)也不盡相同,而具有求是信念的徐訏從不缺乏懷疑與批判精神,因此他透過人類活動來把握人性本質(zhì),把握宇宙系統(tǒng)運(yùn)動發(fā)展的規(guī)律,從而對上述自由觀作了揚(yáng)棄、熔爐的處理,進(jìn)而指導(dǎo)他謀求自由的活動。
在宗教救贖接受性的自由路向中,也即是尋找宇宙本體的路向中,徐訏的文學(xué)作品向我們展現(xiàn)了他對于伊斯蘭教、佛教、基督教自由觀尤其是后兩者漫長的求思體悟過程。
并且,徐訏的文學(xué)作品在東西方文化比較視野中披示東西方自由文化各自的缺失,并加以修繕。
總之,徐訏不懈地求索自由于人本主義學(xué)說的網(wǎng)絡(luò)之中,而自由實(shí)踐活動與難以捉摸的宇宙本體的關(guān)聯(lián)決定了這一過程必然是永無窮盡的,因此我們透過徐訏作品人物的認(rèn)知、倫理、實(shí)踐、超驗(yàn)活動,不難發(fā)現(xiàn)徐訏一直在不斷地對自我的自由觀進(jìn)行調(diào)整。
自由主體意識在20世紀(jì)中外思想界中發(fā)生了美學(xué)轉(zhuǎn)向,表現(xiàn)在三個(gè)方面,一是自由主體更多地思考主體間性;二是自由主體必須將生態(tài)和諧與可持續(xù)性發(fā)展納入其意識之中;三是自由主體以往通過探索宇宙本體來求取自由的方式,現(xiàn)在相當(dāng)大程度地被懸置或置換本體的方式所代替。透過徐訏的文學(xué)作品,我們可以看到徐訏的自由主體意識與時(shí)代并進(jìn)甚至走在了前頭,其理想人物的主體意識之中包孕著主體間性與生態(tài)觀念,此外,其作品中的人物時(shí)而探索宇宙本體以求自由,時(shí)而懸置宇宙本體憑直覺主義張揚(yáng)自由,不過即便如此,從他晚年皈依天主教之舉可以看出,他最終認(rèn)同的還是上帝本體觀。總之,徐訏作品中的自由主體意識極其先鋒。
四、涵泳精神的話語空間型構(gòu)
徐訏的話話空間型構(gòu)與其聚焦于自由的精神建構(gòu)涵泳為一體,從整體上來看,堪稱為“有自由意味的宇宙形式”。具體有以下特點(diǎn):
(一)關(guān)于屬人世界的話語空間有“揭批系統(tǒng)——創(chuàng)化系統(tǒng)”的型構(gòu)。
徐訏的文學(xué)作品從整體上看有“揭批系統(tǒng)——創(chuàng)化系統(tǒng)”的型構(gòu),從單個(gè)文本來看也時(shí)常有此型構(gòu)。這是因?yàn)樾煊挶救耸窍到y(tǒng)型思維,從一篇散文中可以約略窺見其系統(tǒng)的架構(gòu),他說:“小說既是反映人生,人生是離不開生活。生活不外乎人與人的關(guān)系,人與大自然的關(guān)系,人與命運(yùn)的關(guān)系以及人與死亡的關(guān)系”。[7](P146)由此看出,徐訏創(chuàng)作的運(yùn)思離不開這幾層關(guān)系,為了更合于思維習(xí)慣,我們可以將其轉(zhuǎn)換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社會與人的相互作用在人身上顯為“命運(yùn)”)、人與人、人與其生命(“死亡”為人生命物質(zhì)形式的最后顯現(xiàn))。同時(shí),如前所述,徐訏畢生探索宇宙中大小系統(tǒng)的內(nèi)核或必然性并有許多洞見,因此他熱衷于“揭批系統(tǒng)”。并且,徐訏不滿足于給予消極的批判,他往往提出建設(shè)性意見,對系統(tǒng)進(jìn)行補(bǔ)偏救弊,力求促使現(xiàn)有的那個(gè)封閉、僵化、壓抑的生命存在系統(tǒng)向可然的開放、生氣、自由的生命存在系統(tǒng)逐漸進(jìn)化,此乃對柏格森“創(chuàng)造進(jìn)化論”的活用。于是便形成了“揭批系統(tǒng)——創(chuàng)化系統(tǒng)”的話語空間型構(gòu)。
在系統(tǒng)中常常出現(xiàn)復(fù)調(diào)。這有兩種表現(xiàn):一是在同一文本之中,可以同時(shí)有宏觀主題、中觀主題、微觀主題,有時(shí)它們有相近的指向,有時(shí)其邏輯聯(lián)系并不緊密。二是在同一層次或同一論域之中,可以并存兩種或兩種以上觀點(diǎn),它們有時(shí)在辯論中逐漸趨同,有時(shí)各自顯現(xiàn)其合理性或各自顯現(xiàn)其極端性,由此彼此消解或彼此滲透,但并不圖謀說服對方,因此呈現(xiàn)出復(fù)調(diào)和鳴的樣態(tài)。顯而易見,復(fù)調(diào)既是徐訏系統(tǒng)型思維的體現(xiàn),也是其力圖在文本之中建構(gòu)多元共生的自由空間的一種典型表現(xiàn),同時(shí)也是對純理性批判的結(jié)果。
在系統(tǒng)中常常出現(xiàn)“我—你”結(jié)構(gòu)。徐訏向往的是對話,而非互不干擾的消極自由,即便無法對話、難以求同,他也袒露心跡以求可能的了解,這是由于徐訏目視到個(gè)人主體性的張揚(yáng)會孳生出孤獨(dú)的時(shí)代病與不和平,因而他努力地去規(guī)避,并用生命主體間性理論去構(gòu)筑一個(gè)多元和諧的共同體。
系統(tǒng)中也常常出現(xiàn)“‘世界人’深層文化結(jié)構(gòu)”,或者說“跨國生存空間結(jié)構(gòu)”。最典型表現(xiàn)在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常往來于世界各地但安家在故里,這既是徐訏個(gè)人經(jīng)歷的折射,顯然也是其暗示給讀者擴(kuò)充自由的方式。
(二)作為自在之物的“宇宙”空間結(jié)構(gòu)。徐訏面對蒼穹、自然、歷史、未來,不斷地求索宇宙本體,因此,其作品中的系統(tǒng)其最大界域是無垠的宇宙,這是徐訏作品中重要的領(lǐng)域。
由此可見,徐訏作品的話語空間堪稱為“有自由意味的宇宙形式”。換個(gè)角度來看,也可以將徐訏話語空間分為三個(gè)——經(jīng)驗(yàn)空間、超驗(yàn)空間、倫理空間,這三個(gè)空間水乳交融,共同構(gòu)成了徐訏這樣一個(gè)物心論者的完整體驗(yàn),從更廣闊的視閾來看,這也是20世紀(jì)人類體驗(yàn)的一個(gè)角度。
五、結(jié)語
20世紀(jì)的塵埃已經(jīng)落定,如今我們可以更客觀地看待徐訏的作品,因此也更有機(jī)緣來貼近其思想原貌。以往對于徐訏作品哲理意蘊(yùn)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也存在許多不足:對于生命研究挖掘不夠,對于經(jīng)驗(yàn)層面的研究不重視。有的研究過分強(qiáng)調(diào)徐訏作品中消極悲觀虛無的一面,未能充分理解徐訏建構(gòu)自由文化的深意,有的雖然認(rèn)識到徐訏對自由的追求但淺嘗輒止,這使得徐訏作品中的人生自由之思沉寂已久。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局面,主要由于沒有重視更直接、更明顯地表達(dá)自由訴求的徐訏的雜感文,因而容易忽略徐訏文學(xué)作品中以隱喻方式存在的大量的自由文化。這起初是由于徐訏雜感文長期以來在大陸缺佚的客觀原因造成的,而現(xiàn)在更多是由于徐訏作品卷帙浩繁所造成的。
筆者深深體悟到徐訏對于精神建構(gòu)的熱情與執(zhí)著,他傾瀉畢生思力,乃在于求索人生自由幸福的真諦,他還努力創(chuàng)化出一個(gè)自由幸福的社會,因此惟有將其作品精神價(jià)值充分挖掘,才不負(fù)其鵠首之苦,他那編織在層層符碼之中的精神建構(gòu)如能浮出水面,對于求索自由幸福的當(dāng)代人而言將是一種福祉。這是因?yàn)樗淖髌肪哂幸匀藶楸尽㈥P(guān)懷平民的精神品格,并且它們匯集了人類智思去全面地關(guān)懷個(gè)體的生存,在20世紀(jì)喧囂的洪流中猶如擎于高處撫慰眾人之心而不曾失色的一支橄欖枝。在歷史上,徐訏的文學(xué)作品已產(chǎn)生過巨大的影響,其精神建構(gòu)在許多方面具有前瞻性或預(yù)言意味,對于現(xiàn)實(shí)與未來,它們也具有巨大的啟示意義。
[1] 徐訏.論馮友蘭的思想轉(zhuǎn)變[A].場邊文學(xué)[M].香港:上海印書館,1971.
[2] 徐訏.道德要求與道德標(biāo)準(zhǔn)(代序)[A].個(gè)人的覺醒與民主自由(第二版)[M].臺北:傳記文學(xué)出版社,1979.
[3] 徐訏.元元哲學(xué)[M].北平:時(shí)空社,1930.
[4] 徐訏.個(gè)人主義的觀點(diǎn)與自由的限度[A].個(gè)人的覺醒與民主自由(第二版)[M].臺北:傳記文學(xué)出版社,1979.
[5] 徐訏.談鬼神[A].蛇衣集[M].臺北:正中書局,1978.
[6] 徐訏.自由主義與諧和論[J].香港:明報(bào)月刊,1967,(7).
[7] 徐訏.美國短篇小說新輯序[A].門邊文學(xué)[M].香港:南天書業(yè)公司,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