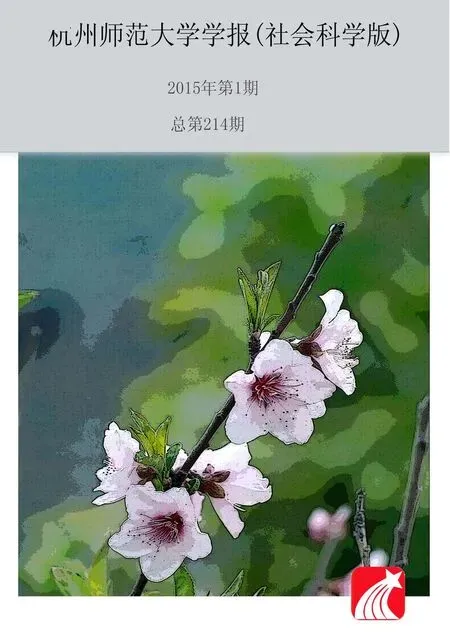超人歸來:尼采詩學再論
徐 岱
(浙江大學 人文學部, 浙江 杭州 310058)
?
文藝新論
超人歸來:尼采詩學再論
徐岱
(浙江大學 人文學部,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作為一門學科的現代詩學,存在著一個“從古典至現代”的轉變,這個歷史時刻能夠以一個人的名字為代表,他就是尼采。本世紀以來,每年出版的有關尼采的書籍,其實超過了關于任何其他思想家的著作。這說明,作為“哲學超人”的尼采事實上早已攜帶著其“不合時宜的思想”悄然歸來。在某種意義上,當尼采被公認為“后現代主義”首席思想家時,事實上也意味著他是從古典“藝術哲學”向現代“生活詩學”轉向的“詩學革命”的真正開創者。凡此種種都使我們有必要對尼采的詩學思想給予重新討論。對待尼采詩學,最忌諱的是帶著偏見的批判,最需要的是擱置成見的理解。
關鍵詞:尼采;超人思想;倫理詩學
一
雖然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美學研究,是與西方啟蒙思想同步發展起來的產物,但從柏拉圖的《大希匹阿斯篇》到20世紀以來的各路美學門派,不可否認在相對意義上,存在著一個“從古典至現代”的轉變。這個歷史時刻能夠以一個人的名字為代表,他就是尼采。迄今為止的當代學界,在“理論之后”的喧囂聲中,隨著曾經聒噪一時的“德里達們”的“解構浪潮”漸漸偃旗息鼓,諸如“現象學”與“存在論”等一度成為理論界的時尚言說,也像巴黎的年度“時裝秀”那樣失去了曾有的光澤,美學領域的那種迷惘感似乎又卷土重來。但盡管如此,仍有證據表明,本世紀以來每年出版的有關尼采的書籍,其實超過了關于任何其他思想家的作品。這說明,作為“哲學超人”的尼采事實上早已攜帶著其“不合時宜的思想”悄然歸來。毫無疑問,關于尼采思想仍有著大量的研究空間。但從“倫理詩學”這個主題來講,尼采的意義顯得更不容忽視。換句話說,缺少對尼采美學的重新認識,任何關于倫理詩學的研究都將是不完整的。
事實上,無論從尼采的《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還是《道德譜系學》等一系列著作,我們都不難發現在尼采的美學中,對倫理問題的思考占據著一個核心的位置。在某種意義上,當尼采被奉為“后現代主義”首席思想家時,事實上也意味著他是從古典“小美學”轉向現代“大美學”的“美學革命”的真正開創者。眾所周知,如果說康德的所謂“哥白尼革命”開啟了西方現代思想;生前遭到同時代學界忽視乃至鄙視的尼采,以一句驚世駭俗的“上帝死了”,讓一如既往地沿著蘇格拉底—柏拉圖思想軌跡前行的西方文明,形成了一個“后現代拐點”。有研究者指出,在尼采作品中至少有15處左右關于上帝之死的描寫,而且“都寫得極其美麗”。[1](P.33)
在有著悠久的崇尚基督教傳統的西方學界,尼采也因此而注定了成為倍受爭議的角色。不僅如此,尼采本人甚至還公開表示,自己能“用十句話表達他人需要用一部書才能做到的表達,并說出他人在一本書中都無法表達的內容”。其傲視群雄的精神溢于言表。
時至今日我們有理由認為,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種狂妄之態,讓眾多因虛榮心膨脹而習慣于自戀的學術名利場,對這位思想巨人的評價形成好惡分明的兩極:恨之者鄙薄之極,愛之者則頂禮膜拜。比如前哈佛大學著名教授桑塔亞那認為,尼采是“富于天才的愚蠢”;英國學者羅素則公開表示,希望尼采的影響能夠“迅速地趨于終了”。在他看來,這位不走運的德國教授算不上是一位真正的哲學家,因為“他在本體論或認識論方面沒創造任何新的專門理論”。[2](第25章)丹麥著名文學史家勃蘭兌斯雖然在尼采生前就對他給予了重視,但也只是說:“關于尼采,我寫下的第一行文字就是,他是值得研究和爭論的。”[3](P.127)謹慎之心顯而易見。意大利人克羅齊的《美學的歷史》中,雖然有關于尼采是那個階段最后和最光輝也最值得尊敬的代表等表述,卻以極少的篇幅對尼采的成名作《悲劇的誕生》,給予了“從未真正地提出過藝術理論”的評價,表現了對尼采美學的不屑。這種現象在尼采生前不勝枚舉,并由此而導致這位不幸的思想天才倍感孤獨。
但在尼采身后,認為他是“后現代思想唯一最重要的影響來源”的評價逐漸升溫。在許多具有反叛精神的讀者眼里,尼采“無疑是自柏拉圖以來最具有顛覆性、最機智的哲學家”。[4](P.445)瑞典戲劇家斯特林堡曾在與別人通信時,一度在其所有的信件末尾都強調“閱讀尼采”,因為他在讀尼采著作時驚訝地發現,尼采所說的許多東西正是他“本來應該寫出來的”。[3](P.185)著名作家托馬斯·曼稱他為人類“思想王國中最無畏的英雄之一”,比喻為“思想舞臺上多愁善感的丹麥王子”。[5](P.313)甚至有人以夸張的口吻表示:“無政府主義者,納粹分子,弗洛伊德主義者,存在主義者,后現代主義者,新異教徒,越軌的理發師,足球運動員,女權主義者,厭女者,甚至哲學家,都陶醉在尼采最著名的書《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興奮中。”[6](P.59)但盡管如此,尼采一直難以從哲學家俱樂部中贏得普遍的尊重。尤其是對于習慣性喜新厭舊的當下中國知識人,所熱衷的仍然是一度倍受青睞的諸如“塞爾”、“格爾”、“默爾”等輩。原因其實并不復雜:用林語堂的話講,通常意義上的那些自稱為哲學家的人,他們“所最不愿承認的一樁最明顯的事實,就是我們有一個身體”。[7](P.22)而眾所周知,在西方哲學史上率先承認身體的重要性,正是尼采思想的重要特點。
因此,如同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那位孩子,在其作品里明確將真正的哲人與單純的孩子相提并論的尼采,撕掉了長期以來養尊處優卻無所事事的哲學家的虛假的面具。在西方思想史中,古往今來哲學家們普遍被作為一名“愛智者”看待,但是尼采卻要追究:“我們今天所謂的‘哲學’真的是對智慧的熱愛嗎?”[8](P.135)他提醒我們:長期以來,雖然哲學家一直以對真理之愛為借口贏得人們的敬佩,但是這種真理卻無關現實中他人的痛癢;雖然哲學家原本的使命是為人類尋找新生活的可能性開道,但是:從蘇格拉底學派到黑格爾主義者的哲學史就是漫長的人的服從史,就是為了讓屈辱服從合法化而尋求理由的歷史。盡管尼采的這些話如同他所有的結論,都能讓人吹毛求疵,但它發人深省。
就像尼采一樣,時至今日這樣的困惑越來越大:“我們在哲學的門人即那些有學識的人中看到了多少哲學的影子?”哲學的衰落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為如今“哲學已經變成了一種可笑的東西,其實它應該是可怕的”。因為哲學家們已經成了對于任何時代都毫無意義的人群,于是“我們必須對他們大喝一聲:‘救人者先救己’”。[8](PP.145-146)對于那些自以為是的現代知識分子,尼采的輕蔑溢于言表:“無學問的下層階級現在是我們的唯一希望。有學問、有教養的階級,以及只理解這個階級并且自己就屬于這個階級成員的教士們,必須一掃而光。”*轉引自劉小楓《尼采的微言大義》,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道風》系列第13期《尼采與神學》,2000年,第59頁。但無論如何在某種意義上,羅素的這番評價還是符合事實的:“尼采向來雖然沒有在專門哲學家中間,卻在有文學和藝術修養的人們中間起了很大影響。”[2](第25章)尤其是上世紀以來,隨著尼采思想的通俗化,一種“把尼采的文本理解為詩而不是哲學”[9](P.9)的傾向越來越突出。這有意無意地與以往那種對作為偉大思想家的尼采的忽視,有著異曲同工之效。因為,就像杰出的丹麥學者約爾根·哈斯所指出的:當那些自視為“更具專業意識”的哲學家們不約而同地將尼采命名為“詩人哲學家”時,這個命名事實上屬于一種貶義詞。[9](P.12)換言之,這是一個既非詩人又非哲人的雙重冒牌者。
因此,如何真正認識這位命運坎坷的思想家?這依然是個問題。誠如有學者所言:說到尼采的形象和作品,今天與20世紀初一樣,充斥著支離破碎、矛盾百出的各種判斷和觀點。[10](P.2)這使得我們“重申尼采”的論題不僅具有迫切的當代意義,同樣也面臨著艱巨的挑戰。當然,這樣的狀況事出有因。據說尼采的著名女友露·馮·莎樂美曾表示:人們不應當逐字逐句地從字面上來理解他。但問題正在于,對每位試圖真實地詮釋尼采思想者而言,最大的困境莫過于,他們難以確定什么時候應當從字面上來理解尼采,而什么時候這位文體大師是在做反諷的表達。[9](P.14)而從思想史看,尼采的言說之所以顯得如此這般其實并不稀罕。法國當代哲學家德勒茲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暫且擱置關于尼采的總體評價,超越以往的糾纏。他認為,閱讀尼采首先必須避免如下四個可能的誤解:(一)關于“權力意志”,即以為它意味著“支配欲”和“渴望權力”;(二)關于強者和弱者,膚淺地把尼采的“超人思想”定性為對弱者的排斥;(三)關于“永遠回歸”,即相信它與循環或“同一”的回歸、向自身的回歸有關;(四)關于后期著作的價值,認為它們已經由于作者的精神失常而沒有意義。[1](P.66)
這些見解固然言之有理,但對于“同尼采思想對話”而言,顯得遠遠不夠。并不夸張地說,尼采是思想史上最委屈、因而也最值得人們給予真誠同情的偉人。比如,因為背負“納粹的教父”之名,這位逝世于瘋人院的學者常被與生前死后都風光無限的海德格爾的命運相提并論,這本身就是對尼采的極大侮辱。無須諱言,海德格爾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動上顯示了他對納粹主義的親密性;而相反,大量事實確鑿的證據表明,親自導演出“超人即希特勒”這個幻相的,是在尼采逝世后肆意篡改其兄長著作的尼采之妹和她的表現出強烈反猶太立場的丈夫。
這提醒我們,對待尼采美學,最忌諱的是帶著偏見的批判,最需要的是擱置成見的理解。因為尼采以其畢生的經歷向世界證明,“他是個充滿英雄氣概,擺脫自憐自怨的人”,[6](P.81)值得我們給予一份崇高的敬意。尤其是當你聽到他如此這般地一再叮囑:“真誠對待塵世,不要相信那些對你說更美好地方的人。這些人悲觀厭世,縮頭縮腦,自暴自棄,塵世討厭他們。”除非那些沒心沒肺的行尸走肉之徒,你很難不被這番洞明世事的高見感動。尤其要特別強調的是,這位思想家對現代美學做出了無可比擬的巨大貢獻。因此,步入尼采美學之門時,有一個問題首先必須予以考慮:尼采思想何以如此易遭誤讀、能被一些別有用心者故意曲解?我認為值得注意的,主要有以下三點。
癥結之一是,在思想的高密度運轉中,他的自相矛盾甚至偏執過激之處無疑比比皆是,就像著名小說家托馬斯·曼所說:“尼采一生不懈地詛咒‘理論人’,但他自己正是這種理論人,而且是杰出的、純種的理論人。”[11]同時,尼采的有些話確實存在讓人詬病之處。比如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尼采借這位波斯先知之口說:只要你把自我宣布為是神圣的崇高的東西,那你就該公開宣布,利己、放縱和權欲是人的真正的道德。諸如此類的言辭很難不讓人產生否定性的解讀。但真正重要的是,尼采的理論寫作與他所批判的理論體系大相徑庭;在尼采式的偏激之辭中,到處可見一種摧枯拉朽的深刻。“在種種被駁倒的體系中,恰好只有個性的東西能夠吸引我們,那是永遠不可駁倒的東西。”尼采在其《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一書序言里的這段話,同樣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用到他自己身上。我們的確能夠說,“重讀他的作品讓人感到這照人的光彩中有某種東西是來自夸張”;甚至也可以不無苛求地承認,“他那些半生不熟的真理沒能成熟為真正的智慧”。[12](P.449)但這都不能抹殺尼采思想非同尋常的意義:無論那些貌似公正的人們從尼采的話語里挑出多少毛病,時至今日,思想史早已做出公正裁決:“由于尼采曾經寫作,歐洲哲壇的空氣現在才能這樣潔凈清新。”[12](P.449)
癥結之二是尼采獨一無二的話語方式。尼采的哲學主要采用了兩種手法:箴言和詩。理解尼采不必像理解康德那樣殫精竭慮地與文本斗智斗勇,但需要同他一起作一種精神散步。“我的文體是一種舞蹈藝術”,[13](P.225)尼采的這番自夸有充足的理由,也給了一些人貶低他為文人墨客而非真正的思想家以把柄。尼采明確說過:我不相信并盡量避免一切體系,對體系的追求是缺乏誠實的表現。所以西美爾說過:“純然邏輯上的詮釋對于叔本華是不必要的,相反,對于尼采則是不可能的。”[14](P.1)事實上,尼采的這種獨特文體意在反對邏輯體系對思想的狹隘控制,成功實現了美學的話語方式由自以為是的“言說”向啟發智慧的“談論”轉變。但就像雅斯貝爾斯在《尼采其人其說》中所強調的,要準確理解尼采文體的關鍵在于看到,它既以輕盈的短句同康德以來的體系性美學家分庭抗禮,同時也與通常意義上的那些格言大師們保持著距離。因為透過那些貌似來無蹤去無影的話語碎片,耐心的讀者并不難看到尼采的思想完整性,有著清晰的問題意識的聚焦點。而問題的癥結恰恰在于,評論者有意無意地常常無視雅斯貝爾斯的這番忠告。
癥結之三,是尼采以其別開生面的“戲劇化方法”,使其思想體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豐富性和多元性,以及以一種靈活的反辯證法的“游戲化”姿態,超越受體系化制約的“辯證法”的復雜性。這種姿態有時候甚至會以一種走向極端主義陷阱的方式,展示其獨樹一幟的魅力。比如他對“為藝術而藝術”論的解釋。在《偶像的黃昏》第81節中,一方面尼采寫道:“反對藝術目的的斗爭就是反對藝術中的道德化傾向、反對把藝術從屬于道德的斗爭。為藝術而藝術意味著:‘讓道德見鬼去吧!’”然而,耐人尋味的是,恰恰在同一本書的同一個段落中,他卻對上述觀點立即做出了“修正”,強調說,即使一個人已經排除了藝術中的道德說教,這也并不意味著藝術是完全無目的、無意義的。在尼采看來,“藝術是對生命的偉大獎勵:(因此)怎么能夠把它說成是無目的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尼采的思想并未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他的結論很明確:“簡而言之,為藝術而藝術——是一條咬住自己尾巴的蛇。”由此可見,那種認為上述言論表現出“尼采在理解藝術上的模棱兩可”[15](P.102)的說法,是十分膚淺和片面的。
因此,理解尼采同時也就意味著“為尼采一辯”,其關鍵在于超越人們習慣性的“非此即彼”的二元選擇,而接受“亦此亦彼”的辯證思維。在此同樣有三個問題必須面對。第一個問題:尼采是個徹頭徹尾的反理性主義者嗎?第二個問題:尼采真的是現代西方虛無主義思想的代表嗎?第三個問題:尼采對于美學史的無可取代的貢獻究竟何在?換句話說,尼采究竟憑什么,有資格被視為實現了美學的“從古典向現代”轉化的代表人物?只有對這三個問題給予有效解釋,我們才能通過“為尼采一辯”而認識尼采思想的精髓所在。但這種辯護無疑都存在相當的難度。
首先,由于尼采晚年近十年時間不幸處于精神崩潰邊緣,給尼采思想貼上“非理性”的標簽,似乎很容易找到某種依據。但其實經不起認真的推敲。讓人產生這種印象的主要依據,是尼采對知識論的明確反對。狄爾泰曾說過:“尼采明確有力地表述出他否定推論的、邏輯的知識得出的最后結論。”[16](P.131)這并不錯,問題在于不能斷章取義地予以解釋。尼采的確寫道:“知識為人類展示了一條美妙的窮途末路”,因而“不加選擇的知識沖動,正如不分對象的性沖動,都是下流的標志”。在尼采看來,對知識貪得無厭的結果是荒涼與丑陋,能有效地扼止這種危險的唯一途徑是審美化。為此大聲疾呼:“讓我們滿足于世界的美學觀點!”他強調:“為了反對中世紀,歷史和自然科學曾是必不可少的:知識反對信仰。我們現在用藝術來反對知識:回到生命!控制知識沖動!加強道德和美學本能!”[8](PP.9-66)
尼采反對知識論的意圖,是對根深蒂固的西方理性主義唯智論霸權的抗議。理解尼采美學中的這個“非理性”精神的關鍵,在于意識到他的目標所向首指自柏拉圖以來的,作為西方理性主義形而上學婢女的認識論美學。在《大希匹阿斯篇》中,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提出,在初級階段,“美就是經視覺和聽覺感官而產生的愉悅”。這個思想在13世紀經院哲學代表托馬斯那里,正式形成為一個關于美的定義:美的事物是一種在人們看見它時能給人以快樂的事物。“凡是一眼見到就使人產生愉快的東西才叫作美的。”[17](P.131)美學史上曾有人給托馬斯這個界定以高度評價:“圣托馬斯的定義雖然簡單,卻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18](P.301)因為這個定義盡管沒有否定“美本身”的客觀實在性,卻多少已在關于“美的理念”的思考之外,提出了屬于主體感官方面的“美感”問題,由此使得向來高高在上的美的理念下降到了具體的感性世界。不過盡管如此,托馬斯的這個定義屬于“離經”而不“叛道”之舉,強調視聽之美的思想仍然沿著認識論的軌道前進。這在尼采看來是不夠的。
眾所周知,笛卡爾懷疑一切,只是不懷疑理性本身。這不僅使得他的懷疑不夠徹底,而且導致了理性至上的傲慢與偏見,最終成為自身的掘墓者。所以海德格爾寫道:“唯當我們已經體會到,千百年來被人們頌揚不絕的理性乃是思想的最頑固的敵人,這時候思想才能起程。”[19]而這顯然是許多以尼采思想的繼承者自居的人所缺乏的,事情正是這樣:恰恰是“尼采的一些繼承者成了他所輕蔑的那種人”。[4](P.459)因為與那些打著尼采的旗幟、以非理性自居的反現代主義者不同,在尼采的非理性里其實并不缺乏理性,他只是將理性歸還給人的最為基本的生存性活動:生命意識。由此而進,尼采創立了一種新型的“生命認識論”:即從生命的感性基礎出發,以具體的生命行為作為認識機制、對生命內在需求、目的、意義等做出把握。在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那里,這個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別爾嘉耶夫指出,從柏拉圖到康德,傳統哲學都始于主體、始于思維、始于某種無生命的形式和空洞的東西。但是,為什么不能從諸如血液循環、不從活物、不從先于一切理性反思和理性分離的東西,不從作為生命職能的思維,總之,“不從非理性化意識的直接原始材料開始進行呢?”[20](P.97)
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問題。我們都意識到思維是一種觀念活動,卻未能看到它本身歸根結底乃是一種生命現象,歸屬于生命自身的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應該把笛卡爾當年“我思故我在”的結論作個顛倒:我在故我思。因為無論如何“我們的認識與我們血肉相關”。[20](P.100)在尼采看來,這種認識的實質在于:“為了認識那永恒的生生不息的喜悅本身。”[21](P.188)所以,尼采的生命認識論歸根到底也就是審美認識論,這種審美的生命認識(體驗)論的目標所向,只能是人類自身的存在奧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雅斯貝爾斯指出:把尼采思想貼上一個“非理性”的標簽,這是荒謬的。因為尼采對“理性”發動的攻擊,是大理性對小理性的攻擊,后者即所謂的無所不知的理智。這個“大理性”不同于通常認為的那種作為思維運動的意識,而是包含在“軀體”之中的通感。[22](P.231)換句話說,尼采所希望的,是以作為人文主義價值理性的、孕育于心靈深處的智慧,來反對作為科學主義工具理性的、來自于大腦活動的知識。正如雅斯貝爾斯所強調的,唯其如此,尼采針對敵視理性的人,為理性作了強有力的辯護:“唯一的幸福存在于理性之中,其他的一切都是無聊的。我在藝術家的杰作中看出了最高的理性。”[22](P.231)
二
但無可諱言的是,為尼采的理性立場辯護有個無法回避的問題:他以“酒神精神”為審美文化定位。尼采美學的核心思想之一,是他在《悲劇的誕生》中用“日神”與“酒神”這對范疇,來對人類藝術活動的精神實質作出的概括:“藝術的持續發展是同日神和酒神的二元性密切相關的。”他曾分別以“夢”與“醉”來概括這兩種精神的實質,并以“史詩”與“音樂”兩種藝術形態作為它們各自的地盤。用他的話說,“日神是美化個體化原理的守護神,唯有通過它才能真正在外觀中獲得解脫;相反,在酒神神秘的歡呼下,個體化的魅力煙消云散,通向存在之母、萬物核心的道路敞開了”。顯然,尼采的這對范疇體現了詩性文化中“靜”與“動”、理智與情感、個體性與普遍性的張力:“夢釋放視覺、聯想、詩意的強力,醉釋放姿態、激情、歌詠、舞蹈的強力。”因此他認為:“無論日神藝術還是酒神藝術,都在日神和酒神的兄弟聯盟中達到了自己的最高目的。”它在藝術上的成功表現,就是誕生于雅典阿提卡半島的古希臘悲劇“這種既是酒神的又是日神的藝術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基礎上尼采進一步指出:在藝術活動中“日神不能離開酒神而生存”。其意思再清楚不過:“在這里,酒神因素比之日神因素顯示為永恒的本原的藝術力量。”所以歸根到底,尼采將“藝術創造狀態”的實質歸之為一種“醉境”,強調“為了藝術得以存在,為了任何一種審美行為或審美直觀得以存在,一種心理前提不可或缺:醉”;與此同時,“日神的和酒神的,二者被理解為醉的類別”,因為“醉的本質是力的提高和充溢之感”,是在希臘人那里完好無損的人類“生命意志”的充分表達。這里的關鍵在于要意識到,“在酒神的希臘人同酒神的野蠻人之間隔著一條鴻溝”。在尼采看來,只有在希臘人那里,酒神才“作為充盈滿溢的生命與活力”,成為真正的藝術動力:“在酒神的魔力之下,不但人與人重新團結了,而且疏遠、敵對、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慶祝她同她的浪子人類的和解的節日。”所以尼采表示:“求生的意志,通過其最高類型的犧牲,為自己的不可窮竭而歡呼——這就是我名之為酒神精神的東西。”[21](P.188)
必須承認,尼采的這個發現意義重大:酒神精神對于審美文化具有舉足輕重的價值。但與此同時癥結也在于:這種價值具有正與負、積極與消極、肯定與否定等兩面性。概括地說,酒神精神既創造了充滿浪漫情懷的優秀杰作,和體現崇高之美的藝術之巔,也產生了諸如“暴力美學”、“縱欲美學”、“邪惡美學”等,注定與審美現象形影相隨的對美的否定的東西。所以,從酒神精神中誕生的“生命美學”最終為一種“困惑詩學”(poetics of perplexity)所接管。困惑的根源一言以蔽之:酒神精神的最終結晶,就是表現為“節日中的節日”的“狂歡美學”。俄羅斯人巴赫金是這種美學之父,按照他的解釋,狂歡化現象自發地觴濫于民間廣場,其核心是一種來自于“狂歡意識”的“狂歡化激情”,這種激情要求“完全擺脫哥特式的嚴肅性”[23](P.320)。這意味著對常規秩序的破壞、對固有等級的顛倒、對日常肯定之事的否定,具有寓否定/肯定于一體的“正反同體”性。在巴赫金看來,狂歡文化的這種特性,可以讓自下而上的民間力量推翻傳統專制政治,從而為重建民主社會帶來一縷希望的曙光。
但事實證明,這只是書齋生物們總是重復犯下的又一樁一廂情愿的謬誤。首先在于,狂歡文化的所謂“正反同體”性,其實意味著價值上的積極/消極的“正負同構”性。不僅如此,實踐表明,這種價值復雜性的“正面取向”通常只存在于理論的論證,不具有現實性。實際發生的狂歡文化大多呈現為消極與負面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狂歡文化并非自下而上體現民意,常常是自上而下地被官方所控制;其二,狂歡化的核心并不只是一般意義上受理智支配的反抗,而是完全擺脫理性控制、因而總是走向極端性的破壞和毀滅,因為這種精神的心理起點是仇恨與否定。因此,盡管狂歡美學以誘人的“歡”發起,卻最終走向極度之“悲”的結局,難免“瘋狂”的命運。
美國學者帕特里奇曾以希臘-羅馬兩個社會為代表,對狂歡文化的這種可怕的兩重性進行區分,他以希臘人的成功在于其控制了狂歡,而羅馬人的失敗則在于其被狂歡所控制的史實為例,指出了“狂歡的作用和它墮落的危險相互并存”[24](P.30)這個事實。比如公元62年2月,在古羅馬皇帝尼祿舉行的“祭神狂歡”儀式中,人們以神的名義濫殺無辜和進行性虐待,讓元老院的夫人們目睹她們的丈夫們紛紛被殺。[25](P.117)正如《狂歡史》中所指出的,對流行于公元前200年的“巴克科斯狂歡節”實施取締有充分的合理性,因為這一節日不僅形成了一個反政府團體,而且也導致參與者失去自我、滋生罪孽。著名心理學家弗洛姆從深層心理學入手指出,狂歡狀態是人出于最高形式的自我肯定需要的產物,往往借助于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比如一些“宗教儀式中的狂歡舞蹈,服用藥品,狂亂性行為,或自行引發的催眠狀態都可以達到這種狂歡”。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儀式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跟侵犯現象有關”。除了那些出于生命的歡欣鼓舞的狂歡化外,在更多情況下“狂歡狀態是以恨與破壞性為經驗的中心”[26](P.340)。
無須贅言,這種現象同樣也是民間狂歡文化的基本組成部分。因為狂歡化的實質是欲望的放縱,這在今天的巴西狂歡節日上仍然清楚可見。俄羅斯思想家別爾嘉耶夫說得好:“在狄奧尼索斯的狂歡中人將消失,個性將消融。狄奧尼索斯的神秘主義具有不是神人的特征,而是神獸的特征,人走向獸性。”總之,“狄奧尼索斯既可以使我們成為天使,也可以使我們成為野獸。”[27](P.186)有必要補充的是,這決非名副其實的希臘精神,真正的希臘精神是“把狄奧尼索斯與阿波羅結合起來”。[28](P.159)正是出于這種認識,符號論思想家卡西爾強調,在藝術中并不是單純由酒神力量來一統天下,而是“酒神的力量得到日神力量的平衡,這種基本的傾向才是每一件偉大藝術品的本質”。[29](P.207)不難看到,如同江湖大盜在民間傳說中被塑造成了武林俠客,對狂歡美學的簡單肯定,是唯智論知識分子閉門造車的結果,事實上已成為20世紀以降“暴力美學”泛濫的重要原因。
現在的問題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能否以及如何為倡導酒神精神的尼采美學進行辯護?只要尊重事實,事情也就顯得簡單。在某種意義上,卡西爾的這番精辟之見恰恰是尼采思想的傳承。西美爾在將尼采與叔本華相提并論時,曾這樣評價尼采:“他總是自稱為非道德主義者,但他的思想比叔本華的思想更加具有倫理傾向。”[14](P.184)這句精辟之見同樣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認識尼采的“非理性美學”。事實上,人們在眾口一詞地強調尼采的酒神精神時,常常忽略了一點:尼采雖以酒神來為藝術精神命名,但從未單一地讓其主宰藝術精神,相反卻一再強調它必須與日神結盟。在《悲劇的誕生》中,他不僅明確表示“悲劇神話只能理解為酒神智慧借日神藝術手段而達到的形象化”,而且也強調了“日神因素以形象、概念、倫理教訓、同情心的激發等巨大能量,把人從儀式縱欲的自我毀滅中拔出”。[30](PP.93-97)這句話足以說明問題的實質。
其次,尼采對現代西方虛無主義的崛起的確產生過影響。他不僅明確說過:“我描寫的,是將要到來、必然產生的現象:虛無主義的興起”,而且承認自己是“歐洲第一位徹頭徹尾的虛無主義者”。但準確理解這些話的意思,就要記住尼采表達思想時一貫的戲劇化展開方式。比如在這句以“虛無主義”自稱的名言下面,緊接著他表示:“但是,(我)同時又已經在自己身上將虛無主義推進了墳墓。”[31](P.278)問題顯然并不出在尼采身上,而是出于世人由于普遍熱衷于旁門左道,而習慣于“妖魔化”對象。在把尼采的第一句話夸張地宣布于天下的同時,有意無意地“遺漏”了后面這句。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應該像解讀休謨的懷疑主義那樣,來解讀尼采的虛無主義。用尼采自己的話說,這就是“為人類最深刻的自我反省做準備”。通過虛無主義視野,對以往一直貌似神圣的荒謬之物給予徹底批判。它仍然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打碎傳統那種對真理的頂禮膜拜。在尼采所處的啟蒙時代,這個真理已由神權政治轉移到了科學技術的手中。這種時代潮流不僅一如既往地把真理絕對化,而且因為貼上了理性標簽更不容置疑。對此尼采強調:每個自以為認識了真理的觀點必然是錯誤的。在此意義上,虛無主義首先意味著真理的破滅。但顯然,這并非是對真理的徹底否定,而只是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從虛幻的“大真理”中拯救實在的“小真理”。第二,揭露傳統以來的那種道貌岸然的道德說教的虛偽。尼采意識到,長久以來,道德宣傳一直存在著“準則”與“行動”的脫離。這個事實說明了這種作為說教的道德的欺騙性。所以,同對真理的否定一樣,尼采以“重估一切價值”這句名言,宣告推翻一切道德說教的目的恰恰體現了道德本身的要求。用他的話說:“道德應該自殺,這是唯一一項合乎道義要求的要求。”第三,作為以上兩項批判結果的延伸,對統治西方思想幾千年的宗教權威的顛覆。在某種意義上,尼采所謂“上帝死了”的宣告本身就意味著虛無主義的出場,但他卻明確指出,謀殺上帝的兇手就是“你們和我,我們大家”。他稱之為人類前所未有的一次壯舉,因為這是必須做的,“為了對得起這件事,我們自己應該成為上帝。”[31](P.279)
三
由此可見,對尼采的“虛無主義”決不能以“望文生義”的方式去解釋。它屬于尼采式的表達。正是通過這個主張,尼采從中不僅提出了“人們是否將永遠停留在虛無主義之中”這個尖銳問題,而且明確給出了一個很好的方案:我們別無選擇,必須對生活采取積極的態度,也就意味著必須對生活的意義給予堅決的肯定。所謂“虛無”也即無意義,是對存在意義的否定。因此,任何想要對意義重新予以肯定的邏輯前提,首先要給予這種以“虛無”命名的無意義的存在。所謂積極的生活態度,也就是“在無意義中頑強地堅持創造意義”。這也正是尼采思想中隨之而來的對“超人”的呼喚。因為不再有救世主,“位于我們之上的,不再是上帝,也不是任何人”。實際上,尼采把個體的人變成了上帝。在這個意義上,尼采筆下的“超人”,可以界定為“敢于努力超越自我的人”。[32](P.265)
在尼采看來,“始而往復,永恒循環”就是塵世生活的實質,也是虛無主義的極端表現形式。但沒有關系,這同時也是人的創造歷史的機會,只要人類意識到自身擔負的責任并付諸實施,人還是能夠從虛無主義的循環中走出來。這是尼采同叔本華的根本差異。還值得一提的是,尼采關于“虛無主義”的論述,在深層次上也是對前蘇格拉底時代思想的回應。比如巴門尼德的名言:“存在存在著。”在看似玩弄詞藻的后面,蘊涵豐富的含義:強調“存在”這個概念的意思是指,具體的事物消亡在虛無之中后,依然存在著的東西。這僅僅只是對存在之物的單維的肯定,完全遮蔽了虛無與存在間無法切割的關系。因此就不可能真正徹底地澄清存在的意義問題。這是尼采勇敢地將虛無主義提上哲學議事日程的用心所在。
對尼采而言,獲得自由的精神懷著一種高興的樂觀和一種不再陌生的宿命主義態度位于宇宙之中,堅信消亡的只是單一的存在,但在整體上,所有的存在都是在消亡中得到了肯定。[31](P.281)從這點來講,無論是“非理性”還是“虛無主義”,對尼采思想的這些指控都不能成立。由此而進我們也就不難看到,理解尼采美學的關鍵,并不在于為他的以“非理性”姿態呈現的“大理性”精神辯護,也不是對他的蘊涵“否定之否定”的虛無主義精神實質的意義的澄清,而是如何認識他對現代美學的重要貢獻。這是我們對作為一位具有劃時代價值的美學家的尼采的關注焦點。眾所周知,西方思想自源頭起所做的,就是對“存在為何”的追問。恰恰是這個追究,引出了“虛無為何”的問題。換言之,正是“存在”這個詞提出了“虛無”,把它作為自己的構成物。這意味著只有一個選擇:“為了能夠思考存在必須同時思考虛無,否則‘存在’這個詞就沒有意義。”[33](P.146)
再則:尼采對現代美學的最大貢獻,概括而言就是作為以身體為基礎、強調主體生命力的“審美人類學”的創始者。“美學的價值判斷必須在肉體的本能欲望當中重新發現其真正的基礎”,[34](P.253)時至今日,這樣的說法早已缺乏新意。但它在誕生之際卻意味著一場美學革命。當然,尼采的思想并非沒有對前人的繼承。事實上,尼采在將康德“以個體為本”的哲學人類學與叔本華注重肉身性的生命意志說相融合的基礎上,在《悲劇的誕生》中提出了他的“人類學美學”宣言:“沒有什么東西是美的,只有人是美的:在這一簡單的真理之上建立了一切美學,它是美學的第一原理。”這一學說的思想基礎是生命體驗,用尼采的話說:“美在什么地方?在我必須以全意志去意欲的地方;在我愿意愛和死、使意象不再是意象的地方。”[35](P.229)在此,尼采既通過對生命欲望的充分肯定而體現了對康德“無利害美學”觀的否定,也通過對“生命的莊嚴感”的強烈表現,呈現出同叔本華去欲論美學的深刻分歧。
這種美學的基礎,就在于尼采的生存論哲學觀。海德格爾認為,雖然尼采“正式”開始了以“生存論”來取代形而上學的思想轉型,但“尼采從來沒有做生存論的哲學思考,而是做了形而上學的思考”。[19]這番結論并不公正,因為海德格爾的意圖是,把生存論開創者這個榮譽位置留給自己。考察尼采思想便不難發現,其全部學說的實質也就是使生命高揚。“使生命高揚的哲學堅決地堅持兩件事情:一方面它拒絕作為普遍原則的機械學,另一方面它拒絕把形而上學奉為獨立的東西和首要的觀念。”[36]但“生命”概念本身仍具有一定的曖昧性,尼采的界定很明確:以活生生的肉體為基礎的、以生理性存在為前提的感性活動。如同伊格爾頓所說:“人體對尼采意味著所有文化的根基”,對于尼采,“正是肉體而不是精神在詮釋著這個世界”。[34](PP.226-227)在這樣的“生命”內涵中,作為人文思想家的尼采和美學家的尼采再度合二為一。他明確表示:“‘全部美學的基礎’是這個‘一般原理’:審美價值立足于生物學價值,審美滿足即生物學的滿足”,“審美狀態僅僅出現在那些能使肉體的活力橫溢的天性之中,永遠是在肉體的活力里面。”[35](P.146)
換句話說,與從柏拉圖到康德的理性主義美學相反,尼采強調“美屬于有用、有益、提高生命等生物學價值的一般范疇之列”。為了予以強調,尼采甚至進一步提出:“動物性的快感和欲望的這些極其精妙的細微差別的混合就是審美狀態”,“每種完滿,事物的完整的美,接觸之下都會重新喚起性欲亢奮的極樂。對藝術和美的渴望是對性欲癲狂的間接渴望,它把這種快感傳達給大腦。”[30](PP.348-354)對于這點,海德格爾也并不否認。他承認:“當尼采談論生理學的時候,盡管他強調的是肉體狀態,但肉體狀態在自身中已經總是某種精神的東西,從而也是‘心理學’的東西。”其實尼采曾明確地說過:“活著的情緒存在,是留在情緒中的肉體存在,是交織在肉體存在中的情緒。”*海德格爾《尼采》,轉引自周國平《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9頁。所以,在海德格爾看來,對于尼采,審美狀態是一種不可分割的肉體—精神狀態的整體,因為“尼采反對陰柔之美,他這樣做是為了鼓吹陽剛之美,這就是他所主張的美學”。*海德格爾《尼采》,轉引自伊格爾頓《美學意識形態》,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46頁。這個見解值得我們重視。但同樣需要予以補充的是,這種“陽剛之美”是一切審美現象的普遍性質:因為在美的感受中,必然蘊涵對形形色色的獨裁專制政治的永不妥協的反抗。
四
由此,我們可以順勢而進地把握“審美人類學”的意義所在。認識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聯系尼采的“超人說”。事實上,尼采的“上帝死了”的斷言只是要求人類承擔起作為“思想者”所應負的責任,從以往那種“等待救世主”的神話里解放出來。公正地講,尼采的“超人”既是一種“高貴的人”,更是一位“詩意的人”。就像法國小說家雨果所說:就開創新的生活方式的意義上來講,“詩人既是人,也是超人”。[37](P.188)換句話說,尼采所呼喚的超人不是指生物學上與現在人類不同的、或者在生理上更加強大的物種,而是在心理上、道德上、美學上更偉大的人。[6](P.59)時至今日來看,這樣的呼喚顯得十分重要。真正的審美者所挑戰的對象,首當其沖的是“集體主義”神話,就像查拉圖斯特拉所說:國家是這樣一種東西,在那里,“所有的慢性自殺都被稱作是生活”。因而,“把為國家服務看作自己的最高職責的人可能實際上并不懂什么是崇高的職責”。[1](P.91)以至于有哲學史家提出:“尼采也許是近代哲學史上最極端的反集體主義者。”[38](第10章)
詩學是探尋人的幸福之路之問,所謂的“審美關懷”最終必須落實于生活世界中的生命個體,否則就不僅是空話,而且是“統治學”的工具。這樣的美學是名副其實的反美學,是借美學的名義對人的奴役。身體解放的真正意義,在于個體精神的自由。這是從“原始的自然人”經過“文化的社會人”之后,最終成為“文明的自然人”的人類夢寐以求的目標。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目標,美學必須擁有體現“倫理正義”的力量,而不能淪為撫慰人心的小夜曲。尼采以畢生之力為此做出了難以估算的貢獻。從這點上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說不是追名逐利的德里達而是為世人所不解的尼采,才是“后現代美學第一人”。因為他首先是誕生于愛琴海的“古典美學的最后代表”。在此意義上我們才能發現,尼采美學的“后現代性”首先體現在方法論上的革故鼎新。這位世人眼里的狂人心中,其實并不乏讓其欽佩的角色,比如俄國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曾在給勃蘭兌斯的信里表示,他尊重所有俄國人的著作,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他視為其思想的“最偉大的泉源之一”。也是在給勃蘭兌斯的信里,尼采寫過一句話耐人尋味:“對我們哲學家來說,最大的樂事莫過于被錯認是藝術家了。”[3](PP.183,168)
怎么理解這句話的微妙性?所謂“錯認”,無疑是強調哲學家與藝術家之間存在本質性的差異。但尼采又樂觀其事,這是因為從那些循規蹈矩的平庸哲學家那里,尼采意識到自己所慘淡經營的方法終于獲得了成功,因為“他將哲學變成一門藝術,一門詮釋和評價的藝術”。這種藝術的特點就在于,它是讓否定性成為肯定的否定性的“反辯證法”。[39](P.286)通過這種方式,尼采在很大程度上成功解決了從理論主義僵尸中拯救理性的難題。德國思想家施勒格爾說得好:“對于精神,有體系與沒有體系同樣是致命的。”[40](P.53)如果說過于周密的體系往往產生思想僵尸,那么絕對無體系的言說容易導致邏輯的混亂,從而走向信口開河的主觀隨意性。尼采式文體的意義就在于超越這種陷阱。他的這種方式不是徹底放逐真理,恰恰相反是迎接真理。用雅斯貝爾斯的話說,尼采渴求“可以隨之翩翩起舞的真理”。[22](P.236)因為只有這樣的真理而不是不茍言笑的假正經,才是人類真正需要的思想。懂得舞蹈無需等到故事的結尾,卻需要仔細辨析其“微言大義”,因為每個步態里都蘊含著意義。
尼采美學的后現代性,其次也體現于由他所推波助瀾的“輕盈詩學”。眾所周知,從社會學視野來看,“后現代”意味著一場由“生產”為中心向“消費”為主導的轉型。伴隨而來的文化范式的改變,就是娛樂活動由過去的邊緣走向中心。在眼球經濟和圖像政治聯袂牟利的消費主義時代,“現代主義的‘嚴肅’讓位于后現代的‘游戲’”。[41](P.171)如果說,在藝術實踐中,對抽象的神的迷戀向具體的形式的喜歡,劃分出了美學的前現代與現代,那么可以說“崇高精神”的興盛與衰落,劃出了現代與后現代的界線。就像法國學者利奧塔指出的:“崇高也許是構成現代性特征的藝術感覺模式……正是在這個名詞的范圍內,美學使其對藝術的批評權有了價值,浪漫主義,也就是現代主義取得了勝利。”[42](PP.103-105)后現代藝術范式的崛起,意味著藝術中的崇高隨著英雄們的消亡而消亡。這既驗證了英國人卡萊爾曾經的預言:“我們對偉大的敬重,一個時代接一個時代地連續在減弱”,[43](P.134)也兌現了利奧塔的發現:“19世紀和20世紀藝術的賭注,是利用崇高美學來使自己成為不確定性的見證者。”[42](P.113)歸根結底,這體現了市場的勝利。因為同娛樂文化相比,“崇高不是一種樂趣,而是一種苦痛的愉悅”。[42](P.139)所以,后現代美學在實質上屬于一種“輕盈美學”,用后現代小說家卡爾維諾的話說:“輕是一種價值而并非缺陷。”[44](P.1)
不得不承認,在某種意義上,這種令人擔憂的后現代美學的源頭,正是把詩人命名為“作為使人生變得輕松的人”[21](P.155)的尼采。他通過對游戲文化的強調而隆重推出了自己的這個詩學主張。雖說這看似與席勒美學存在異曲同工之處,但其實不然。彼此的不同在于:對于席勒,游戲由于承擔著人類解放的責任而具有一種“重”量;而對于尼采,游戲則是作為讓人回到無憂無慮的生命的“本真狀態”的一種童年精神的途徑,而顯得相對的“輕”。但即使在這個方面,同樣也存在著一種“否定性成為肯定的否定性”的尼采式的“反辯證法”。也就是說,準確評價尼采的“輕盈詩學”,我們仍然得看到其與席勒一樣,殊途同歸地通往人性的最終勝利。所以尼采曾特別強調,就像他的非理性乃是恢復理性,他所主張的審美之“輕”并非排斥作為人性內在的神圣性,而是甄別偽神圣。在他看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是輕輕地走的。”[45](P.239)這是一種“舉重若輕”的、負有改變世界的歷史責任感的詩性的勝利。這同以“無痛倫理學”的名義為自戀主義大張旗鼓的后現代的“輕盈美學”貌合神離。
所以對尼采之輕,或許可以用法國學者巴什拉的這番話予以解釋:“為什么心理學家并未考慮建立有關這種輕盈的存在的教育學呢?因此,詩人承擔起教育我們的職責,將輕盈的印象結合到我們生活中,并使常被過分忽略的印象實現。”[46](P.261)但讓人遺憾的是,這個命題再次遭遇尼采式的悲劇命運,被后現代主義者拉大旗作虎皮。所謂的后現代審美體驗受到服從欲望支配的消費主義文化邏輯的排斥,于是,“崇高之后”的藝術悖論是,藝術轉向了一種不轉向精神的產物。[42](P.156)但這種狀況決非時間上的后現代的產物。它其實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表現為古典趣味主義與現代審美主義。美學范疇的“趣味主義”,就是“一時之性與一念之意”主義,它滿足于營造講究心智和機巧的趣味迷宮,使人生中那些原本“尖銳的不可調和的痛苦,還有崇高壯美的歡樂,全都溫和化、委婉化、享受化了”。因而指控趣味主義“就像是蛀蟲,蛀空了感情的肌體,使它坍塌下來”,[47](P.23)這無可置疑。
相比之下,審美主義的后果更嚴重。別爾嘉耶夫曾嚴厲地指出,人類不僅會受政治與宗教等的欺騙,同樣也會受美感的誘惑與奴役,這些對象主要是少數的文化精英分子。他認為“只有文化精致了的時代才造就審美型的人”,這或許并不準確,但他強調的這種所謂的審美者“他們并不懷持真正的美感”很深刻。因為“審美型的人是消費者不是創造者”,他們“對革命或反革命的極端形式不加任何區分,會習慣地依附于它們”。他指出,“當人純粹以審美態度觀照生活時,是在主體的之中而不是在客體的之中。”在此意義上“任何偉大的藝術創造者都不是審美者,甚至也很少以極端的審美態度來觀照生活”,因為“美感誘惑使人做旁觀者,不使人做參與者”。[48](P.211)
但在此我們還得為尼采詩學作最后一辯:把這位思想家貼上“審美主義”標簽是一種隨聲附和的平庸之見,因為尼采的全部思想并非讓人做這樣的旁觀者;恰恰相反,而是要我們以一種責無旁貸的勇氣,承擔起歷史的責任。對于尼采,人的命運不是扮演一個被征服者,而是努力成為一個“向著力量、向著美、向著自由和嚴謹的發展理想”前進的超越者。西美爾說得好:叔本華只認識唯一一種絕對價值:否定生命,而尼采同樣也只認識一個價值:肯定生命。[14](P.140)這個評價十分準確。但承認這點也就意味著,尼采思想不僅超越了叔本華,而且為詩學的繼往開來開辟了一條希望之路,因為“超人的所作所為是為了解放和提升生命,而不是踐踏大眾”。[49](P.102)通過“超人”形象提出而發出“重估一切價值”的尼采,就是完成了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倫理美學”的開創者。
參考文獻:
[1][法]吉爾·德勒茲.解讀尼采[M].張喚民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
[2][英]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
[3][丹麥]喬治·勃蘭兌斯.尼采[M].安延明譯.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
[4][美]丹比.偉大的書[M].曹雅學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5]劉小楓.人類困境中的審美精神[M].上海:知識出版社,1994.
[6][英]尼格爾·羅杰斯.行為糟糕的哲學家[M].吳萬偉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7]林語堂.人生不過如此[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8][德]尼采.哲學與真理[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9][丹麥]約爾根·哈斯.幻覺的哲學[M].京不特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
[10][德]維布萊希特·里斯.尼采[M].王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11][德]托馬斯·曼.從我們的體驗看尼采哲學[C]//劉小楓.人類困境中的審美精神.上海:知識出版社,1994.
[12][美]杜蘭特.哲學的故事[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
[13][法]凡尼爾·哈列維.尼采傳[M].談蓓芳譯.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4.
[14][德]格奧爾格·西美爾.叔本華與尼采[M].朱雁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5][德]恩斯特·貝勒爾.尼采、海德格爾與德里達[M].李朝輝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16]劉小楓.詩化哲學[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
[17]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冊[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18][波蘭]塔塔科維茲.中世紀美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19]海德格爾.尼采的話“上帝死了”[M]//孫周興.海德格爾選集:下冊.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
[20][俄]別爾嘉耶夫.自由的哲學[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21][德]尼采.上帝死了——尼采文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
[22][德]卡爾·雅斯貝爾斯.尼采其人其說[M].魯路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23][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M]//巴赫金選集:第5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4][俄]帕高·帕特里奇.狂歡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25][英]阿蘭·德波頓.哲學的慰藉[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26][美]艾利克·弗洛姆.人類的破壞性剖析[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0.
[27][美]邁克爾·波倫.植物的欲望[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3.
[28][俄]別爾嘉耶夫.精神與實在[M].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
[29][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M].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30][德]尼采.悲劇的誕生[M].周國平譯.北京:三聯書店,1986.
[31][德]威廉·魏施德.通往哲學的后樓梯[M].李文潮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32][美]亨利·托馬斯,等.大哲學家的生活[M].武斌譯.北京:書目出版社,1992.
[33][法]弗朗索瓦·夏特萊.理性史[M].冀可平,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34][英]伊格爾頓.美學意識形態[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35]周國平.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6][德]西美爾.現代文化的沖突[C]//劉小楓.人類困境中的審美精神.上海:知識出版社,1994.
[37][法]雨果.雨果論文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38][美]阿金.思想體系的時代[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
[39][法]吉爾·德勒茲.尼采與哲學[M].周穎,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40][德]施勒格爾.雅典娜神殿斷片集[M].北京:三聯書店,1996.
[41][美]斯蒂芬·貝斯特,道格拉斯·科爾納.后現代轉向[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42][法]讓-弗朗索瓦·利奧塔.非人[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43][英]托馬斯·卡萊爾.英雄和英雄崇拜[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8.
[44][意]埃托奧·卡爾維諾.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
[45][匈]阿諾德·豪塞爾.藝術社會學[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7.
[46][法]加斯東·巴什拉.夢想的詩學[M].北京:三聯書店,1996.
[47]王安憶.重建象牙塔[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
[48][俄]別爾嘉耶夫.人的奴役與自由[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
[49][英]凱文·奧頓奈爾.黃昏后的契機[M].王萍麗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責任編輯:吳芳)
The Return of the Giant: A Revisit of Nietzsche’s Poetics
XU Dai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Being a discipline, modern poetics changes “from classical to modern”, in which Nietzsche is the only one who represents the times via his name. 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century, works about Nietzsche exceed other thinkers in great numbers, indicating that Nietzsche, the giant in philosophy, has already returned with his “untimely thoughts”. In a sense, when Nietzsche was regarded as the chief thinker of the Postmodernism, he, in fact, changed from classical “art philosophy” to modern “life poetics”, and thus became the real founder of “poetics revolution”. Owing to this, it is of great necessity for us to revisit Nietzsche’ thoughts on poetics with indiscriminating understanding.
Key words:Nietzsche; giant’s thoughts; ethical poetics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發展研究”(11BS016)的研究成果。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1.005
中圖分類號:I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2338(2015)01-0026-11
作者簡介:徐岱(1957-),男,山東文登人,浙江大學人文學部教授、主任,著有《基礎詩學》《批評美學》《審美正義論》等著作多部,主要從事詩學與美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收稿日期:2014-11-07 2014-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