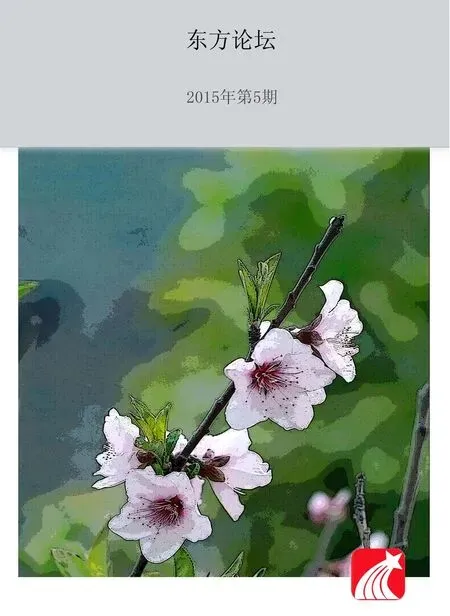啟蒙性·文化性·先鋒性——21世紀山東文學中的鄉土與社會轉型
摘 要:莫言在《紅高粱家族》中通過塑造多種時間形象和空間形象,解構現代歷史主義觀念,建構起一種獨特的現代歷史觀念。在此基礎上,借助以生命為核心和價值評判準則的審美烏托邦,對以啟蒙主義和人道主義為代表的中國現代性話語及其敘事,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表現。莫言的生命主體在與歷史的博弈中,確立和發展自身,并形成了小說的特定美學風格。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7110(2015)05-0070-08
收稿日期: 2015-06-27
作者簡介: 王金勝(1972-),男,山東臨朐人,文學博士,青島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一、多元時間形象與時間線的拆解
敘事需要在時間中展開,因此它是時間的藝術;敘事講述的是時間中的事件,因此它是處理時間的藝術。敘事不僅具有時間的長度和形式,還包含著人對時間的體驗,“敘事給予存在以意義和可掌握的時間形式”。 [1]正如俄國文藝理論家哈利澤夫所說:“文學作品貫穿著時間和空間的觀念,這些觀念無限多樣并且具有深刻意義。” [2](P272)受哈氏啟示,我們可以在《紅高粱家族》中發現多種時間形象。
1.生平時間形象。如“我爺爺”“我奶奶”“二奶奶”“我父親”豆官、羅漢大爺等,尤其是“我爺爺”余占鰲從少年(18歲,殺死與母親私通的和尚)、青年(21歲,參加高密“婚喪服務公司”;23歲,與“我奶奶”相遇;24歲,殺死單廷秀父子;26歲,殺死土匪花脖子)、壯年(1939年,抗日;1941年加入鐵板會,之后整個壯年時期長時間躲藏在日本北海道荒山野嶺)到老年(1976年去世),個人歷史有著較為清晰的時間線索。
2.歷史時間形象。1939年,墨水河伏擊戰;1941年,抗戰進入最殘酷的階段,高密東北鄉在一派安寧中,冷支隊、膠高大隊、鐵板會、日偽軍各派勢力沖突加劇;1958年,大煉鋼鐵、大躍進;“文革”(初起時,紅衛兵到耿十八刀家砸狐仙牌位;1973年,耿十八刀凍餓而死在人民公社門口),“改革開放”(1985年,千人墳被雷劈開,重修墳墓)等等。其中,小說對高密東北鄉的歷史也有所涉及,或者說,歷史時間往往在“高密東北鄉”空間形象中顯影。如,1920年,曹夢九任高密縣長;1925-1928年間,高密東北鄉土匪歷史上的黃金時代;1928年,曹夢九設計剿滅以“我爺爺”為首的高密東北鄉土匪;1938年,日軍屠殺鹽水口子,小姑姑香官死于日本兵刺刀之下,二奶奶被輪奸;1941年,“我奶奶”出大殯,膠高大隊趁機偷襲鐵板會,冷支隊黃雀在后。
3.日歷時間形象。1939年古歷八月十五,中秋節,高密縣城大集,爺爺和父親去縣城購買彈藥;同日,日軍屠殺鄉民;1923年臘月二十三,辭灶,花脖子綁走“我奶奶”;1973年臘月二十三,辭灶,耿十八刀凍餓而死。
4.朝代紀年時間。與其他相比,此類時間在小說中出現較少,如《高梁殯》中“我奶奶”靈位豎書:“大清光緒卅二年五月五日辰時生 中華民國廿八年八月九日午時卒”字樣。這與“生平時間”聯系在一起。
應該說,《家族》通過各類時間的塑形,建構起了較為清晰的時間線和較為明確的時間標識,賦予了紛繁復雜的故事、情節以可把握性,使各類話語在時間形式中具備了連貫性、延續性和直觀性,其意義如利哈喬夫所說:“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隨著世界的可變性這一觀念漸漸地被廣為接受與不斷加深,文學中的時間形象在獲得越來越重要的意義:作家們越來越清晰和緊張地意識到、越來越豐滿地刻畫出‘運動樣式的多樣性’,‘在世界的時間維度中把握世界’。” [2](P272-273)
但是另一方面,小說又有著明確的拆解時間線的意圖和舉措。首先,以分散、跳躍的意識流動來結構小說全篇,各種事件發展的過程、階段被作家近乎無序地組織進文本敘事,人物不同的生活遭遇及命運遭際、生命流程也完全被“敘事”打亂。如莫言在回顧《家族》的敘事結構時所說,“它的故事是切碎了的,把一個故事剁得亂七八糟的,然后分了五骨碌。第一篇講的可能是故事的最后,最后一篇講得是開頭” [3](P189)。這種敘事處置,顯示著現實主義的“故事”被現代主義的“敘事”所取代,屬于先鋒小說形式試驗范疇,但換一個角度看,此舉產生的后果便是,歷時性的時間線被共時性的空間透視所替代。小說中的時間,連同“故事”一起被切割,呈現混沌、無序的狀態。本文開篇所作的“時間形象”分析,實屬對“故事”的帶還原性的重構,是一種解讀的效果而非敘述的原初形態。
其次,對家族性格、生命力頹敗的表現,是拆解敘事時間線的另一手法。小說敘事飽含著對生命力衰頹的批判激情,其中不僅有對先輩的崇仰,對后輩和當下文明狀態的自慚和羞愧,更有著深層的文化意味——這不僅是生命意義的被消解和流失,更是通過生命在不可抗的外力侵蝕下的榮枯興衰而與時間或歷史的自然綿延形成對比和反襯,從而在根本上構成了對時間或歷史的質疑。
時間,對于人和世界及存在于這世界的其他事物而言,并非純然客觀的存在,尤其當以符號的形式出現時,它往往是和歷史的波折動蕩、社會生活的紛繁變遷及人的生活經歷和生命體驗等結合在一起。人對時間的符號化、對時間的劃分、切割,意味著人對時間的規劃和賦值,人對時間的規劃和建制,出發點在于人對自身的理解和規劃,目的在于為自身及與人類建立一個可依托可寄命的框架。因此,作為人存在基本維度的時間,與社會、政治、歷史、文化、哲學、宗教及其變遷等無法脫離,時間的賦形、賦值、建制有著密切而幽微的文化政治和意識形態關聯。如此再看《家族》的時間形象,大體分為兩類:屬于個體時間的“生平時間形象”和屬于公共時間的“歷史時間形象”“日歷時間形象”和“朝代紀年時間”。兩類時間相互交叉、滲透,“我爺爺”“我奶奶”等的個體生命是在與歷史時間和日歷時間的交錯中呈現的,公共時間通過個體生命顯形。如果從時間哲學和時間的歷史特性上看,《家族》的“時間形象”則可分為兩類:傳統時間形象如“日歷時間形象”和“朝代紀年時間形象”;現代時間形象如“歷史時間形象”。在這兩大分類中,又有交差:“歷史時間形象”是西方紀年方式,更隨著率先進入“現代”的西方的殖民擴張,成為世界/全球紀年方式;“日歷時間形象”和“朝代紀年時間”屬于中國傳統紀年方式。綜上而論,《家族》中的各類時間形象內在地形成了如下對子:個體/公共、傳統/現代、中國/西方、區域/世界。“作為深層結構形式,時間不是孤立個人的行為和意識的產物,而是被以生產方式為核心的社會存在(文明)與社會組織化或運動性的宗教—信仰(文化)活動塑造的結果。就此而言,時間的意義先于時間。時間的意義即歷史。” [4]多元混雜的“時間形象”,建立了《家族》獨特的生命—歷史隱喻。
二、多重空間形象與現代時空觀念的建構
時間無可避免地與空間并行同步。時間的存在形態和觀念變遷,系乎空間,于空間中完形。在中國,“家族”既是時間性存在,也是空間性鋪展。但在進入“現代”之后,時間和空間之間的錯位在所難免。作為一個涵納了時間(歷史)和空間的概念,傳統意義上的“家族”在《家族》中是在場的缺席。它的時間(歷史)意義變得匱乏,空間意義得以凸顯。
從生命的內在形態和時間質量上看,小說中“家族”血緣生命綿延的時間性是斷裂、呈不均衡狀態的。祖輩中,“我爺爺”“我奶奶”的生平有較完整的敘述,從《紅高粱》到《奇死》,每章有著相關故事,“二奶奶”故事主要集中在《高梁殯》尤其是《奇死》;父輩中,“我父親”的故事主要分布在前三章,《紅高粱》《狗道》尤其集中,“母親”的故事集中在《狗道》。到孫輩,“我”幾乎無故事可講,雖然“我”在小說中身兼小說人物和敘事者雙重角色,但實際上更多行使敘事功能——只能去講先祖故事,從祖輩獲得啟示,汲取力量。這顯然是以生命力退化來反思現代性時間觀(進化論)。再者,小說也通過將時間線打亂為碎片,淡化、質疑了時間(歷史)。
除了上述兩點,《家族》的獨特時空處理,在小說敘事上亦有獨特美學表征。表征之一,是某些性質相同的事件被劃分成不同的單元在敘事中斷續出現,如“我爺爺”“我奶奶”野合、“我奶奶”之死等。表征之二,是某些意象多次重復出現,如象征生命與野性的紅高粱,象征生命野蠻與蒼涼的狗,象征生命神秘難言的紅狐貍,及頻繁出現的村畔水塘和荷花。古典詩歌中常見的意象,在這篇當代小說中頻繁出現,不僅造成了敘事流程的中斷,削弱了敘事文學的時間性因素,制造出一種空間的永恒感,更顯示著小說的現代主義審美。
在時空觀念上,《家族》作為現代小說卻與古典詩歌有相通相近之處,二者都有時間凝滯、時態淡化的傾向,都跨過時間之流去把握人與天地、宇宙,營造出一個處在往來古今、上下四方中的“人”與天地萬物融合為一的、充滿生命節奏的宇宙。自然,二者的差異更為內在和重要。古典藝術包括詩歌、繪畫、書法、建筑、園林在內,因受到儒家哲學“天地境界”和道家哲學“神游萬物”、佛學“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等傳統觀念影響,其中的時間與空間是水乳交融的。借助對生命的體察、對宇宙萬物流變的感悟,古典藝術傳達出某種永恒性的生命體驗。宗白華認為:“中國古代農人的農舍就是他的世界。他們從屋宇得到空間觀念。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壤歌),由宇中出入而得到時間觀念。空間、時間合成他的宇宙而安頓著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是從容的,是有節奏的。對于他空間與時間是不能分割的。春夏秋冬配合著東南西北。這個意識表現在秦漢的哲學思想里。時間的節奏(一歲十二月二十四節)率領著空間方位(東南西北等)以構成我們的宇宙。所以我們的空間感覺隨著我們的時間感覺而節奏化了、音樂化了!” [5](P106)在中國古典藝術世界中,“時間”統領著“空間”,面對“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時間,古人通過萬物的空間并置,來抵御時間流逝帶來的感傷、悲哀與恐懼,以此對抗時間的流逝。
現代作家莫言反其道而行之,《家族》中“空間”占據主導地位,統馭著“時間”,或者說,“空間”具有了與“時間”同等、乃至于對抗、抵消“時間”的意義。與“時間形象”相對應,《家族》有彼此交匯、交接的三重文學“空間形象”。 通過三重“空間形象”的塑造,小說中“時間對空間的統治所需要的一切”被終結。 [6](P68)一個廣闊而混沌的,新的空間由此誕生并矗立起來。
“空間形象”之一,是地域空間——今人耳熟能詳的“高密東北鄉”。此空間有獨特的聲音、氣味、色彩,有搶食人尸的野狗和被情欲燃燒的青蛙,有敢愛敢恨粗俗野蠻的鄉民,有各種妖魔神仙狐鬼花魅的傳奇和史事先人的傳說……總之,有其獨特的歷史傳統、地理景觀、動物植物、風俗民情。在莫言看來,它是“地球上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也是莫言“極端熱愛”“極端憎恨”之地。 [7](P2)
“空間形象”之二,是祖輩先人的生命空間。作為文學空間的“高密東北鄉”本身就是一個生命空間。小說中的東北鄉是一片偏遠、荒僻、靜寂,歷史和苦難糾纏于此,歷史和苦難同樣久遠的土地,但也是一片深蘊著原始生命強力,雖被歷史風云籠罩卻桀驁不馴的土地,“一隊隊暗紅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網,幾十年如一日。他們殺人越貨,精忠報國,他們演出過一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 [7](P2)。
“空間形象”之三,是看似雜亂無章的敘事空間。《家族》并沒有按照傳統敘事方法,自始至終地遵守自然時序,從家族世代、戰斗始末講述家族史、抗戰史,小說獨出機杼地將一個完整的故事分割為五個故事片段,每個片段有相對的中心,形成一個獨立的故事單元,同時故事之間又有聯系。但是這些獨立而又彼此相連的故事在內容上又不分先后,在前講述的故事,其發生可能在后,發生在中間的故事,可能在此前或此后講述。小說中的時間是混亂、顛倒、交差的。僅就第一章《紅高粱》來看,第一小節開頭是爺爺、父親去橋頭伏擊,接下來是父親在這過程中對和羅漢大爺河邊捉蟹及羅漢大爺被剝皮的回憶,再回到伏擊過程。第二小節主要記述“我”對家族的調查,《縣志》中對羅漢大爺的記錄。第三小節接上節敘述羅漢大爺被抓民夫及鏟傷騾子。第四小節首先回到伏擊現場,再由父親回憶伏擊前夜,余司令和冷支隊長的會面;又回到伏擊現場;再回到羅漢大爺被抓后奶奶和父親的行為;短暫回到伏擊現場后,接著敘述羅漢大爺被剝皮的經過和場景;再回到伏擊現場。第五小節講述奶奶的成長、出嫁的經歷,余占鰲殺死劫道者、逃跑。第六小節先寫父親從伏擊現場回村告訴奶奶給伏擊隊員做飯送飯,接著寫任副官、余大牙。第七小節講述奶奶在送飯路上被日軍子彈擊中,短暫穿插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后回到伏擊現場。第八小節續寫奶奶臨死情境,由奶奶回憶新婚之夜、回娘家、高粱地與爺爺翻云覆雨、這部分有大量奶奶的聯想。第九小節又回到伏擊現場,先寫奶奶之死,接著寫一九七六年爺爺之死和生前狀態,又回到伏擊現場。《紅高粱》中時序顛倒、跳躍、交差,且作者在時間轉換時也未必明確交代,全靠讀者自己去分辨。小說其余章節從《高粱酒》到《奇死》,每章內部、章與章之間、節與節之間也多此類情況。這使閱讀變得困難,但因有爺爺、奶奶、父親、母親生平故事的貫穿,有日軍侵占高密,殘殺百姓的歷史講述和伏擊戰的前后脈絡等等,卻也使讀者在經歷閱讀困難后能把握住小說的基本內容。很重要的一點,是此種講述使得“敘事”較之“故事”占據了小說更顯眼的位置,也使得小說敘事者“我”的形象凸現出來:“我”在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迂回穿梭、“我”對先人心理、行為的推測、分析和評價,……總之,“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對作為“生命空間”的東北鄉民和祖輩先人的生命故事的講述、生命形象的塑造,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此觀之,《家族》的內容可表述為“我”所講述的一個發生在“高密東北鄉”這個地域(其實質為生命灌注的空間)中的先人(其本質為充滿生命力的個體)的生命故事。而據之小說,故事講述者的“我”同樣是一個有著超常的、神秘的感受力的生命存在。
因此,《家族》的三重“空間形象”其實質為同一個“生命形象”。莫言為營造小說三重空間所作的努力,都可視為生命對時間的抵抗,一種對作為肉身生命的死亡的規避和抵抗。“我奶奶”臨死之時的穿越行云的抒情、羅漢大爺的慘死與失蹤,“二奶奶”的死而不僵、戟指怒罵,“我父親”的無字墓碑,阻擋了來自將來時的威脅,而縣志、傳說、民謠,則阻止了來自過去的威脅。藉此,作家讓先輩們生活在開天辟地的現在時。
三、生命主體對啟蒙現代性的反思
《家族》塑造的是一個個體生命感性釋放的空間,是感性生命活化(畫)出的美學壯景,居此空間內核的是一個感性生命主體。這一新的主體,有力地嵌入八十年代特有的宏大的歷史、民族和文化版圖,充分地介入社會生活,同時,它又以非比尋常的個體/生命視角,重新發現曾被壓抑和遮蔽的意義,從個體經驗中獲得對“真實性”“意義”的認知。
逝者已矣,先輩英雄只能存活于久遠的歷史,小說“魂兮歸來”的召喚,起于對當下“活命狀態”的不滿,“歷史是人寫的,英雄是人造的。人對現實不滿時便懷念過去;人對自己不滿時便崇拜祖先。我的小說《紅高粱家族》大概也就是這類東西”,其實,祖先又何嘗都是頂天立地的英雄?“事實上,我們的祖先跟我們差不多,那些昔日的榮耀和輝煌大多是我們的理想。然而這把往昔理想化、把古人傳奇化的傳說,恰是小說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 [8](P17)莫言此言未免讓人失望:先輩英雄竟是一個生命的審美烏托邦!就此,本文對《家族》之“講述生命故事”的設定,究其實質為“營造生命的審美烏托邦”。吊詭的是,作為“生命的審美烏托邦”的《家族》,反倒發散出更重大的歷史—美學力量,正如學者王德威所強調的,“莫言的紙上原鄉原就是敘述的產物,是歷史想象的結晶。與其說他的尋根作品重現某一地理環境下的種種風貌,不如說它們展現又一時空焦點符號,落實歷史辯證的范疇” [9](P14)。
《家族》的歷史—美學力量首先表現于對中國啟蒙現代性及其敘事模式的反思。中國現代性敘事,有著明確的二元對立框架結構:善惡、美丑、野蠻與文明、奴役與自由、束縛與解放、理性與非理性等等。八十年代,整體上占據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核心問題是文化的現代化。古/今、東/西,傳統/現代、愚昧/文明之間存在著必然的無可選擇的沖突,在這二元性結構沖突中,東/西這一地域空間方位或文化形態上的差異,被轉化為古/今的差異,進而在認識論與價值論上被闡釋為野蠻/文明、落后/先進、現代化/傳統之間的本質性區別。啟蒙主義這一“五四”所開啟的思想文化命題必然會被八十年代聚焦,正如學者許紀霖對80年代“文化熱”所作的總結:“八十年代文化熱的核心主題是所謂的中西文化比較,這一比較背后預設著在當時的知識界普遍流行的傳統/現代二元模式: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是二分的,前者代表傳統的價值系統,而后者代表現代的文化價值,從而一個文化的空間并置的關系被轉換成了一種線性的時間敘述。換言之,中國文化的轉型就意味著如何克服古老文化的惰性與弊病,融入世界性的歐美現代文明的浪潮之中。這形成了八十年代中國啟蒙思想的共同預設。” [10](P33-34)啟蒙主義話語是現代化意識形態的表現形式之一,后者是前者形塑的知識型,前者被統攝于后者,并參與了對左傾政治、傳統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的批判,傳達著現代化訴求。“古老文化的惰性與弊病”集中地體現于它所塑造的“國民劣根性”,因此,國民性批判實際上構成了八十年代啟蒙主義文學的一個重要意識或主題。
首先,小說在主題、價值評判上,突破了國民性批判主題,超越國民性話語的二元性框架。從童年到青年的整個階段,莫言掙扎于生活在貧困、偏僻、保守的被中國農村所必須面臨的痛苦經驗和荒誕情境。他對農村社會的現實不抱有任何浪漫的憧憬,也沒有知識者、啟蒙者紆尊降貴的姿態和對故土的懷舊式鄉愁。《家族》開篇就通過充滿矛盾性張力的表述談及離鄉者的“故鄉形象”和原鄉情感:“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我曾經對高密東北鄉極端熱愛,曾經對高密東北鄉極端仇恨” [7](P2)。作者的寫作,亦如在小說扉頁所言,是一個“不肖子孫”“召喚那些游蕩在我的故鄉無邊無際的通紅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作為一部招魂之作,小說寫作出于一種對現代性情境下生命狀態的不滿,“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感到種的退化”。“我”對生命力萎縮的反思、控訴和抗議,更多地是構成了作家訪族尋根的動力,和為家族作傳的目的。這跟啟蒙文學對常人生命狀態的理解和表現有根本差異。作家并未像魯迅對《故鄉》中的閏土一樣,尋找社會的根源;也并未像魯迅那樣,由阿Q的生命萎頓、猥瑣,來深剖國民病根,進而通過嚴厲的自我審判,在生命的創痛中誕生新的現代主體人格。也即在魯迅,雖未曾取消“身體”的肉身存在,但“精神”無疑起著更根本的作用:精神統攝身體和生命,后者構成前者的隱喻,并關聯著社會—政治本體性話語,“如果沒有身體的視野,‘精神勝利法’事實上是無從被診斷為病態的” [11](P71)。
身體的頹敗見證著思想、文化、社會、政治的頹敗。這適合于魯迅也適合于莫言。但莫言與魯迅不同。
差異之一,莫言在《家族》中賦予了個體生命以本體性地位。如果說,在八十年代,啟蒙主義話語連同它作為反思對象的革命話語,將主體完全納入歷史,從而在實質上抽空了感性生命,將主體的生命之輕置換為一種本質意義之重,并從這意義中獲得自身的話,莫言則從切己的體悟中,清理著自我、文學與歷史之根本關系。盡管《家族》通過宏大的時空跨度,書寫人物命運滄桑變幻和歷史風云斗轉星移,但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出于敘事的形式化之需,而不是作家的“史詩化”訴求。小說中也出現了豐富的鄉間民俗景觀,卻也并非眾多“尋根小說”和“史詩小說”中凝重渾厚的文化符號。小說也不以某種文化模式為依據和最終目的,不把個體、生命、欲望置于某種普泛而又僵硬的框架內,從而能穿越先驗性的“文化”建構對“人”的遮蔽,從而還原出一種人的真實處境。如果說,小說中存在著鄉村文化或民間文化,那這文化也不是符號、標簽,它與個體的人、人的生命直接相關,如“紅高粱”和“高粱酒”。在《家族》,“高粱”“酒”是點燃內心解放與革命的物質,更是內心解放和革命的隱喻。小說甚至將剪紙風俗從靜態的文化框架中釋放出來,讓蟈蟈跳出牢籠振翅高歌,讓梅花鹿背上生出紅梅花仰首天地,“我奶奶要是搞了文學這一行,會把一大群文學家踩出屎來。她就是造物主,她就是金口玉牙,她說蟈蟈出籠蟈蟈就出籠,她說鹿背上長樹鹿背上就長樹” [7](P125)。在在皆為個人生命的表達。
差異之二,小說用飽滿淋漓的生命感覺化敘事和自由穿插的意識流動結構,打破線性時間,取代了故事情節結構。“對線性的時間認識是啟蒙主義以歷史、進步、真理為基礎的認識論的一個重要基石”。 [12](P40)莫言在歷史/生命、進步/退化、真理的絕對性/相對性之間,建構了一個論辯性結構。“在過分架空歷史(宿命)意義的環境里,莫言將歷史空間化、局部化的作法,不啻肯定了生命經驗本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莫言敢于運用最結實的文字象征,重新裝飾他所催生的鄉土情境,無疑又開拓了歷史空間無限的奇詭可能”。 [9](P15)誠哉斯言。在小說里,看不到宏大敘事慣有的進步故事,卻頗有舊小說、舊戲曲成分的援引:英雄美人,美女骷髏,以剪紙代女紅抒寫思春女子心曲,曹夢九用鞋底打屁股懲罰欺壓良家婦女者,爺爺苦練“七點梅花槍”,神道設教,異人驅鬼,等等。一方面,小說藉此建構起一種體現民間傳統價值的“知識體系”,另一方面,也許更重要的,通過“舊經驗”在文本中的閃現與浮動,傳達出作家自由的文化想象力。正是這些超出啟蒙理性及其話語規范的、未被“新文化”“新文學”經驗所規訓的東西,構成質詢現代性的異類。
其次,對人道主義及其話語成規的反思。人道主義是啟蒙現代性話語確立自身合法性的重要依據,自我意識、個性解放、個體主義、“自由、民主、平等”是西方啟蒙運動時期人道主義的核心思想,也構成中國自“五四”以來中國啟蒙現代性話語的重要內容。用人道主義話語來詮釋《家族》雖有充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但同時也應對此解讀存在的有限性、甚至對小說思想內質的誤讀,引起充分重視。
事實上,《家族》的精神內質是復雜、混沌的。人道主義話語及其具體存在形式如自我意識、個性解放、戀愛自由等,構成了小說的顯性存在。但生命、本能、欲望等關聯著人的感性形態、生命形態、生命價值而非理性形態、社會形態、社會價值的人本主義,構成了小說易被忽視或誤讀的成分。或者說,我們更傾向于將人本主義納入人道主義話語范疇,按照人道主義話語規則來釋讀人本主義——生命意識。從話語權力角度看,這是溫情人道主義敘事的話語暴力。《家族》的特別之處是,在抒發人道情懷之時對生命意識的傾情。這就使小說具有了對人道主義及其話語成規的反思意義。具體到文本,舉凡高密東北鄉的河流(墨水河)、植物(高粱、梨樹、荷花、狗蛋子草)、牲畜(驢子、騾子、馬)、動物(各色野狗、紅狐、青蛙、云雀)等,不僅是主體活動的背景,也是主體生命精神的外溢與流轉,在文本中,高密東北鄉是天、地、人合為一體、氣脈貫通的世界。它是宇宙的具體而微。當眾多尋根小說在自然、大地、暴力、野蠻等與現代化距離較遠的區域,尋求民族/文化衰頹、生命力敗落的根由時,莫言恰恰在其中尋回了民族、生命力健旺的根脈。《家族》 把強烈的個體自由訴求、生命力贊頌和文明批判,濃縮于一個祖輩高粱地野合的故事(場景)中,用充滿野性、靈性的感覺捕捉生命迸發的瞬間,將之定格、放大,凝結成生命永恒的風景,同時,借助于深具力度的抒情、評論,傳達出巨大的、抽象的,洶涌而來、不可遏止的生命力量。同時,“我”以插科打諢的方式,借助革命氣質的抒寫,顛覆著理性、文明、保守哲學對身心的困縛和奴役。
《家族》在民間生命傳達的意義上,是現代性神話的自我顛覆,它逐步剝離了籠罩在身體、生命、自然場景之上的人文面紗,使其得到還原式呈現,一種讓人觸目驚心的裸呈,羅漢大爺之慘死,母親井底躲避戰禍之骯臟、饑渴與恐懼,小舅舅安子因病渴而死、土匪及各方勢力之間的殘殺、小姑姑之被日本兵殘殺,野狗肆虐爭食尸肉……諸番慘象昭揭著歷史與生命之間的交纏、交鋒,宿命的、也是致命的搏擊和纏斗。《家族》全方位地提供了當代文學中匱乏的異質經驗:“抗戰”歷史的異質經驗、生命的異質經驗、土匪生活的異質經驗、地域風習的異質經驗、敘事的異質經驗,乃至感覺審美的異質經驗……對于這些處于曖昧未明區域的異質性經驗、對于那些無法為現實主義透鏡所細察的異質性經驗,作家也不多做解釋,并不用澄明的理性之光,將其照得如其他經驗般通體透徹,而是把它們的混亂、模糊、支離破碎直接呈現于文本表層,使經驗的異質性得以最大程度地保存。
言說、記錄這些與感性生命密切相關的異質性經驗,講述一個個“生命故事”的,是一個感性生命主體。
四、感性生命主體對歷史的重寫
20世紀80年代,傳統的時間—歷史觀(循環論)和現代的時間—歷史觀(進化論)同時被作為反思的對象。受這種時間觀念變遷的影響,此時誕生的《家族》也表現出特別的歷史意識。不僅在切身的現實中,也在表現這現實和歷史的文學中,作家看到、身受了生命意義在整體性歷史中的流失。于是,在《家族》中出現了整體性歷史意義的流失。在小說文本中,時間—歷史也無法完成對人的歷史化和形式化。換一種說法,《家族》即使有著較為明確的年月日之類的時間,但究其實質,這種時間是虛化的,它可以構成我們了解事件來龍去脈和人物生死情仇的一個個節點,但實際上,小說人物處于時間或歷史長河之外。可以說,小說中的“人”與歷史構成了某種疏離、對抗的關系,“人”超出了歷史本身的價值系統,在價值認同上與后者格格不入。于是,“人”在與歷史的對抗中誕生,而這一新生的“人”,就其本身來看,是一個個始終秉持著自己生命意志的存在,“我爺爺”“我奶奶”“我父親”自不必說,即便羅漢大爺、余大牙、二奶奶等次要人物也是如此。就其在世的具體生命形態和生活關聯而言,《家族》中的各番奪予給取、愛恨情仇,小到“我爺爺”“我奶奶”“二奶奶”之間的爭風吃醋,“我爺爺”“我奶奶”與土匪“花脖子”之間,及“我奶奶”與羅漢大爺之間的曖昧關系,大到國、共、匪、日之間,鐵板會內部“我爺爺”和會長黑眼之間,土匪、“我爺爺”與高密縣長之間的勾心斗角、爭權奪利,既展示出民間藏污納垢的原生形態,又活畫了生命狀態的混沌與復雜。
死亡,如同誕生,是生命的極端形態。《家族》以死亡的形式宣告著生命意志。在小說,死亡并非生命的自然終結,并非時間造成的自然后果,而是歷史對生命的粗暴介入和摧毀。小說中這種歷史的力量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鬼子的殘暴虐殺,另一是以城市為代表的現代文明。前者帶來了死亡、破敗、頹喪。“我奶奶”“二奶奶”、羅漢大爺、小舅舅、小姑姑之死,“父親”身體受到戕殘,“母親”令人恐懼的躲難經歷,被斫殺的鄉人、高粱、莊稼,被焚燒的村莊,不可阻遏的歷史力量終止了生命的歡愉,打破了自然與生命之間的圓融狀態,感性的生命被歷史的長矛刺穿、撕裂。原本在傳統文化想象中的那個生氣灌注、流轉不息的生命世界,那種人、河流、植物、牲畜融為一體的整體生命感,被現代性的歷史徹底打破。
面對歷史暴力,作家并沒有徹底迷醉于高粱如火、生命如血的酒神精神,小說在《紅高粱》《高粱酒》對美好人性的抒情文字之后,自開始《狗道》獲得了更具歷史感和現實感的鄉土、歷史的在世經驗,一種此前莫言小說很少出現的赤裸、粗糲、酷烈的,閃耀著自然主義光澤的筆法,帶出了讓人眩暈、瞠目的,近乎原初的生命形態,裸呈著生命的隱秘褶皺和暗陬。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奇死》以“二奶奶”的奇死,呼應了《紅高粱》中“我奶奶”的奇死。如果說,在“我奶奶”的死亡鏡像中,凸顯的是一個個性主義的浪漫、傳奇女子形象,那么,“二奶奶”則以自己頗有神秘色彩的死亡,執著地傳達著自己內心的聲音。如果說,在“我奶奶”之死中,“我”尚且以頗顯時代精神的各類話語為其命名,那么,“二奶奶”則拒絕了這一命名,以幽靈、鬼魂的方式,將自己沉入神秘、深邃的生命幽暗之地。
莫言小說之獨特性,在于其中的“歷史”并不徹底地凌越了身體與生命,生命的歌唱并未完全融入歷史、時代的大合唱。生命、欲望以其倔強的自主性形象,既關聯著一種“重返五四”式的個性解放話語,又關聯著一種審美主義、自然主義的“純文學”話語。關于前者,小說中的欲望表現,是一種關涉個性主義的社會性/意識形態性敘事;關于后者,它是一種關于個我情感體驗的自由性、審美性言說。從前者而言,它是一種“歷史”的存在;從后者而言,它是一種超歷史的存在。從前者而論,它走的是《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路子;從后者而言,它是《小城之戀》的浪漫化再造。“人”,從小城、從練功房的沉悶、壓抑、逼仄,走向了東北鄉、高粱地的明朗、野性、廣袤。不管怎樣,練功房、高粱地都是人性與赤裸欲望的展示與演練之地。只是,前者,因欲望與天地的溝通,而被認為是天性、是自然,而后者,因被人窺視被人議論,而被視為扭曲,是變態。在王安憶,回歸母性,是善終,是神圣;在莫言,回歸自然,是本真,是至境。
生命的解放,是身體的解放,也是文學的解放。這一新生的感性生命主體,激揚文字,天馬行空,不拘形跡,肆意揮灑出支離破碎、隨意隨機的敘事痕跡。盡管如此,新主體仍然顯示出駕馭時間的主動性和能力,它在時間的演進、曲折、停留、延伸或回旋中,把過去、現在和未來,統合為一種完整、有機的狀態。這體現著莫言對歷史進行重新總體性規劃的努力。這一努力主要是通過把作家本人切身的鄉村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融入一次顛覆性、革命性的書寫實踐之中,拒絕將歷史看作某種具有先在“規律”和“意義”的、穩固的抽象法則的被動、直接的呈現,拒絕使“生命”“人”作為一個被“異己”的抽象體系無條件征用的符號。
《家族》是欲望的一次集中釋放,也是本然生命的一次輝煌綻放。在諸種現代性話語威權征集并占有所有欲望的時代面臨終結之時,小說把被強制征集起來的欲望,放在一個宏大的歷史話語框架中,進行了一次超越理性規范的審美展示,在破解了感性/理性、肉體/精神的二分之后,莫言以唯一的、不可復制的在世肉身,導演了一場壯麗而凄婉、蒼涼卻張揚的舞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