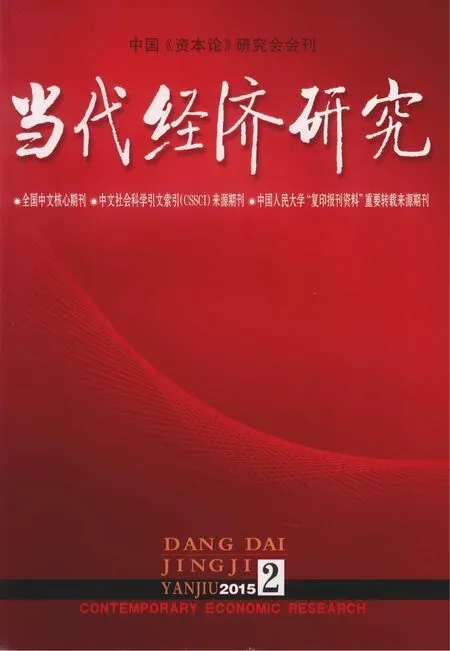論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一種基于利益相關者重新分類的解釋
趙德志
(遼寧大學 商學院,沈陽 110136)
論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
——一種基于利益相關者重新分類的解釋
趙德志
(遼寧大學 商學院,沈陽 110136)
企業究竟應當向誰承擔社會責任?或者說社會責任的對象都有那些?是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和實踐中應該首先厘清的問題。企業社會責任屬于“應然”的范疇,是企業的一種自愿選擇,并不具有強制性;企業社會責任不應包含企業必須承擔的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從利益相關者重新分類的視角分析,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應是那些沒有能力參與橫向締約,與企業主要是社會契約關系的利益相關者。
企業;利益相關者;社會責任對象
一、企業社會責任對象認識的模糊性及其根源
開宗明義。企業社會責任包含著三個基本問題:向誰承擔社會責任、承擔什么樣的社會責任和怎樣承擔社會責任。第一個問題涉及到企業責任的對象,第二問題涉及到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第三個問題涉及到企業社會責任承擔的方式。厘清第一個問題,是搞清楚其他問題的重要前提,因此,更具有關鍵性意義。
然而,就是對這更具關鍵性的第一個問題,學術界討論恰恰比較少,一直比較模糊,其具體表現就是將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籠統地歸結為“社會”。例如,較早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鮑爾(Raymond Bauer)就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關于公司行為對社會影響的認真考慮。”[1]23我們知道,社會構成是極其復雜的,包含著諸多相互聯系和滲透的領域,其基本構成包括人及各類組織,包括各種觀念、制度和習俗,也包括人們賴以生存的環境。將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籠統歸結為社會,必然導致對第二和第三個問題的認識產生分歧,從而使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時無所遵循,也使人們難以對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是否適當作出評價。
首先,企業社會責任對象的模糊和籠統,導致企業社會責任的范圍和內容不斷擴展,以至于無所不包。據美國學者波斯特(James E.Post)考察,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發端于20世紀初,最早是企業家個人行為,內容主要是濟貧救窮的慈善。到了1920年代,企業社會責任開始成為公司行為,內容也逐漸擴大,一些企業開始設立撫恤金項目,主動限制工時和提高工資,資助教堂、公寓和學校等公共服務設施建設。1970年代以后,伴隨著西方發達國家進入所謂“后工業化”時代,人們對環境破壞、技術變革的副作用和企業活動的外部性愈來愈關切,要求企業承擔起經濟職能以外的更多的社會責任,以便在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之間維持一種平衡。[2]40-44今天,企業社會責任的范圍和內容更得到空前的擴展,從經濟、文化到法律領域,從股東、員工、消費者到所有受公司決策影響的個人和團體,從救助特殊人群到改善全社會的福利,企業社會責任已近乎無所不包,達到極為泛化的程度。如卡羅爾(Archie B.Carroll)就認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慈善責任=企業的所有社會責任。”[1]27
其次,企業社會責任對象的模糊和籠統,使公眾和政府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期待和倡導存在著較大的差異。資料顯示,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人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關注明顯不同。例如,美國政府比較重視對企業社會責任項目和具體實施方式的指導,[2]45而法國和英國政府更重視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在中國,政府、公眾和監管機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和倡導亦不盡相同。在深交所《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和上交所《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指引》中,比較偏重鼓勵上市公司對職工、股東、債權人、供應商及消費者承擔責任,對回報股東的責任有特別強調,而在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的《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中,除了充分關注包括公司員工、債權人、客戶、消費者及社區在內的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利益,更重視企業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推進自主創新、技術進步和參與社會公益事業。[3]這些區別和差異,真實地反映了人們對企業社會責任對象認識上的分歧。
再次,企業社會責任對象的模糊和籠統,使企業對社會責任內容的理解和承擔社會責任的方式迥然不同。調查表明,企業基本上都是從自身的角度去理解社會責任,承擔社會責任的方式可謂五花八門。一些企業關注環境保護,一些企業熱衷濟貧救窮,一些企業喜歡幫助有需要的特殊群體,一些企業則更愿意資助文化教育等公共事業。這正如卡羅爾所說:“因為不同的企業,在規模、生產的產品類型、盈利能力和資源、對社會和利益相關者的影響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而他們信奉、履行社會責任之道也就不同。”[1]23
人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缺少共識,與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歧義較多,對社會責任對象的解釋模糊有關。現代的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始于1950年代鮑恩(Howard R.Bowen)的著作《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理論之父”,鮑恩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是:“企業人從事符合社會的目標或價值觀的政策、決策、或行動的一種義務”。[4]這一定義強調企業社會責任,就是企業的行為要超越企業自身的利益,要符合社會的目標和價值觀。定義揭示了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基本特征,但沒有涉及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更沒有涉及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此后的一段時間,學者們嘗試將社會責任與類似概念進行比較,以準確界定社會責任的內涵。在此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希斯(S.Prakash Sethi)關于企業社會行為的劃分。希斯將企業社會行為區分為三種形態,一是社會義務,指企業對市場力量或法律限制做出的反應;二是社會責任,指企業采取的能夠達到社會規范、價值觀和公眾期望水平的行為;三是社會反應,指企業對社會需求作出的預防性適應。通過與“社會義務”與“社會反應”比較,希斯強調:社會責任行為既不是法律等強制性規范下的必然選擇,也不是對公眾期待的被動反應,而是企業為滿足社會規范和價值觀要求的主動選擇。[5]這一定義更突出地強調了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自由選擇的特征,但同樣沒有涉及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和對象。
二、現有利益相關者分類標準的意義與局限
筆者認為,所謂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就是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時所選定的目標受體,是因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而使其狀況得到改善的社會構成要素。然而,社會是極為復雜的,期待企業把社會所有的構成要素都作為其社會責任的對象,理論上說不通,實踐中更難做到。
要解決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問題,首先必須解決對“社會”的模糊化理解。在此方面,利益相關者理論,特別是利益相關者分類理論,為我們開辟了一條道路。所謂利益相關者,按照美國經濟學家弗里曼(R.Edward Freeman)的經典定義,就是“那些能夠影響企業目標實現,或者能夠被企業實現目標的過程影響的任何個人和群體”。[6]25在利益相關者理論那里,社會具體化為各種利益相關者,從而不再是抽象或者混沌的,企業與社會的關系,就是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關系;企業的社會責任,就包含在對利益相關者的責任之中。利益相關者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關于企業性質和使命、企業與社會關系的傳統觀念,將人們對企業責任,包括企業社會責任對象的思考,引向受到企業行為影響的個人、群體和環境。
利益相關者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是關于利益相關者的分類。由于利益相關者理論最初是為了重構企業戰略而提出來的,一些學者便以對企業生存發展的重要性程度作為標準,對利益相關者進行分類。例如,弗里曼從所有權、經濟依賴性和社會利益三個不同的角度把利益相關者分為三類:一是擁有企業所有權的利益相關者,包括經理人員、董事和所有其他持有企業股票者;二是與企業在經濟上有依賴關系的利益相關者,主要有經理人員、員工、消費者、供應商、債權人、競爭者、地方社區、管理機構等;三是與企業在社會利益上有關系的利益相關者,主要有政府管理者、特殊群體和媒體等。[6]24-25美國學者米切爾和伍德(R.K.Mitchell;D.J.Wood,1997)通過評分方法即米切爾法,從權利性、合法性、緊急性三個維度對企業的利益相關者進行了劃分,按照所得到的分值來確定某一個體或群體是否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以及是哪一類型的利益相關者。[7]
上述分類以是否有助于實現企業自身的經濟利益為分類標準,具有極強的功利性,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并不在其視野之內。與此不同,以卡羅爾為代表的另外一些學者將利益相關者理論引入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嘗試運用利益相關者理論來解決企業社會責任內容含混和對象不清的問題。在卡羅爾看來,“企業社會責任意指某一特定時期社會對組織所寄托的經濟、法律、倫理和自由決定(慈善)的期望。”[1]23這些期望都對應著某個或某些利益相關者,因此,“企業社會責任定義和企業社會責任的金字塔圖相當于一個利益相關者模型。在這個模型中,每一類責任對應體現著與不同的利益相關者的關系。”[1]27如經濟責任對所有者和雇員起的影響作用最大,慈善責任對社區影響要遠遠大過消費者,而倫理責任影響著所有利益相關者群體。將利益相關者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聯系起來,是卡羅爾的一個重要貢獻,然而,卡羅爾并沒有對利益相關者進行分類,這是因為在他的觀念中,企業社會責任包含了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范圍極其廣大,因而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也就應該涵蓋所有的利益相關者。
將利益相關者理論引入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并嘗試從新的角度對利益相關者做出分類的是弗雷德里克(William C.Frederick,1998)和威勒(David Wheeler)。弗雷德里克從是否與企業發生市場關系角度,將利益相關者分成直接利益相關者和間接利益相關者。前者主要包括股東、企業員工、供應商、債權人、零售商、消費者、競爭者等,是與企業直接發生市場交易關系的利益相關者,后者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外國政府、社會團體、一般公眾、媒體等,是與企業發生非市場關系的利益相關者。[8]威勒等也將社會性維度引入到利益相關者的分類中,認為有些利益相關者是有社會性的,即他們與企業的關系直接通過人的參與而形成;有些利益相關者卻不具有社會性,即他們并不是通過“實際存在的具體的人”與企業發生聯系的,比如自然環境、人類的后代、非人物種等等。[9]按照威勒的分類,企業利益相關者的外延被大大拓展,從而促使企業超越“對自身生存發展是否有影響”的狹隘思考,將應當承擔的責任擴展到更廣闊的領域。但是,該種分類同樣沒有對不同利益相關者的責任作出區分,沒有明確是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還是利益相關者的一部分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
總之,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引入,將企業管理視野中的“社會”具體化,將人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相關問題的思考,聚焦于利益相關者。但是,這一理論本身和一些分類方法,對企業社會責任具體對象的界定仍然不夠清晰。問題的癥結在于:利益相關者實在是范圍廣大,不可能要求企業把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視為社會責任的對象,因為這樣做在理論上并不符合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本來意義,在實踐上的也沒有可實施性。企業社會責任必須有一個邊界,企業社會責任的范圍和領域不可能無限擴張,利益相關者不應該不加區分地都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當前亟需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基于對企業社會責任一些基本概念的深入辨析,通過運用新的分類工具,從眾多的利益相關者中,分離出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時應該選定的目標。
三、新分類標準下對企業社會責任對象的討論
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究竟包括哪些?解決這一問題,恐怕還要從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和利益相關者的分類標準分析入手。
首先,我們來分析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前文引述了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幾個有代表性的定義,可以看出,這些定義的分歧還是比較大的,正是這些分歧導致了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領域和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的不同看法。一些企業社會責任定義,典型的如鮑恩和希斯,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企業的行為要超越企業自身的利益,要符合社會的目標和價值觀;社會責任行為既不是法律等強制性規范下的必然選擇,也不是對公眾期待的被動反應,而是為滿足社會規范和價值觀要求的主動選擇。另外一些定義,典型的如卡羅爾,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涵蓋了企業所有行為領域,無論是法律所強制的,還是完全出于企業自愿的——“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慈善責任=企業的所有社會責任。”經濟責任是指企業能夠提供好的產品和服務并由此而獲利;法律責任是指企業能夠信守合約,遵守法律;倫理責任超越了法律的要求,指企業行為能夠遵守社會道德規范;自愿的責任是指企業完全出自于自覺自愿,滿足社會對企業的更高的期待。
筆者贊同鮑恩和希斯等人的定義,而不贊成卡羅爾定義,原因是卡羅爾的定義太過寬泛,包含了并不屬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其他企業責任。如上所述,從卡羅爾的定義出發,必然邏輯地導出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是企業社會責任對象的結論,而這顯然是不正確的。企業社會責任是一種工商企業追求有利于社會的長遠目標的義務,而不是法律和經濟所要求的義務。當我們談論企業社會責任時,暗含著一個假定,這就是假設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和不承擔社會責任的)都會遵守法律,合理合法地追求經濟利益。同時企業也被看作一種道德機構,在其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能夠分清正確和錯誤的行為,在沒有法律強制性約束的條件下,主動自覺去做對社會有益的事情。正如美國學者羅賓斯在對比社會責任與社會義務(Social obligation)和社會響應(Social responsiveness)時所說的,社會義務是一個公司的行為符合其應履行的經濟和法律責任。換句話說,一個企業承擔了它的社會義務,是指它的行為達到了法律的最低要求,企業所追求的社會目標僅限于有利于該企業實現其經濟目標。社會義務只是工商企業參與社會的基礎,是企業無條件必須做到的,而社會責任則是對企業更高的期待。與社會義務概念相比,社會責任加入了一種道德規則,是對企業超出法律義務的一種更高的要求,目的是促使企業主動從事有利于社會文明進步的事情。[10]
基于對企業社會責任的上述理解,筆者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領域應限于企業可以自由選擇的領域,凡是在經濟上、法律上企業沒有選擇的自由而必須承擔的責任,不能稱之為社會責任。與此相關,通過有自主意識和行為能力的個體的自然人參與,與企業建立起經濟關系、法律關系而成為企業利益相關者的,就不應納入企業社會責任對象的范疇,換言之,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應該是那些與企業無直接市場關系亦即無法律契約關系的利益相關者。將履行經濟責任和法律義務也視為在履行社會責任,就等于說所有的企業都承擔了社會責任,這無疑降低甚至取消了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
其次,我們再來分析利益相關者的分類標準。如前所述,相關分類方法很多,然而,當我們從企業本質出發,將企業視為一個契約的結合體,就會發現由于契約關系的性質不同,企業利益相關者會呈現出新的類型組合。
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契約,從是否有強制性約束力的角度可分為兩類:明契與默契。所謂明契,就是上述具有強制性而必須履行某種義務的法律契約。法律契約包括以自愿簽約的方式,約定締約各方必須履行某些義務的橫向法律契約,也包括由公權力機關如國家單方面頒布規定,要求有關方必須履行某些義務的縱向法律契約。橫向法律契約都是通過有自主意識和行為能力的個體自然人參與締結的,參與締約各方的義務所涉及的領域簡單而明了,契約可以很好地保護締約參與者的權益。而縱向法律契約則是公權力機關依據自己的意志,為保護沒有能力或沒有可能參與橫向締約的利益相關者而單方面頒布和強制實施的,其要求有關方履行義務所涉及的領域極為廣闊和復雜,一些領域很難被規范到,甚至被遺忘和忽視,利益相關者的權益遠不如橫向締約參與者那樣受到有效保護。如是,人們有關義務和責任的行為還必須有另一種契約——默契來調節。
所謂默契,就是并不具有強制性,而只是應該履行某種義務的社會契約。按照社會契約論創立者盧梭和霍布斯的解釋,政府等有影響力的機構是人們為了保障自身的權利與和平,通過相互訂立社會契約而建立起來的,政府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認可,政府必須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來行駛權力。較之于法律契約,社會契約沒有明確的條文,沒有必須履行的強制性,是一種人們與統治當局之間達成的一種默契,一種兩者之間自愿同意并相互受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社會契約思想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社會契約賦予統治當局一定的道德基礎,使其權力的行使合法化;另一方面,統治當局也必須按照約定來行使權力,不能獨斷專行。盡管社會契約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假設,并沒有法律的強制性,但它卻強烈地表達了人們對各種有影響力的機構或社會組織正確行使權力的一種期待,對各種有影響力的組織構成了一種無形而巨大的壓力。
企業作為有巨大影響力的組織,人們自然期待它能夠同樣受到社會契約的約束,在法律規范不到的領域,能夠按照公眾的愿望行使其所具有的權力,“由于企業影響力對于個人自由和財產通常會有潛在的影響,……毋庸置疑,社會合約的思想適用于產業和企業。”[11]56而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為社會提供某些公共物品,對公眾的期待和要求做出積極反應,也便被視為在履行社會契約。換言之,人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期待反映的是一種社會契約式的要求,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乃是履行社會契約的一種表現。“社會契約理論是一種非常抽象的概念,但它卻暗含著企業必須符合公眾的期望,契約主義是企業責任的一種擴展概念,因為它不加任何嚴格限制地增強了企業對許多社會因素的義務……比今天它們樂意承擔的種類更多的義務。”[11]151
社會契約是對法律契約的重要補充和替代。那些與企業存在法律契約關系的利益相關者,其權益通過企業履行法律責任便可以得到較好保護,而那些與企業不存在法律契約關系,或已有的法律契約關系難以保障其權益的利益相關者,企業社會責任就成為了維護這部分利益相關者利益的重要途徑。進而言之,那些有能力參與橫向締約,與企業的關系同時被橫向和縱向法律契約涵蓋的利益相關者,由于其利益完全可以通過法律契約得到保障,就不應該成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而那些沒有能力參與橫向締約,或如威勒所說,不能通過“實際存在的具體的人”與企業發生關系的利益相關者,由于其只與企業存在縱向法律關系,其與企業的關系主要受社會契約的調節,其權益主要依靠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來維護,才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
四、結論
綜上所述,那些與企業同時存在縱向和橫向法律契約關系,企業必須對之承擔法律責任,而且其權益完全可以通過法律途徑得到有效維護的利益相關者,不構成企業社會責任對象。這一類的利益相關者有:企業員工、顧客、供應商、股東或債權人等。
除此之外,因沒有能力參與橫向締約,與企業之間主要是社會契約關系,企業應該對其承擔社會責任,因而構成企業社會責任對象的利益相關者有:
(1)一般民眾。企業的任何行為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民眾,而任何個人和組織都不能代表民眾和企業簽訂橫向的法律契約來保證民眾權益。民眾與企業的關系,主要是社會契約關系。民眾對企業的共同期待,如維護社會主流價值、促進社會安定祥和、支持教育文化事業、增進社會進步與繁榮等等,并不具備法律的強制性,主要靠企業通過承擔社會責任去實現。
(2)特殊社會群體。婦女、兒童、老年人、殘疾人、災民等,諸如此類的社會群體,有特殊的權利和利益,也有廣泛的慈善需求,但這些群體本身均不構成簽訂法律契約的主體,與企業不存在橫向的法律契約關系。特殊社會群體與企業的關系,主要是社會契約關系。企業資助社會慈善事業、救助有需要的社會群體,反映的是企業一種將自身看作一種道德機構,主動去做對社會有益的事情的自覺自愿,法律對此沒有任何強制。
(3)社區。社區作為生產經營活動所在地區和距離企業最近的社會區域,包含了區域內的管理部門、非政府組織、社區居民等等。社區構成了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基本環境,企業與社區之間的互動對企業和社區各自的發展均有重要影響。但社區與企業同樣不存在橫向的法律契約關系,社區對企業的一些愿望,如增加當地居民就業、改善公共基礎設施、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和社會環境等等,完全屬于社會契約式的期待。
(4)自然環境。自然環境即屬于威勒所說的不是通過“實際存在的具體的人”與企業發生關系的利益相關者,其與企業同樣不存在橫向的法律契約關系。合理利用當地的資源,保護生產經營地的自然環境,積極參與生態環境改造,搶救瀕臨滅絕的物種,更多地需要企業的自覺。
以上分類標準,通過區分企業的利益相關者——無論是個人還是群體——與企業結成的不同的契約關系,將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確定為那些只與企業存在縱向法律關系,與企業的關系大部分受社會契約的調節,其權益主要依靠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來維護的利益相關者。不可否認,在現實中,企業利益相關者與企業之間可能具有多重關系,但這并不會造成企業社會責任對象認知的混亂。同一個利益相關者,當其與企業以經濟關系和法律關系的身份出現,如作為股東或客戶出現,企業就只對其負有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當其與企業以社會契約關系的身份出現,如作為殘疾人、災民或其他社會群體的一員,企業就對其負有社會責任。另外,企業的利益相關者也是變化的,并且還有一些潛在的利益相關者,但只要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和劃分利益相關者的標準是清晰的,我們就能辨別出那些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從利益相關者中劃分出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并不否定企業對社會責任對象之外的利益相關者承擔超越法律責任的表現,如關愛員工、善待顧客、以各種形式幫助供應商發展等等。企業愿意對社會承擔更多的責任,理應受到歡迎和鼓勵。本文只是想強調,當企業有履行社會責任的愿望時,應該首先考慮那些作為社會責任對象的利益相關者,而我們在評價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表現時,應重點考察對這部分利益相關者所盡的義務。
[1]阿奇B·卡羅爾,安·K·巴克霍爾茨.企業與社會:倫理與利益相關者管理(第5版)[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
[2]詹姆斯E·波斯特,安妮·T·勞倫斯,詹姆斯·韋伯.企業與社會(英文版第8版)[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98.
[3]http://www.sasac.gov.cn/n1180/n20240/n7291323/index_9.html.
[4]Howard R.Bowen,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nessman[M].New York:Harper,1953:6.
[5]S.Prskash Sethi,Dimensions of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An Analytical Framework[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Spring 1975):58-64.
[6]R.Edward Freeman,Strategic Management:A Stakeholder Approach[M].Boston:Pitman,1984.
[7]Ronald K.Mitchell,Bradley R.Agle and Doona J.Wood,Toward a Theory of Stakeholder Identification and Salience:Defining the Principle of Who and What Really Count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0ctober 1997):853-886.
[8]William C.Frederick,Business and Society,Corporate Strategy,Public Policy,Ethics(6th Ed.)[M].McGraw-Hill Book Co,1998,p.82.
[9]威勒,西蘭琶等.利益相關者公司: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之藍圖[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9.
[10]斯蒂芬·P·羅賓斯,瑪麗·庫爾特.管理學(第4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97-98.
[11]喬治·斯蒂納,約翰·斯蒂納.企業、政府與社會[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F272-05
A
1005-2674(2015)02-044-06
2014-10-15
2014-12-18
趙德志(1955-),男,遼寧鳳城人,經濟學博士,遼寧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企業與社會研究。
責任編輯:張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