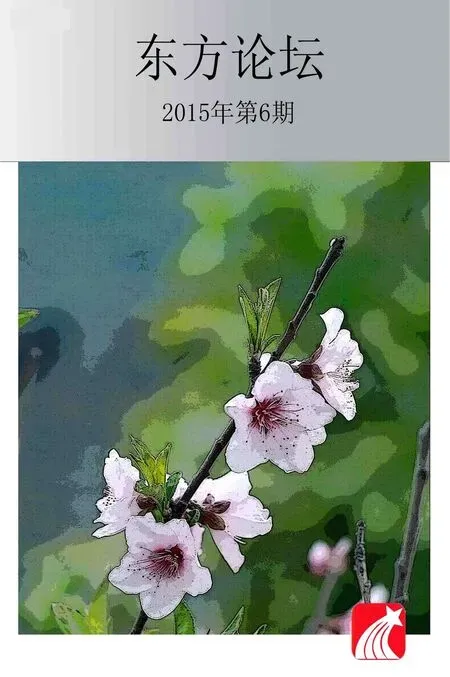佛教文學文類學初探
侯 傳 文
(青島大學 文學院, 山東 青島 266071)
?
佛教文學文類學初探
侯傳文
(青島大學文學院, 山東青島266071)
摘 要:中印佛教文學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些獨特的文學體式和類型,如詩歌類的偈頌與贊歌、故事類的本生與譬喻、說唱類的唱導與變文等,都特色鮮明而且影響深遠,在東方文學文類的發展演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佛教文學;文類學;偈頌;譬喻;變文
文體學(Genology)又稱文類學或體裁學,是比較文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主要研究如何按照文學本身的特點對文學進行分類,研究各種文學體式的發展演變、基本特征和相互影響。佛教文學是東方文學中重要而又普遍的現象,歷史悠久,空間跨度大,文學類型豐富,體式多樣,非常適合比較文學文類學研究。
一
佛教文學文類中種類最多、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是詩歌,其中最有特色、最具可比性的是偈頌和贊歌。
偈頌是佛經中最重要的文學體式之一。“偈”是梵文gatha的譯音“偈陀”的簡稱,又譯為“伽陀”或“伽他”,是印度古代韻文的一個單位,一般是一個對句為一偈,其作為詩體類似中國古代詩歌中的頌體,支謙在《法句經》譯本序中說:“偈者結語,猶詩頌也。”[1](P566)所以又意譯為“頌”或者“諷頌”,后中外混合為“偈頌”。“偈頌”在佛經中運用非常廣泛,成為與“長行”(即散文體)相對的一種表述方式。原始佛教的四部《阿含經》中已經穿插了大量的偈頌,部派佛教時期產生了更多的偈頌體文學作品,如巴利文佛典小部15部經中有10部是偈頌體。“偈頌”或“偈陀”是佛典分類“九分教”和“十二分教”之一,又稱為“孤起頌”,即單獨的偈頌。還有一種“Geya祇夜”,意譯“重頌”或“應頌”,即與長行散文相配合的偈頌。按印度傳統,佛教師徒付法傳經主要靠口耳相傳,因而言簡意賅、具有高度概括力而又便于記憶的偈頌非常適用。偈頌內容富含哲理,形式上用韻律,可長可短,但一般比較短小精煉,因而可以看作格言詩或哲理詩。當然偈頌也可以用來抒情、說教、贊頌或敘事。
偈頌類佛經很早就翻譯到中國,對中國詩歌的內容和形式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之一就是中國佛教偈頌詩的大量涌現。中國高僧們通過漢譯佛典對“偈”作了區分,如三論宗奠基人吉藏《百論疏》卷上指出:“偈有二種,一者通偈,二者別偈。言別偈者,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皆以四句而成,目之為偈,為別偈也。二者通偈,為首盧偈,釋道安云:蓋是胡人數經法也,莫問長行與偈,但令三十二字滿,即便名偈,謂通偈也。”①轉引自項楚《寒山詩注(附拾得詩注)》,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844頁。在這樣的通偈與別偈二分的基礎上,中國語境中的偈主要是“四句而成”的別偈。在內容方面,中國僧人對“偈”也有獨特的理解,如拾得詩:“有偈有千萬,卒急述應難。若要相知者,但入天臺山。巖中深處坐,說理及談玄。共我不相見,對面似千山。”[2](P845)可見偈的內容主要是“說理及談玄”,需要慢慢體悟,而且只有相知者能夠理解。因此項楚先生對“偈”的解釋是:“構成佛經的文體之一,具有類似詩的形式和宗教性的內容。”[2](P844)
偈頌文類的特點在內容上主要表現為哲理性。在文學作品和現實生活中,一些有道高僧常以說“偈”的方式表現自己的悟道體驗,其中往往蘊涵深刻的哲理或玄妙的“天機”。就藝術形式和表現手法而言,偈頌一般言簡意賅、形象生動,常用象征、暗示等手法,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
與偈頌相似又不盡相同的佛教詩歌文類是“贊頌”,或者稱為佛教贊歌。在印度,此類作品的代表作是著名詩人摩咥哩制吒的《一百五十贊佛頌》和《四百贊》,義凈稱贊其:“文情婉麗,共天蘤而齊芳;理致清高,與地岳而爭峻。西方造贊者,莫不咸同祖習。”像無著、世親那樣的大德“皆悉仰止”,五天之地,初出家者,“須先教誦斯二贊”。[3] (P179)佛教贊歌是佛教文學中的特殊種類。從形式上說,贊頌和偈頌基本相同,一般都是采用“輸洛迦”體,是一種按音節的數目和長短來計算的詩律,有四個音步,每個音步有8個音節,一韻共有32個音節,稱為一頌或一偈,譯成漢語可以是兩個長句,也可以是四個或六個短句,古代一般譯成四言,五言或七言的形式。從內容的角度說,一般的偈頌是格言詩、哲理詩和抒情詩,而贊頌可以單列一類。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曾經述及:“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弦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嘆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4](P53)這一方面說明偈頌是可以入弦歌詠的,另一方面說明其內容以贊頌為主。從詩歌起源的角度說,頌神詩是詩的源頭之一,各種成熟的宗教都有自己的頌神詩或贊美詩傳統,對內表達對神靈的崇拜之情,以堅定宗教信仰,對外可以宣傳教義,吸引信徒,戰勝外道,佛教也不例外。歷代佛徒創作了大量贊佛文學,其形式多為偈頌。即使是以表現個人體驗為主的僧尼詩歌,也往往伴隨著對佛祖與佛法的贊美和稱頌。這樣的贊佛文學進一步發展成為一種獨立的佛教詩歌類型,稱為贊頌(stotra)。①參閱陳明《漢譯佛經中的偈頌與贊頌簡要辨析》,載《南亞研究》2007年第2期。
在中國,有許多高僧著有贊佛詩,如《廣弘明集》卷十五“佛德篇”收錄東晉高僧支遁法師的《釋迦文佛像贊》《阿彌陀佛像贊》《文殊師利贊》《彌勒贊》《維摩詰贊》《善思菩薩贊》等“佛菩薩像贊”13首,謝靈運的《佛法銘贊》《和范光祿祇洹像贊三首》(佛贊、菩薩贊、緣覺聲聞合贊)、《維摩詰經中十譬贊八首》等;卷三十“統歸篇”收錄支遁《贊佛詩》八首,都屬于贊頌詩。這些贊頌佛菩薩的作品,一方面受中國傳統“頌贊”文體的影響,如劉勰所謂:“贊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贊,蓋唱發之辭也。……然本其義,事生獎嘆,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廣,必結言于四字之句,盤桓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5](P106-107)另一方面也借鑒了佛教偈頌的形式。隋唐時期,中國佛教宗派形成,大多借重文學弘法傳教,由此中國佛教文學也進入一個高峰期,佛教詩歌也更加繁榮。中國佛教詩歌在不同宗派詩人那里也有不同的表現,如禪宗反對研經念佛,主張頓悟本性、見性成佛,因而禪門偈頌大多是探討心性、表現禪境的哲理詩,很少贊頌詩。而凈土宗則相反,主張通過念佛和贊佛實現往生凈土的終極目標,所以凈土宗形成之后,進一步推動了中國佛教贊頌文學的發展。凈土宗的奠基人和代表人物曇鸞、善導、法照等,都創作了許多贊佛詩。凈土大師們的贊佛詩歌內容以贊佛為主,形式更偏重和樂,作品大多有和聲標志,如善導《轉經行道愿往生凈土法事贊》中的“般舟三昧樂”附有“愿往生”與“無量樂”兩種和聲,交替使用;其“行道贊梵偈”則附有和聲“散華樂”;《依觀經等明般舟三昧行道往生贊》中有洋洋千句的長篇贊歌“般舟三昧樂”,交互使用“愿往生”與“無量樂”兩種和聲。法照《凈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贊》中的《寶鳥贊》,每上句用和聲“彌陀佛”,每下句用和聲“彌陀佛彌陀佛”;《維摩贊》每上句用和聲“難思議”,每下句用和聲“難思議維摩詰”;《離六根贊》前一部分用和聲“我凈樂”,后一部分交互使用“努力”與“難識”兩種和聲;《西方樂贊》交替使用“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樂”“西方樂”與“諸佛子”三種和聲。②見《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7冊、第85冊。參見加地哲定《中國佛教文學》,劉衛星譯,今日中國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171頁。這些“和聲”的名稱有的僅僅是重復句,有的近似曲牌。估計最初是通過重復詩中的詞句形成復踏效果,以增強感染力,進而發展成為旋律的應和,形成和聲。顯然,這種贊歌的形式是伴隨一定儀式的配樂歌詩,離偈頌體式已經比較遠了,具有了獨立的文類學意義。中國佛教文學中的贊歌與偈頌主要有兩點差別:其一、偈頌作為法句是佛教義理的概括,屬于佛教的精英文學,偏重哲理情趣,表現多用象征,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贊歌作為情感表現,屬于佛教中的大眾文學,一般通俗易懂。其二、在中國佛教文學中,偈頌以表現宗教體驗和感悟為主,一般不再講究入弦和樂,而贊歌則是用來唱的歌詩,必須和樂能唱。
二
傳統佛經分類中“九分教”或“十二分教”中的本生、本事、希有法、緣起、譬喻、授記等,都屬于散文敘事文學,其中最有文類學意義的是本生和譬喻。
根據佛教的業報輪回觀念,每個人都有前生、今生和來生。釋迦牟尼在成佛之前經過無數次轉生,積累下無量功德,才最終成佛。佛本生故事講的就是釋迦牟尼前生輪回轉生的故事。印度佛教各部派都有自己的佛本生故事,南傳上座部將有關釋迦牟尼前生的故事編輯在一起,共有547個,成為巴利文佛典小部中的一部經,即《佛本生經》。其中每個本生故事基本由五部分組成:1、今生故事,說明佛陀講述前生故事的地點和緣由;2、前生故事,這是作品的主體;3、偈頌詩,穿插于故事講述之中或放在故事最后以點明題旨;4、注釋,解釋偈頌詩每個詞的含義;5、對應,把前生故事中的角色與今生故事中的人物對應起來。可見,輪回轉生在佛本生故事中不僅是基本觀念,而且具有結構功能。作為觀念題旨,它具有主題學意義;作為結構模式,它具有文體學意義。
在印度,佛本生故事與兩種佛教文學文體密切相關。一是小說。佛本生故事是經過藝術加工的虛構性散文敘事文學,與小說本質相同,因此可以看作印度早期的小說或小說雛型。二是傳記。由于印度古人篤信輪回轉生,而且前生與今生緊密聯系,沒有截然分割,因此釋迦牟尼的前生故事也成為佛陀生平的一部分。佛教各部派都編有佛陀傳記,如大眾部的《大事》 、法藏部的《釋迦牟尼本行》、說一切有部的《大莊嚴》等,都將釋迦牟尼的前生事跡納入,作為佛傳的一部分。
在中國,“五百本生”曾經有過翻譯,但已經失傳。現存漢譯佛經中的佛本生故事散見于《六度集經》《生經》《佛本行集經》《賢愚經》《菩薩本生鬘論》等,所收故事亦上百數。這些故事與巴利文《佛本生經》屬于不同的佛教部派,但故事來源和編纂手法基本一致,因而大同小異。由于佛本生故事的廣泛傳播,使其成為中國佛教文學藝術的重要源泉,小說、戲曲、繪畫、雕塑等佛教文學藝術不僅從佛本生故事取材,而且在文學敘事和藝術表述等方面,也深受佛本生故事的影響。
譬喻有廣義和狹義。從廣泛的意義上說,凡是通過故事說明道理的作品都是譬喻,由此“九分教”或“十二分教”中的本事、本生、因緣、無問自說等,都可以看作譬喻;而狹義的譬喻只是“九分教”或“十二分教”中的一類,是佛經中或者佛教文學中的一種特殊文體。在釋迦牟尼時代,譬喻是佛陀及其弟子說法的一種方式。佛祖釋迦牟尼說法傳教之時便善用譬喻,《中阿含經》中有許多以“喻”為題的佛經,如《箭喻經》《城喻經》《水喻經》《木積喻經》《鹽喻經》《象喻經》 等。其中《箭喻經》講一身中毒箭之人,不抓緊拔箭療傷,反而追問箭之來歷,結果不等問完已經喪命。說明不要追問世界有常無常等形而上問題,解決生老病死問題才是當務之急。《鹽喻經》以鹽投水的咸淡程度喻業報之理。佛弟子承師之道,也善用譬喻。《長阿含·弊宿經》寫的是佛滅度之后,童女迦葉與一名叫弊宿的婆羅門論道。弊宿說,他的親友中有一位惡人,照理死后應入地獄,弊宿請他回來告訴地獄中的情況,但他一直沒有回來。另有一位善人,照理死后應升天界,但也沒有回來告知天界情況。所以弊宿認為沒有他世更生,也沒有善惡報應。迦葉說:“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今當為汝引喻解之。”然后為弊宿說了兩個譬喻,其一是一位盜賊被抓住,關進獄中,他想回去告訴家人獄中情況,獄卒不會放他回家;其二是一個掉進廁所糞坑中的人,好容易爬上來洗干凈,讓他再回到糞坑里去,他絕對不愿回去。弊宿死去的親友也是如此,得到惡報想回也回不來,得到善報的再也不愿回來。最后迦葉以巧妙的譬喻折服了弊宿。
大乘佛經雖然不是釋迦牟尼所說,但繼承并發展了釋迦牟尼譬喻說法的傳統,如《法華經》中有著名的“法華七喻”,其中“火宅喻”講一位長者見三個兒子在著火的房子里玩耍,不肯出來,為了讓他們走出火宅,便假說外面有好玩的羊車、鹿車和牛車。孩子們聽說外面有車玩,都走出火宅。長者便給他們每人一輛七寶牛車。以此說明佛教三乘和一乘的關系。“窮子喻”講一個少小離家的窮子,若干年后乞食路經自己的富貴之家,惶恐而走。父親認出兒子,派人追趕。窮子驚恐昏厥,只好讓其離去。長者為了誘子歸家,先雇其除糞,后留作長工,認為義子。長者臨終宣布父子關系,讓其繼承家業,窮子喜出望外。以此表現聲聞弟子們被佛授記時的心情。“化城喻”講一位聰明的導師引導眾人經過漫長而艱險的道路去珍寶處。眾人中途懈怠,畏難不前。導師為使眾人堅定信心,便以方便力于險道中途化現一城,讓眾人入城歇息。待眾人得到休息之后,即滅化城,對眾人說珍寶處已近,勉勵大家繼續前進。以此解釋佛陀為何先說小乘后說大乘。這些故事本身含意雋永,用以說理更顯形象生動,意趣盎然。當然,譬喻不同于一般的故事,它不注重情節的完整性,而追求說理的形象和透辟,而且一般比較簡短。
在后代佛徒中,譬喻成為講解佛經的一種方式。大約在公元前后,出現了一些擅長譬喻的佛教論師,被稱為“譬喻師”,如童受、法救等,創作了一批典型的譬喻作品,如《大莊嚴論經》《法句譬喻經》等。漢譯佛典中有《大莊嚴論經》15卷,是一部訓誡故事集,共收89個故事。鳩摩羅什譯本明確說是“馬鳴菩薩造”,義凈也說“馬鳴亦造歌詞及《莊嚴論》”,但在我國新疆發現的內容與《大莊嚴論經》相近的一個殘卷(1926年刊行于德國來比錫),卻署名為童受。童受是稍后于馬鳴而又與馬鳴齊名的有部論師,渥德爾在其《印度佛教史》中便把《大莊嚴論經》歸于童受,①詳見渥德爾《印度佛教史》,王世安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526頁。所以這部作品的著作權還是一個問題。呂澂先生認為童受和馬鳴先后相接,稍后的童受很有補訂馬鳴舊制而成的可能。②詳見呂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7頁。《法句譬喻經》是用一些小故事來解釋《法句經》,其中的譬喻故事多為附會之談,有些比較牽強。譬喻師并非“譬喻”的發明者,而是對佛經譬喻文學傳統的繼承和發展者。不僅早期的《阿含經》多用譬喻,后來的《那先比丘經》中那先對彌蘭陀王說法,也主要用譬喻,所以呂澂先生說他“甚似后來的譬喻師,可以稱為譬喻師的先驅者。”[6](P62)隨著佛教譬喻文學的發展,形成了一些專門收集譬喻故事的經典。其中《百緣經》是譬喻經中最古老的一部,屬于小乘經典,有三世紀支謙的漢譯,題為《撰集百緣經》,其中夾雜了許多授記和本生故事,可以看出本生、授記、因緣、譬喻之間并無嚴格的界限。《天譬喻經》敬辭和題署都顯示為大乘經,內容仍主要是從早期律藏和經藏中搜集的故事。該經沒有完整漢譯,但其中有些故事可以在漢譯佛典中找到對應。漢譯佛典中重要的譬喻類經典還有《雜譬喻經》《百喻經》《雜寶藏經》《菩薩本緣經》等。關于《百喻經》,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九《百句譬喻經前記》記載:“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師求那毗地出。修多羅藏十二部經中抄出譬喻聚為一部,凡一百事,天竺僧伽斯法師集行大乘,為新學者撰說此經。”[7](P355)說明這部作品的來歷是抄自眾經,其用途主要是教授新學。
散文敘事文學的最高形態是小說。故事屬于小說的前身,為小說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佛教小說也體現了這樣的文類發展規律。在佛教文學中,小說與本生故事、譬喻故事、傳記故事等散文敘事文學血脈聯系非常明顯,上述各類故事文學,都為佛教小說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準備了條件。小說較之故事并無嚴格界限,只是相對地情節結構更復雜一些,描寫刻畫更細致一些。從這個意義上說,佛經中許多故事已具備了小說的特質。如漢譯《太子須大拿經》是佛本生故事之一,寫太子須大拿樂善好施的故事,不僅篇幅較長,而且對太子流放、送子舍妻的場面和人物心態作了細致傳神的描寫。然而小說文類在印度佛教文學中沒有真正發展起來。印度小說成熟之時,佛教在印度趨于衰落,而且印度小說一開始就陷入了言文分離的形式主義泥沼,所以在印度佛教文學中,沒有成熟的典型的小說。
在中國小說的發展過程中,佛教文學發揮了重要作用。佛教的神話思維打開了人們的想象空間,佛經故事的魔幻表現提供了藝術借鑒,佛門弟子的傳奇經歷提供了故事素材,這些都有助于小說文類的發展。佛教為了面向大眾贏得信徒,也要借助新興的受大眾歡迎的小說文體。從魏晉開始,到唐宋元明,出現了佛教與小說互動共進的局面,期間產生了許多在題材、情節、人物、主題及藝術表現等方面都具有佛教特色的小說作品。與印度相比,中國佛教小說具有更重要的文體學意義。在中國,佛教小說不僅貫穿中國小說發展的每一個階段,而且起著引領作用,如南北朝的志怪小說、唐代傳奇小說、俗講變文、說唱話本等,都是佛教文學開風氣之先。
從印度到中國,佛教小說有自己的發展軌跡和演變規律。佛教小說的文體特點,如思想方面的出世性與超越性,內容方面的志怪、述異和傳奇,敘述方面的故事套故事和韻散結合,藝術表現方面的魔幻等,都與本生、譬喻等佛教故事文學有著內在的聯系。
三
從文類學的角度看,說唱文學是戲劇的源頭之一,印度佛教戲劇也體現了這樣的發展規律。佛陀時代就有一些善于歌唱的詩人加入了佛教僧團,以自己的歌詩為佛法服務,以面向大眾的通俗化的詩歌和故事。阿育王時期佛教發展到高峰,佛教通俗文學也更加繁榮,此時流行的“梵唄”是佛教說唱文學發展的新階段。關于梵唄,梁慧皎《高僧傳》卷十三解釋說:“然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唄。至于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贊則號為梵唄。昔諸天贊唄,皆以韻入弦綰。五眾既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為妙。”[4](P508)從早期佛經中對話體歌詩的詠唱,到阿育王時代的梵唄,再到馬鳴的伎樂和世俗劇,有著明顯的發展軌跡。
目前發現印度最早的成熟戲劇是公元2世紀佛教戲劇家馬鳴的作品。1910年,在我國新疆吐魯番發現了三部梵文佛教戲劇殘卷,1911年由魯德斯(Heinrich Lüders)校刊,以《佛教戲劇殘本》的書名在德國柏林出版。其中有一部九幕劇《舍利弗傳》保存的是最后兩幕,以印度習慣于卷末署名為“金眼之子馬鳴著舍利弗世俗劇”,從而確定為馬鳴的作品。馬鳴是重要的佛教詩人和戲劇家,他的戲劇創作有著非常重要的文類學研究價值。馬鳴嘗試過多種類型的戲劇的寫作,可以看出戲劇藝術形式的發展演變。一是以《賴吒和羅》為代表的,以演唱為主要表現方式的戲曲。該劇沒有流傳下來,但《付法藏因緣傳》中的記載可以看出其藝術形式:“(馬鳴)于華氏城游行教化,欲度彼城諸眾生故,作妙伎樂名《賴吒和羅》,其音清雅哀婉調暢。……如是廣說空無我義,令作樂者演暢斯音,時諸伎人不能了解,曲調音節皆悉乖錯。爾時馬鳴,著白氈衣入眾伎中,自擊鐘鼓,調和琴瑟,音節哀雅,曲調成就,演宣諸法苦空無我。”①參見高振農《大乘起信論校釋》附錄,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02頁。這是一種曲藝形式的戲劇,是印度戲劇比較原初的形式。二是以《舍利弗傳》為代表的“世俗劇”。該劇比較符合戲劇理論著作《舞論》的要求,古典梵語戲劇的主要特征,包括角色的分類固定,戲文的韻散雜糅,人物語言的雅俗之分,以及舞臺提示和劇終的祝福詩等,都已基本具備。三是抽象概念人物化的戲劇。在新疆發現的三個佛教戲劇殘卷中有一部抽象概念人物化的作品,登場的角色有“覺”(智慧)、“稱”(名聲)、“定”(禪定)等,只有一個佛算是實有人物。這種形式的來源實際就是佛經本身。早期的《雜阿含經》中經常用問答形式表現佛教思想和外道思想的斗爭,有的運用“概念人物化”的方式,如佛陀即將成道時,魔王的女兒“欲望”“不滿”“煩惱”等前來誘惑,被他各個擊潰;還有佛教的“無嗔”“忍辱”與世俗價值觀之間的沖突等。這樣的象征表現手法經過表演就成為一種獨特的戲劇形式。這種概念人物化的象征劇在印度戲劇史上屢見不鮮。②參閱金克木《概念的人物化——介紹古代印度的一種戲劇類型》,載《外國戲劇》1980年第3期。
有些佛教劇是在佛經的基礎上改造而成,如現存吐火羅文和回鶻文的《彌勒會見記》,兩種文本都標明是“劇本”,且有“幕間插曲終”“全體下”等舞臺術語,有丑角等戲劇要素,但仍有學者認為“它同其他散文夾詩的敘事文章一點也沒有區別”[8](P11),因此否認它是真正的劇本。季羨林先生經過充分論證,認為它“是一個劇本,可是嚴格說起來,它只是一個羽毛還沒有豐滿,不太成熟的劇本。”[8](P14)正因為其不成熟,更有文體學研究的價值,可以據此研究印度乃至東方戲劇文類的形成和特點。季羨林先生指出:“吐火羅文劇本,無論在形式方面,還是在技巧方面,都與歐洲的傳統劇本不同。帶著歐洲的眼光來看吐火羅劇,必然格格不入。”[8](P12)他借鑒了A. von Gabain 的觀點,認為“流傳下來的寫本絕大多數不是為了閱讀,而是為了朗誦,伴之以表演。在某種情況下,從中就產生出了戲劇。在中世中國,中亞的朗誦藝術非常流行,中國的歌唱劇可能受到西面來的影響。中國劇中的帝王或大將的裝束同吐魯番壁畫中的金剛手相同,這也可能是西方的影響。……在回鶻文本的一些后記中甚至在文本中可以看到,這部書是為了在朔望之日供養彌勒時作為一個劇來朗誦的。”季先生又借鑒了魯德斯關于印度戲劇起源于皮影戲的觀點,進一步指出:“吐火羅文劇本的敘述者是從印度古代看圖講故事者發展出來的。看圖者眼前是有圖畫的,而吐火羅文劇則沒有。于是原來用圖畫表述的情節,只能用表演者來表演了。”[8](P12-14)由此可以了解佛教戲劇、印度戲劇甚至東方戲劇的形成過程。
中國的“變文”與“變相”,以及由變文到戲劇的演進,也可以由此得到啟示。中國本土也有自己的說唱文學傳統,但中國佛教說唱文學并非直接繼承本土傳統,而是更多地受印度佛教梵唄和唱導的影響。印度的梵唄即頌贊,包括詠經與歌贊,傳入中國后,詠經獨立成為轉讀,即以抑揚頓挫的音調和節奏朗誦經文;歌贊以唱經贊佛為主。唱導是從梵唄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佛教說唱藝術。關于印度佛教寺院的唱導,義凈《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32“贊詠之禮”有這樣的記述:“此唱導師,恒受寺家別料供養。或復獨對香臺,則只坐而心贊。或翔臨于梵宇,則眾跪而高闡。”[3](P177)這是中國寺院“唱導”制度的印度淵源。慧皎《高僧傳》指出:“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眾心也。昔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霄疲極,事資啟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旁引譬喻。”[4](P521)中國魏晉時期佛教寺院中已經形成“唱導”制度,其奠基和推動者是廬山慧遠。慧皎《高僧傳》說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齊集,輒自升高座,躬為導首。先明三世因果,卻辯一齊大意,后代傳受,遂成用則。”[4](P521)慧皎《高僧傳》將“唱導”與譯經、義解、習禪、明律等并列,形成獨立的一科,可見“唱導”在佛教中的重要地位。唱導的內容主要是佛教義理,其中的因緣譬喻,已經具有文學性,加之借重文采聲律,更具藝術感染力。唱導師需要具備聲、辯、才、博四個方面的素質,慧皎指出:“非聲則無以警眾,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采,非博則語無依據。至若響韻鐘鼓,則四眾驚心,聲之為用也。辭吐俊發,適會無差,辯之為用也。綺制彫華,文藻橫逸,才之為用也。商榷經論,采撮書史,博之為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以人時。如為出家五眾,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為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為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為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而興。可謂知時知眾,又能善說。雖然,故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4](P521)在慧皎之前,唱導不受重視,唱導師也沒有進入僧傳。慧皎在自己的著作中增列唱導一科,是有感于杰出的唱導在佛教集會和佛事活動中的藝術效果:“爾時導師則擎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栗;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核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報暢悅;敘哀感,則灑淚含酸。于是闔眾傾心,舉堂惻愴。無體輸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4](P521-522)可見唱導在佛教傳播發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唱導”主要面向僧人,隨著不出家的佛教信眾增加,出于傳教需要,出現了面向群眾的“俗講”,即通俗的講經,由此演變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說唱文學體式“變文”。“變文”有廣義和狹義。狹義的“變文”是一種有說有唱、韻散結合來敘述鋪陳故事的文體,屬于典型的說唱文學;廣義的變文還包括講經文、因緣(緣起)、押座文、解座文、詞文、詩話、話本、賦等在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各種說唱類俗文學文體。①參見項楚《敦煌變文選注》(增訂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4-5頁。宋代以后變文消失,但由變文開創的說唱文學卻愈加興旺,并且由廟宇走出進入市井“瓦子”,從而演化出許多新文學體裁,包括以說為主的平話,以唱為主的諸宮調、大曲、寶卷、鼓子詞等。鄭振鐸先生指出:“在‘變文’沒有發現以前,我們簡直不知道:‘平話’怎么會突然在宋代產生出來?‘諸宮調’的來歷是怎樣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寶卷、彈詞及鼓詞,到底是近代的產物呢?還是‘古已有之’的?許多文學史上的重要問題,都成為疑案而難以有確定的回答。但自從三十年前斯坦因把敦煌寶庫打開了而發現了變文一種文體之后,一切的疑問,我們才漸漸的可以得到解決了。我們才在古代文學與近代文學之間得到一個連鎖。我們才知道宋、元話本和六朝小說及唐代傳奇之間并沒有什么因果關系。我們才明白許多千余年來支配著民間思想的寶卷、鼓詞、彈詞一類的讀物,其來歷原來是這樣的。這個發現使我們對于中國文學史的探討,面目為之一新。”[9](P155)這段話對變文的文類學意義作了高度的概括,只是鄭振鐸先生沒有提到戲劇。實際上,變文和佛曲也是中國戲劇的源頭和基礎之一。元雜劇是中國古代戲劇史上的一個高峰,雜劇是由諸宮調、大曲等說唱藝術演變而來,諸宮調和大曲則直接源于變文和佛曲,只是曲調更為復雜。佛教劇在元雜劇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如鄭廷玉的《布袋和尚忍字記》,寫羅漢轉世的汴梁富戶劉均佐忘卻前世,陷入世俗,貪財吝嗇;彌勒佛化為布袋和尚前往點化,使其出家修行,又成為護法羅漢。李壽卿的《月明和尚度柳翠》,寫觀音菩薩凈瓶中的柳枝,轉生為杭州美女柳翠,淪落風塵。經過月明禪師度化,悟道出家。以上都是典型的佛教度化劇。傳世作品中還有無名氏的《龍濟山野猿聽經》,也是典型的佛教劇,寫的是龍濟山有一個千年玄猿,經常在寺院附近聞經聽法,并受到修公禪師的點化,最終悟道。劇中的野猿是《西游記》孫悟空形象的淵源之一。另外,元代已有《目連救母》雜劇流行,是中國佛教戲劇的重頭戲“目連戲”的開端,而這些“目連戲”與目連救母變文都是一脈相傳的。
參考文獻:
[1]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冊[M].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79.
[2] 項楚.寒山詩注(附拾得詩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0.
[3]義凈著.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M].王邦維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5.
[4] 釋慧皎.高僧傳[M].湯用彤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
[5]郭晉稀.文心雕龍注譯[M]. 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
[6] 呂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7] 僧祐.出三藏記集[M].蘇晉仁,蕭煉子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5.
[8]季羨林.季羨林全集:第11卷[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
[9]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M].北京:團結出版社,2006.
責任編輯:馮濟平
On the Genology of Buddhist Literature
HOU Chuan-wen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266071, China )
Abstract:Some unique styles have been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and Indian Buddhist literature, such as gatha and stotra in poetry, jātaka and avadāna in narration, changdao and bianwen in talking and singing art. These styl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genre because of their unique features and profound infl uence.
Key words:Buddhist literature; genology; gatha; avadāna; bianwen
作者簡介:侯傳文(1959-),男,山東泰安人,文學博士,青島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東方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印佛教文學比較研究”(批準號:11BWW022)的階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08-29
中圖分類號:I0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7110(2015)06-0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