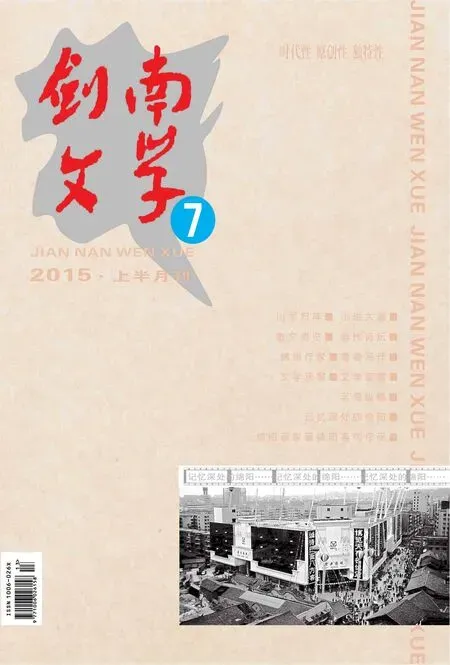困厄的局:《我彌留之際》的困境探究
■夏 君
一、引言
創(chuàng)作于1929 年的《我彌留之際》,是福克納的代表作品。該書故事情節(jié)簡單,但文字雋永,令人深思。其間對(duì)人類生存困境的描寫更是入木三分。作者描寫了艾迪對(duì)存在的追求和夢(mèng)想的幻滅,也用一個(gè)個(gè)的實(shí)例表現(xiàn)了交流的困境和語言的蒼白無力。文章將對(duì)《我彌留之際》中困境描寫進(jìn)行剖析,并分析作者關(guān)注困境命題的原因及意義。
二、《我彌留之際》的困境表達(dá)
困境,意即困難之境況,在《我彌留之際》一書中,本德倫一家遇到許多困難:貧困、水火、喪母、失貞、失財(cái)?shù)鹊龋鄬?duì)于這些外在的困難和損失,本文更多的關(guān)注內(nèi)心層面的困境:艾迪的存在困境和語言交流的困境。艾迪始終困惑自己的存在的意義,她終其一生在尋找這一命題的答案。本德倫一家貌合神離,語言失去了意義和作用,這種交流的困境也是每個(gè)現(xiàn)代人所面對(duì)的難題。
1.艾迪之困:存在還是毀滅?
死亡,將人們引入一場存在的困局。它仿若一張無形的網(wǎng),讓所有的生命無處遁逃。然而,倘若沒有死亡,存在又將何存?正是死亡,才使得存在的意義得以彰顯。正是死亡,才使得生命顯得珍貴。死亡無時(shí)無刻不在對(duì)存在提出嚴(yán)峻的拷問。面對(duì)死亡,如何將僅有一次的寶貴生命活得精彩?如何證明自己的存在?這些問題都在拷問著人們的存在處境。人們徒勞地在掙扎在這張困境的網(wǎng)中,卻無力掙脫。只有死亡,才能最終宣告存在困境的化解:生命已然逝去,與之依存的存在困境也必然不復(fù)存在。這一至死方休的存在困境,是所有人必須面對(duì)、卻又無法逾越的溝壑。
人既向死而生,存在的意義何在? 如何面對(duì)慘淡的人生?這便是艾迪·本德倫的困惑,也是她的存在困境。福克納筆下的艾迪·本德倫是文學(xué)作品中最偉大的悲劇命運(yùn)的女主人公之一。常有評(píng)論家把她和霍桑《紅字》中的海絲特·白蘭相比較, 也有評(píng)論家把她和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 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或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進(jìn)行比較。這些人物都感到被糟糕的人際關(guān)系或社會(huì)環(huán)境所困,急于找到某種方式逃脫。
艾迪,是一個(gè)極為獨(dú)立、堅(jiān)強(qiáng)的女性,她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夢(mèng)想著實(shí)現(xiàn)自己的理想和報(bào)復(fù),卻從未成功。她是所有被生活欺騙了的理想主義者的代表。她的父親告訴她,“活在世上的理由僅僅是為長久的安眠做準(zhǔn)備”,然而艾迪卻堅(jiān)持自己的信念。 她和其他教徒不同,她不相信死后的世界,這種信念更促使她找到活著的意義和幸福。她尋找存在主義者所說的“真正的存在”,試圖剝離所有的偽裝和假象。 她鞭打自己的學(xué)生,希望借助暴力成為他們 “秘密的自私的生活的一部分…永遠(yuǎn)地在(他們)的血液里留下了痕跡。”此后她嫁給安斯,希望婚姻和子女能緩解她的失望和焦慮,帶給她信念。 再次失望之后,她又找惠特菲爾德牧師作情人,然而這段關(guān)系,也以失敗告終。 現(xiàn)實(shí)和夢(mèng)想的鴻溝使她苦悶、絕望。 最終,她對(duì)所有的關(guān)系和理想都不相信了。 面對(duì)存在的困境,艾迪心如死灰,失去了對(duì)生活的夢(mèng)想和希冀——“于是我準(zhǔn)備可以死了”。 對(duì)于艾迪而言,“她跟死了沒什么兩樣”。生命是一場毫無希望可言的、等待死亡的漫漫之旅。她早就是個(gè)活死人了,她的后半生,不過是在等待甚至歡迎肉體的死亡。 她用自己的死亡,終結(jié)了對(duì)存在的追問,一場存在的困局,至此方才破解。
2.語言之困:交流表達(dá)的困境
柏拉圖在《理想國》里提出了三種床的理論,即:理念的床、木匠制作的床和畫家繪制的床。 他認(rèn)為畫家繪制的床是“影子的影子”。意即語言是事物的象征和近似物,而非事物的真實(shí)表達(dá)。 而真正的真實(shí)始終也是不可捉摸的神秘之物,很難用語言描述,要將人生、真實(shí)、自我種種用某個(gè)字眼精準(zhǔn)的表達(dá)出來, 著實(shí)是一件難事。佛經(jīng)當(dāng)中也有類似的表述:不可說,不可說,一說即是錯(cuò)。真正的真實(shí)只在心間,一旦說出來,便淪為實(shí)相了。語言是有局限性的,怎能用它限制真實(shí)呢?
《我彌留之際》 的核心主題之一就是人類交流的困境。這種交流的困境在《我彌留之際》中俯拾皆是,甚至體現(xiàn)于作品的結(jié)構(gòu)形式上,表現(xiàn)為多章節(jié),片段式的結(jié)構(gòu)。小說采用的多重視角,篇章結(jié)構(gòu)看似零散,每個(gè)人物都囿于自己的一方小小天地之中,沉浸在自說自話的意識(shí)流里。 這些人物一個(gè)接一個(gè)的出場獨(dú)白,互不牽涉地構(gòu)成全書的59 個(gè)章節(jié),他們所說的事件或許有相重合之處,然而并未融合為一個(gè)整體。 小說在形式上就給讀者帶來這樣一種感受,即,主人公們身處孤獨(dú)的困局之中,每個(gè)敘事者都限于自己的一方天地,無法與他人交流。
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一是找不到詞匯表達(dá),二是即使找到詞匯,言語和真實(shí)也具有不完全對(duì)等性。 人們很難用某個(gè)字眼精確的表述真實(shí)的想法。 簡言之,即表達(dá)的困境。
艾迪·本德倫在她對(duì)語言的懷疑論的論述說道:“罪啊愛啊怕啊都僅僅是從來沒有罪沒有愛沒有怕的人所擁有的一種聲音,用來代替直到他們忘掉這些言詞時(shí)都沒有也不可能有的東西。 ”她還說:“話語是最沒有價(jià)值的;人正說話間那意思就已經(jīng)走樣了。”
艾迪并非小說中唯一有這樣感受的人。各個(gè)角色在表述內(nèi)心想法和聯(lián)系詞語和現(xiàn)實(shí)之間都面臨一種困局,無法表達(dá)語言與真實(shí)的關(guān)系。 達(dá)爾鄙視語言,他總能不用說話就能了解別人的內(nèi)心。瓦達(dá)曼的一句話更能體現(xiàn)這一困境:“我媽是一條魚。”語言是如此的蒼白無力,只能說出一句謎一樣的話語。 論及語言和真實(shí)的關(guān)系,這種難解的感受,很好的傳遞了作者的意圖:語言無力,交流困難。
三、原因探究
為什么福克納要在《我彌留之際》中極力表現(xiàn)存在困境和交流的困境?究其原因,有以下三點(diǎn):一為現(xiàn)代主義潮流大勢(shì)所趨,二為迷惘的一代表達(dá)需要,三為家庭不幸的心理印記。
1.現(xiàn)代主義的潮流
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潮流興盛于20 世紀(jì)。 面對(duì)工業(yè)化的浪潮,現(xiàn)代主義作家們更多的關(guān)注人物的精神世界。 他們用現(xiàn)代人的哲學(xué)和心理語言重新提出了一個(gè)古老的疑問:人的存在到底是什么?在他們的文學(xué)作品中,更多的關(guān)注了人類的精神世界的孤獨(dú)、困惑和憂郁。 這種認(rèn)識(shí)體現(xiàn)在文學(xué)作品中,悲觀、孤獨(dú)、困境成為他們經(jīng)常表現(xiàn)的主題。
在薩特的《臥室》中,我們看到父女間、夫妻間總有一層隔膜,人與人之間仿佛隔著一堵無形的的墻。 在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中,我們看到一群囿于小鎮(zhèn)的現(xiàn)代畸人的形象。 伊麗莎白曾經(jīng)追求愛情和美貌,夢(mèng)想破滅后,心理失常;伊諾克“知道自己想說什么”,可是“永遠(yuǎn)不可能說出來”,只好形影相吊,一個(gè)人在屋子里自說自話。 在卡夫卡的《變形記》中,格里高利變成了一只大甲蟲,掙扎著、扭動(dòng)著,沒有人能理解他的話語。 在魯迅的《狂人日記》中,“我”內(nèi)心惶惶,無處可逃。
在這些現(xiàn)代主義作家的作品中,我們時(shí)常可以看到這種描述:孤獨(dú)、困惑、無法交流、無力抗拒、無處可逃。這些現(xiàn)代人的精神困境,也同樣表現(xiàn)在福克納的作品之中。

2.迷惘的一代的表達(dá)需要
福克納說,他的作品沒有一部能達(dá)到自己心中理想的程度。總有一些夢(mèng)想、一些情感在落筆之時(shí),在冰冷的文字間溜走了。作家借助文字表情達(dá)意。像福克納這樣的語言大家卻對(duì)語言表達(dá)提出質(zhì)疑,似乎令人不解。 然而,統(tǒng)觀福克納同一時(shí)代的作家,持這樣觀點(diǎn)的人并不在少數(shù):海明威在《永別了,武器》中借亨利之口,認(rèn)為例如“光榮”、“犧牲”、“神圣”等字眼,純屬欺人之談,毫無意義,都體現(xiàn)出戰(zhàn)爭的愚蠢。 羅·佩·沃倫的《國王的人馬》中的杰克也說“好人做事,騙子說話"。作為“迷惘的一代”,一戰(zhàn)帶給他們巨大的創(chuàng)傷,價(jià)值觀和夢(mèng)想的破碎讓他們有一種被生活虛夸的言辭欺騙的感覺。華麗的措辭不過是巨大的謊言,語言并不代表真實(shí)。 福克納借人物之口,表達(dá)的正是這樣一種語言的困境。
3.家庭的不幸
幾乎所有作家的作品中都有他們個(gè)人經(jīng)歷的影子。福克納也經(jīng)常在自己創(chuàng)作的人物、情節(jié)中留下自己生活的經(jīng)歷、觀察和形象。我彌留之際的困境表達(dá),和福克納自身的生活經(jīng)歷也有密切的聯(lián)系。
艾迪在生活中的原型有兩個(gè):福克納的母親和福克納自己。莫德·福克納是一位聰明、受過良好教育、有才華、意志堅(jiān)強(qiáng)的女性。她嫁給了一位一事無成的丈夫。福克納的父親,默里·福克納長期酗酒,經(jīng)常自怨自艾。 在88 歲的莫德病重之際,她問福克納自己是否會(huì)在天堂與丈夫默里相遇,福克納答道:“如果你不想見,就不會(huì)見”。她答道“好的,我從未喜歡過他。”艾迪理想的幻滅、對(duì)于死后世界的懷疑,在此可見一斑。
福克納自己的婚姻也是不幸的。福克納和埃絲特爾·奧爾德姆原本青梅竹馬,準(zhǔn)備結(jié)婚,但因女方家庭的反對(duì)而作罷。埃絲特爾拋棄了福克納,嫁給了富有的律師。這段婚姻持續(xù)的幾年之后,以離婚告終。 埃絲特爾帶著兩個(gè)女兒回到家鄉(xiāng),恢復(fù)了和福克納的關(guān)系。 盡管不太情愿,福克納還是和她在1929 年結(jié)婚了。不料埃絲特爾仍然沉浸在離婚的痛苦之中,酗酒嚴(yán)重,蜜月期間甚至試圖在墨西哥灣跳海自盡。這段不幸婚姻帶給福克納的情感印記,反映在他對(duì)作品中女主人的刻畫中。福克納婚后5個(gè)月,就創(chuàng)作了《我彌留之際》,艾迪的幻滅感和絕望、她對(duì)于語言的質(zhì)疑,或許是福克納自己內(nèi)心感受的體現(xiàn)。
四、結(jié)語
《我彌留之際》的命名,取自古老的《荷馬史詩》中阿伽門農(nóng)的故事,作者用這種方式,展示出一種亙古不變的主題:這些事情發(fā)生過,還會(huì)繼續(xù)發(fā)生。他們就是人類的生存狀態(tài)——內(nèi)心在苦苦掙扎。福克納大膽地展示著人生種種困厄的狀態(tài),實(shí)際上也是實(shí)現(xiàn)了作家對(duì)存在的追問和對(duì)人性的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