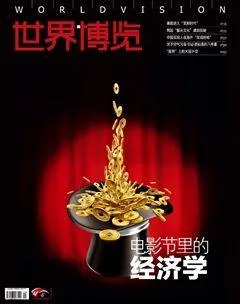美國進入“瓦解時代”
喬治·佩克
1978年光景,美國的精神變了。上世紀30年代之后的近半個世紀,美國社會孕育出了一個平民化的、穩定的、中產階級構成中堅的民主體制,社會鼓勵平民百姓追逐自己的凌云之志。有人把它稱為“羅斯福共和國時代”。盡管當時的美國社會也為戰爭、罷工、種族關系緊張、青年反抗社會等等所困擾,美國人秉持的基本處世信仰始終不曾動搖,盡管現實并不總是如此,但至少人們堅信如此:努力工作、遵守規則、教育子女,然后你就能得到回報——不僅給你滿意的生活,也不僅澤及下一代,而且還能得到社會的認可。
始于上世紀70年代末的衰落
這份不成文的“社會契約”附帶有各種條條框框,把黑人和少數族裔、女性、同性戀者摒除在外,即便沒那么嚴重,那么他們也至少處于不尷不尬的位置。好在這個國家有自我修補缺陷的利器:健康的民主機構,諸如國會、法院、教堂、學校、新組織、商務-勞務合伙人等等。60年代南方黑人掀起了民權運動,民主制度下的各個機構都支持這場非暴力的反抗,它們承認運動的主張契合道德和法律正義,退一步講,至少承認這場運動滿足社會安定的需求。“羅斯福共和國”充斥著種種不正義,但它有自我糾正的能力。
當年的美國人和現在一樣吝嗇、無知、自利、粗暴,也并不比現在的人更慷慨、公允、更富理想主義,不過,當年的民主制度下的各個機制總是能夠壓倒個人的貪婪,引導人們往更有益的方向發展。人性是恒定的,社會結構卻會改變,而且確實變了。
俄亥俄州的揚斯敦,一個世紀以來作為這座城市支柱的煉鋼廠以秋風掃落葉的速度一個接一個倒閉,隨之飄逝的,還有這片以工業為主的小河谷的5000個工作崗位,沒有新的東西填補這個空缺。加利福尼亞州的庫比蒂諾,蘋果計算機公司推出了第一臺個人微機“蘋果二代。全加州的選民們投票通過了第13號提案,從而掀起了一場抗稅運動,侵蝕了原本維系著全美最佳學校系統的公共撥款。華盛頓,一些公司耗費上百萬美金,組織起一個強力的游說團,否定自己曾答應的勞務和消費者法案——他們一度視之為自己肩負的社會契約的一部分。金瑞契(Newt Gingrich)以一名保守共和黨人的身份步入國會,心里懷揣著顛覆國會、然后在廢墟上建一個屬于他自己和共和黨的新國會的異志。在華爾街,所羅門兄弟公司創造出一項稱之為“抵押擔保證券”的全新金融產品,由此成為第一家上市的投資銀行。
去工業化、平均工資趨同、經濟的金融化、收入不平等、信息技術進步、資金涌入華盛頓、右翼抬頭……過去整整一代人的大趨勢,無不濫觴于70年代末。美國變得更接近企業,更遠離政府;更多個人主義,更少集體主義;更多自由,更少平等;更多包容,更少公平。云集于東、西海岸的銀行和高科技行業搖身成為積聚財富的火車頭,把原料的世界變為信息的世界,與之同時,美國的中部地區卻被掏空,銀行和高科技的繁榮并沒有澤及大眾。構成昔日中產階級民主制的各種機構,從公立學校、各種“鐵飯碗”,到繁榮的報業、實權在握的立法機關,都踏上了漫長的衰落之旅。我把它稱作“瓦解時代”。
美國精英背棄價值觀
有一種觀點認為,“瓦解時代”僅僅是回歸美國人生活的正常態。根據這種宿命論,美國一直就是開放自由的國度,在一個活躍的社會里,大家機會均等,對大贏家和大輸家都極度包容。
“羅斯福共和國”時代的規則是歷史的意外出軌:大蕭條、二戰、冷戰接踵而至,受此刺激,美國人不得不犧牲部分自由以換取安穩。如果沒有1933年的銀行破產,那么也就不會誕生把貿易和投行相割裂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如果美國經濟不是惟一經歷了二戰依然屹立不倒的那個,那么也就不會有中產階級的黃金歲月;如果不是外敵刺激催生出民族利益的共同信仰,那么也就不會有商務-勞工-政府界之間的協議;如果不是整個20世紀中葉始終緊閉的移民大門,那么也就不會有一個高度凝聚的社會。一旦美國的優越地位遭到國際競爭者的挑戰,加之70年代經濟遭遇重創,加之外部威脅減輕,這套社會信仰就走向了終點。全球化、高科技、移民潮加速了“瓦解時代”的腳步。
一切真的如宿命論般不可避免嗎?有道理,卻不盡然,因為它漏了一點:人的選擇。我們不僅要看到這些大的歷史因素,還要看到精英們——當年掌控著現已銹跡斑斑的民主機構的人——如何利用這些因素,唯有如此方能全面理解“瓦解時代”。
美國在戰后面臨的挑戰,讓共和、民主兩黨在國會里保持互相協作的關系,隨著冷戰逐漸走向終點,這種協作關系注定將隨之黯淡——不過,金瑞契和其他保守派在美國政壇散布惡語穢言和污濁空氣,絕對不是無可選擇的命定。金氏之流用這種下流手段謀取短視的一己私利,而隨著他們掀起的浪潮幫助共和黨重新占據眾議院的多數席位,這一套風行開來。今天,金氏早已成為過去時,但華盛頓的天已經變不回來了。在全球化競爭和地方減少投資的大背景下,揚斯敦的煉鋼廠終究逃不了倒閉的命運,但倒閉之后的這幅場景:收購商以垃圾債券的形式賤買閑置設備,掠奪走工廠剩余價值,留下一個無人負責的爛攤子,把失業工人扔給社會,讓他們自謀生路——卻完全不是不可避免的。
很多人提到過去一代經歷的全球化影響,卻鮮有人關注與之相伴的社會規范所發生的變化。美國精英們趁著深刻劇烈的經濟轉型當口,修改了一度約束自己的規則:國會曾經不允許,首席執行官的薪水曾經必須限制在平均職工的40倍,行業巨頭曾經不能鉆空子偷稅漏稅……現狀讓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相信,生活不過是一場可以作弊的游戲,所以明明供不起房也要貸款買房,反正沒錢就斷供好了。一旦社會契約千瘡百孔,一旦處世信仰失去意義,那么只有傻子才遵守規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