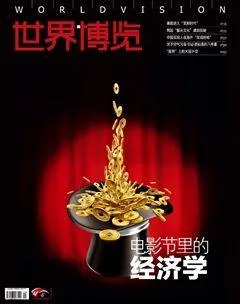未來世界電影核心會在北京?
云飛揚
北京國際電影節已走過了四個年頭,始終本著“融匯國內國際電影資源,搭建展示交流交易平臺”這一宗旨,以“國際性、專業性、創新性和高端化、市場化”為定位,與世界上其他電影節一樣是電影人參與的流動的盛宴,名與利的舞會,然而這樣確實是天壇與世界交流的好場所。
歷史上的黃金時代
中國電影人還是有福的,畢竟有那么多電影節歡迎他們去參與、去摻和、去折騰。如今內地的電影生態依然是畸形,基本上是10%的電影占有90%的投資,而且占有基本相仿的宣傳資源和票房收入,那么剩下的電影人們如何生存,除了少數電影可以上映之外,80%的電影要么自生自滅,要么去海外逛逛。一旦入圍大的電影節,或者在小的電影節上獲獎,就可以炒作一下,也能為下一部電影拉拉投資,甚至可以把在內地上映不了的電影找到海外買家,最起碼可以混個臉熟。
一回生二回熟,呼朋喚友之后,以后的電影也就好賣了。久而久之,這反而成了一條很可行、很具有操作的途徑,于是出現了很多電影節導演,他們在拍攝時根本不考慮、或者不以本土為回收成本的目的地,諸如蔡明亮、李康生、賈樟柯、侯孝賢等人都是如此。雖然國際上有400來個電影節,但某一些過于區域化,知名度太低,進入不了盤點的范圍,當然那些自持是著名導演們也未必會去。不過在這些五彩斑斕的電影節當中,盡管姹紫嫣紅不一般,還是能夠分出等級。
法國的戛納電影節在二戰之前的1939年成立,本身便是為了對抗威尼斯電影節,因為威尼斯電影節彌散著濃厚的獨裁者墨索里尼的氣息,從開始到現在,戛納和威尼斯就大張旗鼓的競爭,當然威尼斯人對中國電影人是相當的愛護。法國人的浪漫和開放,對于具有創新、叛逆、激進精神的導演來說就是天堂,最高獎項金棕櫚經常獎勵給有獨創意識、開拓精神的導演,比如大衛·林奇、大衛·芬奇、王家衛、索德伯格、昆廷·塔倫蒂諾等人都在此領得大獎,但由于評審會主席往往過于強勢,影響其他成員,因此經常出現爆炸性新聞,2004年的金棕櫚給了紀錄片《華氏911》就引起很大爭議。
如今,柏林國際電影節的影響稍微小于威尼斯及戛納,1951年創始于西柏林。最高獎項為金熊獎,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多數頒發給了伯格曼、安東尼奧尼、羅曼·波蘭斯基、戈達爾、特呂弗等新歐洲、新浪潮等大師,但是后來陷入停滯狀態,但是在東西德統一前后,在兩大陣容中特別的作用。不過,《白日焰火》和廖凡的獲獎又讓中國人感到柏林的熱情。
除卻三大之外,有特色的小城鎮也有發揮余地。眾所周知,洛迦諾是瑞士一個偏僻的小城鎮,可是她卻搖身一變躋身于世界文化的舞臺,無疑,這是國際電影節帶給了她如此殊榮。再者奧斯卡的天價廣告,短短的30秒竟然是180萬美元的代價,簡直超乎人的想象。當然這只是冰山一角,不過也足以窺探電影節這場文化盛宴與“圈錢運動”。
在獨立電影人的眼里,無疑圣丹斯和鹿特丹兩個電影節都是福地,前者瘋狂的支持獨立電影,而后者“以世界獨立電影為己任”。圣丹斯電影節專為沒有名氣的電影人和影片設立的電影節,由好萊塢巨星羅伯特·雷德福于1984年一手創辦,后來推出索德伯格和昆廷·塔倫蒂諾,這兩人的一鳴驚人要鳴謝圣丹斯。而鹿特丹尤其支持中國電影人,張元、韓杰等人都獲獎和受到資助。
電影節能夠衍生出電影策劃、制片、發行及產品開發等一系列的經濟鏈條,又集中了會展、廣告、旅游、通訊、媒體等相關行業的資源,輻射到金融、出版、咨詢、餐飲等多個相關領域,形成一個富有生機的電影市場。比如上海國際電影節,能夠依托大都市的優勢,開辟獨具特色的電影游。這樣電影與城市共生的方式,不僅讓世界了解了上海,而且使上海從這一窗口中了解外面的資源,從而獲得廣泛的文化、經濟等效益。而電影節旅游專線的開辟勢必會刺激餐飲,酒店,購物交通等的營業收入。可以說當下的電影節一直在演繹著“電影搭臺,經濟唱戲”的角色。
電影文化的橋梁作用
北京國際電影節也不例外。電影節國際性和高端化的定位再加上“帝都”的地理優勢使得電影節本身就充斥著巨大的文化、經濟賣點。比方說廣告代理,頒獎典禮的轉播權、明星服裝的品牌代言等方面都蘊含商業契機。以第三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為例,“北京展映活動共放影片近800部,放映場次達1600場,電影市場累計吸引了約1800家電影公司和機構的近7000名業內人士,總計167.98億元的市場簽約額,創下中國電影節展交易額紀錄。”這些數字顯示,電影節確實在扮演著“電影搭臺,經濟唱戲”這樣的角色,刺激著經濟以及城市各個相關行業的發展。除此之外,北京有其天然優勢,是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中心,若其抓好電影這一橋梁,拓展電影價值鏈條勢必會有不菲的收益,也極大促進了北京“東方影視之都”建設,鞏固了“全國文化中心”地位。
北京國際電影節是體現“國際水平、中國特色、北京風格”的世界文化交流品牌。電影文化是不容忽視的一個元素,通過電影文化向世界傳達國家文化,也是國家文化輸出的一種方式。比如戛納電影節著重追求電影的“藝術性”,柏林電影節則側重于青年政治題材,在選片和審片的過程中,“政治正確”是非常關鍵的指標。無可厚非,濃縮在影片中的價值文化也就潛移默化的散落在受眾之間。
北京國際電影節設立的“天壇獎”明確提出了“天人合一,美美與共”的核心價值,充分體現中國文化和中國元素。中國電影評論學會副會長王人殷說:“一個電影節沒有鮮明的價值理念就等于沒有靈魂和特色,就很難有大的突破。北京國際電影節推出這一理念,既顯示出國際眼光,又有中國文化根基,其核心價值是‘和諧。天壇獎的設立,標志著北京電影節日益與國際標準對接。”當然,北京電影節與國際接軌更大的好處便是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
電影是綜合藝術,是國際化,金融化,大眾化的引人注目的藝術形式。可以更通俗地說,電影是一種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比起小說有其獨特的優勢,它能夠通過畫面向全世界傳達一種思想一種理念,它的路子比小說要寬泛許多。因此電影界常常會有這樣的說法“只要電影節堅持藝術性,有創新能力,路子走的正,走的實,不斷積累口碑,對城市形象的提升效應會日益顯現。”戛納、洛迦諾、柏林如果不是電影節恐怕不會像現在這樣有這么大的吸引力,電影節本身的文化攜帶滲透著舉辦地的文化,無論是從前期策劃,中期運作還是后期推廣無處不依附著城市文化的影子。這樣一來,電影的傳播過程實際上也是文化傳播與消費的過程。附載在電影中的國家文化以及文化理念也就被合理地“偷渡”,以此,悄無聲息地走出國門,走向世界,而這樣的文化傳播也是最經濟,最震撼的一種文化傳播方式,簡單快捷,更具吸引力。endprint
吉亞諾普洛斯曾表示,“未來世界電影的核心會在北京”,我們有理由相信北京能夠成為世界電影的核心。四屆電影節,可以說北京國際電影節已經漸入佳境,早已具有了獨特的東方情思和神韻。北京國際電影節有其獨特的定位——中國特色、北京風格。這兩方面相結合便可以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電影文化節。沒有個性也就沒有吸引力,沒有吸引力也就沒有注意力。電影從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注意力產業,必須賺足眼球才能又好又快的發展。在電影又好又快發展的過程中不斷積累口碑打造品牌,提高影響力。這種影響力的提高也會使城市形象“增值”,打造魅力新北京,使北京以更開放的姿態走向世界。
電影節怎么也繞不過去的便是影片,好的電影節應該提供一個電影交流的平臺。比如影片《人在囧途之泰囧》小制作,小投資卻是大收益,歸根結底是迎合了觀眾的需求。快節奏下壓力越來越大的現代生活帶給人們不愿意承受的壓抑,而這種喜劇便應運而生,而且大受歡迎。相反的,有些大制作的影片,耗費巨資卻收效不明顯,電影節提供的這一平臺能夠有效地調節觀眾市場和電影市場的不平衡,以此使得電影良性發展。其實電影作為一種藝術一方面取悅于受眾,這就必須使電影迎合觀眾需求。一方面更加的“藝術化”,以滿足“學院派”中一些骨子里透出電影藝術氣質的“電影人”。電影節可以提供一個平臺,各類電影之間的交流,導演之間的交流,這無疑會使影片的質量得到提升,會使電影以更直接的方式進入受眾之中,通過這種優化和重組,形成健康而有序的國際電影市場。
當然,電影節對新人的培養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貧民窟的百萬富翁》中的男主角戴夫帕特爾,因為這部影片在電影節獲獎,他也水漲船高,身價倍增。再如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第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首設的“紀錄佳作”單元、“華語電影新焦點”單元以及“注目未來”國際展映單元,等等,都旨在發掘電影新人,推動電影新發展。由此可以看出電影節對發掘和成就新人的巨大作用。導演、演員在電影中處于一種很奇特的地位,最核心,最顯要也最引人注目。導演、演員對電影事業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電影歸根結底靠導演和演員來表現,發掘出一個好導演和一個絕佳演員可以說是電影事業的助力劑。
電影節不單單是電影的盛會,其實電影本身也不單單是電影。好的影片蘊含著人文關懷,社會熱點問題等,更依托于電影的價值觀通過畫面和故事來進行傳遞。當下是大融合的時代,世界性的問題不斷發生,又不斷地融合。而電影恰恰成了一個“橋梁”,將內部與外部的資源互換,以此達到雙贏。面對越來越開放,及其包容的時代,北京國際電影節依時而變,提供更加自由的平臺。在這平臺上不同語言、文化沖突,充分體現人們探討制作電影的各種新的方式。同時帶動風格迥異的電影人的成長,更好地交流和理解。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