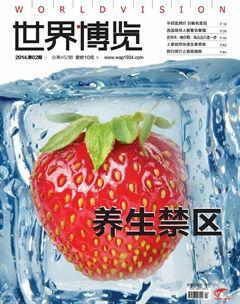衣錦還鄉(xiāng)
常凱
長這么大,我一次春運都沒經(jīng)歷過,所以每次年關前,看到外地同事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刷票,總有點瞧熱鬧不嫌事兒大的意思。老實講我對春節(jié)已經(jīng)沒什么感覺了,小時候盼著壓歲錢,買新衣服,現(xiàn)在連盼頭都沒有了,非要揪出一個來,或許就是希望春運開始后,北京可以恢復它許久未有過的稀松和安靜。我總想著,一年到頭,也該讓這座城市歇口氣了。
2006年,我當時的單位在白石橋,那里距離西直門很近,上下班路上堵個兩小時那是家常便飯。那一年的春節(jié),我印象特別深,我坐著一個叫916的公交車,從南四環(huán)一直殺進城,半個小時,司機連一剎車都沒踩。我站在他身邊,看著前擋風玻璃上,寬闊的二環(huán)路,看著草橋、西便門、復興門、車公莊,看著整個環(huán)線和主干路,連個賣煎餅的都沒有,宛如一座鬼城。這令我想起三年前的那個夏天,時而兵荒馬亂,時而靜如死水的北京城,很多人一邊在刮它的肉,一邊在抱怨,這肉太難吃了。
中國人過年講究四個字,衣錦還鄉(xiāng)。不論你是富甲一方,還是販夫走卒,過年了,報喜不報憂。那喜從何來呢?喜的基礎,就是車票。說出來都寒磣,我?guī)缀鯖]有在春節(jié)期間,進過火車站。好像僅有的一次,也帶著采訪任務,報社給的題目是,“發(fā)現(xiàn)春運里的美”。于是我就去了,結(jié)果舉著相機在北京站溜達一整天,屁都沒有。我感覺特別不公平,老天似乎沒有給我一雙善于發(fā)現(xiàn)美的眼睛。我看到的,只有疲憊的歸鄉(xiāng)人,老的老,小的小,還有一對對苦命鴛鴦,互相從保溫壺里倒熱水,泡方便面給對方吃。有一位滿臉黑油的打工者,坐在候車大廳的地上,磚地又滑又涼,他一個人很費力的想咬開那根香腸,努力很久,最后交給旁邊的工友,請他幫忙。最后是對方咬開了,然后還給他,看著他一口一口吃下去。我端著鏡頭,卻無法按下快門,因為這不符合,單位對于“美”的要求。很多人當時都能看到一個白癡似的矮個子,拿一個相機在他們身邊走來走去,明知道這個人是在拍自己,卻無力做出反應,他們太累了,只求背靠背的睡一小會兒。
北京從來都不是一座,固步自封的城市,只談新中國,五十年代響應周總理的號召,全國人民,齊心協(xié)力支援北京。自己家鄉(xiāng)再苦再窮,人才、物資、商鋪,甚至財政,全部輸血到中央,現(xiàn)在北京變成國際化大都市了,這里的人再說得便宜賣乖的話,確實有點兒理虧。那些整天在社交網(wǎng)站上,嚷嚷著懷念童年的所謂“小老北京”們,我想他們只是在宣泄一種不滿的情緒,如果這座城市真的回到以前,要啥沒啥,最先哭的估計還是他們。崔健有一句話形容的特別準確,我們這代人,“沒吃過什么苦,也沒享過什么福。”但是北京城,又的確可憐,因為在梁思成,在汪曾祺,在王世襄的心里,北京城不應該是這樣的,我們現(xiàn)在的活法,都不對。那我們又該去問誰呢?誰又和我們商量過嗎?
現(xiàn)在的北京,每到春節(jié)期間,我就記得,以前洗車15元,現(xiàn)在不敢洗,車都發(fā)臭了,長毛了也不能洗,否則價錢翻翻。盡管這也合情合理,但是我總覺得,這座城市,少了它本來最寶貴的一種精氣神。那種人與人之間的謙和、幫襯、松散和幽默感,有些人,想到的是如何榨干這座城市的財富和機會,能帶走便罷,帶不走的,寧可毀掉也不能落入他手。于是,我眼中的北京城,滿目瘡痍,他甚至不比上海、南京、廈門和深圳。那種本該屬于這座城市,最原始的結(jié)構(gòu)和色調(diào),灰飛煙滅,它在一年中的11個月里,就是一臺龐大的機器,翻來覆去的攪動著每個人的利益與希望。而在這僅有的1個月里,請讓它好好休息吧。
在這一個月,哪怕是半個月,甚至只有一個星期的時間里。你去想一想,你能為這座城市做點什么,哪怕只是一件不傷害到它的事,哪怕只是一件。也許我們現(xiàn)在需要做的,只是安靜的離開,或者只是安靜,就好了。當然,誰都不容易,你可以去埋怨任何人,如果你認為,那么做真的會對你,對這座城市有幫助的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