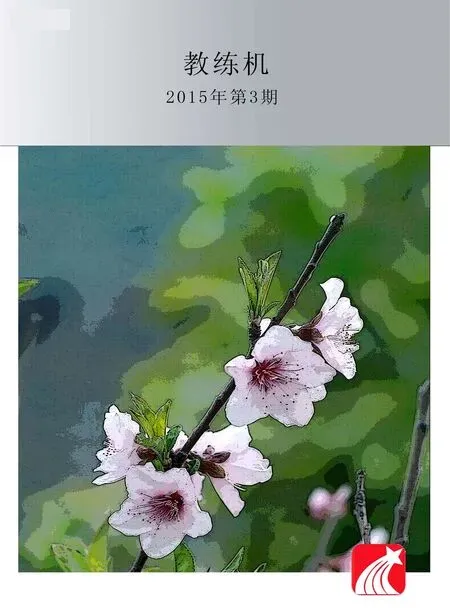教練機活動艙透明件故障分析研究
高 翔,胡建冬,呂曉雷,郭蕊娜,陳 琦
(中航工業洪都,江西 南昌330024)
0 引 言
活動艙蓋透明件是飛機機體的關鍵結構部件,作為飛行員觀察窗口,它不僅要具備優良的光學性能,還要具備足夠的承載能力,以在滿足飛行性能條件下可承受各種載荷并保護飛行員。由于軍用飛機使用載荷高、飛行速度大以及國內艙蓋玻璃使用材質、生產工藝、結構形式和維護措施等方面不足,艙蓋玻璃各類故障時有發生,嚴重時可能導致事故征候甚至飛行事故[1]。因而,在飛機生產、試驗、使用的各環節,對各種不利影響要高度重視,特別是對產生故障的飛機座艙透明件要進行系統分析,找出故障源和產生故障原因,并進行相應的改進。目前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航空有機玻璃被大量用于制備飛機座艙透明件,很多文獻對其不同條件下的斷裂行為及斷口特征的大量研究[2-7],可為后期類似故障提供分析借鑒。
某型教練機的一架試驗機,在飛行幾個架次后的例行檢查中,發現活動艙蓋透明件邊緣上多處出現裂紋和疑似腐蝕凹坑。該活動艙艙蓋透明件材料為YB-M-3,邊緣連接結構采用復合連接,即透明件周邊前后弧框處與D-QAS滌綸鋼邊條進行對接,用滌絲帶將滌綸鋼邊條與透明件邊緣進行包覆式膠接固化[8]。本文對發生缺陷的座艙進行了觀察與分析,并結合損傷區域的低倍形貌觀察,損傷區域和未發生損傷區域的金相組織觀察,斷口金相觀察和環境掃面電鏡(ESEM)觀察,紅外光譜試驗,以及制造、試驗過程調查,分析了裂紋、銀紋、腐蝕凹坑的性質與形成的原因,提出了改進措施。
1 試樣的選取及試驗方法
1.1 試樣宏觀與低倍形貌觀察
通過棱鏡排查整個座艙透明件,故障發生在活動艙蓋前艙,分布于透明件玻璃與滌絲帶膠接周緣,見圖1。為深入分析各缺陷的性質與形成原因,從故障機上分解前艙活動艙蓋透明件,并按故障類型取樣進行宏觀與低倍形貌觀察。

圖1 透明件故障分布
取自活動艙蓋前艙透明件底部拐角A區的故障試樣進行宏觀觀察,在透明件與膠接結合處,有機玻璃外側存在一處明顯的淡棕色凹坑,見圖2(a)。通過視頻顯微鏡觀察發現,凹坑形狀不規則,橫向最大尺寸約為17mm,縱向最大尺寸約為12mm。
透明件膠接結構底部B區、C區兩側外存在一排細小的裂紋,如圖2(b)。裂紋分布均勻,從膠接結構方向向透明件擴展,長度約為2~4mm。通過視頻顯微鏡對裂紋低倍放大進行觀察,可以看出存在大量裂紋及氣泡,裂紋分布在膠接界面處,各個裂紋長度相差不大。在裂紋中部位置,存在炸開形貌。大部分裂紋中間部分較深,兩側逐漸變淺,部分裂紋擴展到膠接結構的氣泡內,但并未發現氣泡破裂現象,可排除由氣泡破裂導致裂紋萌生。

圖2 故障宏觀與低倍形貌
1.2 環境掃描電鏡(ESEM)觀察
A區試樣凹坑放大ESEM形貌如圖3(a),經過對凹坑內部放大觀測,可見分布大量銀紋,具有一定的方向性,但并不完全平行,銀紋與銀紋之間有一定的交叉,見圖3(b)。從銀紋的方向性判斷是由溶劑、應力因素導致銀紋的產生,從而使該處強度降低,造成有機玻璃表面層剝落。
試樣B區膠接面處裂紋放大的ESEM如圖4所示,靠近膠接面處裂紋尺寸較大,距離界面處越遠裂紋尺寸越小。將裂紋放大觀測,見圖4(b),靠近邊緣膠接界面處裂紋的尺寸較大,裂紋向透明件方向延伸,裂紋中有碎屑填充,并且裂紋周圍有銀紋向四周擴展,裂紋末端較為密集,銀紋并未穿越裂紋,且均止于裂紋。

圖3 A區凹坑ESEM形貌

圖4 B區裂紋ESEM形貌
試樣C區膠接面處裂紋放大ESEM如圖5。可以看到,裂紋穿越了透明件、膠接面和滌絲帶,膠接面處裂紋的尺寸較大,透明件和滌絲帶上裂紋尺寸較小。

圖5 C區裂紋ESEM形貌
為了判定裂紋萌生位置,將試樣用砂紙打磨至0.6mm左右,進行ESEM觀察。可以看到,裂紋從膠接面處萌生,有的只向滌絲帶擴展,如圖6(a)所示形貌,裂紋最長約2mm;有的只向玻璃件擴展,如圖6(b),裂紋最長約1.4mm;有的既向滌絲帶擴展也向玻璃件擴展,如圖6(c),滌絲帶中裂紋最長約1.5mm,玻璃件中裂紋最長約0.6mm。試樣上裂紋是從滌絲帶與玻璃件的膠接面處萌生的,分別向不同的方向擴展。將裂紋末端放大具有如圖6(d)形貌。可以看到,裂紋末端處的銀紋較集中,并且向四周擴展,但是銀紋并未穿越裂紋,且均止于裂紋。

圖6 開裂密封圈斷口源區形貌ESEM
1.3 裂紋斷口形貌
為進一步研究裂紋的形成機制,選擇典型C區試樣的多處裂紋沿其擴展方向打開,從中再選擇四處典型形貌通過環境掃描電鏡進行觀察,四處典型形貌分別記為1#、2#、3#和4#。
首先對1#面斷口形貌進行了環境掃描電鏡觀察,其整體形貌如圖7(a),裂紋長度約1.4mm,深度約0.7mm。將斷口源區及擴展區放大,如圖7(b)。從圖中斷口的擴展形貌,可以判定,箭頭區域為斷裂源區。斷口源區(即裂紋)表面光滑,無夾雜、分層、氣孔、疏松等加工缺陷和腐蝕形貌,此處裂紋為非工藝缺陷和腐蝕導致的。斷口擴展區呈現放射性形貌,垂直于源區邊緣往外擴展。對2#、3#、4#斷口進行環境掃描電鏡觀察,其整體形貌及源區形貌與1#斷口具有完全相似的形貌,源區表面光滑,擴展區呈放射性擴展。觀察表明,斷口源區(裂紋區)無加工缺陷。
1.4 試樣紅外圖譜(FTIR)分析
試樣凹坑的紅外光譜如圖8(a),通過與有機玻璃基體紅外光譜圖8(b)對照發現,凹坑與有機玻璃基體的紅外光譜完全一致。說明凹坑與有機玻璃基體的成分一致,或者也可能由于腐蝕溶劑是酸、堿類有機溶劑,在紅外光譜圖上不顯示。

圖7 裂紋斷口源區形貌

圖8 紅外分析譜圖
2 分析與討論
2.1 裂紋性質與原因分析
裂紋形貌呈均勻排列,主要存在于活動艙蓋的前艙有機玻璃上,且裂紋集中在有機玻璃透明件與滌絲帶膠接界面外側部位 (見圖9),即應力集中部位。這種應力集中主要來自于艙蓋裝配機身不協調和后續試驗、使用等在開啟關閉時發生阻磨,從而使艙蓋的鉸鏈、鎖、開艙作動筒支架的傳力關系變成一個扭力關系,以及透明件在艙蓋裝配時的強迫操作,使得膠接邊發生應力集中。根據制造、試驗調查,本試驗機在裝配中有強迫行為,后續的檢驗、試驗、試飛等過程中開關次數頻繁。

圖9 透明件邊緣結構及裂紋區
透明件邊緣屬于膠接結構,如圖9所示,滌綸鋼墊塊和滌絲帶均與有機玻璃膠接為一體。就膠接而言有兩種基本形式:
1)粘接,依靠膠粘劑在粗糙的待粘接表面充分吸附,利用膠粘劑強度保證最佳粘附力。
2)溶接,依靠膠粘劑對其中的待粘接物的溶蝕滲透,使待粘物結合為一體。
本文研究有機玻璃透明件邊緣的膠接就屬于第二種形式。檢查故障區時發現的氣泡為多余的膠粘接。其形成為:在膠接過程中,膠接區加壓使得多余膠液外溢,在固化溫度作用下產生泡沫(氣泡),俗稱膠瘤。膠瘤本身不具備受力載體的能力,加上本身對有機玻璃透明件的溶蝕,使透明件局部有效承載厚度變淺,使之成為應力容易集中區。
另外根據試驗分析,B、C區試樣裂紋底端存在氣泡。通過視頻顯微鏡放大后觀察發現,兩個故障區的裂紋并未從氣泡處萌生,雖然有部分裂紋擴展進入氣泡,但未導致氣泡破裂,應與氣泡破裂造成應力集中導致裂紋萌生無關。通過環境掃描電鏡觀察發現,裂紋在透明件與滌絲帶對接界面處尺寸最大,向透明件及粘接層方向尺寸之間減小。其裂紋擴展存在三種不同情況,分別為向透明件方向擴展、向粘接層方向擴展及向兩個方向同時擴展。通過對比觀察B、C區試樣宏觀及視頻顯微鏡形貌,發現兩者形貌相近,為進一步研究其性質及形成原因,將裂紋沿其擴展方向打開,通過對斷口環境掃描電鏡觀察發現,裂紋斷口表面平整,具有明顯的休止線,未見除膠瘤(氣泡)外其它明顯的夾雜、分層、氣孔、疏松等缺陷。
綜合以上分析,可判斷裂紋斷面源區未發現夾雜、分層、氣孔、疏松以及加工缺陷,其形成應與加工損傷無關。裂紋細小,并排密布于透明件與粘接層界面處,不可能為一次或多次沖擊載荷而形成的過載裂紋;且斷面上未發現明顯的溶劑腐蝕形貌,由溶劑腐蝕導致裂紋的可能性也不大。裂紋斷面平坦,整個斷面呈扇形,休止線呈弧形,因此,該裂紋應為疲勞裂紋,是飛機飛行過程中,在交變循環載荷作用下,于透明件與粘接層界面處首先萌生并擴展,其主要原因是粘接層與透明件部分結合部位存在應力集中,加上多余的膠瘤,使該處的應力集中增加。裂紋末端銀紋產生于裂紋生成之后,為裂紋擴展過程中產生的二次裂紋。
2.2 凹坑銀紋性質與原因分析
從低倍形貌觀察可以看到,凹坑中有剝落部分,這種剝落是由銀紋發展而來。PMMA有機玻璃銀紋分為溶劑銀紋、應力銀紋和應力-溶劑銀紋[8]。溶劑銀紋是在溶劑作用下產生的,其雜亂無章,呈現無序狀態分布;應力銀紋是在沒有溶劑而只有外力作用下產生的,其垂直于應力作用方向,呈現有序分布;應力-溶劑銀紋則是在應力和溶劑共同作用下造成的,既有溶劑銀紋特點又有應力銀紋特點。通過對凹坑試樣的宏觀觀察、視頻顯微鏡及環境掃描電鏡觀察可以看到,凹坑的剝落處有銀紋,且此處銀紋既有方向性較強、呈有序分布的應力銀紋,也有短而密、呈魚鱗般閃亮、方向性不明顯、無序分布的溶劑銀紋,這是溶劑-應力銀紋的主要形貌特征。通過對凹坑式樣的紅外光譜分析,發現此處與有機玻璃基體的成分一致,但若與有機玻璃反應的溶劑是酸、堿等有機溶劑,紅外光譜圖中是無法反映的。由此判斷,導致銀紋的物質可能是對有機玻璃有弱腐蝕性的溶劑、水或其它液體。其應力來源與裂紋一致,主要是強迫裝配應力、艙蓋啟、關阻力;飛行過程中的艙內氣壓以及氣動力;還有透明件自身的殘余應力綜合作用。
另外,凹坑銀紋形貌在座艙前艙有機玻璃外側,集中在前艙底部拐角處,如A區。對于本文教練機座艙傾斜角較大,機艙表面上有液體流過,容易在此處聚集,如圖10所示,若該處密封失效就容易造成液體滲透。透明件分解前未能對密封情況進行觀察,但根據剝離密封劑較為容易,且凹坑處的剝離面光滑,可以斷定此處密封失效。通過對制造和試驗過程調查,飛機裝配過程中經常使用汽油對機身進行清洗,整機的淋雨試驗,以及試飛和使用階段環境中的清洗和雨水,均是外來液體從外出浸入透明件的方式。結合銀紋產生區域的應力特點和試驗分析,凹坑應是應力和溶劑聯合作用產生應力-溶劑銀紋,最后導致有機玻璃剝落。溶劑的來源為機身清洗,淋雨試驗或試飛階段維護等外來液體經失效的密封處滲入凹坑區造成。

圖10 艙蓋外來液體聚集示意
3 改進措施
1)將透明件的邊緣膠接固化工藝改進為預固化和固化,并實施分段、分次膠接[9],預固化后進行了膠接面修整,避免膠瘤產生。
2)透明件裝配于座艙骨架使用壓緊測力器[10]檢查貼合情況,避免需使用較大應力的透明件進行裝配;透明件裝配后的邊緣密封應嚴格按照工藝方法進行清洗、涂膠、整形、硫化,使得密封有效。
3)控制艙蓋上鉸鏈、鎖座等與機身連接的裝配協調精度,使座艙能在低阻磨下正常開啟關閉。
4)在原有透明件玻璃保護的基礎上增加保護罩,對座艙整體進行保護,并設計了用于活動艙的玻璃鋼保護罩,在飛機制造、試驗過程中對其進行保護。
5)對座艙維護過程中的溶劑使用進行嚴格控制,及時擦拭、干燥,避免造成透明件的浸蝕。
4 結 論
1)裂紋為應力下的疲勞裂紋,在透明件邊緣膠接界面處首先萌生,主要受透明件與滌絲帶對接界面應力集中的影響。這種應力集中主要來自于艙蓋裝配機身不協調,膠接界面產生的膠瘤,透明件生產后的殘余應力以及透明件在艙蓋裝配時的強迫操作,與有機玻璃中夾雜、分層、氣孔、疏松等工藝缺陷無關。裂紋末端銀紋為裂紋擴展過程的二次裂紋。
2)凹坑應為清洗、試驗、使用環境等過程中外來液體滲入密封失效的前艙拐角處后,有機玻璃殘余應力與外來液體聯合作用造成應力-溶劑銀紋,加上飛機玻璃的特殊受力狀態和苛刻的大氣條件,加速銀紋的擴展,導致的有機玻璃剝落。
3)針對故障原因,對透明件邊緣膠接固化工藝、透明件裝配定力、密封控制、座艙裝配制造和保護等進行的工藝改進,較為有效地消除了故障產生的因素。
[1]王新坤,魏世丞,徐濱士,等.飛機艙蓋玻璃故障分析實用理論技術[C].首屆透明結構材料及透明件學術會議論文集,2014:145-151.
[2]StartsevO V,Rudnew V P.Reversible moisture effects in the climatic ageing of organic glass [J].Polymer Degradation and Stability 1993,39:373-379.
[3]郭梅麗,劉貴春,張復盛,等.4號航空有機玻璃在大氣老化中表面開裂的原因分析[J].航空學報,1990,11(6):281-289.
[4]肖亮燦,李仲彰,杜玲儀,等.PMMA斷口形態及其破壞機理[J].高分子材料科學與工程,1990,(4):61-65.
[5]許鳳和.轟六飛機領航艙玻璃空中爆破斷口分析[J].材料工程,1995,(4):46-47.
[6]陳潔,厲蕾.飛機舷窗銀紋故障分析[J].失效分析與預測,2009,4(4):242-246.
[7]高翔,郭蕊娜,萬映輝.某型飛機前風擋有機玻璃裂紋故障分析和換裝[J].教練機,2011.4:50-55.
[8]許鳳和.高分子力學試驗[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8:92-94.
[9]高翔,陳文君,胡建冬,等.教練機活動艙蓋復合連接透明組件的研制[C].首屆透明結構材料及透明件學術會議論文集,2014:59-64.
[10]高翔,萬建平,胡建冬,萬映輝.一種用于測試有機玻璃與飛機座艙骨架裝配貼合力的裝置[P].中國專利:CN 201320373389.5,2013,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