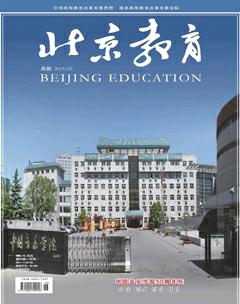試論大學章程的修訂程序
洪煜++郭德紅
摘 要:章程修訂是凝練辦學特色、落實依法治校的關鍵。章程修訂中要把握穩定性與適應性、權威性與民主性、規范性與特殊性這三對矛盾。目前,教育部核準的47所高校章程在修訂程序上仍不夠周密,需發揮校長在章程修訂中的關鍵作用,加強學阿術委員會、校內學生、校外群體在章程修訂中的民主參與,為章程修訂集思廣益。
關鍵詞:依法治校;大學章程修訂
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隨著依法治國成為我國新時期的施政綱領,在高等教育領域,通過章程推進依法治校的呼聲日益高漲。縱觀教育部核準的47所大學章程,存在著特色不夠突出、表述不夠嚴謹等問題。因此,章程制定并不是一勞永逸,而是要通過修訂不斷加以完善。章程修訂關乎各所大學辦學特色的凝練和依法治校的落實。
本文以上述47所大學為研究對象,參考借鑒國外大學章程修訂的有益經驗,試圖為完善我國大學章程修訂程序提供理論支撐和政策建議。
章程修訂的原則
1.穩定性與適應性
章程作為學校管理制度的總綱,需保持一定的穩定性,若章程修改過于頻繁,無疑會給校內外群體留下朝令夕改的印象,阻礙章程的有效落實。但章程保持穩定絕不意味著一成不變、抱殘守缺,尤其是目前的辦學環境瞬息萬變,大學章程不僅要固化現有的優秀制度,更要體現社會適應性和戰略前瞻性,成為大學的基石而非掣肘。實際上,部分美國大學章程的修訂次數多、周期短。例如:密歇根州立大學的章程自1965年生效之后,分別在1977年、1979年、1980年、1990年、1994年、2000年和2003年進行了修訂,其中僅1994年便修訂了2次;麻省理工學院章程(2008年3月修訂)與上次章程修訂的時間相隔一年半。[1]
2.權威性與民主性
從國內外大學章程的修訂程序來看,由最高權力機構修訂章程已成通例,其合理性在于通過最高權力機構賦予章程修訂的權威性。但過于強調權威可能導致章程的修訂成為一家之言,使其由于缺乏民主參與而失去合法性。若章程的修訂不是基于校內群體的民主共識,而是來自校內最高權力機構的行政指令,或是個別領導的“拍腦袋”決策,這種修訂即使程序上合法,在具體執行中也會阻力重重,甚至使大學誤入歧途。
3.規范性與特殊性
大學章程不僅是校內制度規章的綱領文件,而且是規范學校自主辦學的法律依據,我國大學的章程都需經過教育主管部門的核準。從本質上看,大學章程是教育法規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大學章程作為法律文件,必然不能與上位法相沖突,這就要求章程的修訂具有嚴謹的法律規范性。但章程絕不是上位法的“復本”。實際上,上位法只能作出原則性的規定,落實到章程的具體條款,還需考慮每所大學辦學歷史、獨特校情和現階段的具體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修訂,以適應各所學校的辦學實際。
國內大學章程的修訂
章程的修訂需回應3個關鍵問題:一是章程在什么情況下修訂?二是誰有權提出章程修改動議?三是按照哪些程序審核章程修改動議?
目前核準的大學章程中,包括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在內的17所大學章程將制定和修訂放到同一條款中,如清華大學規定:“本章程的制定和修訂經學校教職工代表大會討論、校務會議審議、黨委會全體會議討論審定后,報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核準”。這種表述行文簡潔,但只回應了第3個問題,對前2個問題未予明確,難免不夠周全。下文以上述3個問題為脈絡,分析比較各校章程中有關修訂的條款。
1.章程修改的條件
對于章程修改的條件,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浙江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這6所學校章程作出了具體規定,一般來說,出現以下情況時需要修改章程:一是章程所依據的法律發生變化或章程與上位法相抵觸;二是學校合并、分立、更名等;三是學校辦學宗旨目標、類型層次、體制機制等發生重大變化。
2.提議修改的主體
章程的修改不同于章程的制定,必須有一個啟動環節,即由某一主體提出修改章程的動議。在已核準的大學章程中,有25所大學的章程對于誰有權提議章程修改作出了規定。
從提議主體的數量來看,25所大學中,有16所大學的章程修訂提議主體僅有1個,6所大學規定了2個提議主體,章程修訂提議主體的數量在3個以上的僅有3所(上海交通大學、中山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山大學的修訂提議主體最多,包括校長、教代會、二級單位和學代會。從出現的頻次來看,有17所大學的章程規定由校長或校長辦公會議提出章程修改動議,10所大學的章程可由教職工代表大會提議修改,5所大學的章程可由黨委常委會或黨委代表聯名提議修改,有2所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礦業大學)設置了專門機構負責章程修訂,值得注意的是,僅有上海交通大學規定章程的修改動議可由學術委員會提出。對于修改草案的形成,吉林大學規定黨委常委會提出修改動議后,由校長辦公會形成修改草案;中山大學則要求提出章程修改動議的單位或個人應附交修正案建議稿。通過上述分析,可歸納出我國大學章程修改的5種啟動模式:一是由校長啟動章程修改。章程修改的動議僅由校長或校長辦公會提出,以東南大學為代表。此種模式的優點在于充分發揮校長在完善章程中的主觀能動性。校長作為學校的行政首腦,對于學校運行狀況和前景規劃最有發言權,將章程的修改提議權賦予校長,更能發揮校長作為“教育家”的作用。但這種模式對于校長專業化的要求較高,需要大學校長能夠把握高校辦學的基本規律,形成獨具特色的辦學理念,并需要具備堅定不移的執行能力。二是由教代會啟動章程修改。章程的修改動議僅由教職工代表大會提出,以武漢理工大學為代表。一般來說,教職工代表大會五分之一以上的代表聯名,即可提出動議并啟動修改程序。這種模式的優點在于充分體現章程修訂的民主性,落實了教代會民主監督、審查評議的職權。此外,這種模式還能與章程制定的程序相耦合。大多數學校的章程修改依舊沿用了章程制定中的“提交教代會討論、校長辦公會審議、黨委審定”這一程序,若由教代會提出章程修改動議,則可與“提交教代會討論”有效對接,形成完整的制度“鏈條”。但這種模式需教代會就章程修改達成統一意見,在遇到某些爭執不下的重大問題時,可能會滯礙改革進程。三是由黨委啟動章程修改。章程的修改動議僅由黨委或黨委常委會提出,以吉林大學為代表。這種模式的優點在于章程的修訂由掌握校內最高權力的黨委來啟動,增強了章程修訂的權威性;但另一方面,黨委既是章程修改的提議主體,又是最終審定主體,可能導致章程修訂過于注重黨委的作用,使得校內其他群體的意見難以充分表達。四是設置專門機構啟動章程修改。以北京大學為代表。這種模式的優點在于通過常設機構加強章程修訂工作的專業性,這些專門機構還承擔了其他與章程相關的任務,如北京大學的章程委員會負責對章程進行解釋、組織制定實施細則、監督章程執行情況等,這種做法可以避免章程的相關工作出現“多頭管理”的問題,有利于將章程落到實處。缺點是校內師生群體不能直接提出章程修改意見,章程的修訂須經過章程委員會這一中介,可能變相削弱了師生群體的發言權。五是由多個主體啟動章程修改。章程的修訂可由兩個以上的主體提議,如中山大學章程規定,章程的修訂動議可由校長、教職工代表大會、五個以上二級單位、學生代表大會和研究生代表大會向校長辦公會提出。這種模式的優點在于為章程的修訂建立了多種渠道,有利于及時發現問題并予以糾正;其缺點是可能導致章程的頻繁修改。
3.修訂的審核程序
在提出修改動議之后,章程修訂進入審核程序。正如前文所述,目前大部分學校章程的修訂參照制定過程,采用了“提交教代會討論、校長辦公會審議、黨委審定”這一程序。部分學校在修訂程序上有所創新,如華東師范大學充分發揮理事會在章程修訂中的作用,規定:“章程修訂方案須提交學校教職工代表大會討論、校長辦公會審議,并經學校理事會提出意見,學校黨委會審定后,報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核準,核準后,向本校和社會重新公布”。這一條款有兩點值得借鑒:一是在章程修訂中,理事會代表校外利益相關群體提出意見,擴大了征詢面,提高了科學性;二是強調章程核準之后的公布環節,保證章程修訂的公開透明。
國外大學章程修訂的程序
國外大學章程的修訂程序主要有以下幾個共同點:
1.章程修訂須由最高權力機構審定
美國大學的最高權力核心一般是董事會,修改大學章程的權力掌握在董事會手上,如耶魯大學章程規定:“在董事會常規或特別會議上,出席會議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數成員投票通過即可對本章程進行修改、補充、廢除、增加或刪除”,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南加州大學、康奈爾大學、密歇根大學均有類似規定。英國大學章程的修改不僅要校內最高權力部門審定,還需經過樞密院批準,如牛津大學章程規定:章程由高級教職員全體會議批準通過,同時由樞密院審議批準。德國大學的最高權力機構與英美大學有所不同,但同樣享有修改章程的權力,如慕尼黑大學的評議大會作為校內最高決策機構,享有制定和修改大學法規和章程的權力;柏林洪堡大學章程的修改需經過學術評議會同意和校董會的批準,最后提交柏林州政府中負責高校事務的主管部門批準。[2]
2.章程修訂須遵循民主公開的原則
國外章程修訂的民主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章程的修訂必然是校內各群體充分討論之后達成共識的結果,如柏林洪堡大學的章程規定:“本章程的修訂須經全校大會多數成員批準,修訂案原則上必須至少經過兩次大會討論;章程修訂后應在官方公報中重新公布”。新西蘭梅西大學的章程修訂是根據“在北帕墨斯頓校區、惠靈頓校區以及奧爾巴尼校區為學生代表和所有員工舉行副校長討論會,從討論會上收集的反饋意見、個人和團體的提案”。[3]二是最高權力機構的人員構成和議事程序具有民主性,如慕尼黑大學的最高權力機構—評議大會的人員構成中,教授代表36人,其他學術人員代表12人,學生代表12人,非學術人員代表6人。莫斯科大學的最高管理機關是學校代表大會,由科研教育工作人員、其他領域工作人員代表和學校學生組成,代表大會成員的選舉規則由學校學術委員會決定。來自學術委員會的代表成員不應超過總人數的50%。在議事規則方面,較普遍的做法是采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如美國大學的章程修訂需提前通知董事,并征得董事會多數成員(一般為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三是國外大學通過公開透明來加強學校各群體的民主參與。例如:康奈爾大學在章程修訂過程中,把更改的章程條款一一列出,校內成員有異議的,可以向董事會咨詢機構咨詢。劍橋大學章程詳細記錄了每個修改條款、修改過程和投票結果,修改的生效日期在Michaelmas雜志的“Reporter”欄目中公示。[4]
3.部分大學規定了由誰提議章程修改
例如:倫敦大學的理事會由校長、各學院的領導、高級研究學院院長組成,有權就章程和條例的修訂向董事會提出建議;慕尼黑大學評議會作為評議大會休會期間所設的常務機構,有權擬定大學法規和章程中需要修訂部分的修訂草案,供評議大會研究討論;莫斯科大學的學術委員會由擔任主席的校長、副校長、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學校董事和選舉代表(通過學校代表大會不記名投票選舉產生)組成,有權對學校章程提出修改建議。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章程可經理事會、評議會或執行委員會提議,并以評議會和執行委員會在場投票的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方式或以理事會在場投票的簡單多數通過的方式進行修訂。
此外,還有部分大學指定了專門的人員或機構負責章程修訂。例如:巴黎第一大學的章程規定:行政管理委員會下設章程理事會,負責處理修改章程的請求,對請求進行預審,并在一個月內提出意見,行政管理委員會需在其后一個月內審議章程理事會提出的意見。東京大學章程則規定由校長負責章程修訂。
借鑒和建議
1.章程修訂應發揮大學校長的作用
大學校長作為總攬全局的行政首腦和溝通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樞紐,在學校改革發展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關鍵角色。大學校長是否具備先進的辦學理念和過人的勇氣魄力,往往能影響一所大學的興衰成敗。縱觀國內外大學發展歷史,一流校長建設一流大學的案例屢見不鮮,如查爾斯·艾略特之于哈佛大學,威廉·哈珀之于芝加哥大學,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學,梅貽琦之于清華大學等。因此,在章程修訂中,也應當發揮大學校長的戰略前瞻和引領統籌的作用,使其辦學理念能通過章程的修訂落實到具體辦學活動中。那么如何更好地發揮大學校長的作用?筆者認為關鍵是要推進大學校長的職業化,改革完善大學校長的選聘制度,通過充分授權為其履職創設良好制度環境,確保大學校長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以教育教學為核心的高校改革發展中,真正成為一個“教育家”,而不是“政治家”“社會活動家”。
2.章程修訂要體現學術權力的地位
國外大學的學術組織和學術權力在章程的制定和修改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德國大學實行教授治校,以柏林洪堡大學為例,其章程修改需經過學術評議會的同意;英國大學普遍采取學院制,學術權力居于學院治理的中心,而學校作為學院組成的“聯邦”,在章程修訂中十分重視學術權力;美國大學的民主集中制保障了學者通過學術委員會等制度渠道參與學校治理和章程修訂。反觀已核準的47所大學章程,僅有上海交通大學章程規定學術委員會有權就章程修改提出動議。目前,我國大學普遍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政治權力和行政權力占據了高校權力核心,在大多數已核準的章程中,校長和黨委在章程修改中的權能較大,而學術組織和學術權力在章程修訂中缺乏制度渠道。若不加強學術組織和學術權力在章程修訂中的權能,不僅教授治學無法落實,甚至可能因為黨政權力在章程修訂中的一家獨大,導致大學行政化弊病越演越烈。
3.章程修訂應聆聽校內學生的聲音
學生作為學校辦學活動的參與主體和作用對象,其就讀經驗的滿意與否、個體發展的水平高低是反映學校人才培養質量的重要指標,很難想象一所不被大多數學生認可的大學是一所好大學。同樣的,一個不被學生群體認可的大學章程也談不上是一個好章程,甚至不是一個合法、有效的章程。因此,在大學章程的修訂中必然要重視校內學生的聲音,為學生群體的意見表達廣開言路。不少國外大學的最高權力機構中往往有一定比例的學生代表,在章程修訂中能為學生權益代言。我國大學雖受限于現行辦學體制,難以將學生代表吸納到權力核心中,但也有學生會、研究生會等制度化的民主監督評議機構,建議在章程修訂中充分發揮學生會、研究生會的作用,為學生參與學校章程修訂提供有效渠道。
4.章程修訂應征詢校外群體的意見
校友和關心學校發展的社會人士是推動大學發展的重要力量,在章程的修訂中征詢校外群體的意見,有幾點好處:一是校外專家的閱歷豐富、眼界開闊,不局限于學校現有的管理體制和辦學思路,更能為章程的修訂提供新視角、新思維;二是校外專家與學校改革發展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更能中立客觀地為學校章程的修訂出謀劃策,提出中肯意見;三是在章程修訂時廣泛征求校友意見,有利于提升校友的歸屬感。目前,教育部已頒發《普通高等學校理事會規程》,理事會將成為校外人士參與學校管理的重要媒介,而在已核準的47所高校章程中,華東師范大學將理事會作為章程的審議主體之一,這種做法值得其他高校借鑒。
綜上所述,章程的修訂是學校管理體制自我完善的必要過程,是結合學校實際落實依法治校的關鍵環節,在修訂過程中既要維護章程的權威,更要加強校內外群體的民主參與,應鼓勵多方參與,可參考中山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的做法,賦予學術委員會、理事會、教職工代表大會、學生會和研究生會提出章程修改動議的權力。在審議環節要發揮校長統籌協調的作用,通過召開校長辦公會或設立專門機構等方式受理修改動議,對于意義重大、切實可行的修改提案予以批準并啟動后續審定程序。這種制度設計既體現了程序性和權威性,又有利于集思廣益,在章程草創的初期,能最大限度借助集體智慧完善章程,為推進依法治校和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打牢根基。
參考文獻:
[1]陳立鵬,陶智. 美國大學章程特點分析[J]. 中國高等教育. 2009(09).
[2]張國有. 大學章程(第2卷)[M].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10.
[3]陳立鵬,李娜. 新西蘭國立大學章程文本的要素分析及啟示[J]. 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 2011(01).
[4]于麗娟. 國外大學章程文本探析—以英國牛津大學和美國康奈爾大學為主要案例[J]. 高教探索. 2009(01).
(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
[責任編輯: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