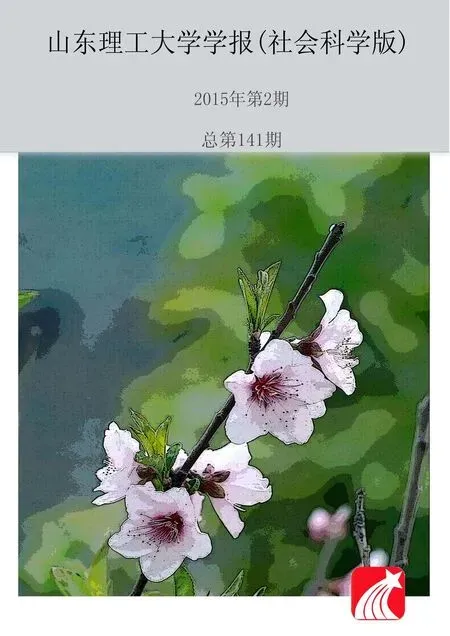西方美學暴力審美線索探討
張 星 晨
(上海大學數碼藝術學院,上海201800)
西方美學暴力審美線索探討
張 星 晨
(上海大學數碼藝術學院,上海201800)
在西方美學的三個重要時期,很多學者對暴力審美問題均有涉及,主要觀點有:暴力如果以善的名義出場或以善的名義存在,暴力便具有審美價值;暴力的形式可以與其反映的政治、道德的內容分離,可以單獨被欣賞;虛擬中的暴力或與觀眾保持遠距離的暴力,也是可以被欣賞的;美無處不在,任何事物都具有審美價值,暴力也不例外。這些觀點對現在正確認識暴力審美問題仍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美學;暴力;審美
當前,電影與網絡游戲等新媒介中存在較多的暴力內容,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與爭議。關注與爭議的焦點是這些暴力行為對青少年教育的負面影響,以及暴力行為在文藝作品中存在的意義及審美價值如何。本文試圖在梳理西方美學脈絡的基礎上,發現有關暴力審美的線索,以期從美學角度和暴力審美歷史的角度,探討暴力審美的價值。
一、本體論美學時期的暴力審美線索
從古希臘開始一直到16世紀,關于審美和藝術的理論是在本體論視野下展開的,主要探討的核心問題是“美的本質是什么?”這一時期隨著笛卡爾提出“人能不能認識美”的問題而結束,隨之轉向美學的認識論階段。
在美學的本體論階段,暴力并非站在美的對立面。雖然這一時期的審美對象是那些努力接近理想美的內容,但西方思想體系中對于理性和思辨的追求卻恰恰體現了美的相對性。
(一)古希臘時期
在柏拉圖眼中暴力是屬于丑的范疇,但美與丑的界定卻是相對的。他在《大希比阿斯篇》中敘述了蘇格拉底與希比阿斯的對話:“和人類相比之下,最美麗的猴子也是丑的;和女性相比之下,最美麗的壺也是丑的;……如果我們拿女性和女神相比,不也如拿壺和少女相比嗎?最美麗的少女和神相比不也是丑的嗎?”[1]183此時,暴力作為“丑”的現象之一也進入了審美范疇。
在柏拉圖的觀念里,真善美是一體的。所以不但智慧、理性是美的,正義、公正等內容都是美的。但是,美分為上界之美與塵世之美:上界之美是真善美的集合體,是美的本身;塵世之美是對上界之美的追思,但由于受到肉體、感官的束縛而需要有一個對真善美追求的過程。此外,柏拉圖也將形式從塵世之美中抽取出來作為追求上界之美的通道。在柏拉圖的眼里,上界之美是意義美與形式美的統一。
亞里士多德的美學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詩學》中。他是柏拉圖的學生,部分繼承了柏拉圖美學思想的內容。如他與柏拉圖都認為存在一個客觀真理的世界。但與柏拉圖不同的是,亞里士多德認為這一世界并不存在于上界,而是存在于人世間;真理是不能脫離現實而存在的,只能存在于紛繁復雜的現實之中。獲得美的方式不僅僅通過對理想的形式、內容的追求,也可以通過對“不美”之物的體驗獲得,如通過悲劇人的情感可以得到凈化。而暴力恰是悲劇的重要表現元素之一。
亞里士多德的悲劇分為情節、性格、思想、言詞、形象和歌曲六個部分。其中情節是處于首要地位的。悲劇之所以驚心動魄、千轉回腸,就在于情節的“逆轉”和“認知”,暴力在此是觸發“逆轉”和“認知”情節的原因。
(二)中世紀時期
在中世紀,當神學凌駕于一切哲學之上,美便成為上帝的一個屬性,并作為神學本體論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進而顯得更具神秘主義色彩。
在柏拉圖構造的世界中存在不完美和罪惡,世間諸多的“瑕疵”是對絕對真理、完美世界的拙劣模仿。而在基督教的理念中世界是上帝的杰作,是完美無瑕的。真善美都統一于上帝的光環之下,即便是罪惡也都與上帝的善和美有關系,暴力也在其中。
在這一時期,因精神上無限靠近神性而使暴力彰顯出崇高美感的藝術作品,有三個基本主題:受難、殉道、死亡。
受難:在耶路撒冷耶穌被自己的門徒猶大出賣,受到羅馬統治者不公的審判及虐待,最后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此時的基督經歷了其生命中最為殘酷、暴力的劫難,受盡了屈辱與迫害。
殉道:是指對基督受難過程的模仿。為了見證對上帝信仰的忠貞,接受暴力和殘酷的肉體折磨甚至被處死都是殉道者所要面對的。但是對于殉道者的描繪,卻與基督有明顯的不同。基督受難時的形象往往是被扭曲的不成人形,對肢體的殘害旨在帶給觀者以巨大的痛苦,從而彰顯出上帝的仁慈與偉力。而對于殉道者的描繪,雖然也有血腥暴力的場面,但殉道者的神情與動態卻安詳、平和得多。有的甚至以優美的構圖、舞蹈般的動作來展現殉道者從容赴死的決心,以號召觀者效仿。
死亡: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現代,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對社會群體,死亡都是避之不及的話題。但是在中世紀,卻形成了“死亡勝利”的藝術表現題材。在生活中追隨上帝的人可以平靜甚至喜悅地面對死亡。然而在世間如果犯過罪惡并不能被上帝寬恕的不法之徒,被認定為終將會走入地獄。“死亡勝利”的藝術表現便是在告誡此類人及時悔悟,否則便是死亡在前。同時也是培養普通人對地獄及各種受罰的酷刑的畏懼之心。
直至今日“死亡勝利”的主題在各種媒體內容中還有顯現,但其用意與中世紀時期已完全不同,更多的是通過對死亡的表現來使情緒達到宣泄與釋放的目的。如,數字游戲《但丁·地獄》將原著揭示人類罪惡、借地獄展現現實問題的內容,轉變為同死亡、地獄進行戰斗,贏回愛人生命的旅程。死亡此時只是一種形式,觀眾藉此來滿足感官上的刺激和情緒上的宣泄,并進一步演化為一種“死亡嘉年華”。
(三)文藝復興時期
文藝復興是一個使藝術重新獲得榮耀的時代,整個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傾向都在努力擺脫上帝的影響而直接呈現出人的美和藝術家的價值。如果談到整個文藝復興時期在藝術上所呈現出的特征,那就是“模仿自然”。這里的模仿不是像古希臘時期提倡的機械的、毫厘不差的模仿,而是尊重自然、超越自然甚至改善自然的模仿。如這一時期關于藝術的“鏡子說”。明確提出“鏡子說”的是達芬奇,他認為:“畫家的心應該像一面鏡子, 永遠把它所反映事物的色彩攝進來, 前面擺著多少事物, 就攝取多少形象。”[2]183不過,達芬奇的“鏡子”并非機械地反映自然,而是反映感官與經驗背后更為深邃的東西。莎士比亞也多次通過鏡子來比喻藝術對自然的模仿,但是他對于這對關系更為準確的描述是其“中道說”。
達芬奇及其他中世紀學者并沒有或者極少有對暴力內容或現象進行直接的表述,這與文藝復興時期藝術總體上追求平和、安靜的藝術風格相同。但中世紀藝術家們卻將科學引入藝術,開始以科學理性的解剖刀解讀人們的身體和生活,身體的結構被公開地展示、講授。在人性的光輝還沒有開始照耀時,冰冷的理性開始左右精英階層的嗜好,以至于形成病態的迷戀。其中一個較為突出的現象就是廣泛地開始對人體進行解剖研究,人體解剖圖、解剖手稿大量出現在藝術家的作品中。然而,更為有趣的是以人體解剖為題材的作品也開始大量出現,并最后形成一個固定的表現主題。后來對單純表現人體自然結構的熱情逐漸退去,藝術家與公眾開始欣賞被解剖的人體之“美”。在科學與理性的外衣下,解剖展示這種暴力行為具有了欣賞價值。
二、認識論美學時期的暴力審美線索
哲學在認識論時期主要的美學問題不再是“美得本質是什么”,而是“識別美的意識是怎樣的”及與審美意識相關的各類問題。美學在這一時期的主要成就集中在審美理想、審美心理學、審美與各種意識的關聯問題等。
在這一時期,暴力進入審美領域的兩個條件已經初露端倪,分別由休謨的“形式組合帶來美感”和霍布斯的“善就是美的”觀點體現出來。此外,在伯克與康德談論崇高與理性之美時,我們也可以發現暴力的蹤跡。
(一)休謨:形式引發美感
休謨是英國經驗主義的集大成者,在他的觀念中“美”是源自人的內心而不是審美的對象,對象的形式(秩序與結構)與人面對審美對象時所產生的情感有關。對象本身并不產生美感,對象的形式卻可以引發人的美感。
不同的形式組合可以激發人的各種審美感覺,休謨舉例說,藝術表現中經常出現的“驚奇”就不是描繪對象本身固有的屬性,因而我們可以重新組合、運用這些形式,創造出虛構的故事與畫面來傳達驚奇的美感。
(二)霍布斯:欲望先于善,美丑則是有跡象預期善惡的東西
早期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霍布斯將美看作善的一種。他認為美并非存在于實物的本質或者比例中,而是因為其滿足了人類的欲念(需求)而具有美感。美感的產生在于人的欲念得到了滿足。對于對象來說,有用的就是善的,善的就是美的。
通過善的跡象喚起美感,即便這一跡象是附著在暴力身上。這說明我們并不是面對所有的暴力行為都會感到厭惡,而是只要其中有我們可以接受的善的跡象,我們就可以接受暴力,甚至去參與暴力。這也是暴力進入審美領域的前提條件之一,即帶有善的目的。
(三)伯克:恐怖是崇高的一個來源
另一位值得我們關注的經驗主義學者是伯克。他提出崇高與美是不同的心理感受,故而將崇高與美區分開來。伯克認為崇高來自于“自我保護”的本能,面對兇險與我們不能控制的情況時,我們便產生恐懼,乃至于痛苦的感覺。顯然這與美感是不同的。但他也肯定了這類場景可以轉化為美感的源泉。因為痛苦的感覺都伴隨著快感,當我們意識到險境與恐怖不能傷害到自己時,潛意識地就會去咀嚼甚至欣賞這種快感。他在其著作《崇高與美》中作了如下的描述:“當危險或苦痛逼迫太近時,不可能引起任何欣喜,而只有單純的恐怖。但當相隔一段距離時,得到某種緩解時,這時如同我們日常經歷,就有可能是欣喜。”[3]37
(四)康德:合目的的形式與理性的崇高之美
康德是哲學認識論時期重要的美學研究者,他不但以獨特的思路分析了美的質、量與美的各種關系,還在前人基礎上進一步論證了美學在哲學中的合法地位。更為重要的在于康德是現代主義美學的奠基人。
康德提出了“合目的的形式”的概念,認為某些藝術作品即便采取暴力的形式也可以帶給人愉悅的美感。“美是一對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在它不具有一個目的的表象而在對象身上被知覺時”。“構成鑒賞判斷的規定根據的,沒有任何別的東西,而只有對象表象的不帶任何目的(不管是主觀目的還是客觀目的)的主觀合目的性”。[4]57藝術之所以具有感人的表現力,就在于其形式,而內容居于次要的地位。藝術并非是對現實的模仿,藝術的感染力源自于其形式。藝術作品的內容因素,如道德、政治、歷史等都可以從作品中抽離出來,而作品的藝術性并不減少。藝術的形式本身就有一定的內涵,這一內涵可以脫離所表現的內容而存在,但又不同于快感并能夠帶給人深刻的想象。康德稱其為“合目的的形式”。正是基于這一判斷,現代主義尤其是現代主義藝術流派中的抽象主義和構成主義,徹底將形式抽象出來阻斷藝術形式與其現實內容的聯想,使藝術創作極大地擺脫了現實內容的束縛。
在暴力可以成為審美對象的諸多觀念中,廣為接受的便是暴力的形式可以脫離其內容而被欣賞。暴力的行動、暴力的破壞力甚至暴力所形成的創傷,都可以被以“美”的方式單獨表現。在后人的實踐中,尤其是后現代主義的藝術類型都十分樂于采取暴力的形式來標榜其作品的獨特性,以致當代影視理論中出現“暴力美學”的概念,繼而又在文學、戲劇、繪畫領域中得到共鳴。暴力美學重要的美學特征之一即為:暴力的形式可以被人單獨欣賞,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即東方的武俠電影。暴力的形式在此類電影中都已被舞蹈化處理,甚至暴力的工具——各種殺人的武器也被罩上了幻想般、傳奇般的色彩,對此,我們從《臥虎藏龍》《十面埋伏》《新龍門客棧》等優秀的東方動作電影中可見一斑。
康德在《批判力批判》中也談論崇高之美,他將崇高劃分為數學式的崇高和力學式的崇高兩種類型。“對于數學式的崇高……與其說是某個更大的數的概念,不如說是作為想象力的尺度的大的單位”,比如“地球直徑對于我們所知道的太陽系、太陽系對于銀河系都是如此”。[4]101對于力學上的崇高,他這樣闡釋:“險峻高懸的、仿佛威脅著人的山崖,天邊高高匯聚挾帶著閃電雷鳴的云層……諸如此類,都使我們與之對抗的能力在和它們的強力相比較時成了毫無意義的渺小。但只要我們處于安全地帶,那么這些景象越是可怕,就只會越是吸引人;而我們愿意把這些對象稱之為崇高。”[4]107
康德對崇高的理解恰恰道出了我們可以接受暴力產生美的原因,也道出了含有暴力因素的藝術作品創作的價值指向。外力的強大超出了我們的接受范圍,在這種暴力下自身顯得渺小和無力。但是我們并不是完全沒有反抗,我們通過勇氣、智慧、毅力可以抵擋甚至擊退暴力,而其源泉就來自于道德。
這一判斷正暗合了當代暴力影視、游戲作品的創作思路。主角在暴力面前是渺小的,但通過自身的努力和外界的幫助以暴力或著非暴力的方法最終戰勝了暴力。
(五)17世紀、18世紀暴力的美學呈現
正如美國導演斯坦利·庫布里克在其電影《亂世兒女》(Barry Lyndon)中描繪的那樣,17世紀、18世紀是一個既文雅又殘酷的世界,上流社會的甜美生活與暴政的斷頭臺在這一時期并存;呈現理性主義光輝的盧梭、席勒與展現人性陰暗面的薩德侯爵在這一時期并存。在巴洛克極盛時期艷麗的矯飾下,一種暴力的、無拘無束的激情在暗流涌動。
1.殘酷的理性。在康德關于理性的結論里,絕對理性是超越自然的存在,而其中卻隱含著理性的陰暗面。很多研究者都將這種超越人性的存在看作暴力的誘因。“理性獨立于自然,以及人需要相信自然是善的,雖然自然之善并無根據。人的理性能將任何之善化為它隨意左右的觀念,也就是說使它自己獨立。然則有什么能夠防止?非但事務,連人也被簡化成被操縱、剝削、修理的對象?誰能防止邪惡的理性計劃毀滅他人的心靈?”[5]269從感性的層面看,面對自然時人類是渺小的。但因人具有理性而使自己擁有了可以超越、獨立于一切局限的感覺。人的精神能夠超越一切感官。但是這種理性的自由卻又表現出了黑暗的一面,這就是沒有約束的理性會背離人性需求。它因其獨立性而可以任意左右人的觀念與認知,使非理性、非善的行為,甚至暴力的行為穿上合理的、善的外衣。理性對感性的超越本身就具有極大的風險,當理性不受拘束時人性就會面臨扭曲的風險。
2. 哥特風格——浪漫主義對丑惡和暴力的拯救。在這一時期“扭曲的理性”突出表現便是科學幻想小說的肇端。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被譽為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幻想小說,其創作時代正是科學技術開始滲透進人們生活的時候。人類具有了探索世界的強大工具和勇氣,但同時也因自我認知與社會發展的脫節而感到無所適從。對于科技的恐懼和中世紀理想生活的向往開始彌漫于文學藝術的各個方面,其突出表現為“哥特式風格”的藝術創作。哥特式小說流行于18世紀、19世紀,內容多為恐怖、暴力、神怪以及對中世紀的向往,因其情節多發生在荒涼、陰暗的哥特式古堡(流行于18世紀英國的一種建筑形式)中而得名。故事充滿懸念,通常以毀滅為結局。哥特小說通常以吸血鬼、血腥犯罪、恐怖墓穴、腐爛尸體等為題材。同時,代表“停尸間情色主義”的墳場詩和喪葬挽歌也頗為流行。
3.崇高——對自然的敬畏與臣服。崇高是西方美學中的古老命題,對崇高的論述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他稱悲劇帶來崇高,以恐怖、巨大而且超出人接受范圍的力量來體現。在文藝復興時期也出現了大量的對于暴風雨、斷崖、驚濤駭浪等場景的描繪。18世紀人們對異域的探索,使人們身臨其境地感受到了自然的魅力與威力。這一時期的廢墟詩學以及大量出現的關于廢棄遠古建筑、異域景色的繪畫都表現出崇高意味。
三、語言論美學時期的暴力審美線索
語言論美學,是指西方19世紀末期發生“語言論轉向”以來盛行于20世紀的以語言問題為中心的美學,包括俄國和英美“新批評”、心理分析美學、分析美學、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存在主義和新歷史主義等美學流派。其主要特征有三個:第一,語言取代理性而成為美學的中心問題;第二,放棄美的本質及其他本質問題,注重用語言學模型去分析審美現象;第三,放棄美學的系統化和體系化追求,認可具體問題的文本闡釋。
語言論美學集中體現于所謂的后現代美學思想。后現代美學的宗旨是“反美學”,不僅反古典美學,也反現代美學,因為以倡導非中心化、反本質主義和元敘述為特征的后現代主義者不容許美的原則、美的本質和美的概念的存在。他們認為世間不存在統一的審美標準,也不存在美學非美學、藝術非藝術的界限。因而他們竭力反對“為藝術而藝術”,并為通俗藝術和通俗美學正名。他們致力于將藝術從形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象牙之塔中解放出來,強調日常生活的藝術化、審美化,強調審美觀念的無處不在。他們主張美的多元論,否認絕對的美、唯一的美的存在,為各種各樣美的存在留下了生存空間。自然,暴力作為一種審美現象在后現代美學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了。難怪所謂的暴力美學發端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那正是后現代思潮興盛的時候。正因為此,也有人將暴力美學理解為是后現代美學的產物。
當然,暴力并不僅僅存在于后現代藝術中,在藝術發展的不同時期暴力元素都一直有所表現。但暴力在藝術中的出現是有條件的,往往具有上下文語境。在天主教藝術當中的暴力表現,如拷打、受難的慘烈場面往往象征著對信仰的篤信。人們之所以接受它們也是因為這些行為在其心中先入為主的圣潔性。神話中的暴力也轉化為傳統而被接受。
暴力在藝術中存在的條件之一是“虛擬性”。它首先是不真實的。但它并非是完全虛擬的,只是在觀者的接受心理上認定它的虛擬性。對于中世紀的宗教篤信者來說,觀賞殉教者的受難就會認定其是圣潔的,會得到力量。然而圍觀異教徒的處刑,卻抱著獲得刺激和宣泄的目的。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心理活動。
到了當代,藝術中的暴力卻有了脫離上下文語境的傾向。例如,英國的弗蘭西斯·培根的作品,還有安迪·沃霍爾關于電刑和交通事故的系列作品等。暴力的表現已經獲得了自由,不再需要宗教、歷史、神話的背景,藝術家可以表述個人的噩夢。
四、小結
通過對西方美學發展歷史及理論問題的簡要梳理,我們發現,在西方美學的三個重要時期,對暴力審美的問題均有涉及,其中某些重要的認識和觀點,對今天我們正確認識暴力審美問題仍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價值,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暴力以善的名義出場、以善的名義存在,使暴力具有審美價值。這里的善是指欲望的滿足,但不是低俗的欲望,而是崇高的欲望。就是說,以善為目的而行使的暴力是能夠被人接受并欣賞的。
第二,暴力的形式可以單獨被欣賞。休謨認為審美對象的形式,或不同的形式組合可以產生美;康德提出“合目的的形式”概念,認為藝術的感染力在于其形式。因此,暴力的形式與其反映的政治、道德的內容可以分離,暴力的形式可以單獨被欣賞。這或許是暴力美學的理論根據所在,因為當前影視作品中的暴力美學就是突出暴力的形式美。
第三,神話中的暴力、宗教信仰涉及的暴力,是可以被人接受和欣賞的。如觀賞殉道者的受難被認為是圣潔的。
第四,虛擬中的暴力或與觀眾保持遠距離的暴力是可以被欣賞的。正如伯克所言,我們覺得一件事物恐怖,但這件事不能控制或傷害我們時,這些印象就會變成快感。[3]37
第五,在西方體現悲劇、崇高等審美范疇的藝術作品中,暴力往往是觸發劇情逆轉的重要元素。
第六,后現代美學認為美無處不在,任何事物都具有審美價值。這使藝術作品中的暴力表現獲得了充分的自由。
[1][古希臘]柏拉圖.文藝對話錄·大希比阿斯篇[M].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2][意]達芬奇.筆記[A].伍蠡甫.西方文論選(上卷)[C].朱光潛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
[3][英]伯克.崇高與美——伯克美學論文選[M].李善慶譯.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0.
[4][德]康德.批判力批判[M].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5][意]翁貝托·艾柯. 美的歷史[M].彭淮棟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
(責任編輯 李逢超)
2014-11-23
上海市大文科研究生學術新人培育項目(B.16-0127-12-003)。
張星晨,男,山東濟南人,上海大學數碼藝術學院博士研究生。
B83-0
A
1672-0040(2015)02-009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