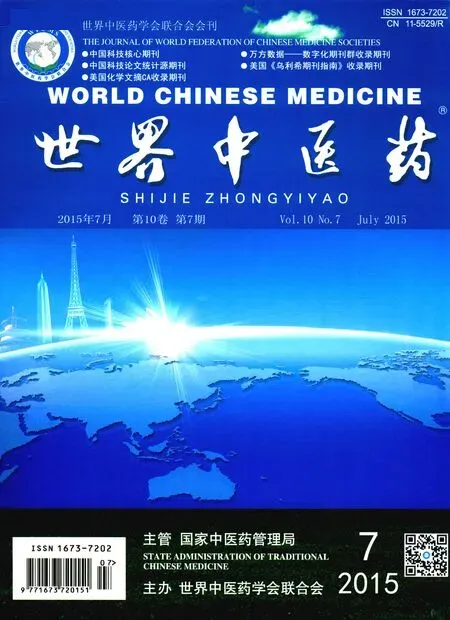蔣健以救破湯為主治療偏頭痛經驗探討
崔 晨 耿 琦 李敬偉 李 欣 楊曉帆 周 丹 蔣 健
(1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上海,201203;2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岳陽醫院,上海,200437)
救破湯出自清·陳士鐸《辨證錄·頭痛門》,由川芎一兩、白芷一錢、細辛一錢組成,水煎服,主治劇烈頭痛。原文云:“人有頭痛如破,走來走去無一定之位者,此飲酒之后,當風而臥,風邪乘酒氣之出入而中之也。酒氣既散,而風邪不去,遂留于太陽之經。太陽本上于頭,而頭為諸陽之首,陽邪與陽氣相戰,故往來于經絡之間而作痛也。病既得之于酒,治法似宜兼治酒矣,不知用解酒之藥必致轉耗真氣,而頭痛愈不能效,不若直治風邪能奏效之速也。”原書描述其療效為“一劑而痛止,不必再劑也”。陳氏另一著作《石室秘錄·完治法》中論頭痛亦以救破湯治療,惟加大其劑量,以川芎三兩、白芷一兩、細辛一兩,用黃酒一升煮之,一醉而愈,云其可大散終年累月、邪深入于腦之頭痛。蔣健教授臨證喜用大劑量救破湯為基本方治療偏頭痛。偏頭痛痛勢劇烈,且反復發作、病情頑固,治療較一般頭痛更為棘手。茲列舉其臨床驗案數例,介紹其以救破湯為基本方治療偏頭痛的臨證思維,期與同道探討。
1 驗案舉隅
1.1 案1 某,男,45歲,2010年11月9日就診。主訴:偏頭痛20余年,加重1年。曾就診于外地多家西醫院,服用多種藥物(具體藥物不詳),收效欠佳,遂來求治。腦血流圖示腦供血不足;頭顱CT、心電圖檢查未見異常。頃診右半頭痛呈陣發性發作,發作時間無規律,近1年發作明顯加重。發作時,右半頭部疼痛,呈脹痛或刺痛,伴頭暈,或有沉重感、飄然感。大便不成形但排出困難,小便無力。舌淡紅,苔薄,舌下靜脈迂曲,脈細弦。西醫診斷:偏頭痛;中醫診斷:偏頭風;治以活血行氣、祛風止痛為主,輔以平肝、活血化瘀通絡之法;以大劑量救破湯加減化裁:川芎 40 g,白芷30 g,細辛3 g,白芍30 g,當歸 15 g,威靈仙12 g,僵蠶12 g,蜈蚣2 條,全蝎粉(吞)2 g,天麻 12 g,鉤藤12 g,川牛膝15 g,茯苓15 g,7 劑。囑患者全蝎粉每日分兩次吞服。二診(12月3日):患者居于外地,就診不便,故停藥數日。服上藥后頭痛幾止,僅偶有輕微頭痛,發作頻次、程度較前均明顯好轉。停藥后亦無明顯反復。唯大便不成形、排出困難及小便無力感依舊,舌脈同上。原方加山藥15 g,蒲公英30 g,14劑。2011年2月20日電話隨訪:患者訴自去年服用中藥21劑后,迄今再無偏頭痛發作,僅于事多煩心時偶有頭部輕度不適。此為中藥治療前所未曾有過。按:本案偏頭痛日久,久病多瘀,舌下靜脈迂曲亦可佐證;頭痛伴脹、暈及飄然感,乃肝風之象,故以大劑量救破湯緩其疼痛外,取止痙散、天麻鉤藤湯平肝熄風、活血化瘀通絡。服藥3周,多年所苦得以解除,停藥亦未見反復。
1.2 案2 某,女,36歲,2011年10月7日就診。主訴:左半頭痛連及左耳疼痛近1年。患者因工作繁忙,自覺壓力較大導致偏頭痛頻發。頃診左側偏頭痛,每周發作2~3次,每次發作可持續1 d,痛勢較甚連及左耳,伴惡心。近5月來,月經周期為21 d左右,量可,夾血塊,經期腰酸。其偏頭痛發作與月經無明顯關聯。舌淡紅,苔黃,脈細。西醫診斷:偏頭痛;中醫診斷:偏頭風;治以活血行氣、祛風止痛為主,輔以溫經通絡調經;以大劑量救破湯加減化裁:川芎50 g,白芷30 g,細辛10 g,當歸50 g,吳茱萸10 g,肉桂 10 g,炮姜 15 g,威靈仙 10 g,黃芩 12 g,全蝎粉(吞)2 g,7劑。二診(10月18日):患者因外出未能及時復診,停藥4日。訴上藥后,偏頭痛減輕,主要表現為發作頻率降低,原每周發作2~3次,現約每隔10 d發作1次,唯頭痛持續時間及疼痛程度同前,舌脈同上。原方加僵蠶12 g,地龍12 g,蜈蚣2條,制川烏、制草烏各6 g,7劑。11月29日門診隨訪:二診藥后患者偏頭痛即止,未見反復。按:本案偏頭痛痛勢較甚,痛及左耳并伴惡心。故在救破湯基礎上,加大劑量當歸,既可加強活血止痛之功,又達補血調經之效;吳茱萸、肉桂、炮姜補火助陽、溫經通脈,以助散寒止痛、調經之力;更以全蝎、僵蠶、地龍、蜈蚣蟲類搜風通絡以加強止痛之力。
1.3 案3 某,女,53歲,2012年10月9日就診。主訴:偏頭痛數十載,加重2年。患者自幼即有偏頭痛,偶有發作,與情緒無明顯關聯。2011年初,行左側腦動脈血管瘤手術,術后偏頭痛明顯加重,發作次數較前頻繁,程度亦有加重。于他處服用中藥調理多時,效果平平,遂來求治。頃診患者偏頭痛每周平均發作4~5次,疼痛程度較甚,另伴有左側頭皮麻木及左半身麻木。舌淡紅,苔薄,脈細弦。西醫診斷:偏頭痛;中醫診斷:偏頭風;治以活血行氣、祛風止痛為主,輔以和營通痹之法;以大劑量救破湯合黃芪桂枝五物湯加減化裁:川芎50 g,白芷50 g,細辛3 g,地龍 12 g,全蝎粉(吞)2 g,蜈蚣2條,生黃芪 30 g,桂枝 12 g,白芍 30 g,土鱉蟲 12 g,澤瀉 30 g,甘草9 g,7劑。二診(10月19日):服藥后,患者頭痛發作頻率未見降低,但頭痛程度稍有減輕。訴近日稍有嗜睡,舌脈同上。原方去澤瀉,川芎增至60 g,加威靈仙12 g,當歸15 g,延胡索30 g,菖蒲12 g,肉桂粉(吞)2 g,7劑。三診(10月26日):服上藥期間,頭痛程度減輕三成;一周發作次數減為3次。唯左側頭皮麻木依舊,舌脈同上。進一步加大救破湯之劑量:川芎 60 g,白芷 50 g,細辛6 g,地龍 12 g,全蝎粉(吞)2 g,蜈蚣粉(吞)2 g,生黃芪 30 g,白芍 30 g,土鱉蟲12 g,威靈仙12 g,延胡索30 g,當歸30 g,淫羊藿15 g,肉桂粉(吞)2 g,7劑。四診(11月2日):患偏頭痛發作頻度及疼痛程度均減一半,左側頭皮及左半身麻木減輕八成,舌脈同上。原方加桃仁12 g,紅花12 g,生地黃12 g,7劑。五診(11月9日):服上藥后,偏頭痛改善尤為明顯。服藥至今,頭痛發作頻度及疼痛程度共減九成,左側頭皮及半身麻木感幾除。續予原方7劑以資鞏固。六診(11月16日):偏頭痛止,左側頭皮及半身麻木亦止,此后繼續調理。按:本案患者偏頭痛多年,頭部手術后痛勢加重。首診后疼痛稍減,此后加大川芎、細辛用量,加延胡索、威靈仙、地龍、全蝎、蜈蚣等通絡止痛、活血化瘀之品后,偏頭痛改善尤為明顯,此或與救破湯等藥物量效關系、藥效積累有關。服藥35劑后,偏頭痛止,左側頭皮及半身麻木亦止。
1.4 案4 某,女,58歲,2014年6月3日就診。主訴:偏頭痛30余年。患者頭部兩側絞痛,每于飲酒后痛甚,曾多處求診無果。MRI、腦電圖等多項檢查未見明顯異常。常自服阿咖酚散(成分:阿司匹林230 mg,咖啡因30 mg,對乙酰氨基酚126 mg)以緩解疼痛。近年來疼痛逐漸加重、持續時間延長,阿咖酚散從每次1包逐漸加量至每次4包,每日3次,頭痛仍無法緩解,遂求治于中醫。患者吸煙、飲酒史近20年。頃診,偏頭痛每日均發作,痛甚,伴惡心、嘔吐、冷汗淋漓,痛時服用阿咖酚散4包,無明顯療效。舌偏紅,苔黃膩,舌下靜脈迂曲,脈細。西醫診斷:偏頭痛;中醫診斷:偏頭風;治以活血行氣祛風、緩急止痛為主;以大劑量救破湯合芍藥甘草湯、止痙散加減化裁:川芎 60 g,白芷 50 g,細辛 10 g,當歸 30 g,白芍50 g,炙甘草 12 g,全蝎粉(吞)2 g,蜈蚣粉(吞)2 g,7劑。二診(6月10日):上藥服至第2~4劑,頭痛程度始見減輕。現每日除早晚2次服用中藥外,只需晨起加服4包阿咖酚散即可,其余時間頭痛雖有,但尚可耐受,無需加服阿咖酚散。另患者訴每次服用中藥后,即刻冷汗出,伴胸悶、心悸等不適,需平躺約5~10 min后可緩解,不平躺則惡心欲吐,舌脈同上。蔣健教授慮此現象可能為細辛不良反應,遂將細辛減至6 g,加制川草烏各12 g,7劑。三診(6月17日):上藥期間,冷汗出、胸悶、心悸等不適未再發生。唯晨起頭痛,服用中藥及4包阿咖酚散后可緩解,其余時間再無頭痛。續予原方7劑。此后患者因家中事務繁忙、路途遙遠等原因未能堅持治療。10月26日經電話隨訪,患者評價服用中藥期間,頭痛頻次、程度明顯好轉,頭痛僅晨起發作。停藥后頭痛雖有反復,但與服用中藥之前比較,頭痛程度減輕,僅服用阿咖酚散即可緩解。按:本案屬嚴重偏頭痛患者,病史多年,痛勢頗劇。首診投以大劑量救破湯、芍藥甘草湯及止痙散等峻猛之劑,劑量已臻極限。其療效評價主要包含兩點:一是服用阿咖酚散每日12包減少到每日4包;二是服用中藥21劑后,頭痛發作頻度減少,程度減輕。值得注意的是,本案首診用細辛10 g,患者出現出冷汗、胸悶、心悸、不平躺則惡心欲吐等不適,當細辛減量至6 g后,上述不適未再出現,可視為細辛的藥物不良反應。
2 討論
2.1 救破湯中川芎、白芷、細辛乃治療頭痛要藥蔣健教授臨證之所以喜用救破湯,因其認為救破湯所用川芎、白芷、細辛乃治療偏頭痛一般頭痛之要藥。從病因病機來看,頭為“諸陽之會”“清陽之府”,又為髓海所在,偏頭痛病因病機盡管十分復雜,凡風、寒、濕、熱等外邪上犯巔頂阻抑清陽,或肝、脾、腎功能失調,致使寒凝、風動、痰阻、瘀滯等,皆可導致偏頭痛的發生。然歷代醫家公認,外邪侵襲、氣機不暢、瘀血阻絡為偏頭痛的主要病因病機。救破湯具有辛溫升散、活血行氣、祛風止痛之功,正可針對偏頭痛的主要病機。從藥物組成來看,川芎祛風行氣活血以止痛,白芷祛風通竅以止痛,細辛祛風散寒通竅以止痛,正如陳氏所云,可“直治其風邪,能奏效之速也。”其中以“川芎最止頭痛,非用細辛則不能直上于巔頂,非用白芷則不能盡解其邪氣,而遍達于經絡也(陳士鐸《辨證錄》)”。救破湯藥物雖少,然則集歷代治療頭痛藥物之大成。《是齋百一選方》之都梁丸、《古今醫鑒》之芎芷散、《世醫得效方》之四生丸、《張氏醫通》之芎辛湯、《仙拈集》之風熱散、《衛生寶鑒》之石膏散、《辨證錄》之芷桂川芎湯、《普濟方》之清香散、《石室秘錄》之清上至圣丸、《壽世保元》之清上蠲痛湯、《重樓玉鑰》之開關散等治療頭痛的古方,均含有救破湯三藥之中的兩味或全部。《中醫方劑大辭典》收載的古今502首以頭痛為主治的方劑中,使用頻次在前5位的即為川芎、甘草、防風、白芷、細辛[1],當前我國的川芎治療方劑居頭痛用藥的首位,與他藥靈活組方,臨床應用廣泛[2-3]。從現代藥理研究來看,川芎水煎劑能抑制小鼠中樞神經系統的興奮性,有鎮靜催眠作用[4]。其活性組分如川芎嗪、川芎內酯類化合物具有明顯的抗血管痙攣、舒張血管、保護血管內皮、改善腦部微循環、抑制血小板聚集等作用[5-6];阿魏酸鈉可抑制血小板釋放5-HT,阻止顱內外血管異常收縮,起到治療和預防偏頭痛的作用[7]。白芷具有解痙止痛、鎮靜作用[8],其揮發油可促進β-內啡肽的前體物質前阿黑皮素(POMC)mRNA的表達,進一步激活內源性鎮痛機制、調整體內單胺類神經質含量而發揮鎮痛作用[9-10]。細辛揮發油對小鼠腹痛、足痛等有明顯鎮痛作用[11],并可抑制神經動作電位的傳導[12]。以上藥理作用,均與偏頭痛發病機制的主流學說—血管源學說和三叉神經血管反射學說有關,通過干預5-HT、降鈣素基因相關肽(CGRP)、調控神經動作電位等,緩解偏頭痛發作[13]。
2.2 蔣健教授以救破湯治療偏頭痛的臨床經驗探討
2.2.1 救破湯劑量、療效特點及其不良反應 蔣健教授指出,救破湯之名,顧名思義有三層含義:一是形容頭痛甚劇如破;二是暗示該方堪當大任以解破痛于頃刻之間,如同救火;三是療效較為可靠。蔣健教授認為以本方治療輕度偏頭痛者,謹遵救破湯原方及其劑量即可;欲治中度偏頭痛者,須以大劑量,如川芎30~60 g,白芷30~50 g,細辛3~10 g;欲治中重度偏頭痛者,僅以大劑量救破湯尚恐不逮,還需進一步配合運用其他藥物。而本文所舉案例,均為中重度偏頭痛患者。臨證應用中,大劑量川芎、白芷相對較為安全,唯細辛大劑量使用時需注意其不良反應。古代本草言“細辛不過錢”一般系針對單用細辛末而言,如宋·陳承《本草別說》云:“細辛若單用末,不可過一錢,太多則氣悶塞,不通而死”;藥典亦規定細辛用量為3 g。現代藥理研究表明細辛存在呼吸抑制及心肌急性毒性等作用,過量服用可導致中樞神經系統陷入麻痹狀態及嚴重的心肌損傷[14-15]。復方湯藥中,細辛不良反應可一是藥物用量有關(如案四中細辛用量為10 g,患者出現不良反應,減至6 g后則未再出現);二是存在個體差異(如同樣用細辛10 g,案2未見不良反應,案4則出現)。因此,蔣健教授認為,盡管有應用大劑量細辛(30~160 g)見效而不見弊的臨床報道[16-17];亦有研究證實細辛所含揮發油隨煎煮時間延長而揮發、細辛水提液臨床應用安全有效[18],但臨床細辛的大劑量應用仍當高度謹慎,需密切注意觀察患者藥后反應,一旦出現藥物不良反應當立即停藥并及時采取相應保護性措施。
2.2.2 病證合辨、標本兼治是治療偏頭痛的基本方法 清代以降的南方溫病學派認為辛溫香竄的理氣藥多有傷陰之嫌,用于熱病往往畏首畏尾。蔣健教授認為:一是當今中醫所治疾病譜中熱病甚少,而對于一般雜病來講,其香竄傷陰之弊較為少見;二是通過辨證加減及藥物適當配伍可減少其弊端。例如,熱性頭痛配伍生石膏、黃芩、菊花、生地黃等;兼見肝風內動者配伍天麻、鉤藤、石決明等;氣虛者配伍黨參、黃芪等;寒甚者加用烏頭、吳茱萸等;肝氣郁結則配伍柴胡、香附、白芍等;痰濁明顯者配伍天南星、半夏、白附子等。本文所舉臨床驗案中,案1加用天麻鉤藤湯,案2加用吳茱萸、肉桂、炮姜以加大溫經通絡之功,案3加用黃芪桂枝五物湯,案4加用大劑量芍藥甘草湯。此外,陳士鐸雖云救破湯治療頭痛“一劑而痛止,不必再劑也”,但臨床上未必盡如此。對頭痛頗劇、病情頑固者,可再加用止痙散(案一、案散、案四),吞服全蝎粉、蜈蚣粉以搜風剔絡,收效更巨。因此,以救破湯辨證加減,基本可以治療具有寒熱虛實屬性的多種類型的偏頭痛。同時,本方不僅治療偏頭痛,也可用于治療一般頭痛,其臨證加減、劑量變化亦如上所述。
綜上,在救破湯基礎上施以辨證論治、隨癥加減治療偏頭痛,乃辨證與辨病(止痛)相結合、治本與治標(止痛)相結合、治療主癥(疼痛)與治療其他兼雜癥相結合,是為蔣健教授基本的臨證診療思維。
[1]楊洪軍,王永炎.頭痛方劑用藥規律研究[J].中國中藥雜志,2005,30(3):226-228.
[2]鄭琴,魏韶鋒,熊文海,等.川芎在治療頭痛中成藥中的組方應用分析[J].中草藥,2013,44(19):2777-2781.
[3]余奕漱.淺論川芎在頭痛治療中的應用[J].中國處方藥,2014,12(2):69-70.
[4]阮琴.川芎水煎劑對小鼠神經功能的影響[J].浙江中醫雜志,2008,43(12):723.
[5]Huang WH,Song CQ.Chem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advances of the study on Angelica Sinensis[J].China J Chin Mater Med,2001,26(3):147-151.
[6]陳益君,黃長順,王峰,等.川芎嗪對體外循環下心臟手術凝血功能和術后出血的影響[J].中華全科醫學,2015,13(2):184-186,240.
[7]王光浩,張敬芳.阿魏酸鈉對血管內皮細胞的作用及其機制研究[J].微循環學雜志,2015,25(1):71-72.
[8]高小坤.白芷揮發油鎮痛鎮靜作用實驗研究[J].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2013,22(35):3880-3882,3888.
[9]聶紅,沈映君.白芷總揮發油對疼痛模型大鼠的β-內啡肽、促腎上腺皮質激素、一氧化氮及前阿黑皮素的影響[J].中國中藥雜志,2002,27(9):690.
[10]聶紅,沈映君,曾南,等.白芷總揮發油對疼痛模型大鼠的神經遞質的影響[J].中藥藥理與臨床,2002,18(3):11.
[11]陳超,鄭衛紅,熊素兵,等.細辛verapamil鎮痛協同作用的實驗研究[J].中國藥理學通報,2003,19(3):339.
[12]張瑤,宋志永,王林麗.細辛的藥理作用及臨床應用[J].中國藥業,2007,16(14):62.
[13]譚亮,樊光輝.偏頭痛發病機制的研究進展[J].中國臨床神經外科雜志,2012,17(9):571-573.
[14]楊麗娜,鞠儉奎.細辛用量研究探討[J].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2010,12(1):194-195.
[15]明海霞,陳彥文,王強,等.單葉細辛對家兔心肌的急性毒性作用[J].中國老年學雜志,2015,35(5):1337-1339.
[16]馮恒善.重用細辛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100例分析[J].河北中醫,1984(1):16-17.
[17]劉文漢.細辛用量與用法之我見[J].中醫雜志,1983(2):80.
[18]馬國秀,于艷.北細辛全草和根中與馬兜鈴酸A的含量測定及小鼠急性毒性實驗研究[J].中醫藥學刊,2006,24(6):1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