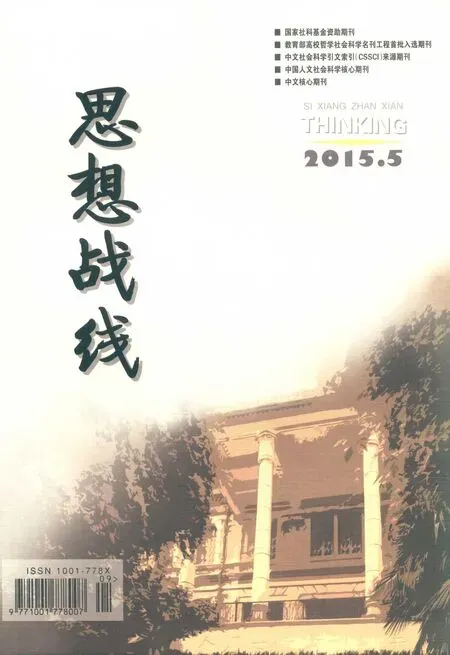對當代文論建設的幾個所謂“共識”與“常識”的質疑
曹順慶,曹美琳
對當代文論建設的幾個所謂“共識”與“常識”的質疑
曹順慶,曹美琳①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有不少學者發表過重寫中國文學史的看法和觀點、提出反思中國文論研究 “失語”現狀的論文,提出了中國文論的重建問題。然而,迄今為止卻收效不大,基本上仍然無法確實地推進當代中國文學史的重寫與發展,無法推進中國文論的重建進程。可見當下仍存在著一些嚴重困擾著文學史與文論界的問題。其中一個常常被人們忽略而又十分重要的困擾是,很多當代人形成了所謂的文學史與文學理論的 “共識”與 “常識”: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教材不應該收錄古體詩詞、中國古代文論沒有體系、古代沒有白話詩、中國文學史不包括少數民族文學,并視其為理所當然。其實這些 “共識”與 “常識”是很有問題的,恰恰是這些 “共識”與 “常識”,阻礙了中國當代文學史與文學理論的建設與發展。
中國文學史;文論重建;“共識”與 “常識”;批判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有不少學者發表過反思中國文學與文論研究 “失語”現狀的論文,提出了重寫中國文學史、重建中國文論的問題。可我們卻始終無法實實在在地推進當代中國文學史重寫與文論重建進程,中國文論至今仍然嚴重 “失語”。可見仍存在著一些困擾文論界的問題。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是必須修正很多所謂的 “共識”與 “常識”。我們認為,正是這些 “共識”與 “常識”,阻礙了中國文學史與中國文學理論的建設與發展。如果不修正這些“共識”“常識”,不把這些 “共識” “常識”汰除,中國文論永遠都別想真正重建。例如:有一個所謂 “常識”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教材就是不應該收錄古體詩詞”,這在現當代文學界不僅是 “常識”,也是 “共識”。我們今天所有的現當代文學史教材,沒有任何一部收錄現當代人創作的古體詩詞,筆者曾經多次與現當代文學研究者論戰,比如筆者在武漢大學等多所高校開會時就曾提到過這一問題,前不久筆者在香港開和這一主題相關的會,筆者的標題就專門改為“炮轟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炮轟之后,很多人又反過來炮轟筆者,說 “曹順慶你根本就是個外行,因為這是個現當代文學的常識問題,你怎么連常識問題都不懂?現當代文學史就是不應當收錄古體詩詞,因為它沒有現代性。哪怕是魯迅等大家寫的古體詩詞,也不能收錄,這是常識,更是學術界的共識問題”。這其實是一種錯誤的“常識”,這種錯誤 “常識”極大地妨害了我們中國文學研究,它其實是指一種很強的偏見。這種 “共識”“常識”無形中極大地阻礙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延續以及在當代產生影響,假若古體詩詞在現當代文學史教材中被收錄、被承認,大量的現當代古體詩詞作者就必須要運用中國古代文論來創作,你講中國古體詩詞,你必須要講押韻、煉字、聲律,這些是西方文論不講的內容,還有像韻味、意境之類的概念,我們的傳統文論就有了用武之地,不會失語。可惜當代不少學者根本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下面分別詳述之。
一、“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教材不應該收錄古體詩詞”質疑
迄今為止,所有的現當代文學史教材,沒有任何一部收錄現當代人創作的古體詩詞,為什么會有如此奇怪的現象?其中一個 “共識”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教材不應該收錄古體詩詞”。其理由有許多,大致是:現當代人創作的古體詩詞語言陳腐,思想陳舊,沒有群眾基礎,沒有現代性等等。現代文學老前輩錢玄同將古體詩視為“腐臭的舊文學,應該極端驅除,淘汰凈盡”。①錢玄同:《嘗試集·序》,《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2號。當代學者王澤龍教授曾以 “非現代性”為由,論述將古體詩詞收進現當代文學史的不合理性:
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根本的不同,是 “五四”開始的現代文學具有了古代文學不具備的現代性特征……20世紀的舊體詩詞出現了一批具有現代思想品質的作品,但是舊的格律體形式中的創作,仍然不是我們所認定的具有文學現代形式與審美品質意義的現代性詩歌。②王澤龍:《關于現代舊體詩詞的入史問題》,《文學評論》2007年第5期。
陳國恩教授也指出:
中國現代文學之 “現代”,是相對于整個古代文學而言的。它不是一個朝代的文學,而是相對于古代文學的一種新的文學,它的根本點是現代性。這個現代性,不僅要表現在思想情感上,也必然要表現在作品的語言形式上。③陳國恩:《時勢變遷與現代人的古典詩詞入史》,《博覽群書》2009年第5期。
于是,現當代文學界形成了一個 “共識”:極力反對把現當代人所創作的古體詩詞收入現當代文學史,“我們在 ‘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長起來的人,現在怎么能提倡寫舊體詩?不應該走回頭路。所以,許多文學史完全沒有必要把舊體詩放在里面做一個部分來講”。④唐 弢:《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載 《唐弢文集》第9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379頁。哪怕是魯迅寫的很有藝術價值的古體詩詞,哪怕是非常具有現代性的 “天安門詩抄”,只要是古體詩詞,統統都不能收入現當代文學史教材,即使是收錄進的毛澤東的 《沁園春·雪》等古體詩詞,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而非真正意識到現當代古體詩的有用價值。這不僅僅是 “常識”問題,更是一個極為重要的 “共識”問題:朱自清于1929年至1933年在清華大學開授課程的講義 《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可算是現當代文學史的始祖性著作,首次規定了新聞學即現當代文學的概念和范圍,構建了一個嶄新完整的體系,劃定了一門學科。在這套講義中,朱自清詳細論述了 “五四”運動以來主要詩人的作品和風格,以及新詩的發展軌跡和獲得成就,但并未提及在這期間被創作出來的古體詩詞。⑤參見劉晶雯 《朱自清中國文學批評研究講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王哲甫在山西省立教育學院開設的新文學相關課程也被整理成書,名為《中國新文學運動史》,是我國第一部新文學史專著,體現了較為全面的文學史觀,但依然沒有絲毫對古體詩詞的研究討論。⑥參見王哲甫 《中國新文學運動史》,北平:杰成印書局,1933年。除此之外,林志浩主編的 《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79年版),唐弢和嚴家炎主編的 《中國現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等人合著的 《中國現代文學30年》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王慶生主編的 《中國當代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黃修己編著的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洪子誠編寫的 《中國當代文學史》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陳思和主編的 《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的 《中國現代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教材,這些教材的一個共同點(“共識”)是:統統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對現當代人所創作古體詩詞的論述與研究。當今許多學者認為,“現當代文學史教材中不收錄古體詩詞”是個毋庸置疑的 “常識”問題,也是現當代文學毋庸置疑的 “共識”。事實上,這個 “常識”是具有極大的偏見錯誤 “共識”,若不糾正,這個錯誤會一直嚴重地妨礙中國文學的研究和發展,人為地造成整個中國文學傳統的斷裂,人為地造成中國當代文論的失語,嚴重地影響了中國優秀文化的傳承。這種奇怪的 “常識”,或許只有中國才有,全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會形成這種連本民族傳統文學形式都要徹底拋棄的極端偏激的 “共識”。
反對在現當代教材中收錄古體詩詞的人士一般持如下觀點:現當代作家創作的古體詩詞一不具有現代性,二不具有審美價值,三不具有群眾基礎。筆者認為,非也。新文化運動以后,西方思潮使中國接受了一次從思想到文學、文化上的革新,文言文被抨擊打倒,白話文走上中國歷史舞臺。但這一切并不代表文言文與古體詩詞從此滅亡,即便是今天,在我們的書面語言乃至日常生活中,都仍有一些詞匯帶有文言痕跡。古體詩詞對韻律、平仄等有著嚴格的要求,因此現當代文學創作中仍然不乏一些極具藝術價值的古體詩詞作品。例如魯迅所作 《自題小像》:
靈臺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薦軒轅。
巧妙運用典故,筆法抑揚頓挫,飽含著激烈的情感,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最后一句 “我以我血薦軒轅”,切合了當時的民族境況,是詩人對人民和祖國的莊嚴宣誓,具有強烈的現代性。除此之外,“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為世人所傳頌,用精妙的比喻傳達詩人身處當時黑暗恐怖的氛圍仍不愿舍棄的一身傲氣和硬骨頭性格,同樣具有極大的審美價值和明顯的現代性。眾所周知的 《天安門詩抄》沖破 “四人幫”的迫害與禁令,為斗爭的人民增添了無窮無盡的勇氣,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天安門詩抄》大都是古體詩詞,是一部思想內容極具現代性的作品。許多現當代人所作的古體詩 “……表現了對真、善、美、自由、平等、正義等人類終極價值的關注和追求,對國家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渴望,具有濃烈的現代色彩”。①陳友康:《二十世紀中國舊體詩詞的合法性和現代性》,《中國現代科學》2005年第6期。值得欣慰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黃修己、錢理群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開始重視并逐漸提出現當代人所作古典詩詞入史的相關問題。黃修己發表了 《現代舊體詩詞應入文學史說》(載 《粵海風》2001年第3期)、《舊體詩詞與現代文學的啼笑因緣》(載 《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年第2期)等文,錢理群和袁本良合作編注《二十世紀詩詞注評》,②參見錢理群,袁本良 《二十世紀詩詞注評》,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年。在長序 《一個有待開拓的研究領域》中,為現當代舊體詩詞合法地位的爭取作了努力。盡管如此,由于眾所周知的 “共識”與 “常識”,古體詩詞進入現當代文學史依然路漫漫,依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在筆者看來,這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卻因為這些 “共識”與 “常識”,讓我們糾結了多少年!
二、“中國古代文論沒有體系”質疑
由此延伸開的第二個需要糾正的 “常識”是: “中國古代文論是不科學、不成體系的”。在很多談及中國古代文論的文章中,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觀點:中國古代文論忽略思辨與系統的理論構建,在概念范疇方面是含混、模糊的,總而言之是不科學的。朱光潛先生就曾說:“中國向來只有詩話沒有詩學”“詩話大半是偶感隨筆,信手拈來”“但它的短處在凌亂瑣碎,不成系統,有時偏重主觀,有時過信傳統,缺乏科學的精神和方法”。③朱光潛:《詩論抗戰版序》,載 《朱光潛美學文集》第2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第3頁。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中國古代文論的確重視感悟與實踐經驗,卻仍有自己的思辨模式與體系構成。
如今越來越多的學者也承認中國古代文論是有自己的體系特征的。蔣凡就說:
中國文論在總體上也存在著體系特征,但這種特征與西方文論是不一樣的,表現為中國文論體系是以文藝主體論為中心的,是在長期歷史積淀中逐漸形成的,是在微觀的具體批評和審美欣賞中呈現出來的。④蔣 凡:《中國古文論體系探索》,《社會科學戰線》1990年第4期。
李壯鷹則提出了 “潛體系”說,其認為:
我國的傳統文論在表面形態上雖然是零散而缺乏系統的,但卻存在著嚴密的體系,只不過這種體系內在地隱埋在零散的體系背后,它是一種 “潛體系”。⑤李壯鷹:《中國詩學六論》,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第32頁。
中國古代的文藝文論與西方文藝理論具有完全不同的模式,但這并不代表中國古代文藝文論就不成體系。季羨林先生有云:
我們中國的文藝理論不能跟著西方走,中西是兩個不同的思維體系,用個新名詞,就是彼此的 “切入”不一樣。嚴滄浪提到“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這種與禪宗結合起來的文藝理論,西方是沒法領會的。再說王漁洋的 “神韻說”, “神韻”這個詞用英文翻譯不出來。袁子才的 “性靈”無法翻譯,翁方綱的 “肌理”無法翻譯,至于王國維的 “境界”,你就更翻不出來了。這只能說明,這是兩個體系。⑥季羨林:《東方文化復興與中國文藝理論重建》,《文藝理論研究》1995年第6期。
例如劉勰所著 《文心雕龍》,李漁所撰 《閑情偶寄》,葉燮所寫 《原詩》,都是有思辨、有體系的。具體說來,作為中國古代最重要的一部文論著作,在談及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時, 《文心雕龍》是最無法回避的。全書共50篇,具有完整的體系、科學的框架和嚴謹的結構,不僅論證了文學及其本質,還敘述了文之起源,各種文體的流變,文學的創作過程,涉及了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理論。系統而深邃, “體大慮周”,為學界所公認。《閑情偶寄》為清代李漁所撰,全書包括詞曲、演習、聲容、居室、器玩、飲饌、種植、頤養共8部,內容豐富。前3部涉及中國古代戲曲理論,構建了一套完整的戲曲理論體系。在這部書中,李漁提出了 “結構第一”的命題,把結構這個概念放在首位,排列出 “詞采第二”“音律第三”“賓白第四” “科諢第五” “格局第六”的次序,層次分明地論述了戲曲創作中的諸多方面元素,在這些次序下,李漁又分出了小標題,以作進一步的補充闡述,例如在 “結構第一”下提出了 “立主腦” “密針線” “減頭緒”“審虛實” “戒浮泛” “忌填塞”的理論主張,以求戲曲創作能達到主題明晰、情節緊湊、脈絡清楚、語言簡練有力、故事情節無破綻的要求;在 “賓白第四”下提出 “語求肖似”“少用方言”等,主張戲曲語言生動貼切,語言潔凈通俗……這部著作邏輯嚴密、條理清楚,實乃中國古代戲曲理論的集大成者,如此文論著作,怎么可以評為 “無體系”呢?葉燮 《原詩》分內外兩篇共4卷,是繼 《文心雕龍》后又一部系統論述文學理論的專著,以詩歌為研究對象,不僅研究詩歌原理,更作出了詩歌批評理論闡述,其理論的創造性與論說的系統性是不容我們忽視的。由以上得知,“中國古代文論是無系統、無思辨的”這個所謂 “常識”是錯誤的。早在幾百年前,中國文學理論就已經有了自己的科學體系。今天需要我們反思的是,為什么這種謬論卻成了學術界的 “共識”與 “常識”!
三、“古代沒有白話詩”質疑
除了 “現當代文學史教材不收錄古體詩詞”這一錯誤的 “常識”外,中國古代文學史沒有白話詩,亦是大家普遍公認的一個 “常識”。不少人甚至認為,白話詩是 “五四”運動以后才有的。這樣無知的 “常識”,形成了我國今天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又一個奇怪現象:現有的古代文學史教材中幾乎都看不到古代白話詩的影子。幾套影響力比較大的古代文學教材如由傅斯年主編的 《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版),劉大杰主編的 《中國文學發展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章培恒主編的 《中國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馬積高主編的 《中國古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羅宗強、陳洪主編的 《中國古代文學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郭預衡主編的 《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都未曾對白話詩有過專門的章節記述。由于在我國古代文言話語占主導地位,白話詩派不入流、不受重視,多年來一直被主流文學史忽視。直到白話話語占主導的今天,人們在編寫古代文學史教材時仍然對白話詩沒有多少記述。導致大部分人誤以為 “五四”之后,中國才出現了白話詩,而胡適的 《嘗試集》,才是我國第一部白話詩集。事實并非如此。早在唐代就出現了白話詩流派,僧人王梵志是唐代白話詩人的代表人物,寫下過眾多通俗易懂、淺顯直白的白話詩篇,例如 “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腳”①蔣述卓:《禪詩三百首賞析》,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7頁。或 “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里。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世無百年人,強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②蔣述卓:《禪詩三百首賞析》,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6頁。等,大多無題,或感悟生活瑣碎,或正視自然規律、感慨生死之必然,或隨意自嘲,或勸人向善、諄諄教誨,皆是有別于文言詩工整嚴謹的平仄、格律要求,但句式整齊,的確又充滿 “詩”意。在王梵志之后又出現了寒山子、拾得、王績等,甚至于形成了一個白話詩流派。這個白話詩流派雖游離于文言話語占主流的大團隊以外,眾多詩人連生卒年都至今不詳,卻在詩歌史上也是不容忽視的一支。尤其是據考證為隋朝皇室后裔的寒山子,③嚴振非:《寒山子身世考》,《東南文化》1994年第2期。其詩句在20世紀50年代后傳入美國,為 “垮掉的一代”迷惘的年輕人們送去了精神慰藉,以至于寒山子在北美乃至世界上都享有一定的聲譽。寒山子的詩歌技法在唐代眾多優秀詩人中并不算十分出眾,但通俗易懂、機趣盎然也是其獨有的藝術特色,且隱居山林的他醉心佛法,所作詩篇大多如佛門警句,留下了 “今日得佛身,急急如律令”④參見《寒山子詩集》,蘇州寒山寺印,2003年,第25頁。等頗具意味的詩句。因詩人群中有很多僧人,這個流派與佛教聯系緊密,不僅弘揚了佛學文化,更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古代的白話詩歌進程,可謂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一卷。但如今我們編寫的古代文學史教材卻未曾收錄我國古代的這些白話詩作,大家還習以為常,這個“共識”與 “常識”,也是不正常的錯誤 “共識”與 “常識”。
四、“中國文學史不包括少數民族文學”質疑
最后一個本文要討論的所謂 “共識”或“常識”是:中國文學史教材中不收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這是一個錯誤的 “共識”或 “常識”。中華民族本來就由多個民族組成,自古以來中國的歷史就是多民族共同發展的歷史,中國古代官修史書 《二十四史》就是明證,其中的《魏書》《北史》 《遼史》 《金史》等等,都是少數民族政權史,但同時也是正宗的中國史,與岳飛打仗的金兀術,同樣是中國人,我們切莫將其視為外人。但如今的中國文學史教材,卻不完全符合中國歷代官修的歷史,基本上不承認少數民族文學是中國文學。無論是中國古代文學史,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幾乎不曾收錄少數民族文學,這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即中國文學史就是漢民族的文學史。自從中國有文學史開始,少數民族文學的存在就一直是缺席的。①對于這一觀點的證據,可詳見曹順慶 《三重話語霸權下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民族文學研究》2005年第3期。但值得欣慰的是,其中唐弢主編的 《中國現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中有少量篇幅最早地介紹了蒙古族和維吾爾族的詩人及其詩歌散文,雖著墨不多,卻是一個良好的開端。②參見唐 弢 《中國現代文學史》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隨后的新編文學史教材也有幾部注意到了收錄少數民族文學的問題。例如由劉元樹主編的 《中國現代文學史新編》 (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就設專章 “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老舍等少數民族作家作品”進行過論述。③參見劉元樹 《中國現代文學史新編》,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1989年6月,第一部關于現代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專著 《中國少數民族現代文學》 (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問世,詳盡地記述了現代以后我國少數民族的文學發展,并以各少數民族的歷史背景、風土人情、地理面貌為基礎,在向讀者介紹作家作品等文學方面的狀況之前,首先展示了各少數民族的民族概貌。其概括的全面性,記述的詳盡性,是很有價值的。④參見王保林 《中國少數民族現代文學》,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雖然很多學者已經開始重視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但將少數民族文學作為中國文學不可切割的一部分入史,依然還未形成普遍的觀念。多年來大家把漢族文學當做中國文學,已成了所謂 “共識”,這是很可悲的,因此為少數民族文學入史發聲的學者聲音,就顯得彌足珍貴:
盡管由于歷史的原因,創造現代文學主流的是漢族作家,但少數民族作家和群眾的創作,也應在現代文學史上有一定地位,才能全面反映我國現代文學的完整面貌。表現我國現代文學多民族性的特點,這任務至今尚未完成。⑤黃修己:《談我國少數民族現代文學史的編纂》,《民族文學研究》1994年第3期。
盡管如此,少數民族文學的作用和價值仍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幾大史詩: 《格薩爾王傳》《瑪納絲》 《江格爾》等等,文學價值極高。以《格薩爾王傳》為例,作為一部至今仍為吟游詩人所傳唱的活形態史詩,代表了中國古代藏族民間文化的最高成就,講述了英雄格薩爾憑借自身非凡的才能與品格,降妖除魔、造福百姓的經歷,以格薩爾功德圓滿,與其母其妃一同返回天界為終結。這部英雄史詩結構宏偉,卷帙浩繁,情節精彩生動,氣勢輝煌磅礴,具有極高的文學藝術價值與史學價值。其中引用了多個民間神話傳說與詩歌,亦為后世的文學藝術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寶庫。全詩采用散文與詩歌相結合的形式,在我國藏民族詩歌乃至中華民族詩歌史上都起著承古通今的作用。《格薩爾王傳》在宋代即成型,至少中國明代文學史就應當收入,很可惜,我們的文學史并沒有做到這一點。以至于形成了所謂的中國古代沒有史詩的謬論。
中國文學史理應是一部多民族的文學史,少數民族文學是中華民族文學史上不可分割的一支,只收納漢族文學的中國文學史是殘缺的中國文學史。正是因為我們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對少數民族文學的忽視,使各類文學史教材中見不到其身影,才造成了少數民族文學在中華民族文學史上的失語,即是造成了中華民族文學一部分血脈的流失。多年以來,我們從未意識到中國文學史教材中未收錄少數民族文學的不合理性,反之將之視作 “常識”,視作理所應當的 “共識”,這是很可悲的。只有盡快將這一缺口填補起來,才能真正重寫文學史,才真正有利于補充現有的文學史,才能真正推動中國文論重建進程。
綜上所述,錯誤的 “共識”或 “常識”,造成了中華文化傳承的人為斷裂,極大地傷害了中國當代文化建設,同時造成中國文學史研究與教學的重大失誤,形成了中國文學理論的嚴重失語。重新認識這些 “共識”或 “常識”,糾正這些偏見,已經成為當今學術界的重要問題,應當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其中或許蘊蓄著中國學術重大突破與進展的機遇!
(責任編輯 段麗波)
教育部高校財政基金項目 “比較文學前沿研究”階段性成果 (CD0015);教育部重大招標項目 “英語世界的中國文學譯介與研究”階段性成果 (12JZD016);四川大學 “2011”創新基地項目 “中國多民族文化凝聚與文化認同”階段性成果(DMZ0001)
曹順慶,四川大學杰出教授,教育部 “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曹美琳,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研究生 (四川成都,61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