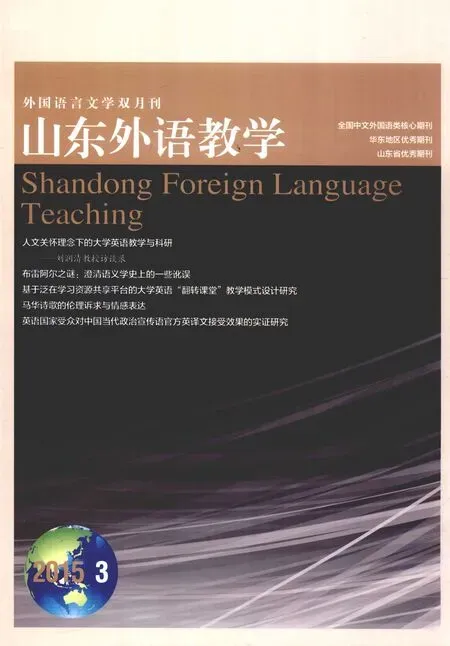PACTE翻譯能力模式和譯本質量評估
——以《勇敢的船長》的翻譯為例
高存, 張允
(1.天津商業(yè)大學外國語學院,天津 300134;2.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天津 300387; 3.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PACTE翻譯能力模式和譯本質量評估
——以《勇敢的船長》的翻譯為例
高存1,2, 張允1,3
(1.天津商業(yè)大學外國語學院,天津 300134;2.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天津 300387; 3.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英國最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魯?shù)聛喌隆ぜ妨值拈L篇小說《勇敢的船長》(Captains Courageous),在如何從道德教育的層面創(chuàng)作出高質量的兒童文學上,堪稱典范,至今已擁有不下10種中文譯本。這些譯本是否都能從意義和風格兩方面再現(xiàn)小說的精髓?本文選取譯者翻譯能力這一維度,將西班牙PACTE小組的翻譯能力模式應用于小說譯本的質量評估,特別是其中典型誤譯的評析之中,增強了誤譯評析的科學性,對譯者翻譯能力的習得具有啟發(fā)作用。
PACTE翻譯能力模式;翻譯質量評估;《勇敢的船長》
1.0 《勇敢的船長》的翻譯
英國最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魯?shù)聛喌隆ぜ妨肿钤缬?896年在美國《麥克盧爾》雜志上以連載形式刊載的長篇小說《勇敢的船長》(Captains Courageous),以其驚心動魄的海上歷險情節(jié)和瑰麗壯闊的海景描寫,彰顯了作家“觀察入微、想象獨特、氣概雄渾、敘述卓越”(諾獎獲獎詞)的獨特寫作風格。而在如何從道德教育的層面創(chuàng)作出高質量的兒童文學上,這部小說也具有很大的啟發(fā)作用。正因為如此,該小說也借助“翻譯”的翅膀,為中國的青少年讀者開啟了神奇的想象之門。至今,它已擁有了不下10種中文版本,其巨大的讀者市場可見一斑。(吉卜林,2013:譯者序)
我們在為其長盛不衰的生命力贊嘆之余,也在從翻譯的角度思索著另一個問題,那就是,這數(shù)目繁多的種種譯本是否都能從意義和風格兩方面?zhèn)魃竦卦佻F(xiàn)出這部小說的精髓?在這樣一部具有積極的啟迪與教育意義、在意識形態(tài)與詩學觀上均順應主流的小說翻譯中,譯者個人的翻譯能力便躍升為決定翻譯質量的主要因素。本文正是選取譯者翻譯能力這一維度,將具有較強解釋力的PACTE翻譯能力模式,應用于小說譯本質量評估中最重要的領域——誤譯的評析之中,以增強對誤譯評析的科學性和可信度,同時也對譯者翻譯能力的習得與養(yǎng)成具有一定的啟發(fā)作用。
2.0 翻譯能力與PACTE翻譯能力模式
什么是翻譯能力,至今尚沒有人給出明確清楚的答案(譚載喜,2012:114),對其所包含的具體內容認識也并不統(tǒng)一。(仝亞輝,2010)威爾斯(Wilss)是西方學者中較早提出翻譯能力組成的學者,他認為,翻譯能力包含第一語言能力(L1 competence)、第二語言能力(L2 competence)和超語言能力(supercompetence)。皮姆(Pym)從行為分析的角度將翻譯能力定義為同一源文本生產多種譯文本的能力和遵從特定翻譯目的和讀者需求,選擇合適譯文本的能力。(王傳英,2012)諾德(Nord)認為,“翻譯文本能力”包括元能力、文本生成能力、文本分析能力、文本比較能力。紐伯特(Neubert)則認為它包含了語言能力、文本能力、主題能力、文化能力、轉換能力。馬肯切(Mackenzie)指出,翻譯能力不僅包括語言文化運用能力,而且包括溝通能力、計算機運用能力、營銷能力、管理能力。(譚載喜,2012:114)
國內對于翻譯能力進行的研究中,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楊曉榮、蔣秋霞、權曉輝、劉宓慶、文軍、戴忠信、劉軍、苗菊、王樹槐、王若維、劉和平、李瑞林等。(張瑞娥,2012)黃子東,冼景炬,劉宓慶認為翻譯能力是雙語能力、雙文化能力、創(chuàng)造能力、思考能力、表達能力、語言之外的能力和轉換能力。(譚載喜,2012:114)譚載喜則在基拉里(Kiraly)對“譯者能力”界定的基礎上,將對譯者或翻譯專才能力的界定拓展為:“譯者或翻譯專才所必須具有的包含了所有基本項的翻譯能力。”作為基本項的子能力包括四種,即認知能力、相關雙語能力、技術輔助能力和轉換能力。(同上,2012:115)
綜觀國內外對于翻譯能力的研究,以PACTE小組(西班牙巴塞羅那自治大學翻譯系翻譯能力習得與評估過程研究小組)在該領域研究的成果最豐,貢獻最大。近年來,該小組一直致力于從整體的角度出發(fā),用實證-實驗的方法,研究翻譯能力的性質和習得。PACTE將翻譯能力定義為“從事翻譯所必備的潛在的知識系統(tǒng)”,并建立了翻譯能力模式,包括譯者的工具
使用能力(instrumental sub-competence)、策略能力(strategic sub-competence)、翻譯專業(yè)知識能力(know ledge about translation)、雙語能力(bilingual sub-competence)、語言外能力(extra-linguistic sub-competence)這五個子能力和相關的心理 -生理因素(psycho-physiological components)。(PACTE,2011:33)
本文擬運用PACTE翻譯能力模式對《勇敢的船長》譯本進行質量評估,并聚焦于最能直接體現(xiàn)翻譯質量、并在其評估中占權重最大的領域——誤譯,把譯本中典型誤譯的分析與模式中的各項子能力結合起來,揭示造成這些典型誤譯背后的真正原因,即譯者相應翻譯子能力的缺失。
3.0 《勇敢的船長》譯本中的典型誤譯與翻譯子能力的缺失
PACTE小組從翻譯能力模式的五個子能力中進一步細化出翻譯專屬能力(translation-specific competence),即策略能力、工具使用能力和翻譯專業(yè)知識能力。(PACTE,2011:33)與傳統(tǒng)的翻譯評估中主要依賴“專家的直覺”(expert intuition)(Gutt,2004:19)、圍繞譯者雙語能力進行評析的做法相比,從翻譯子能力和專屬能力的角度對譯文質量進行評估,從根本上將普通的雙語學習者與作為特殊雙語學習者的譯者區(qū)分開來,使得結論更為全面、客觀、科學,而譯本評估中反映出的譯者相應子能力的缺失,對于譯者翻譯能力的培養(yǎng)與習得,具有較強的針對性與借鑒性。下文中筆者擬從翻譯專屬能力及其它各項子能力入手,逐一對典型的誤譯進行評析。
3.1 工具使用能力和策略能力的欠缺
工具使用能力主要指翻譯過程中對文獻資料、信息和交際技術使用的過程性知識,具體體現(xiàn)為對詞典、百科全書、語法書、文體書、平行文本、電子語料庫和搜索引擎的使用知識。策略能力則指確保翻譯過程的有效進展和問題順利解決的過程性知識。該能力主要體現(xiàn)于對整個翻譯過程的控制之中。譯者一旦具備了相當?shù)牟呗阅芰Γ隳苡媱澐g全程、選擇最切合的方法實施翻譯項目、對翻譯的過程與翻譯達成的部分結果進行評估、激活其它翻譯子能力、彌補翻譯中出現(xiàn)的不足、識別翻譯中的問題并能采取相應步驟解決問題。(PACTE,2011:33)這兩種能力同時也被致力于對翻譯能力習得進行縱向發(fā)展跟蹤研究的TansComp小組(翻譯能力研究小組的簡稱)列為翻譯專屬能力(O’Brien,2011:7),其核心地位不容置疑。而《勇敢的船長》幾個中譯本中最具典型性、篇幅跨度最大的一個誤譯,便暴露了譯者這兩種能力的缺失。請看原文:
(1)Ready?Also arrange with Lake Shore and Michigan Southern to take“Constance”on New York Central and Hudson River Buffalo to Albany,and B.and A.the same Albany to Boston.Indispensable I should reach Boston Wednesday evening.Be sure nothing prevents.Have also wired Canniff,Toucey,and Barnes.—Sign,Cheyne.
Now then.Canniff,Toucey,and Barnes,of course.Ready?Canniff Chicago.Please take my private car“Constance”from Santa Fe at Sixteenth Street next Tuesday p.m.on N.Y.Limited through to Buffalo and deliver N.Y.C.for Albany...Take car Buffalo to Albany on Limited Tuesday p.m.That’s for Toucey.
Now,Boston and Albany,Barnes,same instructions from Albany through to Boston.Leave three-five P.M.(you needn’t wire that);arrive nine-five P.M.Wednesday.(Kipling,2010: Chapter 9)
這是小說的主人公哈維的父親在最終得知哈維的下落時,迫不及待安排秘書確定的橫穿美國的線路,成為后世有關鐵路旅行描述的典范。小說第九章正是以此為主線,展開了對鐵路沿途發(fā)生的一系列奇異冒險的記敘和瑰麗風光的描述,而切尼夫婦盼兒心切的焦急心情以及日夜兼程中心理上所承受的苦痛折磨,也將整部小說推向了情感上的高潮。因此,這段線路安排能否被準確地傳達過來,對于整章,甚至是整部小說的連貫性、邏輯性、可靠性和可讀性都是至關重要的。且看譯本1①:
a.準備好了嗎?請同時安排湖畔線和密執(zhí)安南方線迎接“康斯坦絲號”,轉紐約中央線和哈德遜河線的“布法羅號”前往奧爾巴尼,再從奧爾巴尼的同一個車站前往波士頓。我必須于周三晚間趕到波士頓,請務必保證此行暢通無阻。請分別電告這三條線路的經理卡尼夫、圖賽和巴恩斯。落款“切尼”。
好,接下來當然是要發(fā)給卡尼夫、圖賽和巴恩斯了。準備好了嗎?芝加哥,卡尼夫先生。我自圣塔菲發(fā)車的私人專列“康斯坦絲號”將于下周二晚間在第十六大街車站到達,請將該車轉至紐約快速列車,并轉至紐約中央線,經布法羅前往奧爾巴尼……請安排周二晚間乘坐“布法羅號”前往奧爾巴尼。這是給圖賽的。
現(xiàn)在,波士頓和奧爾巴尼,給巴斯恩的指令就和從奧爾巴尼到波士頓的指令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下午三點零五分出發(fā)(這點你不用發(fā)送),周三晚上九點零五分到達。(黑體為筆者所加)
原著的信息經過譯者的“搬運”,我們不禁對切尼先生在電報中敘述的邏輯性和合理性產生質疑:首先,在線路安排上,切尼夫婦二人準備乘“康斯坦絲號”專列在經“湖畔線和密執(zhí)安南方線”后,即轉乘“紐約中央線和哈德遜河線”上的“布法羅號”列車經奧爾巴尼到達波士頓,他們將這個總體安排同時電告了三位鐵路經理。可是接下來在分別致電三位經理時,切尼先生似乎改變了主意,安排將“康斯坦絲號”“轉至紐約快速列車”,此時,他沒有按照原計劃換乘“布法羅號”列車,而是到達了一個與該列車同名的城市——布法羅,然后再前往奧爾巴尼。在隨后的行程中,“紐約快速列車”神奇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突然出現(xiàn)的“布法羅號”列車,載著夫婦二人繼續(xù)前往奧爾巴尼。列車轉乘中出現(xiàn)的種種“差錯”我們暫且不做分辨,但對譯本中出現(xiàn)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矛盾點,無論是讀者,還是譯者都無法回避:這段譯文明確告訴讀者,切尼夫婦是中途離開“康斯坦絲號”專列,轉乘“布法羅號”列車到達波士頓與兒子哈維見面的,這與該譯本后兩章中“‘康斯坦絲號’專列到達波士頓”的故事情節(jié)嚴重不符。
另外,該譯本呈現(xiàn)出的路線中還存在著幾處顯而易見的邏輯或表達不通之處:“布法羅”(文中劃線部分)一詞在譯文中時而是列車的名稱,時而又成了城市名,是巧合,是偶然,令人迷惑;首段中“再從奧爾巴尼的同一個車站前往波士頓”的表達,刻意強調從同一個車站出發(fā),不僅未傳達任何有用信息,還有畫蛇添足之嫌,令人生疑;第二段“將該車轉至紐約快速列車”的表達中,專列如何能“轉至”另一列車上,令人費解。
如果說譯本1中的種種問題尚可算作失誤的話,那么譯本2②距原著就相去較遠了:
b.準備好了嗎?同時安排“湖濱號”和“密執(zhí)安南部人號”,帶“康斯坦賽號”經紐約中央車站和哈得孫河布法羅站到奧爾巴尼。分別通知布法羅站和奧爾巴尼站。同時安排從奧爾巴尼到達波士頓。我必須于星期三傍晚到達波士頓。要保證暢通無阻。此外,分別電告坎尼夫、陶賽和巴恩斯三站,落款“切尼”。
接下來當然要發(fā)電報給坎尼夫、陶賽和巴恩斯站。準備好了嗎?芝加哥的坎尼夫站,請讓
我的私人列車經由十六號專用線的圣多菲于下星期二下午掛接紐約直達布法羅的高級快車,然后掛接紐約中央車站到達奧爾巴尼站的特別快車……私人列車于星期二下午由布法羅到達奧爾巴尼,掛接特別快車。接下來發(fā)給陶賽站。
現(xiàn)在發(fā)給波士頓,奧爾巴尼和巴恩斯車站,重復從奧爾巴尼到波士頓的指令。下午三點零五分離站(這個你不必打電報);星期三下午九點零五分到達。
在譯本2中,幾乎所有的鐵路路線名、列車名、車站名、甚至是鐵路經理的名字,都被譯者混為一談,不分彼此。原本計劃周密、精心安排、路線復雜的穿越全美之旅,在譯者的筆下竟變得如此“簡便易行”,因為所有的鐵路線與各個線路的負責經理都被譯作了車站,這次的旅行就成了“康斯坦賽號”在“湖濱號”和“密執(zhí)安南部人號”的帶領下,穿梭于各大車站之間。不難判斷,這部分譯文基本是建立在猜測的基礎上的。由于譯者對于旅行中基本元素的妄加猜測,以至后文中出現(xiàn)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使得譯本中的相關情節(jié)出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扭曲。
從兩個譯本呈現(xiàn)的狀態(tài)來看,兩位譯者都沒有完全讀懂原著中所描述的路線圖。在單純依靠雙語能力仍有“不能確定或心存疑慮的問題”時,他們沒有“調動使用輔助工具能力與鉆研能力,積極查閱相關參考資料”來解決問題(G?pferich et al.,2011:70),致使譯文中出現(xiàn)了大量自相矛盾之處。此時,譯者若具備充分的策略能力,對翻譯的結果進行自我評估,識別出翻譯中出現(xiàn)的問題并努力加以彌補,尚能確保譯文的翻譯質量。但譯者卻在沒有找到確切依據(jù)的前提下,采取了推測或猜測的方法,造成翻譯決策的失誤。TransComp小組經過長期研究與實驗證明,翻譯過程中出現(xiàn)的臆想或猜測現(xiàn)象,正是譯者策略能力缺失或不足的具體體現(xiàn)。而譯者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猜測,便成為衡量譯者策略能力的指標。(同上:66)雖然兩個譯本中都或多或少有譯者猜測的成分,但相比之下,客觀地說,由于譯本1的譯者具備較強的雙語能力,其猜測成分要遠遠少于譯本2。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譯文中出現(xiàn)的種種問題,遠非語言層面所能完全涵蓋的,譯者的工具使用能力、策略能力等翻譯專屬能力的欠缺才是癥結之所在。當譯者的雙語能力不足以解決翻譯中遇到的問題時,要果斷決策,避免猜測,拿出鉆研到底的精神,調動諸如工具使用能力等各項子能力。(G?pferich et al.,2011:66)我們循著這樣的思路,充分運用搜索引擎,查閱文獻資料,不難發(fā)現(xiàn),該小說曾被收入《牛津世界經典》系列并由利奧尼·奧爾蒙德維教授做過詳細而專業(yè)的注解。從小說名字的由來,到漁歌的來源,再到字詞背后的典故,均可在該注解中查到,當然,這次行程的細節(jié)也不例外。根據(jù)注解,我們得知,小說中這一情節(jié)的安排并非作家憑空捏造,而是源自1895年7月某報紙的一份特刊。據(jù)特刊記載,當月23到26日之間,一名鐵路主管為趕回波士頓看望自己生病的兒子,擬定了跨越幾條鐵路線的行程。原來,小說中鐵路線、沿線的城市名都并非虛構,而是真實存在的,吉卜林只是將其稍加改造,搬入了自己的小說之中,增加了小說的真實性和可讀性。同時,為便于讀者理解,奧爾蒙德維教授還手繪出一幅路線圖,途經的鐵路、城市、車站,都有清晰的標注。經過對書寫筆跡的辨識,并結合文本進行對照研究,便可將路線一一厘清。請看筆者的譯文③:
c.準備好了嗎?發(fā):同時請安排湖岸-密歇根南方線做好迎接“康士坦姒”號專列準備,并將其順利轉至紐約中央-哈德遜河線,使其經由布法羅到達奧爾巴尼,再經波士頓-奧爾巴尼一線,由奧爾巴尼發(fā)車,開往波士頓。
好,下面當然就是要分別致電卡尼夫、托西和巴恩斯了。準備好了嗎?發(fā):芝加哥卡尼夫,我自圣達菲開來的“康士坦姒”號專列將于下周二下午抵達十六號大街站,請安排其與紐約豪
華快車對接,發(fā)往布法羅,列車將繼續(xù)經紐約中央-哈德遜河一線,開往奧爾巴尼。……我“康士坦姒”號專列已與紐約豪華快車對接,請安排周二晚于布法羅發(fā)車,開往奧爾巴尼。這條是發(fā)給托西的(他負責紐約中央-哈德遜河一線)。
好,下面該致電巴恩斯了,他負責波士頓-奧爾巴尼一線,指令還是一樣,只把地點改為:專列途經奧爾巴尼,開往波士頓,下午三時五分發(fā)車(這個不需要發(fā)送),務必于周三晚九時五分到達。
這樣,這次橫穿美國的旅程便可清晰地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由洛杉磯調來的專列先到圣地亞哥,將切尼夫婦接上車,再向東到達新墨西哥州的圣達菲,然后直奔芝加哥,在那里與紐約豪華快車對接后,經湖岸-密歇根南方線,到紐約州境內的布法羅,轉紐約中央-哈德遜河線,到紐約州東部的奧爾巴尼,最后經波士頓-奧爾巴尼線,到達波士頓。行程共經三條鐵路線,譯本1漏譯了最后一條路線,并將前兩條鐵路線擴展為四條。譯本2更是將三條鐵路線均譯為車站。由于兩位譯者工具使用能力與策略能力的不足,造成了在該情節(jié)翻譯決策上的失誤或失敗,動搖了占據(jù)整部小說五分之一篇幅的高潮部分的根基。
3.2 翻譯專業(yè)知識能力的欠缺
翻譯專業(yè)知識能力是翻譯的專屬能力之一,主要指對于翻譯本身以及翻譯職業(yè)的方方面面的隱性或顯性的陳述性知識,具體表現(xiàn)為對于翻譯的功能、翻譯的原則及實際翻譯操作的專業(yè)性知識。(PACTE,2011:33,45)PACTE(2008,2009)經實驗研究證實,該能力是區(qū)分專業(yè)譯者與普通雙語學習者的關鍵能力。小說中一些典型的誤譯也同樣暴露了譯者這方面能力的欠缺:
(2)“Jounce ye,an’strip ye,an’trip ye!”yelled Uncle Abishai.“A livin’gale—a livin’gale.Yah!Cast up fer your last trip.”(Kip ling,2010:Chapter 4)
a.“大風會把你們顛來顛去,把船上的東西都吹走,把你們的船吹得飄來蕩去!”阿比昔西埃伯伯對著他們吼道,“絕對的大風——絕對的大風啊。呀!送你們踏上最后一次的旅途。”(譯本1)
b.“你們在顛簸,砍去桅桿,趕快起錨!”阿比歇舅舅嚷道,“狂風來了,狂風來了,……那是你們最后一次出海捕魚啦。”(譯本2)
這里的Uncle Abishai是小說第四章中一位頗具特色的人物。他掌管著一艘臟兮兮的破船,霉運纏身、負債累累,整日瘋癲癲、醉醺醺,見了人就破口大罵,發(fā)下毒咒。例文便是他在海上遭遇主人公哈維一行人航行的“海上”號時喊出的瘋話。原文中的“jounce”表示“to jolt or bounce”(Pearsall,1998);“strip”表示“to remove,pull or tear the covering or outer layer from something”(Wood ford,2003);“trip”的含義為“to cause someone to lose his balance after knocking his foot against something”(同上)。
從意義轉達的層面評價,在譯本2中,“你們在顛簸”的譯法,將原文的祈使句改為陳述句式,“砍去桅桿,趕快起錨”的表達在原文中找不到對應詞,顯然是誤譯。相比之下,譯本1較為忠實地傳達出原文的意義,說明譯者具備了較為扎實的雙語能力。但若從翻譯原則的角度來評析,譯本1卻暴露出明顯的不足之處。原文句式極短,幾乎單詞成句,節(jié)奏明快,用語隨意,如“an’”(and),“l(fā)ivin’”(living)和“fer”(for)等詞。譯者卻以拖沓冗長的句式、正式完整的用語、文縐縐的腔調,書寫出一個風格錯位的譯本。一個肚子里沒幾滴墨水、神志不清的老水手,恰逢狂風大作,在茫茫大海上隔船詛咒對方,卻在譯本中從容鎮(zhèn)定地說出了“大風會把
你們顛來顛去”、“把你們的船吹得飄來蕩去”、“呀!送你們踏上最后一次的旅途”這樣有板有眼的話語,特別是連用兩個四字詞語“顛來顛去”和“飄來蕩去”,文質彬彬的口吻與原來那個滿嘴臟話的無賴水手完全不符。
思果曾提出譯者要始終遵循翻譯的三字原則——“信、達、切”,其中的“切”字,就是要求譯者“能設身處地想象文章里面人物的身份、心情、口吻”(思果,2001:33),并時常反省,譯文與“原文的文體、氣勢、說話人的身份等各方面是否做到恰如其分的地步了”。(同上:7)譯者雖然雙語能力過硬,但正因為缺乏翻譯專業(yè)知識能力,即對相應的翻譯原則的模糊認識,對翻譯的結果未能及時反思,才造成了風格、口吻層面上的錯位,導致翻譯決策上的失誤。筆者本著切合說話者身份和口吻的原則,兼顧句式與詞語的省略,將例句翻譯如下:
c.“刮風嘍,把你們那船,可勁搖,你們那東西,都刮跑,掀他個底朝天!”阿比沙艾大叔聲嘶力竭地叫喊,“大風來嘍,呼啦啦——呼啦啦,啊哈哈!送你們最后一程嘍。”(譯本3)
3.3 雙語能力與語言外能力的欠缺
PACTE小組將雙語能力定義為由語用知識、社會文化知識、語法知識和詞匯知識構成、確保雙語順利交流的過程性知識。語言外能力主要指隱性和顯性的陳述性知識,包括常識性知識、專門領域知識、雙文化知識和百科知識。(PACTE,2011:33)譯者不是普通的雙語學習者,而是文化間賴以交流的橋梁,稍有不慎,便會造成失誤,請看下文:
(3)Getting that way.I tell you,the Leland Stan ford Junior isn’t a circumstance to the old“We’re Here”;but I’m coming into the business for keeps next fall.(Kipling,2010:Chapter 10)
a.差不多了。告訴你吧,利蘭-斯坦福初級大學的環(huán)境跟“海上號”可沒得比,不過我明年就要投身到生意中去自食其力了。(譯本1)
b.差不多了。我跟你說,做一個利蘭·斯坦福學院的三年級生不像在咱的“海上號”上,真不是個滋味,不過明年秋天我要進事務所辦事了。”(譯本2)
這是小說結尾處,丹與哈維分別幾年后,再次重逢的問候。丹在海上打拼,哈維則去高等學府深造。那么哈維去的究竟是哪所學校呢?譯本1告訴我們是“利蘭-斯坦福初級大學”,而譯本2卻認為是“利蘭·斯坦福學院(的三年級生)”。其實,“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是斯坦福大學的全稱,是由當年的加州鐵路大王、曾擔任加州州長的老利蘭斯坦福為紀念他在意大利游歷時染病而死的兒子,捐錢在帕洛·阿爾托成立的大學。這是吉卜林繼例(1)“橫穿全美之旅”的情節(jié)后,將現(xiàn)實事件搬入小說中的又一例。兩位譯者由于相關雙語文化知識或常識性知識的缺乏,又缺少嚴謹、反思的精神,疏于查閱,以至于為青少年讀者“創(chuàng)造”出了一所美國的“初級大學”和“學院”。更有甚者,譯本2甚至忽視了“Junior”一詞的大寫形式,將其理解為“三年級生”,句末的“進事務所辦事”也屬對“the business”的誤譯,其不認真的態(tài)度,不求甚解、妄自揣測的做法,值得我們所有譯者引以為戒。
4.0 結語
筆者選取了吉卜林《勇敢的船長》譯本中典型的誤譯,只是想管中窺豹,揭示當前文學翻譯中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即譯者翻譯能力,特別是翻譯專屬能力的欠缺。譯者與普通雙語學習者最大的區(qū)別便是具備問題意識,能夠自我反思,發(fā)現(xiàn)邏輯、文義不通之處,主動調動各種子能力進行自我糾正。(G?pferich et al.,2011:66)而具備問題意識則是翻譯能力提高的關鍵。(O’Brien,2011:8)翻譯如同在大海上航行,面臨無數(shù)大浪與險灘,只有處處小心,時時謹慎,瞻前顧后,時常反思,才會功德圓滿,到達彼岸。
可是在當下文學名著重譯之風盛行的翻譯市場,譯者迫于出版社巨大的壓力,通常都會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大部頭作品的翻譯。以《勇敢的船長》的翻譯為例,短短一年之中,竟出現(xiàn)了三個譯本。與其說是重譯,不如說是搶譯,這樣的做法無疑會大大影響譯者翻譯能力的正常發(fā)揮,更是譯者能力發(fā)展道路上最大的絆腳石,這也許是一個更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
注釋:
①譯本1為吳剛翻譯的《勇敢的船長》(2012)。
②譯本2為徐樸、汪成章翻譯的《勇敢的船長》(2010)。
③譯本3為高存翻譯的《勇敢的船長》(2013)。
[1]G?pferich,S.,G.Bayer-Hohenwarter,F(xiàn).Prassl&J.Stadlober.Explor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cquisition: Criteria of analysis put to the test[A].In S.O’Brien(ed.).Cognitive Explorations of Translation[C].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11.66.
[2]Gutt,E.A.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Kipling,R.Captains Courageous:A Story of the Grand Banks[M].Createspace:Nabu Press,2010.
[4]O’Brien,S.Cognitive Explorations of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11.
[5]PACTE.First results of a translation competence experiment:Knowledge of translation and efficacy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A].In J.Kearns(ed.).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Training:Issues,Methods and Debates[C].London:Continuum,2008.104-126.
[6]PACTE.Results of the validation of the PACTE Translation Competence Model:Acceptability and Decisionmaking[J].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2009,10(2):207-230.
[7]PACTE.Results of the validation of the PACTE Translation Competence Model:Translation project and dynamic translation index[A].In S.O’Brien(ed.).Cognitive Explorations of Translation[C].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11.33-34.
[8]Pearsall,J.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Z].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9]Woodford,K.&G.Jackson(eds.).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Z].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0]吉卜林.勇敢的船長[M].徐樸,汪成章譯.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0.
[11]吉卜林.勇敢的船長[M].吳剛譯.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12]吉卜林.勇敢的船長[M].高存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3.
[13]思果.翻譯研究[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
[14]譚載喜.翻譯與翻譯研究概論——認知·視角·課題[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有限公司,2012.
[15]仝亞輝.PACTE翻譯能力模式研究[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0,(5):88-93.
[16]王傳英.從“自然譯者”到PACTE模型:西方翻譯能力研究管窺[J].中國科技翻譯,2012,(4):32-35.
[17]張瑞娥.翻譯能力構成體系的重新建構與教學啟示——從成分分析到再范疇化[J].外語界,2012,(3):51-58.
PACTE’s Translation Competence Model and Translation Evaluation: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Versions of Captains Courageous
GAO Cun1,2, ZHANG Yun1,3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Tianjin 300134,China; 2.School of Liberal Arts,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387,China;3.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As a good example of high-quality children’s literature with morally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Captains Courageous by Rudyad Kipling,the youngest British writer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no less than ten Chinese versions.The concern of this paper is whether these versions can convey the essence o f the original novel both in meaning and style.The paper will apply PACTE’s Translation Competence Model to the evaluation of these versions of translation,especially to the scientific analysis of some typical mistakes in them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some enlightment for the
PACTE’s Translation Competence Mode l;translation evaluation;Captains Courageous
I046
A
1002-2643(2015)03-0100-08
10.16482/j.sdwy37-1026.2015-03-013
2014-05-06
本文為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比較文學主題學研究”(項目編號:12BWW007)的階段性成果。
高存(1979-),女,漢族,山東鄆城人,天津商業(yè)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專業(yè)博士。研究方向:西方翻譯理論;文學翻譯實踐。張允(1977-),男,漢族,山東金鄉(xiāng)人,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生,天津商業(yè)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應用語言學。
acquisi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on the part of the trans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