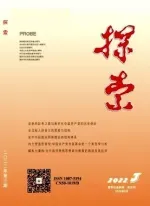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扎牢關住權力的制度籠子
(國家行政學院,北京 100089)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以雷霆萬鈞之力,出重拳反腐肅貪,掀起了“老虎”“蒼蠅”一起打的狂飆巨浪。腐敗,蓋源于公共權力的不正當使用。遏制和清除腐敗,從根本上說必須制約監督權力。為此,習近平提出“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1]388。本文擬就如何治理權力,切實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的問題,進行討論。
1 權力腐敗問題的診察
從當前的情況看,我國的權力腐敗十分嚴重。有關統計表明,從2000年至2014年3月底,15年間共有367名廳局級以上官員發生權力腐敗案件。其中,擔任或曾經擔任“一把手”領導職務的有219人,占了60%左右,近八成在黨委核心部門工作;2014年1月至7月,涉及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500余名官員,被中紀委先后點名通報,而在落馬官員中位高權重的“一把手”也居多[2]。那么,我國各級領導者手中的權力究竟發生了怎樣的問題呢?從深層次說,就是要尋找權力腐敗的根源,這主要在于:
其一,權力存在盲區的問題。我國現有各級領導者到底擁有哪些權力呢?我們試以黨政“一把手”為例,進行相關的診察分析。

對于黨政“一把手”的權力,我國已有黨章和黨的相關文件、憲法和相關的法律作出了規定。例如,對書記和黨委的權力規定是,從權力涉及的內容范圍來說,黨要“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對整個國家和社會實行“總的領導”;從權力運行的方式方法來說,黨章規定,“黨的各級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委員會成員要根據集體的決定和分工,切實履行自己的職責”。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權力運行方式。對政府各行政首腦或行政主管的權力規定,從權力涉及的內容范圍來說,是要“加強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等制定和實施”,加強“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從權力運行的方式方法來說,憲法規定,“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同時強調負責制,“國務院實行總理負責制”,“各部、各委員會實行部長、主任負責制”,“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實行省長、市長、縣長、區長、鄉長、鎮長負責制”。從這樣的制度設計來看,我國對黨政部門以及黨政“一把手”的權力,可以說在其“權重”“權值”“權規”“權界”等方面,都有了一個相應的規定。
但是,從上述規定可知,它們也只是一些原則性的、大致的規定,這就造成了當前我國“一把手”權力事實上存在著模糊地帶,容易產生真空、盲區。黨章和憲法所作的原則說明,不可能具體明細,這就需要在黨章之下的黨內其他規則規制中和在憲法之下的其他法律條例中,作出更為具體的規定。坦率地說,在這些方面目前還比較缺乏,做得很不夠。
其二,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權力需要集中統一,才能發揮治國理政的應有效用。但是,過猶不及,目前我國的現實情況,一如既往,仍是權力過分集中。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就提出,我國政治體制的總病根是權力“過分集中”,由此造成了社會主義的根本弊端和很多奇怪現象。其中就有“一把手”的權力在我國黨政部門中實際上成了“一霸手”,形成“決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話、花錢一支筆”的權力壟斷。權力過分集中,造成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各方面治理的嚴重危害:第一,官僚主義、高高在上,拍腦袋、瞎指揮,最終很可能出現顛覆性、毀滅性的失誤;第二,官大的說了算,有權就有真理,壓抑、窒息了社會的生機活力;第三,濫用權力,貪污受賄,腐敗泛濫,因為權力過分集中就會產生絕對權力,而絕對權力就會導致絕對腐敗。
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究其實質是一個體制性的問題。它來自于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形成的蘇聯模式,或者說斯大林模式。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具有三大特征:經濟方面實行計劃經濟,產供銷、人財物都管得死死的;政治方面實行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強調“一元化”領導,實際上就是黨委領導,黨委領導實際上變成書記領導,又搞了領導職務終身制;文化方面實行輿論一律,假、大、空盛行,千人一面,萬口一調。以上這些特征聚焦到一點,就是權力過分集中。
我國政治領域權力過大和過于集中的情況,就與我們過去長期受到極左思想的侵蝕、沿襲斯大林模式的做法分不開。它造成對領袖的崇拜、迷信,領袖一句話頂一萬句,乾綱獨斷,大家不能持有異議、不能反對,領袖的權力也不受任何制約。最高領袖是這樣,上行下效,下面各級的領導者也成了大大小小的領袖式人物,也可以說一不二。這樣一來,歷史唯物論就被歷史唯心論所代替,黨的民主集中制和憲法的規定就被徹底破壞了。中國共產黨在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時就深刻地指出,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搞了家長制、一言堂、權力專斷,民主集中制不管用了。
權力過分集中的具體表現,在于把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不適當地集于領導者一身。對權力作總體的分析,若從橫向的方面進行劃分,可以分為“決策、執行、監督”三個權力環節。科學的權力配置,絕不可把“三權”集于某一個領導機構和某一個領導自身,而一定要“三權”分離。把“三權”集于“一把手”一身,正是現存權力結構的根本弊端。比方說,辦一個運動會,如果某一組織或某些人既當“組織員”——制定游戲規則、擁有決策權,又當“運動員”——親自參與比賽、擁有執行權,還當“裁判員”——可以對是否違規進行裁決判定、擁有監督權,那就沒有其他人敢來參加比賽了,因為哪怕別人成績再好,也會被判為犯規而罰下場去,冠軍總能歸于他們自己[3]。因此,要革除權力過分集中且不受制約監督的弊端,惟有對權力結構進行科學重構。
其三,權比法大、官比法大的問題。“權比法大、官比法大”的觀念源于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封建意識形態崇尚“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而讀書就是為了能夠做官掌權,以便高居于民眾、社會之上,也包括高居于法律之上。由于受到封建思想的侵蝕影響,時至今日,我們的一些干部仍然法治意識薄弱,存在著“權比法大、官比法大”的觀念。由于身居高位、手握重權,工作中習慣于把法律拋在一邊,喜歡自己說了算,正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所指出的,“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依法辦事觀念不強”,“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4]。毫無疑義,不解決權比法大的問題,權力就會無法無天,橫行無忌。應該樹立憲法法律的權威,樹立法比權大的觀念,對此,《決定》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對法律懷有敬畏之心,牢記法律紅線不可逾越、法律底線不可觸碰,帶頭遵守法律,帶頭依法辦事,不得違法行使權力”[4]。必須堅決掃除權比法大、官比法大的流毒遺禍。
2 以民主集中制治理權力
解決黨政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必須依靠制度,走制度化、法治化的道路。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組織制度,也是國家的根本組織原則、法律制度。治理權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歸根到底,必須把民主集中制堅持好、完善好。民主集中制是關住權力最強、最嚴、最好的制度籠子。2015年1月12日,習近平在同中央黨校第一期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時強調指出,縣委書記“要帶頭執行民主集中制,按照程序進行決策,做到總攬不包攬、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要注意聽取班子成員意見,帶頭增進和維護縣委班子團結”[5]。這就為運用民主集中制治理權力,澄清權力盲區,防止權力過分集中,肅清權比法大的錯誤觀念,克服權力腐敗,正確行使權力,依法用權、秉公用權、廉潔用權,發揮民主集中制作為關住權力的強大而有效的籠子的作用,指明了根本的途徑。
當前,民主集中制對治理權力的作用發揮不夠,涉及對民主集中制這個根本的組織原則和組織制度在理論上沒有理解好、在實踐中沒有執行好的問題。當然,我們也還需要不斷發展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和制度規定。概括起來,運用民主集中制治理權力必須解決兩個關鍵問題,一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沒有被正確理解和執行出現偏差的問題;二是民主集中制作為制度,其本身確實也還存在著一些缺陷,需要加以改進和完善的問題。
先看關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沒有被正確理解和執行出現偏差的問題。民主集中制的定義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民主集中制在權力運行方面,為了貫徹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必須實行兩條重要的工作原則:一是集體領導,二是分工負責。實行集體領導,就是說凡屬于重大問題必須集體討論、研究、決定,這是決策權的問題。決策權不能歸于某個人,書記和委員是平等的,作決策進行表決時一人一票,必須實行少數服從多數,這就防止了個人或少數人拍板。實行分工負責,就是說經過決策定了要做的事情后,要有專人去承擔、負責,這是執行權。與決策權不同的是,執行權可以歸于個人,而且應該歸于個人。列寧曾經指出,民主集中制是一個好制度,但如果只有集體領導而沒有分工負責,那就會成為最壞的制度,出現最糟糕的情況。因此應要求,在執行過程中出問題了,任務沒有完成,某個人作為總負責人,要負起全部的責任。
那么,現在的問題出在哪里呢?主要就出在對民主集中制的這兩條工作原則,不能正確地理解和執行。首先,該集體決策的時候,沒有具體討論、研究,一個人或一兩個人可以隨意拍板定案,集體領導淪為一個人或少數人領導。為此,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健全依法決策機制。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機關內部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未經合法性審查或經審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討論”[4]。強調了民主集中制的鐵律,只有經集體討論,才能對重大問題作出決策。
其次,在分工負責的時候,沒有給分工負責的領導者以真正的職權,權力還是牢牢地攥在“一把手”的手中。現在,各級黨政領導班子和成員雖然也有一定的分工,每個領導成員也有分管的一塊,但可以說都沒有真正的實權,最終還要請示“一把手”,實際上這個分工不過是名義上的。可是,到了出問題的時候,因為是你分管的,又要讓你負責任,對你進行問責,所以,副職普遍感到很憋屈,實際上是為“一把手”而代責受過。那么,現在為什么會產生“一把手”不被問責,而由副職代責的悖謬情況呢?只能說明在我們現有的這個權力體制下,一些地方的“一把手”太過于強勢了,本來是他的責任,但他可以找到“替罪羊”,讓別人為他“背黑鍋”。對此,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要“全面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嚴格確定不同部門及機構、崗位執法人員執法責任和責任追究機制”[4]。真正執行民主集中制,就必須分清誰是行使執行權的負責人,出了問題,就要把責任落實到真正負責人的頭上。
再看民主集中制還有不完善的問題。這個不完善在于,民主集中制關于權力運行的工作原則,只涵蓋了決策權、執行權。那么,還有監督權呢?目前確實沒有這方面的原則規定,應該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漏洞。須知,決策權和執行權都需要受到嚴密監督,如果沒有監督,就會變形走樣。現在,恰恰缺了這么重要的一個原則。民主集中制作為根本的組織原則和組織制度,必須補上監督權方面的原則規定。只要是決策了、執行了,都必須受到有效的制約監督。民主集中制既然講了要分工負責、要講責任,就要對責任進行問責、追責。因此,民主集中制的工作原則,不應只限于現有的兩條,還必須加上第三條即監督問責的原則[3]。
關于對決策權的制約監督,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在論述“健全依法決策機制”時指出,“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對決策嚴重失誤或者依法應該及時作出決策但久拖不決造成重大損失、惡劣影響的,嚴格追究行政首長、負有責任的其他領導人員和相關責任人員的法律責任”[4]。這實際上已經肯定了在貫徹民主集中制、行使決策權時,必須同時包含監督問責的原則規定。
關于對執行權的制約監督,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努力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增強監督合力和實效”,“對財政資金分配使用、國有資產監管、政府投資、政府采購、公共資源轉讓、公共工程建設等權力集中的部門和崗位實行分事行權、分崗設權、分級授權,定期輪崗,強化內部流程控制,防止權力濫用。完善政府內部層級監督和專門監督,改進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的監督,建立常態化監督制度。完善糾錯問責機制,健全責令公開道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責令辭職、罷免等問責方式和程序”[4]。這更明確地強調了,在貫徹民主集中制、行使執行權過程中一旦出現問題,必須有問責、追責的原則跟進,而且規定了具體的五種問責方式。
3 切實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認真執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為公開制度,保證領導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權、權重不謀私。”[1]388習近平的論述,為運用民主集中制治理權力,指明了正確的路徑,給出了對癥下藥的方子。治理權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應采取下述三個措施。
一是進行分權治理。如前所述,權力結構是由“三權”即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構成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已提出,要“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6]。這就是說,決策權這一塊要做到科學決策,就要求實行集體領導;執行權這一塊要做到堅決執行,就必須落實分工負責;監督權這一塊要做到監督問責,就必須保證監督權的獨立性。我們要對權力進行分權,再不能由領導者個人掌管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分權的結果,就是明確領導者究竟享有怎樣的權力才是合適的權力。
首先,領導者特別是“一把手”擁有決策參與權。政黨和政府的活動及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對國內外重大問題和黨政重大事務包括重大人事安排作出決策。在實施這些重大決策的過程中,必須充分發揚民主,廣泛征求意見。決策是否可行,要采取會議表決的形式,達到過半數或三分之二的才能獲得通過。顯而易見,作為黨政各級組織和領導班子的“一把手”,在集體領導制度下,必須擁有參與決策的權力。而且,“一把手”在決策過程中還要發揮重要的作用,這就是要善于集中大家的好主意、好看法,或者自身能夠提出好主意、好想法并引導大家形成新見解、新共識。當然,“一把手”所擁有的這樣的決策參與權,不是權力的壟斷權。
其次,領導者擁有專屬執行權。在各級黨的委員會集體分工、個人負責的情況下,以及在各級政府中作為各級行政長官或行政部門主管的情況下,領導者具有完成任務的執行權,即首長負責制的辦事權力。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首長負責制的辦事權力,僅僅是為完成任務而具有的執行權力,具體地說,即是為執行和完成任務過程中所負有的一定的用事權、指揮權、督查權、處罰權等等。這樣的執行權是專屬的,必須是有職有權、實實在在、能夠令行禁止的權力。當然,領導者在行使這樣的專屬執行權時,必須遵守和符合黨規國法。
最后,領導者也享有紀律監督權。領導者所擁有的監督權,就是對班子其他成員和黨內其他人員在違紀違規違法方面的監督權。領導者中的“一把手”同樣享有黨的規章制度和法律規定所賦予的檢舉揭發權、罷免撤換權,以及控告權、申訴權、辯護權、保留意見權等等。當然,這樣的監督權和執行權不一樣,并不是唯一專屬于他的,他自身也要受到來自他人的監督和專門監督機構的監督[3]。
二是進行限權治理。對權力的限權,針對的是主要領導干部主管的權力,也就是分工管轄的實權、執行權。過去,主要領導者和“一把手”的權力太多、太大,諸如干部人事、財政金融、產業規劃、外資引進、工程項目等等,無不經由“一把手”。主要領導者和“一把手”的權力過大,這就有必要進行限權。最近,全國已有不少地方紛紛出臺了條例規定,對主要領導者和“一把手”的權力進行限權。比如媒體報道的,山西省、安徽省都要求黨政主要領導干部不直接分管人事、財務、工程項目等;安徽省還要求“一把手”實行“末位表態制”,也就是作決定時最后表態;國家海洋局要求各級領導班子要明確分工、保持制衡。又如,北京市西城區黨委常委的權力一共是116項,其中作為黨委“一把手”的區委書記有15項,作為行政首長的區長有19項[7]。而在過去,這樣的黨政“一把手”究竟手握多少權力,是講不清道不明的。
對主要領導者的權力進行限權治理,還要做到使權力公開透明。仍以北京市西城區為例,該區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全面理清各類行政權力,制定了權力清單和權力運行流程,將區政府68個職能部門、街道辦事處的9大類6 636項“行政權力清單”一一公開,同時張榜公布了2 128張“行政權力運行流程圖”,說明了行使權力的條件、承辦崗位、辦理時限、監督制約環節、投訴舉報途徑和方式等[7]。通過這樣的公開,就讓群眾知道政府手中究竟有多少權力,政府部門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類似北京市西城區這樣的做法,全國不少地方都在實行,既曬出了“權力清單”,也曬出了“權力流程”。這樣,群眾如果在辦事過程中遇有不明事項,就可以“按圖索驥”、查詢了解,從而將有效規范權力的行使,防止出現權力不作為和越權行為。
三是進行控權治理。對領導者無法進行有效權力制約監督的情況,可歸納為四個“不管”:上級管不到,同級不好管,下級不敢管,群眾管不了。四個“不管”,成為領導者監督難的主要原因。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要對權力實行有效的制約,必須擺脫監督過弱太軟的窘境。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確保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要確保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8]。權力要依法獨立行使,權力對權力要能夠依法獨立地進行監督制約,使領導者的權力受到有效的管控。
為了對領導者權力進行有效的管控,應著手實施以下四方面獨立的監督:第一,各級黨的紀檢委由同級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向其負責,作工作報告,接受同級黨的代表大會領導和上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直接領導。并且,各級黨的紀檢委主要受上級紀檢委直接領導。第二,各省、市、縣監察廳(局)和預防腐敗局不受地方黨委、政法委和地方政府的領導,成為一個由上至下的獨立機構,接受上一級直接領導,財政撥款和人事任命也由上級決定。第三,各省、市、縣的反貪污賄賂局不受地方黨委、政法委和地方政府的領導,成為一個由上至下的獨立機構,接受上一級直接領導。第四,各省、市、縣的法院不受地方黨委、政法委和地方政府的領導,成為一個由上至下的獨立機構,各省、市、縣的法院接受上一級直接領導。財政撥款、人事任命都由上級領導和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只有取得了這些監督的獨立性,才能保證對權力的制約監督真正落實到位。
參考文獻:
[1]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會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外文局,編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林平.管住“一把手”,限權比監督成本更低[N].檢察日報,2014-08-05.
[3]許耀桐.黨政“一把手”分權限權的若干認識[J].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14(6).
[4]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人民日報,2014-10-29.
[5]習近平同中央黨校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強調做焦裕祿式的縣委書記心中有黨心中有民心中有責心中有戒[N].人民日報,2015-01-13.
[6]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人民日報,2013-11-16.
[7]金國坤.按圖“索權”:權力透明運行的北京試驗[J].決策,2013(Z1).
[8]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2年11月8日)[N].人民日報,2012-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