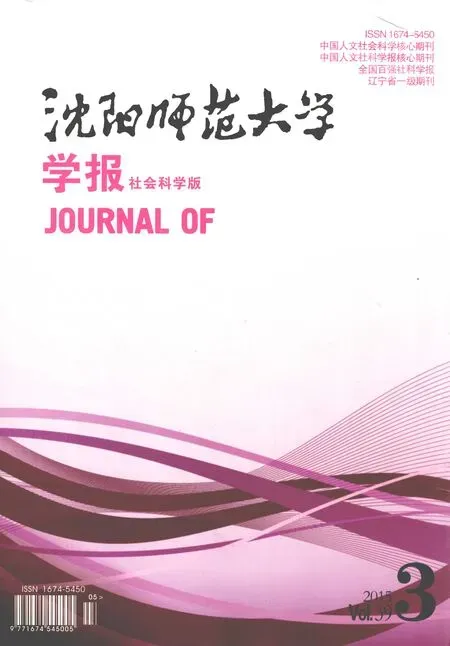滿通古斯語言文化研究的學術價值與政策建議
劉曉春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北京100081)
【關東文化與北方民族】
滿通古斯語言文化研究的學術價值與政策建議
劉曉春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北京100081)
東北亞地區跨界民族眾多,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東北亞文化共同體的構建,如果不考慮該區域民族文化多樣性的事實,以及族際、區域性的差異,有時會對國家造成一種文化危機或威脅,如語言安全、文化安全、生態安全等。所以,將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納入國際政治學的視野,探討民族這一客觀現象在區域合作中的結構與功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也符合東北亞文化共同體各國的長遠發展和利益訴求。研究東北亞滿通古斯諸民族,可以克服研究者只從單方國家研究跨界民族的缺陷,對東北亞文化共同體的構建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論文以中國滿通古斯語言文化歷史研究現狀為切入點,闡述了加強東北亞滿通古斯語言文化研究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提出了加大東北亞滿通古斯語言文化研究力度的政策建議。
東北亞;文化共同體構建;滿通古斯語族;研究現狀;政策建議
一、跨界民族與東北亞文化共同體的構建
滿通古斯語族為阿爾泰語系三大語族之一,是橫跨歐亞大陸的世界性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國的北方地區、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地區、蒙古國的巴爾虎地區和日本的北海道等地。
東北亞地區,是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分布最廣的地區。那里,跨界民族眾多,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跨界民族是指由于長期的歷史發展而形成的,分別在兩個或多個現代國家中居住的同一民族。所謂“界”是指國界,即國家疆界,通過疆界區分,劃分了各國的主權范圍,因而也使跨界民族與一般的民族概念有所區別。跨界民族除了文化的、群體的意義之外,也包括了所在國的主權和該民族對于所有國的國家歸屬認同。
東北亞跨界民族是那些東北亞土著和其傳統聚居地被分割在不同國家內而在地域相連并擁有民族聚居地的民族。主要是指東北亞區域內中俄跨界民族,中蒙跨界民族,中朝(韓)跨界民族,蒙俄跨界民族,俄朝(韓)跨界民族等。東北亞跨界民族具有跨界民族的普遍性特征,同時,也存在自身獨特的方面。如原來的土著被劃分成碎片,古老的滿通古斯文化不斷被弱化,文化可持續發展問題已成為該區域非常突出的問題。
東北亞地區,跨界而居的民族主要有俄羅斯人、朝鮮人、那乃(赫哲)、奧羅奇人、埃文基人(鄂溫克、鄂倫春)、滿族人、蒙古人、漢人、達斡爾人、愛斯基摩人等等。這些跨界民族,具有世代親緣關系。中國史書上記載:“黑龍江以北,精奇里江以南為虞人鄂倫春地”[1]。“鄂倫春、索倫、達乎爾類也,黑龍江以北,精奇里江以南,皆其射獵之地,其眾來精奇里以居”[2]。“黑龍江左崦40余屯,旗戶數百,有索倫人,有鄂倫春人,有打虎兒人。”[3]
僅以鄂倫春族為例,俄羅斯學者С.К.帕特卡諾夫寫道:阿穆爾州西部、外貝加爾州和雅庫茨克州與阿穆爾州交界地區的“真正的通古斯人”,被稱為鄂倫春人[4]。據俄羅斯1897年人口普查統計,阿穆爾州有677名鄂倫春人,外貝加爾州有952名鄂倫春人。阿穆爾州和外貝加爾州的鄂倫春人總數為1629人。其中6.1%已定居,其余則從事打獵、養鹿和捕魚。當時,92.9%的鄂倫春人講母語[5]。
19世紀,俄羅斯境內的鄂倫春人就已經劃分為使鹿通古斯和使馬通古斯。而在阿穆爾河兩岸林木茂密的河岸山坡和額爾古納河,以及農尼河的上游谷地,獵人們騎著小馬在興安坡地上來回行走,過著遷徙生活,其中有一些人跟達斡爾人一樣,從事貿易、耕作和畜牧業,過著定居生活。19世紀80年代,俄羅斯官方對生活在阿穆爾地區的鄂倫春人進行了人口普查。普查發現鄂倫春人主要有以下部族:坎德吉部,我認為這里指的是金德吉部,他的后裔至今仍居住在阿穆爾州,還有尼卡吉部、布爾多特部、尼納干部、波牙吉部,總人口946人(男474人,女472人)[6]。1900年,阿穆爾州的鄂倫春人口總數為460人(男218人,女242人)[7]。
俄羅斯科學院語言學研究所主任研究員、語言文學副博士Н.Я.布拉托娃女士認為,從1930年開始,居住在阿穆爾州、外貝加爾邊疆區和布里亞特地區的鄂倫春族群,被官方劃歸埃文基族,但把他們同化為埃文基人的過程比較困難,至今尚未完成。盡管有政府命令,但在20世紀中葉以前,很多埃文基人的身份證上“民族”一欄仍然寫著“鄂倫春”。“根據2002年人口普查數據,外貝加爾邊疆區只有5名鄂倫春人(講埃文基語),布里亞特3人,阿穆爾州3人。”[8]因此,中俄兩國邊界發生變化之后,俄羅斯的鄂倫春人成為埃文基人的一部分,開始被稱作“埃文基人”;而在中國他們被劃為“鄂倫春”這樣一個單獨的民族。
思想是有故鄉的,文化是有地域的,血濃于水,能走到一起的,應該是文化的共同體,而不完全是功利主義極強的經濟共同體和軍事共同體。一直以來,世界對東北亞關注的焦點主要是“政治、經濟和軍事”,其實最應該關注的是那里的文化和那里的民族。
“東北亞共同體”的構建,如果不考慮該區域民族文化多樣性的事實,以及族際、區域性的差異,有時會對國家造成一種危機或威脅,如語言安全、文化安全、生態安全等。所以,將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納入國際政治學的視野,探討民族這一客觀現象在區域合作中的結構與功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也符合東北亞共同體各國的長遠發展和利益訴求。
因此,研究東北亞滿通古斯諸民族的歷史與文化,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和國家問題。如何保護跨界民族的文化發展權力?這個問題只有通過東北亞國家之間的合作才能實現。研究東北亞滿通古斯諸民族,可以克服研究者只從單方國家研究跨界民族的缺陷,對東北亞文化共同體的構建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如何研究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文化,如何認識滿通古斯民族的歷史與功能定位?筆者認為,研究滿通古斯文化必須要有全球意識、當代意識、歷史意識、國家意識、民族意識、權利意識、發展意識、安全意識和問題意識。在亞北極地區,滿通古斯諸民族分布在多個國家,中國的滿通古斯諸民族使北極文化延伸到我們面前。滿通古斯語言文化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倫理道德價值、審美價值、生態價值、經濟價值、宗教價值和考古價值。因此,研究滿通古斯語言文化,僅僅研究中國的滿通古斯諸民族是遠遠不夠的。
二、中國滿通古斯語言文化歷史研究現狀與功能定位
(一)中國滿通古斯語言文化歷史研究現狀
中國滿通古斯語族所含諸民族主要居住在黑龍江、遼寧、吉林、河北、北京、內蒙古、新疆等省、市、自治區。據2010年人口統計,滿通古斯諸民族共有人口10 623 327人。其中,滿族人口為10 387 958人,錫伯族人口為190 481人,鄂溫克族人口為30 875人,鄂倫春族人口為8 659人,赫哲族人口為5 354人。根據學者統計,其中使用母語者約3萬人。當前我國的滿通古斯諸民族,已全范圍地面臨本民族語的瀕危難題或即將開始的瀕危問題,對滿通古斯語族語言文化進行搶救和研究刻不容緩。
在中國境內,滿通古斯語族包括滿語、錫伯語、赫哲語、鄂溫克語、鄂倫春語和歷史上的女真語。滿通古斯語族下分滿語支和通古斯語支,滿語支包括滿語、女真語、錫伯語;通古斯語支包括鄂溫克語、鄂倫春語、赫哲語;在俄羅斯境內,通古斯語支包括埃文基語、埃文語、涅基達爾語、那乃語、烏利奇語、奧羅克語、奧羅奇語、烏德蓋語等。滿通古斯語族除了與蒙古語族、突厥語族有著密切關系外,還與日本的阿伊努語、日本語、朝鮮語、美國和加拿大等地的愛斯基摩語、因紐特語、印第安語等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滿通古斯諸民族至今保存著人類早期文明的諸多形態和特征,并且該族群相互間關系具有諸多的神秘性與擴散性,以及歷史來源的復雜性和文化習俗的豐富性。因而,滿通古斯語言文化研究愈來愈引人注目,成為國際學術熱點。
20世紀以來,經過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中國滿通古斯語言文化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學者們從語言學、民族學、人類學、文化學、歷史學、宗教學、文學、民俗學等不同角度對滿通古斯語言文字、歷史、文化、文學、宗教、民俗等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近年來,有的學者還打破原有的學科界限,對相關問題進行跨學科綜合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為本領域研究帶來了新的活力與生機。到20世紀90年代,滿學開始從人文學科中逐漸形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通古斯學亦日趨發展成熟。[9]然而,跨國界研究卻很薄弱,尤其是對東北亞地區相關國家滿通古斯語言文化歷史研究不足,有些研究尚處于空白狀態。
(二)加強東北亞滿通古斯語言文化研究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1.滿通古斯語族諸語言,是我國北方重要的民族語言,這些語言均已進入或即將進入嚴重瀕危狀態。研究東北亞地區滿通古斯語族諸語言及文化,有助于彌補中國阿爾泰語系語言研究領域一直以來存在的某些不足。
2.加強國際滿通古斯語族諸語言文化研究,對我國滿通古斯諸民族語言文化安全,強化我國在此學術領域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均有積極作用。
3.加強滿通古斯語族與阿爾泰語系其他語言以及東北亞諸民族語言的比較和對比研究,對我國滿通古斯語族語言研究體系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4.我國大小興安嶺地區以及俄羅斯遠東地區是傳承森林文化的主要母體。森林文化與森林地帶構成共生共存的關系,森林是產生森林文化的母體,森林文化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產業的物質母體,是繁榮發展民族文化產業的基石,是滿通古斯森林民族深刻的歷史記憶,是森林民族知識和智慧的結晶。
5.是加強我國民族團結和邊疆穩定的前提。東北亞地區是滿通古斯諸民族集中分布區,中國東部邊境的穩定事關全國穩定的大局。
6.信奉薩滿教的滿通古斯人,對自然的保護是整體的,是沒有任何功利和欲望的。薩滿教倡導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理念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和存在價值。考慮到“確信則有”的心理暗示作用,即使在物質極度豐富的當下,薩滿的精神療法依舊重要。因此,薩滿教參與社會關懷具有重要意義。薩滿文化的價值在理論上不斷被認可,但在現實中,其文化功能卻依然停留在社會的邊緣,薩滿教的社會功能尚未得到很好發揮。因此,對滿通古斯薩滿文化進行深入探討和適當扶持,不僅有助于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保護,也有助于推動東北亞地區社會的和諧與發展。
三、加大滿通古斯語言文化研究力度的建議
(一)深化滿通古斯語言文化基礎理論研究,拓展應用研究,從人類學的視角對滿通古斯語言文化進行多方位綜合研究。加強滿通古斯語言文化理論深層次研究,深化滿通古斯語言文化與相關學科結合研究,加強滿文文獻的整理和科學分類研究,加大滿通古斯語言文化的搶救調查及有關資料的數字化處理工作。繼續深化滿通古斯語族語言研究工作,加強語言學與史學等其他學科的交流和互動,推動多學科、跨學科合作。
(二)進一步加強國際交流與國際合作。如訪問講學、雙邊研討、合作課題、交換成果、查閱資料以及國外田野調查等。在滿通古斯語言文化的研究及發展中,國內外的專家學者應進一步加強聯系,互通信息,密切合作,對重大課題、難點課題進行聯合攻關,從而取得突破性成果。
(三)加強滿通古斯語料庫建設。滿語已經處于瀕危狀態,滿語口語是研究滿族語言文化的第一手珍貴資料,也是滿學及相關學科研究的活化石,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然而,受各種歷史因素與社會因素的影響,滿語口語日趨消亡。滿學專家趙阿平女士認為,語料庫建設是現代語言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是利用計算機信息技術深化語言應用與研究的新方向,對于保存瀕危的滿語與浩瀚的滿文檔案翻譯工作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與應用意義。建立滿語語料庫,能夠永久保存滿語語料等珍貴的文化遺產,為滿語本體深入研究奠定基礎。同時,在滿語語料庫基礎上,建設滿漢雙語平行語料庫,以解決滿文檔案的初步翻譯問題,將有助于快速改善目前我國現存的大量滿文檔案缺乏人才翻譯整理的狀況,提高滿文文獻研究和開發利用的工作效率[10]。
(四)設立滿通古斯重大工程項目,并投入相應專項經費,使政府、高校、科研機構協同開展瀕危語言保護工作,集中人力物力,多方協作。開展瀕危語言資料的保存和搶救工作,陸續調查研究和刊布瀕危語言資料,出版瀕危語言學專著和詞典,建立計算機詞匯語音數據庫,用多媒體技術、錄音和錄像等現代化手段,大量保存民族語言中各類民間文學作品等聲像資料[11]。
(五)加大滿通古斯語言文化專業后備高層人才的培養力度,如碩士生、博士生等,加強研究隊伍建設,保障研究持續發展,在民族聚居區開展切合實際的雙語教育。趙阿平女士認為,在對領軍人才給予各方面關心和支持的同時,也要關注領軍人才帶領的隊伍,加強對滿通古斯語言文化研究團隊的投資。建立瀕危語言保護網站、論壇,讓傳媒機構更多地關注瀕危語言的狀況,定期召開學術會議,通過這些措施交流經驗、交流成果,擴大社會影響。
(六)建立滿通古斯瀕危語言文化生態保護區。保護瀕危語言生存和發展區域、保護少數民族聚居區、瀕危語言保護示范區等,使民族語言的文化生態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和保持。重點推進搶救保護瀕危語言滿語、赫哲語、鄂倫春語,切實保護和扶持瀕危語言傳承人。如以黑龍江省為例,齊齊哈爾三家子村滿語遺存地;佳木斯、同江赫哲語遺存地;黑河愛輝區新生鄉、呼瑪白銀納鄉、塔河十八站鄉鄂倫春語遺存地等[10]。
(七)建立中國滿通古斯學博物館。在中國東北三省,各類博物館比比皆是。但國家級的民族學博物館、滿通古斯學博物館尚未建立,與東北亞其他國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以日本為例,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是日本引以為豪的博物館,這里不僅以地球上的所有地區和民族為對象進行收集和展出,而且進行深入的研究。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是日本國內唯一的民族學研究機構,收藏有世界各地區、各民族的文物、標本約11萬件,展出約7 000件。陳列室分成大洋洲、美洲、歐洲、非洲、西亞、東南亞、中北亞、東亞8個地區,介紹世界各民族的歷史、文化和生活。此外,還設“世界語言文字”和“世界民族音樂”兩個專題陳列室。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建立滿通古斯學博物館具有重要的國際意義。
(八)建立東北亞滿通古斯語言文化歷史研究中心。滿通古斯語言文化研究作為國內外學術界特殊關注的學術領域,極具民族文化特色與國際學術交流優勢。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高科技迅猛發展,豐富多彩的民族傳統文化遭遇了空前的生存危機。在滿通古斯語族語言中,女真語作為一種消失語言已經不被使用,滿語、赫哲語、鄂倫春語都已成為嚴重瀕危語言,錫伯語、鄂溫克語也即將進入嚴重瀕危狀態。在這樣的緊迫形勢面前,對這些瀕危及嚴重瀕危語言的詞源、研究歷史、基本詞匯進行全面系統研究,對于我國民族語言和文化資源的搶救與保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因此,以國家研究機構和高校為依托,搶救滿通古斯諸民族語言、文化遺產,進行科學系統的綜合研究顯得十分緊迫。
(九)中國在東北亞諸國建立滿通古斯文化研究基地,占領學術制高點。比如,在俄羅斯極北、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生活著一些人數很少、語言文化、宗教信仰和經濟活動都頗具特色的少數民族。他們是涅涅茨人、埃文基人、漢特人、曼西人、埃文人、那乃人、楚科奇人、多爾甘人、利里亞克人、謝爾庫普人、烏爾奇人、尼夫赫人、烏德蓋人、愛斯基摩人、克特人、薩米人、伊捷爾緬人、恩加納善人、尤卡吉爾人、托法拉爾人、涅吉達爾人、奧羅奇人、奧羅克人、埃涅茨人和阿留申人等25個民族[11]。其中,大部分是通古斯人。因此,只有在俄羅斯滿通古斯民族聚居地,建立研究基地或實習點,才能對東北亞滿通古斯諸族進行全面了解。如果不做長遠規劃,未來中國在東北亞地區文化陣地上的話語權將大為缺失。
[1]萬福麟,修.黑龍江志稿[M].1933,卷11:3.
[2]何秋濤.朔方備乘[M].清光緒七年石印本卷2:6
[3]徐宗亮.黑龍江述略[M].觀自得齋叢書卷6,從錄篇.
[4]С.К.帕特卡諾夫.西伯利亞居民部落成分統計數據,異族人的語言和部族(根據1897年專門研究數據)[M].圣彼得堡,1913:88.
[5]С.К.帕特卡諾夫.西伯利亞通古斯部落統計和地理經驗(根據1897年人口普查數據和其他來源)[M]//第一部分(通古斯專輯);其他通古斯部落∥俄羅斯帝國地理學會民族志分部學術論文集[C].圣彼得堡,1906:13.
[6]阿穆爾州阿穆爾河上游過著游牧生活的使鹿通古斯(鄂倫春)資料∥東西伯利亞治理主要官方文件選集[G].伊爾庫茨克,1883:79.
[7]阿穆爾州國家檔案[G].全宗號15,目錄號1,輯號173,頁號75.
[8]索科洛夫斯基.С.В.俄羅斯聯邦民族政策構想的發展前景[M].莫斯科,2004:221.
[9]趙阿平.中國滿—通古斯語言文化研究及發展[J].滿族研究,2004(2).
[10]趙阿平.滿通古斯語族語言文化研究新發展[N].中國社會科學院報,2014-08-08(3).
[11]劉曉春.俄羅斯民族經濟與改革[M].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9:84.
【責任編輯曹萌】
H172.1
A
1674-5450(2015)03-0028-04
2015-03-08
劉曉春,女,黑龍江黑河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主要從事民族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