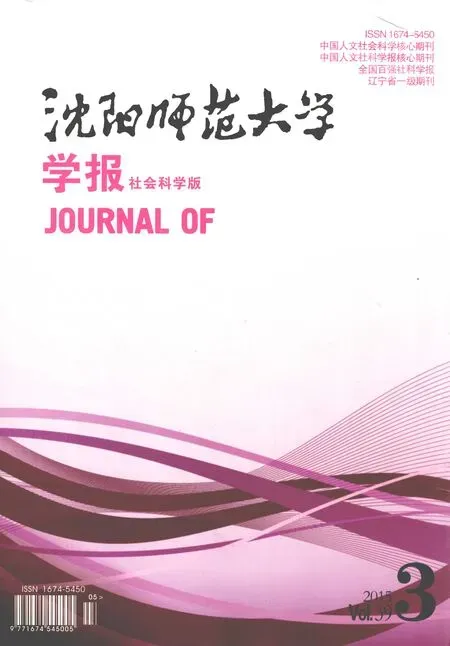馮夢龍文藝思想對李漁的影響——以擬話本小說創作為例
韓亞楠,張寧
(1.遼寧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遼寧沈陽110036;2.沈陽理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遼寧沈陽113122)
馮夢龍文藝思想對李漁的影響——以擬話本小說創作為例
韓亞楠1,張寧2
(1.遼寧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遼寧沈陽110036;2.沈陽理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遼寧沈陽113122)
在明代擬話本創作者中,馮夢龍無疑是貢獻最為突出的一位,他的"三言"不僅為擬話本小說創作樹立了典范,而且這些擬話本小說集鮮明地代表了馮夢龍的文藝思想。與之生活時代相去不遠的李漁,在進行擬話本小說創作的過程中,受馮夢龍影響頗深。
馮夢龍;文藝思想;李漁
馮夢龍是明代杰出而多產的擬話本小說作家,為中國通俗文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其擬話本小說集“三言”的創作,奠定了他在中國小說史上的重要地位。生活在明清之際的李漁也是一位在當時獨樹一幟的擬話本小說作家,其擬話本創作受馮夢龍影響頗深,并在繼承前者思想的基礎上另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與闡釋。
一、重視小說教化人心的社會功用
文學屬于意識形態領域,與社會的政治、經濟、人文風俗、思想傳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幾乎都承擔了一定的社會內容,發揮著或大或小的社會功用。那些審美中蘊含大量道德倫理內核的作品不僅能夠在封建文化環境下生存下去,而且易于被普通人接受。中國古代的作家深諳此道,都在力圖使自家的作品具備如此審美取向,生活在晚明時期的馮夢龍亦不例外。他在小說創作中非常注意強調文藝的社會性,也就是重視作品的教化與倫理作用。
那么,在此之前需要解決小說的地位問題,只有小說“名正”了,方可“言順”——說這種文藝形式具有教化人心的作用。中國古典小說從萌芽時期起就在以史學為正統的文化影響下生存,少受重視,但幸好沒有一直遲滯不前。至明代,小說創作雖已取得巨大進步,但文化地位仍顯尷尬。如何解決小說所處之正名與傳道的兩難境地,馮夢龍頗費苦心。他在《古今小說》序中提出“史統散而小說興”的觀點,在回顧小說發展歷程的基礎上認為:“大抵唐人選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諧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則小說之資于選言者少,而資于通俗者多。”[1]2馮子猶在此不僅將小說創作納進史統文化領域,還結合了市民階層的欣賞品味,提出重視通俗小說的觀點。這樣做并非心血來潮,欲使小說在傳統話語權面前獲得一定地位,就必須凸顯小說有裨益于世道人心的方面,馮夢龍看中了小說所具有的強烈藝術感染力和通俗易懂的特點,最大限度地發揮著小說的社會教育作用,傳播教化德育思想。“試今說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日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1]2-3馮氏將通俗小說與《孝經》《論語》這樣的儒家經典之作相提并論,認為后者在教化人心方面甚至不如小說,無形中大大提升了小說的社會價值。秉承著這樣的創作理念,馮夢龍在對“三言”篇目進行選擇時非常注意選取那些具有教化意義的題材。《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命名已經表達了作家的良苦用心,就是希望利用小說取得警醒世人、改變世風的藝術效果。他曾這樣描述“三言”的創作宗旨:“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世俗也。恒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2]既要通俗,又能導愚、啟迪人心,馮夢龍對“三言”產生教化作用寄予了很大的期望,無論是利用入話勸善懲惡、通過故事表達善惡有報的觀點,還是以道德化標準點評人物命運結局,馮氏小說緊緊圍繞著“教化”二字展開。《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一則講述了淫亂女子失去正妻之位最后淪為妾室,好色男子終因漁色而命喪黃泉的故事,無論是情節內容本身還是入話中的《西江月》詞,都在勸人不要好色貪淫。相同的主旨,在“三言”中就還有《何大卿遺恨鴛鴦絳》《金海陵縱欲亡身》等諸多篇目。其他諸如戒嫖賭、表貞節、寫報應、倡忠義等主題,相關篇目在小說集中同樣俯拾皆是。
馮夢龍重視小說教化作用的文藝思想影響了李漁對擬話本主題的選擇,二人生活時代雖有較大差異,但在此問題上非常有默契。李漁的《十二樓》又名《覺世名言十二樓》,是仿效馮氏“三言”最好的明證。此外,李漁還多次利用“三言”中的情節講述相似故事,大發引論。李漁認為,“作書之旨不在主而在客,……要使觀者味此,知非言過之難而聞過之難也。覺世稗官之小說大率類此。其能見收于人、不致作覆瓶抹桌之具者,賴有此耳。”[3]291認為小說應該使讀者在精神上有所領悟,不能僅僅當成休閑娛樂、過目即忘的玩笑。以《無聲戲》為例,第五回《女陳平計生七出》、第六回《男孟母教合三遷》,倡導貞節觀念;第七回《人宿妓窮鬼訴嫖冤》、第八回《鬼輸錢活人還賭債》,提倡戒賭;第九回《變女為兒菩薩巧》、第十回《移妻換妾鬼神奇》,討論果報不爽;第十一回《兒孫棄骸骨僮仆奔喪》、第十二回《妻妾抱琵琶梅香守節》,表彰忠義。在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李漁在《無聲戲》中每表達一個教化思想,都會選擇兩則緊鄰的故事加以闡釋,對某一教化主題進行反復言說,這樣的結構安排,無疑出于作家希圖強化受眾接受認可的心理。
有時,李漁利用小說教化人心比馮夢龍更加現實真切。《無聲戲》第七回《人宿妓窮鬼訴嫖冤》源自馮夢龍《醒世恒言》第三卷《賣油郎獨占花魁》,情節、人物身份均照搬馮氏作品,但是小說并沒有按照秦重與王美娘的愛情路線發展。《無聲戲》中的這位篦頭待詔錢財被騙還受到名妓雪娘的言語奚落,如果不是有運官為其主持公道,錢財定會盡失無回。李漁對此大發議論:“奉勸世間的嫖客及早回頭,不可被戲文小說引偏了心,把血汗錢被他騙去,再沒有第二個不識字的運官肯替人扶持公道了。”[4]這篇小說打破了人們心中那旖旎的愛情泡沫,直指社會現實,雖有不解風情之嫌,但更加實用真切。足見李漁對社會現實的清醒程度,其小說在教化人心、勸導世人方面的多側面、多維度。
與馮夢龍有所差異的是,李漁將勸善懲惡思想使用得更加游刃有余,他討論的范圍突破了入話,開始融匯到小說講述過程、小說評論內容中,而且帶有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風格。馮夢龍受晚明心學影響頗深,任情重性,但他又按照封建文人的標準要求自己,重視道統。這就使得馮夢龍小說創作處于既要適俗重情又要強調道統的兩種張力之下,以通俗文學進行教化宣傳是他為小說創作所尋求到的最佳平衡點,“三言”中那些反復說教天道輪回、果報不爽觀念的篇目就是最佳代表。李漁則是一位商業化的文人,亦可視為文人化的商人,他的文學創作直接關系生計,是否符合市場需要是他不可忽視的問題。因此李漁在宣揚傳統道德觀念、勸懲世人時,也沒有忘記娛樂人心:他改編與“三言”相似的故事,使情節更加離奇曲折;在開篇、文中、結尾穿插大量詼諧幽默的議論性文字;甚至虛構一個故事,突破了馮夢龍所建立的擬話本小說體例,寫作不僅更加自由靈活,內容也更具娛樂性。這就使簡單枯燥的說教內容變得生動有趣,也更易于被受眾認可。
二、對小說適俗功用的闡述
衡量通俗小說成功與否的標準就是看其能否為廣大讀者所接受,因此適俗是明清擬話本小說創作的另一要素。在馮夢龍、李漁的擬話本小說中,適俗表現為:以自寓性故事、以當代所見新奇事物拉近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大量描繪、講述愛情婚姻故事以滿足讀者閱讀審美。
撰寫自寓性故事不僅能夠滿足讀者對作者的好奇心理,而且能夠抒發作者的個人感情。《警世通言》第十八卷《老門生三世報恩》的主人公鮮于同身上就有馮夢龍的影子。鮮于同八歲被稱作神童,十一歲游庠,超增補廩,是個有大學識的人物。此人心氣極高,看不上貢途的前程,從三十歲開始一連讓了八遍貢,到五十七歲時,頭發都白了,還只是個秀才,可謂才高運蹇。目前的研究資料顯示,馮夢龍少年時期頗有文名,頗受同輩推賞,但屢試不第,由此郁郁難歡而寄情青樓舞場,更傳有與妓女侯慧卿的一段佳話。崇禎七年始得出貢,此時他已五十七歲。崇禎七年六十一歲時出任福建壽寧知縣,不就便辭官回鄉。作者與小說主人公的身世極為相似,馮夢龍還借鮮于同之口表達了他對科舉、官場的諸多看法。稍有不同的是,鮮于同的官途雖然開始較晚,但平順美好,這可看作馮夢龍對自己蹉跎人生的一種心理補償和對人生晚景的一種美好期許。
與馮夢龍創作手法接近,李漁也在小說作品中有自寓性的描述。李漁生平有兩大愛好:辨審音樂、置造園亭。“創造園亭,因地制宜,不拘成見,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裁。”[5]156如李漁所言,他生平極喜建造園林亭樓,曾于順治五年、康熙八年、晚年移居杭州后分別建造了伊山別業、芥子園、層園三處住宅。在擬話本小說《三與樓》中,主人公虞素臣“一生一世沒有別的嗜好,只喜歡構造園亭,一年到頭,沒有一日不興工作。所造之屋定要窮精極雅,不類尋常”[3]54,但虞素臣因家庭生活所迫不得不將所建之“三與樓”逐步賣與唐家父子,唐家獲罪后虞素臣兒子虞繼武歷經磨難終于將此樓買回,完成了父親的心愿。虞素臣就是李漁的化身,李漁一生所建三處庭園,都賣與他人。雖然《三與樓》的刊刻時間應在順治十五年左右,此時李漁的芥子園和層園尚未建立,但并不影響他對賣樓經歷的深刻回憶,他在賣樓后所作的七絕《賣樓徙居舊宅》、七律《賣樓》就被寫入《三與樓》的開篇當作入話,借助虞素臣之事表達了自己賣樓時的無奈與不舍。而“三與樓”完璧歸趙的結局,也暗含李漁希望能夠回歸舊園的美好暢想。
這些自寓性的小說不僅可以滿足作家的補償心理,還能令讀者了解作家經歷、思想,從而拉近相互之間的距離。
此外,李漁生平尚奇,對新鮮事物有較大熱情,他在擬話本小說就選取了當時流行的新鮮事物進行描寫,這也是他適俗思想的一種表現。《夏宜樓》中男主人公瞿生不僅贏得了美女詹小姐的愛情,而且將詹家眾多美貌丫鬟收入房中,他能夠成就齊人之福的秘密武器是一件新奇物件——千里鏡,也就是今天的望遠鏡。由此小說文本在這里不僅是娛樂性文體,更是介紹新知的工具。
除了進行自寓性創作,馮夢龍、李漁還寫下了大量有關愛情婚姻的故事,這也是他們重視小說適俗功用的一個表現。晚明的思想解放潮流裹挾著巨大的力量沖決了以往封建禮教所設下的重重阻礙,蕩滌著人們的心靈。即使清初政府加強文網收縮、施行高壓手段的文化政策,也不能立刻將人們的審美視域調整如初,提倡性靈、歌頌真情是明末清初文學文化的審美取向。馮夢龍、李漁就順應了這一潮流,同時也在擬話本小說創作中有各異的表達方式。
馮夢龍提出“情教”之說,進一步發展了李卓吾、湯顯祖的主情思想。湯顯祖認為情與理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形態,《牡丹亭》是他真情至上、以情反理的代表作。馮夢龍顯然不愿完全按照湯氏的“唯情”模式進行創作,他在肯定湯氏的基礎上努力把傳統倫理、時代思潮調和為一體。“自來忠孝節烈之事,從道理上做者必勉強,從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婦其最近者也,無情之夫,必不能為義夫;無情之婦,必不能為節婦。世儒但知理為情之范,孰知情為理之維乎。”[6]36他認為情、理不是處在天平兩端不可統一的產物,帶有真情的忠孝節義是最好的處理方式,這樣做既能考慮到傳統道德文化的影響,同時更能“合理”地闡述真情。于是,馮夢龍順理成章地提出“情教”說,將情提升到無以復加的崇高地位。“天地若無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無情,不能環相生。生生而不滅,由情不滅故。四大皆幻設,惟情不虛假。有情疏者親,無情親者疏。無情與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誨諸眾生。”[6]1馮猶龍將情視為天地間萬物生存、互相連結的紐帶,這與道家所推崇的“道”處于同一地位,甚至欲建立具有宗教性質的“情教”,以情行教化人心之實。馮夢龍的“情”,內容極為廣泛,既有親情、友情,也有愛情,顯然后者更為廣大讀者所津津樂道。他在“三言”中描繪的愛情純潔、美好、大膽、自由。《賣油郎獨占花魁》中秦重只是個小本生意人,每天所獲利潤非常微薄,但他能夠為見王美娘每日節衣縮食,相會之夜悉心照料佳人而無逾矩行為,更是在美娘落難之際伸出援手。秦重的行為贏得了美娘的芳心,兩人的感情真摯、美好。秦重是馮夢龍傾力打造的“情種”,他借由這一人物展示了真情的可貴、純真。《吳衙內鄰舟赴約》中吳衙內與秀娥小姐這對小情侶定情速度顯然比秦重、王美娘快得多,一見鐘情之下吳衙內決定過船私會,卻因風浪未能及時返回吳家座船,秀娥小姐大膽決定將情郎藏在自己船中,每日照料衣食。被雙方父母發現后,兩人終結連理。如果不是有熱烈感情作為支撐,熟知封建禮教的兩個年輕人也不會有如此大膽的舉動。
馮夢龍的故事顯然影響到李漁的擬話本創作,他在小說中也歌頌了真摯的感情。《譚楚玉戲里傳情劉藐姑曲終死節》中譚楚玉和劉藐姑互相鐘情,但礙于戲班規矩不能成就眷屬,無奈之下兩人只得在臺上演出時借助人物口吻韻事談情說愛,“做到風流的去處,……竟像從他骨髓里面透露出來,都是戲中所未有的,一般使人看了,無不動情。做到苦楚的去處,那些怨天恨地之詞,傷心刻骨之語,竟像從他心窩里面發泄出來”[7]。但他們的愛情沒有得到家長的允許,劉藐姑因此含恨赴水,譚楚玉慷慨追隨。兩人最終感動了神靈,幫助他們成為真正夫妻。在此則小說中,李漁推舉真情,這是馮夢龍“情教”思想的延續。但李漁是個享樂主義者,真情與享樂相比要稍顯遜色。“行樂之地,首數房中”[5]338,房中之愛即為性愛,縱觀李漁的小說作品,絕大數作品都描寫男主人公一妻多妾,大享齊人之福。以《十二樓》為例,《奪錦樓》中的兩位小姐歷經退婚風波,好不容易在官府主持之下各自婚配,結果卻發現如意夫婿為同一人,最后一同嫁給此男。《夏宜樓》中瞿生對詹小姐愛慕非常,費盡心力終于得到女方父母首肯覓得佳緣,但他色心仍熾,因在觀察佳人的過程中利用千里鏡還看過其他女婢的嬉水場景,知曉她們的身體特征,以此調笑,實際上也取得了對這些女性的占有權。《無聲戲》中另有一個更加特殊的故事:一個長相極為丑陋、無才無德、穢氣滿身的男子,憑借手中的財富娶到三位貌美聰明的妻子,妻子們心中雖有不甘甚至曾經反抗,但最終還是屈服于男權道統,陪伴無德無貌的丈夫安心度日。在這個故事中,女性的權益沒有得到尊重,只考慮到男性的“夫綱”,真情已經不是作家的描寫重點,他重視的是男性的享受歡樂。
李漁的其他小說作品中,尚有對男女情事的描寫片段,雖不至露骨難讀,也是頗為香艷。與馮夢龍的真愛、真情相比,李漁的愛情似乎更加物質化、更為情欲化,他筆下的大多數男主人公們與其說在尋覓愛情,還不如看作是在追尋愛欲。雖然在如何看待真情這個問題上,馮夢龍、李漁的取舍標準不盡相同,但并不妨礙他們小說發揮適俗的社會功用,受眾有欣賞馮氏純真戀情的,也有享受李氏新奇熱烈愛欲的,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他們的愛情婚姻小說都能夠達到讀者的期待視野,滿足受眾的審美享受。可以說,兩位作家擬話本小說適俗的社會功用一次次得到充分發揮,他們的創作均取得了巨大成功。
[1]馮夢龍.古今小說.馮夢龍全集:第一冊[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2]馮夢龍.醒世恒言.馮夢龍全集:第三冊[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1.
[3]李漁.十二樓.李漁全集:第九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291.
[4]李漁.無聲戲.李漁全集:第八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146-147.
[5]李漁.閑情偶寄.李漁全集:第三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156.
[6]馮夢龍.情史:卷一.情貞類·朱葵.馮夢龍全集:第七冊[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36.
[7]李漁.連城璧.李漁全集:第八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260.
【責任編輯楊抱樸】
I207.41
A
1674-5450(2015)03-0089-03
2014-01-18
2014年度遼寧社會科學規劃基金(L14DZW014)
韓亞楠,女,遼寧大連人,遼寧大學文藝學博士研究生;張寧,女,遼寧沈陽人,沈陽理工大學講師,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