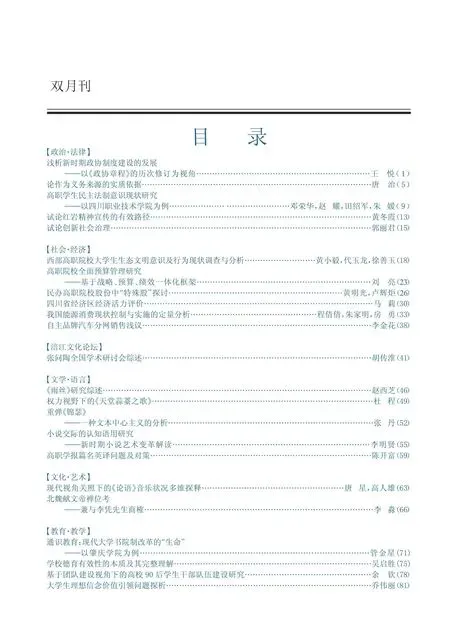論作為義務來源的實質依據
唐治
(四川大學法學院,四川 成都 610207)
論作為義務來源的實質依據
唐治
(四川大學法學院,四川 成都610207)
摘要:我國刑法理論中關于作為義務來源并沒有實質依據,這說明我國的不純正不作為犯理論尚需創新。德國關于作為義務來源的實質依據包括保證人說、實質違法觀、整體考察法、刑法獨立觀、公共福祉說。這些學說的引薦與分析可以為我國刑法理論中關于作為義務來源之實質依據的創新,提供比較法意義上的借鑒以及資料性的啟示,以推動我國刑法理論在不純正不作為犯上的理論創新。
關鍵詞:作為義務來源;實質依據;不純正不作為犯
不純正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來源(保證人地位)的實質依據,在我國刑法理論中,并沒有得到闡述。這一點不同于德日刑法理論。然而,法學是一門說理的學問。作為義務來源于何處必須得到充分論證,才能從邏輯上符合法學的特質。作為義務來源的代表性實質依據,除了下文所闡述類型,還有考夫曼(Kaufmann)的社會功能關系說、麥耶(M ayer)的信賴關系說、羅克辛(Ro x in)的支配說、雅科布斯(Jakobs)的組織管轄說。限于篇幅,本文不探討上述學說,而是詳細探討德國刑法理論中的代表性實質依據,為我國的作為義務來源尋找一個符合我國立法、學說與實務具體情況的實質依據,提供比較法意義上的借鑒。
1 保證人說
不純正不作為犯何以與作為犯罪具備等價性,即同等可罰性?這是不純正不作為犯首當其沖難以避免的問題。路登(L uden)身先士卒,提出因果關系說,即不作為是否與作為具備等價性,取決于不作為是否具有原因力。但費爾巴哈以違法性說反駁之,認為等價性在于不作為與作為是否具備違法性。費爾巴哈的學說當時未受重視,到19世紀末,被李斯特(L is z t)舊話重提,遂成通說。違法性說分為形式違法性說和實質違法性說。前者以法律條文為作為義務的實質依據,后者以倫理道德為作為義務的實質依據。為批判當時風行一時的實質違法性說,那格勒(Nagler)提出保證人說。[1]
保證人說認為,刑法分則除了少數純正不作為犯之外,其他構成要件均為作為犯。不純正不作為要與作為具備等價性,必須具備作為犯的構成要件該當性。不純正不作為如何具備作為犯的構成要件該當性?很簡單,取決于不作為者是否為具備特殊法律地位的保證人。怎么界定特殊法律地位?也很簡單,具備防止結果發生義務的人即為保證人。那格勒還認為,刑法禁止規范包含命令規范,因此作為包括不作為。
筆者認為,保證人說,有兩大矛盾。一方面,其認為禁止規范包含命令規范,依據何在?按那格勒所言,刑法分則也規定了少數純正不作為犯,為何非以刑法明文規定,才有命令規范獨立存在的空間,一旦刑法無規定,命令規范只能寄于禁止規范的籬下,而無獨立位置?應當肯定,刑法包含禁止規范和命令規范,兩者在哲學上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命令規范始終有獨立存在的空間,就不純正不作為犯而言,命令規范并非位于禁止規范之下,而是與禁止規范并駕齊驅、同等存在。與其將命令規范生拉硬湊在禁止規范之下,不如坦率承認兩者具備同等空間、同等地位。另一方面,按保證人說,不純正不作為犯使用作為犯的構成要件,既然構成要件相同,為何不純正不作為犯須附加“不作為者為具備特殊法律地位的保證人”這一要素?這一要素究竟歸屬于作為犯構成要件,還是不純正不作為犯構成要件?恐怕那格勒也自圓其說。
2 對保證人說之評判
保證人說一經提出,出盡風頭,有人批判,有人擁護。無論批判還是擁護,都或多或少提出了新觀點,正因觀點激蕩,作為義務的實質依據在爭議中逐漸成熟。批判者以格林瓦爾德(Grüwald)和阿敏·考夫曼(Armin k aufmann)為代表,擁護者以貝爾汶科(brwin k el)和安德魯拉基斯(Androula k is)為典型。[2]
2.1格林瓦爾德
格林瓦爾德認為,刑法分則設定的構成要件除純正不作為犯之外,均為作為犯的構成要件,雖然處罰不純正不作為必須根據作為犯的構成要件,但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實質上,處罰不純正不作為的根據在于法律未明文規定的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構成要件。不純正不作為犯的構成要件包括兩方面:一是作為義務,二是不純正不作為犯構成要件的法律條文表述,如故意殺人罪的表述:“不防止他人死亡的,處……。”
筆者認為,格林瓦爾德打破保證人說的藩籬,明確承認不純正不作為犯具備獨立構成要件,這是最大的創新。就刑法分則而言,除純正不作為犯之外,確實只設定了作為犯的構成要件。處罰不純正不作為,也只有借重于獨立構成要件,才能避免進入保證人說“共用一構成要件為何又多出作為業務”的困境。當然,這里隱含一邏輯前提: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構成要件,也能成為歸責根據。但是,格林瓦爾德認為不純正不作為犯的構成要件包括法律條文表述,似嫌多余。因為這種適用于不純正不作為犯構成要件的法律條文表述,其內涵已融合于不純正不作為犯作為義務的判斷中,根本沒有專門強調的余地。換言之,只要合理認定作為義務,即便不提此表述,也不會造成不純正不作為犯的認定障礙。
2.2阿敏·考夫曼
阿敏·考夫曼一方面承繼格林瓦爾德,另一方面大刀闊斧修正保證人說,提出兩點意見:第一,不純正不作為犯要與作為犯等值,取決于能否實現其獨立的構成要件。不純正不作為犯的構成要件與作為犯構成要件迥異,多出一個保證人地位,即作為義務。第二,不純正不作為犯違反命令規范,作為犯違反禁止規范,兩者邏輯上并駕齊驅。
筆者贊同阿敏·考夫曼,但擔心第一點能否在分則中實現。雖然認為不純正不作為犯具備獨立構成要件才能在邏輯上更順暢地闡明不純正不作為犯的歸責根據,但是迄今為止,沒有任何國家刑法分則獨立規定不純正不作為犯的構成要件,特別是作為義務。如果硬性修改,浩繁的分則恐怕承受不起巨大的立法損耗。解決之道也許是,通過總則設定作為義務。在總則都無作為義務的情形下(這種情形實在常見,當今大多數國家刑法典總則都無此規定),只得承認格林瓦爾德的邏輯前提: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構成要件,也能成為歸責根據。這也是暫時為之辯護“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權宜之道。
2.3安德魯拉基斯
安德魯拉基斯舉起維護保證人說的大旗,認為作為構成要件與不作為構成要件有不同之處,但可以統攝于作為犯的構成要件該當性之中。因為刑法分則規定的構成要件(作為犯構成要件)是復合規范,即復合行為,既包括作為,也包括不作為,所以不作為的構成要件使用作為的構成要件。
筆者認為,安德魯拉基斯為維護保證人說而在理論上玩花樣,實際上承繼了保證人說相同的邏輯矛盾。既然作為與不作為各有其構成要件,以作為犯構成要當件統攝兩者,成其上位概念,顯然前后矛盾。所謂刑法規范是復合規范,這也是保證人說“禁止規范包括命令規范”的同意重復,不僅難自圓其說,也無理論創新。
3 實質違法觀
實質違法觀是對作為義務找尋實質化依據的初始努力。此說代表性學者是騷爾(Sauer)和基辛(Kissin),其倡導實質違法性說,即作為與不作為是否等價在于二者是否具備相同不法內涵。[3]
實質違法觀認為,具備構成要件該當性的不作為,還不足以構成犯罪,因為這只是形式上違法,實質上違法才能入罪。實質上違法指不作為“對國家及成員造成的危害多于利益”。因此,作為義務是否存在,要看履行作為義務而防止結果發生,是否“對國家及成員造成的危害多于利益”。此外,形式上的作為義務,比如法律規定的義務、職位或業務上的義務、合同義務等,都沒有根本依據,來歷不明,不能服眾。唯獨實質違法觀,才是能說清作為義務依據的利器,只有探求實質違法性說,才能弄清為何刑法規定如此這般作為義務的理由。根據實質違法觀,騷爾和基辛將作為義務分成兩類:一是具備實質違法性的先行行為之作為義務,即行為人因為其危險行為引起法益侵害結果的風險時,要防止這種結果產生的作為義務。因為先行行為已有實質違法性,如果不作為,自然對國家及成員造成的危害多于利益;二是行為人處于法律上社會地位產生的作為義務。比如教師、醫生等,都處在整體法秩序中,具備這種法律上社會地位。
筆者認為,實質違法觀不滿足于形式作為義務的說理缺位而嘗試為作為義務找尋實質化依據,邁出彌足珍貴的一步,難能可貴。但此說也有問題。首先,實質違法觀認為,先行行為之所以能產生作為義務,在于其具備實質違法性,那么毫無疑問,處罰的對象是先行行為本身的違法性,而非先行行為之后行為人的不作為。但不純正不作為犯的處罰對象,顯然只能是不作為本身,而非先行行為,否則混淆了作為犯與不純正不作為犯的區別。反過來說,如果先行行為只具備形式違法性,根據此說,就不能產生作為義務,這顯然不合理。其次,以法律上社會地位為作為義務的根據,立論太過龐統、抽象,容易流于混亂。最后,實質違法觀的最上位原則“對國家及成員造成的危害多于利益”根本就是一紙空言。這種利弊權衡究竟指站得住腳嗎?不作為導致的法益侵害結果,就是一種危害,怎能有利益?既然無利益,利弊權衡又有何意義?
4 整體考察法
實質違法觀之后,經過在德國基爾大學執教的夏夫史坦(Schaf fstein)和丹姆(Dahm)改進,演變為整體考察法。
整體考察法誕生之前,德國法哲學、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大師拉德布魯赫(Radburch)提出方法二元論。其認為,存在與規范是相互獨立、互不混搭的一對范疇,規范不能由存在歸納而成。整體考察法針鋒相對方法二元論,認為存在并非完全獨立,隱含著可以提煉的規范;存在并非價值中立,蘊含著倫理和價值。整體考察法也因此指從生活中提煉法律概念,從社會倫理道德中過濾刑法原則規則。表現在作為義務的根據上,則指“健全的國民感情”。也就是說,以廣大民眾的共同價值觀為作為義務的實質依據。
根據整體考察法,據此確立的作為義務包括社會團體關系(共同生活團體、血緣團體、特定職業、公務關系等)、合同關系(所謂信賴和忠誠關系)、私法上的法律地位。
筆者認為,整體考察法的弊病,絕不亞于實質違法觀。一方面,整體考察法的理論依據“健全的國民感情”抽象程度較“法律社會地位”更甚,遠超出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之程度,[4]這根本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律的做派,背離罪刑法定原則和刑法保障機能。[5]另一方面,合同關系如果解釋為信賴和忠誠關系,那么也不能理所當然導出作為義務,因為如果信賴和忠誠關系是作為義務的依據,那么信賴和忠誠的依據何在?信賴和忠誠的依據只能是法律設定的義務。先有法律設定某人作為或不作為的義務,以及違反義務的效果,人們之間信賴和忠誠關系才能建立,所以是法律義務設定了信賴和忠誠關系,而非信賴和忠誠關系設定了法律義務。整體考察法就這點說理,倒果為因。
5 刑法獨立觀
夏夫史坦不僅致力于創造整體考察法,也提出具備跨時代意義的學說:刑法獨立觀。當時德國通行的是形式作為義務說,形式作為義務說始于19世紀初期的費爾巴哈和斯鳩貝爾(Stübel),直至20世紀50年代都為通說。形式作為義務說的作為義務包括法律規定的義務、合同義務、先行行為之義務三類。法律規定的義務,大多為民法所規定;合同義務成立與否,也依據民法中法律行為的效力判斷。這就在作為義務的判斷中呈現民法主宰刑法的格局。此外,刑法上違法概念也因之出現雙重標準:一方面刑法違法概念具有獨立性,另一方面刑法違法概念又倚重民法。夏夫史坦認為,這種非常現象,是形式作為義務說的重大缺陷,為克服此缺陷,他倡導刑法獨立觀。[6]
筆者認為,刑法獨立觀表面倡導刑法上違法概念要獨立,根本上卻是實質違法性說的表現。如前所述,按照形式法義務說,作為義務為法定,亦即不管什么法,只要是法,就可以設定作為義務,這明顯是形式主義的推論。要克服形式主義流弊,就必須從實質上限定作為義務。這種實質上的限定,一方面表現在只能由刑法才能設定作為義務,此即刑法獨立觀;另一方面表現在刑法設定作為義務的依據是社會倫理道德,此即整體考察法。由此可知,整體考察法和刑法獨立觀,都是實質違法性說的表現。實質違法性說迎合當時德國納粹政權的需要,一時受寵,但后來法西斯崩敗,此學說也曇花一現,被威爾澤爾(Wel z el)的目的行為論取代。[7]
6 公共福祉說
從上文可看出,大多數學說在找尋作為義務的實質依據之后,都未正面探究法律和道德的界分。貝爾汶科有鑒于此,找出作為義務實質依據后,立即分析法律與道德的界限。作為義務的實質依據,貝爾汶科承繼前輩學者觀點,認為是社會關系。對法律與道德的界限,他提出公共福祉說。[8]>
貝爾汶科認為,不法的本質是違反倫理道德。但違反倫理道德并非一概不法。某些社會倫理道德規范已經超越個人福利,涉及多數人整體的的公共福祉,以社會成員共同生活的繁榮進步為目標,那么這種公共福祉,就具備了法的品質。當然,也不是違反了這種公共福祉就為刑法所不容,因為刑法具有第二位特征,即補充性、謙抑性,[9]公共福祉也有輕重之分,只有違反重大公共福祉,才有刑事不法可言。就不純正不作為犯來講,只有維護重大公共福祉的義務,才是作為義務。公共福祉包括個人及團體發展所必需的各種文化條件,如經濟、技術、精神、風俗、藝術、國家和國際的各種條件。公共福祉并非一成不變,而是伴隨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演進而變易。
貝爾汶科除了揭示公共福祉的概念,還具體闡述其基本內容:法益、社會角色、客觀評價要素。
法益相對于法,固然是保護的目的,但保護法益的目的,在于維護社會成員共同生活的繁榮進步,所以法益對于公共福祉,只有工具的意義。法益只能是公共福祉的要素。
公共福祉的另一要素是社會角色。在社會關系中,社會成員雖然各有特性,但長期的共同相處形成共同的行為方式,即風俗習慣。風俗習慣促成了社會成員團體化。社會團體要求社會成員符合特定的行為模式。社會團體中每個人都扮演不同的社會角色,且角色之間相互依賴、互補、不可割裂。一個角色的扮演往往依賴另一個角色的配合,若其不配合,社會關系就會受擾。所以法律就命令各社會角色依角色要求為之該為。如果為了維護重大公共福祉,而要求一社會角色必須有所為,那么此社會角色就有了作為義務。
最后一個是客觀評價要素,旨在再度確定作為義務是否為維護重大公共福祉所必需,具體包括法益的重要性、危險狀況的具體程度、社會角色的壟斷地位等,用以限定作為義務的范圍。客觀評價要素難以統一抽離,只能個案確定。
一言蔽之,貝爾汶科認為,判斷行為人是否有作為義務,要先確定法益,再看行為人的社會角色在社會團體中,是否有防止此法益被侵害的義務,最后以客觀評價要素,來判斷這種防止法益被侵害的義務,是否為維護共同生活的繁榮進步,即重大公共福祉所必需。
筆者認為,在作為義務實質依據的德國諸家學說中,公共福祉說是集大成者,規模宏大、邏輯縝密、極富深度,標志作為義務實質依據的研究已趨成熟。公共福祉說的優點較明顯:首先,貝爾汶科遵循規范、價值、演繹的研究進路,完全異于歸納法,其成效昭示了此研究方法是作為義務實質依據研究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其次,貝爾汶科將各類社會關系,放入公共福祉的三類要素中,一一檢驗,過濾出作為義務,完全不像佛格特和安德魯拉基斯從已有學說和判例中抽離出片面的作為義務,研究范式從自下而上轉變為自上而下,這才能真正找到作為義務的實質依據。最后,貝爾汶科將法益作為研究的起點,完全正確。法益是法律保護的客體。作為義務實質依據的研究,自然以法益作為出發點。貝爾汶科之所以取得巨大成效,在于其“定點”正確,以法益為起點,佛格特和安德魯拉基斯所獲結論問題重重,源于“定點”失誤。但是,此學說也有問題:首先,公共福祉太過抽象,太過事實性、原料性,而缺乏法律原則必備的規范性和可依循性。其次,社會角色概念不明確,缺乏規范、價值色彩,有失抽象化。最后,貝爾汶科認為,客觀評價要素只能個案確定,這實質上沒有提出任何判準,客觀評價要素說穿了只是個空洞的概念。公共福祉說的癥結所在,質言之,在于從法律規范觀進入社會規范觀,從而衍生出的問題,這也是多數學說皆有的弊病。盡管如此,貝爾汶科的公共福祉說仍為作為義務實質依據各類學說中說服力最強者,這點無可否認。
7 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德國關于作為義務來源的實質依據,呈現百花齊放的多元性,這反映了德國刑法學的精細。我國刑法理論現在面臨德日理論與蘇俄理論相沖突、甚至對決的境況,這更加促使我們為我國刑法理論的轉型付出努力。以上關于作為義務來源的實質依據的分析,就是從比較法的角度,引薦并評析德國刑法理論中作為義務來源的實質依據,以期拋磚引玉,為我國作為義務來源的實質依據的創立,提供資料性的有益啟示。
參考文獻:
[1][3]許玉秀.主觀與客觀之間—主觀理論與客觀歸責[M].法律出版社,2008.
[2][6][8]許玉秀.當代刑法思潮[M].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
[3]許玉秀.主觀與客觀之間—主觀理論與客觀歸責[M].法律出版社,2008.263.
[4][德]恩施特·貝林.構成要件理論[M].王安異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14.
[5][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M].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77.
[7][德]格呂恩特·雅科布斯.行為責任刑法—機能性描述[M].馮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78.
[9]李海東.刑法原理入門(犯罪論基礎)[M].法律出版社,1998.16.
責任編輯:鄧榮華
中圖分類號:D F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094(2015)02-0005-04
收稿日期:2015-02-13
作者簡介:唐 治(1990-),女,四川富順人,四川大學法學院刑法學碩士在讀。研究方向:外國刑法學。
Study on the Essence Evidence of the Source of Obligation
TANG Zhi
(Law School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207)
Abstract:There is no essence evidence of the source of obligation in our country criminal law theory, which shows that China's offense of nontypical omission theory needs innovation. Essence evidence of the source of obligation in Germany includes guarantee said, law concept, the overall concept of criminal law, investigation method, independent public welfare said.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heory can provide the comparative reference and information revelation for the innovation in our country criminal law theor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ffense of nontypical omission theory.
Keywords:Source of Obligation; Essence Evidence; Offense of Nontypical Omi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