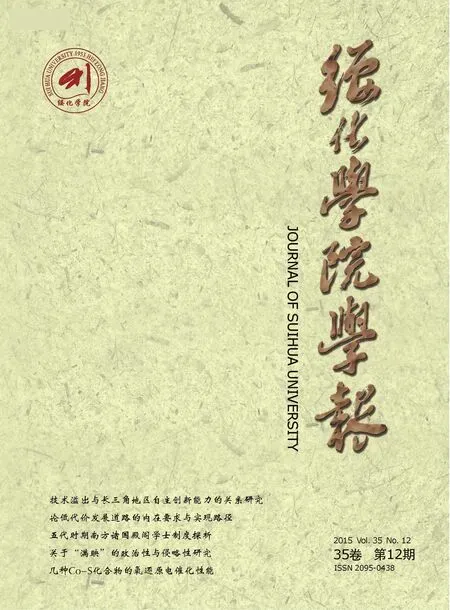辛格的《冤家,一個愛情故事》谫談
彭威
(蘭州財經大學外語學院 甘肅蘭州 730020)
辛格的《冤家,一個愛情故事》谫談
彭威
(蘭州財經大學外語學院 甘肅蘭州 730020)
美國猶太作家辛格的長篇小說《冤家,一個愛情故事》采用現實主義手法,深刻揭露了納粹大屠殺對猶太幸存者造成的肉體與精神創傷、倫理危機以及身份認同困惑。小說既表達了作者對猶太人遭受深重苦難的同情和對納粹分子所犯滔天罪行的嚴厲譴責,也折射出作者自身慘痛的人生經歷。
辛格;《冤家,一個愛情故事》;納粹大屠殺
艾·巴·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4-1991)是美國著名猶太作家,于197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小說受到世界各地讀者的廣泛喜愛。作為一名猶太裔作家,辛格的小說充滿了濃厚的猶太性,“表現了猶太民族的歷史命運和現實際遇,從而在美國當代文學史上占有獨特的地位。”[1](P394)《冤家,一個愛情故事》詳細描述了納粹大屠殺后流散到美國的猶太幸存者生活狀況的長篇小說,也是二戰后較早對猶太幸存者給予深切關注的小說,具有深遠的文學和歷史意義。本文結合小說所反映的特殊歷史語境以及辛格本人的人生經歷,從肉體與精神創傷、倫理危機以及身份認同困惑三個層面闡釋作者對大屠殺猶太幸存者這一特殊群體的思考,試圖為我們深刻理解小說的獨特內涵提供新的視角。
一、肉體與精神創傷
猶太人自從兩千多年前被趕出“流著奶與蜜”的應許之地后就流散于世界各地,成為無根的漂泊者,屢屢遭到歧視、驅逐、殺戮乃至幾近種族滅絕。二戰期間德國納粹分子對猶太人種族滅絕式的大屠殺是猶太人遭受的最為嚴重、慘痛的苦難。“600萬活生生的人類僅僅因為他們是猶太人而被滅絕。歐洲猶太人幾乎停止存在,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猶太人被殺害。”[2](P37)辛格的長篇小說《冤家,一個愛情故事》正是基于這一歷史背景,圍繞著從歐洲逃亡到美國的猶太幸存者的生存狀況而展開。小說以赫爾曼為主人公,講述了他作為一個大屠殺幸存者在美國的愛情、婚姻、宗教等方面生活故事。小說中的猶太幸存者大多是帶著滿身的傷痛逃亡到美國的,這些傷痛伴隨終生且時時折磨著他們,讓他們痛苦萬分。大屠殺期間,赫爾曼為了逃避納粹的搜捕躲藏在一個只能容身的草料棚中達三年之久,他家的傭人雅德維珈每天“給他端來食物和水,把他的糞便端走”[3](P238)。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藏了三年之久的赫爾曼出來后患上了嚴重風濕病和坐骨神經痛。“吃東西以后,他就胃痛。吹到一點風他的鼻子就塞住了。他常常喉嚨痛,嗓音變得越來越嘶啞。耳朵里有什么東西使他感到痛——化膿了,還是長了東西?”[3](P273)赫爾曼的身體已經垮掉了,帶著渾身的病痛,他只能茍延殘喘地活著。瑪莎也是傷痕累累地逃到美國,她曾經在納粹集中營呆過,僥幸逃過大屠殺,但身上沒幾處完好的皮肉。睡覺前,“她總是喜歡打開手電,讓赫爾曼看那些死人在她胳膊、胸脯和大腿上留下的傷痕。”[3](P278)瑪莎的母親厄普身體則更加糟糕,“他患有心臟病、肝病、腎臟病和肺病。每隔幾個月,她就要昏過去一次,每次醫生都說她沒救了,可每次她又逐漸復原了。”[3](P276)而赫爾曼原來的妻子塔瑪拉身體上也留下了一大片傷疤。辛格并沒有通過人物之口詳細描述納粹分子如何折磨猶太人,然而他們永久的肉體創傷中足以看出納粹超乎人類想象的殘忍,這是納粹所犯下滔天罪行的明證。
納粹留給猶太幸存者的肉體創傷和病痛或許可以通過醫藥來救治和緩解,而唯獨精神上的大屠殺創傷后遺癥是任何高明的心理治療師也難以撫慰的。辛格對猶太幸存者肉體傷痛的勾勒只有寥寥幾筆,然而對他們所遭受精神創傷的刻畫在小說中則俯拾即是,細致入微。小說中的每一個幸存者幾乎都有精神問題,如果從醫學的角度來進行診斷,他們都可視為精神病患者,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赫爾曼就是一個典型的飽受精神折磨的病人。草料棚里三年的非人生活使他的精神一直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態,來到美國后他經常出現幻覺,認為自己仍然生活在被納粹統治的波蘭。他總是感覺納粹分子在跟蹤他,擔心自己的住處被他們發現,時時幻想著納粹分子藏在地鐵站、門背后、大街拐角處、商場里等,似乎無處不在。赫爾曼每晚都在做與納粹分子廝殺的噩夢,經常算計著哪些地方適合藏身,要多少食物才能維持生存。這種精神折磨讓他整天頭腦昏昏沉沉,恍恍惚惚,仿佛生活在幻境之中。蘭伯特拉比是赫爾曼的雇主,赫爾曼的工作實際上就是為他代寫各種文章。這個外表豪爽的猶太拉比看似已經擺脫了納粹噩夢,但實際上他同樣遭受著精神上的折磨。當蘭伯特看到赫爾曼整天因為擔心納粹分子找上門而變得神經兮兮時,便建議他去看看精神醫生,然而他自己卻也坦承:“就是我,有一段時間也找過精神分析醫生。”[3](P257)而蘭伯特還透露他的妻子也整天精神恍惚,有時開著煤氣就外出買東西,有時突然變得歇斯底里開始罵人等等。
小說中人物的精神創傷不僅表現為一種大屠殺后恐懼癥所有引起的精神疾病,還表現為一種幸存下來的愧疚感和自責感。小說中的猶太幸存者從未表現出一種逃離死亡的慶幸感,相反他們內心覺得當家人和同胞在大屠殺中慘死而自己卻幸存下來是一種無法饒恕的罪過。赫爾曼一想到兩個孩子被納粹殺死而自己卻在美國活了下來就開始自責,他甚至打算這輩子再也不生孩子。瑪莎的母親希拉普認為親人死去而自己活著是一種莫大的恥辱。在瑪莎看來,“她犯下的最大的罪行就是:在這么許多無辜的男女慘遭殺害的時候,她居然一直活著。”[3](P276)死去的人已經結束了肉體和精神的折磨,而留給這些幸存者的是無盡的自責和愧疚感,讓他們覺得自己的生命是由死去的家人和同胞換來的。也許只有“生不如死”這個詞才能恰當地描述他們的真切感受。
可見,這些猶太幸存者是幸運的,然而又是極其可憐的。說他們幸運,因為相對于那些被驅趕進焚尸爐的猶太人,他們僥幸撿了一條命,但納粹留給他們的肉體和精神創傷又時時刻刻在折磨著他們,勾起那段噩夢般的日子,讓他們隨時想起自己夢魘般的經歷和被屠殺的親人。他們在美國這個繁榮的國家過著一種行尸走肉般的生活。辛格通過刻畫猶太幸存者的傷痛表達了對猶太人遭受人類歷史上罕見磨難的血淚控訴。
二、倫理危機
倫理道德問題是猶太文化的核心之一,也是辛格小說的重要主題。猶太文化以猶太教文化為基礎,而猶太教本質上又是一種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宗教。猶太教教義中充滿了各種道德訓誡,摩西十誡是最為重要的道德戒律。大屠殺顛覆了猶太人心中各種道德戒律,小說中的猶太幸存者除了要忍受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外,還往往陷入前所未有的倫理危機中而無法自拔。
從猶太教倫理的角度來看,信仰上帝應該是每一個猶太人首先要遵守的倫理準則。上帝與摩西在西奈山訂立契約,如果猶太人信仰全知全能的上帝,上帝則會拯救猶太人于水火之中。千百年來,猶太人抱著這一信念虔誠地信仰上帝,遵守與上帝的契約。然而,幸存者在經歷了大屠殺的災難后卻出現了嚴重的信仰危機。他們開始懷疑上帝,詰問上帝,甚至謾罵和詆毀上帝。在親人和同胞慘遭屠殺,自己受盡磨難后,原本虔誠的赫爾曼開始懷疑這個仁慈的上帝為何當時袖手旁觀。他經常在內心詰問:上帝到底是否存在?猶太人受難時他躲到哪里去了?猶太人為何要相信一個并不存在的上帝?赫爾曼原來的妻子塔瑪拉則直言不諱地說:“在孩子們遇難以后,我不會相信上帝了。”[3](P359)確實,一個能在無辜的孩子們被殺死、活埋、焚化時而袖手旁觀的上帝如何讓人相信呢?瑪莎對上帝的態度則更加直接,她明確表示自己“憎恨上帝”,甚至還譏諷上帝:“屠殺猶太人是合乎天理人情的。猶太人一定要被屠殺——這是上帝的希望。”[3](P269)塔瑪拉的叔叔里布——一個原本無比虔誠的人也無法相信這樣的上帝,他感慨“怎么可能要求那些經歷過毀滅的人去信仰上帝和他的仁慈呢?”[3](P462)由此可見,大屠殺已經徹底動搖了上帝在猶太人心中的地位,讓猶太人漸漸失去精神支柱和道德理念,不僅對猶太人身體和精神造成戕害,更是對猶太宗教倫理準則的一種殘害。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整體上采用第三人稱全知全能的敘述方式,然而在談及上帝在猶太人慘遭屠殺而為何袖手旁觀這問題時,作者本人則直接插入敘述,將自己對上帝的看法毫不掩飾地表達出來:“各種宗教都是謊言。哲學從一開始就徹底破產。有關進步的種種不兌現的諾言不過是吐在世世代代殉道者臉上的唾沫……猶太人永遠要在奧斯維辛被燒死。”[3](P262)“在慕尼黑的小酒館里,那些曾玩弄過兒童的顱骨的兇手們從高大的酒杯里喝啤酒,在教堂里唱贊美詩。真理?不在這片叢林中,不再坐在火熱的熔巖的地球上。上帝?誰的上帝?猶太人的?還是法老的?”[3](P466)這種以作者口吻直接對上帝發出詰問的例子還有很多,從中可以看出辛格是有意通過轉換敘事者口吻的手法來直接表達對上帝懷疑和不滿的情緒。由此可見,小說中虛擬人物對上帝的信仰危機實際上也是積郁在辛格本人的內心,在這點上作者與小說人物心理有共通之處。
辛格本人對上帝的詰問與其人生經歷有很大關聯。辛格于1935年輾轉來到美國,目的就是為了躲避日后即將到來的滅頂之災。辛格的嗅覺是敏銳的,在一份訪談錄中辛格談到:“1935年希特勒已經執掌了權政……我預見到了那場大屠殺。”[4](P330)然而,不幸的是,他的母親和弟弟卻在這場屠殺中因缺少食物供給,被活活餓死。辛格本人也正是為了逃命才漂洋過海到美國避難。上帝眼睜睜看著他的親人遭難而袖手旁觀,這是辛格心中永遠的傷痛,也是辛格在幾乎所有小說中都對上帝提出質疑的重要原因。總之,大屠殺讓無數原本虔誠的猶太人開始懷疑上帝,動搖了本堅定的宗教信仰倫理根基,在信仰層面對猶太人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大屠殺不僅直接導致了猶太人的宗教信仰倫理危機,還間接地造成了猶太人在很多其他層面過著一種違反倫理規范的生活。大屠殺對猶太幸存者婚戀倫理觀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各種不倫之戀、未婚生育、重婚、多個情人等現象普遍地發生在他們身上。赫爾曼在波蘭時原本有著幸福美滿的婚姻,然而,逃難到美國后為了報答瑪德維珈救命之恩,他違背猶太教婚姻倫理,先是與非猶太裔的雅德維珈舉行了世俗的婚禮結婚,卻又背地里與瑪莎——一個有夫之婦偷情,后來意外發現原來波蘭的妻子塔瑪拉還活著,又跟塔瑪拉糾纏不清。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猶太人或迫于無奈或主動放棄心中的道德戒律。為了維持生存,赫爾曼成了一個捉刀者,給蘭伯特代筆寫各種布道稿、文章、書籍,這是一種赤裸裸的欺騙行為。蘭伯特拉比本人一面在猶太人面前布道,宣揚上帝的福祉,一面卻又通過坑蒙拐騙來聚斂錢財。瑪莎為了保住性命和得到一點物質上的好處,也曾經跟不同的男人保持性關系。很多猶太人已經開始不遵守習俗蓄留胡子和鬢角,不過猶太人的節日,不遵守安息日,與異族通婚,等等。這些都不符合猶太倫理規范,而這樣的猶太人在小說中比比皆是,可見這種現象的普遍和嚴重。
正如辛格在序言中寫到的,倫理的缺失一方面是緣于小說人物的個性和命運,但其背后的原因基本上都可以歸咎于大屠殺。如果沒有這場屠殺,這些猶太人會像往常一樣在各自的生活中扮演應有的角色,而非被驅趕到一個陌生的國家,發生如此多不幸的事情。猶太人建立起來的道德秩序都因為大屠殺的到來而受到嚴重的沖擊。在這一過程中這些猶太人并非樂意這樣做,而是身不由己,他們內心極度痛苦。倫理秩序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一角度來看,大屠殺對猶太倫理規范造成額沖擊實際上也是對猶太文化造成的一種嚴重的文化創傷。
三、身份認同困惑
身份認同的基本涵義指:“個人與特定社會文化的認同。這個詞總愛追問:我(現代人)是誰?從何而來、到何處去?”[5](P37)猶太人在幾千年的流散歷程中盡管也常常對“我是誰?”“我屬于哪里?”等身份問題產生困惑,但絕大多數猶太人都擁有一種共同的民族認同感,即我是猶太人。這是因為二戰前的猶太人主要分布在歐洲大陸,他們往往形成自己的猶太社區——“格托”(ghetto)。“格托”中的猶太人較為完好地保存著猶太文化,如信仰、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形成了一種相對封閉的文化圈,因而生活其中的猶太人也形成了比較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歸屬感。然而,大屠殺徹底改變了這一格局,逃難到美國的猶太幸存者面臨著嚴重的民族認同危機。赫爾曼經常問自己“我是誰?”他身邊的很多猶太人也開始對自己是否是真正的猶太人而感到困惑和迷茫。這些人已經開始拋棄猶太人的傳統,過著一種現代美國的生活,然而他們又不被美國人所認可,處于一種邊緣地帶。他們偏離了猶太文化和習俗,但是又不敢徹底與之決裂,他們開始懷疑自己猶太人的身份,卻又無法承認自己屬于任何其他民族。這種游離在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的尷尬給讓他們內心備受煎熬,痛苦萬分。
從原因上看,民族身份認同危機和困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初入美國的猶太人沒有形成能產生文化凝聚力和民族認同感的猶太社區。小說中的赫爾曼租住在一棟整天夾雜著各種口音的大樓中,幾乎不認識周圍的鄰居,也從不打交道。瑪莎與母親租住在一個狹小的房子里相依為命,塔瑪拉與叔叔住在一起。這些猶太人都散落在美國的各個角落。散居的方式以及猶太人之間缺乏交流和溝通難以形成一種文化凝聚力和歸屬管以及認同感。此外,猶太人民族身份認同危機與美國文化的同化力量有著密切的聯系。對于猶太人來說,美國文化有著一種難以抗拒的誘惑力。美國人倡導個性、民主、自由,在生活方式上崇尚簡單、舒適的原則。受到現代美國文化的影響,猶太人開始逐漸拋棄猶太風俗習慣,對猶太節日、族內通婚習俗、飲食原則等也采取非嚴格的方式,在美國這個多元文化的國家一步步被同化。然而,同化又不是徹底的,他們畢竟還在很多方面保留著猶太文化根基,但又無法得到美國主流社會的認可,同時也經常招致一些仍然堅守猶太傳統的同胞的鄙視,因此這些猶太人對自己的身份感到非常困惑。
小說中猶太人的身份認同困惑還體現在國家身份認同層面上。逃到美國的猶太人不僅面臨著民族身份喪失的危機和痛苦,還面臨著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對他們認同的問題。小說中的幸存者大多通過逃難等方式來到美國的,根本不被視作美國人看待。他們大多面臨著語言、就業、醫療等多方面的困難,通常只能從事一些收入低的累活、臟活或者干脆找不到任何工作。赫爾曼盡管擁有大學文憑且學識淵博,但根本無法找到能發揮其才華的工作,因而他只能給蘭伯特拉比做槍手。瑪莎在一個餐廳當出納,賺取微博的工資以解決自己和母親的日常開支。塔瑪拉沒有工作,只能四處游蕩,靠他叔叔開的那間小書店勉強維持生活。他們都沒有取得美國國籍,只是以難民的身份寄居在這個國家,因為并不被視為美國人。然而,他們又失去了自己的祖國,或者遭到祖國的拋棄,或者在自己的祖國被屠殺。他們既不是波蘭人、法國人、俄國人,也不是美國人,他們成了沒有國籍的漂泊者。這種國家身份認同的危機折磨著這些身處異鄉的猶太人。他既不是原來的國家身份,也不被新世界的美國所認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無法真正融入到美國社會,因而痛苦萬分。這種身份認同危機和困惑固然有人物個人的原因,然而如果沒有大屠殺,這種情況也不會出現。
事實上,辛格本人對于這種身份認同的困惑深有感觸。根據辛格的傳記,他歷經千辛萬苦來到美國后,在這個人生地不熟,語言不通的地方感覺被懸置起來。他經濟窘迫,認識的人極少,找不到合適的工作,離開猶太文化土壤,又不被美國所接受和認可,甚至在長達四五年的時間里寫不出任何東西,因而沮喪萬分,痛苦至極。可以看出,發生在小說人物身上的身份認同困惑和痛苦也是早年辛格本人內心的真實寫照。
結語
從標題上看,小說《冤家,一個愛情故事》是有關愛情的,但實際上隱藏在小說錯綜復雜的愛情故事背后的是辛格對納粹分子大屠殺罪行的控訴和痛斥。小說中猶太幸存者所遭遇的種種創傷、不幸、磨難、痛苦本質上都是納粹大屠殺所造成的。事實上,銘記和反思猶太大屠殺不僅對于猶太人具有重要意義,對其他民族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因為“納粹大屠殺,是人類共有的歷史財產,人類有責任和義務反思,并開展相應的大屠殺教育。”[6](P92)
[1]傅景川.二十世紀美國小說史[M].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
[2]黃陵渝.猶太教[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3]辛格著.楊怡譯.冤家,一個愛情故事[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
[4]艾·巴·辛格.亞伯拉編.艾·辛格的魔盒——艾·辛格短篇小說精編[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
[5]陶家俊.身份認同導論[J].外國文學,2004(2).
[6]相征.關于以色列納粹大屠殺教育的研究[A].潘光等.納粹大屠殺的政治和文化影響[C].北京:時事出版社,2009.
[責任編輯 王占峰]
I106
A
2095-0438(2015)12-0060-04
2015-06-15
彭威(1982-),男,湖北赤壁人,蘭州財經大學外語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比較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