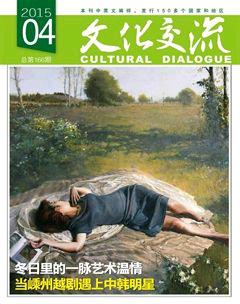回憶中的劉大白墓地保護
《文化交流》雜志的編輯要我回憶一下關于杭州劉大白墓地的保護情況,于是一朵記憶之云漸漸飄入腦海,越積越濃。
那朵云里,一位面目清秀的老太太首先清晰起來。這位老太太在1990年8月上中旬的某一天,尋著了中國作家協會浙江分會駐地,進了我所在的辦公室。我請她坐,她不坐,一直堅持站在我的辦公桌一側,原來是有事相求。
她說她叫劉緣子,是劉大白三個女兒中最小的一個,七八年前就與兩個姐姐開始奔走求助于相關單位,希望為自己父親的墓重建墓碑,加以修繕保護,因為“文化大革命”前夕墓碑被砸碎、墳墓被平毀,現在連墓地都被一家單位圈進了圍墻,幾近湮沒了。但這一請求一直無處落實,而且不久前杭州市政府又發了文件,要再一次清理西湖景區內的非保護墳墓,偏偏劉大白墓沒有被列入保護名單,那就意味著不知什么時候這墓就會被徹底掘掉。
劉老太太愁容很濃,說,現在,兩個姐姐都走了,她自己也是70多歲的人,“如果我也死了,這個要求就不會有人再提,所以趁我現在還活著,請求你們一定幫幫我,挽救我父親的墓,不要被清理掉。”
我聽著。我畢竟也是個寫詩的,有點明白劉大白在中國新詩發展史上的地位,在新文化運動中,他可是一位響當當的新詩闖將,許多詩作呼吁關注民間疾苦,別具一格。他1924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新詩集,還是那位翻譯過《共產黨宣言》的浙江老鄉陳望道為之寫序,一出版就很轟動。劉大白后來到南京當了民國政府教育部的常務副部長,也是寫詩不倦,照樣有詩集陸續出版,當然還寫其他東西,如文學評論之類,直至1932年逝于病榻。
想來真是可嘆。自然,更可嘆的是連墳墓都要在六十多年后以“革命”的名義平毀。
劉老太太走后,我就尋思著趕緊安排時間去一趟法云弄。那是靈隱寺上方的一條小徑,幽靜得很,我以前走過那條路。但作協辦公室的幾位同志議論起來,就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認為這件事其實屬于政府部門的管理范圍,我們沒法管,作協是為會員提供服務的,那個劉大白雖說是中國文化人,但1932年就離世了,讓我們今天來忙碌這事算什么名堂?另一種意見認為劉大白畢竟是名詩人,現在既然沒有什么單位來挑頭解決這件事,我們作協出面代勞一下也未嘗不可,一旦墳墓真的掘了就晚了。我自然持后一種態度。省作協分管辦公室工作的李秉宏也是這個態度。
我當時具體負責省作協的辦公室工作,剛借調到杭州不久,辦公室的幾位同志最終還是很配合我工作的。記得幾天后,我帶上負責財務行政工作的李華明,然后接上劉老太太,一起往靈隱方向出發。小車順山坡蜿蜒駛上法云弄,按劉老太太說的地址找,就找著了一家圍墻圍著的單位,一看牌子是杭州市城市雕塑研究院,進去后也沒見有幾個人。劉老太太指著園子后面的一處空曠之地,說有點像是這里。
我們四周察看一下,除了一堆斷手、斷腳、斷頭各種形狀的石膏殘缺件如一座小山似的,周遭找不出任何像是墓地的痕跡。于是我們走近廢料堆,難道墓穴會是在這個地方?記得我當時跪了下來,趴低身子,把手掌貼著地皮,使勁往廢品堆的縫隙里曲曲折折伸手進去。李華明擔心我的手被壓著,又擔心廢料堆會轟然崩塌傷著我,一個勁叫我小心。
我的手慢慢伸長伸平之后,再往下慢慢摳,忽然就摸到有硬硬的平整的石板,于是大叫“摸到了摸到了”。憑我直覺,墓地無疑。
此時,劉老太太看方位也越看越像,說可能就是這里了。
后來《江南》雜志的編輯陳繼光在記敘這一經過時,很有詩意地說:“黃亞洲終于用他寫詩的手,在法云弄6號杭州市雕塑院內一片堆滿廢棄雕像的荒草叢中,摸到了這位六十年前的詩人的墓石。”
回到單位后,我便向領導盛鐘健、李秉宏匯報了這次探尋經過,建議以作協的名義,趕緊向杭州市政府打一份報告,請求簡易修繕劉大白墓地,以便讓這座墓能在大力清理西湖景區墓地的背景下得以保護。兩位領導態度十分明確,說就這么辦。后來我就起草了一份文件,題目好像是“關于簡易修繕愛國詩人劉大白墓地的函”,編上號,作為正式文件在當月的下旬發給杭州市政府,抄送給幾位市領導,也抄送了市園林文物局、省文物局。
杭州市當時的副市長是散文作家俞劍明,我直接跟他通了電話,請他關注此事,盡力幫助解決。
后來得知,杭州市園林文物局的態度還是很積極的,一個多月后就向市政府辦公廳發出了“同意簡單修繕墓地、清理雜草、重建墓碑”的公函,而市政府秘書長施錦祥在同一天就批示“同意”,并作出“墓碑高度不高于八十公分”的具體批示。然后,這一決定很快就付諸實施了。墓地修繕得簡潔大方,周圍場地也清理干凈了,墓碑是橫的,由沙孟海書“劉大白先生墓”。我們后來都去看過,心里很是欣慰。在這一過程中,俞劍明副市長、省文物局的陳文錦副局長都表示了很大的關切,也去現場察看過。
當然,更高興的是劉緣子老太太。在一個秋日的下午,我從外面辦事回辦公室時,忽然發現辦公桌上有一大盒包裝精美的巧克力,問是怎么回事,辦公室同事說是劉老太太剛才來過了,千恩萬謝的,為了表達她的心意,特意送一盒巧克力給我。
我馬上拆封,讓大家在夕陽里開開心心品嘗了。
(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