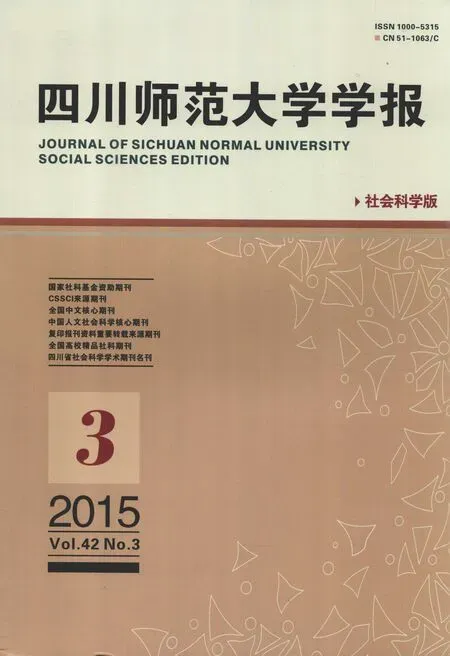從《喪服》的經、傳差異看“親親”、“尊尊”服制觀念的變化
何 丹
(四川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成都610064)
從《喪服》的經、傳差異看“親親”、“尊尊”服制觀念的變化
何 丹
(四川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成都610064)
五服制度自周代形成以來,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引起了古今不少學者的關注。通過分析《喪服》經文的編排之義和傳文的闡釋之義來看,二者在對待“親親”與“尊尊”兩大服制原則上存在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正是禮制變化的印記,體現了《喪服》經文、傳文的編撰者在服制觀念上存在著一種緩慢而又明確的變化過程,即隨著君主集權制逐漸受到認同,“尊尊”原則逐漸超越了“親親”原則,這樣喪服內在的宗法背景逐漸內隱,而外在的君臣尊卑大義則逐漸外顯。
《喪服》;西周;東周;“親親”;“尊尊”
對于《喪服》制度的相關研究,學者屢有涉及,五服制度以“親親”、“尊尊”為核心的禮制原則,亦為學界通識。但是,從《喪服》經文、傳文差異比較分析而探討“親親”、“尊尊”何者為重的相關研究論著,則似為較少。本文認為,成書于春秋末期的《儀禮·喪服》經文所記也并非全是西周服制,而是在經過孔子及其弟子的編訂過程中加入了己意,亦即根據當時通行的禮制而有所修訂,文獻關于為母、妻服喪期限的不同記載就是最好的說明。同樣,《儀禮·喪服》傳文雖然是對《喪服》經文的解釋論著,但是,這種經過不同時代、不同學者累次修訂和更正的《喪服》經文和傳文,并非意味著他們始終遵循著同樣的服制原則。進一步言,通過比較、分析《喪服》經文、傳文的編排和闡釋重心的差異,不難看出《喪服》經文和《喪服》傳文在“親親”、“尊尊”兩種服制原則何者為重的問題上,有著不同的解釋傾向,即《喪服》經文強調了“親親”為首的服制原則,而《喪服》傳文則以“尊尊”為重。對于這種不同時代的服制觀念,我們就從《喪服》的經、傳并存談起。
一 從《喪服》的經、傳并存談《儀禮》的時代信息
金景芳先生說:“在喪禮中,《喪服》一篇最為重要。它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用衣服的精粗和年月的長短來表示,辨析毫芒,精密之至,確實已達到‘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的地步。”[1]163事實上,《喪服》的重要性還在于其內容由經、傳、記三部分所構成,這是《儀禮》十七篇中獨一無二的,其中經文與傳文既有相合之處,又有相悖之處,故對此所蘊含的時代信息值得我們深究。
1.《喪服》經文與西周的關系
關于《儀禮》的成書,多認為與孔子復禮有著直接的關系。如《莊子·天運》載孔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制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2]95又如《禮記·雜記下》載:“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3]1222再如太史公所著《史記》的諸篇皆言及孔子修《禮》,《儒林列傳》曰:“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4]3115《孔子世家》曰:“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4]1914以上引文中之《禮》,皆指《儀禮》而言。由《儒林列傳》與《孔子世家》所記觀之,孔子確曾對包括《儀禮》在內的諸多典籍做過修訂編次的工作,并傳道授業。這從《雜記下》所記魯哀公命孺悲師從孔子學禮來看,也可知孔子確曾以禮育人,且頗負盛名。而孺悲所“書”《士喪禮》既直接來源于孔子,那么也可推知《儀禮》現存篇章也皆與孔子的傳授有關。所以,通常所言《儀禮》的成書時間當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
既知孔子僅為《儀禮》的修訂者,那么《儀禮》的原創者自然另有其人。由上述引文可知,孔子修訂《儀禮》是鑒于王室的衰微,原有等級的失序,而“論先王制之道,而明周召之跡”的,所以聯系到“周公制禮”的史實,我們推知所謂“先王制之道”、“周召之跡”,主要指的就是周公為治理天下而制定的一系列禮樂制度。這種觀點早在漢代就已存在,如《漢書·藝文志》云:“《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逾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顏師古注曰:“禮經三百……蓋《儀禮》是也。”[5]1710也正因為如此,孔子所修訂的《儀禮》經文雖成書于春秋末期,卻主要反映的是西周時期的禮制信息。
這種觀點也得到了《儀禮》之外的其他文獻和考古材料的證實。如《喪服》經文記有三年之喪,而據《史記·魯周公世家》載:“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后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后除之,故遲。’”[4]1524可見早在伯禽時期,魯國就實行過三年之喪。又如《士喪禮》經文載有“幎目”、“握手”之儀,鄭玄注:“幎目,覆面者也。”[6]670而絳縣橫水 M2就出土有一組玉覆面,墓主為倗伯;橫水M1就出土有玉握,墓主為倗伯夫人,年代均為穆王時期或略晚[7]。再如 《士 喪 禮》經 文 載 有 “飯 含”之儀[6]679-680,而張家坡 M6、M10、M11、M12均有唅貝現象,年代為武、成至康王時期[8]15-32。 所以,《儀禮》經文所載的喪禮,大體上反映了西周時期存在的禮制。
2.《喪服》傳文與東周的關系
以上所言孔子所修之《儀禮》,實則指經文而言,《喪服》傳文則晚于經文而出,且經文、傳文最初是單獨流傳的,這從漢代對《喪服》的引用情況可以看出。此處以《白虎通》的記載為例予以說明,如其卷四《封公侯·為人后》載:“《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為后為人作子何?明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后,往為后于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9]151又如其卷八《宗族·論五宗》載:“《喪服經》曰:‘大夫為宗子。’”[9]397再如其卷十《嫁娶·卿大夫士妻妾之制》載:“《禮·服經》曰:‘貴臣貴妾’,明有卑賤妾也。”[9]481從所舉諸例可看出,漢代的《白虎通》對《喪服》經、傳之文都是分別稱引,引用經文,或稱“喪服經”,或稱“禮·服經”,引用傳文,則皆稱“禮·服傳”,從經、傳相對而言的狀態,可知《喪服》的經文與傳文最初是分別流傳的。
這種別本單行的現象,直接關系傳文的成書。就《喪服》傳文的成書來說,學者多認為是子夏所作。如《后漢書·徐防傳》載司空徐防上疏和帝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10]1500“發明章句”即指注解一類的工作,故徐防應當是認同時下子夏作“傳”的流傳的。又如當代學者葛志毅、張惟明先生說:“當孔子既修六經之后,發明章句,傳授經學,使儒學發皇于戰國,垂遺于將來,必得其人方可。考諸史籍,孔門諸子中,唯子夏學行最為近之。要之,子夏實以傳授經學弘揚孔子之道。”[11]184子夏作為最早有明確記載的傳文作者,在沒有確鑿的證據前我們不便輕易否定,且諸多證據表明,子夏作傳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子夏作為孔子的得意門生,得到孔子賞識,所憑借的正是對典籍的精通與發揮。如《論語·八佾》載:“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 始可與言《詩》已矣。’”[12]25子夏由孔子先有白底再有繪畫的解釋,引申出先有仁義,再有禮樂的想法,使孔子認為對自己有所啟發,可見其對于典籍的造詣極高。受到孔子如此贊揚的,在孔門弟子中也屬罕見,故《論語·先進》載孔子在總結弟子特長時說“文學:子游、子夏”[12]110,此“文學”,即是指對古代文獻的熟悉。
不僅如此,子夏也精于“喪禮”,此點在文獻中頗為引人矚目,《禮記》所纂輯的關涉子夏的禮文中,就多與喪禮有關。如《檀弓上》載:“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矣。’”[3]217可見子夏對先王所制喪禮的精義不僅熟練掌握,且嚴格踐行。《檀弓上》又載:“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于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 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3]232可見子夏對時下通行的喪禮也掌握較多,且對時人喪禮的踐行也有著重要影響。《檀弓上》還載:“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3]238可見子夏對于不甚明了的喪禮,也是虛心求教。又如《禮記·曾子問》載:“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3]619可見子夏對于時下通行的喪禮,有著自己的見解,認為喪禮于金革之事當有避。
子夏正是因為具有如此的學術素養,故其有能力傳授儒家經典。據史籍載,孔子去世之后,子夏確以講學為生。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4]2203《史記·儒林列傳》又載:“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厘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4]3116子夏講學于西河,應當是頗負盛名的,故魏文侯才能以其為師。故子夏既具有“作傳”的能力,又具有“作傳”的時機,所以子夏作傳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按照尊師重道的傳統,子夏作傳的時間應當是在孔子死后,并在其講學口授的過程中,將其觀點傳揚出去的,這些觀點自當大部分受自孔子,故“傳”與“經”之文多為相合。但也有小部分為自己根據時代所發揚者,所以《喪服》“傳”文與“經”文,又有不符合甚至相違背的地方。這些不合之處,則正是東周時代禮制變化的最好印記。其中尤以三年之喪最能說明《喪服》經、傳的差異與服制觀念改變的關系,拙文《三年之喪起源諸說考辨》[13]1-26對此有詳細論述。 限于篇幅,此處不再進一步說明。
概括來說,孔子所修的《儀禮》經文,雖也有自己根據時代修訂之處,但大多本自周公所制之禮,反映的是西周時期的禮制情況;子夏所作的《儀禮》傳文多為解經或補經之說,其不合經文之處,反映的就是東周時期的禮制情況。所以文獻的成書年代與所含內容的時代信息并非一定對稱,所含內容也并非一定是某一個時代的特征,這就要求我們在引用論證時,辨別哪些屬于西周舊制,哪些屬于后儒所修訂的內容,對于不合之處,不可妄自以此為是,以彼為非;若與出土文物相沖突,也不可輕易地全盤否定文獻,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結合時間、地點、人物等綜合考察,盡可能還歷史一個真相。也正因為“傳”與“經”不是出于一人、成于一時,故傳與經最初會別本單行,而周公制禮、孔子復禮、子夏作傳就是兩周禮制史上極為重大的歷史事件。以上通過對《喪服》經、傳并存體例的分析,認為經文雖有東周之禮,但大多反映的是西周禮制,傳文雖有西周之禮,但卻是東周禮制的很好體現,對此大體趨向的總結,同樣可以得到《喪服》經文與傳文的支持,以下分別予以說明。
二 《喪服》經文的編排之義
細審《喪服》經文所列各等服制的服喪對象,可以發現各類對象在整體排序上是存在著一定的章法的。從中,我們不難看出以“親親”為首的宗法等級制度是《喪服》經文編排體例的基本指導原則。鑒于三年與期年之喪為重服,故在此僅以斬衰三年、齊衰三年和齊衰杖期這三個等級服喪對象的編排為例說明。
1.斬衰三年
根據《喪服》經文的記載,服斬衰之服者有十類,分別為:子為父;諸侯為天子;臣為君;父為長子;為人后者,為所后者;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在室為父;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公卿大夫之眾臣為其君[6]553-561。 細加分析,可以發現這些對象的排序,是遵循著一定的原則的。
從《喪服》編排體例來看,經文先講子為父所服,再講諸侯為天子、臣為君所服,可見遵從的是先有父子、再有君臣的觀念。而從先講諸侯為天子所服,再講臣為君所服的編排次序,可見遵從的是天子為先、諸侯為次的觀念。此處既然諸侯與天子本就是一種君臣關系,為何又要特意從臣為君的服例中提取出來,對此,胡培翚解釋為:“嫌諸侯有君國之體,或不為天子服斬,故特著之。”[14]1364胡氏以為作者對諸侯是否為天子服斬衰存有疑慮,才特別標出。但筆者認為此處特別標出的原因有二:一為諸侯也有“君”之名,若將諸侯為天子所服列于臣為君服之列,則勢必掩沒諸侯的國君之名;二為如同天無二日,天子至高無上的君位自然應當予以特別強調,而不能與眾君一起列出。且由“臣為君”斬衰,可知不僅諸侯(指畿外諸侯),且供職于王室的諸臣,包括畿內諸侯、卿、大夫、士,皆要為天子服斬衰三年。《周禮·春官宗伯·司服》亦云:“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15]555此“天王”就是王死告喪于諸侯之稱。因為周代講究臣之臣不是君之臣,所以為天子服斬衰之眾臣并不包括諸侯之臣。且除天子、諸侯之外,稱“君”者,還包括卿大夫之有地者。這種將天子家臣與畿外諸侯等同視之的觀點,實際上體現的是家天下的宗法制度。同樣,將諸侯之臣與天子家臣分列,也是以宗法“親親”原則為基本服制原則下整齊君臣關系的結果。
2.齊衰三年
按《喪服》經文的記載,服齊衰三年者有四類,分別為:父卒之子為母、父卒之子為繼母、父卒之子為慈母、母為長子[6]564-567,可見服齊衰三年者均為母子關系。這四類的排序,同樣有著內在的原則。如前三類先講子為母所服,再講母為長子所服,可見遵循著母尊子卑的觀念。又如在前三類子為母所服中,先講為母,再講為繼母,可見遵循著有血緣關系的親母重于名位相同的繼母的觀念;先講為繼母所服,再講為慈母所服,則遵循著嫡尊庶卑的觀念,因慈母于己既無血肉之親,又無配父之尊,故列于親母與繼母之后。
3.齊衰杖期
據《喪服》經文載,此服的服喪對象也包括四類,分別為:父在之子為母、夫為妻、出妻之子為母、從嫁之子為改嫁之繼母[6]569-571。這四類包含了母子關系和夫妻關系,其內在的排序也有一定的原則。如就子為母服的三類中,母、出母、改嫁之繼母,明顯存在著由親到疏的關系,故也按從先到后的順序排列。又如先講父在之子為母,再講夫為妻,明顯遵循著母尊妻卑的觀念。再如先講父在之子為母、夫為妻,再講出妻之子為母、從嫁之子為改嫁之繼母,明顯遵循著宗族內外的觀念,因為服喪者與服喪對象在前兩類中屬于同宗,在后兩類中不屬同宗。
總結經文對以上服喪對象的編排順序,可看出經文對待各類關系重要性的排序,為父子、君臣、男女、父女、母子,各類關系中,均以前者為尊,后者為卑。且父子關系中,嫡長子重于其后之子;君臣關系中,天子重于諸侯和其他有地之君,臣重于家臣,家臣之貴臣重于眾臣;男女關系中,妻重于妾;父女關系中,在室的女子重于歸宗的女子,更重于出嫁的女子;母子關系中,母重于繼母,更重于慈母,更重于出母,更重于改嫁之繼母。由父子、父女和母子關系的服例,可看出《喪服》經文是以先天血緣關系為基礎,并結合后天的宗法制度而設,故最終以宗族內的血緣之親為重。
至于經文所體現的父子關系重于君臣關系的觀點,也與其他許多文獻記載相符合。如《周易·序卦》曰:“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16]294又如《禮記·昏義》曰:“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3]1620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資(齊)衰,服母之義也。”[3]1625上述文獻可見:先有父子之親,而后才有君臣之義,有了君臣之義又才有上下之序,禮儀也才因此得以施行。天子完善對男子的教化,是做父親的職責;王后完善對婦女柔順德行的教化,是做母親的職責;因此說,天子和王后如同父親和母親。所以為天子服斬衰喪,體現的是為父服喪之意;為王后服齊衰喪,體現的是為母服喪之意。所以父子有親,君臣關系才能得以端正。
然后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到東周時期,對于父喪重于君喪的傳統出現質疑,而這也是《喪服》傳文撰作的基本背景。《說苑·修文》載:“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為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 凡事君,所以為親也。’”[17]459齊宣王對傳統喪制的質疑,說明了隨著君權的加強,國君也欲以改變喪制來進一步鞏固君權。田過對父喪重于君喪的堅持,則說明東周時期仍有人堅守著傳統喪制。但這種觀念到戰國晚期即已普遍發生轉變。如《荀子·禮論》云:“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三年畢矣哉!……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18]248-249即認為君主是治理國家的主宰,是禮法文理的根本,是忠誠恭敬的楷模,且本就有為民父母之說,既能給臣下衣食,又善于教誨臣下,所以臣下才要為他服喪三年以示推崇。因此荀子認為臣下為君主服喪三年,是最完備的禮法和最充分的情感表達,且只有這樣做,國家才能得以治理而安定;反之,就會混亂而危險。荀子對于此條禮法的推崇,應當視為是對戰國時期重君思想的一種總結和肯定。
對比前文的敘述,可明顯看到對于臣為君服的解釋,有了一個從側重“君如父”到側重“君為主”的轉變,這應當是對宗權下降和君權上升的反映。所以,在分封諸宗親和姻親的西周社會大背景下,政治關系內在的即是血緣關系,父權與君權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融合的,所以周人視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的起點,而尊崇父子之親也就是維護君臣之義,血緣關系雖重于政治關系,二者卻更多的是一種融合。到東周時期,則逐漸變為政治關系重于血緣關系,二者也開始呈現出一種緊張的對立狀態。
三 《喪服》傳文的闡釋之義
《喪服》傳文晚于經文而出,多為對經文的闡釋。而這些闡釋之文最顯著的特點即是通常以“尊”為解,這種詮釋維度表明“親親”原則逐漸被“尊尊”大義所取代。既便是父子之親等服例,傳文也以“尊尊”作為新的服制解釋維度,在此同樣以斬衰三年、齊衰三年和齊衰杖期這三等服例予以說明。
1.斬衰三年
在斬衰的十類服例中,《喪服》傳文都以“尊”為釋。 如子為父之服,《喪服》傳曰“父至尊也”[6]553;諸侯為天子之服,傳曰“天子至尊也”[6]553;臣為君之服,傳曰“君至尊也”[6]553;父為長子之服,傳曰“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6]554;為人后者為所后者之服,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6]555;妻為夫之服,傳曰“夫至尊也”[6]556;妾為君之服,傳曰“君至尊也”[6]556;至于女子在室和反歸父室之服,傳文雖未明言因尊而服,但應當都是比同子為父所服的,所以還是因“父至尊也”。另外,公卿大夫之眾臣為其君之服,傳文也沒有明言是因尊而服,但其雖因身為私臣,而與臣為君之公臣分列開來,但仍然屬于君臣關系,所以還是因“君至尊也”。由此可見,《喪服》傳文認為所為服斬衰者,服喪對象都是因為己尊而得服的。
與服喪對象為“尊”相應地是服喪者往往相對為“卑”,如父尊子(包括“女”)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等。需要指出的是“父為長子”之例,并非是因父卑子尊,而是為了突出“長子”的特殊身份。此“長子”指宗子的繼承人,通常為嫡長子,之所以不言“嫡子”,是因為嫡妻所生之子均可稱“嫡子”,故言“嫡子”就有指意不明之嫌。再者,“嫡子”之稱只適用于大夫或士之子,諸侯的繼承人稱“世子”;天子的繼承人則稱“太子”或“世子”。且若遇嫡長子死亡的情況,就要在眾嫡子中立第二子,對于在世者而言,此子仍可名“長子”。若遇嫡妻無子的情況,就要從眾庶子中選擇最為年長者為繼承人,而此子也可名“長子”。所以,“長子”之名的適用范圍更為廣泛和準確。至于父為嫡長子服斬衰的原因可概括為二:一為嫡長子是繼承先祖正體之人,所以如果父親本人是庶子(即嫡長子之外的眾子),那就不得為他的嫡長子服三年之喪,因為他的嫡長子并非繼祖的正體;二為嫡長子將代替自己成為宗廟之主,即“傳重”。這“繼祖”與“繼父”二者,“繼祖”顯得更為重要,因為“繼祖”通常即包含“繼父”之義在內;若單言“繼父”則不包含“繼祖”之義在內,因為庶子可為小宗,庶子的嫡長子自然也可以承繼為新的小宗之主。可見,此條規定意在突顯嫡長子作為父、祖繼承人的特殊身份和宗法社會賦予他的特殊地位。這種區別長子與眾子的服制規定,顯然是為了適應周代以嫡長子繼承制為核心的宗法制度而設立的,即大宗之禮的根本就在于立嫡之義。由此看來,“為長子”服以斬衰,同樣是出于長子尊貴的身份,不同于其他諸例的是服喪之“父”不是由于自身的卑下,“長子”之“尊”是與庶子的“卑”相對而言的。
總結來說,《喪服》傳文均以尊卑來解釋斬衰的這十類服例。強調“父”、“夫”為一家之尊,體現的是父權、夫權的高高在上,這種觀念實際是周代宗法社會的典型體現;強調天子為天下之尊、君為領地之尊,體現的則是王權、君權的高高在上。
2.齊衰三年
在齊衰三年的四類服例中,《喪服》傳文同樣以“尊”為釋。如父卒之子為繼母之服,是因為“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6]565,由此可知為母與為繼母所服,都是源于她們是父親的配偶,繼母與己雖無血緣關系,但出于尊父的緣故,孝子對待繼母之喪不敢有所不同。這是針對自己的親生母親早卒或被出后,父親另娶的情況所設的條例。又如父卒之子為慈母所服,是因為“貴父之命也”[6]566,即在有妾無子、有妾子無母的情況下,二者奉命以彼此為母子,該子即稱該母為“慈母”,因為尊重父命的緣故,慈母如親母般撫養該子,該子也如對待親母般生時奉養終身,死后服喪三年。再如“母為長子”所服,是因為“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6]567。此“長子”,同樣指父祖的繼承人;此“母”,則指宗子之妻。“長子”有承重之責,故父親不因己之尊而降低為其服喪的等級,母親自然也就不敢降低等級了。宗子為繼承人服斬衰三年,宗子之妻也自當從夫而服三年,但因為宗子之妻不能與宗子平起平坐,且母為子服不能過于子為母服,所以宗子之妻為“長子”只能服齊衰三年之服。雖然子為母有屈降之義,但因為“長子”為父祖之正體,所以父母對長子皆無厭降之義,母為長子則不論父在與否,皆服齊衰三年之服。
總結來說,《喪服》傳文均以“尊”來解釋齊衰三年的這四類服例,認為其中父卒之子為母、繼母、慈母的三類服例,都是因為尊父的緣故;而母為長子之服,則如同“父為長子”之服,是因為長子身份尊貴的緣故。
3.齊衰杖期
在齊衰杖期的四類服例中,除夫為妻之外,《喪服》傳文同樣以“尊”為釋。如父在之子為母所服,《喪服》傳曰:“屈也。 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6]569“屈”指子為母本當服齊衰三年,卻礙于至尊的父尚存,而只能降為齊衰杖期之服。又如出妻之子為母所服,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為父后者,則為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6]570若依傳文之意,則為出母服期之子,只是指其未被立為繼承人的庶子,若其子為繼承人,則為表示尊父,為出母無服;且庶子為表尊父,也對出母之族無服。再如,從嫁之子為改嫁之繼母所服,《喪服》傳曰“貴終也”[6]571,即因其曾經有“母”名而為之服,但“母”名是因曾與父婚配而得名,故該服同樣是出于尊父的緣故。
總結以上三等服例《喪服》傳文對經文的闡釋,可以發現除對于君臣關系以尊作解之外,《喪服》經文所列的這些為血親的服例,也都被傳文以“尊”為釋。這種情況還見于未列舉的其他等級服制,如關于孫男為祖父母之服,《喪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6]572關于孫女為祖父母之服,《喪服》傳曰:“何以期也? 不敢降其祖也。”[6]587即通常情況下,孫男和出嫁、未出嫁的孫女皆為祖父母服齊衰不杖期。又如關于大夫為祖父母、嫡孫為士者之服,《喪服》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6]590又如關于侄為世父、叔父之服,《喪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 與尊者一體也。”[6]572又如關于曾孫為曾祖父母之服,《喪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6]595關于大夫為曾祖父母為士者之服,《喪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6]597關于“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之服,《喪服》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6]597可見為曾祖父母之服不分身份高低,不分出嫁與否皆服以齊衰三月。又如關于為外祖父母之服,《喪服》傳曰:“何以小功也? 以尊加也。”[6]620即認為外親之服通常為緦麻三月,而為外祖父母服以小功,則是因為他們都是母所至尊的人,所以為他們加一等喪服。
由這些解釋可知,《喪服》傳文或以“至尊”,或以“旁尊”,或以“不敢降其祖”,或以“不敢降其嫡”為解的這些服例,實際上都是因為服喪者與服喪對象之間具有血脈親情。因為按照尊從上的原則,由父到祖等是越來越尊,則喪服應該逐代增重,故《喪服》經文的初義應當是按照由父到祖以上,血緣逐代疏遠而減輕的,因此為祖、曾祖之服才會不受服喪對象的身份等級和出嫁與否的限制。由此也可看出《喪服》經、傳之義的差異,故傳文更多地注入了寫作時代的印記,才會將“親親”服例以“尊尊”為釋。
四 小結
綜上所述,“尊尊”與“親親”二者雖相互支撐,但也存在彼此競爭的一面,當宗權強盛時,更突出“親親”之義;當君權強盛時,則服從于“尊尊”之義。《儀禮·喪服》經、傳之義的差異,正體現出禮制變化的印記。整個先秦乃至兩漢時期,禮制的基本準則并非是完全不變的,而是與社會政治、文化和習俗觀念的變遷而發生某種程度上的同步變化。所以,當君權為重的觀點逐漸受到認同時,《喪服》傳文就以“尊尊”之義來解釋本來的“親親”之服。
最后,可略作補充說明的是,上述兩種服制原則在當時亦有融合的趨向。例如就父、祖之服而言,《喪服四制》曰:“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3]1673即認為為父服斬衰三年之喪,是依據親情關系最為深厚而制定的。但《大傳》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3]1000《喪服小記》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3]963認為往上對于父祖者,是尊尊之義,往下對于子孫,才是親親之道,并被認為是人倫禮儀的根本所在。這種“上尊下親”的制服原則,則可視為是“親親”與“尊尊”二者調和的產物。
[1]金景芳.孔子的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六經[M]//金景芳古史論集.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1.
[2]王先謙.莊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2006.
[3]鄭玄,孔穎達.禮記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4]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5]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6]鄭玄,賈公彥.儀禮注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運城市文物工作站,絳縣文化局.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發掘報告[J].文物,2000,(8).
[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豐鎬考古隊.1984—85年灃西西周遺址、墓葬發掘報告[J].考古,1987,(1).
[9]陳立.白虎通疏證[M].北京:中華書局,1994.
[10]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11]葛志毅,張惟明.先秦兩漢的制度與文化[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
[12]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13]何丹.三年之喪起源諸說考辨[J].〔韓國〕中國史研究,2014,92.
[14]胡培翚.儀禮正義[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15]鄭玄,賈公彥.周禮注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16]周振甫.周易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1.
[17]劉向.說苑[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
[18]王先謙.荀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2006.
[責任編輯:張 卉]
B222
A
1000-5315(2015)03-0012-07
2014-11-28
何丹(1986—),女,四川蒼溪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先秦史專業博士生,研究方向為先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