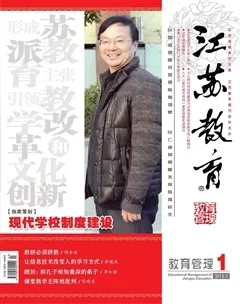文化自覺與內部管理2
“文化自覺”,由費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開辦的第二屆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上首次提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歷史圈子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包括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創建。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文化即人化,凡后天人為而成的都屬文化,包括人類從古至今所創造的所有物質和精神成果,可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方面。狹義的文化僅指精神文化。艾君先生認為,對文化的理解,更應該看成是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思維方式等主觀因素。與一個單位的內部管理相關聯的文化,與“自覺”相關聯的文化,應該是什么文化呢?人們有運用符號或概念的自由,一個概念實際上也存在各種用法。有人認為,文化自覺就是把單位的規章制度內化,做到隨心所欲而不逾矩,這講的是制度文化的自覺。本文所說的文化限于精神文化,主要指稱人的生命價值或意義觀念,文化自覺就是人意識到自己生命的價值、意義,尤其是崇高的價值、意義。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如柏拉圖要培養“哲學王”,培根要為整個人類在宇宙中爭取權力,康德要引導人類實現人類天性所能夠容納的最高的善。
人是一種精神生命,人的精神是永遠不滅的,只不過在“物質富裕”壓倒一切的時代,精神處于蟄伏狀態,或者個別自覺狀態。
溫飽之后,物質的魅力總會下降,精神必然與“尊榮”產生更緊密的關聯。以精神追求“尊榮”這種精神滿足似乎更加順理成章。可以預測,精神在人生的動力機制中將會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以精神追求精神的生活,這是人類的至高生活,它使人類超拔于一般動物之上,超然于生命的渺小之外,給人的生存以神圣的光彩。西方的哲學圣人斯賓諾莎,為了自己的思想獨立拒絕大學教授職位,也謝絕了崇拜者的財產相贈,靠磨鏡片為生,但每月只花幾天磨鏡片,一旦掙的錢能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就全身心投入自己的精神創造。另一位哲學圣人蘇格拉底,衣衫襤褸,光著腳丫,逛了一圈市場,說世界上竟然有這么多我不需要的東西。他沒有利用祖傳的雕刻手藝致富,而是把主要的精力和時間用于追尋永恒的善。他有多次機會避開死刑,但因不愿放棄自己的原則和信念而坦然喝下毒酒。
總之,人可以是一個精神生命體,精神可以成為追尋的目標和動力,這使文化自覺成為可能,使管理擁有了寶貴的精神資源。
文化自覺也是必要的。在現代的組織機構中,組織文化非常發達,各種規章制度組成一個立體網絡,密如蛛網,人就如這蛛網中被困的昆蟲。韋伯認為,這種科層制文化的特征是:權限明確界定;嚴格照章辦事;事本主義的人際關系;服從抽象權威。這雖然能夠保證行動的精確性、可靠性、有效性,也使人成為秩序人,陷入“鐵囚籠”中。科層制越發達,個性越貶損,人的情感與意志等個性因素越受壓抑。另一位社會學家默頓也指出了其缺點:刻板僵化;墨守成規;訓練性無能;工具價值變成最終價值;不利于相互溝通與協作。如果被管理者是流水線上的工人,這些弊端造成的危害并不明顯;如果被管理者從事的是創造性、靈活性、不方便用硬指標衡量的工作,這些弊端造成的危害可能就是致命的。學校的老師從事的教育工作就是具有創造性、靈活性,不方便用硬指標衡量的。細密的規章制度和外在的監督檢查勢必把教師變成被動、僵化、齊一的機械人,使教育行為變成機械動作,失去生命。至今仍常被人提起的“錢學森之問”,即為什么我們培養不出杰出人才或大師級人才?其實,還有一個“錢學森之答”,只不過罕有人提起,錢學森給出的解答是:教育最終的機理在于思維過程的訓練。我們的教育圍繞知識灌輸,思維訓練嚴重不足,這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解決辦法就是把思維訓練作為教育(道德培養除外)的核心。“錢學森之答”后面還有一個“錢學森之困”。錢學森在《關于教育科學的基礎理論》一文中提到:“我也曾到一所重點高等院校去聽課,聽了兩節內容相關聯的教學課,我聽了之后,感到教師講授太繁瑣,連習題也在課堂上講,有的學生連筆記都不記!課后我找兩位教師說,我說兩節課改成一節課就行了,留下習題讓學生自己思考去做,教學效果會好些,而上課時間減少了。我說,這不是很好嗎?兩位教師說,他們同意我的意見,但不能照我們認為正確的方法去辦,因為那樣辦,有些學生不習慣,是灌慣了改不過來了,就會向教師提批評意見,‘條子’多了,就會影響教師評職稱,提級別!這是落后阻礙了前進,不準前進!”(《高教戰線》,1985年第一期)
要還教育以生命力,規章制度需疏一點,監督檢查需緩一點,統一要求需少一點。會不會一放就亂?極有可能,畢竟“一抓就死,一放就亂”是常見現象,要放而不亂,只能靠文化自覺,即有點精神追求,以精神獲得精神滿足的教師可以不待揚鞭自奮蹄,他們是積極主動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們也是快樂幸福的。筆者認識兩位普通老師,山東的李向華和安徽的田金輝。李老師遇到一個小女生,她的衣服很臟,鞋子有大洞,書包看不出原色,襪子是兩個襪筒,上課時小手不停地抓腳面,腳丫子血淋淋的,沒有學生愿意與她接觸,她還在與同學打架時,抓破過同學的手和臉。李老師給她洗了腳丫,抹了藥,去商店給她買了一件小孩子們很喜歡的衣服、一個新書包、一雙新鞋子和10雙襪子。此后,一個小天使出現了,孩子幸福,李老師也幸福。在田老師生日那天,有個七年前的學生,從江蘇特地趕回來。為了在田老師生日那天繡好十字繡,這位學生每天白天上班,晚上熬夜做十字繡,一連繡了半個月。為什么田老師這樣受學生愛戴?因為田老師把關愛學生當成自己的生命意義。愛學生、愛教育是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帶來的精神幸福是一般的物質幸福不可比的。
除了個別的圣人,精神文化的自覺受制于制度文化和物質文化,制度要達到基本公正,物質要達到不憂溫飽。在《理想國》中,提到城邦的善有四種:勇敢、智慧、節制、正義(公正),其中正義(公正)能夠使勇敢、節制、智慧在這個城邦產生,并在它們產生以后一直保護著它們。一個群體,如果沒有基本的公正,勢必一盤散沙,邪惡橫行,文化自覺也是邪惡文化的自覺。對于溫飽的意義,中國古人認識得很到位,衣食足而知禮節,這不是必然但是常態。在制度上、物質上善待教師,與教師的文化自覺是聯動的。因此,學校里的文化自覺,應該是教師、管理人員、后勤人員共同的文化自覺,教師以文化自覺善待學生,管理人員、后勤人員以文化自覺善待教師。
做同樣的工作,人們賦予的意義和價值是不同的。愛因斯坦曾提到:做同樣的工作,它的出發點可以是恐怖和強制,可以是追求威信和榮譽的好勝心,也可以是對于對象的誠摯的興趣和追求真理與理解的愿望。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段子:三個工人在工地砌墻,有人問他們在干什么?第一個人沒好氣地說:砌墻,你沒看到嗎?第二個人笑笑:我們在蓋一幢高樓。第三個人笑容滿面:我們正在建一座新城市。10年后,第一個人仍在砌墻,第二個人成了工程師,而第三個人,是前兩個人的老板。文化自覺作為生命價值、意義的自覺,具體表現之一就是工作價值、意義的自覺,覺察到的正面價值、意義越大、越多、越崇高,越不需要外在的監督強迫,就越有創造力,越精力旺盛、心情愉悅,人生成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