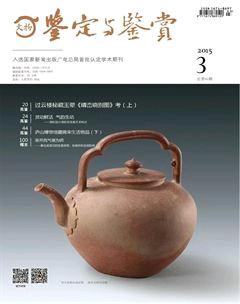靈動鮮活 氣韻生動
沙偉



被徐悲鴻譽為“中國花鳥第一人”的趙少昂(1905—1998年),為20世紀“嶺南畫派”第二代大師。他在繼承了“嶺南畫派”傳統的同時,率先提出了“國畫是藝術的最高峰”的觀點,并以“融會古今,折衷中外”的藝術理念,一生致力于中國畫的傳統發揚和革新拓展。他創作的花鳥畫根植于傳統中國畫的深厚土壤,對傳統改革的同時努力向傳統回歸,成為傳統藝術的精華,在中國美術史上亦占有不可動搖的地位。他的藝術創作理論及其作品,尤其是花鳥畫,對推動近現代中國畫的創新和轉變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
趙少昂的花鳥畫氣韻生動,形象逼真,在海內外享有盛譽,深受人們的喜愛。由于他在創作前必做深入的審度、體察和妙悟,注重對花鳥的仔細觀察,強調對大自然生命的把握,準確對花鳥形神的概括,故筆下描繪的花鳥靈活生動而富有神韻,寥寥數筆即可塑造出一個個靈動鮮活的生命。同時他還充分發揮了書法用筆的表現力,筆墨奇肆,獨具風格。在他的藝術生涯中,其早期創作的花鳥畫勾線、著色尤其灑脫工致,特別著重于寫生的真實感。至晚年,花鳥畫創作則是“由博返約,老而愈妙”,強調神韻而能于奔放、粗狂之中見精細。2015年3月6日是趙少昂誕辰110周年,為此筆者在此簡析其創作的花鳥畫藝術特點,以此緬懷“中國花鳥第一人”的藝術人生。
一、我之為我,自有我在
關山月在他《試論趙少昂的繪畫藝術》一文中提到,趙少昂雖然師承“嶺南三杰”之一的高奇峰,但畫風卻不像其老師,早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個人風格。故人們都公認他的畫風極其新鮮突出,確實達到了“我之為我,自有我在”的藝術境界。在他的花鳥畫中,既有傳統、師承的寫生筆墨,又將它們與寫意融于一爐進行創新,在不斷否定、揚棄中發展了花鳥畫創作水平。他的學生桃李滿天下,但要求學生的畫風卻不要跟他一樣,要創造各自的風格,鼓勵“青出于藍而勝于藍”“要為人所不能,不為人所不為,我過去的畫不能代表我。”他在師承“嶺南畫派”革新精神的同時,也批判地繼承了中國畫藝術的優良傳統。他還強調“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將古今中外好的養料消化成自己的血液,而且身體力行用了功夫,并且用得很到位,用之來表現時代精神,從而發展了傳統。他筆下的花鳥畫沒有照相式的照搬,沒有工筆畫的須眉畢現,也沒有文人畫的擴張自我,而只有“我之為我,自有我在”的獨特畫風。世人皆知畫白孔雀比畫彩孔雀難,但趙少昂卻是反其道而行,迎難而上。例如,現藏于香港文化博物館的、他創作于1969年的《霜光素羽》(見圖1)。該畫中正在開屏的素白孔雀似乎即刻就要展翅高飛,讓觀者感受到美得炫目的孔雀不僅散發著高雅的氣度,而且感覺它富有極強的生命力。無怪乎人們形容他的花鳥畫“好像被上帝親吻過”,畫面中的花鳥都是有靈魂的。
在批判地繼承中國畫傳統藝術的同時,趙少昂的花鳥畫創作鼓勵解放思想,“筆墨當隨時代”。不要人云亦云、作繭自縛、東施效顰;不要以仿古為榮,反對食古不化地學習遺產和陳陳相因地抄襲;不要充當古畫和洋畫的奴隸,反對生吞活剝地仿效西洋。要不失主宰地表現客觀現實,反對自然主義地描繪,更反對曲高和寡、脫離大眾的所謂“國粹”。他的花鳥畫創作提倡雅俗共賞的大眾化畫風,主張“畫抒情”“詩言志”,還原藝術于人民大眾。如他創作的非常符合大眾審美情趣的代表作《桐花孔翠》(見圖2)。此作曾收錄于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趙少昂畫輯》和1985年出版的《趙少昂畫集》。畫中立于樹干上的孔雀以兼工帶寫的筆法出之,五彩的羽翼層層勾染,尾羽華麗但不繁縟,錦翎構圖優美自然。孔雀頭部羽冠開張,眼神炯然,精工的描摹將它高貴悠然的神態刻畫畢現。濃墨大寫意繪出的枝干落筆粗狂,而遠近錯落有致、富有層次感的枝干與纏繞花卉,則巧妙填充了畫面的空白。該作雖然沒有自然主義地描繪,但是卻獨到地表現了客觀現實,表現了孔雀的華麗、大美。由此可見,他的花鳥畫雅俗共賞、栩栩如生,甚至比自然界的花鳥更真、更美、更富有活力。
二、以形寫神,形神兼備
趙少昂的花鳥畫最大特點,就是以形寫神,形神兼備,充分體現了準、穩、狠的“一筆過”之功。他自己也養鳥,并且走入了花鳥的客觀世界做深入細致的觀察、分析和研究。他數十年如一日忠實花鳥寫生,在腦海中累積了各種花鳥活潑多姿的“形”,才達到了簡練準確的“一揮而就”。他腦子里如果沒有“形”作為堅實深厚的基礎,就是再高超的筆墨亦是枉然。
他的花鳥畫行筆、用墨和著色一般是先在沾筆上下功夫,同時又講究行筆輕重、快慢和剛柔的分寸,因此他筆下的花瓣鮮艷欲滴,蟬翼蟲翅透明輕盈,雀鳥嘴爪堅硬有力。花鳥“一筆過”后即可以見出深淺和濃淡的程度,更可見出各種顏色的變化,妙筆入神達到氣韻生動的藝術境界。在趙少昂1970年創作的《木棉紅占嶺南春》里(見圖3),自然界的色彩得到肆意的迸發。畫面里春日的繁花體現出他獨特的藝術審美,犀利的線條和多種顏色的運用為小鳥注入了生命力。以形寫神的小鳥形神兼備,極具活力的“一筆過”勾畫了繁盛的木棉和春日萬物勃發的景象。
三、濃彩重抹,善于調色
在色彩的調節方面,趙少昂能充分利用英國水彩,創造出純凈妍麗、對比強烈、超凡脫俗、拍案叫絕的藝術效果。他首創濕粉寫法,善于用濕粉寫色紙和“撞粉法”寫熟宣,并且控制水分有方,濃彩重抹,使色調變化莫測,深淺干濕適宜,所繪花鳥的色彩既對比強烈又協調統一,既鮮艷欲滴而又含蘊凝練。他創造的調色與運筆相結合,能將色彩的微妙變化完成于剎那間的一筆之中,用色明快且深淺天然,痛快淋漓且榮枯畢具,表現了極其豐富的藝術內涵。例如,收錄于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趙少昂畫集》中趙少昂的代表作《一池楊柳垂新綠》(見圖4),色彩于凝重之中見鮮麗,表現了那種迷惘的空間感,令人陶醉。而在現藏于中國美術館、1945年創作的《蝴蝶花卉》中(見圖5),他借鑒了日本畫藝,蝴蝶在花卉中飛揚的瞬間筆墨造型用筆精妙,調色體現了畫家精于用水用粉的神功。同時作品強調了蝴蝶與花卉在色彩中的對比,使得畫面情趣別致,簡練生動,具有強烈的藝術個性。
四、小巧秀雅,主題鮮明
趙少昂的花鳥畫多以小品形式創作,畫幅雖小巧秀雅,但表現卻是主題鮮明。其眾多的花鳥畫作品短小精悍,耐人尋味,通過“以少總多,以小見大”,靈動變化、虛實相應地表現了生命的流動,創造了由有限而通無限的境界與生機。他筆下創作的斗方精妙小品雖尺幅不大,但所傾注的精力不亞于大幅巨作。在香港藝術館藏、1973年他創作的《秋林如醉》中(見圖6),小巧的畫幅雖只用了寥寥幾筆,構圖用色也非常簡潔,卻已將枝頭小鳥迎著秋風在林中如癡如醉地歡唱的動態,栩栩如生地表現了出來,突出了他的用筆技巧和造型概括能力。
在趙少昂所著《實用繪畫學》一書中,他示范的花卉就有數十種之多,可見其花鳥畫題材非常廣泛。他的花鳥畫小品以筆墨論之,筆法奇詭多變。畫花卉時多用羊毫側鋒濡筆,以表現其輕柔嬌嫩的姿態。而在四季花卉的點綴上,他多配以小鳥或不同的草蟲作畫。如香港文化藝術館藏、1992年他創作的《蟬聲幽咽》(見圖7)。趙少昂非常喜歡蟬,自譽其為蟬,認為蟬就是寓意清高,且他創作的畫室稱為“蟬焉室”。常人與他的蟬畫亦難以匹敵,據說齊白石還曾托他在香港的朋友向趙少昂求過蟬畫。該作以極淡的筆墨畫出花卉與枝葉,卻突出了奮力向上爬躍的蟬,其小巧秀雅、主題鮮明的畫風躍然紙上。
五、布局講究,留白尋味
繪畫中堅實的內容需要良好的表現方式,而表現方式中的構圖布局最考畫家的功力。因此趙少昂的花鳥畫特別講究布局,筆墨所到之處盡顯其構圖神功,尤其是畫面的空白處更慧心思。他善于恰如其分地使用“知白守黑”這種虛實對比的關系,在尺幅的天地中能夠縱橫馳騁觀者的想象,從而將表現的對象更加集中、更為突出,予人以空靈流暢之感。
畫面留白是一種繪畫藝術技法,傳統的花鳥畫大都不交代空間,背景留白。通過所繪花鳥聯想空白處所存在的相關空間,從而造就畫家與觀者心理溝通的想象空間。此畫技為一種“藏境”手法,景愈藏而境愈大、意愈深。香港文化藝術館藏、1992年趙少昂創作的花鳥畫《霜葉偏紅》(見圖8),整幅畫獨有一只小鳥,畫面左側基本留白,僅在下方清點淡墨樹枝。構圖干凈利落,主題突出,給觀者創造了一個奇妙、幽美、神秘的畫面形象。
六、詩情畫意,氣韻生動
趙少昂精于書法,善題詩,其花鳥畫極富詩情畫意。他喜以狂草字體在花鳥畫上作長題,題詩畫行云流水猶如天馬行空,無束無拘,個性十足。同時詩畫相同相連,相互映襯,相得益彰,在創作上窮自然之秘奧,極繪畫之能事。在他收錄于人民美術出版社《趙少昂畫集》中的代表作《秋去春來常為伴》中(見圖9),他兼工帶寫地繪四只鴛鴦棲息于溪畔濕潤的沙洲上,前后相偎,安靜祥和。背景以淡赭渲染沙渚水面,蘆葦瑟瑟,曠野中僅鴛鴦相互依偎,極富“溪上鴛鴦獨有情,秋來冬去長為伴”詩意。
中國美術界歷來講究“書畫同體”,書畫創作均為筆墨運行,用線條的節奏表現自然的形與意。而畫學上講究的最高原則,為由筆墨產生的“氣韻生動”,趙少昂的花鳥畫就完全做到了這一點。特別是畫中的題跋從形式上匠心獨運,別具一格,與畫面渾然一體。創作時意到筆到,一氣呵成。其早期作品即已受到詩趣的影響,詩趣亦成了他在藝術發展的一個方面。如香港文化藝術館藏、1969年他創作的《迷蒙月色滿橫塘》(見圖10)。那半浸水中依舊張開的殘荷在做生命最后的堅持,瑟縮斜伏在枯莖上的麻雀凍得閉上了眼,生命的榮枯無常盡現眼前。尤其是畫作中“迷蒙月色滿橫塘,幾葉殘荷減翠妝,夜來露冷凝冰雪,吱吱寒雀話荒涼”題跋的濃情詩意,則使得“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表達層次超脫物象,升華到詩意、哲理的精神境地。
趙少昂的花鳥畫以獨特的目光,詩人的情懷,為后人留下了無盡的寶貴財富。無怪乎原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吳作人曾高度評價其“于山水人物、走獸、翎毛、花木、蟲魚無所不能,而猶以花鳥魚蟲,擇精取萃,傳寫入微,最為人所珍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