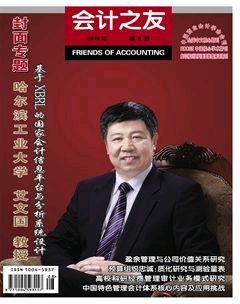基于負所得稅的以家庭征收個人所得稅研究
鞠可一 唐超 吳君民
【摘 要】 通過對現有以個人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存在問題的剖析,論證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的必要性、可行性,基于負所得稅理論,提出了以負所得稅向低收入家庭進行財政轉移支付,按家庭納稅模式對應納稅額以上的家庭征收所得稅,以期最大限度地發揮個人所得稅在縮小貧富差距、調節社會分配方面的功能與作用。
【關鍵詞】 個人所得稅; 負所得稅; 家庭為單位
中圖分類號:F810.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937(2015)08-0104-04
一、引言
2011年6月30日個人所得稅修訂法案將免征額由2 000元提高到了3 500元,將最低稅率降到3%,原來的9級超額累進改為7級。但據國家稅務總局2013年數據統計:我國城鎮居民工資性收入占城鎮居民人均總收入的比重為64.1%,而工薪所得收入占個人所得稅收入的比重為62.7%,這顯然不盡合理和有失公平。另據國家統計局發布:我國2013年基尼系數為0.473,顯示收入差距較大,這說明當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并未能合理發揮調節收入差距、緩解社會矛盾的作用。
近年來,我國許多學者對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進行研究,部分學者提出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征收模式。馬伶俐(2012)認為“應將申報單位由個人改為家庭。因為這比我國現行的定額扣除法更公平、合理”。遲騁(2012)認為“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個稅征收有助于實現橫向公平,充分考慮納稅人實際家庭負擔和經濟狀況,且有利于我國傳統觀念的保留和發揚”。但是他們的研究方向僅局限于對納稅家庭調節,忽視了對納稅額以下家庭的照顧和保障。李翔海(2006)認為“負所得稅的社會福利思想對正處于轉軌期的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聶佃忠(2004)認為“我國政府應盡快實施負所得稅政策來充實我國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王春萍(2008)認為“負所得稅的提出和應用,為社會保障、收入轉移問題提供了新方法。從我國實際出發,借鑒國外負所得稅理論,實現負所得稅與社會保障制度的結合,以克服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提高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與效率”。王冬華(2011)認為“負所得稅與社會保障稅統籌設計是有必要的”。他們的出發點都是將負所得稅理論應用在社會保障制度上,認為負所得稅理論可以為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障制度提供借鑒意義,但是沒有對具體如何借鑒,如何結合中國實際進行個人所得稅改革進行深入研究。本文擬結合前人的相關研究成果,分析當前個人所得稅存在的問題,論證以家庭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基于負所得稅理論對以家庭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進行應用研究。
二、以個人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存在的問題
(一)個人所得相同,納稅額不同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以個人為單位,分類計征,分類扣除,對不同收入來源分別適用不同的費用扣除,而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收入單一的人多繳稅,收入多元化的人少繳稅。假設納稅人甲本月工資、薪金所得3 500元,勞務報酬所得700元,房屋出租取得財產租賃所得700元,稿酬所得600元,但由于各項所得都未超過扣除標準,所以他本月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納稅人乙工資、薪金所得5 500元,應納稅額為95元;納稅人丙工資、薪金所得2 500元,勞務報酬所得3 000元,應繳納所得稅額為(3 000-800)×20%=440(元)。見表1。
表1表明,所得相同,但是收入來源不同,稅收負擔不同,影響稅收公平性,這樣會變相地促使納稅人分解各項所得額,進而逃避應納稅額,造成國家稅收損失。
(二)家庭所得相同,納稅額不同
目前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只考慮了單個人的基本情況,忽視了家庭實際狀況,而家庭是構成社會穩定的基本元素,同樣所得的家庭由于家庭成員構成不同而導致承擔的稅負不同,因此可能會加重納稅家庭負擔,挫傷納稅人的積極性。假設有A、B、C三組家庭。A家庭丈夫工資、薪金所得7 000元,妻子待業無工作,家庭應納稅額(7 000-3 500)×10%-105=245(元);B家庭丈夫工資、薪金所得3 500元,妻子工資、薪金所得3 500元,應納稅額0元;C家庭丈夫工資、薪金所得4 000元,妻子工資、薪金所得3 000元,家庭應納稅額(4 000-3 500)×3%=15(元)。見表2。
表2表明,相同所得的家庭,應納稅額可能會相差很大,這就說明當前個人所得稅設置不盡合理,只是硬性地對個人所得進行調節,忽視了家庭成員、收入來源等實際狀況,從而導致家庭所得相同納稅壓力不同,顯然這是有悖于稅收公平性原則的。
(三)家庭所得相同,可支配收入不同
目前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實行“一刀切”做法,免征額全國統一為3 500元,看似公平實則不公平:一是忽略了現實社會生活情況;二是忽略了地區發展不平衡狀況。假設現有三個不同地區相同所得家庭,丈夫工資、薪金所得6 000元,妻子工資、薪金所得6 000元,那么每個家庭每月應納稅額=[(6 000-3 500)×10%-105]×2=290(元)。家庭A一對夫妻一個孩子,生活在上海,租房居住;家庭B一對夫妻兩個孩子,生活在南京,已購房無房貸;家庭C一對夫妻無孩子,生活在西安,購房有房貸。家庭A每月支出:租房3 000元,生活費4 000元,教育1 000元,可支配收入=6 000+6 000-290-3 000-4 000-1 000=3 710(元);家庭B每月支出:生活費3 000元,教育1 500元,可支配收入=6 000+6 000-290-3 000-1 500=7 210(元);家庭C每月支出:房貸1 500元,生活費2 000元,可支配收入=6 000+6 000-290-1 500-2 000=8 210(元)。見表3。
由表3可知,不同地區間家庭所得相同,可支配收入卻有很大差異。由于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一刀切”的個人所得稅征收做法缺乏有效的彈性,忽視了家庭所得來源差異和各地生活水平差異。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沒有考慮購房、教育等大額生活發展性必要支出情況,而在現實生活中房貸、子女撫養、老人贍養、教育醫療等支出是重大而且必不可少的支出,忽略這些現實情況將不僅影響稅收的公平性,還影響我國居民生活的幸福度。
三、以家庭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以家庭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理論依據
1.負所得稅理論。196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貨幣主義學派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首次提出負所得稅理論,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提出以負所得稅對收入分配方案進行改革。曼昆在《經濟學原理》中將負所得稅簡單定義為:“向高收入家庭征稅并給低收入家庭轉移支付的稅制。”其主要目標為:提供一種對現有福利救助體系的替代,有效地反貧困和激勵貧困家庭工作的積極性。負所得稅理論的出發點是將現有的累進所得稅結構擴展到低收入階層中。換句話說就是政府對于低收入家庭依照其實際收入與維持一定社會生活水平需要的差額,運用稅收形式,對低收入者補助。
2.國民經濟兩部門理論。現代財政學之父理查德·阿貝爾·馬斯格雷夫在《財政理論與實踐》一書中將國民經濟分為兩個部門:家庭和企業,這兩個部門是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家庭作為最基本的社會組成部分,是由婚姻、血緣或收養關系組成的基本單位,個人是家庭的組成部分,一個人的家庭是家庭,多個人的家庭同樣也是家庭。在我國,傳統儒家文化家庭觀念根深蒂固,為以家庭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提供了群眾基礎。
3.馬克思主義勞動力價值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勞動力的價值同其他一切商品價值一樣,是由生產它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勞動力價值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馬克思,2012)。而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在費用扣除上沒有考慮勞動者為保障和提高勞動能力的生存、發展支出,也沒有考慮到勞動者為延續勞動力市場不斷供應而對子女的保障、教育、醫療等支出。所以從馬克思主義勞動力價值觀出發,我國應實行基于家庭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
在我國,以個人為單位的征稅模式不能考慮到家庭負擔等因素,相同收入的家庭可能因為不同的家庭環境產生稅收不公平現象,而按照家庭為單位征稅能兼顧家庭實際情況,體現稅收公平,調節家庭收入差距,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二)以家庭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必要性
1.體現稅收量能負擔原則。個人所得稅制以個人為征稅對象,忽視了納稅人的家庭構成和負擔,容易導致相同收入不同稅額,特殊家庭稅額加重等現象,進而失去對收入的調節作用,影響稅收公平性的體現。而實行以家庭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可以有效避免以上現象,照顧特殊家庭,體現以人為本思想,實現稅收公平。
2.切合中國國情與實際。(1)中國個人所得稅改革核心幾乎是免征額的提高,免征額的提高的確可以局部調節收入,但是調節作用是極其有限的,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工薪家庭是納稅主體這一現狀;(2)“一刀切”的免征額忽視了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加重了富裕地區弱勢群體的生活負擔,減輕了貧困地區富裕家庭壓力,失去了調節作用,不能緩解貧富差距擴大化;(3)當前個人所得稅體制具有嚴重的滯后性,我國個人所得稅的調整需要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程序復雜歷時長久,而經濟發展程度、通貨膨脹率每年都會變化,當前稅制不能進行及時有效的調整,喪失了稅收的調節作用。以家庭為單位征收個人所得稅可以區域為單位根據當地經濟水平進行調整,采取定額扣除與消費者物價指數相結合的浮動扣除方法,真實有效地對納稅群體納稅額作出反應,增強個人所得稅的彈性,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質量,提高人民生活幸福度。
3.當前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完善。市場經濟是效率型經濟,在社會經濟資源得到有效配置的同時也必然會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現象,社會保障制度是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重要部分,旨在對貧困家庭提供幫助。“現行社會保障制度是以養老、失業、醫療三大保險為基本單位,以工傷、生育、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為輔助項目的社會保險體系”(王冬華,2011)。而低收入家庭由于收入過低不能納入三大基本保障項目中,受救濟對象也僅能維持溫飽,醫療、教育等權利不能得到享受,再有我國收入調查核準手段缺失,從而導致騙保現象的發生。這一系列的弊端都會加劇貧富差距擴大化,使得窮困者更窮,顯然不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而實行家庭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可以通過收入證明準確核實家庭收入實際狀況,運用負所得稅對貧困家庭實施補貼,從而有效地緩解目前社會保障制度對低收入家庭低效率的有限幫助,真正意義上使人民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
(三)以家庭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實行的可行性
1.信息化建設已不斷完善。我國互聯網發展迅速,政務信息已經可以做到互聯互通、信息共享,戶籍制度歷史悠久,可以為以家庭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實行提供技術支持。
2.發達國家稅法實踐經驗可以提供借鑒。加拿大已經開始較大范圍實行負所得稅制,而且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實行家庭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已有多年,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也實行家庭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這些國家都可以為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提供借鑒。
3.受到廣大工薪階層的歡迎。工薪階層一直戲謔中國個人所得稅是“工薪稅”,而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廣大工薪階層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了全額的65%,而最富有的富人層只繳納了10%,這顯然是極不合理的。以家庭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能夠使公平性發揮出來,顯然會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同時由于我國傳統儒家家庭思想影響深遠,以家庭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征收模式將更易于接受和維護。
四、基于負所得稅理論的家庭納稅模式應用研究
(一)負所得稅財政轉移支付低收入家庭
對低收入家庭實行累進機制的負所得稅比低保社會保障制度更有優越性,可實現從高收入家庭征稅轉移支付給低收入家庭。當前個人所得稅對低收入家庭稅負考慮不夠,對貧困家庭實行低保社會保障制度,而這種低保“社會保障制度采用差額補足式救助,只要在保障線以下,補助以后最終全部可支配收入相等”(王春萍,2008)。這種補助制度是無效的,不能刺激勞動積極性,相反容易出現“養懶漢”現象。而負所得稅實行累進機制,消除了定額補助下臨界點附近稅負的不公平現象,將低收入者也納入了個人所得稅范疇進行反向轉移支付,體現了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將對富人的征稅反補窮人,調節收入差距,緩解社會矛盾,而且負所得稅的累進機制有助于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勞動積極性,提高其可支配收入水平,從而使得窮困家庭醫療、教育等得到有效改善,增加脫貧機會。負所得稅理論體系旨在完善社會福利制度,使得窮困家庭受益。負所得稅計算公式為:負所得稅=收入保障數額-實際收入×負所得稅稅率,可支配收入=實際收入+負所得稅,轉折收入(免征額)=收入保障額/負所得稅稅率。
由表4可知,實際年收入在0到30 000元范圍內,負所得稅額隨實際年收入累進,實際年收入越低,可獲得政府補助越多,實際收入越高獲得越少,隨著實際收入增加達到轉折收入30 000元(即免征額以上)時,負所得稅的反補作用消失,對于家庭收入高于30 000元以上的將按照稅前可抵扣項目扣除征稅。負所得稅對低收入者補助不搞平均主義,而是量能補助,鼓勵低收入者工作增加收入,最終減少對補助的依賴。同時隨著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有助于低收入家庭提高消費能力,改善生活質量,提高受教育、醫療保健水平,最終徹底改善貧困狀況。負所得稅率的核定以及地區生活保障線是負所得稅實行過程中最重要之處,負所得稅稅率一般固定,以不超過50%為宜。負所得稅額由低收入家庭根據實情向稅務部門申報,經稅務部門審核批準之后向符合條件家庭發放轉移補貼資金。低收入家庭獲得的各類政府救助、社會捐助等將視為其收入。
(二)家庭所得稅調節征收正向應納稅所得額
改變當前以個人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同時改變分類征稅模式,對于應納稅所得額超過免征額的以家庭為單位按照正向所得稅稅率進行納稅,具體建議如下:
1.實行綜合所得征稅模式。不再區分納稅人所得的性質和來源,將全年所有收入全部計入應納稅收入,扣除免征額,扣減可抵扣費用后的應納稅所得額按照對應的各級累進稅率實行綜合征收。對于應稅所得額在取得時代扣代繳的部分,年底進行匯算清繳,實行多退少補。
2.合理設定申報主體。可以由納稅人自主選擇單身納稅人、已婚單獨申報納稅人、已婚聯合申報納稅人、以戶主身份申報納稅人四類申報主體(劉效辰,2013),充分考慮納稅主體的特殊性,合理設定稅率,設置符合納稅人實際稅負能力和家庭成員數量、年齡、健康等實際狀況的納稅模式,一經選定不得隨意變更,更公平地衡量家庭的實際納稅能力。
3.合理設定免征額。由于我國地區經濟發展不均衡,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收入差距過大,各地的標準也應該有所不同。國家對地方放權,由省級人民政府根據地區經濟水平設定免征額,上報全國人大審批確定。免征額的設定為地方生活保障線除以負所得稅稅率。
4.合理設定稅率。我國家庭所得稅應實行多級超額累進稅率,稅率由國務院根據我國實際國情制定,并經全國人大審議通過實施。稅率設定應體現公平稅負、量能負擔原則,從而更好地調節社會分配。
5.完善扣除項目。細化費用扣除項目,參照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將對費用扣除項目進行指數化調整,根據地區每年通貨膨脹情況,將物價指數與個人收入形成聯動機制,定期調整,充分發揮稅收的彈性調節作用。細化費用扣除項目,考慮家庭構成人數、食品支出、衣物支出、住房情況等項目確立家庭基本生存可抵扣項目,對家庭教育費用、受教育子女人數、個人自我發展支出等項目確定基本發展可抵扣項目,對醫療大病費用、幼兒保健、老人贍養等項目確定基本保健可抵扣項目。此外,還應考慮到其他稅收抵免項目,如國務院特殊津貼、政府獎勵等項目。總之要以人權為基本出發點,具體細化量化可抵扣項目,在兼顧家庭特殊性的同時體現人性化,實現稅收的公平。
6.完善稅收征管制度。(1)完善稅務信息系統,實現金融稅務信息一體化,將納稅卡、身份證、戶籍、銀行卡等進行一體化綁定,推行非現金結算,建立納稅誠信檔案,對納稅違規違法等行為進行嚴懲;(2)推行稅務代理人制度,方便納稅人納稅申報,避免由于納稅信息不對稱導致的納稅違規現象。
五、結語
曼昆(2013)曾經說過:“稅收是我們文明社會所付出的代價。”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從設計之初到不斷完善,個人所得稅發揮的作用會越來越大,現有的個人所得稅制顯然不符合當前經濟社會需求。因此,以家庭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制具有較好的可行性,它的征收充分體現了公平、民主、人權等思想,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則,對個人所得稅的改革與完善將有更深遠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馬伶俐.重構我國個人所得稅稅收體系[J].合作經濟與科技,2012(19):89-91.
[2] 遲騁.個人所得稅以家庭為單位征收問題研究[J].現代營銷,2012(7):265-266.
[3] 李翔海.弗里德曼的社會福利思想研究[D].華中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4] 聶佃忠.負所得稅:我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J].甘肅理論學刊,2004(5):64.
[5] 王春萍.負所得稅理論對社會保障制度與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借鑒[J].吉林金融研究,2008(1):60-61.
[6] 王冬華.負所得稅理論視角下個人所得稅制度研究[D].東北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7] 曼昆.經濟學原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 劉效辰.以家庭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稅制改革問題研究[D].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