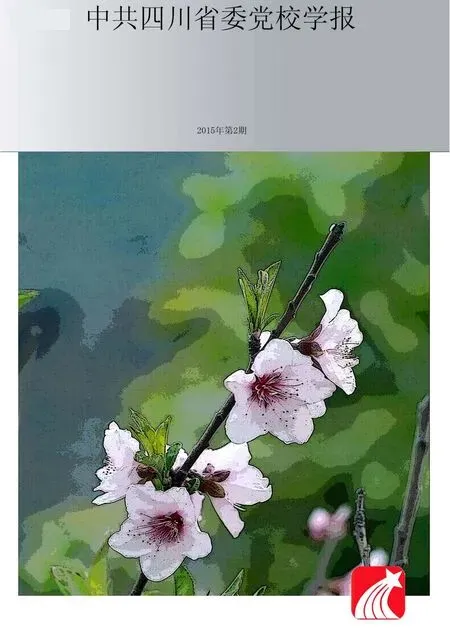論法治社會的基礎
——以西方市民社會為借鑒的研究
李文波
(中共國家稅務總局黨校涉稅法律教研室,江蘇揚州 225007 )
?
論法治社會的基礎
——以西方市民社會為借鑒的研究
李文波
(中共國家稅務總局黨校涉稅法律教研室,江蘇揚州 225007 )
法治社會;市民社會;社會基礎
十八屆三中全會形成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這種從國家、政府到社會的立體圖示揭示了法治的生態性。本文試圖通過對西方法治中市民社會的研究,提出市民社會是西方法治的重要社會基礎,其中的有益社會實踐可以為中國法治社會的形成提供一種研究的視角,一種可嘗試的實踐。
市民社會,英文為“Civil Society”,在我國又有“公民社會”和“民間社會”的譯法①。德語為“burgerliche Gesellschoft”,可譯為“市民社會”、“公民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②。市民社會是從拉丁文Civil Societas演化而來的。在拉丁文中,Societas一詞具有協會、聯盟、結社之意,與英文Society(社會、社團、協會)之意相近,而拉丁文civilis在古代尤其是羅馬共和國時期就代表了一種西方特有的法律和社會至上的意思。③另外,civilis不僅指法律而且指私人權利,不僅包括私人自由活動和居住的權利,而且主要指公民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權利,及與他人訂立契約和從事貿易活動的權利等,這體現了市民社會與民主精神的聯系④。此外還有將“Civil Society”稱為市場社會的⑤。與此同時,在馬克思之前出現的市民階級(階層)、中產階級、第三等級及其在馬克思之后的“公共領域”、“第三域”、“第三部門”等術語也都同“市民社會”具有同一質性。可以看出學界對于市民社會概念的定位一直眾說紛紜⑥,在我國近年來普遍性的定義是:市民社會不是廣義的社會概念,而是與政治國家相對應的特定范疇,它指的是個人、團體按照非強制原則和契約觀念進行自主活動,以實現物質利益和社會交往的、不受國家直接控制的民間獨立自治組織和非官方亦非私人性質的公共領域,亦稱公民社會或民間社會⑦。
市民社會是西方法治政府建立的社會基礎,其自身所蘊含的特質為法治政府所需具備的合法性、民主性以及限權性觀念提供了社會基礎。
一、市民社會的契約性為合法性觀念提供了社會基礎
按照基恩的看法,對市民社會的界定主要是從以下兩條路徑展開的:古典的市民社會概念表征與自然狀態相對的文明社會的生活,從亞里士多德始,中經西塞羅,至近代的休謨、盧梭、康德乃遵從此進路⑧;近代市民社會始于18世紀的啟蒙時代,表征的是一種與國家相對立的社會經濟結構,是一種不同于國家的實體,以黑格爾為其典型代表,他是在西方學術界首先確認了與國家二元分離存在的“市民社會”這一術語的第一人。然而無論是相對于自然狀態的文明社會還是相對于政治國家領域的經濟領域,兩者都強調人為秩序的重要性,而這種人為秩序的形成和存續依靠的便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契約。可以說市民社會依賴的是契約和法律,在古希臘,Civil概念已經“是一個超越血緣關系又超越王權專制的帶有普遍性的法律資格的概念”⑨。喬治·霍蘭·薩拜因教授指出,當時的人們不認為法律代表國家,也不認為法律是統治階層或立法團體中少數人私人意志的產物。相反,他們認為法律是人類為了共同生活所必須遵守的天賦的或至高無上的原則;在人們心目中,法律是代表社會的,人們把社會和人民看得高于國家和長官。⑩


二、多元性為民主觀念提供了社會基礎

事實上,社會權利相對于國家權力而言顯得十分松散甚至顯得單薄,但社會權利的真正作用在于它的潛在性,也就是說社會權利對國家權力的抗衡不是一種面對面的較量,而是一種潛在的較量:國家喪失社會的認可,也就喪失了權威,權威的喪失導致合法性的喪失,合法性的喪失最終會導致國家權力的弱化。正是多元性的存在,才有社會的存在,才有了社會權利;正是有了社會的存在,才能有有效參與法治政府建立的民眾的存在。如果僅僅只有國家的存在,社會完全是國家的附屬,那么法治政府的存在就喪失了社會理由、社會動力,就根本沒有意義從而也根本不可能實現。一個獨立于政府的、多元的、擁有多重利益的社會的存在,是對政府權力進行制約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曾經強調一個存在有貴族階層的社會對于維護自由的重要性。多元化的社會構成了一個國家的中間結構,對于任何制度的國家來說,都是實現民主與法治的重要維系。當民眾缺乏獨立的個人利益,當民眾都深深依附于國家權力所帶來的利益從而一切都以國家利益為判斷、取舍標準時,也即當人們的利益因為國家而單一化,多元的觀念就無生存的土壤,進而,國家權力就不可能成為人們監督的對象。相反,國家權力會進一步地通過利益的得失來控制民眾。
三、自治性為限制權力觀念提供了社會基礎

總之,在市民社會中自治性可總結為:“特定的政治框架形成并限制個人可利用的機會,在這個框架范圍內,個人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因而承擔同等的義務;這就是說,只要他們不用這種框架來否定別人的權利,那么,他們在決定自己的生活條件時就應該是自由和平等的”。因此,自治性必須被限定在法定范圍和一定框架之下,只不過這種范圍和框架不是由公共權力自由意志設定的而是由市場需要決定的,自治性并不能逃避責任和義務。


總之,市民社會的自治性是產生人權觀念的社會土壤,同時市民社會的自治性把專斷權力和非正當國家干預的能力降到最低程度,限制了權力網絡向社會的擴展,為實現法治提供了社會力量的支撐。
注釋:
①參見何增科主編:《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何先生指出,該詞在國內有三種不同的譯名,即“公民社會”、“市民社會”和“民間社會”。何先生提到正如俞可平教授所指出的那樣,這三種不同的中文譯名之間存在著一些微妙的差別。“市民社會”是最為流行的術語,也是civil society 的經典譯名,它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中文譯名。但這一術語在實際使用中帶有一定的貶義,傳統上人們往往把它等同于資產階級社會。“民間社會”是臺灣學者的譯法,它是一個中性的稱謂,但不少人認為它過于邊緣化。“公民社會”則是一個褒義的稱謂,它強調公民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參與和對國家權力的監督與制約。本文并不著力于分析市民社會的深層問題,故此,遵循學界傳統,用市民社會籠統代之。
②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會同資產階級社會系同一個詞,市民社會在他的前期思想中使用得較多,而后期思想多用作資產階級社會。關于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是非常復雜且在多重意義上被使用。應在具體的語境中具體地分析。關于此,可參見俞可平的“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及其歷史地位”(《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方朝暉的“市民社會的兩個傳統及其在現代的匯合”(《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5期)。
③Civilis在拉丁文中可指羅馬共和國時期的民法,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法律用語。
④方朝暉:《市民社會的兩個傳統及其在現代的匯合》,載《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5期第29頁。
⑤可參見鄧正來等編,《國家與市民社會》,第39頁;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載于《知識分子的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第86頁。);根據波蘭尼的解釋,市場社會就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⑥故此,學界對市民社會這一術語的使用都很慎重,以致出現為論證某個問題前,都需要而且必須重新界定市民社會才不致會引起歧義與誤解。甚至為了避免歧義而拋棄市民社會代之以“社會”概念的做法很受人歡迎。但是社會作為一個范疇其內涵與外延是遠遠大于市民社會的:社會的歷史長于國家,國家的存在與否并不影響社會的存在,而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具有天然的聯系,沒有政治國家的出現,市民社會的存在也就不會彰顯。此從意義上社會無法說明市民社會的特定內涵和特殊功能。在中國,正如法治、人權、民主、自由一樣,市民社會也是舶來品,甚至在特定意識形態的籠罩下,它們在政治道德上是處于被批判的,這些都造成了我們在理解“市民社會”過程中容易走向它的反面,其結果是市民社會成為證成政治國家合法性的理由,國家進一步吞噬社會壟斷權力,進一步成為Hobbes筆下的利維坦。
⑦霍新賓:《近代中國市民社會問題研究評述》,載《社會科學動態》,2000年第4期第35頁。
⑧Civil是先由希臘文衍變為拉丁文,再由拉丁文衍變為英語和法語,故而Civil有文明之意,在其古典意義上,又稱為“文明社會”,例如弗格森和盧梭都將Civil Society闡述為文明社會。
⑨參見蔣先福著:《契約文明:法治文明的源與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頁。
⑩參見[美]喬治·霍蘭·薩拜因著:《政治學說史》(下冊),劉山等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729頁。












(責任編輯:白 林)
2015-05-15
李文波(1979—),山東淄博人,碩士,講師,主要從事稅法理論研究。
D920.0
A
1008-5955(2015)02-00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