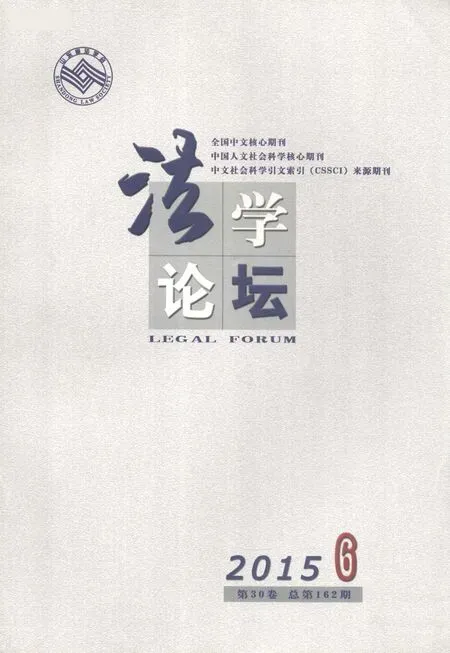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的銜接
——從《環境保護法》第60條切入
涂永前
(遼寧大學 法學院,遼寧沈陽 110136)
【熱點聚焦】
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的銜接
——從《環境保護法》第60條切入
涂永前
(遼寧大學 法學院,遼寧沈陽 110136)
2014年通過并頒布的新《環境保護法》被譽為“史上最嚴厲環保法”。其“最嚴厲”的特色從法理上看應當重點從其構建的環境法律責任制度層面去考察。該法第60條規定了行政相對人承擔的環境行政處罰的幾種形式,但這些具體形式在《環境行政處罰辦法》等既有的制度體系中被二分為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這在當前環境法律制度體系中有四種關系類型,存在著立法內涵界限模糊與適用混淆之處。我們應當在厘清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的內涵并確定其區分標準的基礎上,確立二者之間的銜接模式為環境行政命令作為適用環境行政處罰的前置程序,綜合發揮二者在當前環境保護中的不同價值與功效。
環境行政處罰;環境行政命令;混淆;銜接
一、問題的提出
2014年4月24日十二屆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以下簡稱新《環保法》)于2015年1月1日開始實施。新《環保法》正式通過頒布后,受到了社會各界廣泛贊譽,被譽為“史上最嚴厲環保法”,確立了最嚴厲的制度體系。*參見呂忠梅:《〈環境保護法〉的前世今生》,載《政法論叢》2014年第5期。此次修法因應“向污染宣戰”的當下訴求,新《環保法》的出臺則標志著中國的“治污之戰”從立法上取得了突破,它所建立的最為嚴厲的法律機制將為這場戰役奠定基石。*參見呂忠梅:《論生態文明建設的綜合決策法律機制》,載《中國法學》2014年第3期。然而,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史上最嚴厲環保法”的特色如何體現?新《環保法》出臺后,社會媒體連篇累牘地宣傳與解讀了其“最嚴格”特色,擇其要者,主要從強化政府監督管理責任、加大對違法行為的懲處力度、生態保護紅線入法、規定實行全民共治等制度創新層面進行闡釋。*參見汪鐵民:《最嚴格的法律尚需最嚴格的執行》,載《中國人大》2014年第9期。從法理角度論,法律的嚴厲程度應當體現在法律責任的規定上。沒有環境法律責任制度作保障,環境法律、法規設定的各種環境義務就如同“環境道德”的宣示,難以實現其調整社會關系的功能,更難以實現環境法的立法目的。*參見張梓太:《環境法律責任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43-44頁。
梳理新《環保法》對法律責任的規定,新增了很多環境法律責任的條文,包括第59條的按日連續計罰、第60條的停止危害、第63條的環境行政拘留處罰、第65條的環境中介機構法律責任的規定,等等。概覽新《環保法》第六章關于法律責任的11條規定,環境行政責任制度規范占有多數,這符合環境法制的特色,因為,“總體來說,利用環境政策目標設定的執行,一個重要的附屬及補充功能,非刑罰與秩序罰莫屬”,“在應用各種重要調查方法時,可以確定的是,環境保護的刑法上社會控制,是沒有效率的”。*鄭昆山:《環境刑法之基礎理論》,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69頁。行政機關相對于立法機關與司法機關的法律創設活動而言,在日常性、數量以及經驗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參見[美]杰里·馬肖:《貪婪、混沌和治理——利用公共選擇改良公法》,宋功德譯,畢紅海校,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68頁。環境法制的實施關鍵在于環境風險的規制,而環境風險的規制核心環節在于行政規制措施的效果。*參見劉超:《環境風險行政規制的斷裂與統合》,載《法學評論》2013年3期。因此,環境行政法律責任成為了各國在重視環境法律制度實施及其目標實現中非常重視的法律手段。法律的生命在于執行,對于長期飽受可執行性不強詬病的《環境保護法》尤其如此。“最嚴格”的法律預期實現其效果,需要最嚴格的執行。法律執行的前提是要對法律本身的正確理解和對其內在結構、制度選擇背景與邏輯關系的清晰把握。如上分析,從法理角度考察,新《環保法》作為“史上最嚴厲環保法”的特色應當集中體現在其法律責任的規定上,而基于當前環境法制的鮮明行政法特色,新《環保法》環境法律責任制度體系中大多數為環境行政法律責任。因此,有必要對新《環保法》中環境行政法律責任制度的體系、內容、結構及其內在關聯進行系統剖析。
本文并不預期對新《環保法》規定的環境法律責任制度進行系統解讀,而選取的角度和分析的重點是,在對新《環保法》第60條規定的制度結構及其與現行的相關規范之間的邏輯關系進行解析的基礎上,梳理與辨析環境行政處罰制度與環境行政命令之間的制度邏輯關系。在新《環保法》第60條的規定中,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超過污染物排放標準或者超過重點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指標排放污染物,要承擔的環境行政法律責任是被“責令采取限制生產、停產整治”或“責令停業、關閉”。在該條規定的制度邏輯中,二者都屬于行政相對人要承擔的環境行政處罰,只是二者在嚴厲程度上以及相應的有權實施主體上存在著差異,但其手段具有同質性。由此規定提出的問題是,在既有的以《環境行政處罰辦法》為代表的相關規范中,卻區分了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二者的具體形式多樣,與新《環保法》第60條的規定在形式和內涵上存在著交叉之處。由此,如何處理該矛盾或沖突?我們當然可以說《環境保護法》的法律位階更高,應當上位法優于下位法,但在現實法律運行中不能作如此簡單粗暴的處理,因為,其折射出的問題卻是來源于現實。因此,有必要在對相關規定進行法解釋學分析的基礎上,在以新《環保法》為統領的環境法制語境中,考察環境行政處罰制度與環境行政命令制度之間存在的區別、聯系與銜接機制。
、
二、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的立法界定與內涵混淆
目前我國環境法律規范大多數屬于環境行政法律規范,*參見蔡守秋主編:《環境資源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頁。這些法律規范努力追求行政法律制度的共性理論與環境保護領域特殊制度需求的互動與契合,形成了有鮮明部門法特色的環境行政法律制度。在當前社會普遍呼吁改變環保領域“守法成本過高,違法成本過低”,從而要完善環境法律責任的背景下,環境行政法律責任制度是關注的重點。其中,環境行政處罰制度既是日臻完善的制度體系,又與環境行政命令等其他制度類型相交叉,在實踐的制度適用中會引起制度混淆,我們可以對其內涵與混淆之處予以辨析。
(一)新《環保法》第60條規定之內涵與溯源
環境行政法律責任是環境行政法律關系的主體在違反環境行政法律規范或者不履行環境行政法律義務時應當承擔的不利法律后果。按照環境行政法律關系主體類型可將其分為環境行政主體的環境行政責任與環境行政相對人的環境行政責任。環境行政相對人承擔的環境行政法律責任包括補救性的法律責任和懲罰性的法律責任,補救性的行政責任包括消除危害、支付治理費用、恢復原狀、繳納排污費、賠償損失等,懲罰性的行政法律責任即為環境行政處罰。*參見呂忠梅:《環境法學(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151頁。新《環保法》第60條規定:“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超過污染物排放標準或者超過重點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指標排放污染物的,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可以責令其采取限制生產、停產整治等措施;情節嚴重的,報經有批準權的人民政府批準,責令停業、關閉。”新《環保法》第60條規定的是“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也即環境行政相對人承擔的環境行政法律責任。
在新《環保法》第60條規定的幾種環境行政處罰的形式中,“責令停業、關閉”是長期性、永久性的最為嚴厲的處罰,只能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決定批準。該處罰形式來源于《環境保護法》(1989年)第39條的規定,*《環境保護法》(1989年)第39條規定:“對經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務的企業事業單位,除依照國家規定加收超標準排污費外,可以根據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處以罰款,或者責令停業、關閉。前款規定的罰款由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決定。責令停業、關閉,由作出限期治理決定的人民政府決定;責令中央直接管轄的企業事業單位停業、關閉,須報國務院批準。”在其他的一些單行法中也有規定,*比如,《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第77、78條。《環境行政處罰辦法》(2010年)將其明確為環境行政處罰的一種形式,新《環保法》吸收了該立法經驗。“責令其采取限制生產、停產整治”是臨時性的、階段性的相對較輕的處罰,針對的是情節較輕的超過污染物排放標準或者超過重點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指標排放污染物的行為,只要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經過整頓,排污符合法律要求,經環保主管部門驗收合格的,可以恢復正常生產經營活動。其中,“責令停業整治”來源于《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第74條“責令停產整治”和第75條“責令停產整頓”的規定,*《水污染防治法》第74條第2款規定:“限期治理期間,由環境保護主管部門責令限制生產、限制排放或者停產整治。限期治理的期限最長不超過一年;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務的,報經有批準權的人民政府批準,責令關閉。”第75條第1、2款規定:“在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內設置排污口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責令限期拆除,處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逾期不拆除的,強制拆除,所需費用由違法者承擔,處五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罰款,并可以責令停產整頓。除前款規定外,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的規定設置排污口或者私設暗管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拆除,處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的罰款;逾期不拆除的,強制拆除,所需費用由違法者承擔,處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私設暗管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可以提請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責令停產整頓。”《環境行政處罰辦法》(2010年)第10條也將“責令停產整頓”明確規定為環境行政處罰的一種形式,新《環保法》第60條也對該規定予以吸收。
“責令限制生產”是新《環保法》新增的一種行政處罰形式,其早見于《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第74條第2款的規定:“限期治理期間,由環境保護主管部門責令限制生產、限制排放或者停產整治。限期治理的期限最長不超過一年;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務的,報經有批準權的人民政府批準,責令關閉。”同時,環境保護部2009年頒布的《限期治理管理辦法(試行)》第17條規定,“對被決定限期治理的排污單位,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還應當在《限期治理決定書》中告知以下事項:……限期治理期間排放水污染物超標或者超總量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可以直接責令限產限排或者停產整治……。”該規定“責令限產限排”也可以認為是對“責令限制生產”的直接規定。
然而,這里需要進一步探究的是,“責令其采取限制生產、停產整治”與“責令停業、關閉”是否僅有嚴厲程度與實施主體的區別?在新《環保法》第60條的規定中均為環境行政處罰的形式,這種立法現狀是新《環保法》對既有相關規定的沿襲、整合抑或創新?至少從形式上看,“責令限制生產”在新《環保法》之外的既有的相關規定中并不能完全歸入環境行政處罰范疇,但新《環保法》似乎并沒有對既有的環境行政命令這種行政手段予以同等重視,甚至是有意忽視。由此,需要進一步探討,在既有的環境行政法律規范體系中,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的規定的現狀及其關系范疇。
(二)《環境行政處罰辦法》對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之二分
環境保護部于2009年12月30日修訂通過《環境行政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該《辦法》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后,其立法理念、制度設計與執法效果受到廣泛贊譽。其規定的內容不但規范了環境行政處罰,而且兼顧到環境行政執法整個環節的多種執法形式。已有研究總結了新《辦法》的八大創新與亮點,其中之一是詳細列舉處罰種類、明確區分行政處罰與行政命令。*參見李錚:《〈環境行政處罰辦法〉的八大亮點》,載《環境保護》2010年第3期。
《辦法》第10條規定了處罰種類,第12條規定了責令改正形式,明確區分了“行政處罰”與“責令改正違法行為”并分別對二者種類與形式進行了具體列舉。如此規定因應了環境違法侵害一旦發生則難以逆轉的特殊性,所以從預防原則與罰教結合原則出發,既需要懲罰違法行為人,更要注重糾正違法行為、整治恢復環境。《辦法》第10條的規定具體列舉了環境行政處罰的7種形式,分別為:警告;罰款;責令停產整頓;責令停產、停業、關閉;暫扣、吊銷許可證或者其他具有許可性質的證件;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行政拘留。與此同時,《辦法》第12條的規定列舉了責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違法行為的8種主要形式,分別為:責令停止建設;責令停止試生產;責令停止生產或者使用;責令限期建設配套設施;責令重新安裝使用;責令限期拆除;責令停止違法行為;責令限期治理。其實,作為《行政處罰法》(2009年)的下位法的部門規章,《辦法》第10條規定的環境行政處罰種類的依據直接來源于《行政處罰法》第8條對行政處罰種類的規定,但《辦法》同時又吸收了環境保護單行法的規定,比如《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在第75條、78條等條文中對于“責令停產整頓”和“責令關閉”的法律責任的規定。
(三)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在適用中的混淆
雖然《辦法》從執法手段、形式和程序上對環境行政處罰作出了具體規定以增加其可操作性,但環境執法人員在執法中適用《辦法》時也存在諸多困惑。筆者近些年在參與一些研究環境司法和執法現狀調研項目時,收集了很多環境司法和環境執法的一手資料,通過與環境執法人員進行深入交流時,發現很多環境執法人員在表示《辦法》“好用”的同時,也認為在依據《辦法》進行執法時會因為制度界限的模糊而導致的執法形式與程序適用中的困惑。反映較為普遍的問題是在具體適用環境行政處罰制度和環境行政命令制度時存在的混淆。
雖然《辦法》分別對環境行政處罰的環境行政命令的種類形式進行了細致界定與明確區分,但環境執法人員在執法實踐中依然存在困惑。比如,《辦法》第12條規定的“責令停止生產或者使用”與第10條規定的“責令停產、停業”在現實執法中很難有清晰的界限。從法理邏輯和制度規定上看,《辦法》將“責令停止建設”和“責令停止生產或者使用”明確作為責令改正的具體形式之一而不是行政處罰,但現實執法過程中,如果責令一家企業“停止建設”或者是責令其主要生產設備“停止生產或者使用”,其實際效果與責令該企業停產、停業有何本質區別?基于執法部門在行使行政命令與行政處罰兩種行政行為時,在職權、程序等方面的差異,固然環保執法部門會遭遇上述的困惑,但也可能通過責令企業“停產建設”或“停產生產或者使用”的方式達到“責令停產、停業”的目的,也即是說以實施行政命令行為達致行政處罰的結果。
事實上,很多地方環保執法人員的確會利用當前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之間的混淆之處,當他們認為需要對某企業實施“責令停產、停業”的處罰時,他們有時會采取“責令停止建設”和“責令停止生產或者使用”的形式。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是:(1)二者職權主體不同。根據我國現行法律體系職權設置,在上述七種行政處罰種類中,環保部門可以行使四種:警告,罰款,暫扣、吊銷許可證或者其他具有許可性質的證件以及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但環保部門無行使“責令停產、停業、關閉”的職權,只能在立案調查的基礎上提出處罰建議報本級人民政府,由政府實施該項行政處罰。2014年新《環保法》第60條規定“……情節嚴重的,報經有批準權的人民政府批準,責令停業、關閉”,也即新《環保法》也進一步明確“責令停業、關閉”的職權只能由人民政府而非其環境保護主管部門行使。而“責令停止建設”和“責令停止生產或者使用”卻可以由環保部門實施。新《環保法》第60條也明確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可以責令其采取限制生產、停產整治等措施”。(2)二者的法律程序不同。根據《行政處罰法》(2009年)和《辦法》的規定,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前必須履行告知和聽證程序,但對于責令改正違法行為的實施,當前法律體系尚無明確的告知和聽證程序的規定,由執法部門自行決定是否需要進行告知和聽證,因此,“責令停止建設”和“責令停止生產或者使用”雖然可以實現“責令停產、停業”行政處罰的實際效果,但前者作為行政命令的程序需求遠沒有后者嚴格,環保部門在執法中當然會選擇前者以規避復雜的法律程序性規定。
三、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在環境法律體系中的關系類型
在新《環保法》構建的制度體系中并未明確區分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的制度語境下,將“責令限制生產”定性為環境行政處罰。但是,若將其納入《辦法》構建的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二分的制度系統中考察,則其性質存在模糊之處。這種現象的出現,折射出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在現實適用過程中存在著一些混淆或者說邊界的模糊。該現象之所以會出現,既因為在當前的環境行政法律制度體系中的相關立法存在著表達不周延之處,也受制于環境法律體系中行政處罰與行政命令的制度關系。
(一)環境行政命令立法之混亂與不周延
新《環保法》第60條規定的“責令限制生產”在《行政處罰法》、《環境行政處罰辦法》中均未有規定,追根溯源,它是首見于《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第74條,現被新《環保法》第60條吸納、作為一種環境行政處罰形式的規定。但是,新《環保法》第60條與《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第74條規定“責令限制生產”的制度語境卻存在差異。在新《環保法》第60條將“責令限制生產”作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在“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超過污染物排放標準或者超過重點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指標排放污染物”時,直接要求其承擔的不利法律后果,是對其實施的制裁行為,屬于典型的行政處罰的范疇。而在《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第74條第2款的規定中,“責令限制生產”是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對相對人在限期治理期間責令改正的具體形式之一,“(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務的,報經有批準權的人民政府批準,責令關閉。”《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的這種立法思路及其表達路徑,在《環境行政處罰辦法》(2010年)進一步具體化和明確化,即《辦法》第11條第1款規定的“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實施行政處罰時,應當及時作出責令當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違法行為的行政命令。”也即是說,“責令限制生產”在《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的制度語境中,應當屬于責令改正的一種具體形式,是一種行政命令,而《環境行政處罰辦法》(2010年)第12條明確規定“行政命令不屬行政處罰,行政命令不適用行政處罰程序的規定。”因此,從法律體系解釋和文本解釋的角度而言,新《環保法》第60條規定的“責令限制生產”在其他相關法律體系中屬于“環境行政命令”而不屬于環境行政處罰的具體形式,而新《環保法》第60條及其他條文并未將二者予以區分,而是將“責令限制生產”統一界定為環境行政處罰。現實中該如何界定?因為這涉及到該制度適用時的具體法律程序的選擇問題。
只是,《環境行政處罰辦法》(2010年)對環境行政命令的立法存在著表達形式混亂與不周延之處,這使得以“責令……”為立法表述的性質到底是責令改正(行政命令)抑或行政處罰難以區分。在《環境行政處罰辦法》(2010年)所區分的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的制度語境中,新《環保法》第60條規定的“責令限制生產”因為未有明確界定,從其性質、程度及相對人承擔的義務與承受的后果而言,更接近于《辦法》第12條列舉的責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違法行為的行政命令的具體形式而不是行政處罰。只是,因為《辦法》對責令改正(行政命令)的立法存在著疏漏,該規定只是單純的名稱列舉而并無概括責令改正的內涵,并未體現出責令改正所共有的獨特的形式特征,共性的缺乏是由被責令改正行為具體表現情狀的多樣性所決定,特性的不足是因為責令改正與明文納入環境行政處罰的某些“責令……”并無本質上的區別。*參見程雨燕:《試論責令改正環境違法行為之制度歸屬——兼評〈環境行政處罰辦法〉第12條》,載《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這種立法現狀導致現有立法中部分本質相同的責令改正行為因為表述上的些微差異而無法識別,也導致了以“責令……”為立法表述的內容的性質到底屬于環境行政命令抑或環境行政處罰會產生疑惑與爭議。
(二)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之間的關系類型
在當前的制度體系中剖析“責令限制生產”的性質所可能產生的爭議,還來源于從宏觀上看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之間的關系的界定。行政處罰是指特定的行政主體依法對違反行政管理秩序而尚未構成犯罪的行政相對人所給予的行政制裁,它具有行政性、具體性、處分性、不利性、法定性和制裁性等特性。*參見胡建淼:《行政法學(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290頁。行政處罰必須依法設定,根據我國《行政處罰法》(2009年),實施行政處罰的機關、種類、范圍和程序都必須依法設定。行政命令是指行政主體依法要求行政相對人為或不為一定行為的意思表示。它是行政主體作出的、適用特定程序的、對行政相對人設定義務性行為規則的意思表示行為。行政處罰與行政命令的區別可以概括為:(1)行政處罰的種類、程序等嚴格法定,要遵照《行政處罰法》(2009年)適用,而行政命令沒有具體的法律條文依據,適用一般行政法原理,由行政主體依據憲法或組織法所賦予的職權作出;(2)行政處罰的實施從對行政相對人在人身自由、財產、名譽或其他權益的限制或剝奪,具有強烈的制裁性與懲戒性,而行政命令主要是為行政相對人設置義務性行為規則,行政主體不能直接處分該義務。現實中,行政相對人違反行政命令以行政處罰為保障,行政主體可依法對其制裁或采取行政強制執行。*參見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214頁。
環境行政處罰的立法基于嚴格法定的要求,則其內容、形式和程序相對較為穩固,而當前尚無關系行政命令的專門立法,這使得環境法律體系關于環境命令的立法呈現出靈活性、多樣性以及普遍適用性等特征。梳理環境法律規范體系,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之間的關系可以概括為以下幾種:
1.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的選用與排他性關系。大部分環境法律法規在《行政處罰法》出臺后都不再將責令改正作為環境行政處罰的罰種,也即當行為人出現環境違法行為時,環境法律根據其行為的性質與程度分別規定行政處罰或者行政命令。這種關系典型體現在《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1996年)第53條根據違法情節嚴重分別適用的規定,“違反本法第十八條的規定,生產、銷售、進口禁止生產、銷售、進口的設備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經濟綜合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情節嚴重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經濟綜合主管部門提出意見,報請同級人民政府按照國務院規定的權限責令停業、關閉。”
2.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的種屬關系。即將責令改正明確列為環境行政處罰的罰種,這既包括于《行政處罰法》出臺前即已實施的情況,例如《違反礦產資源法規行政處罰辦法》(1994年)第8條:“對范圍礦產資源法規的行為的行政處罰包括:……(二)責令限期改正……。”也包括《行政處罰法》(1996年)出臺后仍然予以規定的情形,例如《安全生產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辦法》(2007年)第5條:“安全生產違法行為行政處罰種類包括責令改正、責令限期改正、責令停止違法行為、責令停產建設等。”*程雨燕:《環境行政處罰制度研究》,廣東省出版集團、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頁。
3.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并行適用。并用的情形又分為兩種,一種是可以并用一種是應當并用。前者如《固體廢棄物污染環境防治法》(2005年)第69條規定:“……由審批該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文件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生產或者使用,可以并處十萬元以下的罰款。”后者如《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第70條規定:“……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或者其他依照本法規定行使監督管理權的部門責令改正,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4.將環境行政命令作為環境行政處罰適用的前置條件。如《固體廢棄物污染環境防治法》(2005年)第70條規定:“……由執行現場檢查的部門責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者在檢查時弄虛作假的,處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的罰款。”《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第72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在上述分析的關系框架中去檢視《環境保護法》(修訂案)第60條的規定,則可以發現該規定存在的一些令人產生疑惑的矛盾:(1)從立法用語上看,該條使用的“責令停業、關閉”是《行政處罰法》(2009年)、《環境行政處罰辦法》(2010年)及其他環境保護單行法所明確列舉的環境行政處罰形式,這毋庸置疑;但如上分析該條使用的“責令限制生產”的性質該如何界定?若從《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對其使用來看,則定位為一種環境行政命令,屬于責令改正的一種具體形式,但是,從《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第75條的立法表述、制度語境與權力配置(“……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可以提請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責令停產整頓”)來看,則“責令停產整治”是一種行政處罰行使,而《環境行政處罰辦法》(2010年)在第10條也明確作出了同樣的制度性質界定。由此,新《環保法》在第60條將“責令限制生產”與“責令停產整治”相并,與該條中的“責令停產、停業”相對應?制度邏輯該如何理解?(2)如果將該條規定的“責令限制生產、停產整治”與“責令停業、關閉”均界定為環境行政處罰形式,則除了存在與既有大量環境保護單行法協調的問題,而且更為嚴重的問題是意味著《環境保護法》中舍棄了環境行政命令的手段適用。(3)如果將“責令限制生產、停產整治”界定為環境行政命令,對應于“責令停業、關閉”的環境行政處罰形式,則除了依然存在的與其他環境保護法律法規不協調問題之外,還直接提出了《環境行政處罰辦法》的修改的迫切要求,并且,《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第75條規定的“私設暗管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需要在“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可以提請”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責令停產整頓”的權限改為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行使,這也導致擴大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的職權范圍。(4)與前述第三點相關聯,若將新《環保法》第60條規定的“責令限制生產、停產整治”界定為環境行政命令,對應于“責令停業、關閉”的環境行政處罰形式,則意味著該條選擇了一種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之間的關系模式。梳理新《環保法》第60條的規定,從其“……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可以責令其采取限制生產、停產整治等措施;情節嚴重的,報經有批準權的人民政府批準,責令停業、關閉”的表述,對照上述梳理的現有法律體系中的四種關系模式可知,則新《環保法》第60條對于環境行政命令與環境行政處罰采取的是一種選用與排他性關系。而上述的關系模式的梳理僅為從實然的視角對現有關系類型的概括,本文下文的論述將從應然價值選擇視角剖析其中存在的問題以及我們應然的取舍。
四、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關系的厘清與銜接
現實執法中,環保部門適用《辦法》第10條規定的“責令停產、停業”與第12條規定的“責令停止生產或者使用”之所以存在混淆與困惑,是因為雖然適用二者執法效果差異不大,但“責令停產、停業”是一種環境行政處罰罰種,環保部門無此職權且程序要求嚴格(比如需要聽證等)。“責令停止生產或者使用”則是一種行政命令,環保部門有此職權且程序相對寬松。針對該問題,環境保護部針對福建省環境保護廳請求解釋的《關于環保部門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責令改正決定的復函》(環函[2010]214號)稱:“是‘責令停產’還是‘責令停止生產’,應當結合違法行為的性質和具體的法律法規規章條款選擇適用”。但該復函并未就二者的性質與相互關系進行清晰的界定與區分。因為作為部門規章,該《辦法》對于“責令停產”和“責令停止生產”為代表的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關系的處理,是對現有的法律體系的梳理和列舉,真實的關系界定還應當訴諸既有的環境法律、行政法規體系的界定。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從兩個向度確定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的關系,從而實現二者在適用中的協調一致。
(一)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的區分標準
基于當前環境法律體系之間出現的相互不協調甚至抵牾、沖突的頑疾,要清晰界定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應當追本溯源,從行政處罰與行政命令的本質屬性上界定二者區分標準。行政處罰是行政主體針對有違法行為的行政相對人的制裁,行政命令是行政主體為相對人設定義務性行為規則的意思表示行為,因此,應當從是否針對相對人的違法行為、是否是制裁行為以及是否是行政主體的意思表示行為這三個標準作為劃分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的標準。一般而言,行政處罰的內在屬性是以相對人違法行為的存在和具有制裁性為要件,而行政命令則不需要以相對人存在違法行為為前提,也不具有制裁性。同時,環境行政處罰一般是實力行政行為,即行政主體通過力的動作對行政相對人所作的一種行為,環境行政命令一般是意思行政行為,即指行政主體僅以意思力對行政相對人所作的一種行為。
“責令停產”與“責令停止生產”之所以出現混淆,就是因為現實中,行政處罰與行政命令的上述區分標準并不完全是界限分明的。比如,“限期治理”制度雖然是一種典型的行政命令,但卻以相對人存在違法行為為前提;再如,很多污染防治法有規定“責令限期拆除”并處罰款的情況,“責令限期拆除”應當屬于具有制裁性的行政命令。同時,雖然行政處罰一般是實力行政行為,但也有意思表示行為的情況,比如,《環境行政處罰辦法》(2010年)第10條規定的“責令停產整頓”和“責令停產、停業、關閉”的罰種,這種處罰是由相對人自己“停產整頓”或是“停產、停業、關閉”,而不是由行政主體采取措施實施的行為,因此,屬于是行政主體通過意思表示行為的行政處罰。正是因為《環境行政處罰辦法》第10條規定的“責令停產”與第12條規定的“責令停止生產”之間雖然分屬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但二者均為行政主體作為的意思表示行政行為,因此,存在著適用中的模糊與混淆。為了應對此問題,建議在立法梳理中將標準明確化和簡化:第一,以是否有制裁性為標準,只要行為的內容有制裁性就定性其為環境行政處罰,而不管其是否為意思表示行為,剔除具有制裁性環境行政命令的存在;第二,以是否表現為意思表示行為為標準,只要該行為表現為意思表示行為,就定性其為環境行政命令,而不管其內容上是否具有制裁性,剔除表現為意思表示行為的環境行政處罰的存在。*參見王志華:《行政命令與行政處罰關系之辨析與整合》,載《河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年第5期。
(二)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的價值分野
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是國家矯正環境違法行為、保護環境資源的兩類手段,如上所述,就環境行政相對人需要承擔的法律后果而言,環境行政處罰嚴厲于環境行政命令。但是,即使在當前社會各界普遍指斥環境法律體系可實施性不強、法律責任規定缺失導致“違法成本過低”的背景下,也不能在制度設計上傾向環境行政懲罰的規定壓制甚至是取代環境行政命令的情況,因為二者的價值選擇的分野導致二者承載的社會功能有差異。
環境違法行政相對人環境行政處罰是行政主體對環境違法但尚未構成環境犯罪行為的一種行政制裁,體現了國家對于社會主體在環境領域實施的某些違法行為的懲戒和非難,代表國家對這些行為的否定評價,帶有懲罰性質。環境行政處罰的后果體現為限制或剝奪人身自由、某種財產權或行為能力與資格,是僅次于環境刑罰的一種制裁。因此,合理設計和使用環境行政處罰制度不但可以制裁環境違法行為、實現國家環境保護和管理職能,還可以有效威懾、警示和阻嚇潛在的環境違法行為。環境行政命令是行政主體設定義務性行為的意思表示行為,它重在敦促違法行為人履行既有的法定義務,以實現糾正違法、恢復原狀和維持既定法律秩序的目標。我們應當矯正當前傾向于擴大環境行政處罰的形式和范疇、甚至將一些環境行政命令行為遮蔽而統一納入環境行政處罰行為的做法,因為,雖然表面上看,相對人基于環境行政命令所承受的法律后果的嚴重性要低于環境行政處罰,但是,環境行政命令相較于環境行政處罰也具有特定的優勢:第一,環境行政處罰表征了國家對于某些環境行政行為的價值非難性,行政處罰制度的實施背后隱含的價值判斷是該違法行為對于社會是一種毫無價值的應受責難的行為,但是當前的很多環境違法行為本身具有正當性,是人們對已知技術使用而產生的未知風險*參見張梓太:《環境法律責任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63頁。,此時,環境行政命令重視從行為本身的制止及其在價值選擇上的教育性與引導性更能為當事人接受,也更能體現制度設計與實施上的社會評價與引導意義;第二,環境違法行為普遍體現了累積性、潛伏性和難以逆轉性的特點,若適用環境行政處罰制度,基于其后果的嚴重性要有復雜的法律程序,而環境行政命令的便捷性更能及時制止當下發生的環境違法行為,這一優勢是向后預防、后果懲罰的環境行政處罰制度所不能具備的。基于二者具有不同的價值選擇與社會功能,應當在制度設計時慎重對待。
(三)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的銜接模式
如上分析,環境行政處罰制度與環境行政命令制度其在發揮制止環境違法行為、實現國家環境職能時有不同的價值選擇,承載了不同的社會功能,從而也會產生不同效果的行為導向,因此,在制度設計時不可偏廢,而應當重視二者功能的協同發揮。
如上所述,當前環境法律法規體系中,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存在著種屬、選用、并用和銜接使用四種模式。選用模式中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是排他性關系,其不足之處是只規定行政處罰雖然可能以其制裁性使相對人停止違法行為或不再為違法行為,但是會導致重處罰、輕監管的后果,不能實現“罰教結合”的原則。并用模式是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同時適用,但何種情況下可以并處或應當并處行政處罰的規定隨意性較大,沒有一個原則性的適用條件或區分標準,而且可以并罰的規定本身已經賦予了行政機關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容易造成對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參見王志華:《行政命令與行政處罰程序和諧關系之構建》,載《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在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的種屬關系中,將被定性為行政命令的責令改正列為環境行政處罰的罰種,這也是新《環保法》第60條的立法思路。將責令改正定位為一種環境行政處罰,這契合當前要加強環境行政法律責任、嚴懲環境違法行為的時代需求,但是,不加區分地將不同性質的環境規制手段統合為環境行政處罰,不但模糊了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的界限,也忽視了不同行政手段在環境保護領域的獨特價值與功效,還會限制環境行政處罰的效果。
因此,合理的選擇是采取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的銜接使用的模式。雖然《環境行政處罰辦法》將二者進行了明確區分,也在第11條規定“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實施行政處罰時,應當及時作出責令當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違法行為的行政命令。”但并未明確二者之間在適用程序上的具體銜接模式。因此,應當在整個環境法律體系中構建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的銜接模式是將環境行政命令作為適用環境行政處罰的前置程序。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這種前置程序既能保證環境執法輕重適度地因應可能導致環境影響與破壞的行為,又能促進執法部門的裁量權的規范行使,還可以針對環境執法領域的特殊需求。即應當明確,環境執法部門在實施環境行政處罰時,以責令改正作為前置性條件,當“責令改正期限屆滿,當事人未按要求改正,違法行為仍處于繼續或者連續狀態的”,再實施環境行政處罰。
五、結語
2014年的《環境保護法(修訂案)》第60條對相對人承擔的環境行政法律責任的規定更為嚴格,增設和創新了環境行政處罰的具體形式。從整個環境法律體系中考察,實際上將原來環境保護法律法規中規定的環境行政命令納入到環境行政處罰的罰種。這樣的立法思路雖然能夠嚴格環境法律責任,但忽視了不同性質的行政手段在實現環境保護中的不同價值與功效,也會導致環境法律制度體系的不協調,還會造成環保部門現實執法中的困惑。我們應當通過適用該辦法所折射出的問題完善當前環境執法制度體系,深入梳理和清晰區分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命令的界限標準,并構建二者之間合理的協調與銜接關系。
[責任編輯:王德福]
Subject:The Conne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enalty and Order: An Analysis from Art. 60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Author & unit:TU Yongqian(Law School,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 110136,China)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passed and issued in 2014, is called “the most severe environmental laws in the history”,whose feature should focu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environmental legal liability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risprudence. Art. 60 of the Law stipulates the some measures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for the administrative relative person to undertake, however these specific forms in Ordinance Concerning the Measures for the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and some other existing systems are divided into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enalty and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order, which are classified into four types of relationships 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legal system, and further there are many confusing connotations and areas among them. Therefore, what we shall do is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s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enalty and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commands and determine their differential standards,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linking mode between them is to be established as follows, i.e., taking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orders as the prior procedur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enalty, and thus exert their different values and effects comprehensively in the pres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order; confusion; connection
2015-09-15
涂永前(1974-),男,湖北武漢人,法學博士,遼寧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環境法學。
D912.112
A
1009-8003(2015)06-006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