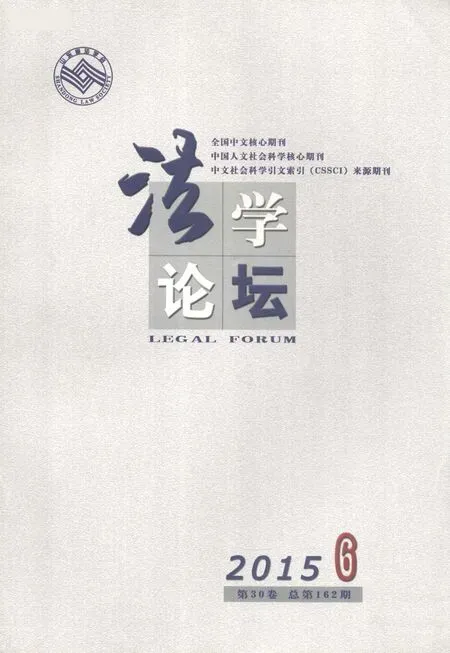“拾金獨(dú)(共)昧”法律問題之我見
張 龍
(中國政法大學(xué) 中歐法學(xué)院,北京 102249)
“拾金獨(dú)(共)昧”法律問題之我見
張 龍
(中國政法大學(xué) 中歐法學(xué)院,北京 102249)
拾金不昧是我國傳統(tǒng)道德風(fēng)尚,然而如今道德約束疲軟,物盡其用效率優(yōu)先的功利主義思想盛行,致使社會(huì)上“拾金獨(dú)(共)昧”拒不物歸原主的現(xiàn)象時(shí)有發(fā)生,往往給失主造成巨大財(cái)產(chǎn)損失。為避免“拾金獨(dú)昧”的不良之風(fēng)蔓延,重塑社會(huì)道德風(fēng)尚,需要通過法律的干預(yù)引導(dǎo)社會(huì)行為準(zhǔn)則。本文綜合運(yùn)用民法與刑法規(guī)范對不同情節(jié)的拾金獨(dú)昧行為進(jìn)行規(guī)制,以期行當(dāng)其罰、獎(jiǎng)懲并舉。
拾金獨(dú)(共)昧;侵占罪;敲詐勒索罪;拾得遺失物報(bào)酬請求權(quán)
“道有遺而不拾,拾而還其主亦無所求”,此謂之“拾金不昧”。中華民族素有以“拾金不昧”為道德風(fēng)尚之傳統(tǒng),早在南朝《列女傳·樂羊子妻》載道:“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柄,還以與妻。妻曰:‘竊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于野,而遠(yuǎn)尋師學(xué)。”*拾金不昧在中國古代特定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下有著獨(dú)立而深刻的制約機(jī)制,在“禮法合一”的社會(huì)制度下,這種行為不僅受道德的內(nèi)在約束,還受制于古代法的外在強(qiáng)制力。本文則期冀在現(xiàn)代法治框架下,尋找一種既能維護(hù)這種道德風(fēng)尚,又不僭越法律的做法。引用話語原文參見范曄:《后漢書·列女傳·樂羊子妻》,中華書局出版社1965年版,第378頁。拾金不昧不僅是個(gè)人道德節(jié)操的標(biāo)榜,而且亦為一國社會(huì)治理程度之體現(xiàn),自古即有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作為衡量盛世興旺之標(biāo)準(zhǔn)。然而,以德治大行其道的古典時(shí)代已然不無遺憾地遠(yuǎn)去,當(dāng)前世風(fēng)日下、道德滑坡的現(xiàn)象層出不窮,社會(huì)上拾金獨(dú)昧,以據(jù)為己有之故意拒不歸還失主的事件屢有發(fā)生。這些行為不僅損害了失主的合法權(quán)益,亦造成不良之社會(huì)影響,換言之,“拾金獨(dú)昧”行為絕非僅僅舉步于道德失范之范疇,而是延伸至觸及法律禁區(qū)之違法甚至犯罪行為。在法治社會(huì)下,如何運(yùn)用具有強(qiáng)制力的法律替代已然疲軟的道德約束力以規(guī)制該類行為,成為當(dāng)前法學(xué)界急需解決之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
案例一:案件當(dāng)事人武某某、陳某某、李某某、王某某,四人系北京市西客站W(wǎng)物業(yè)管理公司保潔員。其四人被安排在同一保潔小組,負(fù)責(zé)北京西客站北出口男衛(wèi)生間的清掃工作。2012年9月25日8時(shí)許,當(dāng)事人武某某在北京市西客站地下一層之廁所內(nèi)打掃時(shí),撿到一錢包,包里裝有65000元美金和兩部手機(jī)。武某某出于據(jù)為己有之心將錢帶回自住宿舍。后來此事被同組的李某某、陳某某與王某某得知,武某某為防止被人揭發(fā)、息事寧人,與其他三個(gè)知情人協(xié)商共分“拾來之金”。后來由于分贓不均使得陳某某得贓最少,陳由此心生怨恨,多次以報(bào)警相威脅從武某某處多索取了一萬美金,武某某最后在威脅的逼迫和良心的譴責(zé)下,無奈向警方自首,并控告陳某某涉嫌敲詐勒索罪。
案例二:2008年12月9日,深圳機(jī)場女保潔員梁麗在機(jī)場B號登機(jī)樓的19號登記口附近打掃衛(wèi)生時(shí),發(fā)現(xiàn)垃圾箱旁的行李車上有一個(gè)被遺棄的小型紙箱。據(jù)梁麗事后交代,此小紙箱系之前坐在垃圾桶旁的兩位女乘客所攜帶并置之于行李車上,后來兩女乘客登飛機(jī)而小紙箱卻依舊在行李車上。梁麗主觀認(rèn)為該紙箱系乘客丟棄之物,且當(dāng)時(shí)環(huán)視左右無人,遂隨手將紙箱放入清潔車作廢棄物處理。隨后梁麗將該紙箱存放于殘疾人廁所內(nèi),并囑咐同事此乃拾得之物,可能內(nèi)裝電瓶,若有失主前來認(rèn)領(lǐng)當(dāng)予以交還。至當(dāng)日下午下班時(shí),尚無人認(rèn)領(lǐng)此箱,梁麗遂攜之歸家。傍晚6時(shí)許,公安民警前來詢問,梁麗便主動(dòng)交出此箱。當(dāng)日梁麗即被刑事拘留,數(shù)日后被批捕。2009年3月,深圳市公安局以涉嫌盜竊罪為由,向深圳市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梁麗一案,檢察院以盜竊罪證據(jù)不足多次退回公安機(jī)關(guān)補(bǔ)充偵查。2009年9月,檢察機(jī)關(guān)以證據(jù)不足為由認(rèn)為梁麗不構(gòu)成盜竊罪,但其行為涉嫌侵占罪,因侵占罪是刑事自訴案件,基于刑事自訴“不告不理”之原則及受害人金龍珠寶公司明確表示不再起訴,梁麗被無罪開釋,重獲自由。
以上兩案例有著諸多共同性,如拾金者皆為公共場所保潔工人,都在保潔工作中拾得他人財(cái)物,拾財(cái)后皆有據(jù)為己有之主觀心態(tài)等。此類案件固然對規(guī)范公共場所遺失物管理制度上有警示與教育意義,但是筆者認(rèn)為,此類案件所產(chǎn)生的法律問題,更值得反思與研究。具體而言,諸上二則案例引發(fā)的法律問題有三點(diǎn):其一,如何界定“拾金獨(dú)(共)昧”行為在道德與法律領(lǐng)域上的邊界;其二,如何合理運(yùn)用刑法來規(guī)制嚴(yán)重之“拾金獨(dú)(共)昧”行為;其三,如何解決拾得遺失物報(bào)酬請求權(quán)的行權(quán)與犯罪關(guān)系。
二、“拾金獨(dú)昧”行為在道德與法律上的邊界
“拾金獨(dú)昧”行為并非純道德領(lǐng)域范疇,亦非純法律領(lǐng)域范疇,而是一種介于道德與法律之間的社會(huì)行為。筆者認(rèn)為,對“拾金獨(dú)昧”行為之性質(zhì)界定不可一概而論,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拾金者所拾財(cái)物的性質(zhì)作不同的區(qū)分。所拾之“金”抑或?yàn)樵腥朔艞壦袡?quán)的丟棄之物,抑或?yàn)樗腥艘蜃陨硎韬龆z忘或遺失之物,因所拾之“金”性質(zhì)不同,對拾金行為的評價(jià)亦不相同。
(一)拾得無主物的行為性質(zhì)
無主物系無人占有之物或原所有人放棄所有權(quán)而遺棄之物,從法律的角度來看,無主物之上是沒有所有權(quán)與其他用益物權(quán)的,因此拾得無主物的行為在法律上系先占。雖然我國當(dāng)前《民法通則》及《物權(quán)法》尚未對無主物及先占制度作出明確規(guī)定,但是在司法實(shí)踐和社會(huì)生活層面上已經(jīng)承認(rèn)“對無主物之先占取得所有權(quán)”系合法行為。*參見孟俊紅:《論無主物與遺失物的區(qū)別及無主物的推定》,載《河南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9年第6期。先占的原始取得制度最早可追溯至古羅馬法,古羅馬法學(xué)家蓋猶斯曾言:“不屬于任何人之物,根據(jù)自然理性歸先占者所有。”*[意]桑德羅·斯奇巴尼:《物與物權(quán)》,范懷俊譯,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頁。國外及我國臺(tái)灣地區(qū)的法律對無主物及先占已建立較為完善的體系,例如《德國民法典》第959條規(guī)定:“動(dòng)產(chǎn)所有權(quán)人出于放棄所有權(quán)的意圖而放棄其對物的占有時(shí),此動(dòng)產(chǎn)即為無主物。”而對于無主物的先占,德國法律直接認(rèn)可系所有權(quán)之原始取得。我國臺(tái)灣民法典沿襲德國法之精神,于第802條規(guī)定:“以所有之意思,占有無主之動(dòng)產(chǎn)者,取得其所有權(quán)。”除此之外,我國民法學(xué)者對無主物與先占制度亦有較為系統(tǒng)的理論闡述,即認(rèn)為對無主物之先占行為乃所有權(quán)之原始取得方式之一。*參見梁慧星:《中國物權(quán)法草案建議稿》,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378頁;另見史尚寬:《物權(quán)法論》,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頁。筆者贊同以上學(xué)者之觀點(diǎn)及相關(guān)立法實(shí)踐,對于先占自始無主之物及被原所有人拋棄所有權(quán)之物,法律沒有阻卻權(quán)利形成的必要,道德層面亦無可非議;對于當(dāng)事人基于真實(shí)意思所拋棄之物應(yīng)當(dāng)成為無主物,附著于該物之上的權(quán)利亦隨之消亡。民法誕生于市民社會(huì),其核心精神在于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當(dāng)事人主觀放棄某物之所有權(quán)乃民事權(quán)利行使之表現(xiàn),當(dāng)某物對所有人失去存在的價(jià)值時(shí),便需要通過拋棄以減輕權(quán)利負(fù)擔(dān)。倘若法律不承認(rèn)此種權(quán)利剝離,則會(huì)徒增原所有人之負(fù)擔(dān),外觀上看似保護(hù)權(quán)利實(shí)則苛加義務(wù)。因此,法律應(yīng)當(dāng)認(rèn)可拋棄物的無主物地位,無主物之先占亦不應(yīng)受民事法律阻卻,對于撿拾無主物之行為,自然也就不存在侵犯他人權(quán)利一說。
(二)拾得遺失物的民事責(zé)任
相比于無主物原始取得上之法律空白,我國民法對拾得遺失物的規(guī)范較為明確。但是何為遺失物,我國當(dāng)前的法律體系中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界定。有學(xué)者認(rèn)為:“遺失物,是所有人遺忘于某處,不為任何人占有的物。”還有學(xué)者認(rèn)為:“遺失物者,系指非基于占有人之意思而喪失占有,現(xiàn)又無人占有且非為無主之動(dòng)產(chǎn)。”*參見魏振瀛:《民法學(xué)》,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頁;謝在全:《民法物權(quán)法論》,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頁。雖然對遺失物定義的表述不同,但含義大體相致。概而言之,遺失物即為所有人遺忘于某處,非放棄占有意思之物。
我國民法上規(guī)定遺失物之所有權(quán)歸屬原所有人,他人撿拾遺失物不能當(dāng)然取得該物之所有權(quán)。例如,我國《民法通則》第79條第2款規(guī)定:“拾得遺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飼養(yǎng)動(dòng)物,應(yīng)當(dāng)歸還失主。”《物權(quán)法》第109條規(guī)定:“拾得遺失物,應(yīng)當(dāng)返還權(quán)利人。拾得人應(yīng)當(dāng)及時(shí)通知權(quán)利人領(lǐng)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關(guān)部門。”我國的此種立法顯然繼受了羅馬法上拾得者不取得所有權(quán)主義的立法例,*參見馬俊駒、余延滿:《民法原論》,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35-336頁。縱使終無覓尋原所有權(quán)人之可能,撿拾人亦不可當(dāng)然成為該物主人,而應(yīng)收歸國有。按照傳統(tǒng)的道德觀念,撿拾人在占有遺失物后負(fù)有妥善保管并物歸原主之道德義務(wù),但是為了規(guī)范社會(huì)行為,使拾金不昧這一傳統(tǒng)美德成為行為準(zhǔn)則風(fēng)向標(biāo),我國法律加強(qiáng)了對拾得遺失物這一法律事實(shí)的干預(yù),將此種保管返還義務(wù)上升為法律義務(wù)。《物權(quán)法》即為遺失物拾得人創(chuàng)設(shè)了三項(xiàng)應(yīng)承擔(dān)的法律義務(wù):其一,妥善保管義務(wù),拾得人在拾得遺失物后,應(yīng)盡一般之審慎注意以保護(hù)遺失物不受毀損、滅失之風(fēng)險(xiǎn);其二,及時(shí)通知義務(wù),拾得人對遺失物實(shí)施占有后應(yīng)當(dāng)盡一切之可能方法聯(lián)系失主,以使失主得以知曉相關(guān)事宜;其三,物歸原主義務(wù),此項(xiàng)義務(wù)乃道德義務(wù)之法律化,即拾得人在得知失主或應(yīng)當(dāng)?shù)弥е骱髴?yīng)盡善意之目的將遺失物返還于失主。然而,我國法律并未將規(guī)范僅停留于法律義務(wù)階段,對于那些企圖將遺失物據(jù)為己有而拒不返還的行為,法律還科加了相應(yīng)之責(zé)任承擔(dān)方式。根據(jù)《關(guān)于貫徹執(zhí)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94條之規(guī)定,“拾得人將拾得物據(jù)為己有,拒不返還而引起訴訟的,按侵權(quán)之訴處理”,司法實(shí)務(wù)中亦有按不當(dāng)?shù)美?zé)任處理的情形。*對此,學(xué)術(shù)界與司法界的意見頗有爭議。對于責(zé)任承擔(dān)形式主要有:不當(dāng)?shù)美f、侵權(quán)行為說、公平責(zé)任說和不當(dāng)?shù)美c侵權(quán)行為競合說,但是我國大多數(shù)學(xué)者支持侵權(quán)行為責(zé)任說,詳見王利明:《物權(quán)法論》,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226頁;曲桂玲:《試論拾得遺失物拒不返還的性質(zhì)》,載《北京人民警察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3年第1期。若情節(jié)嚴(yán)重構(gòu)成犯罪的,可以按刑法上之侵占罪論處。
綜上可知,拾得遺失物應(yīng)當(dāng)負(fù)有返還原物之義務(wù),這不僅是一項(xiàng)傳統(tǒng)之道德義務(wù),亦為一項(xiàng)法律義務(wù)。如果行為人以據(jù)為己有之心拒不歸還原物而強(qiáng)行占有,則可能會(huì)引起侵權(quán)甚至犯罪之法律責(zé)任。但筆者認(rèn)為,對于拾得遺失物法律責(zé)任之科處應(yīng)當(dāng)分情況而區(qū)別對待,對于那些可以找到失主或者失主通過懸賞廣告等媒介主動(dòng)覓尋之情形,法律應(yīng)當(dāng)保護(hù)失物與原主間的權(quán)屬關(guān)系,令那些拒不返還原物的拾得人承擔(dān)相應(yīng)的法律責(zé)任,其做法亦應(yīng)值得肯定和認(rèn)同;然而對于那些根本無法覓得失主的撿拾人,依然令其承擔(dān)相應(yīng)法律義務(wù),其做法值得商榷。筆者認(rèn)為,對后者情況,當(dāng)拾得人窮盡一切合理之手段依然無法覓尋原主或?qū)ふ沂е鞲緹o望時(shí),應(yīng)當(dāng)按無主物之做法處理,拾得人宜取得該物之所有權(quán)至少取得該物之用益物權(quán)。此種做法一方面可以實(shí)現(xiàn)物盡其用、避免資源浪費(fèi);另一方面可以與當(dāng)前國際通行的“拾得遺失物”制度接軌,平衡我國拾金不昧傳統(tǒng)法律化與國際通行做法之間的矛盾。*近代以來,關(guān)于拾得遺失物的制度規(guī)定,大多數(shù)國家和地區(qū)都繼受了日耳曼法“取得所有權(quán)主義”之立法例。我國部分學(xué)者亦主張日耳曼法立法例,詳見梁慧星:《中國物權(quán)法研究》(上),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21-522頁;郭明瑞:《民商法原理》,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第97-98頁。
(三)拾得遺失物之刑事責(zé)任
遺失物拾得制度僅僅創(chuàng)設(shè)民事法律義務(wù)和民事責(zé)任不足以有效定紛止?fàn)帯C穹ň科浔举|(zhì)實(shí)乃市民社會(huì)通行習(xí)慣之法典化結(jié)晶,包括我國在內(nèi)的世界各國,皆于民法中明令承認(rèn)法無明列之空白領(lǐng)域可憑一般習(xí)慣行之。但是,依習(xí)慣和公序良俗的做法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與爭議。拾得遺失物制度縱有物權(quán)法定之對世效力庇護(hù),然其終究系民事自治范疇,其強(qiáng)制力甚為有限,誠可謂“徒民法無以自行”。由于民事訴訟有限的約束力難以恢復(fù)受害人的利益,對于那些拾得他人遺失財(cái)物拒不歸還,且數(shù)額巨大的情形,即使通過侵權(quán)之訴予以維權(quán),亦不足以威懾并防范該類行為之繼發(fā)。因此為了規(guī)制嚴(yán)重的“拾金獨(dú)昧”行為,有必要?jiǎng)佑眯谭ㄟM(jìn)行規(guī)制(對于難以找到失主的遺失物情形不在本文討論之列)。鑒于單純依靠民事責(zé)任維護(hù)遺失物之合法權(quán)屬關(guān)系的局限,我國《刑法》第270條規(guī)定了對情節(jié)嚴(yán)重的“拾金獨(dú)昧”行為的刑事制裁,即將他人的遺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拒為己有,數(shù)額較大,拒不交出的,以侵占罪論處。筆者認(rèn)為,將情節(jié)嚴(yán)重的“拾金獨(dú)昧”行為規(guī)定為“侵占罪”有獨(dú)具匠心的用意,在司法實(shí)務(wù)中的優(yōu)勢有三:其一,威懾作用。侵占罪在刑法中系自訴型犯罪,刑事訴訟啟動(dòng)的主動(dòng)權(quán)在被害人和其家屬手中,故拾金獨(dú)昧的刑事責(zé)任可以作為威懾“獨(dú)昧”人的手段,這種威懾效果既可以是抽象的亦可以在具體案件中變成具體威懾;其二,構(gòu)建了一條連接刑事責(zé)任與民事責(zé)任的橋梁。本罪在設(shè)計(jì)上既安排了民事意思自治——當(dāng)事人自決協(xié)商的空間,又注入了刑事強(qiáng)制力和制裁力,體現(xiàn)了國家對維護(hù)私權(quán)的力度,有助于有效打擊拾金獨(dú)昧行為;其三,僅把情節(jié)嚴(yán)重的“拾金獨(dú)昧”行為列入刑事打擊的范疇,符合刑法“謙抑性”、“最后手段性”精神,避免公法過分干預(yù)市民社會(huì)私法領(lǐng)域生活。
2)通過粒度變量Gv對矩陣Nm進(jìn)行劃分,將融合后的數(shù)據(jù)劃分為一個(gè)個(gè)樣本簇C={avg1, avg2,…, avgi},其中avgi表示樣本簇中的數(shù)據(jù)點(diǎn)均值.
三、如何運(yùn)用刑法來規(guī)范“拾金獨(dú)(共)昧”行為
(一)真“拾金共昧”:一人拾金,多人共分
“拾金共昧”涉及到刑法學(xué)的共同犯罪問題,典型情形即為一人撿拾到數(shù)額較大之財(cái)物之后與他人共同分贓,各分贓人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拒不歸還。對于發(fā)現(xiàn)遺失物并拾得繼而據(jù)為己有且拒不歸還者,以當(dāng)前《刑法》第270條之規(guī)定認(rèn)定構(gòu)成“侵占罪”,自無異議。但是根據(jù)分贓所基于之目的與各分贓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各分贓人以何罪定罪處罰亦有所不同,依據(jù)不同之情勢主要有如下兩種區(qū)分:
1. 分贓人協(xié)助撿拾遺失物,共同分成。此種情況一般適用于一人發(fā)現(xiàn)遺失物,然后多人協(xié)助共同將其帶離原遺失地點(diǎn)的情況。為了更形象說明此種情形,筆者將上文案例二稍作改編:若某機(jī)場保潔工人A在一次清掃中發(fā)現(xiàn)機(jī)場行李車上放置一大箱子,A環(huán)望四周見四下無人即自認(rèn)為此為他人遺棄或丟失之物,便將此箱推到清潔室,后來發(fā)現(xiàn)該箱所裝皆為24K純度金條,此時(shí)A便心生據(jù)為己有之心,但由于箱子沉重自己難以通過掩人耳目之形式搬離,便伙同機(jī)場另外三名保潔員B、C、D共同將其搬走并約定四人各分一部分。事后得知此箱黃金乃珠寶商甲某遺失之物,在甲某得知A、B、C、D四人撿拾并前來索回之時(shí),四人謊稱不知情并拒不歸還。
筆者認(rèn)為,本案中A、B、C、D四人均構(gòu)成侵占罪。A構(gòu)成侵占罪的主犯,而B、C、D構(gòu)成侵占罪的幫助犯。其中對于B、C、D的罪責(zé)認(rèn)定上有兩可之難,換言之,究竟構(gòu)成“侵占罪”共犯,抑或構(gòu)成《刑法》第312條之“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在罪責(zé)認(rèn)定上存在模糊。筆者認(rèn)為對于此案之問題,可以通過對侵占罪的條文解讀予以解決。構(gòu)成侵占罪須同時(shí)滿足三個(gè)條件:第一,行為人有占有遺失物之事實(shí);其二,主觀上有非法據(jù)為己有之心;其三,客觀上表現(xiàn)為拒不返還。而認(rèn)定B、C、D三人之行為到底構(gòu)成何罪的關(guān)鍵在于“A是否完成了侵占罪的全部構(gòu)成要件”,換言之,如果A已經(jīng)實(shí)施完畢侵占罪而后與另外三人共分遺失物,則另外三人構(gòu)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如果A在分割所拾遺失物時(shí)尚未完成侵占罪之構(gòu)成要件,而是通過另三人之協(xié)助而共同完成對遺失物的侵占,則四人都應(yīng)當(dāng)以侵占罪論處。本案中之所以認(rèn)定B、C、D三人均構(gòu)成侵占罪,是因?yàn)锽、C、D的協(xié)助行為使得A得以完成侵占罪犯罪行為,因此B、C、D三人促成了侵占罪的成立,有刑法上之因果關(guān)系,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構(gòu)成侵占罪之共犯。
2. 拾得人為息事寧人而分贓,分贓人協(xié)助隱瞞實(shí)情、拒不歸還。此種情形主要是指,一人拾得遺失物并完成侵占之后,為使其他知情人不控告揭發(fā)自己,而分割一部分拾得之財(cái)物給予知情人以求息事寧人,知情人分得財(cái)物后亦答應(yīng)不滋生此事。本文的案例一即為此情形之典型。案例一中的武某某系個(gè)人發(fā)現(xiàn)該遺失錢包,而后以據(jù)為己有之心將此錢包帶回自己所住宿舍并將其藏起來。武某某的行為到此階段已經(jīng)完成刑法上侵占罪所需要的全部構(gòu)成要件,認(rèn)定武某某構(gòu)成侵占罪毫無異議。但之后王某某、李某某與陳某某幫助武某某隱瞞事實(shí)、掩人耳目而分得部分拾得物的行為,已經(jīng)超出了侵占罪的范圍。筆者認(rèn)為,王某某、李某某與陳某某三人明知武某某拾得之巨額美金系非法占有之遺失物而仍以非法占有之心收受并幫助隱瞞,其行為應(yīng)認(rèn)定為我國《刑法》第312條“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從外觀上看,此三人所實(shí)施的行為似乎同時(shí)構(gòu)成侵占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由于該二罪所保護(hù)的法益不存在包涵或交叉關(guān)系,因此根據(jù)我國法學(xué)界通行理論應(yīng)認(rèn)定想象競合犯情形。對于想象競合犯的處理上理論界認(rèn)為應(yīng)按行為所觸犯的罪名中擇一重罪論處,*參見張明楷:《刑法學(xué)》(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37頁。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處罰重于侵占罪,故以前者論處為宜。除此之外,筆者認(rèn)為本案按“構(gòu)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處罰還有兩大理由:其一,本案陳某某、李某某和王某某三人在主觀上構(gòu)成要件上已經(jīng)超越侵占罪的范圍。即三人明知該美元系武某某侵占所得贓款而依然收受并幫助武某某一起隱瞞事實(shí),其犯罪構(gòu)成已經(jīng)超出了侵占罪;其二,該三人的主觀惡性明顯高于侵占罪,明知所得財(cái)物系他人非法獲取而依然接受并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且拒不歸還失主,社會(huì)危害性更大,若以自訴型的“侵占罪”處理,有違罪行相適應(yīng)原則。綜上,對劉某某、陳某某、李某某之行為應(yīng)認(rèn)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在拾金共昧的情況下,有一種“假共昧”情形,即一人撿拾遺失物,而另一知情人以揭發(fā)為要挾,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向撿拾人索取錢財(cái),拾金人因內(nèi)心恐懼而被迫處分財(cái)產(chǎn)。對于“假共昧”的情形,不要求遺失物拾得人以構(gòu)成“侵占罪”為前提,即對拾得人所拾得之財(cái)物的多少?zèng)]有數(shù)額上的限制。“假共昧”情形討論的重點(diǎn)是如何對實(shí)施要挾行為的“共昧人”進(jìn)行責(zé)任認(rèn)定。筆者認(rèn)為,對于“假共昧”的要挾人應(yīng)當(dāng)以“敲詐勒索罪”處理。但是根據(jù)索要的具體數(shù)額與情節(jié)輕重的不同,有兩種不同之區(qū)分:其一,認(rèn)定構(gòu)成“敲詐勒索罪”的情形。根據(jù)我國《刑法》的規(guī)定,敲詐勒索罪所侵犯的法益為財(cái)產(chǎn)權(quán),在入刑標(biāo)準(zhǔn)上有數(shù)額和次數(shù)的要求,須有勒索財(cái)物數(shù)額較大或多次勒索的情節(jié)時(shí),方構(gòu)成本罪。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敲詐勒索罪數(shù)額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問題的規(guī)定》,“數(shù)額較大”以1000-3000元為起點(diǎn);“多次敲詐勒索”應(yīng)為三次以上,且每次敲詐行為不必獨(dú)立構(gòu)成本罪,即使多次敲詐之累計(jì)數(shù)額未達(dá)至數(shù)額較大標(biāo)準(zhǔn),亦可成立本罪。在案例一中,陳某某因分贓不均,多次以報(bào)警舉報(bào)相威脅,向拾得人武某某索取到一萬美金,其行為符合敲詐勒索罪的構(gòu)成要件,在對陳某某的最終處理上,筆者認(rèn)為應(yīng)以“敲詐勒索罪”與“掩飾、隱瞞非法所得罪”對其予以并罰;其二,可以認(rèn)定構(gòu)成“敲詐勒索罪”未遂的情形。對于敲詐勒索數(shù)額較小,且未行多次敲詐之舉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情節(jié)嚴(yán)重,可以敲詐勒索的未遂犯論處。如果行為人僅實(shí)施一次敲詐行為,且索得金額不足1000元,但是其敲詐要挾的手段頗為惡劣致使受害人陷入心理恐慌、影響正常工作生活,對該行為人應(yīng)當(dāng)以敲詐勒索罪的未遂犯論處。
(三)拾得違禁物而據(jù)為己有
本文所討論的“違禁品”是指有害于公共安全與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管理秩序,國家限制或禁止自由流通,且《刑法》明令禁止私人持有之物,例如,槍支彈藥、毒品和偽造的發(fā)票等。對于未經(jīng)有關(guān)部門許可而私自持有此類違禁物的,《刑法》單獨(dú)設(shè)定罪名予以規(guī)制,而持有人實(shí)際使用或買賣與否在所不問。*例如,我國《刑法》第210條規(guī)定了“持有偽造的發(fā)票罪”,第128條規(guī)定了“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第348條規(guī)定了“非法持有毒品罪”。筆者認(rèn)為,“拾金獨(dú)昧”行為所拾得之遺失物不應(yīng)僅囿于一般正常流通之財(cái)貨,亦應(yīng)包括國家限制或禁止流通的違禁物品。但是撿拾數(shù)額較大的上述違禁物據(jù)為己有而拒不歸還的,不僅構(gòu)成侵占罪,而且還可能構(gòu)成刑法其他罪名。筆者以拾得槍支彈藥為例,假設(shè)甲某平時(shí)是一名軍事愛好者,一日于歸家途中偶然拾得一把名貴的新式軍用手槍,甲見其做工精良,遂企圖將此拾得之槍據(jù)為己有,并將其存放于家中自留收藏。筆者認(rèn)為,在此種情形下,甲的行為觸犯了刑法上兩個(gè)罪名,即“侵占罪”與“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在最終處理上應(yīng)當(dāng)以該二罪數(shù)罪并罰。之所以如是規(guī)定,一方面是因?yàn)榍终甲锱c持有違禁物品犯罪所侵害的法益不同,一個(gè)系侵犯財(cái)產(chǎn)權(quán),另一個(gè)系侵害公共安全;另一方面,在通常情況下兩罪不具有前因后果的接續(xù)關(guān)系,因?yàn)閷τ谶`禁物的撿拾一般都是基于偶然因素,即先前占有行為并非為事后的非法持有行為預(yù)謀階段,而事后的非法持有行為亦非為事先占有行為在邏輯上的必然發(fā)展結(jié)果。以此種邏輯類推,對于撿拾毒品或數(shù)額巨大的偽造發(fā)票,據(jù)為己有而拒不歸還或上繳,按照《刑法》總則之理論,應(yīng)對行為人以侵占罪與具體的持有違禁品罪并罰論處。
四、行權(quán)與違法——遺失物報(bào)酬請求權(quán)之討論
“拾金不昧”雖是值得傳頌的美德,但是畢竟囿于道德范疇,對于社會(huì)大眾沒有強(qiáng)制約束力,為了揚(yáng)傳善舉,有必要從法律層面對拾金不昧者予以一定激勵(lì)政策以鼓勵(lì)此類善舉形成社會(huì)風(fēng)尚。我國《物權(quán)法》雖未將報(bào)酬請求權(quán)作為“拾金人”交還遺失物時(shí)的一項(xiàng)法定權(quán)利,但為了規(guī)范此類行為的社會(huì)價(jià)值導(dǎo)向,在拾得遺失物制度中承認(rèn)當(dāng)事人可通過意思自治來約定“報(bào)酬請求權(quán)”,實(shí)為一種立法之進(jìn)步,其積極意義不言自明。然對此項(xiàng)制度的安排,部分學(xué)者頗有微詞,反對之聲亦不絕于耳。關(guān)于此制度安排是非優(yōu)劣的比較,學(xué)界理論早已浩如煙海,在此不予贅述,筆者僅就此制度在運(yùn)行中所可能產(chǎn)生的涉及“拾金獨(dú)昧”之問題,抒發(fā)己見。
(一)報(bào)酬請求權(quán)制度的價(jià)值考量
之所以有學(xué)者詬病遺失物報(bào)酬請求權(quán)制度,源于將拾金不昧視為純道德領(lǐng)域問題,但是筆者認(rèn)為拾金不昧不僅是道德問題亦是法律問題。縱使《物權(quán)法》頒布之前,《民法通則》就已經(jīng)將拾得遺失物物歸原主作為一項(xiàng)法律義務(wù)予以規(guī)范。但是單純的民事義務(wù)太過于單薄,而啟動(dòng)刑事責(zé)任司法成本又太高。因此介于兩種極端的困境,《物權(quán)法》應(yīng)當(dāng)順?biāo)浦郏瑯?gòu)建出一種相對柔性的制度來解決“拾金獨(dú)昧”問題,以求達(dá)到拾金者與失金者間的利益雙贏。
對拾金不昧者給予一定激勵(lì)措施最早是由著名心理學(xué)家索斯蓋特提出。他通過研究提出,許多人在撿到錢包時(shí)不由自主地都會(huì)看看錢包里裝些什么,這就說明,這些人的潛意識里有邪惡的占有欲。如果對拾金不昧者進(jìn)行物質(zhì)和精神的獎(jiǎng)勵(lì),讓拾金不昧者獲得的精神愉悅增加,就會(huì)鼓勵(lì)更多的人從善。*參見一哲:《德國人的獎(jiǎng)與罰》,載《領(lǐng)導(dǎo)萃文》2009年第5期。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逐漸接受這一理論,在法律中明文規(guī)定遺失物報(bào)酬請求權(quán)制度。*例如,《德國民法典》第971條規(guī)定:“拾得物的價(jià)值在一千馬克以下者,其報(bào)酬為百分之五,超過此數(shù)部分,價(jià)值百分之三;關(guān)于動(dòng)物為價(jià)值的百分之三”。《日本遺失物法》第4條規(guī)定:“受物件返還者,應(yīng)將不少于物件價(jià)格百分之五,不多于物件價(jià)格百分之二十的酬勞金給予拾得人。”我國臺(tái)灣地區(qū)《民法》第805條規(guī)定:“有受領(lǐng)權(quán)之人認(rèn)領(lǐng)遺失物時(shí),拾得人得請求報(bào)酬。但不得超過其物財(cái)產(chǎn)上價(jià)值十分之三;其不具有財(cái)產(chǎn)上價(jià)值者,拾得人亦得請求相當(dāng)之報(bào)酬”。我國亦早在古代西周時(shí)期,即有對拾得遺失物報(bào)酬權(quán)的記載,例如“馬牛其風(fēng),臣妾捕逃,無敢越逐,詆復(fù)之,我商賚汝”,*原文詳見魯侯伯禽:《尚書·費(fèi)誓》,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86頁。即拾得他人牛馬等遺失財(cái)物,可得到失主之報(bào)酬。民國時(shí)期法學(xué)家史尚寬先生認(rèn)為:“拾得人報(bào)酬,不獨(dú)為辛勞報(bào)酬,而且為榮譽(yù)賞金。”報(bào)酬,是指對拾得人付出勞動(dòng)的補(bǔ)償,而“榮譽(yù)賞金”的提法則明確體現(xiàn)了對拾得人行為的肯定性評價(jià),體現(xiàn)了鼓勵(lì)人們?nèi)ナ叭∵z失物并設(shè)法歸還失主的意圖,拾得人報(bào)酬請求權(quán)因而起到了鼓勵(lì)人們從善的教化作用。我國《物權(quán)法》(草案)中,曾規(guī)定了拾得遺失物之人可獲得3%-20%之報(bào)酬,但考慮到由此可能帶來的對我國道德體系的負(fù)面沖擊,最后這一良善制度沒能成為物權(quán)法定之權(quán)利,而歸為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范疇。*我國部分民法學(xué)者對法定報(bào)酬請求權(quán)一直持肯定態(tài)度,并在相關(guān)著作與立法建議中予以明示。具體可參見王利明等:《中國物權(quán)法草案建議稿》之第88條(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0年版);梁慧星等:《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之第368條(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筆者認(rèn)為此種做法有待商榷。在法律上承認(rèn)報(bào)酬請求權(quán)制度,使其成為一項(xiàng)法定的權(quán)利,不僅可以激勵(lì)拾金人積極追還失主,而且可以催化良好的道德風(fēng)尚。道德規(guī)范必須通過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才能發(fā)揮其良善的效果,人有趨利避害的本性,只有將制裁與獎(jiǎng)勵(lì)相結(jié)合,才可以有效避免拾金獨(dú)昧現(xiàn)象的蔓延。因此肯定拾得人的報(bào)酬請求權(quán)不僅不違背社會(huì)主義精神文明,反倒能夠更好地促進(jìn)精神文明的建設(shè)。*參見王陳平等:《關(guān)于遺失物拾得制度的思考》,載《法制與社會(huì)》2010年第7期。
(二)行權(quán)與犯罪的界限
雖然我國尚未將遺失物報(bào)酬請求權(quán)上升為法定權(quán)利,但是拾金人可以通過失主所發(fā)布的懸賞廣告等意思自治形式,獲得約定之報(bào)酬請求權(quán),我國《物權(quán)法》亦對此種權(quán)利之取得給予承認(rèn)。但是實(shí)踐中,此種報(bào)酬請求權(quán)的行使時(shí)有糾紛產(chǎn)生,對失主與良善之拾金人之間造成莫大困擾。
通常情況下,失主為了及時(shí)覓回遺失物,會(huì)通過懸賞廣告之形式以一定物資回報(bào)來鼓勵(lì)拾得人交還遺失物。對懸賞廣告之性質(zhì)目前學(xué)術(shù)界尚有爭議,筆者認(rèn)為,從整個(gè)民法學(xué)之自治體系觀之,將懸賞廣告認(rèn)定為單方行為說更為合宜,即失主一旦發(fā)出懸賞廣告,懸賞合同即告成立,此時(shí)失主負(fù)有給付拾金人所約定的報(bào)酬數(shù)義務(wù),而拾得人享有獲取報(bào)酬之權(quán)利。但這并不意味著權(quán)利的行使不受任何制約和限制。在一個(gè)法治社會(huì),權(quán)利的行使不僅要具備目的正當(dāng)性,而且還應(yīng)具備手段合法性。借私力救濟(jì)之方式進(jìn)行索債或者索賠行為,亦應(yīng)受到制約。針對拾得人對報(bào)酬利益的索取,應(yīng)區(qū)分三種情況予以不同對待:其一,如果拾得人在交還遺失物過程中,為了索要約定數(shù)額之報(bào)酬請求權(quán)與失主發(fā)生爭議,若拾金人通過訴訟等合法手段維權(quán),此乃基于合同約定內(nèi)容行使正當(dāng)之權(quán)利,法律上應(yīng)當(dāng)予以支持,對此種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導(dǎo)案例《李珉訴朱晉華、李紹華懸賞廣告酬金糾紛上訴案》中做出了肯定態(tài)度;其二,拾得人因未獲得懸賞約定之報(bào)酬,留置部分或全部拾得物,待失主履行報(bào)酬后歸還。雖然我國有學(xué)者主張拾得人在報(bào)酬請求權(quán)未獲實(shí)現(xiàn)前得留置拾得物,*參見馬俊駒、余延滿:《民法原論》,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37頁。但我國《物權(quán)法》和其他法律并未明確予以認(rèn)可,況且返還拾得物于原主乃法定義務(wù),故此種權(quán)利之行使方式實(shí)為不妥。鑒于拾得人留置之意圖僅為取得報(bào)酬權(quán),而非為據(jù)為己有,故在處理上不應(yīng)以侵權(quán)或刑事侵占相論,應(yīng)認(rèn)定構(gòu)成不當(dāng)?shù)美袚?dān)不當(dāng)?shù)美颠€義務(wù);其三,若拾得人未獲得或未完全獲得報(bào)酬請求權(quán),拒不返還失物并以用該物充抵或毀壞該物為威脅,使失主陷于內(nèi)心恐慌且數(shù)額較大,筆者認(rèn)為,此種情形下,拾得人涉嫌構(gòu)成敲詐勒索罪。如果拾得人是通過威脅恐嚇之手段,迫使權(quán)利人在不得已的無奈下交付報(bào)酬請求權(quán),即使報(bào)酬數(shù)額在懸賞廣告約定的范圍內(nèi),拾得人也構(gòu)成敲詐勒索罪。*在英國法律中亦有類似的法律規(guī)定,例如,“如果一個(gè)人脅迫他人支付依合同所發(fā)生之金錢債務(wù),即使債務(wù)是客觀存在的,但如果騷擾行為性質(zhì)嚴(yán)重,則可能被按簡易程序治罪,處以罰金。”參見[英]戴維·歐蒙德:《史密斯與哈根刑法學(xué)》,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627-629頁。因?yàn)椋环矫媸暗萌诵惺箼?quán)力的手段超出了必要性與合法性,另一方面,此時(shí)失主對財(cái)物的處分乃基于心理上的恐懼,侵害了失主對自己財(cái)物的占有、使用、處分這一本權(quán)事實(shí)上的機(jī)能,實(shí)際上是侵犯了失主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因此,應(yīng)以“敲詐勒索罪”論處,如果數(shù)額較小可以本罪未遂論處。
對于以上第二、第三種情形的處理,筆者建議拾得人首先應(yīng)當(dāng)返還失物,畢竟遺失物的返還義務(wù)乃法定之義務(wù),無可爭議;其次對于不履行懸賞義務(wù)的失主,當(dāng)事人可憑懸賞廣告所產(chǎn)生之債權(quán),向法院主張權(quán)利,以合法的手段解決避免陷入做好事反而被處罰的尷尬境地。
拾金不昧、路不拾遺雖自古被奉為社會(huì)道德至上標(biāo)榜與治世典范,然時(shí)過境遷,上古民風(fēng)不再,道德之內(nèi)省亦失其信仰,加之缺乏外在強(qiáng)制性而難以有效規(guī)范社會(huì)行為,故需要通過法律規(guī)范來規(guī)制拾金獨(dú)昧行為。即對于拾金不昧者給予一定物質(zhì)激勵(lì),在法律中承認(rèn)其報(bào)酬請求權(quán);對于輕微拾金獨(dú)昧者科以民事責(zé)任;對于情節(jié)嚴(yán)重的拾金獨(dú)昧者,應(yīng)科處刑事處罰。人無常心,習(xí)以成性;國無常俗,教則移風(fēng),唯獎(jiǎng)懲并舉以法導(dǎo)民方能有效避免“拾金獨(dú)昧”之風(fēng)蔓延。長此以往可使外在約束成為內(nèi)心遵守,內(nèi)心遵守漸而轉(zhuǎn)為民眾的社會(huì)意識,當(dāng)法律使人們確立“拾金不昧”的正確價(jià)值導(dǎo)向時(shí),此問題亦迎刃而解。
[責(zé)任編輯:譚 靜]
Subject:My Personal Perspective on the Legal Problem of “Pocketing the Money One Picks Up”
Author & unit:ZHANG Long (China-Europe School of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2249, China)
“Not to pocket the money one picks up”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orality, however, with the weak moral constraint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best use of theory prevalent in society, the phenomenon that pocketing the money one picks up often occurs, which has caused substantial damage to the owner of property. In order to prevent its negative effect, and to reshape social morality, we need to guide social conduct through legal intervention. However, how to use the civil and criminal rules to regulate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about the behavior of “pocketing the money one picks up”, is the discussion focus of this thesis.
pocketing the money one picks up; crime of embezzlement; crime of extortion; Lost property claim
2015-10-06
張龍(1988-),男,遼寧大連人,中國政法大學(xué)中歐法學(xué)院博士候選人,研究方向:刑法、歐盟法。
D924.3
A
1009-8003(2015)06-009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