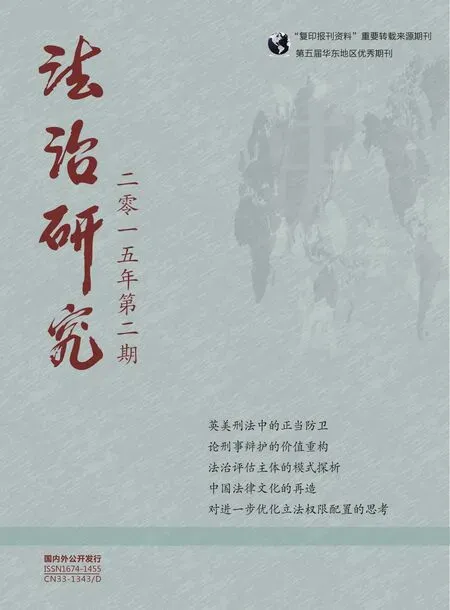單位累犯建構的前置性條件梳理*
陳 偉
單位主體與自然人主體具有較為顯著的內在差異性,體現在累犯構成上,單位累犯與自然人累犯也具有明顯的不同。在累犯已然進入刑法規范之下,除了自然人累犯,單位究竟能否作為累犯而成立呢?盡管現今學界對單位累犯擁有正反不同的見解,但是對單位累犯前提性條件的未達統一致使雙方自說自話,在學術研究時更是爭論不休、莫衷一是,因而兩種結論究竟孰是孰非并不明了。鑒于此現狀,筆者站在肯定說的立場上,擬對單位累犯成立的前置性條件予以系統審視,并將單位累犯中的關鍵性問題予以揭示,從而期許對現有單位累犯理論糾葛的化解有所助益,對未來刑事法律的完善有所借鑒。
一、問題的提出:單位能否構成累犯存在正反兩方的爭議
累犯制度主要規定在現有《刑法》第65條、第66條之中,其中,《刑法》第65條規定的是普通累犯,《刑法》第66條規定的是特殊累犯。無論是普通累犯還是特殊累犯,現有的相關規定都沒有界定累犯的主體。盡管《刑法修正案(八)》對《刑法》第65條、第66條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但是,對單位累犯的問題仍然只字未提,因而單位主體究竟能否納入到累犯之中予以評價,仍然是一懸而未決的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在《刑法修正案(八)》之中,對《刑法》第65條的主體確實有所涉及,即明確規定了“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的除外”,即在原有“過失犯罪的除外”的基礎上,又把未成年人主體也排斥在累犯之外。這一修改明顯是為了擴大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以貫徹“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刑事政策精神。但是,僅就現有的這一調整來看,并未涉及到累犯的單位主體問題。除此之外,《刑法》第66條特殊累犯也進行了相應調整,即在危害國家安全犯罪之外,又增加了“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大大拓展了特殊累犯成立的范圍,有對上述三類犯罪予以從重處罰和加大打擊力度的明顯意味。但是,與普通累犯相似的是,在特殊累犯中同樣沒有對單位能否構成累犯作出任何規定。
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形下,單位能否成立累犯的問題,學者對此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究與爭論,歸納起來主要存在正反兩方的爭議。
“肯定說”明確支持單位能夠構成累犯,理由主要有如下方面:
1.單位重復犯罪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和不斷完善,單位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與之相伴的是,單位犯罪也呈現較為嚴重的態勢,單位重復犯罪也并不少見,基于此現狀,認定單位累犯并從重處罰,方能與其危害行為與主觀惡性相一致。與之相反,如果有些單位不斷以身試法、挑戰法律界限,卻不能以累犯予以從重處罰,必將嚴重影響到法治建設與法律權威。
2.認定單位累犯是刑法適用人人平等原則的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是《刑法》總則第4條明確規定的,這里的“人人平等”既要求自然人犯罪之間的平等,也要求單位犯罪之間的平等,同時還要求自然人與單位之間的平等。既然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法治經濟強調的是公平正義,那么,對不斷重復犯罪的單位來說,就需要予以區別對待,適用更重的刑罰。這對完善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以及保障單位之間的公平競爭來說,都是可以接受的。
3.單位累犯與自然人累犯具有直接的對應性。之所以自然人累犯并沒有太多的爭議,源于自然人犯罪主體是一種基本性的認識,或者說我們對自然人犯罪主體從未像單位犯罪那樣產生過激烈爭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現有刑事法律規范中,既然單位犯罪已經被納入刑事法律體系之下,那么單位犯罪就具有與自然人一樣的主體資格。換言之,既然自然人可以適用累犯制度,那么為何單位就不可以成立累犯呢?
4.認定單位累犯符合刑罰的目的性追求。單位犯罪是單位整體意志的表現,在單位犯罪之后予以刑罰適用,同樣帶有目的性的追求。并且,累犯制度的存在是預防刑的典型表現,單位作為犯罪主體在執行原判刑罰之后,一定期限之內又實施性質嚴重的罪行,說明前期的刑罰沒有達到預期性目的,因而需要通過累犯制度的認定來從重處罰,達到刑罰目的的基本要求。
基于對單位累犯制度的肯定,有學者對我國現行累犯制度進行了立法創設,認為《刑法》第65條應當作如下補充:“被判處50萬以上罰金的犯罪單位,在刑罰執行完畢或免除后,在5年以內再犯應當判處50萬元以上罰金之罪的,是單位累犯,罰金從重,但是過失犯罪的除外。”“單位累犯的,予以解散。該款不適用于國家機關、人民團體。”①蘇彩霞:《累犯制度比較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頁。這一圍繞單位罰金刑所作的立法建議,就是基于單位累犯肯定說的立場之上,并且以單位罰金刑進行的重新安排。
與前面相對的是,“否定說”明確主張單位根本不能構成累犯。其包括的主要理由有如下方面:
1.單位與自然人具有不同的構造與屬性。原因在于,單位是一個動態化的運行體系,是由多元化的因素組合而成的,其組合要素的變動性是一客觀情形。質言之,單位與其背后的領導機構、執行機構、主管人員、直接責任人員須臾不可分離,在當今人事變動、組織調整較為頻繁的社會情形下,盡管此時單位表面上還是同一個主體,但是內在要素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此時以累犯論處,明顯不合適。
2.單位的雙罰制處罰后果不可能構成累犯。根據我國現有《刑法》第65條的規定,構成普通累犯的刑罰條件有明確限制,即必須要求前后兩罪均為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罰。而在我國的刑事責任體系中,單位的刑罰處罰是以“雙罰制為原則、單罰制為例外”。在單位犯罪較為普遍的是以雙罰制處罰的前提下,與現有刑法普通累犯的成立條件根本難以對接。盡管特殊累犯沒有規定刑罰程度,但是,在普通累犯被排斥在外的情形下,單位累犯單純局限于特殊累犯就非常有限。
3.單位主觀罪過與意志的特殊性決定了累犯成立的不可能。累犯從重處罰的根據并不在于外在的危害行為,因為如果單純就行為的危害性來說,其與其他人實施的危害行為并無二致。累犯從重處罰就是因為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大,并且具有較為嚴重的人身危險性。盡管單位已經作為犯罪主體被納入刑事法律體系之下,并且按照“無罪過則無犯罪”的適用原則,單位與自然人犯罪主體一樣都必須要有主觀罪過才能成立犯罪,但是,作為兩種完全不同的犯罪主體,單位與自然人的主觀罪過內容明顯不同。從根本上來說,單位罪過是單位整體性的體現,它是一種群體意識和整體意志,而自然人罪過則完全是個人意識和個人意志的體現。單位犯罪離不了自然人意志在其背后的支撐與控制,單位之下的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往往是代行單位作出決策與行為的主體,這與典型的自然人犯罪明顯不同。可以說,單位之下的自然人意識和意志的延展,并不是代表自然人本身并謀取個人利益,而是行使的單位權力及其意志,并為單位整體來謀取利益,因而單位犯罪是超個人意識和意志的一種集體表現。單位犯罪不應該套用自然人犯罪并適用累犯制度。
4.單位累犯違反了刑法的基本原則。有學者指出,“累犯只有一個犯罪行為,且已經按照相關規范予以定罪處罰,除此再無犯罪行為,因而在罪刑法定原則體系里,它是有刑罰而無犯罪行為的唯一一個例外,是無罪行之刑罰法定。大多數刑罰的給予,都是以刑法分則條款為依據,然后結合總則刑罰章節而確立,但累犯制度則幾乎與分則條文毫無關聯因而它與罪刑相適應原則也是不相容的。另外,它還與刑法適用一律平等、不溯及既往、禁止重復評價等原則也存在著結構性沖突”②熊建明:《基于刑法原則性體系視角之累犯透視》,載《法治研究》2012年第5期。。照此予以推論,如果累犯都是違反刑法基本原則的,那么累犯的自身危機就不可避免,累犯的合理性必然遭受質疑。那么,單位累犯的不成立也就順理成章。
二、單位累犯必須以單位成立犯罪為理論前提
在我國,單位刑事責任的肯定論與否定論之間的論辯曾進行了相當長的時間。隨著新刑法在立法上對單位犯罪的確立,否定論者最初的明顯優勢被肯定論者完全逆轉。然而,立法上的明確規定并不是正反兩方正式謝幕的完美注腳,盡管立法的規定對單位刑事責任的肯定順應了肯定論者的初衷,但是穿越規范層面的文字表述,否定論者對肯定論者的辯解仍然存在。
比如,趙秉志教授就直接指出,“中國刑法對法人犯罪的規定本身就是立法回應社會現實的倉促之舉,缺乏理論上深入的探討”③趙秉志:《外向刑法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頁。。其話語中無疑也透露出對單位犯罪立法的一種深深擔憂。另外,周振杰教授也指出,“宏觀數據與微觀案例都表明,我國當前的法人犯罪立法,因為地方政府的消極態度等因素,并沒有得到嚴格的執行,而日漸淪為空文,徒具象征意義。”④周振杰:《法人犯罪立法的批判性政治解讀》,載《法治研究》2013年第6期。很顯然,其是從司法適用上的弊端來反對單位犯罪的立法的。在此基礎上,如果投之于單位累犯之上,由于內在仍然不太贊同單位犯罪,那么,對單位累犯問題自然也就難以認同了。
因此,這種表面趨于平靜而實質沒有化解的矛盾沖突,投射于單位累犯問題上,就極有可能步入從前所經歷的爭論不休的歧途之中,重演“單位成立犯罪與否”正反論戰的歷史。⑤這種論戰對理論探討當然是有積極價值的,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了解單位及其犯罪問題。但是,無窮盡地抓住單位能否成立犯罪的問題不放,實際上又遮蔽了更多值得研究的問題,其弊端也是客觀存在的。換言之,對單位累犯成立與否的討論,很可能一不小心就步入了單位成立犯罪與否的窠臼之中,而無法對單位累犯的實質性問題有所突破。比如,關于單位的本質、單位的犯罪能力、單位負刑事責任的能力、超越單位合法目的范圍的行為、單位的刑罰主體、懲罰單位在刑事政策上的必要性等等,實質上都是對單位是否負刑事責任的討論。⑥何秉松:《法人犯罪與刑事責任》,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76~89頁。由此就引出一個前提,我們在討論單位累犯的時候還有沒有必要檢視單位犯罪成立與否這一帶有根本性的前置性問題?
對此,筆者認為大可不必。因為單位累犯是單位犯罪之后的累犯問題,而不是單位成立犯罪與否之后的累犯問題。如果不堅持這一界限的區分,我們在討論單位累犯時將仍然要受縛于單位犯罪的舊有思維,相關的理論研究只能是原地轉圈,從而無法在單位累犯問題上邁出實質性的步伐,無法結合累犯與單位的各自內涵予以實質性地考察。其中的道理也相當簡單,如果單位作為犯罪的問題都沒有得以前置性地解決,單位作為犯罪主體都未得以承認,在單位能否認定為犯罪尚未明晰的情形下,所謂的對單位判處刑罰就是一句空話,此時探討單位累犯當然也毫無意義可言。
就犯罪與刑罰的關系,從邏輯發生關系來說,犯罪在前、刑罰在后,這是自然的因果關系。有學者指出,“正因為犯罪與刑罰的對應與共存關系,使得傳統刑法將犯罪與刑罰視為共同體,即使在今天,我們在評價犯罪是‘惡’的同時,也承認刑罰是一種‘惡’”⑦黃偉明:《論刑罰本位立場之倡導》,載《法治研究》2013年第2期。。即使犯罪與刑罰有著所謂的共生關系,我們也不可能把犯罪與刑罰混為一談,更不可能用刑罰完全來取代犯罪。
何況,單從語義學角度來看,其結論同樣是肯定的。原因在于,“單位累犯”是“單位”成立犯罪之后的“累犯”,只有單位已經被認定為犯罪主體,才有必要進一步討論其刑罰懲處的現實問題。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全然否定單位不能成立犯罪,單位累犯自然不能成立,這是任何人都清楚的道理。反過來說,我們探討單位累犯不是重新探討單位犯罪成立與否的問題,而是在單位成立犯罪之后的累犯適用與否的問題。基于一般性的語言使用,“單位累犯”這一語詞所暗含的前提只能是單位犯罪的肯定論,即“單位累犯”重在單位之“累”,而不在單位之“犯”,單位之“累”必須在單位之“犯”的肯定結論之上予以規范性構建。
肯定單位能夠作為犯罪主體,就是要肯定單位能夠與自然人一樣具有犯罪主體資格,具有主觀罪過及其人身危險性。盡管兩者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些微差異,但是,由于單位與自然人主體本身就是兩個不同的主體類型,因而這些差異只是說明主體類型上的不同,而不能說明主觀惡性與人身危險性的完全不可比擬性,更不能說明自然人可以成立累犯,而單位就不能成立累犯。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強調單位成立犯罪中單位累犯探討的前提性條件,主要還是為了避免在理論上進行徒勞的重復性勞動,避免人為地把單位累犯的復雜問題簡化為已經論戰過的單位犯罪問題。⑧當然,也必須承認,學理上的單位犯罪之爭確實沒有因為單位入刑就銷聲匿跡。而且,學界人士也從來沒有將刑事法律的規定奉為圭臬,反對單位犯罪者仍然可以對此予以反思與批判。但是,就現有的司法適用來說,或者說對單位累犯的研究來說,如果沒有單位犯罪主體的平臺,“單位累犯”根本上就是一個偽命題,無任何探討之必要。這完全不是筆者的杞人憂天,從相關學者所持的否定單位累犯的理由來看,很多層面仍然是否定單位成立犯罪的理由,而不是直接針對單位累犯而言的。基于此考慮,單位累犯的探討不能重新步入單位是否構成犯罪的泥淖之中,而是必須在單位已然能夠成立犯罪的理論前提之下,在明確肯定現有刑法已經把單位納入犯罪主體的立法規定之中,予以重新審視與批判性研究。
三、單位累犯必須立足于單位主體的人格特性進行探討
在承認單位犯罪的理論預設下,接下來必須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單位主體有沒有人格特性?單位累犯成立的理論基礎何在?是單位重復性的行為還是單位具有人身危險性的人格特性?
人格的概念是一個歧義叢生的概念,不同的學者基于不同的視角得出了不同的認識。一般認為,人格是個體在行為上的內部傾向,它表現為個體適用環境時在能力、情緒、需要、動機、興趣、態度、價值觀、氣質、性格和體質等方面的整合,是具有動力一致性和連續性的自我,是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給人以特色的心身組織。⑨黃希庭:《人格心理學》,東華書局1998年版,第8頁。雖然學者們在對人格的內涵予以闡述時,并沒有對單位主體人格加以單獨描述,但是如果將上述人格的定義投之于單位主體身上,可以清楚地發現,除了人格的生物性特征之外(如情緒、氣質、體質特征),單位主體同樣具有“一致性和連續性的自我”,同樣可以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特色的有機組織體。單位“這個特定的社會系統,作為法律所確認的人,也像自然人一樣,具有獨立的人格,具有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它在社會生活中,以特定的社會關系主體的身份,并以自己的名義獨立地決定和處理它與周圍自然人或法人的相互關系,獨立地進行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行使自己的權利和履行自己的義務,以自己的名義在法院起訴和應訴,它甚至有自己的生命,可以出生和死亡”⑩同注⑥,第473頁。。由此可見,在日漸頻繁的經濟往來與社會關系交往中,單位主體的人格特性是一種客觀現實。不承認甚或否定單位的人格特性,就否定了單位從事對外經濟或相關事務的主體資格,否定了單位組織體可以靈活地進行民商事活動的現實性。
明確承認單位主體的人格特性,不僅是從“行為累犯”轉向“行為人累犯”的理論根據,而且是對累犯成立的正當性進行說明的理由所在。累犯最直接的表象在于行為的重復性和連續性,實質根據卻在于行為背后人格的動態發展,即我們通常所認為的“怙惡不悛、不知悔改”。不從行為人的人格角度展開累犯的全部理論論述,就無法說明累犯設立的必要性根源,更無法對累犯從重處罰的原因作出合理性解釋。因為如果嚴格按照行為人前后的行為予以社會危害性的衡量,其刑罰幅度就只能以行為所反映的社會危害性為標尺,或輕或重必須以此為中軸上下波動,“從重處罰”就不是當然之理。有臺灣學者明確指出,“因而對于累犯加重之理由,須考量到行為責任以外之理由”?許福生:《累犯加重之比較研究》,載《刑事法雜志》2003年第4期。。日本學者大塚仁教授也認為,“累犯之所以要接受特別處遇,乃是累犯因前刑而接受刑罰后,卻仍不知悔改反省復再犯,因而對其行為有較高的道德非難;以及因反復犯罪,所顯現其人格的特別危險性”?大塚仁:《刑法概說(總論)》,有斐閣1991年版,第741頁。。
因而,明確承認單位主體的人格特性不僅是單位主體成立犯罪的基礎,也是構建單位累犯必不可少的前提性條件,可以說,正是通過單位主體人格的動態或連續性關注,才由此構建了一幅單位主體人身危險性的全景圖,并以此為理由有對單位進行個別考察之可能,有對單位重復犯罪進行從重處罰之必要。?需要提出注意的是,單位主體究竟有無人身危險性,這是更深層次的問題,也是更直接觸及到單位累犯有無成立可能的更為核心的問題。在筆者看來,只要承認單位犯罪主體,并且認可單位犯罪具有主觀惡性,那么,在單位人格之下的人身危險性也是難以否定的,其規范性評價也是具有可行性的。
單位作為一個獨立的機構,原本不會存在所謂的人格性特征。但是,單位作為犯罪主體能夠客觀存在,并不是就其機構本身而言的,而是包含了單位及其單位組合要素的多元存在體。把單位上升到人格體的層面,才能真正建立起單位為何犯罪的原因追問,才能解讀單位為何能夠構成犯罪并適用刑罰的深層次問題。否則,如果單位僅僅只是一個空洞的機構,那么單位的罪刑關系根本無法建立,更不可能建立起動態對應關系。單位累犯作為自然人累犯的對應物,單位的人格性與自然人的人格性是兩者共同性的存在,這是我們在解構單位累犯并進行理論剖析時務必把握的核心所在。
四、單位累犯必須通過單位的整體性予以考量
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的區別就在于它的整體性,單位是作為一個有機的不可分割的整體進行相關的犯罪活動和承擔相關的刑事責任的。“單位作為一個社會系統,其首要特征是其整體性,在法律關系中,它以這種整體性出現。”?沙君俊:《單位犯罪的定罪與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頁。“單位是人格化的社會系統,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趙秉志:《單位犯罪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頁。單位累犯雖然是基于單位犯罪之上的,但是單位累犯的整體性顯然不是單位犯罪整體性的同義反復。也就是說,單位累犯的整體性有它獨特的內涵。
單位刑事責任的整體性,“即單位的刑事責任是單位整體的刑事責任,而不是單位內部各成員的刑事責任”?張明楷:《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頁。。“單位責任,應看成是自然人責任和組織體責任的復合。”?黎宏:《單位刑事責任論》,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頁。單位刑事責任的整體性,決定了原則上不僅要追究單位本身的刑事責任,還要追究單位直接責任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單位前犯與后犯的整體性是單位累犯外在客觀行為的說明,只有同一個單位實施了兩次以上的犯罪,才有構成單位累犯的可能,才符合單位累犯的形式要件。單位人格的整體性是單位累犯成立的實質性內容,帶有明顯的抽象性,并且其抽象性是通過單位具體的前后犯罪以及案外、案中情節予以征表說明的,人格的這種整體性其實也是圍繞前后犯罪行為的動態性描述出來的。單位與單位之下的機構、人員、設施、規章制度等的整體性,說明單位是一個有機體,這個有機體是一個系統或開放性的個體,并且通過單位整體性的歸納表述,我們可以知道,盡管單位內部的組成部分處于不斷的更換或流動之中,但是單位的整體性決定了單位有固守自我的本性,有自己的行為選擇方式與行為慣性,通過單位變動不居的表象我們仍然可以考察單位人身危險性的變動趨勢。對此,黎宏教授認為,“法人是具有遠在其組成人員的自然人的總和之上的影響力的復雜性(complexity)的社會組織體”?同注?,第324頁。。因此,在考察單位累犯時不能把單位主體與單位直接責任人員主體分而論之,也不能把單位主體簡單等同于單位之下自然人的機械相加。“如果只將單位本身作為單位犯罪的主體,而將單位的有關責任人員排除在單位犯罪的主體范圍外,將否定我國刑法學界提出的關于犯罪構成是刑事責任基礎或根據的理論學說,從而對單位犯罪中追究有關責任人的刑事責任喪失了理論根據。”?邱興隆、楊凱:《刑法總論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264頁。并且,這也將否定單位組成人員的行為與單位自身行為的關聯性。單位累犯前后動態性的人格一體性告訴我們,單位的整體性在單位累犯建構層面的關注不是更弱而是更強。
馮軍教授提出了單位犯罪的“規范雙重證明說”,其認為“新刑法規定單位犯罪,不是為了譴責單位,而是為了實現規范的雙重證明:首先是為了通過法律的外在強制來實現對單位人格同一性證明;其次是為了通過繳除單位代表人個體的善良行動根據來保障法規范牢不可破的效力”。?馮軍:《新刑法中的單位犯罪》,載趙秉志主編:《刑法論叢》(第9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頁。但是,他否定單位意志是單位的群眾意志或者集體意志,而把單位意志僅限為規范性意志的理論思路。筆者認為,其最大的缺陷在于,明顯把單位自身與單位之下的自然人割裂開來,很難圓滿地回答單位犯罪為何要通過單位之外的因素來自我證明這一問題。而且,這一“規范雙重證明說”也無法直接回答為何對單位累犯或再犯要多次證明——既然只是雙重證明而非譴責和懲罰,那么這一證明必需動用刑罰嗎?在單位累犯或再犯的情形下,是說明上一次證明失敗,還是說明這一理論根基的喪失?在筆者看來,雖然“規范雙重證明說”對單位主體人格的肯定是一條創新性的理論徑路,但是由于撇開了單位整體性這一前提,對上述問題無法自圓其說,因此這一“規范雙重證明說”仍存有進一步商榷之余地。
筆者認為,這一整體性包括四個方面:
其一,單位刑事責任的整體性。單位是作為獨立的機構而存在的,單獨就這一機構而言,如果沒有自然人的介入與操控,單位將因欠缺主觀意志的支配而缺乏主客觀相統一進行刑事歸責的必要,也根本不可能自行實施任何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對單位追究刑事責任,實際就是對單位這一機構及其機構之下的主管人員或者直接責任人員共同追究刑事責任。雖然單位犯罪并非是單位與自然人結合下的共同犯罪,但是基于單位刑事責任的特殊性,我們以“雙罰制為原則、單罰制為例外”對單位予以刑事歸責的刑罰適用原則,恰恰彰顯的就是單位刑事責任的整體性要求。
其二,單位前犯與單位后犯的整體性。在累犯考察的過程中,必然牽涉的就是單位主體前后實施犯罪的連續性,并在前后犯罪的聯系中進行累犯適用條件的一一對照。單位是單位機構與機構之下自然人的共同組合體,這一事實任何人都不否認。但是,在單位機構仍然存在的前提下,該機構之下的自然人要素卻在頻繁地發生變動,此時單位前犯與單位后犯是否仍為同一單位就成其為問題。如果認為此時的單位主體不同一,考察單位累犯就毫無意義可言,如果認為前后主體相一致,考察單位累犯才有現實可能性。由于此時是以單位作為犯罪主體予以評價的,單位自然是以單位這一機構而示外的,因此單位的機構性特征是其主要特征,基于此考慮,只要單位機構的特征未發生變化,單位前后的同一性就必須得以認可。
其三,單位與單位之下的人員、設施、規章制度等的整體性。單位作為機構本身是一個毫無內容的實體,單位能夠實施犯罪,必然是多元因素組合和促使下的結果。在單位整體性的視角之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單位與單位之下的人員、物理設施、規章制度、文化內涵等是須臾不可分離的。可以說,正是這些內外存在的組合元素,決定了單位自身的品格和外在行事方式,認識單位及其之下的這些因素,是我們在評判單位主體人格與犯罪成立時的重要內容,也是我們對單位進行刑罰與非刑罰處罰時獲得預期理想效果的重要層面。
其四,單位犯前、犯中、犯后情節顯露出來的單位主觀態度的整體性。單位實施前后罪的行為是一個連貫性的客觀存在,這是我們評判單位主觀惡性與人身危險性的基本線索。在把單位作為主體人格予以犯罪化之后,單位犯罪主體就不僅僅只有犯罪中的危害行為,對此,我們必須糾正思維定勢的認識誤區,把單位犯前、犯中、犯后的具體表現作為征表其主觀態度的晴雨表,進行整體性的考察與分析。我們對單位犯罪整體過程中的主觀惡性予以評判,既要確定單位是否存在人身危險性較大的客觀情形,又要在量刑時根據其人身危險性的量度大小作為刑罰裁量的根據。
五、結語
單位累犯的探討必須搭建共同的學術話語平臺,基于這樣的共識,無論是該問題的肯定論者還是否定論者,都可以回到問題源點上進行審慎反思。可以說,現有對單位累犯的理論探討,盡管理論爭鳴異常熱鬧,但是自說自話的學術紛爭不僅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反而由于混淆了思維的邏輯起點而把簡單問題復雜化了。重新厘定單位累犯建構的前置性條件,就是為了把單位累犯的探討引入到正確的路徑中來,以此肯定單位累犯成立的實質理由。筆者相信,單位累犯理論前提的廓清及其思維路徑的重新糾正,是立法者具體設置單位累犯相關條文的根據,是司法實務工作者正確適用法律與解決疑難案件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