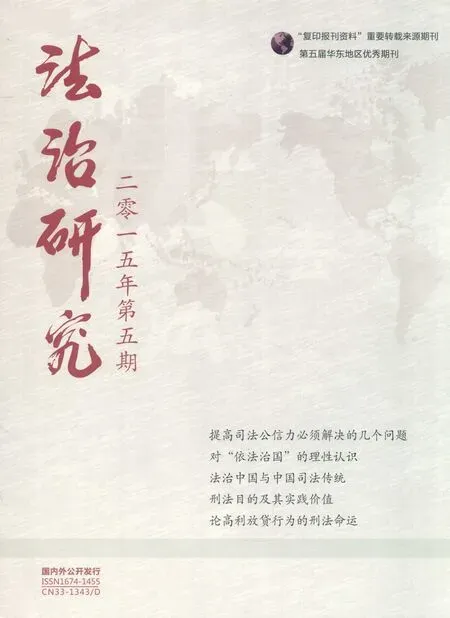故意犯罪前行為建構作為義務問題探究*
王光明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關于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的來源,危險前行為是繼法律、合同之后出現的第三種義務來源,雖然其在創建之始是為了填堵不作為犯的處罰漏洞,但今天卻發展為各國學界與實務界一致認可的一項基本義務來源,①詳見[德]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許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752頁;[意]杜里奧·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原理》,陳忠林譯,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頁;[日]大谷實:《刑法總論》,黎宏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頁。將危險前行為發展為作為義務發生根據的基本原理,在于禁止侵害他人法益的一般性要求。據此而來的誡命規范是:實施危險行為者,有義務消除自己造成的危險。②[德]崗特·施特拉滕維特、洛塔爾·庫倫:《刑法總論Ⅰ——犯罪論》,楊萌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66頁。具體來說,就是因自己行為而對他人法益造成危險者,負有再以自己行為來排除該危險以避免結果發生的義務。
單從邏輯上說,構成作為義務來源的危險前行為既包括合法前行為、違法前行為、過失犯罪前行為,又包括故意犯罪前行為。前三種危險前行為雖然在構成作為義務來源的具體問題上還存在爭議,但在能否成為作為義務的來源這一前提問題上,基本上達成了共識,即,都能成為作為義務的來源。就第四種危險前行為而言,在故意犯罪前行為與后階段的不作為侵害了不同法益時,比如在行為人故意非法采伐珍貴樹木時,樹木倒下時砸著他人的頭部,致使被害人血流不止,如果不及時救助就會導致他人死亡的場合,主流觀點普遍肯定故意犯罪前行為能夠成為后階段不作為的作為義務的來源。③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趙秉志:《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來源應采四來源說——解析不作為犯罪的作為義務之爭》,載《檢察日報》2005年5月20日。但在故意犯罪前行為與后階段的不作為侵害的是同一法益,或者兩個行為所侵害的法益具有包容關系時,比如行為人甲在施工作業中基于殺人故意將乙撞成重傷,傷勢本不會立即致命,但甲任由乙流血不止終致死亡,從而實現其殺人計劃的場合,故意犯罪前行為能否成為后階段不作為的作為義務的來源,刑法學界存在激烈的理論爭議。對此,當前有力的觀點認為,故意犯罪前行為不能成為后階段不作為的作為義務來源,其核心依據為:該種場合下,探討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來源問題,從實踐上來看,缺乏討論的實益,從理論上說,故意的犯罪前行為已經能夠完整充分地評價整個犯罪的過程及不法內涵,后階段的不作為完全沒有獨立評價的意義。承認這種作為義務不啻于先制造問題再解決問題,完全是多此一舉。④許玉秀:《主觀與客觀之間》,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295頁。另外,還有學者以期待可能性原理、重復評價禁止原則與犯罪中止理論為視角,否定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⑤參見蔡墩銘:《刑法總則爭議問題研究》,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0頁;齊文遠、李曉龍:《論不作為犯中的先行行為》,載《法律科學》1999年第5期;[德]許乃曼:《德國不作為犯學理的現況》,陳志輝譯,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13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85頁。與上述否定觀點不同的是,我國通說觀點雖然在此問題上沒有給予深入的論證,但從結論上是持肯定立場的。⑥參見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69頁。值得一提的是,我國著名刑法學者張明楷教授原本在此問題上持否定立場,但最近在對故意犯罪前行為建構作為義務所具有的實益進行現實考量后,轉而支持了通說的立場。⑦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張明楷:《不作為犯中的先前行為》,載《法學研究》2011年第6期。
綜上,在故意犯罪前行為與后階段的不作為侵害同一法益,或者兩個行為所侵害的法益具有包容關系的場合,應否承認故意犯罪前行為成為后階段不作為的作為義務的來源,當前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對此,本文認為應當將故意犯罪前行為建構為后階段不作為的作為義務的來源,如此不僅有助于解決刑法中的一些現實問題,而且具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另外,將故意犯罪前行為建構為后階段不作為的作為義務的來源,并不會出現否定論者所言的違背期待可能性原理、與重復評價禁止原則相沖突、與犯罪中止理論相矛盾等諸多問題。基于論述的便利,本文僅就故意犯罪前行為與后階段的不作為侵害同一法益(同一被害人之同一法益)為例展開討論。
一、故意犯罪前行為建構作為義務的實益分析
(一)有助于妥當地處理共犯問題
一如前述,在故意犯罪前行為與后階段的不作為侵害同一法益的場合,否定論者對之進行否定的一個很重要的理據是認為該種場合承認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缺乏現實的意義。果真如此嗎?請看案例1:甲在施工作業中基于殺人故意將乙撞成重傷,傷勢本不會立即致命,甲看見乙血流不止突然心生悔意,欲施行有效救助。但此時與此無關的第三者丙極力勸阻甲,促使其放棄救助念頭,乙終因失血過多而死亡。⑧蔡圣偉:《論故意不法前行為所建構的保證人義務》,載《東吳法律學報》第18卷第2期。本案中,如果甲在實施了作為行為之后對乙進行有效救助,則乙會幸免于難,而丙的勸阻卻使甲放棄了對乙的救助,進而導致了乙的死亡,由此可見丙的勸阻行為對乙的死亡是“功不可沒”的。若在此種情形下不賦予甲積極救助的義務,根據我國通行的刑法理論,首先,丙的行為難以單獨被評價為犯罪,因為其既沒有實施導致乙生命危險的積極行為,也不具有在乙生命危險狀態下的積極救助義務;其次,丙也不會與甲成立共犯而被追責,因為在甲實施致乙生命危險的作為行為之時,兩者既無共同犯罪的行為,也無共同犯罪的故意。如此歸結使得被害人的利益無法得到有效的保護,無論如何難言妥當。若在此情形下賦予甲積極救助的義務,丙極力勸阻促使甲放棄救助念頭的行為就是甲不作為故意殺人罪的教唆犯,其與甲構成不作為故意殺人罪的共犯。由此看來,肯定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雖然對甲自身行為的定罪量刑并無多大影響,但是對于丙行為的規范評價、妥當地處理共犯問題以及法益保護方面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而不是像否定論者所言的毫無現實意義。
(二)有助于合理地認定犯罪行為
是否承認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還關乎對行為人本人行為性質的規范評價,比如案例2:甲14周歲的當天在某商廈安裝定時炸彈,炸彈設定于第二天中午12:00時爆炸,后來炸彈果真在第二天中午的12:00爆炸,造成人員及財產的重大損害。在本案中,若不承認故意犯罪前行為(根據我國通行的犯罪構成理論,此處的故意犯罪前行為應為故意不法前行為,而非故意犯罪前行為。但是,即使在我國通行的犯罪構成理論中,如果承認犯罪概念的相對性,那符合犯罪構成客觀要件的行為也是“犯罪”;⑨參見黎宏:《刑法總論問題思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頁。同時認為,責任能力不是責任的前提,而是責任的要素,那么,認為上述案例中的故意不法前行為是故意犯罪前行為,亦并無不妥)所建構的作為義務,則只能就甲的故意作為行為予以法律評價,而此時甲由于并不具有責任能力而無法對其予以非難與譴責,因而最終只能認定甲的行為不成立犯罪,該種理論歸結顯然不利于法益的保護。相反,若肯定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雖然無法就甲的故意作為行為予以否定評價與譴責(此時由于甲不滿14周歲不具有責任能力),但對甲后階段的不作為是可以予以否定評價與譴責的(從次日的零點開始其已滿14周歲,具有責任能力),最終,可將甲的行為評價為不作為的故意犯罪,并在此范圍內承擔刑事責任。因此,肯定故意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不僅可以更合理地評價行為人的行為,而且亦能更有效地保護法益。
(三)有助于準確地把握正當防衛的構成
是否承認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還關乎針對故意犯罪前行為而實施的正當防衛的構成。比如案例3:金庸《射雕英雄傳》第十一回“長春服輸”中講到,丹陽真人馬鈺中被彭連虎獨門利器毒針環所傷。丘處機見師兄中毒甚深,非他獨門解藥相救不可,喝道:“管你千手萬手,不留下解藥,休得脫身。”運劍如虹,一道青光向彭連虎刺去。本案所關涉的問題是,在行為人完成了他的攻擊行為但法益仍可挽回時,被害人或者第三者能否主張正當防衛?我國刑法理論通說觀點認為,此時不法侵害所引起的危險狀態仍在持續中,或者說不法侵害即故意犯罪前行為尚未結束,故而當然能夠主張正當防衛。但若細分析則會發現,雖然此時行為人所造成的不法狀態仍在持續,但行為人的行為畢竟已經實施完畢,此時若要通過防衛行為避免法益侵害的發生,防衛行為是無法作用于行為人已經實施完畢的行為進而避免法益侵害的。所以德國才會有學者主張,若要能針對此一危險狀態行使正當防衛,進而避免不法侵害的發生,就必須先賦予作為的行為人排除此一危險狀態的法律義務,之后才可以針對他的不作為主張防衛來避免法益侵害的發生。⑩Stein,JR 1999,S.268。轉引自注⑧。據此也就明晰,在此種情形下,作為不法侵害的故意犯罪前行為已經結束,而我國刑法理論是通過將之視為尚未結束而賦予公民防衛權,從而獲得作為結果的合理性,但這種做法使防衛權所作用的不法侵害行為發生了錯位。誠如德國學者所言,如果我們由果推因,公民享有防衛權的基礎應該是故意犯罪行為人在此一危險狀態下負有排除危險的義務,因其未履行積極排除危險的義務而存在一個不作為的不法侵害,防衛權系針對不作為不法侵害而實施。所以,肯定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可以為準確把握正當防衛行為的構成提供合理的依據。
(四)有助于合理地裁量刑罰
承認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不僅有助于合理地認定相關行為的法律性質,而且有助于合理地裁量刑罰。例如案例4:被害人因患有肺癌身體痛苦萬分,于是苦苦哀求鄰人為其注射致命藥物。但被害人在鄰人注射藥物后心生悔意,又苦苦哀求鄰人將其送醫急救,但鄰人因恐受刑事追究而拒絕送醫,致使被害人死亡。在本案例中,行為人積極的作為殺人是基于得被害人的承諾,而被害人承諾是影響刑事責任輕重的情節,應依法從輕或減輕處罰。但問題在于,案例中的行為人雖基于他人承諾而積極作為殺人,但在被害人陷入危險狀態后卻撤銷了承諾,此時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均已消失。在此種情形下,若否定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則意味著雖然能夠對行為人論以作為殺人,但卻必須要對其予以從輕或減輕處罰,但這樣的結論無視被害人的反悔,不僅導致對行為人整體罪行評價的不完整,對行為人的從寬處罰亦導致對被害人的不公正對待。
誠然,在行為人故意犯罪前行為導致被害人法益處于危險狀態后,行為人未予積極作為從而避免結果發生的行為在大多情形下不會導致定罪量刑上的不合理,但上述例外情形確實也揭示出了反對見解者的不妥。因此,只有肯定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進而認定后續的不作為也成立犯罪,才可以更為精確地對行為進行定性,并在此基礎上對行為人的行為給予更合理地刑罰裁量。
二、故意犯罪前行為建構作為義務的法理基礎
肯定故意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不僅具有上述諸多實益,而且存在堅實的理論支撐。
(一)“舉輕以明重”的法理
肯定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符合“舉輕以明重”當然解釋的法理。當然解釋,即依據事物當然之理所作的解釋,它是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依據形式邏輯、規范目的及事物屬性的當然之理而進行的解釋。唐律有言:“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舉輕以明重”即為當然解釋。據此,在進行出罪解釋時,應秉承“舉重以明輕”的法理,在進行入罪解釋時,應秉承“舉輕以明重”的法理。肯定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進而認為因果流程的后半段成立不作為犯即屬于入罪解釋,應以“舉輕以明重”作為解釋的法理。一如前述,學說上一致認為危險前行為可以為過失犯罪前行為,而故意與過失之間并非對立關系,而是一種階段關系或位階關系,從其不法內涵來看,故意的不法內涵要比過失的不法內涵更為嚴重。?張明楷:《犯罪構成體系與構成要件要素》,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頁以下。根據“舉輕以明重”的法理,既然過失犯罪行為能使行為人具有作為義務,故意犯罪行為就更能使行為人具有作為義務,這是根據當然解釋所得出的邏輯結論。如果換個角度,我們一方面承認過失犯罪前行為可以作為義務來源,而另一方面又否定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必然會得出荒謬的結論來,這點通過比較下面兩個案例就可以看得很明白。案例5:甲在施工作業中過失將乙撞成重傷,傷勢本不會立即致命,甲正欲救助,發現乙竟是自己尋找已久的仇家,遂放棄救助,有意致其死亡。案例6:甲在施工作業中基于殺人故意將乙撞成重傷,傷勢本不會立即致命,但甲任由乙流血不止終致死亡,從而實現其殺人的計劃。案例5中,行為的組合結構為過失犯罪前行為+故意不救助,案例6中,行為的組合結構為故意犯罪前行為+故意不救助。通過對兩者行為組合結構的比較可知,案例6中的不法內涵要高于案例5中的不法內涵。如果認為過失犯罪前行為可以作為義務發生的根據,則案例5中的行為人不僅成立過失致人重傷罪,還會另外成立故意殺人罪;如果認為故意犯罪前行為不可以作為義務發生的根據,則案例6中的行為人就只能成立一個故意殺人罪。這樣就讓不法內涵低的行為人陷入了更為不利的情形,受到了更重的制裁,而不法內涵高的得到的是較輕的處罰。于是,一個違背事理的評價上的矛盾便產生了,評價上的矛盾說明邏輯推理的混亂,而混亂之處就在于對“舉輕以明重”這一當然解釋的背反。
(二)行為規范效力的法理
刑法規范既是裁判規范又是行為規范。作為行為規范,刑法通過將一定的行為規定為犯罪并給予刑罰處罰,從而向人們宣示該行為是被法律所禁止的;同時命令人們作出不實施這種犯罪行為的決定,從而防止犯罪的發生。也就是說,刑法規范是透過行為規范的宣示以及制裁規范的配合來達成法益保護使命的。接下來的問題是,刑法規范作為行為規范保護法益的效力是在法益被侵害(造成實害)之前一直存在?還是在行為人違反規范之后就終止了?答案應該是前者,因為被害人的法益應在受到侵害之前一直得到尊重。行為規范保護法益的效力是一種客觀存在,其產生于刑法規范的創設之始,終止于法益受到實在的侵害,在此期間,行為規范的效力不會因行為人的意愿而改變,亦不會因為行為不法內涵的輕重而有別,而是會一直持續存在,直至侵害終了。所以,在行為人沒有遵守規范的情況下,立法者是不會放棄透過行為規范的效力以保護法益的可能性的,立法者會將積極作為的義務賦予行為人,會清楚無誤地向其宣示:其不僅負有放棄繼續行為的義務(因為繼續行為將會提高被害人的法益受害危險),而且負有積極排除已招致危險的義務。?Stein,JR 1999,S.270。轉引自注⑧。此等義務的導出,來源于對行為規范效力的堅守。一如野村稔教授所正確指出的那般:當沒有發生生命危險的場合,發揮作為禁止規范的機能,回避作出侵害生命的行為,對行為人科以犯罪回避義務(不作為義務)。當叛離這種期待,而實施了犯罪行為時,在實行行為尚未終了的場合,作為次善之策,科以犯罪中止義務,以期待行為人放棄犯罪的繼續進行。進而,當出現了如果放置不理就會發生生命受到侵害的結果這樣的危險狀態時,作為命令規范,科以(根據先行行為)結果防止義務,以命令防止實際侵害的發生。?[日]野村稔:《刑法總論》,全理其、何力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頁。綜上,行為規范效力的堅守亦為肯定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提供了有力的理論基礎。
三、故意犯罪前行為建構作為義務招致的質疑及其反駁
綜上,將故意犯罪前行為建構為作為義務的來源不僅具有諸多實益,而且存在堅實的理論支撐,盡管如此,其仍然受到了一些否定論者的質疑,但在本文看來,否定論者的質疑都經不起推敲,也難言妥當,下面對否定論者的質疑觀點進行歸納,并逐一予以反駁。
(一)質疑與反駁之一——是否不符合期待可能性的原理
1.質疑。蔡墩銘教授反對將故意犯罪前行為建構為作為義務發生的根據,其理由在于:在行為人故意實施犯罪的場合,“行為人對于自己行為所發生之結果并無防止其發生之義務,毋寧其樂于見到結果之發生,更不應該令其負防止結果發生之義務”。?蔡墩銘:《刑法總則爭議問題研究》,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0頁。黃榮堅教授則更加直截了當地指出:“因為行為人原本便是著手于實現其心中的殺人目的,換成任何其他人處于相同的情境下,都不可能在砍殺對方后還會為救助的行為,所以難以期待行為人會有防止結果發生的行為,而必須將這種情況下的不作為看做是刑法所必須接受的宿命。”?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775~776頁。可以看出,兩位教授均是從期待可能性的角度否定故意犯罪前行為作為義務的建構,認為賦予故意犯罪的行為人以作為義務是對人這一本具軟弱人性的主體者提出了超越人性的要求。
2.反駁。但在本文看來,蔡墩銘教授以“樂于見到結果發生”為由免除作為義務的觀點并不可取。因為不僅故意作為犯的行為人可能會“樂于見到結果發生”,故意不作為犯的行為人多半也是會“樂于見到結果發生”的,如果將蔡墩銘教授的觀點貫徹下去,則所有的故意不作為犯均會因為“樂于見到結果發生”而不具有作為義務,進而不能成立犯罪,但這并不合適。理由在于:一如前述,首先,行為規范的創設以及規范的效力本來就與行為人遵守的意愿無關,行為人是否愿意遵守行為規范,行為人是否樂于見到結果的發生這些主觀愿望并不能廢除行為規范的客觀效力;其次,如果立法者想要透過行為規范來維護社會的存續,就更應該在某行為規范未被遵循時堅守該行為規范的效力,亦即透過防果義務的賦予來宣示被抵觸的行為規范一如既往的有效。因此,德國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故意作為之行為人希望犯罪既遂的愿望,并不能算是一種會導致期待作為可能性欠缺的強制;在行為人著手于作為犯的實行前,法規范期待行為人放棄他的犯罪意念,沒有理由只因為行為人已經踏上了犯罪的道路,便使得法規范不能(應)再期待行為人放棄他的犯罪意念。?Herzberg,Die Unterlassung im Strafrecht,1972,S.285。轉引注⑧。所以,以不符合期待可能性為由否定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是欠缺說服力的。
(二)質疑與反駁之二——是否違背禁止重復評價的原則
1.質疑。否定論者認為,承認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將會導致對犯罪既遂所要求的危害結果與犯罪因果流程的后半段進行重復性的評價。因為在此情形下,不僅會將其前行為評價為犯罪的既遂,接著還會對后續的因果流程后半段再作一次否定性的評價,進而認為另外成立一個獨立的不作為犯罪的既遂。那么,對既遂結果與因果流程后半段的兩次評價顯然違背了刑法禁止重復評價的原則。?齊文遠、李曉龍:《論不作為犯中的先行行為》,載《法律科學》1999年第5期;許玉秀:《前行為保證人類型的生存權?——與結果加重犯的比較》,載《主觀與客觀之間》,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303頁。
2.反駁。否定論者以違背禁止重復評價為由否定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著力點無疑在于行為人權益的保障,因為重復評價不僅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還會導致行為人對刑事責任的過度負擔。本文對此亦深表贊同。但應當注意的是,刑法評價不僅應注重對行為人權益的保障,還應體現對被害人權益的充分保護,否則其同樣會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而被刑法所禁止。特別是在一行為侵害數法益或者數行為侵害一法益的情況下,?在一行為侵害一法益或者數行為侵害數法益時,對之的一次評價或者數次評價均不涉及重復評價問題。必須要對每一個被侵害的法益或者每一個侵害法益的行為進行評價,否則就無法全面揭示行為對被害人法益的侵害性或者侵害被害人法益的行為性質,這是完全評價的要求。禁止重復評價和完全評價之于刑法評價,黃榮堅教授有精辟見解:“雙重評價之禁止,是評價行為的上限。完全評價原則,是評價行為的下限。二者觀察的角度不一樣,但其背后的原理則屬相同,都是在尋求一個適度的犯罪宣告及刑罰。”?黃榮堅:《刑罰問題與利益思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頁。換句話說,為了不損害被害人的利益,我們應堅守完全評價這一下限,為了不損害行為人的利益,我們應堅守重復評價之禁止這一上限。對兩者應該予以統籌兼顧,不可偏廢,否則都將導致評價的不公。
在一行為侵害數法益或者數行為侵害一法益的情形下,為了保證評價的完全性,評價過程中,對數法益所對應之一行為或者數行為所對應之一法益的重復評價將不可避免,?一行為侵害數法益時,必須要對每一個被侵害的法益進行評價,故不可避免地要對同一行為進行重復評價;在數行為侵害一法益時,必須要對每一個行為進行評價,表明行為人所實施的每一個行為都是不對的,故不可避免地要對同一法益進行重復評價。否則就等于法律默認其他未作評價的情形為合法,從而有違刑法中的完全評價原則。那么其是否違反了禁止重復評價的原則?本文對此持否定觀點。理由是:重復評價之所以要禁止,原因在于其會造成行為人對刑事責任的過度負擔。顯見的是,能夠侵犯行為人權益的雙重評價是作為判決結果的雙重評價,如果僅有過程中的雙重評價而無作為結果的雙重評價,是不會導致行為人對刑事責任的過度承擔的。也就是說,重復評價之禁止原則禁止的是作為結果的重復評價,其并不反對過程中的重復評價。這一點也為我國確定罪數的犯罪構成理論所認可,一行為侵害數法益或者數行為侵害一法益,由于其只有一個行為或者只侵害了一個法益,故只能符合一罪的犯罪構成,最終只能對其以一罪論處。
肯定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在故意犯罪前行為與后段的不作為所侵害的法益為同一的情形下,即屬于數行為侵害一法益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雖然行為人所侵害的是同一法益,但是法律對于行為人卻是先后各有期待,是一次又一次地期待行為人選擇合法行為而放棄違法行為,但行為人卻一次又一次地違背法律的期待。若對行為人實施行為的過程不允許重復評價,那無異于意味著行為人在實施了第一次侵害法益的行為之后,就取得了重復侵害該法益的權利,也就無異于鼓勵行為人為惡勿盡!因此,應肯定行為人實施了數個侵害法益的行為。從評價行為的目的看,如果侵害行為是數行為,雖然所侵害的只是一個法益(同一被害人之同一法益),對于數行為,并不禁止雙重評價,相反的,應該要雙重評價。?同注?,第211頁。當然,盡管行為人實施了數行為,畢竟其最終侵犯的只是同一法益,從保障行為人利益的角度,最終在論罪上只能以一罪論處。
綜上,肯定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雖在評價過程中會導致重復性評價,但卻不會導致結局上作為結果的重復性評價,故其并不違反重復評價禁止之原則。相反,若否定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在某些情況下卻會產生評價不完全的問題,如前述案例1、2、3中的情形。所以,為了論罪與處罰的公正性與完整性,當以完全評價為下限,而那些為了保障評價的完全性而導致的過程中的重復評價不僅不應被禁止,反而應當予以充分地肯定。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論罪與處罰的公正性。由此反觀否定論者的觀點,其不僅將評價過程中的重復評價與作為結果的重復評價混為一談,而且完全忽視了完全評價這一下限,并以此作為反對故意犯罪前行為建構作為義務的理由,恐怕難以令人信服。
(三)質疑與反駁之三——是否與犯罪中止相矛盾
1.質疑。否定論者認為,如果肯定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那么:第一,若行為人能為有效中止且為有效中止,則其中止行為僅僅是在履行法律所賦予的作為義務,自然也就不再是“出于己意”,也就不再具備犯罪中止“自動性”這一條件,故難以被認定為犯罪中止。第二,在前行為之后既遂結果之前這段時間內,若行為人能為有效中止但未為有效中止,則其不僅成立前行為的既遂犯,還會另成立一個獨立的不作為犯罪;若行為人能為有效中止且為有效中止,則中止行為僅僅是作為義務的履行,僅僅是阻卻不作為犯構成要件的實現,既然僅為履行義務,自然對其中止行為再無減免處罰的理由。故結論是,對為有效中止者不可以減免處罰,對未為有效中止者要加重處罰。但這樣的結論矛盾于現代各國關于犯罪中止的理論與立法規定。?上述觀點整理自[德]許乃曼:《德國不作為犯學理的現況》,陳志輝譯,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13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85頁;許玉秀:《前行為保證人類型的生存權?——與結果加重犯的比較》,載《主觀與客觀之間》,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303頁;李金明:《不真正不作為犯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反駁。
(1)肯定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并沒有否定中止的自動性。若依否定論者“履行義務=否定自動性”的邏輯,將會推導出所有的不作為犯都無法成立犯罪中止的結論。因為不作為犯就是行為人負有作為義務但又未履行作為義務,而且作為的義務將會持續整個犯罪過程直至既遂,若行為人在犯罪過程中為有效中止行為,則中止行為同樣不過是履行義務而已,既然是履行義務,就不再是出于己意,當然也不會成立犯罪中止。但,從來沒有人因此而主張不作為的行為人所為的中止行為絕對不可能是出于己意。?林山田:《刑法通論(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頁;林鈺雄:《新刑法總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 527~528頁。否定論者將“建構作為義務=否定自動性”的推理是有問題的,問題就在于其將中止的自動性不僅理解為必須是出于己意,而且“己意”必須是在沒有壓力(意志以外因素存在)的情況下形成才可以。但中止的自動性不等于中止的倫理性,大多中止行為都是在壓力之下作出的。只要行為人在為中止行為時,仍有為與不為選擇的可能性,而后出于自己的意志選擇了不為,都不可以否定其中止的自動性。作為義務的賦予,確實對行為人造成了一定的壓力,但壓力的量遠未達到抑制其意志的程度,故難以否定其中止的自動性。
(2)肯定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既沒有否定犯罪中止,也沒有加重對行為人的處罰。否定論者反對的聲音里還表達了這樣一層含義,即,既然將故意犯罪前行為建構為作為義務,而履行義務的行為就難以再作為獲得寬宥與獎勵的理由,所以犯罪中止的成立也就不再可能。但果真如此嗎?在肯定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的前提下,故意犯罪前行為、后階段的不作為與行為人中止行為之間的關系表現為以下兩種情況:第一,行為人“為有效中止行為”,該種場合中,鑒于中止行為不僅阻卻了故意犯罪前行為的既遂,而且亦未實現不作為犯的構成要件,因此,行為人的中止行為成立犯罪中止,同時適用中止犯減免處罰的規定。該種情形下,既沒有否定犯罪中止的成立,也沒有加重對行為人的處罰。第二,行為人“未為有效中止行為”,該種場合中,鑒于行為人雖為中止行為,但畢竟未能有效避免損害結果的發生,不符合犯罪中止的成立條件,當然亦不能適用中止犯減輕或免除處罰的規定。故在定罪與量刑時,對其要么以犯罪前行為的既遂追究責任,要么以“未為有效中止”的不作為既遂追究責任。最終究竟應以哪種情形定罪處罰,取決于評價的完全性和處罰的公正性。盡管如此,我們仍需注意到,行為人未為有效中止的行為,雖然不符合犯罪中止的成立,對其不能按照中止犯的規定予以減輕或免除處罰,但也不能無視行為人對保護法益所付出的積極努力,對此應作為酌定從寬量刑情節來考慮,最終亦無加重處罰問題。所以,在肯定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的前提下,在關涉行為人的故意犯罪前行為、后階段的不作為與行為人的中止行為之間的關系的處理上,既沒有否定犯罪中止的成立,也沒有加重對行為人的處罰,換言之,肯定故意犯罪前行為所建構的作為義務與犯罪中止并不存在矛盾關系。因此,否定論者以此為由的質疑同樣不具有說服力。